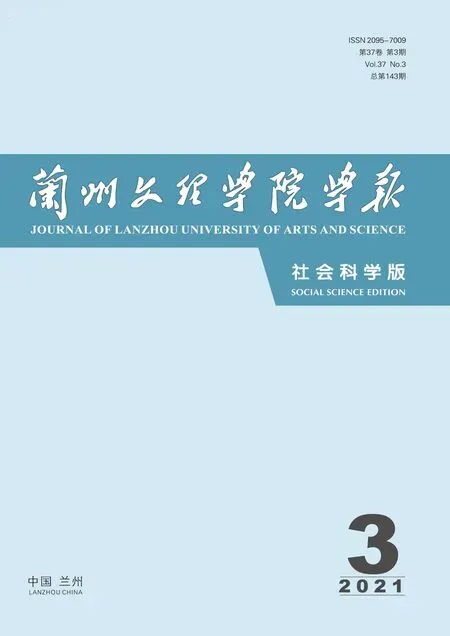白马藏族非遗“池哥昼”成分稽古与发展史钩沉
包 建 强,张 金 生
(1.兰州城市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甘肃陇南市政协,甘肃 陇南 746000)
白马藏族居住在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和甘肃省文县相交界的高山峻岭地带。自古以来,白马藏区是“连接南、北丝绸之路和海、陆丝绸之路的要冲”,“成为历史上诸政治势力角逐的焦点和民族迁徙的走廊”[1]。各民族在此交往、交流、交融,孕育出白马藏族的特色文化“池哥昼”。“池哥昼”依靠口传身授流传,至今存活于白马藏族民间。由于流传年代久远,表演者也不清楚表演动作表达何意,他们只是秉承祖传的跳法。由于文献阙如,“池哥昼”诞生的具体时间很难判定。但“池哥昼”仪式融会了众多的文化成分,各文化成分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载负着时代文化特征。虽然历经了漫长的发展历史,承受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雕饰,但“池哥昼”的宗教属性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其古老成分诞生之初的特征。通过考察、辨析诸成分的文化特征,可探究“池哥昼”古老的发展轮廓,明确它在每个历史时期发生的新变。
一、拟兽舞
拟兽舞是白马藏族“池哥昼”的重要成分之一。无论是内容还是表演形式,“池哥昼”的拟兽舞都呈现出非常古老的形态。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对比“池哥昼”的拟兽舞与我国各地发现的古岩画便可获得。我国各地发现的岩画被学术界区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并整理成许多成果①。根据我国古老的岩画记载,早在新石器至青铜器时期,先民们往往在狩猎之前或狩猎之后举行盛大的祭祀场面,祭祀中用拟兽舞实施模拟巫术,企图通过模拟巫术操控野兽灵魂以达到预期目的。另外,早期部落联盟首领举行礼乐典礼时也用拟兽舞。《尚书·舜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2]《史记》亦载:“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3]在唐尧虞舜时期,参与礼乐仪典的拟兽舞属于图腾崇拜与祭祀行为。彼时各部族均有自己的图腾物,在祭祀典礼中装扮为本部族的图腾物,形成“百兽率舞”“鸟兽翔舞”的盛大场面。
随着文化发展,后来拟兽表演被用于世俗娱乐。《路史·后纪》载:“(夏桀)广优猱戏奇伟,作《东歌》而操《北里》,大合桑林,骄溢妄行,于是群臣相持而唱于庭。”[4]243~244又据《礼记》记载,魏文候与子夏讨论俗乐与雅乐时提到拟兽表演:“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5]“猱”是猴科动物,身体轻捷善攀援。“猱戏”是模拟猴子的滑稽戏表演。从文献记载可看出,自夏朝至春秋时期,用于礼乐典礼的拟兽舞被世俗娱乐所采用,与优戏相并列。孟郊的《弦歌行》这样描述:“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唯齿白。暗中崒崒拽茅鞭,裸足朱裈行戚戚。相顾笑声冲庭燎,桃弧射矢时独叫。”[6]孟诗给我们提供了些许信息:拟猴在唐代已用于民间驱傩祭祀,拟猴者装扮成角色承担驱傩任务;拟猴者从动作与语言两方面务求滑稽与戏谑;为增强驱傩仪式的神秘气氛与恐怖性、更好地震慑鬼疫,扮猴者采用黑魔涂面的脸部化妆方式,成为截止目前发现最早的拟猴脸谱记载。
“池哥昼”傩戏含有多种拟兽舞表演。这些拟兽表演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完整表演,形成一种剧目或一出折子戏,如《麻昼》《秋昼》《阿里改昼》《帕贵塞》等;一是模拟动物的动作,组成“池哥昼”仪式的驱傩舞步。
《麻昼》是一出模拟数种动物的舞剧,共十二大套七十二小路,首套为拜山神舞,其余十一套分别模拟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猪、狗等动物,俨然是《尚书》所载“百兽率舞”的现代版流传。白马藏语“秋”即为“凤凰”,“昼”是“舞蹈”,顾名思义,《秋昼》是一出模拟凤凰的舞剧。但现在流传的《秋昼》变为两位或四位“池哥”两两角逐的舞剧,情节主要由“池哥”面对面弓步跳、肩比肩对抗、背靠背拖动等环节组成,显然是一出武士对抗的舞剧。表演风格刚健有力、原始古朴,具有秦汉角抵戏的面貌和风格。《秋昼》名、实不相符表明,原本模拟凤凰的舞剧,历经漫长的流传过程,表演动作逐渐散佚,仅遗留下一个空名;而另外一出歌颂民族英雄、张扬勇武精神的舞剧在流传过程中佚失剧名而保存了表演动作,于是在二者间发生了李代桃僵的现象。虽然《秋昼》原来的舞蹈动作失传,但其剧名标识的模拟凤凰的内容指向性未变。可看出,舞剧《秋昼》的原内容与《史记》所载“凤皇来仪”具有相同的文化属性,它们是同一时期发生的文化现象。与《秋昼》相类似的舞剧还有《阿里改昼》。白马语“阿里”即“猫”,根据剧名的内容指向性,《阿里改昼》应是一出模拟猫的舞剧,但内容却变为模拟原始狩猎。表演由三个丑角“知玛”和若干位寨民互动进行,有驱赶野兽、围猎、抓捕、宰杀、分肉等情节。表演动作虽以写实为主,但也是经抽象、提升后的艺术化写实。整个舞剧没有对话,只用表情、手势和情景性动作再现原始狩猎场面,渗透着浓厚的原始巫术成分,俨然是古代“打猎的部落在跳舞中象征地摹仿打猎和打死猎物,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对猎物投上一种魔力”[7],达到操控猎物的目的。据此我们可推断,“池哥昼”仪式原来拥有两个舞剧,一为模拟猫的舞剧,一为模拟原始狩猎的舞剧。在漫长的流传过传中,前者佚失了舞蹈内容只保留了剧名,后者保留了舞蹈内容却佚失了剧名,于是二者的遗存部分在流传过程中联结为一个舞剧。《阿里改昼》的内容虽被串换,但装进的内容也很古老,因拟兽和原始狩猎同属原始时代的文化。《帕贵塞》舞剧表演杀野猪的场景,也属原始狩猎模拟。
“池哥昼”中模拟动物动作组建驱傩舞步的拟兽行为,主要是丑角“知玛”的拟猴表演。“池哥昼”的丑角“知玛”共有三个,两个扮夫妇,一个扮小孩。“白马语‘知玛’是猴娃子,寓意是顽皮、滑稽;小‘知玛’称‘知玛鄢摆’,‘鄢摆’是傻子,在滑稽之上又增呆傻搞笑之意。知玛的称呼已彰显了这一角色的审美追求。”[8]“知玛”拟猴动作贯穿“池哥昼”始末,是“知玛”驱傩和即兴表演的重要身段与舞步。
拟兽是原始社会发生的文化现象,无论是保存较完整的《麻昼》,还是内容被串换的《阿里改昼》《秋昼》,表演动作古朴中蕴含着苍劲、神秘,闪现着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特征,表现出白马藏族先民企图以巫术征服自然的淳朴愿望。“池哥昼”的拟兽成分综合了原始巫术、驱傩祭祀、世俗娱乐等功能,说明“池哥昼”诞生于原始社会时期,又历经了不同历史时期,沉积了不同时期的文化。
二、驱傩
驱傩是“池哥昼”仪式的主要内容。据《路史》记载,黄帝命巫咸创立驱傩仪式,“击鼓呼噪,逐疫出魅”[4]122。“逐疫”是驱逐病疫,“出魅”是赶走鬼魅。据此材料可知,傩诞生于父系氏族时期,时为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命手下巫咸创立。彼时的人们将“病疫”与“鬼魅”区别对待,皆列入驱赶之列。《周礼·夏官·方相氏》载:“方相氏,狂夫四人。”[9]又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殴疫。”[9]851方相氏,西周所置官阶,隶属司马,专门负责宫廷傩祭礼仪。此材料表明,方相氏直接承担驱傩仪式,且要进行装扮。除方相氏外,参与驱傩的还有四位“狂夫”。可见,方相氏驱傩已成为西周时期的礼制。
《后汉书·礼仪志》载: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佩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垒、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10]。
汉代,傩仪阵势扩大。时间固定在先腊一日,驱傩队伍成员有:一百二十位侲子、方相氏、十二兽、中黄门、冗从仆射、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黄门令、驺骑、五营骑士、公、卿、将军、特侯、诸侯等。相似的情况在段安节的《乐府杂录》[11]《新唐书·礼乐志·军礼·大傩之礼》和《大唐开元礼》[12]中均有记载。汉代傩仪沿袭了周代方相氏驱傩的体制,只不过驱傩队伍急剧增大,百官公卿将士均参与其中。
至唐、宋时期,官傩发生了变化。《武林旧事》“岁除”条载:
禁中以腊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三十日为大节夜。呈女童驱傩,装六丁、六甲、六神之类,大率如《梦华》所载[13]。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除夕”条亦载:
至除日,禁中皇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14]。
唐、宋时期的官傩已变为“六丁”“六甲”“六神”、判官及钟馗的“驱祟”,不见了汉代之前的“逐疫”成分,也不见了方相氏驱傩的身影。
明清已降,受宫廷傩仪影响,民间傩非常盛行,文献多有记载。《贵州通志》载:
除夕逐除,俗于是夕具牲礼,札草船,列纸马,陈火炬,家长督之,遍各房室驱呼怒吼,如斥遣状,谓之逐鬼,即古傩意也。
是日(除夕),预定桃符于门两旁,挂钟馗于门壁间,以厌邪魅。贴春帖于门枋上,以迎嘉祥。诸夷虽其土著,渐濡既久,近颇效尤,亦足以见圣化之遐被矣[15]。
明清以来,民间傩非常繁盛。与宫廷傩不同的是,民间傩仪多丰富样,总体趋向是从动态的驱傩行为转向静态的符箓驱傩,而且傩仪中钟馗从角色驱傩变为贴于门壁上的驱傩符箓。
现在流传的“池哥昼”的驱傩成分,综合了中国傩仪在各发展阶段的特征,兼融着宫廷傩和民间傩的双重特征。“池哥昼”仪式的主要任务是驱“鬼”逐“疫”。四位“池哥”左手仗剑、右手执牦牛尾,行进在山寨小径、穿梭于户与户之间,迈着刚健的步子为全寨驱鬼逐疫;“池母”与“知玛”也跳着不同的舞步协助“池哥”驱傩,以确保山寨平安吉祥、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在白马藏族人的观念中,“鬼”与“疫”是有差别的。“鬼”是恶灵魂,专做各种坏事;“疫”是带给人疾病的鬼。所以“鬼”和“疫”都要驱赶。而“逐疫出魅”是黄帝时期巫咸首创傩仪时的两大内容。在西周、汉代的宫廷傩仪中,方相氏仍保持着“殴疫”内容,“池哥昼”保留着此传统。“池哥”反穿羊皮,与周代方相氏“掌蒙熊皮”属于同类型的驱傩服饰,就是直接将动物皮蒙在身上。“池哥”面具硕大巨目阔口,与方相氏“黄金四目”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四位“池哥”俨然是《周礼》所载“狂父四人”的现代遗存。麻昼面具可视为《后汉书》载“十二兽”的活态遗存。由全体寨民组成的驱傩队伍声势极为浩大,明显承袭着汉、唐时代驱傩队伍的阵势。寨民家门壁上悬挂的辟邪驱鬼的面具,是明、清已降钟馗驱鬼符箓风俗的延续。无论从哪个方面入手考察,都能清楚窥得白马藏族“池哥昼”驱傩成分的古老属性。
三、傩面具
白马藏族民间流行的面具很多。这些面具分三个用途级别:最高级别的是开过光的面具。开光面具已不再是普通面具,具有了灵性,代表神灵,用于“池哥昼”驱傩祭祀仪式;第二级别的是寨民供奉在自家正房后堂或悬挂于门上的面具。此类面具一般被当做祖先神的象征,用于驱邪避灾保宅邸平安;第三级别的是普通面具,不具神性,是一种艺术作品。从材质分,“池哥昼”面具有动物皮毛面具、木面具、纱面具;按角色分,有“池哥”面具、“池母”面具、大鬼面具、小鬼面具、麻昼面具、各种动物面具等。“池哥昼”傩面具不仅带有中国傩面具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还标示着白马藏族宗教神灵的进化状况和“池哥昼”各发展阶段的特征。
傩面具,无论是神相、鬼相、人相还是动物相,在驱傩仪式中都具有象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信众心目中的神鬼形象。白马藏族的宗教信仰属自然崇拜,所信奉的神灵大都是自然物。他们最大的山神即是四川平武县境内的独峰岗,称为“叶西纳蒙”,汉语称“白马老爷”。每个山寨又有本寨山神,是寨子周围某座神山的化身。除此之外,白马藏人还信奉一切神灵。在他们的观念中,自然界存在的事物都有灵魂,灵魂能脱离物体长期存在。这种众神信仰显然是自然崇拜的产物。就目前调查到的“池哥昼”面具看,明显带有自然物形象与人相融合的特征,或者说是变形的人相。总体来看,“池哥昼”面具带着很大比重的原始状态,反映出白马藏族人心目中的神鬼形象还带有自然物的本来面目。
周华斌在总结中国傩面具发展的历史轮廓及各阶段的面具特征时说:“古老、质朴的巫傩面具神秘而粗犷,程度不同地存留着原始文化的信息;汉唐巫傩面具渐与佛道神灵造型相通,并有中西文化及民族间文化融汇的痕迹;宋元巫傩面具与社火娱戏交杂,众生之相大量出现;明清巫傩面具多属乡傩俗祭的护生神灵,又因‘傩戏’的活跃而呈现为具有类型化特征的戏剧角色面具。”[16]麻昼面具,完全是非牛非马的野兽面相,显然是自然崇拜时代的产物。“池哥”面具虽略具人形,但颇具古意,保留着一些古老的文化信息,其巨目、凸眼、阔口、獠牙等特征仍属于西周之前面具的特征。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受到各时代不同文化的浸染,但“池哥”面具的原始风格始终未被覆盖。故“池哥”面具的古老属性能将“池哥昼”的发展历史推到西周时期甚至更早。“池母”面具丰腴、恬静、慈颜,不具商周时期的面具特征,而带有唐代女性面相与佛教菩萨面相。但这并不意味着“池母”诞生于唐代,更不能以之作为“池哥昼”产生在唐代的证据。从发展的观点看,“池母”面具起码在唐代深受唐文化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班运翔曾说:“这倒不是说白马藏族的朝格面具产生于唐代,只是说明面具的形象,在唐朝社会风气影响下已基本定型。”[17]此说甚是,但将“池哥昼”的三种角色面具未区别开来而笼统加以概说未免有些片面。“池哥”身裹羊皮,头戴巨目、阔嘴、獠牙的面具,舞动古拙的舞步,手执刀剑与牦牛尾,挨家挨户镇宅驱邪,反映出早期人类“只有凶猛恐怖者才能退鬼、逐疫”[18]的蒙昧认识。“池哥昼”的大鬼、小鬼面具则是带着明显世俗化倾向的面相,可看做是照着世俗化的人雕刻而成的面具。
四、自然崇拜
宗教也是白马藏族“池哥昼”的重要成分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王家祐经调查四川省平武县白马藏族山寨之后提出,“白马藏人是信仰自己的宗教‘白莫’的”,“多簸人的‘白莫’就是辛剌卜的早期钵教”[19]。王家祐以为,白马藏族的宗教为“白莫”,“白莫”是吐蕃的早期苯教。姚安也提出,“白马藏族的宗教信仰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有一定渊源关系,‘池哥昼’(鬼面舞)就是一种跳神活动”[20]。白马藏族的宗教是否就是吐蕃的原始苯教,尚需进一步研究。但肯定的是,白马藏族确实有宗教信仰。
白马藏族宗教信仰的独特性很明显。组织形式上,白马藏族宗教无常设的宗教机构,亦无寺院和专门的宗教人士,仅凭借寨民自发的宗教性活动和日常生活禁忌传承,完全是一种生活习俗化的信仰。白马藏族信奉各种神灵,概括起来分为自然神、祖先神和图腾物三类。在众神灵中,山神总领着保佑山寨的一切职责,故山神信仰最为突出。总山神是“叶西纳蒙”,为白马各寨共同敬奉。各山寨又有各自的本寨山神。祖先神既指白马藏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也指每个家族的始祖,抽象为“池哥昼”中的“池哥”。白马藏族信仰的图腾主要是动物图腾。白马藏族早期部落众多,又盛行原始拟兽表演,故白马藏族的动物图腾较多。白马藏族的宗教活动分固定的和临时的两种。临时的宗教性活动是个别寨民为酬神还愿而延请法师择期在自家设坛举行的仪式活动。固定的宗教活动包括春节期间举行的“池哥昼”仪式,和四月十八、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举行的“爨老爷”仪式。“池哥昼”以山寨为单位,全体寨民共同参与。“池哥昼”成为白马藏族的宗教仪式。
“池哥昼”演绎的宗教是一种原始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并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只不过很多地区的自然崇拜随着社会演进或进化或被其它文化覆盖掉,今已不见其原貌。但白马藏族的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自然崇拜的原貌。白马藏族人深信万物有灵,对自然持敬畏之心,将庇护山寨、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的灵魂奉为神灵,将带给山寨灾难、病疫的灵魂视为恶鬼,形成“神灵奉之,恶鬼驱之”的驱傩仪式。
不可否认,白马藏族的宗教信仰在流传过程中吸收了苯、佛、道等因素。有些白马藏族山寨举行“池哥昼”仪式时,神职人员要念诵用古藏文写成的贝叶经。“池母”面具最初的面相不详,现在的面相明显吸收了佛教第二阶层神祗菩萨的面相,变得慈眉善目、恬静淡然而不失庄严神圣,成为“池母”面具共同的特点。“池母”的驱傩舞步是改造了佛教的磕长头礼而成。磕长头是佛教徒至诚的礼佛方式,要求教徒双手举过头顶合十,表示领受佛的教诲;然后用双手顺次击额、口、胸,表示身、语、意与佛相通;之后双膝跪地,双掌分开支于地面以额触地。“池母”的驱傩舞步是,双手举过头顶拍掌合十,然后垂手扶在腰两侧,同时往前跨步,按着锣鼓拍子屈膝顿身,周而复始。《池母歇勒》表演的是白马藏族妇女日常的生活内容,这种世俗生活内容似乎与其严肃的宗教性难以匹配,但追溯佛教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从元、明时期看到宗教世俗化的普遍现象。《草木子》记载:“(元)俗有十六天魇舞,盖以珠璎盛饰美女十六人,为佛菩萨相而舞。”[21]元代已盛行美女盛装扮菩萨而舞,这种文化现象与白马藏族宗教仪式中的“池母”表演擀面内容属于同类型的文化传承。“池母”在驱傩过程中于主人家厅房门廊前跳“拜四方”,祭祀天地四方五岳星辰,是道、佛神灵的相融。
概言之,白马藏族先民崇拜万物有灵,通过具体的祭拜活动,将万物之灵抽象为他们信仰的自然神、图腾物、祖先神三大神系,并定期举行祭拜仪式,以取悦神灵、祈祷神灵为山寨驱邪纳福,形成最初的“池哥昼”仪式②。随着历代发展,“池哥昼”又吸收了苯、佛、道等因素。
五、原始巫术
“池哥昼”至今保留着很大比重的巫术成分,这些巫术尚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根据“巫”字的字形演变可知,巫这一阶层的身份和社会功能在远古时候也发生着变化。“巫”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字形基本相同,是由两个工字形的组件一树立一横卧交叉组成,象形古代巫所用器物。有人也认为,“甲骨文‘巫’字是由两个‘壬’交叉而成,意思应与‘壬’相近,与‘工’则无关系。甲骨文‘壬’上下一横是分别代表天与地,中间一竖是表示贯通天地,整个寓意是沟通天地神灵的人。能沟通天地的人,在上古非巫莫属。‘巫’字甲骨文、金文正是两个‘壬’字交叉而成。”[22]历经春秋与战国时期,“巫”的字形变化较大。篆文“巫”演变为工字的左右两端为两个“人”翩翩起舞,表示以舞降神。以后隶书、楷书皆延承篆文。“巫”的字源义反映出巫在战国之前的职能。《国语·楚语》记载:“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23]巫属于社会精英阶层。《诗经》、《楚辞》里收有许多篇什,是巫降神之时所唱的歌词。可见,巫在古代的职能是手持器物以舞降神、沟通天地神人,而且还兼医的职能。
“池哥昼”的巫术成分总体上可分为行为巫术和语言巫术,且与傩成分密不可分。语言巫术主要指咒语、祝词、祈神词、口诀及经文等。语言巫术由神职人员掌握,用于“池哥昼”仪式中的请神、娱神、送神、卜卦等仪轨当中。很明显,祝词、祈神词是古巫娱神唱词的现代遗存,咒语、口诀、经文来源较复杂,需要深入研究。行为巫术主要指上文提及的各类拟兽舞,还有杀牲献祭、龙舞、送瘟神等仪轨。拟兽舞与龙舞主要由“池哥昼”的角色承担,部分寨民也参与互动,尚保留着“原始人以为借摹仿动物、旁人或自然形象,希望获得一种力量,可以驾驭它们”[7]5的远古特征。表演者虽有角色化趋势,但保留了古巫以舞娱神、驱鬼逐疫的职能。至于杀牲献祭、送瘟神则由神职人员操作。由于社会分工出现,又受各种文化影响,“池哥昼”中本由古巫承担的职能发生分化,一部分由“池哥昼”的角色承担,一部分由神职人员承担。分工不但没有抹去“池哥昼”古老的巫术性质,反倒彰显了“池哥昼”中巫发展的历史轨迹。
六、结语
综上,我们可做如下判断:白马藏族的“池哥昼”仪式包含的拟兽舞蹈、傩仪、傩面具、原始崇拜等文化成分属于史前文化,故“池哥昼”亦属于史前出现的文化现象。虽然无法准确判定它出现的具体时间,但我们可以概括它发展的历史轮廓。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白马藏族先民常以拟兽与狩猎模拟等巫术行为来干预自然,形成最早的“池哥昼”仪式。与此同时,在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白马藏族先民认为万物有灵,对自然持着敬畏之心,并以“池哥昼”仪式祭祀。此时的“池哥昼”仪式中的动植物采用假形扮饰手段。商周以降,在中原傩尤其是方相氏驱傩的影响下,白马藏族的“池哥昼”改进了面具的面相特征,从植物与兽形向人形面具迈进。唐代以后,“池哥昼”发生了一次变化,主要是受佛教影响,“池母”面具改进,“池母”舞步发生变化。“池哥昼”中各角色的装扮驱傩最初由巫承担,随着巫阶层逐渐退出社会历史舞台,“池哥昼”中负责驱傩的各色装扮角色化。
【注释】
①成果主要有: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花山崖壁画资料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63年;汪宁生《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李祥石著《走进岩画》,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盖山林文、盖志浩绘《中国岩画》,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胡桥华、崔越领著《呼伦贝尔草原文化与大兴安岭彩绘岩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宁夏贺兰山岩画拓片精粹》编委会编《宁夏贺兰山岩画拓片精粹》,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参见包建强、靳婷婷《跨学科视域下傩戏“池哥昼”文化成分的参互叙事》,《艺术百家》2021年第1期,159-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