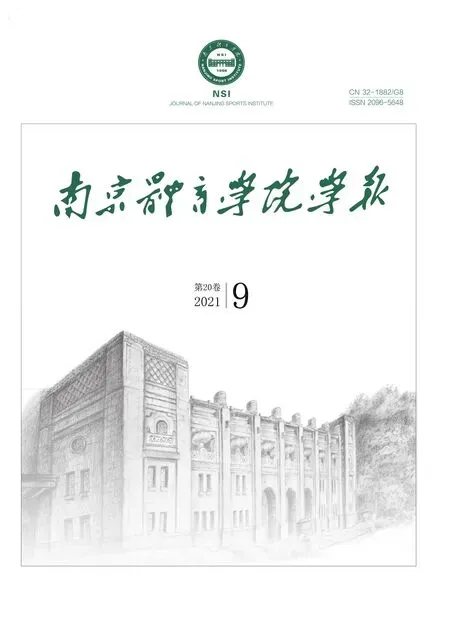旨在全面抗战:陕甘宁边区体育发展特征与历史贡献
朱雪颖,苏浩斌 ,毛亚敏
(1.陇东学院,甘肃庆阳745000;2.庆阳职业技术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1935 年 10 月至 1948 年 3 月,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党中央的所在地,边区由此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枢与指挥中心。其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于是,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中心任务。围绕这一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和发展体育,确立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体育发展方针、目标与任务,形成了体育与抗战紧密结合的体育发展模式,边区体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1],为抗战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陕甘宁边区体育发展的历史动因
20 世纪30 年代,以“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其“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2]。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正如1937年毛泽东在“八一”运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击日本。”[3]强壮的体魄是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基础与前提,“非有钢铁一般的身体和艰苦卓绝的精神不能得到最后胜利。”[4]然而,由于边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资源菲薄,广大军民的体质与健康水平普遍较低,诚如朱德总司令所言,“我们在体力方面是逊于日本很多的”,以“这种体力去和敌人竞争”,是要“吃亏一些的”[4]。
由此,大力发展体育,成为边区以及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必然选择,体育也因此成为广大军民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党中央于是发出了发展体育、抗击侵略的指示与动员。毛泽东号召军民“学习体育,武装手足”“锻炼身体,好打日本”;朱德总司令强调,“运动要经常”“养成尚武精神”;贺龙提出“体育运动军事化”,并要求广大军民“人人参加、个个都练”。边区党和政府颁布了《全苏区八月运动会规程》《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农村俱乐部组织法及工作大纲》《部队游戏》以及学校体育课程规程等一系列的体育政策与法令,成立了边区文教委员会、延安体育会、延安新体育学会、体育工作委员会、民众教育馆等各类体育组织[5],为边区体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与组织保障,推动了边区体育的蓬勃发展。
体育的功能不仅在强身健体、提升军民战斗力,而且在统一思想、鼓舞斗志、培育精神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强调,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6]。在边区,体育也不是单纯的训练与比赛,而是把思想教育、政治动员融入其中,以增强边区军民的革命意志与斗争精神。1937 年,毛泽东在“八一”运动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这个运动会,不仅是运动比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要求广大军民锻炼铁的身体、众志成城、抗击日寇;1938年,他在《论新阶段》中强调,“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以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4];1944 年,他在延安举行的军事体育运动大会上强调,开展军事体育训练,要“实行三大民主,采用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的方法,切实提高阶级觉悟与战斗”[4]。这一思想促进了体育运动与军事斗争、生产劳动、文化教育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边区军民抗战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由此观之,增强军民体质、振奋革命精神、凝聚抗战力量,夺取全面抗战的伟大胜利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发展体育的目标与动因所在。
2 陕甘宁边区体育发展的时代特征
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是边区体育的发展动因与价值所在。围绕“锻炼身体,好打日本”的目标与任务,党中央与边区政府坚持勤俭办体育,把体育融入边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之中,使边区体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全面抗战胜利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与精神支撑。这既是边区体育发展的时代特征,也是边区体育发展的基本经验。
2.1 体育与军事斗争相结合
艰苦卓绝的抗战不仅需要广大军民拥有强健的体魄,而且也需要高超的战术、技术能力。体育与军事斗争相结合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这种结合,其价值取向在于动员和组织全民参与全面抗战,集聚全面抗战的力量,置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种结合首先在于提升部队的战斗力。毛泽东指出,“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目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助,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4]151;朱德强调,“着重军事方面应为体育运动的方向,要把更多人练成坚强的人”[7];贺龙则明确了“体育军事化”的思想。于是,部队无论在项目选择上,还是训练方式上,均从抗战需要与实战出发。虽然战争的不确定性、部队的流动性较强,但部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普遍坚持每天练兵3次,训练内容包括投掷、爬云梯、过独木桥、劈马刀、抬担架、背人赛跑、摔跤、徒手格斗、渡河等,这些项目均是根据实战需要而设计的。其次,在于提升民众的战斗力。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党中央就明确提出,在群从中广泛开展体育运动,“特别要做关于战争的运动”,以“锻炼革命斗争所需要的技能”[3]。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坚持这一思想,强调“发展边区的体育运动,使其成为全区人民都能参加的运动”“我们的体育运动是战斗性群众化的,因为我们提倡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把身体锻炼得更强壮,这样才能打胜仗。”[4]边区人民把本土传统体育文化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传承和发展扭秧歌、踩高跷、舞狮、打腰鼓、赛马、摔跤等传统体育项目,创造性开展抓特务、夜间放哨等新项目,广大农村普遍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并经常开展武术、摔跤、耍大刀等项目的训练和比赛。再次,在于提升青少年学生的革命意识与战斗能力。1938 年颁布的《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要求,“一切课程内容都应与抗战联系,不适应战时需要的课程,应取消或减少”,并要求加强军事体育学习与训练,“中等以上的学校应实行军事教育,小学应实行半军事化的组织,使学生在必要时可以直接参加抗战。”[4]96小学每周体育课时一般为 150~180 分钟,军事体育教学内容包括刺杀、投掷、夜间集合、站岗放哨等;中学军事体育课程内容为侦察、通讯、站岗、防空防毒等,同时增加军事与社会活动时间;大学设置了体育理论,以及投弹、射击、刺杀、越障、野营拉练、紧急集合等军事训练项目。
2.2 体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边区体育发展中,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一开始就强调,把体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体育运动提高生产效率。此后由于日伪顽对边区的残酷“扫荡”和经济封锁,加之边区自然灾害频发,导致边区生存环境异常恶劣、物质异常匮乏。党中央遂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体育也由此融入了大生产运动之中。边区军民把体育训练与生产劳动、体育竞赛与生产大比武密切结合起来,培养出大量的劳动生产能手与英雄团体,比如战士李位每天开荒达3 亩6分,“赵占奎班”开荒多达380亩,这些劳动生产能手与英雄团体,在大生产劳动中产生了很好示范引领效应,激发了边区军民空前的劳动热情,使得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边区经济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军民开垦的荒地从1942 年的21 万亩增至1944 年120 多万亩,粮食产量从1938 年的120 万石增至1944 年的180万石[8],为边区体育发展与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培养出大量的体育能手与先进团体,以三五九旅为例,该旅在1943 年冬季举办的军事大比武中,在射击、投弹两个项目中,全旅89%以上官兵达到了规定标准,立姿投弹距离由原来的人均25米提高到40 米以上,步枪射击命中率为86.3%,其中,七一九团六连官兵人均投弹45.9 米,步枪射击命中率为100%[4]。
在此过程中,边区军民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因地制宜建设体育场、游泳池、跳水台、滑冰场,因陋就简制作各种体育器材。美国著名医生乔治·海德姆回忆道,“在空地上树一根木桩,钉块木板,安上铁圈就是篮球架了,自己动手用麻绳结织球网;用砖和土坯修砌跳马;用木棍作单杠;木板下面钉上铁条,上面系着绳子就成了冰鞋;牛羊皮内装着棉线或鬓毛包缝起来就是球”;曾任延安体育会主任的张远也回忆道,“没有球门,就做个木头架子;没有球杖,就进山找带有弯头的木棍制作——虽然条件简陋,但体育活动却开展得热火朝天。”[1]
2.3 体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
体育是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党中央就强调,重视和发展包括体育在内的文化教育,使之“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使之服务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在边区,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反复强调体育的政治性、文化性与教育性。毛泽东强调,体育与文化教育“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4];要注重学习外国体育文化,“特别应当研究各国发展体育的经验,并准备提出新民主主义体育运动的方向与具体内容。”[4]153朱德强调,体育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加以重视和提倡。李富春强调,“要把适当的生产运动融入体育运动会,让大众习作的东西体育化。”[4]51为此,边区颁布的《国际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规定把知识训练(举行救亡演讲、学唱国防歌曲等)、技能训练(学习军事知识、参加军事体育训练等)与生活训练(行动纪律)结合起来,以“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以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9]。
体育运动成为边区统一抗战思想、凝聚抗战力量的重要形式。边区各种体育比赛,与其说是一种体能的角逐、技能的较量,不如说是一种教育、动员、组织边区军民抗击日寇的盛大集会。比如,在1937 年“八一”运动会上,毛泽东参加开幕式与闭幕式,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坚决抗战是要每个人都参加的,正好像体育运动也要大家参加一样”“我们应该把运动大会精神发扬到全苏区去,发扬到全体人民中去”[4];在1940 年的“三八”运动会上,他勉励女子学员学习军事体育,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4],在边区产生强烈反响;1942 年他在接见一二零师战斗篮球队时,殷切地叮嘱队员们“要跟党走,要追求真理,要忠心耿耿地替无产阶级打仗、做事,要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4]。贺龙十分关心一二零师战斗篮球队的建设,经常告诫大家,“球队是一支队伍、一个集体,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良好的思想作风和坚毅的集体主义精神”“打球不仅仅是锻炼身体,而且也可以通过打球活动促进军民团结,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4]。
3 陕甘宁边区体育发展的历史贡献
全体中华儿女历经浴血奋斗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由此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2]。边区军民在浴血抗战中所呈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定的必胜信念,凝聚和呈示着边区体育的历史价值与贡献。
3.1 增强了边区整体抗战实力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党中央与边区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体育运动,边区军民因地制宜开展军事体育训练,显著提升了军民抗击日寇的整体实力。部队结合抗战需要,学习田径、球类等西方体育项目,传承发展武术、赛马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创新创造背人赛跑、抬担架等适用于战争的体育项目,并有组织地开展周期性的个体及团体军事体育训练,丰富了部队军事训练的内容、模式、趣味,使得官兵的体质、体能和战斗力得以大大提升。从1938 年春至1940 年4 月的河防保卫战中,边区驻军先后与日寇进行80余次的大小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1938 年3 月的神府河防战斗中,经一周激战,边区驻军击退日寇进攻,并收复宁武等7 座城池,敌我伤亡比例为24∶1;在1938 年5 月的宋家川战斗中,边区驻军与日寇展开白刃格斗,歼敌200 余人,粉碎了觊觎军渡、突破河防阵地的目的,敌我伤亡比例为2.5∶1;在1938年12月的马头关河防战斗中,边区驻军击退日寇数次进攻,毙敌80余名,敌我伤亡比例为10∶1;在1939年11月碛口河防战斗中,边区驻军击退日寇10 000 余人的进攻,毙敌100余人[10]。在这些战斗中,边区驻军或翻山越岭,或长途奔袭,或与敌人徒手格斗,或与敌人白刃格斗,或精准射击与投弹,既检验了边区官兵日常军事体育训练的成果,也呈现了日常军事体育训练中所培育的顽强的战斗意志与英勇的拼搏精神。边区民众广泛开展军事体育训练,这种训练既提升了民众的身心素质,也增强了军民的和谐关系。边区民众自觉组织起来,配合主力部队抗击日寇、清除匪患。1937年7月至1940 年夏,边区民众武装与八路军留守兵团一起,消灭土匪36股,毙伤与俘虏匪徒4 000余人[10],维护了边区良好的社会秩序。
3.2 涵养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边区体育的蓬勃发展,既提升了边区军民的体质体能,丰富了边区军民文化生活,也培养了边区军民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滋润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2],为边区军民与全体中华儿女抗击日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在边区体育发展中,边区军民以“锻炼体魄,好打日本”为目标追求,进行军事化的体能技能训练,开展军事化的体育竞赛,孕育和形成了坚定不移、服务抗战的体育精神;边区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指针,上至中央首长、下至普通军民,平等享有体育权,平等参与、民主训练、共同提升,孕育和形成了人民至上、服务人民的体育精神;由于日伪顽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边区的环境异常恶劣、条件异常艰苦、物质极度匮乏,但边区军民却依然保持积极乐观的热情,因地制宜建设体育场,因陋就简制作各种体育器材,勤俭节约办体育赛事,孕育和形成了艰苦奋斗、因陋就简的体育精神;边区军民坚持“具体、切实、灵活、创造”的理念办体育,把体育与军事斗争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文化教育相结合,学习和借鉴外国优秀体育文化,创新创造符合边区实际、战争需要的体育文化,创新体育运动项目、组织形式、比赛方式,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孕育和形成了事实求是、开拓创新的体育精神;无论在体育训练中,还是在体育竞赛,边区军民“比团结、比革命友谊、比体育道德、比战斗作风和意志、比战术和技术”[4]159,大家彼此犹如一家人、一个战斗集体,彼此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孕育和形成了团结拼搏、亲如一家的体育精神。这些体育精神传承了民族精神的精髓,塑造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与抗战精神密切相连、高度一致。
3.3 促进了边区军民的解放
人只有实现自身解放,“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历史的自觉主人。”[11]促进和实现人的解放,既是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终极目标,也是发展体育运动的终极目标。边区体育发展的时代特征,蕴含着促进和实现人的解放的内在逻辑。之所以把体育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是因为人的解放首先是体育作用的物质对象即人的身体的解放,这是以抗击日寇、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为政治前提与先决条件的。列宁指出,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应该培养青年一代具有坚强的健康的身体,钢一般的意志和铁一般的肌肉,去迎接这些战斗。”[12]正因如此,党中央确立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体育发展方针、“体育军事化”的方法论。军事体育的发展,提升了边区军民的体质、抗战能力,既为全面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促进了人的解放。之所以把体育与生产劳动、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是因为这种结合是促进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方法。马克思强调,“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2]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坚持和创造性发展这一思想,把体育作为动员边区军民服务大生产运动、提高生产劳动效率的重要手段与方法,作为教育、动员、组织边区军民抗击日寇的重要形式,作为“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强调“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加强知识训练、体能技能训练与生活训练。边区军民以艰苦奋斗精神,凭着双手创造了劳动奇迹、创造了体育,同时也通过体育与生产运动的结合“发展和改造着自身,形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创造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3]。这种结合,使边区军民切身地感受到人的尊严和人的解放。在1940 年“三八”运动大会上,500多名女子自发组成“妇女解放万岁”字样的队形;1942年“九一”扩大运动会,工人代表发出“工人有资格参加运动会,这还是第一次啊”的感慨,深情表达了边区军民实现了自身解放的浓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而这种获得感与幸福感,又促进了边区军民民族意识的深刻觉醒,增强了边区军民的战斗意志与必胜信念,使之自觉地投身于抗战洪流中,为民族解放与独立英勇奋战,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4 结语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决定了不同历史时期体育发展的不同目标、不同任务和历史使命。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全面抗战这一党的中心工作决定了体育承载着“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战略任务与使命,促进了体育与军事斗争、生产劳动、文化教育的深度融合,为全面抗战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智力支持与物质保障,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全面抗战的伟大胜利,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陕甘宁边区体育奠定了坚实的人才与技术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路径,中国体育发展日益呈现出蓬勃生机与活力,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融合,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正因如此,陕甘宁边区体育的价值成为一种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