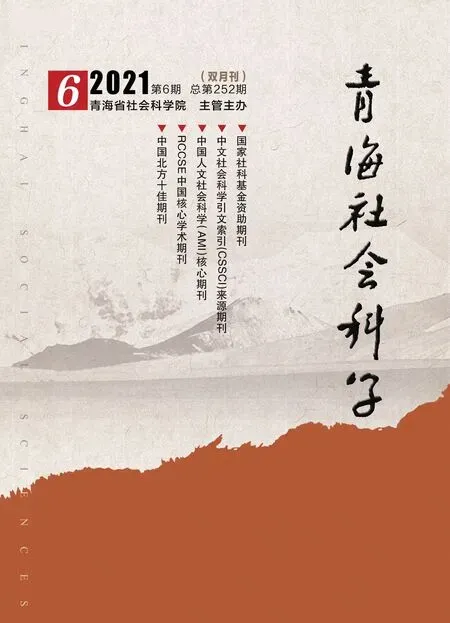京派作家凌叔华创作中的现代主义抽象性特质
——兼与现代主义作家伍尔夫比较
◇李丛朔
凌叔华是一位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女作家。她前期的中文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移民后在英国发表了英文自传体长篇小说,丰富了近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园地。然而学界对她的研究仍然较少,已有的研究也通常是从性别的角度探讨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对家庭与婚姻等问题的思考所传递出来的女性主义内涵,或从跨文化角度分析她的英文自传对于文化多样性、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传播等方面的意义。①如Rey Chow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Virtuous Transactions: A Reading of Three Stories by Ling Shuhua,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4, Issue 1/2. 1988;李宪瑜的《自我陈述与中国想象——凌叔华、韩素音、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平啸的《走进女性——凌叔华笔下的女性世界》,《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章元羚、汪云霞的《从此岸到彼岸——论凌叔华<古韵>的跨文化书写》,《华文文学》2017年第3期;Sasha Su-Ling Welland的A Thousand Miles of Dreams: The Journeys of Two Chinese Sister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等。其他研究视角还很缺乏,譬如缺少审美性特别是现代主义角度的研究。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凌叔华是一名以注重传统为特色的京派作家。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论化诞生于20世纪欧洲,对当时的日本和上海的新感觉派文学影响很深,所以学界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关注海派文学。而凌叔华这样一向被视为文风传统的京派作家,就更少被学者挖掘其现代主义价值。
本文试图分析京派作家凌叔华的文学作品中,对中国传统文艺如古典诗词和水墨画的运用,是如何体现出现代主义抽象性特质的。不仅如此,还通过与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位代表性现代主义作家的比较,探索时间和文化上都不同于20世纪欧洲的非典型性的现代主义表达方式,尤其是中国传统美学与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在现代主义抽象性上的重叠之处。凌叔华与伍尔夫有过密切的交往,受过伍尔夫的影响。表面看来,两位作家仿佛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两端,所以当前对两人的研究,也少有探讨其在现代主义上的共性。笔者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更新对现代主义的整体认知,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理解。
一、京派与现代主义抽象性的传统表达
现代主义诞生于一战后的欧洲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悲观之中。带着对工业化、新科技等现代产物的质疑,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忧虑,现代主义运动包含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一系列概念在欧洲兴起。虽然风格迥异,难以给现代主义下一个单一的明确的定义,但它们有一个基本特征:抽象性,即通过抽象表达对现实主义叙事和人物刻画的颠覆。①Peter Childs, Modernism,London: Routledge, 2008, 4.比如打破传统的有着清晰开头、高潮、结尾的叙事方式,更加关注意识和内心世界的表达,展现出对历史和传统价值的反抗等等。这使得现代主义展现出的似乎主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而非合作。
当今学界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仍然以20世纪上半叶的海派现代主义文学为重点,一个重要原因是海派特别是新感觉派文学,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民国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以半殖民地大都市为背景,海派文学受日本和欧美现代主义影响很大,善于刻画都市享乐,也常常反映出意识流写作手法,其中还塑造了一些都市“新女性”形象,充满个性解放、时尚摩登的现代性特征。例如在《上海摩登》②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书中,李欧梵详细分析了20世纪上海的都市文化与西方世界的交织,包括上海文学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可以看到施蛰存、张爱玲和其他上海作家是如何展现都市中的欲望与诱惑这一主题的。关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英文译作,也多集中在如戴望舒、穆时英等海派作家上。例如在《戴望舒:一位中国现代主义者的生活与诗歌》③Gregory Lee,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中,利大英着重分析了戴望舒现代象征主义诗歌。在《消失的中国现代主义作家:穆时英》④Andrew David Field, Mu Shiying: China’s Lost Modernis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中,Andrew Field翻译了穆时英的作品。相对来说,京派文学对于现代主义研究的意义少有学者关注。
当时的京派文学以坚持传统为特色,看上去与现代主义相距甚远。京派是对19世纪20到30年代活跃在北京、天津等其他中国北方地区的作家的统称。和上海相比,当时的北京保持了一种更为传统闲适的生活方式,京派文学也讲求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京派作家试图重新发掘五四时期所忽视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以达到传统与现代的共存。对传统文化的强调,似乎让京派文学与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等相距甚远,特别是和海派比起来更加明显。凌叔华作为一名京派作家,其作品也包含大量中国传统审美元素。其代表作之一《古韵》⑤Ling Shuhua, Ancient Melodie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69.,受到英国著名现代主义女作家伍尔夫很多的启发和支持。通过将近两年的书信交流,该作品在伍尔夫帮助下于1953年在英国出版。但与凌叔华的其他中文短篇小说一样,《古韵》表面上看仍旧是以传统审美为特色。善于书写传统美学的凌叔华,似乎与伍尔夫这样的现代主义先锋作家站在对立面,因此以往学界也少有人注意他们在现代主义上的共性,对两人的对比多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等角度出发。
海派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新感觉派受日本影响尽管更为直接,但20世纪现代主义公认的发源地依然是欧洲,并深深影响了日本。20世纪20年代,日本新感觉主义者首次使用了“现代主义”(modernism)这一概念。日本先锋文学杂志《诗与诗论》引用这一词语来介绍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等其他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①Dennis Keene, The Modern Japanese Prose Poem: An Anthology of Six Poet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3.尽管日本和上海的现代主义文学都发展出了地方特色,并不仅仅是欧洲现代主义运动的副产品,但仍然诞生于相似的历史背景,也有着欧洲这个共同的现代主义理论先祖。理论根源虽不容置疑,但我认为现代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局限于欧洲、日本和上海的模式,一向被现代主义研究忽略的京派文学之中,就可以有着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凌叔华的京派作品充满大量传统中国审美元素,特别是古诗词和山水画。她生长于一个传统大家族,家人既有官员又有学者,深受传统文学、艺术、哲学的熏陶。作为一个作家同时也是画家,凌叔华深谙视觉与文字艺术结合之道,擅长在文学创作中加入传统诗词和水墨画元素。正如传统不等同于守旧,传统元素也并不一定与现代主义相悖。传统中国艺术包括古诗词和水墨画,其一大特征正是抽象性,并且通过与伍尔夫的比较,可以进一步看出该特质与20世纪欧洲现代主义的相通之处。
二、语言凝练的艺术:古诗词的抽象性
凌叔华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第一批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之一,并未彻底与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她非常喜爱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和哲学,擅长将文学创作和古典诗歌、水墨画元素结合在一起。而现代主义抽象性,恰恰可以体现在中国古诗词凝练的语言上。诗歌通常用于抒发情感、表达志向。②Susan Daruvala, 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p. 117.相比具体的描述,抽象的情感表达更为常见。诗歌语言精练,寥寥数语就可以传递出无限的深意。1928年发表于《新月》的《疯了的诗人》,是凌叔华最知名的早期短篇小说之一,讲述了一个年轻的诗人觉生最后和妻子双双发疯的故事。借助古典诗歌元素,凌叔华抽象地呈现出了主人公错乱的精神状态。
故事的开篇,觉生正走在山间小路上,回家看望他生病了的妻子。途中忽然下起雨来,云雾顿时让觉生心情暗淡下来。他停下脚步,极目远眺,吟诵起唐代诗人王维的诗歌:山万重兮一云 ,混天地兮不分。③凌叔华著:《疯了的诗人》, 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第207—208页。凌叔华并未更细致地展开描述觉生的所思所想,而是借助王维《送友人归山歌》中的一句诗歌,抽象地表达出他惆怅的心情,略微游离的精神状态和潜在的病态感,为他文末发疯做了铺垫。诗人送走的不一定是朋友,也可能是纠缠已久的痛苦。凌叔华引用的这句诗也体现出主人公自我发现过程中的迷茫挣扎,与标题“疯了的诗人”相辉映。文末,觉生和妻子一起“疯了”,但看上去却洋溢着幸福。在周围人眼中,他们是病态的可悲的,但对他们自己来说,却像孩子一样前所未有的精力充沛,在田园里畅快地奔跑。④凌叔华著: 《疯了的诗人》,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第228页。他们不再受世俗打扰,觉生摆脱了故事开头郁郁寡欢的状态,妻子也一扫病容。就像王维这首诗一样,最终找到了通往自己理想世界的道路。关于到底怎样定义理智与疯狂、真实与虚假,这样的结局引人深思。⑤凌叔华利用古诗词抽象性特质所展现出的“疯狂”这一主题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极具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话题。故事最后,周围的人都确定觉生是疯了,但对于这位诗人本身来说,却是一种自由和解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伍尔夫在《谈生病》(On Being Ill)(1930)一文中,也看到了疯狂与精神疾病这一主题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呼吁文学创作者对其给予更多关注。与凌叔华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对疯狂主题的探讨更知名的作品当属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其现代意义也体现在对疯狂主题的探讨上。法国哲学家福柯1961发表的《疯癫与文明》中,也就这个问题发表过相似的见解。《疯了的诗人》里的觉生和双成发疯后重获新生却被人们觉得“可怜”,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疯狂对个体清醒的排挤。总之可以看到《疯了的诗人》和《狂人日记》都体现出对疯狂和理性之间的张力的思考:疯狂不仅是生物学上的,也可以是社会建构的。但相比较之下,《疯狂的诗人》对这一主题的贡献研究仍然不足,以及这个问题如何借助古诗词抽象元素表达出来的,都值得被进一步挖掘。
《疯了的诗人》中,另一个运用古诗词意象表达现代主义抽象性的例子就是对“桃花源”的运用。回家路上,当山上的云雾雨水逐渐散去,如画的风景呈现在了觉生面前,他顿时想到了桃花源。①凌叔华:《疯了的诗人》,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第209页。这个概念取自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渔夫无意间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风景优美生活幸福的村庄的故事,后来桃花源就成了一个象征乌托邦理想世界的抽象意象。当觉生看到眼前的美景时,他自问世界上是否真的有桃花源这样的地方,又是否有人愿意随他一起去。故事的结尾,他与妻子双双发疯,隐喻了他们最终实现了精神的解放,找到了属于他们的桃花源。《疯了的诗人》创作于国共合作破裂时期,作者使用桃花源这一理想化的诗歌意象,或许也是在表达自己希望从倍感压迫的政治氛围下寻得一口自由的空气。
这种试图远离具体外部现实,强调刻画抽象精神世界的手法也与伍尔夫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相似。伍尔夫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被认为是20世纪初意识流技巧运用的典范。②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and Three Guineas ,Oxford: Oxford Paperbacks, 1998, p. 6.在《现代小说》中,她还批判了某些流于物质表面而非努力探索内部感受的实利主义作者,转而强调“存在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③Virginia Woolf,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1925-1928, ed. by Andrew McNeillie,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6,pp. 157–63.捕捉人物那些瞬间的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情感,以此来反应人物最本真的一面。中国传统诗词用凝练的语言抒情言志,意识流文学利用对存在的瞬间的捕捉呈现精神世界。在利用抽象来传递真情实感方面,意识流手法与中国古典诗词有相似之处。
三、言无言之美:水墨画的抽象性
传统中国审美中,语言与视觉艺术往往相辅相成,并称文学艺术。绘画可以有诗情,诗歌可以有画意,两者并无严格界限。传统中国画中,水墨画的抽象性特质尤为明显,特别是通过留白的手法体现出来。画家并不注重细节写实,笔触大胆。这和庄子的道家哲学中的“言无言”有异曲同工之妙。④.Zhang Longxi, ‘Qian Zhongshu on Philosophical and Mystical Paradoxes in the Laozi’, in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the Laozi, ed. by Ma rk Csikszentmihalyi and Philip J. Ivanhoe,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 97–126.道并无具体形态,无法定义,无法解释。水墨画也一样,强调意境的重要性。过多细节刻画反而带来冗余信息,阻碍意境的传达,留白反而有助于抽象地传递出意境之美。凌叔华的作品也有水墨画之感,很少铺陈事实,对人物没有过多细节描写,也不在文中过多发表评论,而是以一种抽象的留白方式烘托意境,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与她的画家身份有很大关系。凌叔华童年时代就展现出绘画天赋,她的父亲和祖父也都热爱艺术。⑤Sasha Su-Ling Welland, A Thousand Miles of Dreams: The Journeys of Two Chinese Sisters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pp. 67–8.受到家人的鼓励,她自六岁起就开始学习传统中国画。即使后来成为了一名作家,她也从未放弃作画。移民国外后,将近三十年内,她在伦敦、巴黎、波士顿等地相继展出了自己的传统画作。作家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让她的文字和绘画一样简约而内敛。
《古韵》是凌叔华1953年发表于英国的自传小说,其中运用到大量留白技巧。该自传以一个小女孩的口吻讲述了作者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由十几个小故事组成,没有犀利的言辞、激烈的情绪,很多故事都有着开放式结局,给读者充足的想象空间。第一章“穿红衣服的人”中,管家马涛带着“我”去看“红差”。⑥凌叔华著:《古韵》,傅光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作者用较多笔墨烘托出欢乐的节庆氛围,人们聚在一起欢声笑语好像有什么喜事要发生。但事实上,这个所谓走运了难得一见的红差竟是斩首行刑:
马涛紧攥着我的手,顺着人流往前挤。前面忽然静下来,我看见红衣人了,只见他躺在地上,鲜血染湿了那件红衣服。这就是那人的血吗?他的头已像鸡的头一样被砍下来,不再唱歌、说话,像一只被宰的鸡。⑦凌叔华著:《古韵》,傅光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孩童天真的视角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我”问马涛那些行刑的人为什么要和红衣人玩这么狠心的游戏,红衣人他疼吗,为什么他死前要唱歌。马涛随口解释了两句,“我”也没有听懂,红差的故事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作者既没有借马涛之口发表看法,也没有以第一人称表达更多的情绪,或对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提供进一步的解释。最终这件事情可大可小,既可以是小女孩一个略带幻想色彩的童年回忆,也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更深层次的隐喻,完全依赖读者个人的理解。
第十五章“樱花节”里也有一个悲伤的片段就是“八姐”的死。然而,作为“我”童年最好的朋友,作者对八姐之死的描述,在情绪上和语言上依旧是内敛自持的。故事开头,作者描述了八姐死前那个如画的秋夜:
……一座大桥载着几个人影浮在月光里。远远的房屋、树木、河堤,飘缈的像水墨画描绘的一般。……数百株樱花树开满了樱花,银色的雾霭为它们披上一层薄纱。……一位身披袈裟的和尚……手里摇着一支长笛,悠闲自在地走来。①凌叔华著:《古韵》,傅光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114页。
尽管一切看上去宁静祥和,却又隐约预示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谁也不说话,就连平时爱多嘴的裴表姐也安静下来。我想跟八姐说什么,可又不知怎么开口,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②凌叔华著:《古韵》,傅光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当大家都在享受着一年中最美的樱花节的时候,“我”却敏感地察觉到八姐似乎不忧伤,她低声吟唱着:
花非花,
雾非雾,
半夜来,
天明去。
来似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③凌叔华著:《古韵》,傅光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在为八姐之死做了长篇的铺垫之后,真正陈述这个事实的却只有好像无足轻重两句话:“京都两年快乐的日子像一首短歌猝然结束了。夏日的一天,七姐和八姐跌入高山瀑布,溺水身亡。”④凌叔华著:《古韵》,傅光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我”最好的姐妹的死却以这种冷淡疏离的语言一笔带过,但正是这种水墨画留白的手法给读者以充分的思考空间,反思传统中式大家族中女子命运的不公。其实,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的八姐生活并不好过。她最爱的这首歌词,似乎也预示了她破碎的命运,如同鲜花转瞬就凋零,最终像云雾一样散去,了无踪迹却无人在意。凌叔华这种戛然而止的写法,也与八姐的结局相呼应,展现出了当时像八姐一样困于闺阁的女孩在男权社会中被打压,直到死亡也没有人关心痛心,始终是一个被忽略的边缘角色的悲惨命运。《古韵》在英国发表后,《泰晤士文学副刊》曾这样评价凌叔华作品的留白之美:“仿佛用一只中国毛笔作画,用笔随心而大胆,情感点到即止恰到好处。”⑤Welland, A Thousand Miles of Dreams: The Journeys of Two Chinese Sisters, p. 307.
伍尔夫的很多小说也有笔触粗粝的素描质感,从具象的表现手法解脱出来转而追求抽象真实,和中国传统水墨画对意境的强调十分相似。伍尔夫希望用尽可能简单的词句为人物形象做速写。她在日记中谈及自己的小说《海浪》(The Waves)(1931),表示想要努力“用精简犀利的笔触一下子将人物的核心性格凸显出来。必须像漫画一样用笔大胆。”⑥Virginia Woolf, A Writer’s Dia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2003, p. 153.比如在《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1925)故事开篇就写到“她有豌豆杆一样瘦小的身材;鸟似的可笑的小尖脸”⑦V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12, p. 10.。顿时达洛维夫人一个有点锋芒却又爱担惊受怕的形象跃然纸上,也暗示了她后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挣扎难以解脱的状态,同时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女性在战后充满压迫感的氛围下的焦虑之感。可见无论是伍尔夫抽象的人物素描,还是凌叔华运用留白技巧传递出意境,都体现出一种将视觉与文字艺术结合的美学。伍尔夫的好友罗杰弗莱是一位中国艺术爱好者,比如在其《中国艺术》一书中就曾探讨过绘画、雕塑、纺织、青铜器等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他曾写信给伍尔夫,赞赏她在其《旅程》 (The Journey)(1923)中将视觉和语言艺术地巧妙结合:“你的‘旅程 ’是多么可爱。你能用(用文字)创作出这样的景致,相比来说画画都没必要了。你用简单几个词就把整个氛围烘托出来,真是令人惊叹。”①Roger Fry and Denys Sutton, Letters of Roger F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2, p. 534.
留白的手法还体现在《古韵》的叙事结构上,和20世纪初中国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线性叙事结构不同。该书共有十八章,每章都着重描写某一天的故事。虽然不能确定这种叙事结构一定直接受伍尔夫直接,但的确和伍尔夫的小说《岁月》(The Years)(1953)在章节安排上有一定可比性。《岁月》记录了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一个英国家族史,但既不是按编年体写成,也没有以史诗的方式呈现。作者在五十个年头中选取了十一年,然后在每一个部分记录一年中某一天的故事。通常线性叙事结构会被认为有助于为读者呈现更充分、更有逻辑性的信息,然而这也往往导致信息冗余。相比来说,《岁月》和《古韵》这种更为简练抽象的结构,虽然仅仅是选取了一天的生活来记录,表面上舍弃了广度,却增加了深度,反而有利于突出重点。与其死板地记录人物生平,一个以一天为单位的小故事更加生动形象。就像水墨画用留白来烘托意境,省略无效信息反倒凸显出掩盖在庞杂细节下真实的内涵。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代主义在不同时代和文化中有丰富的表现形式,互相之间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彼此。虽然现代主义理论根源在20世纪的欧洲,但现代主义本身仍然是一个跨文化和跨时代的体系。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实验中,逐渐形成更加多元化的现代主义,而不是按照一种标准的线性发展。正如Bradbury和McFarlane在《现代主义》(Modernism)中所说,现代主义是一个 “复合、调和、融合、凝聚和相互渗透”的过程。
在上述对凌叔华的短篇小说和自传体小说的分析中,我挖掘了现代主义抽象性特质在中国传统诗歌和绘画中的表现方式,说明中国传统审美元素与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在现代主义抽象性特征方面存在对应关系。但它们的重叠性并不限于这种平行比较的角度。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对20世纪欧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产生过确实的影响。一个典型例子是意象派/意象主义(Imagism)。20世纪初,美国诗人庞德翻译了中国的《诗经》。继承了《诗经》语言犀利、想象力丰富的特点,庞德从中发展出意象主义,即只关注语言与表达(language and presentation)。②Anthony David Moody, Ezra Pound: Poet: A Portrait of The Man and His Work, Volume I, The Young Genius 1885–192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88–222.随后意象主义成为英国诗歌史上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运动,促进了欧美早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欧美文学艺术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中,通常存在一种对战后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东方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有时被欧美视为当时西方文明的解药,试图通过吸收东方文化来帮助解决其内部问题,比如战后西方文明的身份危机(identitycrisis)等等,从而重振西方文化。
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古典诗词和水墨画在时间线上是传统的,其价值却并不保守。传统与现代当然不可等同,但传统也不完全是现代的过去式,从我们习惯性认知的某些“传统”元素中,仍然可以发掘出现代性意义。本研究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探索了中国古诗词和水墨画的抽象性特征为凌叔华的京派文学作品带来现代主义意义。从京派作家凌叔华的角度,并兼与英国代表性现代主义作家伍尔夫的对比,本文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京派现代主义的新案例。的确,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日本和上海现代主义文学是现代主义经典,也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但在中国甚至更普遍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凌叔华这样的因传统特色而被忽略的京派作者,其现代主义内涵依然值得被进一步挖掘。这将有助于补充以海派文学研究为主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丰富对欧洲以外的现代主义表现形式的认知,更新对现代主义的整体理解,并从文学审美性的角度重新认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