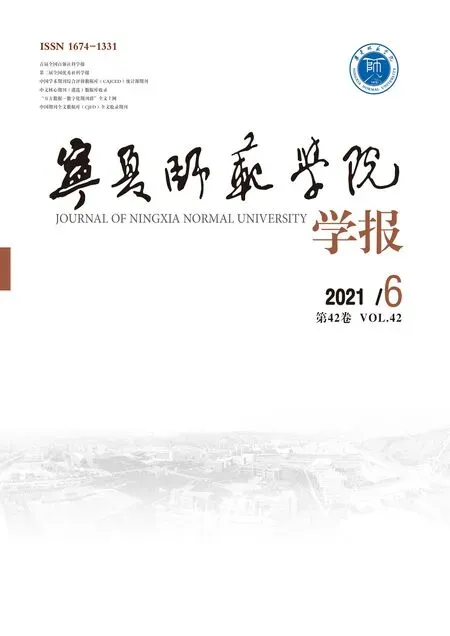《茶酒论》中的民俗与仪式
张焕忠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统治力量被大大削弱,一些部落也乘机侵犯西北边陲,致使敦煌长期脱离中央王朝的控制,后世文献中有关这一地区的史料也就相当匮乏,但随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沉睡千年的敦煌写本被唤醒,在这些遗留下来的敦煌写本中,有大量关于敦煌民众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的写照,《茶酒论》就是其中之一,文章采用代言体的形式,通过大量的语言对话,一方面让我们在趣味中了解到唐代的饮茶饮酒之风;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对话论争造成了一定的故事情节,实际上也塑造了茶酒的人物角色,可视作一个戏剧脚本,而这个戏剧是在敦煌浴佛节上进行演出的。
一、饮茶饮酒之风
敦煌地区是比较注重世俗生活的,从那些保留下来的敦煌写卷中,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茶酒论》虽然不是专门探讨茶与酒的文章,但是它所反映出来的敦煌民众的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敦煌民众的饮茶之风
茶叶产地格局变化,新兴的产茶地促进了饮茶风气。
茶谓酒曰:“阿你不闻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濛顶,其山蓦岭;舒城太胡,买婢买奴。”[1]
浮梁县,今隶属于江西省景德镇市,唐时属江南西道饶州,《元和郡县图志》载:“武德五年,析鄱阳东界置新平县,寻废。开元四年,刺史韦玢再置,改名新昌。天宝元年,改名浮梁。”可知浮梁县由新平县改名而成,此地是唐代重要的产茶之地,以致“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
蒙顶山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境内,此地所产茶叶素有“蒙顶石花”之称。《国补史》曰:“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唐黎阳王《蒙山白云岩茶》称赞:“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这两大新茶叶产地的兴起与发展,极大冲击了传统产茶区歙州、舒城太胡、越郡余杭,虽然这些地方仍产茶叶,但已不占茶叶生产的主导地位了,彻底改变了茶叶产地的格局[2]。
自古以来,喝茶就是我们饮食的一部分,但饮茶之风的真正普及则始于唐代,《新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茶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亦知饮茶矣。”陆羽《茶经》的问世,标志着饮茶之风的正式形成。
茶为酒曰:“我之茗草,万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黄金。明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供养弥勒,奉献观音,千劫万劫,诸佛相钦。”[3]
饮茶常与禅联系在一起。由于茶叶的便宜,因而受到广大民众和僧人的欢迎,饮茶不仅能使僧人摆脱疲劳,助长精神,而且饮茶过程中蕴含的温文尔雅的韵味,是与奢侈放纵相对的,所以茶叶也常作为佛教贡品,贡奉给菩萨。
(二)敦煌民众的饮酒之风
在敦煌写本中,茶与酒往往会相提并论。唐时酒税是地方财政的一笔大收入,又乡饮酒礼是乡贡进士的礼仪之一,所以酒有“礼让乡侣,调和军府”的社会功用;饮酒的同时往往还有歌舞、音乐、游戏的做伴,《茶酒论》中“有酒有令,仁义礼智”“国家音乐,本为酒泉”“曾道赵主弹琴,秦王击缶。不可把茶请歌,不可为茶交舞。”都可以证明唐人饮酒过程中是有一系列的娱乐方式。但在民众的思想中,饮酒常与赌博、娼淫等恶习联系起来,受人唾弃。如文中有“酒能破家散财,广作邪淫”。同卷的《王梵志诗》也有“饮酒是痴报,如人落粪坑”“饮酒妨生计,樗蒲比破家”,这些佛教劝世诗似乎也在指责“酒”的过失。
所以从文章中,我们能很明显感受到,作者是有意识地偏向“茶”的。《茶酒论》通篇采用对话形式展开,茶酒双方相互辩驳,各言其用,但如果细致揣摩全文,可以发现在茶酒争辩中,“茶”明显占据着优势:争辩开始,两方围绕“两个谁有功勋”的论辩题目,茶率先向酒发起质问,它先道出自己身份的高贵“百草之首,万木之花”,接着说自己生长环境的优良“浮梁歙州”“蜀川濛顶”,再者说自己不仅供奉帝王将相,也能为普通百姓效劳;而“酒”的反驳仅言自己的商业价值与艺术催发力,就算有驳斥“茶”的不好,理由又未免牵强,接着又用“仙人杯觞”“中山赵母”的传说与虚无来为自己辩解,再往下,“酒”已经失去傲慢的身份,又陷入了“词穷”的地步。通过四回合的论争,“茶”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但“茶”还有话说,它用“烧香断酒,念佛求天”来反驳“酒”,而这一次“酒”却没有回答,在“酒”尴尬的时候,“水”出来劝解。
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前文已经有所提及,一是因为饮酒时的恶习,二是作者借茶酒争论的形式,实际上也是在宣扬一种佛理,如:
水为茶酒曰:“阿你两个,何用忩忩?阿谁许你,各拟论功!言词相毁,道西说东。人生四大,地水火风。茶不得水,作何相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自不说能圣,两个何用争功?从今已后,切须和同,酒店发富,茶坊不穷。长为兄弟,须得始终。若人读之一本,永世不害酒颠茶风。”[4]
水是带有理性思辨的,它的出场化解了酒的“词穷”,但它并不是为了赞美“茶”,也不是为了支持“酒”,它也对茶酒进行了适当的批评,劝解茶酒兄弟重归言好,各自作好职能表率;同时,水“感得天下亲奉,万姓依从”,我们可以看到水恩泽万物却不求名利的精神,水的寂寂无闻与茶酒争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似乎也在宣讲一种佛理,尘世相争无非茶酒的对峙,只有自己到达水的气概,才能以一种阔达的胸怀包容万物,寓讽戒规劝之意。
二、浴佛节中的百戏
《茶酒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敦煌地区的饮茶饮酒风俗,而这个民俗又影响了茶酒戏剧的创作。张鸿勋虽然在体制上把《茶酒论》归入赋类,但他同时谈到这种故事赋在金代被院本吸收而演出,实际上是开了“茶酒戏剧”的滥觞[5];赵逵夫则把《茶酒论》视为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并且从多个方面指出了它作为戏剧演出的可能性,以及在我国戏剧史上的研究价值[6];王小盾认为《茶酒论》是“一种由表演双方围绕特定命题往复话难、以问答形式进行的伎艺及其文学记录”的“议论”底本,常在民间歌场演出[7]。20世纪90年代至今,前辈学者已对《茶酒论》中的戏剧因素作过细致分析,但学者大多从文本的角度去解读它的戏剧性,而对它背后的仪式讨论得较少。敦煌文学的产生与民俗仪式息息相关,因为敦煌民众并不把传统的文学当作案头文字来欣赏,而是当他们为此类文学赋予另一种内涵时,才能成为敦煌文学,这个内涵主要指社会文化仪式,仪式的一次展演过程就是一个“文学事件”[8]。
《茶酒论》存六个卷子(1)陈静认为有7件,因S.5774应为两个不同写本的残卷拼合而成,见陈静《敦煌写本〈茶酒论〉新考》,《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第85页。,分别是S.406、S.5774、P.2718、P.2875、P.2972、P.3910,其中P.3910、P.2718两件写本有时间可考。P.2718正面题“正月十四日”,P.3910题“正月十八日”。显而易见,这两件时间可考的写本,都是在正月抄写完成的,那么这两件写本是否有特殊用途?又是否与敦煌地区的浴佛活动有关呢?茶酒戏剧是否可以在浴佛当日进行演出呢?答案是肯定的。
有关浴佛节日的时间,历来争论不休,一说为农历四月八日,一说为农历二月八日,唐朝以前的佛诞日多选择在四月八日,而自梁经唐至辽初,大抵定在二月八日[9]。浴佛节是一场盛大的仪式,如P.2940《斋琬文》对这场仪式有细致的描写:
二月八日……于时妙花擎日,清梵携风,浮宝盖于云心,扬珠幡于霞腹。幢拔天而亘道,香翳景而骈空。缁俗遐迩而星奔,士女川原而雾集。同睎圣景,望投尘外之踪;共属良辰,广树檀那之业。于是供陈百味,坐佛千花,投宝地以翘诚,扣金团而沥想。[10]
敦煌写卷P.3103存一篇《浴佛节作斋事文》(2)原卷无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拟题为《浴佛节作斋事文》,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29页。,文曰:
爰当浴佛佳辰,洗僧良节。而乃澄清神思,仰百法以翘诚,洗涤笼烦,趣大乘而恳切,由是求僧侧陋,置席莲宫;导之以阖境玄黄,率之以倾城士庶,幡幢晃炳,梵赞訇锵,论鼓击而会噎填,法旌树而场骈塞。[11]
浴佛活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关注,这场仪式的盛大程度使得“宝盖”“幡幢”遮蔽了天空,人们乘兴出游,观佛仪,仰佛法,以求洗涤烦恼,在行像过程中,除了音乐铿锵、梵呗盈空、鼓声震天给人带来的听觉冲击外,往往还带给人们视觉上的享受,即杂技的表演。如《洛阳伽蓝记》载:“梵乐法音,恬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化”;《辽史·礼志》载:“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长安客话》载:“幡幢铙吹,蔽空震野,百戏毕集,四方来观,肩摩榖击,浃旬乃已,盖若狂云”。
以上几则材料都对浴佛节有一定程度的描述,但值得注意的是,浴佛当日不仅有“梵乐法音”,也有乐舞做伴,更有百戏表演。在敦煌壁画中,我们不仅能直接看到百戏图(3)如莫高窟第72窟有“南壁九人奏乐百戏图”;第361窟有“南壁巾舞百戏图”。,也能看到许多与音乐题材作品中描绘的乐器,这都说明了百戏表演与音乐、戏剧演出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百戏为何?百戏是中国古代杂剧、乐舞表演的总称,与民间逢场作戏类似,它的特点是融入了新鲜活泼的民间歌舞和其他各项新的文艺形式,演出时间多在庙会举行时。在百戏中,我们能找到早期敦煌戏剧的影子,因为在唐五代时期,百戏与戏剧表演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尚未形成分类归属的概念,因此大多处于一个混同的状态,如《茶酒论》的情节设置、演出人员等,这些方面就现代戏剧而言是无法支撑起一个表演剧场的,早期的剧本体制篇幅都很短小、情节简单,表演能在较短时间单元内完成,但为了满足观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审美需要,所以在戏剧表演中或结束后往往会出现与百戏混同演出的现象。如《隋书·音乐志》载:“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足以见此时的各类演出是沿路排列的,但也可以看出这种“粗放型”的表演形式已经具备了观与演的需求,后来随着戏剧的成熟与表演场所的固定化,敦煌戏剧逐渐脱离百戏的串演而成为独立的表演形式。
这些百戏的存在是合理的,一方面,是为了娱民,因为父老乡亲想沾上佛庆而洗涤烦恼;另一方面,是为了娱佛,目的是为了讨好神明而求得庇佑。但并非所有的表演都适用于娱佛,它一定是适用于佛教仪规的。娱佛活动实际上是寺僧把城乡民众卷入佛禅的仪式行列,以便“强行参与更多人众的精神生活,从而使寺庙更进一步成为人们的精神和文化寄托的中心场所”[12]。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作者主观倾向于饮茶了,因为自梁武帝下诏禁酒肉后,饮酒就是佛家大忌,所以敦煌写本中保存了大量《断酒肉文》,又浴佛节是佛家仪式,是不可能倡导民众饮酒的,而代之能使人神志清爽的茶。茶酒戏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本身内容呈现出的诙谐、幽默以及对地方俗语的使用的特点,使得民众更有亲切感,也能缓解民众的心情,并且在这种放松情况下,人们已经不自觉地受到了佛理的教化。
于此,我们便能知晓《茶酒论》与浴佛节的关系了。“在丰富的敦煌说唱艺术基础上,于晚唐时涌现出了一些用说、唱、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演出事先编排好的故事”[13],为庆祝浴佛节的到来,茶酒戏剧会事先编排好剧本、演出的人物、动作、舞台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茶酒论》的抄写时间会早于浴佛节近半月之多。浴佛节的举行,不仅使民众洗涤心灵、摆脱烦恼,同时那些带有娱乐性质的百戏表演,还能使民众放松心情。仪式促进戏剧发生的现象还有很多,如在敦煌写本中保存了大量的“儿郎伟”的驱傩词,这些作品主要是用在敦煌傩仪式中,民众通过戏剧扮演表达辞旧迎新、驱邪逐疫的愿望。所以当敦煌民众把《茶酒论》真正用于仪式过程中,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文学,浴佛节上的百戏表演,刚好为茶酒戏剧的演出提供了条件。
三、宗教性仪式到艺术性仪式
关于戏剧的起源,各家众说纷纭,有游戏娱乐说、巫人俳优说、模仿本能说、原始歌舞说等,虽然这些戏剧起源说立足点不一,但这些学说却存在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戏剧演出与仪式举行是密不可分的。浴佛节本身是一件神圣而庄重的事情,但9至11世纪的敦煌浴佛活动实际上转为祷告为主,与本来的宗教目的相比更重世俗色彩,客观上成为一种娱神的喜庆活动,致使敦煌写本中有关浴佛节日的记载就出现了庄重与娱乐共存的状态[14],而此时的敦煌戏剧已经尝试从仪式化表演向艺术化表演转变。
(一)演出场所的固定化
《茶酒论》以浴佛节为载体而进行演出,演出需要一定的舞台,固定演出场所的出现,极大促进了敦煌早期戏剧向成熟戏剧的演变,敦煌戏剧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百戏同台演出,此时戏剧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种同台演出的形式,实际上是淡化了戏剧自身的独立性,而随着固定演出场所的出现,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在《茶酒论》的6件写本中,其中有三件写本中都提到了“寺庙”。P.2718正面末题“知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知术院就是释道两家的寺院,游国恩据此认为写本所抄内容是在“行院里演唱的”[15];P.2972背面抄有《丁丑年六月十日图李僧正迁化纳□历》,还有“金光明寺”的字样涂鸦;P.3910末题“净土寺(沙)弥赵员住书”。这些寺庙名字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戏剧演出存在一定的联系。唐五代时期,寺庙不仅是高僧居住之所,同时还承担了许多世俗义务,如蒙童教育、迎送使客等,同样的,也可以作为戏剧演出的场所。就目前来看,现存的戏台大多存在于寺庙中,神庙剧场在中国古代剧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剧场的演出“在时间上来讲,以定时为主”,定期的演出一般选在岁时节令中或神灵诞辰[16]。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浴佛节,大多在二月八日举行,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茶酒戏剧也就能被搬上舞台,这个舞台又多设于寺庙中。
(二)《茶酒论》中的戏剧因子
从内容上看,全篇除去结尾处“两人正争你我,不知水在旁边”属旁白叙述外,通篇采用代言体形式,把茶酒拟人化,并且文中还出现了固定的说明性文字,如茶酒的出场都是以“茶为酒曰”或“酒为茶曰”的形式起头,这种形式可以让角色知晓自己该争辩的内容,又证明了这种争论必须是面对面才能进行的。茶酒的出场动作都是“出来”,这个“出来”是相当于现代戏剧里的“上”,是叙述性文字戏剧化的表现,再者,文中也有静场词的使用,如茶出场时“诸人莫闹,听说些些”,可以看出“茶”并不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而是对观众所说的话,言下之意就是希望观众安静下来,以便进行下一步的表演;从作者来看,《茶酒论》的作者署名为乡贡进士王敷,作为地方文人的王敷,是可以创作这一类诙谐作品的,而且因为是下层知识分子,也就更了解民情,更能创作那些亲切生动的作品。茶酒戏剧“不再是社会道德观念或某种宗教教条的简单的演义图解,而是作者个体的社会生活理想和宗教情感通过驾轻就熟的文学手段而得到的自然流露。”[17]所以文章出现了褒茶贬酒的倾向,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因为茶与禅常常联系在一起,文人与僧人的交流也可以通过茶这一媒介,所以王敷是借助茶酒戏剧来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感和生活理想,浴佛节倡导戒荤食素,食斋素就更为民众、僧人所喜爱,茶也就更容易被接受。茶酒戏剧就借助浴佛节仪式呈现出来,一方面,反映了唐代人的饮茶风气,另一方面,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饮品,也就能更吸引观众。
(三)写本装帧形式的变化
传统的敦煌学研究主要以文体分类释录的方式去解读作品,所以学者往往把某一个作品从写本中抽离出来,这种以孤立的方法去探讨文本内容,忽略了写本的整体性,切断了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系。大量研究证明,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写本情景,不仅要把握文本的内容,还要整体把握写本的物质存在状态,以及在动态中洞悉写本从制作到完成时的全过程。
《茶酒论》的6件写本中,S.406、S.5774、P.2718、P.2875、P.2972五件写本都为卷轴装,唯P.3910为敦煌少见的对折册页装,并且从抄写时间来看,P.3910抄得最晚,这说明了《茶酒论》在传抄过程中写本装帧形式发生了改变。册页装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公元9世纪,特点是纸张不易脱落、便于携带。那么P.3910装帧形式的变化是否暗示书写内容有特殊用途?装帧形式是否与书写内容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李际宁认为后起的装帧形式,相对于之前的装帧形式存在着某种必然的继承,并且还谈到“册页装是适应了民间念诵佛经,做功德的灵活性而出现的,它的目的是需要方便携带,而不是供养法宝,因而制作简便,且随个人之方便而没有严格工序和规格的限制”。[18]这个观点得到了李致忠的支持,他也认为装帧形式的变化值得深入研究,或许是由于典章制度的改变,又或许是由于文本内容的特殊性。[19]徐俊从写本学的角度出发,把写本的物质形态与写本内容联系起来,他注意到P.3910卷子中的篇章除《秦妇吟》外都有两个题目,同时也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完整性和可信度,同时在繁杂的写卷中,方便知晓作品的起止,所以他认为P.3910在所有现存的敦煌诗卷中,是最具有演唱底本的特征。[20]另外,与《茶酒论》同抄的《新合孝经一卷》《新合千文一卷》也是具有表演性质的,任半塘认为“皇帝感辞既入歌场,体虽不演故事,若能穿插说白,入演唱,已极明显”;《新合千文皇帝感辞》“因于帝诏,合以歌舞,而演唱于歌场”和“向广众作教育宣传者”。[21]说明了在传抄过程中,抄写者逐渐意识到这些作品都同样具有表演性质,所以把它们抄在一起,并且为了表演时的方便,或者是便于翻阅、携带、记诵,抄者选择了册页装的形式。
四、结语
从《茶酒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唐时敦煌地区的饮茶饮酒之风气,这些饮茶饮酒风气也反映了他们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同时,《茶酒论》中所包含的戏剧表演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茶酒戏剧又刚好是用在敦煌浴佛节上进行表演的,而此时的敦煌浴佛节更多扮演着世俗意义,所以我们也能从《茶酒论》中看出宗教仪式性的表演逐渐向娱乐性的表演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