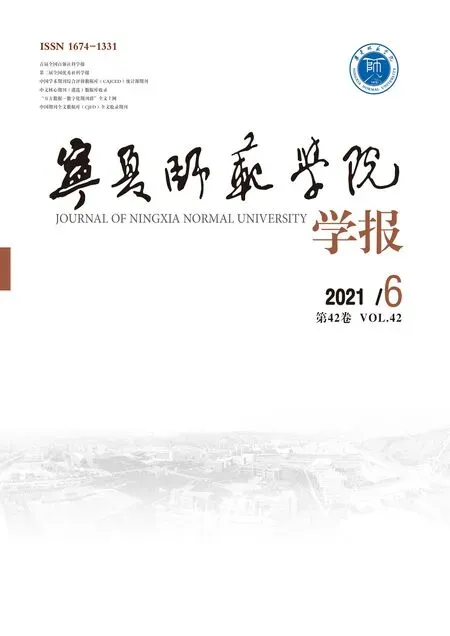从伍子胥谈《九章》伪作辨正
蒋惠雯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九章》之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刘向辑录的《楚辞》中,《九叹·忧苦》篇有言:“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惮于《九章》。”今本《九章》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录依次为:《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王逸曾对《楚辞》进行了详细考辨,认为这九篇均出自屈原之手,但后代学者多有不同看法。
自宋以来,疑古思辨之风盛行,人们不囿于成说,不仅对汉学多有诘问,更提倡对古代文献进行辨伪工作。欧阳修“排《系辞》,疑《周礼》”[1];程颢、程颐辨《诗序》,考《素问》;叶梦得疑《春秋左氏传》;司马光疑《孟子》《文中子》;朱熹更是辨伪大家,其考辨书目广涉经史子集、佛道文献各类,数量也多达44部。正是在这样的风气推动下,学者关于《九章》的研究,除诗意阐发外,还出现了大量关于其真伪的考辨。
一、《九章》伪作说概述
关于《九章》真伪的考辨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其中有一说法颇具代表性,认为《九章》中某些诗篇并非出自屈原之手,乃系后人伪造。尤其是清代曾国藩《读书录·楚辞》与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九章》中提出了具体的几点根据,力主《惜诵》与《九章》的后几篇均为伪作,引起广泛注意,近代一些学者颇受影响。如胡適曾在《读楚辞》中谈到对屈原的看法,将其称为“箭垛式的人物”:“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为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2]闻一多在《论〈九章〉》中以为,“《怀沙》以前,屈子所做,过此以往,即与屈子无关也……(《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不惟不属《九章》范围,且不属屈赋范围矣”[3],矛头所向已经非常明显了。陆侃如、冯沅君也曾在《中国诗史》(1931年版)中对《九章》分类考辨后,提出《九章》仅有半数为屈原真作,其余皆为伪托的观点。
关于《九章》伪作说,学者们曾从内证、外证甚至旁证等多种角度加以举证说明,但他们提出的证据是否都充分且毫无辩驳余地呢?下文笔者将借其中一个内证举例加以探讨。
二、《九章》伪作内证:伍子胥“逆臣”说
在复杂漫长的考辨过程中,最让辨伪者们兴奋的“内证”莫过于发现《九章》存疑作品中都出现了屈原对伍子胥忠贞之志的称颂以及追慕之情,如《涉江》里悲叹“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中痛心“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中更抒发了自己“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的渴望。
战国秦汉史料记载中的伍子胥以“忠”出名,往往与直言进谏被纣王剖心而死的忠臣比干并举。《韩非子·人主》有言:“王子比干谏纣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4];《庄子·盗跖》评价:“世之所谓忠臣者, 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5];《荀子·大略》感叹:“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谏者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6];《鹖冠子·备知第十三》曰:“比干、子胥好忠谏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7],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屈子在行吟泽畔、忧谗畏讥时,以伍子胥自比表达忠贞爱国的不渝之志,貌似合乎情理,无可指摘。但辨伪者们却坚持认为,依据可考的伍子胥生平记载,屈原绝无可能对他推崇备至,《涉江》等篇中流露出对伍子怜悯叹息,恰好证实了它们并非屈原所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伍子胥生平记载最早可考于《左传》,后世史料文献均在此基础上演变、发挥。伍子胥,名员,春秋后期楚国人。因太子少傅费无忌进谗言,其父兄伍奢、伍尚均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辗转流亡至吴国,投入阖闾门下,后助阖闾攻破楚国。《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为报父兄之仇,伍子胥在吴兵入郢后曾“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8]。后吴王夫差继位,伍子胥力谏尽早消灭越国,不可养痈遗患,却遭到太宰伯嚭诬陷,最终自尽而亡。
显然,史料文献中称赞伍子胥为忠臣,并为其遭遇感到惋惜的言论均是以伍子胥的吴国经历为依据。可若从伍子胥楚国人的身份来看,他却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劝吴伐楚,使楚国险遭倾覆,此举可谓是不忠不义,实乃楚国之逆臣。作为与王室同宗同源的贵族阶层,屈原必不可能对这位历史上的楚国公敌怀有物伤其类的哀悯追慕,更谈何仿效其所作所为?
因此自宋至近代以来,不少学者从家国、君臣观念角度出发,断言《九章》内凡歌颂伍子胥的诗篇必不是屈原所作。
首先提出此看法的是南宋李壁,他在《王荆文公诗李壁注·闻望之解舟》注释中称伍子胥“于吴实貔虎,于楚乃枭鸱”,为楚之“逆臣”,屈原作为“三闾同姓之卿,义笃君亲,绝不称胥以自况也”。[9]魏了翁在《鹤山渠阳经外杂抄》中承袭李壁此说,并提出《悲回风》等应为后人凭吊屈原的仿作:“子胥挟吴败楚,几墟其国……《悲回风》章云:‘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吴之忧,楚之喜也。置先王之积怨深怨而忧仇敌之忧,原岂为此哉?又言:‘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词,原安得先沉流而后为文?此足明后人哀原而吊之之作,无疑也。”[10]
近代以来学者对此也颇多认同,如刘永济《屈赋通笺》卷五《九章》:“子胥于吴诚忠矣,然教吴伐楚,残破郢都,鞭平王之尸,自此之后,吴楚构兵不休,贻害楚国甚大,实乃楚之逆臣,屈子决无以忠许之之理。”[11]战国时期游士阶层已然兴起,士人若不得志完全可以前往他国另谋出路,但屈原却“宁死勿去,与当时风气相反”。如此“有忠义之厚”的爱国诗人在作品中夸赞“逆臣”必然是不合理的,因而刘永济定论:《悲回风》《惜往日》等“非屈子所作,殆已可信”。
三、难以成立的“逆臣”之说
上文质疑之说似乎确有可信之处,然而为何直到宋代学者们才发觉这个明显自相矛盾的破绽呢?此恐非前人粗心使然。《悲回风》《惜往日》等篇是否为伪作确实尚有探讨余地,但如果将提及伍子胥作为伪作的重要“内证”,只怕经不住细细推敲。
(一)“天下一家”的氏族意识
伍子胥之所以被冠以“逆臣”的称呼,很大程度上是后世辨伪者们以民族主义或爱国思想作为判断标尺得出的结论。陈子展先生《楚辞直解》中对此明确反对:“王土王臣的观念, 中国一统、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 ,早已成为思想领域上的统治思想,这在无形中压住了褊小的地方观念、狭隘的爱国思想……在那一时代里,这一国的人才一点不避嫌疑地出仕那一国,那一国的君主一点不生猜忌地延揽这一国的人才。楚材晋用、朝秦暮楚,不算一回事。”[12]以孔子为例,他携弟子周游列国的十余年里,也曾欲仕不义之主。公山弗扰在背叛鲁国、割据地方后曾召孔子出仕,身为鲁人的孔子非但没有拒绝,态度反而是积极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就连屈原本人,在遭谗被逐的过程中,也发出这样的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尽管最终未选择去国远游,但确实曾对自己的去留与否踟蹰不定。
可见屈原与伍子胥之间并不存在忠臣与逆臣的天然对立,然而随着社会意识的不断发展,君国意识逐渐取代氏族意识,尤其是宋明理学逐渐成为主流后,君主本位的政治思想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评判标准。例如朱熹就曾称赞屈原有“忠君爱国之诚心”,后世辨伪者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屈原乃爱国诗人之典范,很可能是受朱熹言论的影响,不免以今度古尔。
苏雪林在《楚骚新诂》(1978)中也与陈子展先生持类似意见。她认为学者们不能“以后代兴起的国家观念来批评他(伍子胥),并斥之为‘逆臣’,因为“这种国家观念乃是现代西洋产物,中国从前是没有的”。[13]在此基础上她更进一步阐明,伍子胥的报复是“基于人类天然的情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都是认同并且理解的。
(二)“血族复仇”的社会风气
伍子胥出仕的目的是为了报复父母之邦,对楚平王鞭尸三百的做法也颇为偏激,如果仅用“基于人类天然的情感”的理由来解释,未免有些牵强。
我们不妨来看看《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四年》中提到的一个小细节: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
伍子胥逃亡前对自己的朋友申包胥发誓日后定要灭楚,申包胥说你若灭楚那我必可复楚。这样看来,双方关系是敌对的,但申包胥在开头多说了两个字:“勉之”,这竟与伍尚激弟伍员为父复仇的“尔其免之”如出一辙。申包胥为什么勉励、称许伍子胥所言呢?这似乎令人费解。实际上这并不是申包胥对朋友的敷词,而是基于先秦时期人们共同认定的“血亲复仇”道德准则。
汤炳正《渊研楼屈学存稿》中就此阐发道:“当时伍子胥的出走及其报仇伐楚,乃是氏族社会‘血族复仇’遗风的表现。因‘血族复仇’是氏族社会压倒一切的、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是人们共同认定的道德准则。”[14]有了这样共同理念的支撑,即使伍子胥与申包胥在立场上是敌对的,申包胥也能够理解并肯定伍子胥渴望复仇的心态。汤先生在文中还引用了其他文献作为旁证,如摩尔根《古代社会》提及的印第安部落具有“血亲复仇”风俗以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谈到的易洛魁人以血族复仇为义务等。按照人类发展的共性与惯性来讲,先秦时期楚国很有可能也存在着“血族复仇”的伦理观念。汤炳正先生的材料引证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这种认证方式较为迂回,其实先秦材料里有很多可以直接证明“血亲复仇”观念存在的材料。
《礼记·曲礼》有言:“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要求为人子弟需与自己父兄的仇人誓不两立,及时复仇才是应有的孝悌之道。《礼记·檀弓》中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孔子对待父母之仇的态度是极为强硬的,他提出为人子应不惜一切代价、随时做好为父母报仇的准备,即使没有携带武器也要毫不犹豫上前报仇雪恨。“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这类血债血偿的说法在《孟子·尽心下》亦有体现,甚至当时楚人对于血亲复仇的理念也是认同的。《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襄王因召与语,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15]可见在当时血族复仇乃是人们所普遍承认的神圣任务。
伍子胥的父亲兄长无端遭受楚平王杀害,为他们复仇正是伍子胥义不容辞的责任。申包胥在履行守卫楚国的职责同时,也能够理解伍子胥试图颠覆楚国的计划,于是看似矛盾的双方在“血族复仇”风气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达成了和解。
值得稍加补充的是,汤先生《渊研楼屈学存稿》中认为,“汉人对古人‘血族复仇’这一极其严肃的社会义务,已完全不理解”[16]、屈原诗歌中夸赞伍子胥所蕴含的社会意义“汉人似乎已经不甚了然”,这些言论恐怕有待商榷。事实上,即使是在汉代,人们对“血族复仇”也是相当熟悉的。司马迁《史记》中对伍子胥的评价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高度赞扬了伍子胥忍辱负重,终得报父兄大仇的坚韧心智,可见他对于这一风俗是了解认同的。近代以来,法律史专家们考证后得出的观点也与汤先生所言相悖。如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李隆献《复仇观的省察与诠释》等著作中均认为:在中国古代,血族复仇的习俗一直被视为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美德之一,且并未随着汉代以来法律的明令禁止而消亡,而是绵延不绝,直至明清仍然兴盛。对于复仇行为,古人也普遍抱有怜悯与赞扬的态度,即便法律有时也会网开一面。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重新考量《惜往日》《悲回风》诸篇中屈原对伍子胥的同情与赞美,似乎也就合乎情理,而不至于像先前一些学者们产生疑惑与误解了。
(三)双向选择的君臣关系
值得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上述讨论的是私人之间的一般复仇行为,但伍子胥的复仇具有特殊性,他针对的是君主楚平王,与复仇对象之间存在着阶级差异,以下对上,以臣对君,算得上是个人与国家层面之间的较量。这种复仇行为是否与一般的复仇行为是等值的呢?
在后世的伦理观念里,当私人恩怨与国家大义之间发生冲突需要取舍时,我们往往以大局为重,亲情排在次要位置,但在先秦时期却并非如此。
王元化先生《因伍子胥想起的》中就此着手加以阐发:“倘若根据后来的某种观念来判断,伍子胥不仅不忠,甚至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为什么春秋时代把他看作忠臣呢?是以他对吴王夫差来说的。这与后来对忠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我们对早期儒家道德规范并不理解,后人多以为孔孟倡导的是愚忠愚孝,以君主为本位,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孔孟的君臣之道是建立在互惠互等的双向关系上。”[17]
王元化先生关于孔孟君臣之道乃互惠互等的论述,先秦儒家文献中有不少例证。《论语·八佾篇》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了君臣之间的对应关系,臣子侍奉君主需要忠诚,但付出并不是单向的,君主对待臣子也需有礼节。《孟子·离娄下》也谈到君臣之间你来我往、彼此尊重的需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8]即使君主也需要遵循君主之道,如果没有做到,那也不能强求臣子一味遵循臣道:“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19]诸如此类的话语均反映了其时君臣之间双向选择的儒家理念,士、民对君主不满随时可以抽身离开,并不存在单方面的服从关系。
实际上,这些在我们如今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言论,在先秦时期各家学派中是普遍存在的,甚至连王元化先生以为“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的法家也曾认同此观念。《韩非子·安危》曾讽刺道“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20],即君主不以明主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却希望臣子能够像伍子胥一样忠心可靠,这就好像希望殷人都能够像正直谏言的比干那般不可能,言语间有对人主强烈的反讽意味。
(四)楚地对儒学思想的接纳
楚国虽僻处南鄙,向来被认为是蛮夷之地,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北方的儒家思想观念。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以观盛衰焉。”[21]这说明在先秦时期《诗三百》这部儒家经典常被当成外交辞令来使用,而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记载屈原在担任楚国三闾大夫、左徒等职务期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所以作为“外交官”的屈原从工作来讲完全有机会接触并受到儒家观念的濡染浸润,也肯定是对《诗经》这部儒家经典反复研习的。儒家思想对屈原及其作品有着深刻影响,郭沫若先生甚至评价屈原是“一位南方的儒者”:“屈原思想明显带着儒家的风貌,屈原的道德节目也和儒家所理想的别无二致。”[22]
近些年整理披露《郭店楚简》中有几段材料更进一步说明了楚地当时确然存在着把血亲观念凌驾于君臣关系之上的观念,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郭店楚简·语丛一》中谈到“君臣,朋友其择者也”,君臣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尊卑服从,而是像朋友一样的双向选择关系。《语丛三》中亦有所谓“所以异于父,君臣不相戴也,则可已”的说法与之呼应,君臣关系不同于父子之间生而注定、不能解脱的血缘关系,臣子对君主“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郭店楚简·六德》中“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更是明确将具有血缘基础的父子关系置于仅存义务的君臣关系之上。以上相关材料均说明,即使在楚地,如果血亲与君臣关系之间需要取舍时,时人也定以亲情为重。
四、结语
由此可见,屈赋中的伍子胥问题不应当被孤立地探讨,而应将之放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思想观念变化发展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关于伍子胥是否能够作为辨别《九章》中伪作的“重要内证”,在对各家言论抽丝剥茧、结合先秦文献多方比照印证中,我们终于寻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涉江》诸篇中谈及伍子胥时所饱含的轸恤追慕之情与先秦社会风俗、君臣观念并不抵牾,屈原与伍子胥之间也并非忠臣与逆臣的截然对立。或许《悲回风》《惜往日》等篇是否系后人伪作尚有探讨余地,但可以确定的是,辨伪者们提出伍子胥作为伪作“重要内证”的判断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