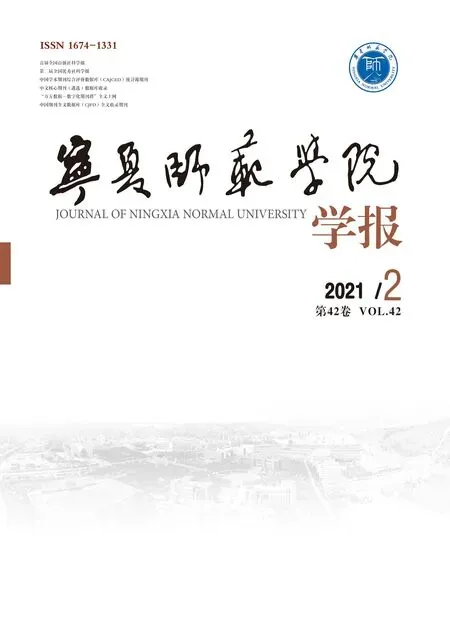生活仪式的文学书写
——以《去特伦顿和卡姆登的快乐旅程》为例
蒋贤萍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去特伦顿和卡姆登的快乐旅程》(The Happy Journey to Trenton and Camden,1931)(以下简称《快乐旅程》)是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的一部独幕剧,也是一部重要的仪式化戏剧,它不仅描写了家庭生活仪式,而且展现了社区生活仪式。剧中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没有震撼人心的事件发生,所有内容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经历的一段普通的假日旅行,或一场生活仪式。剧中引入了舞台经理这一角色,同时扮演着多个小角色,时而超然事外,时而投入其中,既是仪式的观察者,又是仪式的参与者。他指导戏剧行动的发展,旨在实现戏剧的道德目的。从戏剧一开始,舞台上的人物就通过虚拟的动作进行着哑剧式的表演:阿瑟弹着想象中的弹珠,柯比妈妈戴上想象中的帽子,人物走下想象中的楼梯等等。通过这样的呈现方式,怀尔德将仪式巧妙地融入其戏剧当中。人物不仅进行着仪式化的表演,整个戏剧表演仿佛变成一场盛大的仪式展演,而所有观众成为仪式的参与者,并从中获得心灵的启示和精神的升华。怀尔德运用表现主义手法和极简主义风格,以文学化的形式展现了人类生活的仪式,传递出对生活及仪式的深刻思考,旨在寻求仪式的复兴,重申仪式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价值。
一、家庭生活的仪式
《快乐旅程》主要展示的是在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驱车出行的一段旅程。柯比夫妇带着女儿卡罗琳和儿子阿瑟,离开他们在纽瓦克的家,前往新泽西州卡姆登,去看望已婚的女儿贝拉。旅途中他们有快乐的心情,也有争执的烦恼,有美好的相遇,也有悲伤的时刻。途中他们还遇到一支送葬的队伍,母亲想起在战争中牺牲的儿子。跟怀尔德的其他剧作一样,《快乐旅程》的内容非常简单,没有悲壮伟大的英雄人物,没有高潮迭起的故事情节,只是以朴素的语言,讲述了一段平淡无奇的旅程。
这部剧作聚焦于家庭生活中简单的快乐和痛苦,描写了那些通过习惯、陈词滥调和真挚情感来处理巨大损失的人,是一部简单朴素的作品,一部人物的研究,一部印象派的素描。它的兴趣不在于令人震撼的新发现,不在于柏拉图式的“回忆”……尽管这些都巧妙地隐藏在剧作家对剧中人物朴素的宗教虔诚和熟悉的家庭生活琐事的描写当中。[1](P259)
《快乐旅程》也是怀尔德的一部以极简主义的舞台为背景的戏剧,但它追求传统的线性情节,并没有对时间和空间进行任意切割。施罗德(Patricia R.Schroeder)甚至认为,它“展现了一个几乎和怀尔德所回避的现实主义舞台一样狭窄的世界景象”[2](P64)。舞台上没有布景,只摆放了四把椅子,象征汽车上的座位。想要深入了解戏剧的主题,观众需要调动其参与式想象力。正如剧作家在“作者笔记”中所说:“当观众合作式的想象力被激发出来以填补重要的背景,他们的同情式参与就最大程度地被调动起来。”[3](P84)
在这部剧作中,怀尔德揭示了这样的主题: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事件,也具有超出其表层意义的意义。这一主题产生于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表现方式之间的碰撞。为了超越无意义琐事的“表象”,怀尔德在事实的、具体的层面上摧毁了它的现实主义诉求,而是把行动放在道德的、哲学的或神学的层面上。[4](P68)剧中人物从一开始就做着普通的、微不足道的事情。幕启时,阿瑟在玩弹珠游戏,卡罗琳在和朋友聊天,柯比妈妈在戴帽子。人物对话没有任何张力,只是普通人朴素的日常对话。
驱车离开纽瓦克之后,柯比一家人沉浸在旅行的快乐当中。他们穿过开阔的田野,呼吸着野外新鲜的空气。孩子们对车窗外的事物充满好奇,提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柯比一家人的假日出行是一段生命的旅程,也是一场家庭生活的仪式展示,虽然平淡而琐碎,却充满温馨与爱意。然而,开心的旅程被一支送葬的队伍打断。送葬的队伍过去之后,柯比一家继续他们的快乐之旅,孩子们依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路边广告牌不断吸引着阿瑟的注意力,而美丽的田野风光让卡罗琳欣喜不已,她说“我喜欢这样的乡村风光”[3](P91),并请求妈妈经常带他们出来。妈妈也说新鲜的空气里“充满了海洋的气息”[3](P92)。当他们经过一座桥时,妈妈提醒埃尔默“小心开车”[3](P92)。当听到阿瑟说“厕所”一词时,妈妈认为他说话“太可怕了”,并不失时机地教育阿瑟,要学着“做个绅士”[3](P92)。作为道德核心的柯比妈妈,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孩子们的一言一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怀尔德向我们展示了家庭生活仪式被戏剧化的过程。
柯比妈妈是戏剧的核心,家庭的核心。她生活的全部仿佛就是为了全家人的平安和健康。当看到香烟广告牌上的漂亮女孩时,妈妈觉得有点像女儿贝拉,流露出一位母亲对孩子发自内心的爱。当阿瑟问妈妈能否再接一份《纽瓦克每日邮报》的工作时,妈妈坚决地回答说“不能”,因为“我听说他们让报童早上四点半就起床。即使能赚一百万美元,我儿子也不会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3](P92)认为他现在每星期四早上送的《星期六晚报》已经足够了。阿瑟非常沮丧,但妈妈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她不想让儿子“错过上帝赐予他的睡眠时间”[3](P92)。对于妈妈总是把“上帝”挂在嘴边的做法,阿瑟感到厌烦,讥讽地说:“我想她今天早上一定是收到他的来信了。”[3](P92)阿瑟的话更加激怒了妈妈,她生气地叫阿瑟马上下车离开,声称:“上帝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不会让任何人取笑她的。”[3](P92)母子之间不愉快的争吵是剧中出现的最激烈的一次矛盾冲突。柯比妈妈的道德意识非常强烈,使这部描写美国日常生活的剧作具有了浓厚的仪式化色彩。
保罗·利夫顿指出,这次旅程为柯比妈妈提供了“一个给孩子们指出道德真理的机会”[5](P21)。甚至在他们出发之前,妈妈的教导就已经无处不在。当阿瑟说他找不着帽子的时,妈妈说:“如果没有帽子,你就别想离开纽瓦克,你要想好了。我不会跟小混混一起出门的。”[3](P87)这表现出妈妈对孩子严格的要求。后来,妈妈看到卡罗琳的脸颊有点红,以为她化妆了,说:“如果你在脸上涂了什么东西,我会给你一巴掌。”[3](P55)卡罗琳羞愧地说:“我只是擦了擦,让它们变得红润点。所有的女孩高中的时候都会这么做。”[3](P55)而妈妈说,她“从没见过这么愚蠢的事情”[3](P88)。柯比妈妈作为传统的女性,对自己和家人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无视那些她笃信的价值观,而正是这些价值观将他们一家人联系在一起,并让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集体身份”[5](P21)。
尽管在柯比一家人的旅程中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更多的是简单而快乐的事情。当卡罗琳看到路边的热狗店时,说她饿了。于是,一家人停下来。埃尔默让阿瑟去买热狗,妈妈和卡罗琳则走出车子在附近闲步。当看到路边的野花,妈妈说她很喜欢,想要“带一些给贝拉”[3](P96)。母女俩一边唱歌,一边悠闲地散着步。当看到美丽的天空,妈妈显得很兴奋,感叹道:“天呐,看看天空,好吗!我很高兴我出生在新泽西。有人说这是美国最好的州。每个州都有其他州所没有的东西。”[3](P96)阿瑟买回热狗时,主动向妈妈道歉,并且因为懊悔而“泪流满面”[3](P95)。妈妈很快原谅了他,并适时地安慰他。看到孩子能够真诚地悔过,妈妈感到非常开心。看到日落,妈妈变得异常兴奋,说道:“快看夕阳。没有什么比夕阳更美的了。”[3](P96)似乎对妈妈来说,宇宙中的一切都充满了美好。在柯比一家人仪式化的快乐旅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蕴含于日常生活中的永恒真谛。
接下来是一段平静而美好的旅程。“一片梦幻般的寂静笼罩在他们头上”[3](P97)。卡罗琳紧紧地靠父亲坐着,妈妈则搂着阿瑟。之后是又一段再平常不过的家庭对话,阿瑟问妈妈美国有多少人,埃尔默说“有一亿两千六百万”[3](P97)。妈妈接着说:“他们都喜欢晚上开车出去,孩子们也在旁边”[3](P97),这让我们联想到千千万万的美国家庭,甚至世界上所有这样的家庭,在周末晴朗的午后,父母带着孩子愉快出游的画面。通过这样的设计,怀尔德将我们的视线引向埃尔默家庭之外更广阔的空间。从埃尔默一家人典型的生活仪式中,我们看到了所有人类温馨的生活画面。之后,孩子们开始唱起愉快的歌谣,爸爸妈妈也跟着一起唱。这或许是剧中最温暖的时刻,代表着所有家庭仪式般的美好瞬间。在这样的时刻,家人在你我之间坦诚相遇,彼此相拥,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
快到卡姆登时,妈妈叮嘱孩子们说,吃晚饭的时候要保持安静,因为贝拉刚做完一个大手术,还在恢复中。像所有天真的女孩一样,卡罗琳看到第一颗星星时非常激动,便开始许愿,并让妈妈也许愿。但家人清楚地知道,妈妈唯一的心愿就是家人的健康和幸福。当卡罗琳问妈妈,是不是贝拉的家比他们家更有钱时,妈妈的回答清晰地表明了她的价值观:“我不想听到任何人在我身边谈论有钱或没钱。如果人们不善良,他们多有钱我也不在乎。”[3](P99)并且认为她住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因为“我的丈夫和孩子住在那里”[3](P99)。对妈妈来说,只要有家人孩子在一起,就是最大的财富。妈妈为了使女儿能够明白她的话,“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卡罗琳看了一会儿,让这堂课深深地印在女儿心里”[3](P99)。简单的语言,简单的情感,构成了仪式化的简单生活。
一家人团聚时的场景是我们所有人都熟悉的画面,贝拉说弟弟妹妹长高了,妈妈风趣地说:“他们的衣服都快撑破了!”[3](P99)。贝拉“深情地吻了父亲一下”[3](P100)。从一家人相聚时平常的对话中,我们看到彼此之间的关爱与呵护。贝拉也一眼就看出爸爸看上去很劳累,妈妈也决心利用假期时间,好好让他休养。看到年迈的爸爸给自己送礼物,贝拉感到非常愧疚,说:“爸爸,应该是我给您买礼物才对。”[3](P100)爸爸回答说:“世界上只有一个露莉”[3](P100),这句台词道出了世界上所有父亲对孩子的疼爱之心。不管孩子长到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永远是需要呵护的孩子。听到爸爸的话,贝拉倍感温暖和感动。后来,贝拉含着泪说:“爸爸,我还活着,您高兴吗?”[3](P100)贝拉在分娩时差点失去生命,因此见到家人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尽管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和痛苦,但能够有家人的陪伴与安慰,仿佛一切都不再那么难以承受。
当舞台上只留下妈妈和贝拉母女二人,她们进行着大部分母女都会有的聊天。妈妈很高兴看到贝拉住进了漂亮的新房子,“有个很温馨的家”[3](P101)。贝拉也告诉妈妈,她丈夫对她十分照顾,她从医院回来时,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搬进去了,她什么都不用做。当贝拉说妈妈睡在新床上应该很舒服的时候,妈妈说:“我可以睡在一堆鞋子上,露莉!我睡觉没问题。”[3](P101)最朴素的语言,却道出母亲最善良的心意。妈妈更关心的是孩子的安危与健康,而不是自己。当贝拉告诉妈妈,自己分娩时婴儿“活了不到几分钟”,自己也差点失去生命,妈妈用她的方式安慰女儿:“上帝有最好的安排,亲爱的。上帝有最好的安排。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我们只需要继续向前,亲爱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3](P101)简单的对话流露出母亲对女儿真诚的关爱。妈妈朴素的信念支撑着她,也让她的家庭能够继续向前。
拉达维奇(David Radavich)认为,妈妈的语言听上去只是一些陈词滥调,“不足以抚慰真实的人的情感,因而彰显出其不足之处”[6](P143)。但正是这样朴素的语言和信仰,源于一位普通母亲虔诚的心灵和朴素的善良,使她能够在家庭遇到重大变故的时候,表现出异常坚强和勇敢的品质,成为家庭的核心支柱,从而给予家人真正的关心和慰藉,并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祈愿。其实,妈妈的话语表现出她面对生活中的悲伤与痛苦时所具有的勇气和智慧,正是这样的勇气和智慧才使她能够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然而,这并不表示她不会感到痛苦和悲伤,我们清晰地看到“她突然用手背擦拭脸颊”[3](P101),她只是不想让家人看到自己的脆弱和眼泪,不想让悲伤破坏了生活的节奏。这样的勇气,也曾激励了无数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
柯比一家人的假日出行命名为“快乐旅程”,但直到最后我们方才意识到,贝拉不仅仅是生病了,她还失去了尚未出世的孩子,她自己也差点失去生命。至此,我们发现“快乐旅程”的目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哀悼。尽管如此,怀尔德仍将其定义为“快乐旅程”,从中体现了剧作家对生活本质的深刻认识。他仿佛过滤了生命中所有的悲伤与痛苦,只留下“快乐”,因为在这段旅程中,有一家人彼此的呵护,有邻里之间真诚的关爱,还有新鲜的空气和美丽的夕阳。虽然贝拉失去了尚未出世的孩子,但至少她还“活着”,能够与家人团聚。于是,一切的悲伤都化作美丽的音符,融入“生活”这场盛大的仪式当中,成为历史的永恒。怀尔德将戏剧背景置于美国这片土地上,看似在强调“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仪式,但确切地说,他的创作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怀尔德来说,家庭并不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模棱两可的事实,而是一个更大家庭的象征,不受历史的限制。它同样是美国神话和人类发展的核心。[4](P143)
二、社区生活的仪式
在《快乐旅程》中,怀尔德除了描写家庭生活仪式之外,还呈现了社区生活仪式。在柯比一家人驱车前往卡姆登之前,柯比太太跟邻里之间琐碎的对话聊天和漫长的告别仪式便是最好的例证。在这段情境中,邻居太太的角色都是由舞台经理扮演的。柯比妈妈走到虚拟的窗户前,跟施瓦茨太太和霍布迈耶太太打招呼。
妈妈:哦,施瓦茨太太!
舞台经理(对照剧本):我来了,柯比太太。你要走了吗?
妈妈:我想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孩子怎么样了?
舞台经理:她现在没事了。我们拍了拍她的背,她就吐了出来。
妈妈:那太好了。——嗯,如果你能在早上和晚上给猫喂一碟牛奶,施瓦茨太太,我会非常感激你的。——哦,下午好,霍布迈耶太太!
舞台经理:下午好,柯比太太,听说你要走了。
妈妈(谦虚地):哦,就去三天,霍布迈耶太太,去卡姆登看看我的已婚女儿贝拉。埃尔默年初在洗衣店拿到了休假周,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3](P86-87)
柯比妈妈惦记着施瓦茨太太的孩子,还请施瓦茨太太她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帮她照看一下猫,早晚给猫喂点牛奶。随后,霍布迈耶太太也加入她们的对话中。柯比太太告诉她就去三天,去卡姆登看看女儿贝拉,因为她不久前病得很重。柯比太太的话语中透露出她对女儿的极度牵挂:“我只想去看看孩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如果不去看她,我心里就不好受。”[3](P87)聊天的同时,柯比妈妈也让站在旁边的卡罗琳跟霍布迈耶太太说下午好,而霍布迈耶太太贴心地说:“等你们走了我再打这些地毯,因为我不想呛着你们。”[3](P87)柯比妈妈再次叮嘱施瓦茨太太给猫喂牛奶的事,并告诉她“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后门的钥匙就挂在冰箱旁边。”[3](P87)
对于妈妈说“钥匙就挂在冰箱旁边”一事,卡罗琳和阿瑟都觉得非常尴尬,生怕“所有人都听到”[3](P87),偷偷扯她的衣服,想阻止她不要那么大声。而妈妈故意“大声地悄悄说”[3](P87):“后门的钥匙我会挂在冰箱旁边,纱门我会开着的。”[3](P87)邻里之间的对话并没有多少重要的话题,但表现出彼此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友好氛围。而妈妈“大声地悄悄说”,既表现出她对孩子们建议的尊重,又表现出她对邻里的信任,同时也体现了她幽默风趣的一面。在这段简单朴素的对话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邻里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和互相关爱,呈现了一幅温馨和谐的社区生活画面,其中人与人之间保持着最原始、最纯朴的情感纽带,或许这是怀尔德认为我们人类应该有的社区生活状态。
邻里之间简单的问候和对话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仪式化行为,怀尔德将其忠实地呈现在舞台上,旨在强调这种生活仪式在社区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在此,仪式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能够强化群体的凝聚力。这种社会功能尤其体现在宗教仪式方面,其中集体认同感涉及的范围要大得多。在《快乐旅程》中,柯比妈妈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化倾向,这种倾向对于家庭凝聚力及集体身份的确认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怀尔德在其创作中将戏剧和仪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除了对邻里的信任和友好,对孩子的呵护,柯比妈妈对丈夫也表现出十分的信任。在她眼里,埃尔默“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3](P87)。一家人出发前,埃尔默特意去车库最后检查了一下车子,以确保一切正常。妈妈对丈夫的表现非常满意:“我很高兴你这么做。我不想在任何地方出现任何故障。”[3](P88)
埃尔默的性格和语言风格与柯比妈妈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说话声音总是那么平静,总是略显焦急地透过眼镜向外看”[3](P88)。如果说妈妈总是唠唠叨叨,对家人事无巨细地关照,那么埃尔默更多地表现出从容和稳重,虽然言语不多,但处处表现出对家人的呵护。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们走出‘门厅’,迈着小步表示下楼梯,来到街上。”[3](P88)之后是跟邻居冗长的道别,以至于“整条街的人都在说再见”[3](P89)。对于这样平淡无奇的场景,或许不会再有哪个剧作家会表现出任何的兴趣。但怀尔德恰恰相反,他在这些平凡琐事当中发现了人类生活的真谛,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发现了朴素的美德和真挚的情感。阿瑟提醒爸爸不要从他的学校那边过,因为他怕被老师看到,妈妈回答说:“我才不在乎他是否真的会看到我们。我想我可以带孩子们离开学校一天而不必躲躲藏藏。”[3](P89)表现出她的坦然和真诚,并不觉得带孩子出去度假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
怀尔德通过描写家人之间的关爱和邻里之间的友好,勾勒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画面,而这种简单的生活仪式是社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仪式也是人们联系集体、记忆或建构神话般的过去、建立社会团结、形成或维持社区的一种方式。有些仪式是阈限的,存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之间或之外;其他仪式则编织成普通的生活。在其阈限阶段,仪式表演产生共态,这是一种参与者之间的感觉:意识到自己是大于或超出他们个体的东西的一部分。”[7](P1)在更大的范围内,仪式在社会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能够有效地帮助解决危机。如果说社会戏剧是“大制作”,那么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有时很难激起涟漪。我们执行起床仪式、进餐仪式、问候仪式、离别仪式等,都是为了平稳和缓和正在进行的社会生活。但在怀尔德的戏剧中,他将这样简单的生活仪式前景化,使之具有了更加崇高的美学意义。仪式就像语言和音乐一样,是构成人类生活的要素。不同民族的文化档案揭示了仪式的持久性和普遍性。考古学研究发现,仪式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已存在。生物学研究则表明,仪式化是动物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有助于其进化过程。因此,对仪式的思考就是对人类生活的反思,对社会文化的反思。
埃尔默开着雪佛兰,带着妻子孩子开始前往卡姆登的快乐旅程,一路上会跟认识的人点头示意,进一步揭示了邻里之间的温情相待。在他们的旅程中,遇到一支送葬的队伍。这是剧中唯一一次描写严肃的过渡仪式,与日常生活仪式形成鲜明的对照。爸爸摘下帽子以示对死者的敬意,妈妈也让阿瑟照爸爸的样子摘下帽子。“他们都身体前倾,默默地看着葬礼,顿时变得非常庄重。”[3](P99)在怀尔德的文字引导下,不仅剧中人物观看并感受了这场葬礼仪式,而且作为观众也能想象性地参与这场庄严的仪式,并引发对死亡这个永恒宇宙法则的思考。正如柯比妈妈那样,葬礼让她想起了在战场上失去生命的儿子:“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经历过的葬礼,是吗?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好孩子哈罗德。他为国家献出了生命,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3](P90)接着,妈妈一边擦拭眼泪,一边感慨地说:“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都会有几分钟的时间堵塞交通的”[3](P90)。妈妈关于死亡的暗示性话语让孩子们感觉很不舒服,但她显得非常坦然,对这个问题毫不忌讳,也希望家人都能够像她一样“准备好”面临死亡的到来。之后,她把手放在丈夫的肩膀上,说:“我祈祷能先走,埃尔默。”[3](P90)埃尔默会意并安慰地“摸了摸她的手”[3](P90)。即使是一场路遇的葬礼,柯比一家人也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揭示了社区生活中重要的仪式化行为。
在妈妈和阿瑟因为“上帝”的话题发生激烈的争吵之后,一家人在车上保持沉默,直到他们来到加油站。埃尔默想要给水箱加点水。这时舞台经理扮演的是车库工人的角色。根据舞台指示词,在这个场景中,舞台经理“把剧本放在一边,认真地扮演角色”[3](P93)。他询问埃尔默要不要给车加油或加气,埃尔默说不需要,他在纽瓦克刚加满油。在加水的过程中,妈妈跟舞台经理扮演的车库工人进行了一段真诚友好的对话。当听说他们要去卡姆登,舞台经理说:“卡姆登是个漂亮的小镇”[3](P94),妈妈告诉他自己的女儿贝拉就住在卡姆登,而且非常喜欢那里。舞台经理说他也很喜欢,因为他出生在卡姆登附近。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舞台经理告诉柯比太太,他的父母已经不住在那里:“我父亲把农场卖掉了,他们在上面建了个工厂。所以他们搬到了费城。”[3](P94)柯比太太接着说,贝拉的丈夫在电话公司工作。这样的对话再一次令卡罗琳十分尴尬,便示意妈妈不要继续说了。但妈妈执意说:“别戳我了,卡罗琳!”[3](P94)卡罗琳认为妈妈不应该把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但妈妈坚持说:“世界上到处都是好人”[3](P95),也认为自己的方式并没有不合适,而且不无同情地说:“我看他脸色有点苍白。我真希望能给他做几天饭。他母亲住在费城,我想他一定是在那些可怕的希腊饭馆吃饭的。”[3](P95)
尽管妈妈关于“到处都是好人”的观点略带讽刺的意味,但字里行间表现出她对陌生人由衷的关爱。毫无疑问,一方面,剧中柯比妈妈是所有家庭的母亲形象;另一方面,柯比妈妈又是家庭信仰和爱的纽带。25年来她“每天都要做三顿饭”[3](P91),时刻关注着每个家庭成员的吃穿用度和行为举止。“谦虚”一词是剧中描写妈妈时最常使用的词汇,强调了她性格当中善良美好的品质。妈妈不仅对家人百般照顾呵护,对邻居友好善良,而且对陌生人也充满信任和关爱。甚至对路边的小狗也富有爱心。当看到路上跑着的小狗时,妈妈提醒埃尔默别撞了它,还说“它看上去有点瘦,真的需要好好喂喂。”[3](P92)或许这就是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能使然,正如怀尔德在“作者笔记”中所说:“这部戏剧是对一位普通的美国母亲的致敬,她本能地把孩子抚养大,就像鸟儿筑巢一样,她的力量在于,无论生活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她都努力保持一种向前看的勇气和力量。”[3](P84-85)
妈妈是《快乐旅程》中的中心人物,她在家里有着统治性的地位,扮演着一个旧约式的女性人物形象,略有讽刺的意味,却不乏真诚和善良。妈妈关于“堵塞交通”的感叹听上去有点可笑,但其中充满深刻的哲理,是剧作家通过人物之口表达了对生活、对生命的真切感受。即使孩子们提醒妈妈,因为她的表现使得“大家都在笑话你”[3](P91),妈妈也毫不在乎,表现出她对生活或生命的认识有着坚定的信念。柯比妈妈身上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这在她的言谈举止间表现得非常深刻。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怀尔德试图将仪式文学化或戏剧化。在仪式的展演过程中,我们也会退一步思考,也会阅读或书写关于仪式的问题。因此,仪式是一种思考和认识的方式。我们对于仪式的认知和感受不仅在仪式本身中获得,而且通过文本和其他媒介形成。[7](P3)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怀尔德的戏剧文本是文学化的仪式。如果说剧中人物是在舞台上“执行”其生活仪式,那么作为观众是在仪式展演中感受仪式,并形成对仪式的认知。
三、桑顿·怀尔德与仪式化书写
人们每天都会经历许多仪式,包括宗教仪式、日常生活仪式、政治仪式、商业仪式等,甚至动物也有仪式。仪式通常分为两大类,神圣的和世俗的。神圣的仪式是那些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仪式,而世俗的仪式是指与日常生活等非宗教性质的活动有关的仪式。什么是仪式?“广义地说,仪式是指一个或一系列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产生功效……由于注重功效,仪式区别于许多表演,因为它们以积极参与为中心,一个个人或一个群体正在‘执行’而不是‘呈现’某种东西。正是通过这种活动,一种信仰得以确认或改变将要发生。”[8](P243)仪式与表演有着多方面的共同点,但在仪式中,演员与观众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成为一种超戏剧(paratheatre),“演员”不仅仅是在“扮演”角色,更多的是在“阐释”角色。怀尔德的戏剧正是这样,演员以仪式化的表演,向观众阐释怀尔德想要传递的思想和主题,而观众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参与其中,共同实现仪式化的戏剧或戏剧化的仪式。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种信仰得以确认或改变得以发生,这才是怀尔德想要实现的真正目标。
在《快乐旅程》中,舞台经理对舞台进行设置,并适时地阐释戏剧行动,展示了一幅极简主义的家庭生活画面,但舞台上并不存在生活片段式的真实呈现,因为这种真实性在戏剧一开始就遭到破坏。演员们进行着哑剧式的表演,舞台上没有布景,没有道具。通过这种方法,主题目的和戏剧目的相互融合,成为“永恒的行为”(Act in Eternity)[4](P69)。观众不断地被提醒,他们看到的是戏剧,而不是真实的生活。生活是被解释的,而不是表现为现实。但不无悖论的是,到卡姆登的旅程是一段快乐的旅程,因为这些看似不重要的事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怀尔德暗示,这些事件在宇宙哲学层面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怀尔德剧作中具体的仪式性瞬间,在广阔的宇宙背景下,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快乐旅程》中人物的语言具有典型的周日出游式的风格,而人物的动作对观众来说具有陌生化的效果,迫使其在脑海中填补真实的旅行细节及沿途风景。在这部剧作中,怀尔德选择了一种低级模仿模式,这是他的朴素风格中最显著的语言特征。拉达维奇(David Radavich)在怀尔德的语言中发现了浓烈的中西部色彩,但他的语言选择是考虑到中西部环境有更多的普遍性元素。换言之,中西部戏剧或小说“往往侧重于‘通常’或‘一般’的言语和行为,并考察公共语境”[6](P46-47)。拉达维奇的发现适用于分析怀尔德剧作中仪式化的朴素风格。由于仪式叙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普遍性,怀尔德策略性地选择了一种更具有典型性的语言模式。
怀尔德通过选择“典型”的语言,进一步强调了其戏剧普遍的仪式价值,从而将戏剧和仪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更加丰富了美国戏剧的传统。如果说,“仪式是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探究我们的生物或动物存在和我们的文化存在”[7](P20),那么透过怀尔德的仪式书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从而强化我们与周围世界的和谐共处。正如巴里·斯蒂芬森所说:“仪式化有一个功能或目的,它增加了物种生存的可能性。这种思考仪式的功能方法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其中,人们普遍认为,鉴于仪式的普遍性及其集体性、公共性,它必须服务于某种有用的社会目的。仪式是做什么的?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提出,仪式(不论是世俗仪式还是宗教仪式)能够将不同的群体联系在一起,通过产生和维持意义、目的和价值的秩序来确保它们的和谐运作。”[7](P38)自从宗教改革之后,整个西方世界便开始了去仪式化的过程,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这种去仪式化的进程不断持续,或许这正是令怀尔德痛心之处,是他试图复兴仪式化书写的原因所在。
怀尔德的广阔视野归因于他关于不朽和永恒的观念,以及对各个时代人类行为重复性的认识。怀尔德认为,美国人生活在一种无限当中,意识到广袤的距离和无数的存在,因为他从对未来的信念中获得了激励他的勇气。因此,他们倾向于在与整体的关系中考察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的整体即“所有一切、所有地方、所有时间”。[9](P188)怀尔德描述的是普遍的人性,而不仅仅是美国人。正是在这些美国人生活的仪式化书写中,我们看到了整个人类的生活仪式,或者说是整个人类应有的生活仪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仪式是无法避免的。对某些人或某些社会群体而言,特定的仪式可能具有重要的价值。即使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仪式性的存在,也不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以仪式为基础的,但仪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仪式是塑造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仪式和庆典。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这些仪式和庆典或是振奋人心的,或是枯燥乏味的;或是削弱性的,或是力量性的;或是创造性的,或毁灭性的。思考仪式就是探索它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的地位、力量和潜力。”[7](P1)仪式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怀尔德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陌生化书写,让我们重新感知仪式的力量。
在《快乐旅程》中,怀尔德肯定了美国人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道德价值,其目的是使模糊的日常事务变得清晰透明,以期有新的发现。剧作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为基础,而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当中却蕴含着深刻的真理。人物生活中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呈现的,但剧作家通过非现实主义的舞台技术,将这些日常的事件与广阔的宇宙学和形而上学联系起来,从而延伸并扩展了戏剧的主题思想。怀尔德的戏剧成功地将观众纳入其中,成为其仪式化展演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柯比一家人,还是观众,从一开始就踏上了一段“快乐旅程”,并在旅程中经历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事件,并且感受到转变性的能量。如果说柯比一家人经历了一场地理空间的“快乐旅程”,那么观众则经历了一场心灵空间的旅行,使其对生活和生命有了更新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观众也是经历了一场审美的过渡仪式。正如李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所言:“我将那些把旅程作为目标的阈限体验视为审美的,而将那些把旅程作为达到‘另一个’目标的阈限体验视为非审美的。这些目标包括社会认可的地位变化;创造赢家、输家或社区;使权力的合法化;建立社会纽带;娱乐。也就是说,审美经验关注的是阈限体验,关注过程本身;过渡过程本身就已经构成了经验。非审美的阈限体验则关注向某物的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转变。”[10](P199)
怀尔德的仪式化叙事不是作者精湛技艺的自我炫耀,而是对动荡的20世纪的一种对抗。在20世纪,人们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信仰的基础变得岌岌可危。为了完成理想主义的使命,怀尔德不得不转向仪式化的书写,以弥补信仰的缺失,拯救因物质欲望而迷失的灵魂。在艺术的层面上,怀尔德试图通过激发观众的想象力,重振美国戏剧艺术的生命力,这就是怀尔德艺术的价值所在。正如哈钦斯(Robert M.Hutchins)在怀尔德的追悼会上所说:“我们的敌人是庸俗、狭隘和偏执。教育的目标,实际上也是整个生命的目标,就是想象力的开发。这样才有可能产生破窗思想。”[11](P236-237)哈钦斯的话概括了怀尔德留给美国文学的重要遗产,即他在那个时代作为人文主义批评家的角色。
怀尔德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作为一个剧作家所肩负的重要使命,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什么,而仪式化的书写成为他突破传统的重要策略,因为它能够“从历史废墟中拯救那些有可能消失的东西”[12](P68)。怀尔德选择成为一个自觉的仪式作家,其使命是寻找“超越现在的意义”和“使之发声并书写其意义”[13](P6-7)。如果仪式意味着表象与真实之间的分歧,怀尔德当然相信真实寓于过去那些古老而永恒的仪式当中,而现在的人们应该重拾这些被遗忘的东西。正如欧文斯(Craig Owens)所指出的,现代寓言家的两个最基本的冲动是“对遥远过去的信念和现在对其进行救赎的渴望”[12](P68),这同样适合于怀尔德仪式化的书写。怀尔德没有逃避过去,而是呼吁人们,必须回顾过去,并观照现在,寻找过去与现在之间共享的循环模式,而仪式化的书写成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座桥梁,得以使观众/读者在这两种纬度的时空里自由穿梭。
怀尔德的目标并不是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而是要消除外部障碍,旨在促进戏剧行动中的积极投入。此外,怀尔德的集体思想或群体意识与阶级意识毫无关系。事实上,怀尔德的集体通常具有一种无阶级的特征,布莱希特会批评这种无阶级性是非历史的。正是这种集体概念超越社会差异,并将个人与跨历史进程联系起来的能力,对怀尔德具有更大的吸引力。[14](P97-98)
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认为,没有仪式就没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意义、目的和真理一直属于世界宗教的范畴。在现代社会,科学、艺术、大众文化等都具有类似的替代功能。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将这一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仪式不仅是人类众多有意义的活动之一,而且是创造意义系统的原始的和主要的手段,是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生命的源泉。在杜尔凯姆的传统中,一群人通过共同经历神圣的事物、思想或信仰而成为一个社会,而这些神圣的事物、思想或信仰具有重要的价值。拉帕波特认为,围绕着共同神圣感的人最好是通过仪式联系起来,也只有通过仪式才能够联系起来。通过相互分享和相对不变的表演,仪式产生一种永恒、持久、稳固、确定、神圣乃至真理的感觉,一种对世界的普遍姿态和体验,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7](P42)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怀尔德创造的仪式化戏剧更是继承了仪式的重要社会功能。在他创造的仪式化的戏剧或戏剧化的仪式中,我们感受到一种集体的力量,并且产生一种神圣的信仰,那是对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的认可和尊敬。正如谢克纳所说,戏剧能使观众的世界观发生改变。[15](P193)
怀尔德崇尚的是人文主义的道德价值。他不仅肯定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而且肯定美国民主的尊严和价值。他或许是当时美国人文主义价值最强有力的代言人,而这种人文主义价值也是美国由以建立的基础。承认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遗忘了这些价值,并不否认这些价值的有效性,也不否认试图在国民意识中复兴这些价值的重要意义。怀尔德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他描写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也是为他们而写作。尽管他有时会陷入说教主义的泥沼,但他为人类最优秀、最持久的价值赋予了新的表达,使他的作品拥有了特殊的生命力。尽管他的作品没有一些评论家希望的那么深奥,但在许多当代流行小说和戏剧悄然从书架上消失很久之后,他的作品仍将继续给广大读者和观众带来乐趣和启发。[4](P145)正如谢克纳所说:“事件就是仪式。当事件结束的时候,新人都获得成长,所有的人都在一起。”[15](P99)怀尔德的戏剧仿佛就是一种仪式的展演,当戏剧结束的时候,观众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启发,获得对生活和生命重新认知。
四、结语
在《快乐旅程》中,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但剧中揭示的朴素的人性使其成为一部感人至深的杰出作品。怀尔德创造了一种循环性的时间观。他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在他包罗万象的哲学中,不论是最强大的生命形式还是最卑微的生命形式,怀尔德都赋予他们以尊严。[9](P189)几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怀尔德都在强调每一个当下时刻、每一个选择的重要性,因为它决定着尚未获得认可的历史模式。他在表达这一主题时,使用的技巧无论是历史时代的交融、舞台时间的非历时性呈现,还是在一个非地域化的、非边界化的舞台上呈现事件,它总是试图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事物中找出某种崇高的价值,以抗衡那些看似要剥夺其所有尊严的荒谬行径。当我们在观看怀尔德的戏剧时,总会意识到现在时刻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什么将成为过去,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怀尔德的戏剧能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朴素的语言和朴素的舞台,却具有无法抗拒的仪式化力量,深深地触动观众的心灵。这正是怀尔德仪式化戏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