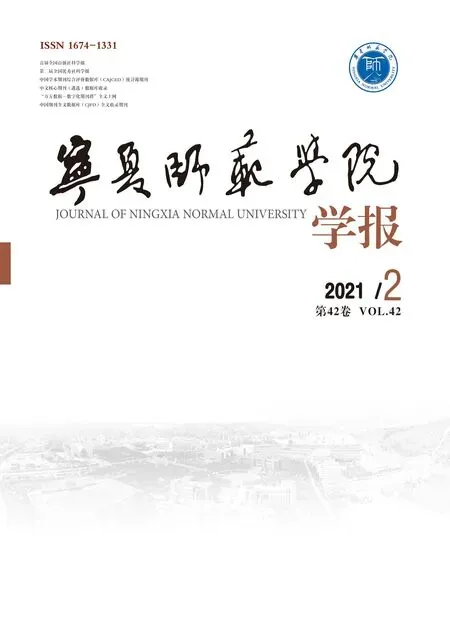文献所见西夏陵选址问题探析
孔德翊,张红英
(1.宁夏文物保护中心,宁夏 银川 750021;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21)
西夏陵是西夏王朝(1038-1227 年)历代统治者的陵墓群,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郊约 35 公里的贺兰山东麓。西夏陵约建于公元 11—13 世纪,陵区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及黄河,地势西高东低,环境开阔。陵区现存9座帝陵陵园、253座陪葬墓、1 处大型建筑群遗址和十余座砖瓦窑址,分布范围约 50 平方公里。[1](P1)整个陵区沿贺兰山东麓南北向次第布列,整体范围呈南北狭长状,规模宏伟。随着西夏陵考古发掘工作不断推进,西夏陵选址问题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目前,除《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西夏书事》《嘉靖宁夏新志》琐碎的记述外,还有一系列相关研究文献,如许成、杜玉冰的《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韩小忙的 《西夏王陵》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和《西夏六号陵》(科学出版社,2013),牛达生的《西夏考古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等,这些成果均对西夏陵的选址、布局和陵寝制度进行了初步探析。此外,孟凡人、余军、彭向前、杨浣等先生也对西夏陵选址因素、陵园构成、布局特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笔者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对西夏陵选址问题进行专门探究,以求教于学界。
一、陵随都建
在中国文化中,陵墓不仅是一个人生命最终的归宿,也是生命进入彼岸世界的生活场所。秦汉以来,在“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影响下,无论平民还是帝王,建造与自身地位相称的陵墓是其生活的必需。作为统治一方的帝王,其陵墓的选择和修建,被看作关乎国运的大事,在帝陵选址中,显得尤为神圣和庄重。一般来说,帝陵依附于国都而建是中国古代帝陵选址的基本传统,国都不仅是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国家的祭祀和礼仪中心。西夏陵在选址中也是如此,帝陵紧紧依附都城兴庆府,与都城遥相呼应。从新石器晚期开始,人们就开始在居住区周围选择墓葬区域。[2](P12)夏商周时期,随着王权强化和丧葬礼制的完备,以都城为中心的帝陵选址方式成为古代帝陵选址的普遍做法。无论是夏都二里头还是商都殷墟,附近都发现了一系列高等级墓葬,其中不乏王侯级大墓。春秋战国时期,都城与帝陵之间关系更加紧密,在此背景下出现了“陵墓若都邑”的观念。“陵墓若都邑”不仅意味着帝陵在选址上与都城相联系,在空间和布局上都与都城存在紧密联系。这一时期的王陵,或建于都城之内,如山东省发现的姜齐王墓;[3]或建于都城之外,如甘肃礼县的秦公墓等;[4]但总体上都是依附于都城而建。
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建立伴随着礼仪和制度的高度统一,以都城为中心选址建陵方式继续沿用。秦人的大型陵墓从西垂、雍城、毕陌到芷阳陵区,是紧跟其国都从西垂、雍城、栎阳到咸阳迁徙而选定的。秦始皇陵依然如此,在离秦朝国都咸阳不足50公里处选址。可见依都城而选址成为秦帝陵选址的普遍方式。汉承秦制,西汉帝陵的选址依然如此。从选址位置来看,西汉十一陵选择在汉长安城附近的咸阳原上,帝陵与都城之间距离与秦朝相比更加接近都城。焦南峰先生指出,在空间布局上,汉帝陵是“陵墓若都邑”理念的具体实践。[5]东汉时期,帝陵依然围绕都城洛阳北部和南部而建,形成了东汉帝陵的两大陵域。《帝王世纪》记述,除汉献帝陵外,洛阳西北部分布着5座帝陵,洛阳东南部分布着6座帝陵。其中光武帝原陵“东南去洛阳十五里”,明帝显节陵“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章帝敬陵“去洛阳三十九里”,和帝慎陵“去洛阳四十一里”,殇帝康陵“去洛阳四十八里”,安帝恭陵“去洛阳十五里”,顺帝宪陵“去洛阳十五里”,冲帝怀陵“西北去洛阳十五里”,质帝静陵“去洛阳三十二里”,桓帝宣陵“去洛阳三十里”,灵帝文陵“在洛阳西北二十里”。从文献记述来看,东汉诸帝陵仍然以国都为中心进行选址,帝陵与都城之间距离与更加接近。
唐朝建立后,高祖李渊开创了“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的原则,在之后的诸帝陵选址建造中,除昭宗和陵和哀宗温陵外,都选择在长安城较近的关中地区。从唐代诸帝陵选址实践来看,均以帝都长安为中心。葬还长安甚至成为部分皇帝的夙愿,如唐高宗晚年表现出“得还长安,死亦无恨”的强烈意望。不仅如此,据《全唐文》记述,在其子李宏丧事安排上,他表示“意欲还京卜葬,冀得近侍昭陵”。[6](P186)由此可见,陵随都建在唐代成为普遍观念被皇室所接受。
唐末藩镇出身的党项拓跋氏,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吸收和借鉴唐宋文化,建立与宋、辽长期并立的割据政权。作为割据一方的统治者,建造与自身地位相对等的陵墓是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在陵墓选址中,一方面积极吸收中原王朝帝陵选址的传统,另一方面沿袭了自身民族传统中的造陵文化,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兼容并蓄、特色鲜明的西夏陵制。从西夏陵选址来看,陵区选择在西夏都城兴庆府以西的贺兰山附近,与都城兴庆府紧密相依,陵区与都城之间相距35公里。
二、风水观念
风水观念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唐宋时期,迷信风水之风更甚于前朝,以《秘葬经》《地理新书》为代表的风水理论著作相继问世,致使官方和民间争相效法。无论帝王陵寝还是平民墓葬,大都依据行风水观念相山川岗阜之形势。作为长期受唐宋文化影响的西夏政权,在帝陵选址中必然受到风水思想的影响。从西夏陵修筑实践来看,墓葬的选址、与环境紧密联系,将传统的风水观念融入具体的实践之中。
成势于山。按照传统风水观念,帝陵选址第一步首先要勘察观势。观势即观察山势走向,地势环境。《葬书》认为“平地之势,其稍高地坦夷广阔,相牵相连”即为一种龙势。按照风水形势说中“积形成势”和“聚巧形而展势”观点,西夏陵与贺兰山在空间上远近组合,达到“积而成势”,进而“聚而展势”。观势的目的就是寻找所谓的“龙脉”,《管氏地理指蒙》云“指山为龙兮,象形势之腾伏”,“借龙之全体,以喻夫山之形真”。通常来讲“龙脉”即山脉。理想状态下的帝王陵寝要求所处山脉横向分枝展叶,舒展开阔,起伏顿挫有致,形成屏障之势,视觉上给人一种“重峦叠嶂,秀丽森然”。从现实选址来看,西夏陵依贺兰山而建,《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贺兰山“在城西六十里。峰峦苍翠,崖壁险削,延亘五百余里,边防倚以为固。”[7](P12)在整体视觉上由远及近的观察,西夏陵通过贺兰山山势地形,以庞大的、雄伟挺拔的空间作为背景,形成“形乘势来”和“形以势得”状态。在具体细节方面,帝陵周围环境要“屏障罗列、远近有致”,意味着山势要有环绕成形,叠嶂有致,主次有序。对照西夏陵周边环境,贺兰山环绕着西夏陵,南北绵延250多公里,呈北偏东30度左右走向,海拔在2000—2800米之间,最高峰3556米。按自然地理特征可将贺兰山分为北、中、南三段,中段山势雄伟陡峭。西夏陵位于中段东麓,地势高亢开阔,东临平原,西高东低,山高险峻,连绵相依,这种景象象征着国运绵长。与此同时,西夏陵周边众山环绕却又不封闭,山峰对称形成主次有序的状态,藏聚生气,这种状态恰恰与传统风水原则相吻合,呈现出一种“驻远势以环形”状态。
聚气于水。水为风水所重在于水与整个环境体系息息相关,造就了自然界的勃勃生机,因此水的地位举足轻重。《管子·水地》云:“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也”。所谓“风水”,就是将水的功用利害考虑到整个大环境中。传统的风水观认为“吉地不可无水”,若无水,则算不上一处吉地。因此,出现“未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和“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的观念。《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西夏陵整个陵区选择在“黄河绕其东,贺兰耸其西。西北以山为固,东南以河为险。黄河襟带东南,贺兰蹲跱西北。背山面河,四塞险固。西据贺兰之雄,东据黄河之险”环境之中[7](P10),在整体环境中符合“得水为上”的风水观。众所周知,黄河在上游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是风水观念中忌讳的“直冲走窜,激湍陡泻”状态,不宜于帝陵选址。而黄河进入银川平原后,蜿蜒曲折,平静缓流,呈“来宜曲水向我,去宜盘旋顾恋”状态,符合“选址河曲”的理念,同时也避免了雨季黄河涨水冲刷,破坏帝陵神圣肃穆的状态。西夏陵选址通过贺兰山与黄河一静一动的组合,动静结合,山环水绕,交相辉映,达到将天地之灵气汇聚于此地,实现 “气感而应,鬼福及人”和“反气入骨,以荫所生”,荫及后世的目的。
草木荫护。“草木郁茂,吉气相随”,可见地表环境也是古代风水观念中吉凶结果的影响因素。古人认为,“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地表裸露,草木不生的山,在风水观念中则不能算吉地,这是源于山不郁葱茂盛,则表明当地生气不通畅所致。隋唐时期,贺兰山一带水草茂盛,树木成荫。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駮马”。[8](P326)至明代,贺兰山依然“山多松,堪栋梁之用,夏城官私庐舍咸赖以用”[9](P45)。足见贺兰山一直草木茂盛,山体被林木所覆盖。周围“翠峰森列,峻极于天”。山中主要树种以松树为主,这种树木四季常青,郁郁葱葱,色泽油油,同时又遮挡沟壑,阻挡风沙,巩固水土,与山体浑然一体,景色宜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所谓“生气自然”。
三、个人因素
在中国古代,帝王个人的喜好也影响着帝陵选址。秦汉以来,随着集权政治的发展,皇帝个人意志对各项政治活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以秦始皇为例,从其周围地形地貌和地下水位等综合因素分析,有学者认为秦始皇陵选址是一个错误的选择。[10](P45)然而,规模宏大、设计复杂的秦始皇陵却依然能继续修建下去,与“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的个人因素有着密切关系。至唐宋,帝王个人因素依然影响着帝陵选址。唐太宗在其昭陵选址中,《唐会要》记载:“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志)”。[11](P45)正是由于太宗皇帝个人对九嵕山喜好,在其陵址选择中,九嵕山成为“朕之本志,亦复如此”,昭陵最终选于九嵕山中。北宋皇陵选址中,皇帝个人喜好直接决定了帝陵位置选择。《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拜谒安陵,“既而至阙台,西北向发鸣镝,指其所,曰:‘我后当葬此’”[12](P367)。太祖最终遵从自己个人意愿,将陵址选择在了巩县。
西夏陵在陵址选择中,统治者的个人喜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陵址最终方位。《西夏书事》记载,“继迁居夏州,修复寝庙,抚绥宗党,举族以安。及得灵武,爱其山川形胜,谋徙都之”。可见,世居夏州的党项统治者一直对灵州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正是由于“爱其山川形胜”,由此产生了徙都之念。李继迁定都灵州地区的理由也十分充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询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游,扼西睡要害,若缮城浚旅,练兵积粟,一旦纵横西出,关中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藕可限哉!’遂令继缓与牙将李知白等督众立宗庙演置官衙,攀宗族,建都焉。”正是基于对灵州地区地理和人文环境的深刻认识,李继迁决定将统治中心由夏州移往灵州,而当时灵州之地,“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也确实适合党项族的发展。正是基于李继迁对灵州之地的特殊感情,最终将灵州地区选择为西夏统治者的陵区,为之后西夏陵区扩展奠定了基础。
到李德明时期,对灵州地区地理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鉴于西平府“地居四塞,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洵万世之业也”的原因,德明将都城进一步西移,迁至怀远。与此同时,新的一轮的神圣化活动接踵而来,进一步神化了贺兰山。《西夏书事》记载,“夏六月,有龙见于温泉山。山在怀远镇北。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13](P118)于是贺兰山随着李德明时期的神化地位快速上升,成为西夏境内的神山,作为龙兴之地,那么将陵区选择在贺兰山下,必然受到神灵庇佑。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西夏统治者的个人因素直接决定着统治中心的选择,正是由于李继迁和李德明对灵州地区认识,使得灵州地区地位不断上升,最终被确定为西夏统治者的陵区。
四、结语
可见,西夏陵在选址过程中颇费功夫,在陵址选择中,遵循了传统的陵随都建的原则,将风水观念和个人喜好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最终将陵区位置确定在贺兰山下。因此,可以说西夏陵选址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确定了西夏陵最终的位置,以独特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尧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