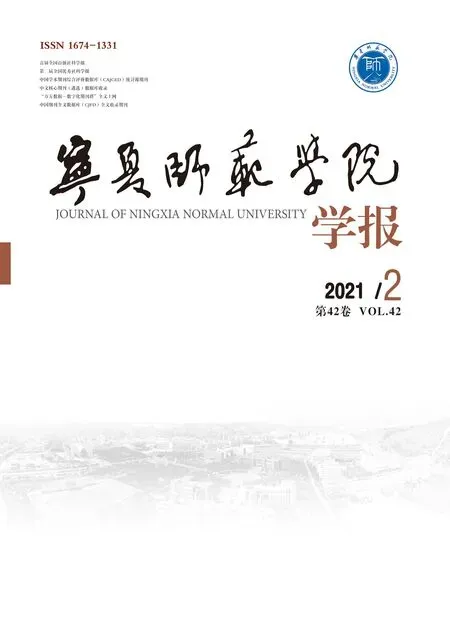宁夏建省与阿拉善旗省治模式的开启
——兼论宁夏建省原因
杨钧期,黄 鑫
(1.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2.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北伐战争结束后,没有明显地盘优势的冯玉祥及其西北军为在新一轮的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开始对其控制下的区域进行整合,着手酝酿甘肃分治案,即将甘肃一分为三。后经过西北军系人物——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的活动,该案随之被列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的议案。1928年9月5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上,该提案得以通过。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9次会议又通过了宁夏、青海建省的决议。甘肃分治与宁夏建省是“民国时期发生在西北的一件大事”,[1]是研究近代西北区域历史变迁中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故学术界对其已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某些方面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笔者试从边疆治理的角度对宁夏建省的相关面向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深化此类问题的思考。
一、宁夏建省原因
关于宁夏建省的原因学术界已有的结论大体可以归纳为:建省是国民政府与冯玉祥西北军双方借此削弱对方实力的结果,是派系斗争的产物。因为对双方而言,分治与建省是不同的两个面相。国民政府侧重于建省后带来的分治,这不仅可以迎合当时为风靡一时的“缩小省区论”,同时还可借此分散和削弱西北军;而西北军方面则更看重分治后的建省——此举不仅可以增加省区数量,以便安置部属,平衡集团内部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藉建省保留更多的军队(当时驻防省区的数量是整军后保留部队数量的重要指标),从而将南京方面借编遣而裁减西北军的目的消解于无形。此外,西北军还有出于与甘肃地方势力较量的需要,藉“分治建省”汲取更多统治合法性的考量。[注]关于宁夏建省的原因,吴忠礼先生的观点最为典型,其认为:第一,国民政府削弱地方势力的需要。“因为把省区划分小了,地方势力就会被分散和削弱,……可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第二,国民军出于保持实力的需要。“据冯部原控制四个省,分配准编12个师的前例,平均每省驻军3个师,那么再增加宁夏、青海两省,就可以再争取多编几个师的兵力”;第三,国民军出于因人设事的需要。“北伐成功,许多人都做了官,……可是西北军毕竟只占据四个省份,因此一时间大有神多庙少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多添一个省,就可以多安排一批部属”;第四,国民军出于与甘肃地方对抗的需要。见吴忠礼:《宁夏建省溯源》,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上述观点对建省原因解读虽符合一定的历史逻辑,但缺乏佐证资料,难免有过度解读之嫌。退而言之,即使成立,似乎也只能解释甘肃分治,不能解释为何是在宁夏与青海建省,而不是当时陇上八镇的其他镇?如果仅就为削弱和限制对方计,在陇东,陇南或河西等地建省又何尝不能实现?就地缘政治而言,宁夏与青海之外的其他六镇何尝不是相对独立统一的区域?由此可见,至少就南京方面而言,其动机远非基于派系斗争的考量,况且分治与建省也很难“分散和削弱”西北军实力,反而有可能使对手扩大局面。宁夏建省背后应有其他超越派系斗争的政治意图。
为考察宁夏建省背后的政治意图,我们不妨对西北军建省议案中所述缘由进行一定的分析。兹将缘由摘录如下:
A甘肃面积过广,北部阿拉善额鲁特旗,及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地方,汉、蒙杂处,夙号难治。B从前设有宁夏护军使管辖。宁夏护军使改为镇守使,该地方仍归宁夏镇守使辖治。现时镇守使既不设立,该两旗地方遂致无所管辖。甘肃省政府鞭长莫及,难以控制,长此以往,殊非所宜。况该处地广人稀,尚待开发,听其自然,亦属可惜。C查甘肃宁夏地方濒黄河,土地肥沃,若将旧宁夏道属各县与阿拉善、额济纳地方合并为一,划设成省,先就宁夏附近之地,从事屯垦,一面向阿拉善、额济纳地方逐渐开发,不十年间,即可与内地相埒。D至于宁夏物产丰富,关于省之经费,较之青海等省,尚有余裕,亦无虞财政之困难也。E“办法”:将宁夏道属各县与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合并成省,名为宁夏省,其省治即设在宁夏。是否可行,敬请公决。[2](注:字母序号为引者所加)
需要说明的是,西北军所述缘由虽并非一定代表本意,但为确保议案顺利通过,其理应迎合国民政府战略意图和施政方略。退而求之,其至少不能与之相违背,故透过该议案我们仍可以窥见国民政府的大致意图。
上述建省缘由中,A可视作甘肃分治的理由,即:甘肃省域辽阔,阿、额两旗情形复杂,省政府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管理。B、C、D则可视为在宁夏建省的理由,即:宁夏具有管辖阿、额两旗的经历,且距两旗较近,管理上较为便利。此外,宁夏建省的财政基础也具备。E则为宁夏建省的具体方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甘肃分治还是宁夏建省,其理由几乎都是围绕阿、额两旗展开的,故加强蒙旗的治理才是宁夏建省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此次朔方道改省动机之一自为治蒙政策,善使仅管八县,则改省毫无意义也”。[3]这也表明,随着北伐的完成,国民政府已将边疆治理提上议程,而将这些地区纳入省治轨道则是其加强治理的重要方略。
这也可以从国民政府此前将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等地区改为行省的先例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察哈尔等新建四省无不处在蒙藏等少数民族集中区域。因由清朝皇室所维系联结的满、蒙、藏、回一体关系已经瓦解, 蒙藏地区与中央政权之间已呈日渐分离之势,这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边防隐患。在新型的民族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尚待构建之际,为维护边防安全,以省治的方式推进对边疆的整合,就成为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基本策略。循此理路,我们进一步得出:国民政府宁夏建省的主要原因为加强对阿、额等蒙旗治理,巩固西北边防。
与国民政府着眼于边疆治理与国防安全相比,作为此次区划调整的动议方西北军之所以主动提出在宁夏建省,其固然有通过增加省区数目,保留更多军队以消解国民政府裁军计划的企图,但其直接目的则是为了借省治取代蒙古王公对两旗的统治,从而扩充自己的统治地盘。
阿、额两旗地域辽阔,各种资源十分丰富,在内蒙古蒙旗系统中享有极高地位。仅以阿拉善一旗为例,该旗面积即为17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与内地一中等省份。此外,该旗物产资源也十分丰富,尤其是盐湖众多,为甘、宁、绥西、晋北食盐的主要来源地。故控制二旗,即意味实力大大的扩张。但与民国后普遍统辖于某一行省的内蒙古其他蒙旗(或类似于行省的特别区)不同,阿、额两旗为特别旗,直辖于中央政府,毗邻的甘肃省概莫能染指其政务,这无不给西北军甘肃当局很大刺激。与此同时,阿、额两旗邻近新疆的地理位置对一直缺乏出海口的西北军也极具诱惑力。该旗对于西北军获得境外战略物资援助,进而抗衡国民政府,具有非凡的意义。北伐时,西北军就是通过与阿拉善旗王公的联合,依靠该旗通往库伦大道获得苏联军火补给的。也正因为如此,控制阿、额两旗对实现西北军集团利益,具有独特的价值。
事实上,控制阿拉善等蒙旗一直是西北军经营西北的重要方略。早在1925年进入甘肃时,西北军(时称国民军)就已开始着手加强对阿拉善旗的控制。其首先将甘肃征收与教育机构延伸至阿拉善旗,企图控制阿拉善旗的财政与教育。随后,又以筹设兵站为名,在阿拉善旗磴口巴格设立县治,将旗属磴口、沙金套海等后套产粮之区悉数划入县治,直接委任官吏治理。[5]与此同时,西北军当局还以挽运苏联援助之军火为由,在阿拉善旗组设办事处,委任师长赵景文为驻阿拉善旗监督委员,带兵常驻定远营。[6]
因事关权力流失,西北军这些活动也遭到了阿拉善旗蒙古王公当局的高度戒备与抵制,其效果并不理想。为推进对阿拉善旗的整合控制,1928年4月22日,宁夏西北军当局又联合阿拉善蒙古贵族德毅忱(又称小三爷)发动起事,推翻原有王公政权,另设旗务处。因触动了蒙旗王公体制,该事件随即引发了蒙古社会的强烈的反应,招致旧势力的强大反扑。为避免整个蒙古社会秩序的震荡,在国民政府的干预下,西北军当局被迫恢复阿拉善旗原有政治秩序,其以武力控制阿拉善旗的努力未取得成功。此后,以省治的方式推进对阿拉善等蒙旗的控制也就成为西北军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
二、省治模式对阿拉善旗的影响
宁夏地方升格建省,使其直接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单元,这对于提升宁夏在全国的地位,促进宁夏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将阿、额两旗纳入中央集权象征下的省治,这也标志着两旗开始由蒙古王公委托治理向中央直接治理的转变,这无疑成为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因额济纳旗距离宁夏过远,此后该旗虽纳入宁夏省,但由甘肃省政府代管。故以下仅以阿拉善一旗为例,探讨宁夏建省的影响。其对阿拉善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阿拉善旗边防。阿拉善旗东临绥西、河套,南隔贺兰山与宁夏相望,西扼新疆,西南紧靠河西走廊,北接外蒙古,并有库伦大道通往外蒙古及苏俄,在国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民初有人就曾断言,“宁夏蒙民,在今日外蒙独立时期,实为中国北边民族最要之一部”。[7]宁夏行政区划的升格,无疑大大扩充了宁夏地方的军政资源,提升了其军事打击能力,这对阿拉善旗内分离势力和境外主权觊觎者起到相当的震慑作用。与此同时,宁夏建省还有利于整合宁夏内地与阿拉善旗武装力量,统一协调两地的军事行动,从而改善西北边疆防务。
阿拉善旗与宁夏仅贺兰山一隔,双方在防务治安上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清朝前期,西北准格尔等部蒙古时有叛乱,威胁着西北内地安全。阿拉善旗作为叛乱的缓冲地带,是宁夏内地最重要的安全防线。陕甘总督岳钟琪谓之为“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8]为加强对阿拉善地区的守卫,雍正即命岳钟琪在贺兰山西麓山口约六十里的阿拉善境内筑城,名曰定远营,与宁夏城“适成掎角之势”。[9]民国后,北洋政府又设宁夏护军使(1921年后又改为镇守使)统一节制宁夏道、阿拉善旗等地军务。至此,阿拉善旗与宁夏遂正式成为统一的的军政单元,诚如当时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所言:“至我民国,各旗军务均归节制,始胡越不啻为一家矣”。[10]事实上,马福祥此言仅为美好的愿景。因双方政治上互不统属,协商沟通依然不畅,军政仍处于分立状态。宁夏建省无疑消除实现两地军政统一的制度障碍,有力地促进双方军事防务上的协调与联系。
第二,有利于进一步密切阿拉善旗与宁夏内地之间的联系,加速阿拉善旗经济开发。一直以来,阿拉善旗与宁夏之间在经济上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一方面,阿拉善旗对宁夏经济有着的重要影响。阿拉善旗地广人稀,物产资源丰富,成为宁夏民众外出谋生的主要去处。据记载,自清中叶后,宁夏一些民众即在阿拉善旗内伐木为生,旗府也曾一度允许其自由开采。如旗政务处所言:“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在位,正际承平时代,政简民安,并无用款之地,而山林畅茂,因准汉民自由樵采,并未索租”[11](P237)。清光绪以后,随着阿拉善旗东部濒临黄河一带大量荒地的开垦,又有大量宁夏民众移入此片区域。据1937年赴此调查的窦震寰写道:
宁夏亦以农村破产,民不聊生,独西套阿拉善旗,以四境交通不便,耸峰阻障,境内盗匪绝迹,民殷物阜,颇有上古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之风。宁、甘两省人民,咸视该地为世外桃源,争赴阿旗谋生,此亦阿旗人口近年逐渐增多,日臻繁荣之一原因也。[12]
同时,宁夏每年都有民众进入阿拉善旗内牧放牛羊、挑挖煤炭、采摘蘑菇、肉苁蓉及甘草等中药材。这些移民的进入活跃了阿拉善旗商品市场的同时,也加速了对阿拉善旗经济的开发。
另一方面,阿拉善旗对宁夏经济也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阿拉善旗为游牧地区,境内所产主要为盐与皮毛产品,而民众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则高度依赖宁夏供给。诚如旗政务处所言:“本旗游牧地址,向无庄稼可耕种,妇孺皆知,每岁蒙地兵民日用粮食均恃宁夏源源运济”。[13]据统计,阿拉善旗每年从宁夏进口粮食总数达16万石,约占进口粮食的五分之四。[14]除粮食外,蒙民所喜好之白酒、茶叶、棉花丝织品、器皿用具也仰赖于宁夏。此外,阿拉善旗初步发展的手工业、煤矿业所需劳动力来源及其产品销售市场也大多为宁夏。正因为阿拉善旗与宁夏经济存着密切关系,故此次阿拉善旗划入宁夏省,既是这种关系发展的反映,同时也能促使二者成为更为稳定的经济共同体,实现优势互补,促进阿拉善旗经济的发展。
第三,有利于加快对阿拉善旗政治一体化的整合。阿拉善旗长期实行封建王公体制。在此种政治下,中央政府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广大民众但知有王爷、神佛,而不知有国家、中央政府。宁夏建省,使阿拉善旗与内地结成了统一的行政单元,进而加速了其与内地政治一体化的道路。自阿拉善旗纳入宁夏省后,宁夏省政府当局即以该旗“经中央明令归省管辖,所有设治行政亟应着手次第进行,用谋统一而期发展”为由,[15]在阿拉善旗内设置紫泥湖设治局,后又筹设香山设治局,以为县治张本。与此同时,宁夏省还在阿拉善旗组设定远营办事处与军警稽查分处,进一步将省政权力延伸至旗内。这些机构组织在不同程度地影响与削弱阿拉善旗封建王公权力的同时,也向该地方传导着国家观念,使旗内民众更真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这为后来实现与内地政治的同一性创造了条件。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论者认为宁夏建省“亦具有某种程度的‘改土归流’的性质与意义”。[16]
三、余论
尽管宁夏建省密切了阿拉善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但此次宁夏与阿拉善旗行政区划关系的调整,一定程度上说实为国民政府军政力量介入的产物,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央政府对阿拉善旗直接治理的转变。但此后国民政府力量并未在宁夏扎根,该省政局一直操控在地方军阀手中,故宁夏建省无疑为地方军阀开辟了一条控制阿拉善旗的合法路径。为避免军阀控制对阿拉善旗的剧烈震荡,进而削弱蒙旗社会的内向之心,此后国民政府又颁布《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在维持宁夏省治格局的前提下,宣布继续保留蒙旗原有的王公体制,又明令阿拉善旗在行政上直辖于行政院,使阿拉善旗在基本维持原有蒙古王公直接治理的同时,又形成了中央与宁夏省参与的多头治理格局。宁夏省军阀政权凭借着在阿拉善旗绝对的军政优势,迅速将参与治理权转化为对阿拉善旗的实际控制,省旗冲突遂呈现常态化趋势。国民政府在阿拉善旗的治理也陷入了以问题解决问题,用代价减免代价的境地,这也可以透视出民国西北边疆治理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