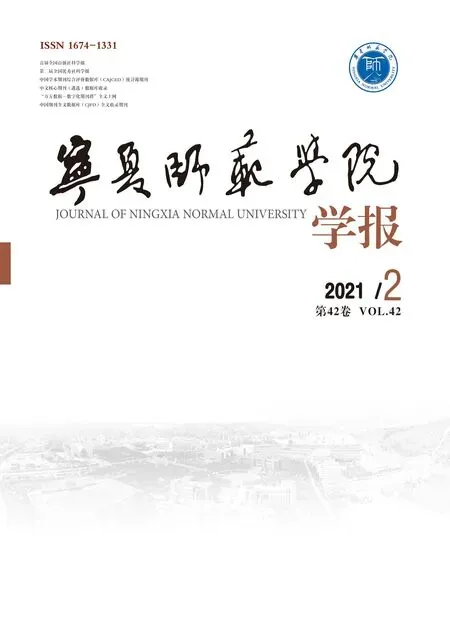神话作为“方法”
——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现象探究
张 栋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作家们在作品中表现了神话的诸多因素,进而丰富了神话在当下存在的样态。这一创作现象从新时期伊始出现萌芽,一直延续至当下,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风潮。整体上来说,当代作家笔下的“神话”,不再是那些以神灵、鬼魅为核心叙事对象的神魔故事,而是进入到小说叙事的具体进程之中,成为作家展开叙事的重要借助对象。因此,神话更多以“方法”的形式进入作家创作视域之中,因而“小说神话叙事”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性、自觉性意义的叙事方式,也具有了存在的价值。笔者认为,小说神话叙事指的是“神话叙事传统在小说创作领域的现代承接和置换变形”,[1]是作家借用神话的思维观念或叙述话语特征进行故事讲述的独特叙事形式。在一般的现实主义叙事中,作家讲述的“故事”与文本的“话语”之间存在着间隔,但在小说神话叙事中,“叙事”与“话语”是融合的,作家以打破现实与虚构之间隔的话语方式,使其营造的故事不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描摹,而是打破了客观现实与人类主观体验的界线,从而再造了一个糅合着人类神话想象与感性经验的审美世界。
当代作家小说创作的多元景观,决定了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神话,因此神话介入小说叙事的方法也存在区别。总的来说,作为方法的“神话”主要在三个不同的层面发生作用。第一,有的作家选择重述中国的传统神话,并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改造,但其目的仍是现实性的。第二,有的作家着重将神话表达所内蕴的思维观念作为叙事的背景,从而形成神话意味浓厚的文学主题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风格。第三,有的作家提炼出神话本有的表达特征(如象征、隐喻等等),从而将神话内蕴的丰富思想内容与人类现实生活相映射,在客观上构成对人类命运的生动呈现。神话叙事作用在上述三个层面的发挥,使小说神话叙事呈现出与其他类型叙事迥异的景观,继而更新了读者大众对当代小说的既有认知。
一、神话的重生与更新
在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曾经的文化经典也会改头换面,重新进入大众的文化视野之中。神话承载着人类的集体记忆,在不同的文化圈层中有着不同的外观。对于中国人来说,盘古开天辟地、嫦娥奔月等神话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心灵内容,在人们的文化观念不断更新的时代,神话也会以重生的形态继续存在于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记录下人们在新的时代中心灵层面发生的变化。因此,神话的重生与更新,既是神话按照自身发展规律演绎的结果,也是作家遵循社会大众心理需要以进行文艺创新的必然。
2005年,重庆出版社与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合作开启了“重述神话”出版计划,并邀请了苏童、叶兆言、阿来、李锐等四位作家进行创作,他们与珍妮特·温特森、桐野夏生等外国作家一起以新的视角重述本民族的经典神话,从而赋予了传统神话新的叙事外观与现代意义。中国作家选取的神话材料都极有代表性,苏童的《碧奴》选取了孟姜女哭长城的神话传说,叶兆言的《后羿》选择了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神话,阿来的《格萨尔王》选择了在藏族地区广泛流传的格萨尔王神话,李锐的《人间》则选择了白蛇传神话。这些神话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早已形成了大致的叙述模式,但在当代作家笔下,它们又被赋予了浓重的现实意味与人类性特质。神话为何被一再重述?这不仅是因为神话为人类的艺术保存了各种类型的叙事原型,而且也是因为其内蕴的文化基因“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诗性智慧,也为人类指明并提供了返归自然的航向与能力”。[2]客观来说,当代作家的神话重述延续了鲁迅等现代作家在《故事新编》诸作品中开创的叙事风格,即以现代眼光重新观照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神话,并试图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新编排神话的情节与结构,使神话成为承载作家现代意识的重要凭借。与现代作家不同的是,苏童等当代作家不再以强烈的启蒙意识作为重新组织神话的参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结合自身的性格志趣、文化态度,并照顾大众的审美趣味,因此他们的重述作品充满着强烈的个人风格。事实上,当代作家的叙事选择,是当代知识分子表达文化焦虑的必然结果。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情况不成正比,因此,借助文学创作的形式向世界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特质,便成为当代作家的共同任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家们的神话重述便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文化意义,传统神话不仅启发着作家们的叙事创新,而且也成为当代作家文化观念的孵化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助推力。
从具体的创作实践层面来看,虽然苏童等作家的重述作品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并成功进入国外图书市场;但从文本角度来说,几位作家之间存在着创作水准上的差异。客观来说,阿来创作的《格萨尔王》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不仅是因为阿来在作品中成功还原了神话叙事的宏大特质,而且对于神话原型的创造性再利用,也使传统神话获得了更为宽广的表现空间。笔者即以《格萨尔王》为代表,阐述当代作家神话重述的典型特征与美学追求。
严格来说,苏童选择的孟姜女故事,李锐选择的白蛇传故事,都应该算作民间传说,而叶兆言对嫦娥奔月神话的再造,也使之成为记录男女情爱纠葛的传奇故事,具有了强烈的世俗性。在这一前提下,阿来对格萨尔王神话的重述,便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格萨尔王神话在中国西藏等地区有着长久的口头言说与传播史,根据这一神话改编成的史诗更在少数民族地区长久传唱,成为民众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阿来对格萨尔王神话的文本改造,一方面有宏大的神话史诗作为创作背景,使得阿来的作品被赋予了宏大、浪漫、瑰奇的品格;另一方面,对传统史诗的再创造,也使格萨尔王神话具有了现代的叙事形式。因此,这种创造对于中国神话叙事传统在当下的延续,也是重要的贡献。虽然阿来将8000余万字的英雄史诗凝练为几十万字的小说,但他并没有以戏说的态度对待神话,而是在文本内部进行了有限度的改造,在尽量尊重史诗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叙事可能。在叙事结构层面,阿来基本上沿袭了史诗的结构,以“神子降生”“赛马称王”“雄狮归天”三个部分,讲述格萨尔王降临人世之后重整人间秩序,乃至最后归天的故事。因为有成熟的民间史诗作为支撑,阿来对格萨尔王这一神话原型的表现要相对从容,而且他在重点表现格萨尔王所创造伟业的同时,也突出了格萨尔王作为英雄个体呈现出的复杂性格。另外,阿来以集中表达的方式刻画英雄神迹与人物性格,从而使原始神话中宏大、悠长的时空变形为小说中原始与现代交融、神灵与凡人交织的时空,这种叙事创新使格萨尔王故事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更加充沛的生命力。在阿来这里,宏大叙事借助神话外观而得以复生,从阅读接受层面来说,读者也能够从叙事的宏大气度中感受到神话的魅力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阿来对格萨尔王神话史诗的创新性表达,也体现在他对神话原型的创造性再利用方面。在小说中,阿来成功地对传统的神话原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并以置换变形的方式编织入神话的现代讲述之中。在《格萨尔王》中,格萨尔王是最具有经典意义的人物原型,阿来不仅在文本中重塑了格萨尔王的形象,对其进行了人性的还原,从而赋予其复杂的神性与人性兼容的性格特征,而且从镜像表现这一角度出发,塑造了说唱人晋美这一形象。晋美从牧羊人转变为史诗说唱人这一条叙事线索,与格萨尔王降临人间成就伟大事业并最终回归上天的叙事线索是紧密糅合在一起的。从叙事的角度来说,晋美这一形象是对格萨尔王人物原型的延伸,格萨尔王的刚勇坚毅、伟大神力,与晋美的孱弱敏感形成了鲜明对比,二者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张力,这就使格萨尔王的传统形象获得了另一重表现。进一步来看,二者之所以能够形成原型的转换与传递,恰恰是因为他们都处于与自我心魔的恒久交战之中,这也是小说所要传达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小说开头,阿来即写道:“魔变成了人自己。魔与人变成一体。当初,在人神合力的追击下,魔差一点就无处可逃,就在这关键的时候,魔找到了一个好去处,那就是人的内心,藏在那暖烘烘的地方,人就没有办法了,魔却随时随地可以拱出头来作弄人一下”。[3](P2)因此,在人、神、魔的转换与影响这一主题下,格萨尔王这一神话原型得到了晋美这一人物形象的有力补充,从而也使格萨尔王神话的现代意义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阿来等作家在传统神话基础上展开的神话重述,成为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的重要现象,虽然这一创作实践并没有延续下来,但不能否定这些作家以现代方式重释中国神话的努力。在他们笔下,神话不再只是传统的故事,而是成为传达现代观念的重要场域,因此具有重要的实验性意义。在之后文化学者朱大可创作的《麒麟》《字造》《神镜》等作品中,仍能看出神话重述的影子,这说明神话重述的创作实践仍是有吸引力的,而且能够产生与一般现实主义创作不一样的价值。在网络文学创作领域,神话的重述现象更是蔚为大观,诸多玄幻小说都是在借鉴中西传统神话的基础上创作出另一个神话世界。因此,对以网络小说为代表的神话重述现象的分析与解读,也应成为小说神话叙事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神话思维的叙事呈现与作家风格构建
神话思维作为原始先民感知世界的主要思维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而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思维方式的消失,它潜藏在人类思维意识的深层,并在人类的诸多艺术创作类型中得到表现。小说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部分,成为作家呈现特殊艺术创作思维,实现传统思维之现代更新的重要场域。
就中国当代作家来说,一些作家因为成长环境、社会经验、知识构成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迥异于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思维,并形成了浓重的超现实,且蕴含着神话哲思的创作风格。举例来说,贾平凹、莫言、张炜、韩少功等是上述作家群体的代表。他们新时期初期即登上文坛,并成为寻根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在对中华文化之根底的探索中,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把神话的某些质素当作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秘密的重要凭借。《商州》《红高粱家族》《爸爸爸》等作品,呈现出具有统一性的神话叙事品格,但比较而言,这些创作又有着内在的区别。作家们选择的神话资源是不同的,这也影响了他们在小说中进行神话表现的方向与特征。贾平凹在创作历史中系统性地发掘湮没在秦岭山林中的神话,由此重新发现了一个神秘与现实兼具的、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神话世界;莫言的神话讲述则着重塑造在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民间英雄原型,莫言借助民间神话的发现,同时细致描绘了中国民间文化的特性与民族性格;张炜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现实境况的反思者,他通过向自然神话回溯与描摹带有神性特质的人物,以及塑造上述表现对象与现实之间的反差,表现出一位具有理性的知识分子的冷静思考;韩少功在小说中刻画了一个神话传说、巫觋信仰、民间仪式并存的南方世界,他在用细致的笔触呈现这个世界诸多细节的同时,也试图从中发现人类生存的根本秘密。在贾平凹等作家的创作中,作家对神话思维方式的借鉴与运用,构成其小说叙事的主体部分,在他们笔下,不仅诸多文化地域的神话特性得以彰显,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补充了新鲜的空气,拓展了当代小说的表现范围,丰富了当代小说的思想内蕴。在上述作家之中,又以贾平凹的创作更具代表性。作为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贾平凹不仅以连续的创作不断完善着秦岭的神话境界,而且在其创作系列内部,神话叙事也在不断发生变迁。笔者即以贾平凹的创作为例,探析神话思维在其创作中的叙事呈现,及其对作家创作风格构建的助推作用。
贾平凹的神话叙事,离不开秦岭对其精神世界的影响。这里的秦岭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秦岭地区林木众多,而且素有鬼神崇拜的传统,按照贾平凹自己的说法,“有山有水有树林有兽的地方,易于产生幻想,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4](P35)因此,在贾平凹的小说中,自然与文化意义上的秦岭实现了融合,并被塑造为神话的外观。虽然秦岭最终难以逃脱现代因素的侵染,但贾平凹仍始终在突出秦岭原始性的纯朴一面。从《古堡》到《太白山记》,从《废都》到《秦腔》,从《老生》到《山本》,错综复杂的故事里面始终离不开那个被神秘的雾霭笼罩的秦岭。贾平凹塑造了独属于秦岭的神话时空,从而使之与人类生存的现代时空区别开来。曼延在秦岭之中的是一种自然的时间,这是一种按照四时节律、季节交替、昼夜变换的变化构成的时间形式,而人们的所有活动都在这一时间参照下进行,因此在贾平凹小说中常见的碎片化、琐细化的书写方式其实都是以自然时间为标准的叙事结果,这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样式。在空间方面,贾平凹则在作品中突出了神圣与世俗的划分。在神话思维的理路中,空间是非均质的,某些空间层次会因为人类思维观念的投射而产生神圣意义。按照卡西尔的观点,“只要神话思维和神话情感赋予某项内容以特殊价值,只要他们把这内容同其他内容区别开并赋予它特殊意义,那么凡是去这样的地方,这种质的区别就要以空间分离的形象表现出来。”[5](P117)在这种神话思维的影响下,贾平凹小说中便经常出现神秘现象与世俗现象的并置,二者互为补充,并行不悖。读者对这些片段的品鉴,犹如在《红楼梦》中看贾宝玉游览太虚幻境,超现实的情境往往成为现实画面的预言,而现实则往往成为神秘现象的注脚。因此,贾平凹在系列创作中勾画的秦岭时空,是神话思维在作家思想中发生作用的结果,它凝练为一个个富有独特光彩的神话意象,成为贾平凹神话叙事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
神话意象是神话思维的凝结,贾平凹笔下的神话意象系统不仅内容丰富、意象多元,而且这些意象自身具有的符号意义也使它们介入到神话叙事的结构之中,并被赋予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总结来说,贾平凹笔下的神话意象主要有两类,一类具有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外观,一类则是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是社会性的意象类型。两种类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转化。早在《太白山记》等作品中,贾平凹即塑造了颇多类型的神话意象,及不同物种之间身份的互换。比如《猎手》中的狼乃是人所化,《公公》中的老人最后化为娃娃鱼,《饮者》中乡长原来是小螃蟹所变,《观斗》中的人-虎-犬-蟋蟀的转化,以及《母子》中模样怪异的熊、三只眼的奇物、长着蛇舌的女人、长角的男人等等。客观来说,此时的神话意象仍停留在表面的层次,贾平凹也较注重一种神秘氛围的渲染,在后来的作品中,神话意象的内涵层次得以提升,且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比如《废都》开头所写的同根生出的红、黄、白、紫四枝花朵,四个太阳、七条彩虹等意象,《老生》中的“倒流河”;或者那些或是神化或是鬼化的人物形象,如《废都》中的智祥大师、《白夜》中的再生人、《高老庄》中的迷胡叔、《极花》中的麻子婶、《山本》中的老魏头等等。这些意象不仅可以作为神话思维存在的证明,而且成为作家组织叙事结构的重要中介。对于贾平凹来说,神话意象的系统性运用是他能够发现一套独特神话叙事结构的重要前提,随着对神话意象认识的不断深入,意象本身承载的结构性意义也越发突出。神话意象的叙事结构介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神话意象的组合与共同作用的发挥形成了一种二元辩证结构,从而形成了具有平衡性的叙事;二是将某一神话意象作为表现的核心,并借助它实现和谐的统一,从而实现作家“神鬼同舍”“天人合一”之创作理想。贾平凹新作《山本》中的“涡潭”意象可作为这种理念的证明。在涡潭中,一黑一白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中间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不管什么事物跌落其中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象征着涡镇这个地方的世事。在诸多势力到来之前,涡镇保持着宁静与稳定,涡潭也以自然的秩序轮转,但当战争的脚步来到涡镇,之前所有的秩序都被打破了。“涡潭本是以阴阳互转的形式象征着自然运行结构的稳定,代表着人类生命运转的自然结局,但现代神话却打破了这一自然秩序,涡潭被重塑为井宗秀等人毁尸灭迹的场所”,[6]在这里,作为神话意象的涡潭产生了隐喻的作用,成为人间失序与社会变革的重要表征。
借助贾平凹作品的分析,即能看出神话思维在某些作家作品中的叙事呈现,及对于作家创作风格的塑造作用。在莫言、张炜、韩少功那里,神话思维又表现出另一种光彩,成为研究者分析当代作家创作的重要依据。在贾平凹等作家的影响下,神话叙事逐渐形成具有潮流性的创作现象,这在刘亮程、马步升、叶舟、冯玉雷等西部作家笔下均有所体现,他们“把文本人物作为中国神话原型的置换变形,作者以后现代笔调重构了河西走廊大地上的神话、历史与现代的关联”。[7]由此可见,神话思维作为神话叙事生成的重要背景,成为当代作家发现新的叙事可能、创造新的叙事风格的重要助推力。
三、神话隐喻与人类命运的深刻呈现
神话不仅帮助人类回望过去,认识当下,也能够使人类获得一种展望未来的能力。这就需要突出神话特有的隐喻功能,在这里,神话变成了一种话语形式,成为作家思考现实世界和探讨人类生存哲学的独特书写方式。对神话的这种理解,使作家展开了对人类命运的广泛思考,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这一思考也划分出不同的类型。有的作家借助神话的隐喻功能表现了人类生存的寓言特质,人物不仅与传统神话人物实现了精神上的续接,而且其生存状况也得到了艺术化呈现。有的作家则从作为“知识”的神话这一层面入手,从考古学层面,揭示神话特有的信息承载与精神批判功能,从而在这一基础上糅合自己的文化批判观念。有的作家则立足于人类发展的未来时空,更注重通过刻画某些极端的生存情境考察人类命运的走向,因此在他们笔下,人类的未来成为技术时代的独特神话。在诸多创作中,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更具代表性,这不仅是因为刘慈欣的科幻创作实现了中国神话叙事传统的当代续接,而且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借助刘慈欣的创作,读者不仅能够感受到文学作品经典性的形成过程,而且也能够体味到传统神话在其创作中的新变,作家将神话的隐喻功能拓展到人类未来命运的呈现之中,并展现了人类生存与心灵秩序的理想样式。
在对作品展开探析之前,需要理清神话与科幻之间的关系。科幻缘何与神话发生关联?这看似不相关的两者其实有着紧密的联结。神话是科幻叙事借助的重要文化根源,科幻作家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神话思维的当下呈现。在原始神话中,灾难情境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人类生存环境,比如在世界各神话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洪水神话中,人类需要在洪水的包围中找到出路,这也成为人类与命运抗争的形象呈现。而在科幻小说中,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未来时代中人类的科技虽然高度发展,但人类却在各种威胁之下重新回到被损害甚至被奴役的境地,仍然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摆脱悲惨的命运,这就是人类在神话时代苦难经历的当代复现。因此,科幻与神话不仅在思维方式上有着深刻的联结,而且表现了同样的人类主题,并共同作用于人类的现实选择。正是因为对神话与科幻之间关联的深刻认识,刘慈欣才会大胆地把神话置放于其科幻叙事之中,并凭借这种创作构成其强烈的史诗风格。刘慈欣认为,“科幻与其他幻想文学的区别就在于它与真实还牵着一根细线,这就使它成为现代神话而不是童话(古代神话在当时的读者心中是真实的)”。[8](P302)在《三体》这部小说中,刘慈欣从创世与灭世的神话主题、神话特有的“宏”叙事,乃至神话时空的技术转化等多个方面介入了神话的科幻叙事表现,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读者提供了与现实经验迥异的神话图景。
在传统神话之中,世界的创造与毁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西方的上帝造人与洪水神话、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与女娲补天神话、北欧神话中诸神的黄昏与世界的毁灭,等等。这些神话经过反复讲述,早已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而这也滋养了像刘慈欣这样的科幻作家。在《三体》中,刘慈欣将创世与灭世的顺序进行了倒转处理,因为科幻的叙事起点往往是人类的现实世界,在外来危机来临之时,这一世界发生动荡,人类世界或者在这一动荡中消失,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延续下去。《三体》中的三体人入侵地球即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遭遇的危机,但刘慈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未把三体人当作不请自来的侵略者,反而是在地球人的“邀请”下到来,这就引出了叶文洁的故事,以及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与变故。在很多人看来,叶文洁按下了毁灭世界的按钮,她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灭世者,但叶文洁选择的发生,恰恰是出于对人类世界秩序的失望,所以她邀请三体人到来的初衷,竟如西方神话中的上帝感于人类道德的败坏而用洪水毁灭人类一样。因此,这样一个灭世者的故事,多了更多现实的成分,神话在其中更多发挥了一种象征作用。在三体的威胁发生之后,罗辑与程心的身份,更像是创世者,因为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人类争取了生存的空间。罗辑作为执剑人,为人类文明争取了几十年的时间,程心则更出于一种文明之爱,不忍心看到任何一个文明在“黑暗森林”法则之下被毁灭。虽然地球最终仍难以逃离被毁灭的命运,但程心却作为新人类的种子存活下来,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创世者。可以看出,在对创世与灭世的书写中,刘慈欣表现出创世者或灭世者本身的复杂性,他们其实都是现实中的普通人,但在特殊的机缘下,他们拥有了毁天灭地的力量,而真正能使人类得以延续下去的,恰恰是那些有着完满人性的人。所以,与其说刘慈欣讲了一个神话,不如说他以神话的方式表现出对美好人性的期待,这是其创作的最终目的。
学者严锋认为,“如果为刘慈欣的作品归纳关键词,其中最显眼的一个就是‘宏’。这不仅是字面的意义,比如其小说创造的一些独特概念:宏电子、宏原子、宏纪元等;‘宏’更代表着一种大尺度、大视野的宏大视域。刘慈欣偏爱巨大的物体、复杂的结构、全息的层次、大跨度的时间,这种思想与审美取向,看上去与那种朋克化的‘小时代’格格不入。”[9]这里的“宏”道出了刘慈欣叙事的秘密。“宏”与“微”相对,是具有大体量、大规模、大形制性质的说明方式,而传统神话的讲述恰恰是一种“宏”叙事。神话中的天地开辟、抟土造人、神魔交战,无一不是在大维度的层次上发生,讲述者之所以偏好从“宏”的角度去还原神话中的事件,正是因为神话叙事解释了人类社会诸多现象的发生,所以一种“宏”视角的借助,能够使人类明白文化的源头所在,同时也从视觉想象的层面产生一种敬畏、崇高之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神话成为先民的信仰也并不令人意外。《三体》中的“宏”叙事比比皆是,刘慈欣不仅在时间维度上使故事的发生跨越千万年的时间,使宏大的故事具有了相当的时间长度,而且在具体的叙事细节上,刘慈欣也不厌其详地描述技术时代的各种奇迹。“文化大革命”时代矗立在叶文洁面前的巨大雷达天线、汪淼在VR游戏中看到的三体文明中的巨大单摆、与三体人的探测器相遇的人类创造的巨大飞船,乃至程心在光速飞船中看到的太阳系从三维向二维的“跌落”等等,这些超越一般时空观念的宏大景象,是刘慈欣为现在的人类所刻画的未来景象。在人类看来,这都是未曾遇见的神话景观,但在这些景观背后,隐藏的却是作者的深刻隐忧。
在人类诞生之时,人类总是运用自己所能理解的事物去解释身边发生的一切。比如自然界中的雷电是因为雷神的存在,太阳的东升西落是因为太阳神架着马车在空中游荡的结果,这是人类在早期时空观影响下对自然现象做出的解释。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原始人的时空观被证明是想象的结果,在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中,空间的三维与时间的一维是时空的本质性存在。作为“硬科幻”的代表,刘慈欣自然对基本的时空原理心知肚明,因此人类在地球的生存是遵守基本的科学原理的,毕竟科幻创作不是神怪故事,在实际生存中过于突出时空的非现实性,所谓的科幻就会变成玄怪创作。虽然刘慈欣没有突破现实的时空界限,但《三体》故事的发生维度是在宇宙层面,地球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所之一,因此他对时空的神话表现,主要发生在广袤的宇宙空间之中,这里仍是现代科学远未到达的地方。《三体》中人类经历的诸多“纪元”,本身就是一种神话的标志,这种标志只有在足够长的时间范围内才会发生,而人类光速飞船的发明,更是实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时间想象,这是只有在神话中才可能发生的景象。而在空间方面,刘慈欣则大胆地描绘了人类面临四维时空的感受。按照现代物理学与天文学的观点,多维时空是客观存在的,但只有在文学家笔下,四维空间的景象才能被准确传达出来。小说中这样写道,“我们在三维空间中称之为广阔、浩渺的这类东西会在第四个维度上被无限重复,在那个三维世界中不存在的方向上被无限复制……感受高维空间是一场灵魂的洗礼,在那一刻,像自由、开放、深远、无限这类概念突然都有了全新的含义”。[10](P194-195)刘慈欣并没有排斥技术的作用,因为在理性的时代,对技术的拒绝就是一种愚昧,他巧妙地借助技术将神话景象呈现出来,从而开辟出人类想象的新空间。在刘慈欣笔下,人类的命运得到了另外一种设想,人类也能够在这种神话隐喻中获得关于技术的客观认知,以及人类爱与善所蕴藏的巨大能量足以改变自身命运走向。
传统神话发展到当下,早已不再只是一个个故事,虽然埋藏在民间的神话资料被一点点发掘出来,但当代作家更喜欢从“方法”的角度去理解神话。神话中诸多充满光彩的原型,成为人类记忆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在当代作家的笔下改换了形式,但其内核却没有改变。不管是对神话的重述,还是神话思维的现代叙事转换,抑或是从神话隐喻的角度展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当代作家的创作展示了神话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这实质上是对神话共性的发现,使神话成为发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中介[11]。虽然在有的作家那里,对神话的理解还稍显单薄,或者把神话当作某种权力欲望实现的器皿,但这毕竟仍是少数现象,绝大多数作家仍怀着对神话的敬重之心,孜孜不倦地写下对神话新理解,延续着神话对人类的启发。神话蕴含着人类的智慧,也满溢着人类渴望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在当代作家笔下,读者显然能够读解出神话助力于美好生活实现的诸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