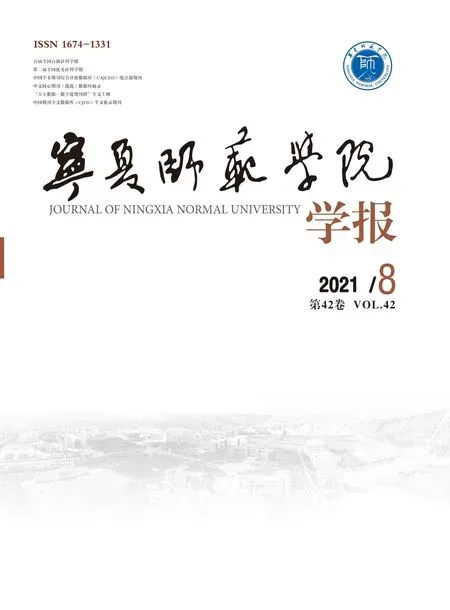论李进祥小说沉郁内敛的审美品格
任淑媛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在宁夏的小说创作领域,李进祥的文学思想介于文化守成和现代进取之间,他仿佛总能看到社会良性发展的一面,也能发现普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地域和个体的差异。他的小说有一定的社会批判价值。对于生活、对于人情、对于底层、对于人性,他用犀利的眼光考察、用冷峻的笔调书写。纵观李进祥的文学创作,他以清水河畔的河湾村、梨花村乡民的生存状态为主要创作内容,兼及城乡二元生存模式,钩沉历史文化,突显家园意识,他的创作透露出一种沉郁内敛的美学品格,宛如他刚毅英俊面庞上刻印的艰辛生活的纹路,黝黑粗重皮肤上反射的忧愤生命的礼歌。
小说的生命,最紧要的是能够看出其历史、地理背景。人是活在时代洪流中的,没有人能够逃离。积极面对,负重前行,是小说家的历史使命。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站在历史的高度,精辟阐明了文学艺术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1世纪以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异常迅速,城与乡,文明与野蛮是作家敏锐的发现与表达。李进祥深刻意识到乡民在追逐物质生活优渥的同时,失却了许多原始纯净。故而用一条可以涤荡心灵的清水河作为意象,呼唤人性良知、重塑家国情怀,展示转型期城乡变换的时代背景,艺术再现宁夏乡村的静谧,乡民的淳朴,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和追逐。
一、清水河:深沉的爱与乡愁
李进祥的小说,大多以清水河为意象,有的明写,有的暗喻,创作前期基本是一种理想化、艺术化的描摹,显现出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乡土叙事惯用的散文化、诗意化表达,试图创设一种精神向度,是一种知识者对底层小人物的愿景。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说:“意象一词,在中国语言发展史上,萌芽于先秦,成词于汉代,六朝用于文学,唐宋沿用,到明清而大行。”[2]中国文学含蓄的艺术品质,决定了意象可以有万千种隐喻。这是一种意蕴深邃、沉郁内敛的艺术呈现。李进祥的这类作品占很大分量,是李进祥早、中期基本的文学审美向度,河流这一意象无限延展了李进祥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宁夏南部山区位于黄土高原,以六盘山为屏障,有黄河支流清水河穿行南北。南部山区区域文化的生成,既和这里的自然地理密切相关,也和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相关。多民族融合和文化生成,使得宁夏这个地方自古底蕴丰厚,兼容阔达。杜甫的脚步就踏过了古灵州,他诗歌的“沉郁顿挫”书写着一代诗人的精神向度。沉郁是一种深重的家国情怀,是一种深沉的故土之恋。李进祥的小说创作和这位伟大的诗人的精神诉求是何等的一致,其沉郁的精神,冷峻的笔调,内敛的品质,拙朴的语言,构成了“清水河”书写这一主题意蕴,这种故园之恋,思乡之情,始终围绕着李进祥的文学表达。清水河意象可以代表李进祥的创作。清水河是李进祥创作的基本场域,也是最能够代表李进祥创作的一条河流。河流自古就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孕育地,有着无限丰富的文化蕴藉和精神内涵。尼罗河、两河、恒河都是文明奔腾的象征。华夏文明来自黄河、长江,成为古今诗家的精神母题。清水河作为黄河的支流,和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象征,李进祥选择这一意象,体现了他文学思想的深邃和隽永。面对细小、有时候甚至快要干涸的清水河,李进祥常常感觉到孤独、沉郁、忧愤,慨叹读过师范的他,没有很好的用自己的笔为文学做点什么,更慨叹作为读书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力气为这世世代代生活在清水河边,生活在河湾村的乡民做点什么,这是一种抱朴守拙而又积极进取的创作思想,这种文学观,对于提升清水河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及宁夏的地域文学创作,都有着可以进入文学史的价值。
“清水河”这个意象无限延展的可能性与空间,正如夏多布里昂的美洲、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迟子建的兴安岭、王安忆的上海、苏童的江南、叶兆言的南京、邱华栋的北京、贾平凹的陕西、阿来的川藏。“清水河”这个意象无限延展的可能性与空间,正是李进祥小说空间叙事的特征。钱穆说:“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黄河自身,他所凭依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3]清水河穿越固原、同心,成就了古丝绸之路的走向,也承载着两岸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生命历程。我们必须承认,山川、河流对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发生、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代表作《口弦子奶奶》,写的是清水河畔河湾村一个美丽的女子与外地货郎子的凄美传奇故事。清水河不仅是叙事的背景,也是一湾生活的清亮与韵致。《鹞子客》借清水河畔玩鹰与玩鹞子的小伙子和姑娘“下马羊”的恋情,展示新的历史时期,乡村青年人的生活追求和婚恋观念的进步。《一路风雪》写河湾村的杨娟、代课教师、杨明等渴求读书识礼的故事。杨娟这个女娃,为了支持弟弟读书,改变生活,用尽了自己的气力。《换水》写河湾村的乡民出门要大净,类似洗澡,平时省水,都是用汤瓶小净,由日常的清洁上升到精神清洁的高度。从这一篇开始,乡民就逐渐离开清水河,离开河湾村,走向城镇,走向城乡间来回奔波的生活。这也是李进祥以清水河为意象叙述走向成熟的标志,在以后的创作中,基本就是在清水河与城镇之间游离,《梨花醉》就写了不光是年轻人离开了梨花村,就是老人也被年轻人接走离开梨花村,清水河畔的人家越来越少了,奔着好生活去了。尽管故土难离,尽管不愿意受大苦改变,终究这是大趋势。从中可以看到国家政策的扶持,读书明理的重要,精神还乡的价值诉求。《清水河人物》系列,进一步明确了李进祥的创作,围绕着这一意象,他的创作有了更为高贵的精神依托。
李进祥成功把握“清水河”这一文学意象,使得清水河两岸的乡民走出了河岸,走向了城镇的现代和生活的多重维度。傅道彬认为,“意象展示着中国文学的审美蕴涵,也叙述着我们民族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艰难历程。”[4]这样说,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李进祥开拓的“清水河”这一文化价值,使得贫瘠落后的宁夏南部山区在继六盘山文化挖掘以后,又有了新的文化增长点,并且通过文学文本的文化积淀,反映转型期西部山乡社会生活、思维方式。河流这一自然意象成为宁夏地域文学发展的特征,并且河流也使得地域文学走向了中华民族以黄河为精神依托的大的文学、文化背景中,阐释了道德与伦理的价值要义。李进祥构建的“清水河”意蕴,已经不是宁夏南部山区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文化情态,而是一种普适的人类心底的淳朴与善良、悲悯与感伤。李进祥构建了以清水河为依托的自然生灵,提升了南部山区乡民的精神品质,这样的审美和价值,是对于故土最诚挚的情感,是对于家园最有生命的歌咏,无论这里的文化如何交融发展,道德与伦理成为自然追求的理性表达,突出体现了文学文本的哲思、体悟和精神向度。
清水河这一意象成为李进祥的标志,李进祥借助清水河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个性成长旅程和精神提升历程,逐渐由最初的诗化、散文化的小说风格走向冷峻、沉郁、内敛的艺术内蕴,也更关注清水河两岸乡民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切入点基本都是女性形象。
二、如花美眷:纯洁的爱与乡恋
李进祥的小说创作,善于书写如花的女子和她们对于美好纯洁爱情的执着与向往,矢志不渝与坚守困苦。李进祥给予她们最美好的与最浓烈的笔墨,书写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的如花美眷图谱,体现了乡村女子的纯洁美好,也最大限度地表达了李进祥的乡恋。
《口弦子奶奶》写了西部乡村特有的文化习俗,女人们通过口弦表情达意,抒发内心深处的爱与忧伤。这些描写初显了李进祥朴拙的叙述特征:善于描写细节,刻画内心丰富的个性。口弦子奶奶的生命,随着与心上人的分离,随着远嫁到河湾村,随着那口弦的声调,随着矢志不渝的执着、失去孩子的命数,一点一点地来到了我们面前,给了清水河这条咸水河以新的生命价值。
《女人的河》写阿依舍在清水河边长大,从河的上游嫁到了河的下游,伺候婆家一家老小,公公出去多年不见音信,应该是已经完了。大伯子出去多年也不见音信,同样出去打工的男人穆萨幸好有信来。天天来到清水河挑水的阿依舍想,“眼泪是咸的,清水河也是咸的,河水一定尝不出眼泪的咸味,正如它尝不出自己的咸味一样”。[5]清水河见证了阿依舍和同学马星晨的初恋,考上大学的马星晨再也没有来看清水河,家境贫寒嫁给放羊娃的阿依舍心高气傲,不甘心丈夫就是个放羊娃,宁愿自己承担下家里家外所有的活计,鼓动丈夫出去找营生。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乡村女子心性之高。每天到清水河挑水的倩影,柔弱纤细的身条承载的是坚强不屈的、向往现代城市文明的心。阿依舍的眼睛在清水河,心在天上。水自古就是一种美的象征,水的无限也是女子相思的无限。李进祥叙述的苦涩如清水河,女子的命运也如这清水河,连眼泪都是不敢流的,怕和这河水一相聚,会更加苦涩。
《一路风雪》写为弟弟杨明上学牺牲了自己读书机会的杨娟。其实在中国乡村,牺牲姐姐或者妹妹的读书机会,给了男孩子,是很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李进祥小说开始着意关注女性命运的阐发,尤其是读书与明理的问题,从而揭示中国乡村传统弊病和落后的思想。在现代性进程中,经济是重要的衡量标准,文化守成与现代性进程之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问题。李进祥的小说对于这些问题,多有涉猎,具有很深刻的批判意识。
《害口》写倔强的桃花和她的小伙伴杏花的生活选择和生活状态,有许多小心理,小细节,将乡村小女子特有的表面看起来柔顺、实则倔强的内心刻画了出来。《害口》也涉及乡村女孩子选择远嫁城市,或者进城打工,还是留守在家,与一大家子人孤独的相处等主题。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命题摆在了叙述的中心,城市也不是选择的唯一,待在村里,虽然衣食无忧,但是面对一大家子人,要独自学会处理一切生活事务,不免感觉孤单无依,且没有文化还是活不好。进了城,经济不独立,显然也不可取,总是指靠男人生活,终究是靠不住的。这种城乡二元生存困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具有民俗价值意义的是《挦脸》。挦脸是女孩子出嫁前的一种古老的、传统的仪式,可以让面庞更加白净、水嫩,由挦脸的老奶奶,或者巧手女子,用两根线将小姑娘脸上的毫毛去掉,再用瓦片等清理,后用鸡蛋滚滚,就是新人了。小说前三段都在写挦脸的习俗、方法、意义,读来颇有意思。这种传统的仪式和方法不仅具有民俗学意义,更重要的是一种传承和延续,一种礼赞和期许。小说家的故事,不仅仅有故事,还有故事背后的风俗、风景和风情。
《向日葵》里的小米背着少了双腿的男人、抱着越来越重的儿子生活。《天堂一样的家》里的小老板马成进了城,创业的艰辛和挣钱的屈辱深刻烙在心底。从清水河出来的人们都很不容易,无论是乡土守成还是城镇出力,都是血水和泪水并存。尤其女人,离乡背井,不是下苦就可以有好生活的。毕竟没有文化,许多时候是没得选择。
《丫鬟》写人的贪恋、自私的本性,但从小女人的拈酸吃醋写起,又有了很多意趣。写丁满财在城市挣了钱,在村里盖了满院子的房子,屋里的女人全天伺候公婆,尤其婆婆瘫了,想雇个人帮忙。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写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丁满财女人其实不是真心想雇人,是因为支书家雇了人,且支书的女人以前是说给丁满财的,可是当初丁家没彩礼,就嫁给了支书家,且读过一些书,显得温婉高贵、知书达理的,后来丁满财有了钱,在城里有了叫美莲的女人,但是婆姨闹过一阵,居然接受了,但是对于支书家的女人却总是放不下,支书家雇个人,自家也必须雇个人,写得太精彩了,写出了女人那种复杂的嫉妒心、微妙的情感变化。乡里有了经济基础后,村民生活好了的样子,经济上宽裕了,物质上富足了,乡民们也开始追寻精神层面的依托了。李进祥书写乡村,显得自然、流畅,乡村的一景、一物、一光、一影,都足以慰藉作家自己的现代性焦虑。
李进祥笔下的女子,都很有个性,不是一般的女人,要么非常能吃苦,要么对爱情大胆追求,要么特别有个性,要么不合群,写得梨花带雨,又坚毅刚强,但重要的是,最美好的一定是乡间的女子。这些女人支撑着一个一个乡村家庭,拉扯着几个孩子,服侍着公婆甚至还有祖公婆。她们的生活压力不比都市女人小,因为她们还需要下地干活,养鸡喂鸭贴补家用。这就是实实在在生活着的女人们,她们永远是生活的大多数,是过日子的大多数。这与城市的无病呻吟以及都市病、公主病相比,其社会价值和生命价值以及批判意识,都高了许多。生活就是日常和凡俗,她们是生活的本色。
三、理性反思:关于生命的价值要义
李进祥初、中期借清水河,艺术地描绘乡民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是一种理想化的现实主义,当笔触真正走向小人物的内心,当城乡二元生存的残酷现实,不断的警醒了和鞭策着他时,李进祥对于社会生存的亮色抓得更紧,也能够直面和抨击社会阴暗面。艺术追求逐渐高远,艺术表现力也更加老道了。
《屠户》写一位屠户总是去清水河洗牛肚肠。屠户每次看到清水河,他就有回到老家的感觉,他的老家就是河湾村。一条河,连接着一个硬汉内心的柔软和温情。清水河洗得净屎尿,却难以洗掉人心的贪婪和狭小。屠户用儿子的命换来了一个伦理道德。只有经过生死的淘洗,真正的清洁的精神才会自人心底出现。河湾村也是李进祥创作内容的又一个标志。一位作家只有纯熟地写自己熟悉和理解的场域,才能写出其精髓和实质。清水河、河湾村在李进祥笔下,成为一种文明的标志,李进祥的创作使得苦涩的清水河有了神圣的价值,赋予其灵性和文化意蕴。
《剃头匠》写给快完的人剃头的事情,人物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匠人了,使人一下子想起电影《入殓师》,写入殓师赋予人入殓前最后的尊严和体面,已经不仅仅是一项工作,是值得人们尊重和敬仰的事情。谁没有那个时刻?我们当下的一些文学和文化,特别缺乏这种温暖的、关于人的最起码的尊严的持守。《遍地毒蝎》里对瘸尔利、家、三口水缸、河湾村与人心的贪婪的书写,标志着李进祥的创作内容走向着意探索人性善恶的高度,追问生命轮回的广度。《换水》的价值在于人的反思与忏悔精神。一个真正的高品质的人的成长的生命体悟,人们只有回到人类本初的淳朴、自然,才会离“人”更近一些,这种思考和杜甫同质,这样宏阔、高洁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追求构建了李进祥的生命价值。
苏珊·桑塔格认为,“作家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狗村长》的创作思路非常独特,且这个问题直接影射和关照人性,“揭示真相”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情。《狗村长》已经脱离了讲故事的层面,很多方面都在构建一种艺术魅力,尝试一种低到尘埃里的眼界。李进祥在这冷峻和沉郁的气质上,又中和了一些内敛,不时地也会有一些亮色、一股暖意。
《立交桥》这部中篇,写的是由于要建立交桥,周边拆迁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地方的特例,李进祥关照的视角好,从法官梅笙和民工杨志两个角度写,两条线索,两个对立的群体,两个人,法与人情透彻入肺。能写当下,也能够回顾历史。《生生不息》写的是关于麦尔燕这个孤寡的女子,关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海原大地震。地震把村子揉碎了,把女人的心也揉碎了。《带着男人去北京》写乡村女人带着男人去北京治病,病很重,男人很无力,一路各色人等,不过虽然陌路,知道了他们的事情后,都伸出了援手。这个时候的李进祥对于人性已经有了准确的把握,生活很残酷,命运很悲凉,生命中的良善却是大多数,不由让人有了希冀和生命的光辉。
三部长篇,《孤独成双》讲述了穆萨的孤独,大概也是李进祥内心成倍增长的孤独的精神写照。这时,李进祥长篇小说的驾驭才刚开始,在作品的宏大叙事和历史感方面还是欠一些火候,但是在个体生命价值的反思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拯救者》,这部长篇是李进祥打算大力度离开清水河,探索新的创作路子的一个尝试。生命有时候感觉走到了极窄的地方,甚至没有了出路,一个心念,或许就豁然开朗,不以为意了,还有什么比命更重要。从文学性来看,是值得一读的好作品,但是放在整个当代文坛,每年长篇小说都有几千部,就没有明显的、超凡脱俗的个性特征了。最后一部《亚尔玛尼》,也是缘起逃离,回归落寞与孤寂的人的终极。六指是一个凡人,又不是一个凡人,是一个农村人,又不是一个农村人,李进祥在追问逃离与回归,在探索生命的哲思与苦痛。有时候想,作家思想的深邃,就在于他们看得比常人透彻。
李进祥一心探索人性,小说创作渐趋内敛、凝重,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不断增强,爱是一种最起码的人情,饱含了丰富复杂的情感内容,而不是一切都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活得卑微而又艰难。卑微与高贵和身份有关,大多时候又无关,生命价值要义在于首先活成个人。
四、审视现实:沉郁内敛的审美品格
沉郁是一种深重的家国情怀,是一种深沉的故土之恋。李进祥沉郁的精神、冷峻的笔调、内敛的品质、朴拙的语言,构成了清水河书写这一主题,抒发无尽的乡愁、忧思和爱。李进祥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围绕着清水河,还是另辟蹊径,寻找悬疑和神秘,在艺术上皆是经过了绵密的量的积累,由最初自然、生态、诗意的想象,中期反思人性、反思生活价值,到逐渐审视社会,走向深重的现实,达到艺术创作的成熟。其沉郁的情思、苍凉的笔触、内敛的气质,流利质朴的语言,在宁夏小说创作中,也算得上是独树一帜。“倘若研究者只是想当然地把文学单纯当作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的一种翻版,或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献,这类研究似乎就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且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6]李进祥的小说对转型期宁夏南部山区乡村的生活有着全面的把握,对乡民的生活追求和精神诉求也理解得比较透彻,能够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丰富、复杂,进行艺术呈现和理性升华。 “文学的确不是社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7]从反映论的角度看,深度阐释作家艺术手法的重要地位,更加有利于揭示作家的艺术手法对于揭示社会生活、反应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花样子》里“花样子”这个女人,她的故事充满了传奇和神秘,既有李进祥初期的诗化和唯美,写出了河湾村宛如桃花岛,又有中期善于构建小说叙述氛围和基调的艺术张力,在文本的处理上显得很是成熟,并且逐渐显示内敛含蓄的笔调。《鹞子客》刻画了敢爱敢恨的法图麦,这部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又凸显了李进祥独有的艺术特质,他太善于观察人和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瞬间和一闪而过的心灵。
李进祥围绕着清水河和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两个主题,不断地交错,也反映出创作的无法超越自己,以及焦虑痛苦的创作状态。写了五十多个中短篇以后,李进祥在创作手法上才渐次形成和稳定下来,沉郁与悲凉、哀伤与愤怒,使得李进祥对现实的书写增加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李进祥举凡书写人物,无论是正面描写还是侧面烘托,都是写得饶有趣味,读起来文字流利,语言清新明丽,就是写是悲剧,也是不温不火,有时候甚至轻描淡写,令人扼腕、唏嘘不已。
《路上遇见的几个人》,突显了李进祥善于观察和刻画人物,且善于诉说,并且很有亲近感。这一篇,我们可以看作总体体现李进祥艺术风格的作品。在新的历史时期,温饱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精神的慰藉,文化的交融,故乡与精神还乡,成为主要命题。小说写主人公去大都市上海看世博会,路上遇见了几个人,一个是上海的哥,写“我”去上海看世博会,主要是去上海交大看女儿,由于路线不熟,就打了车,一路和的哥的闲聊,透视出在大都市生活的底层人的不容易,也写出了的哥的乐观情怀。一个是杭州保安,写“我”去历史名城杭州游玩,与一位自安徽出来打工的保安聊了起来,这次李进祥关注农民工是从城市的视角,写了保安这一很重要的打工群体。还写了一位北京保洁员,年龄实在很大了,说是自山东来北京,由于男人有病,只好来北京讨生活,二十多年了,做保洁,借保洁之口,讲述了在北京打工的种种情形。还写了广州的服务员,居然是从固原到的广州,也三四年了,当过保姆,也在一些厂子干过,如今和当厨师的男朋友一起在一家饭馆打工,由于“我”是宁夏人,到了广州专门找了一个清真面馆,想吃个炒揪面,可是外地厨子不会,小服务员一听“我”是老乡,就自告奋勇的给“我”揪了面,还把腌好的他们自己吃的酸菜给我,吃完面,还不收饭钱,从小姑娘听到乡音,缓缓流淌的泪水,“我”知道了,她是真的想家了。这一篇,没有过多地写打工的艰辛,反而描写了女孩子的盖头,写了女孩子出外的原因,也算是逃婚或者选择城市生活,细节展现惟妙惟肖,尤其写“我”和女孩子“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女孩子的男朋友敌视地端详着我们聊天的样子,真的是太出神入化了。一种乡愁、一抹小姑娘脸上的红晕、一条飘动的有流苏的盖头。仿佛李进祥出道时候的那种写法又出现了,那种废名的,或者沈从文的,特有的描摹女孩子的写法。
李进祥围绕着一条河流、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镇子展开,社会转型对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的生活追求、精神理想、文化进步等等,都被无限放大。没有了宏大叙事的日常,更注重人物心理特征、思想提升,成为一个时期重要的叙事艺术,也成就了李进祥的艺术审美特质。
《白头》写了爷爷和大爹的故事,很有一些西北民间的历史感。适合拍个剧,很传奇。悬疑和传奇,奇思与妙想,是李进祥追求的审美想象。六十多个中短篇,李进祥不可谓不勤奋,应该说很勤奋,量很大。出彩和新意确实很难,李进祥依然感到很困扰。同时也开始关注整个世界局势,眼光放在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且21世纪初,宁夏出外打工已经不仅仅到外省了,许多人已经出国做生意和打工了。这也是同心这个地方的特别之处,回族善于经商。眼界和心思的开阔,就有了《四个穆萨》,写了四个同叫穆萨的人,作家“我”,一个中国的农民工,一个在阿富汗,一个在叙利亚。写域外的两个穆萨背井离乡的绝望和挣扎,外出打工的穆萨依然遇到的是普遍的打工者的问题,我是见证者,更是慨叹者。明显地,李进祥的眼界、理趣、精神向度都得到很大提升,老百姓生活不就求个安稳吗!
李进祥的小说创作量多质优,出版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集3部、中短篇小说集1部,发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3篇、短篇小说68篇。每一篇都是一部心血,都是又一种可能的尝试。在这种新的艺术可能的尝试中,回归最初的朴拙,仿佛也是李进祥最后的感伤。
李进祥一心探索人性,小说创作渐趋内敛、凝重,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不断增强,更注重人物的内心。李进祥小说里的人物既是小人物,也是一种常态。他的创作不仅仅探索乡土守成,更挖掘城市生存困境,追索现代生活。总体而言,不读书,没有文化,总是没有出路的。读了书,心黑了,没有了人味,恐怕是更可怕的了。
李进祥从来没有站在高处俯视。他的孤独、忧愤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洞悉了生活的难处,尝过生活的苦涩。但追问生命的价值要义,是苦痛的事情,囿于多年的忧思和劳累,“可惜流年,忧愁风雨”(辛弃疾语)。
对于城与乡,这个两难话题,自五四时期,更是文学热衷的话题,鲁迅的《故乡》,听到一声“老爷”,我们还能说什么呢。鲁迅认为团圆主义文学就是“瞒与骗”的文学,需要“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8]沈从文《生命》则说“每个活人都像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我说的是离开自己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这样事情,活人中就很少那么作。”[9]沈从文大概说的就是文化自觉吧。我想李进祥的小说创作还是有明显的文化自觉的。追问生命的价值要义,是苦痛的事情,凡俗与高贵也就差那么半步,谁又比谁更清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