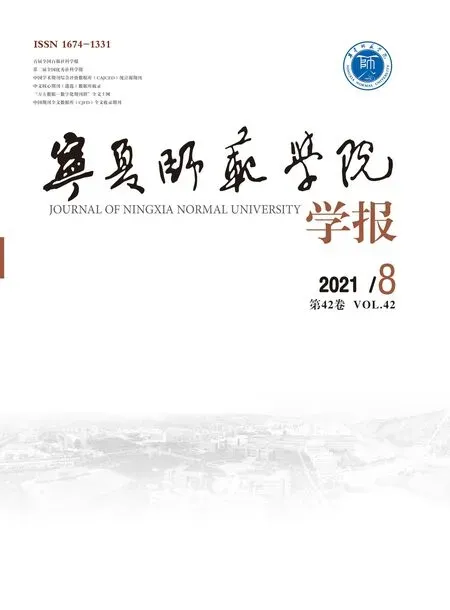生态文明视域下环境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司法研究
洒 爽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刑事政策作为国家对犯罪的正式回应,历来是刑事政策最重要的核心和亮点。我国刑事立法司法总体缓轻的形势下,唯独对环境犯罪体现了刑事政策趋严的一面,这是我国当前环境犯罪严峻性和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政治理念之一所决定的。良法还需善治,法律制定的目的是依法执行,环境犯罪罪刑的执行都应以刑事政策的观点为出发点与落脚点,都要以是否符合刑事政策的目的作为检测标准。环境犯罪“从严”刑事政策须贯穿至环境犯罪司法工作的全过程,达到二者良好互动的状态。
一、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制定的刑法依据进路
研究环境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司法运用首先要了解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指定的法律依据,通过研究环境犯罪刑事法律发展轨迹,可以涵射出法律背后刑事政策实践导向和价值选择。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进程主要分为以下三方面:
(一)萌芽阶段
我国环境犯罪萌芽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受时代发展限制,1979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为工作之重,且这一时期我国环境犯罪问题并不突出,人们的环保意识较薄弱,社会一切工作基本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与目标,故此在1979年《刑法》中并未单章规定环境犯罪,只是散落在刑法分则的其他章节中,如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等。
(二)起步阶段
经济建设常常伴随环境污染问题的发生,伴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经济发展迅速,环境犯罪问题逐渐显现,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与影响,法律规制作用不突出。立法者认识到在1979年《刑法》中分散规定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并不能发挥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威慑与遏制作用。刑法作为保障法,应保持严肃性与稳定性,不可轻易修改,针对环境犯罪立法滞后性的弊端,在考量刑法的性质地位后,立法者采用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弥补法律不足,尽管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进一步加大了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丰富了我国环境犯罪法律体系,但规定不够宏观,处于分散状态,相关法律里关于生态环境的整体考虑不够,刑罚尺度不够统一且处于偏低状态,与我国司法实践匹配度不高,缺乏司法操作性与借鉴性。
(三)进塑阶段
随着民众对良好环境的诉求不断加码,环境犯罪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众矢之的[1],环境刑事立法也得到了“里程碑式”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1997年《刑法》分则在第六章第六节中设置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该专节主要对污染环境与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这一立法改动意味着我国刑法正式承认和确立环境犯罪的存在。在此之后,在国家对生态建设愈发重视的背景影响下,为了响应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立法机关以刑法修正案为改进途径,对环境犯罪立法不断进行修正与补充,如《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修改后的罪名不仅注重环境污染危害结果,也注重污染环境的危害行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提高污染环境罪法定刑,解决了污染环境罪量刑偏低的现状,加大了对环境犯罪的惩处力度。
二、我国环境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司法适用微观审视
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具有方向性的、根本性的指导原则。立法与司法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环境犯罪“从严”刑事政策通过立法进一步影响司法适用。在严厉打击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下,污染环境罪案件在司法适用中呈现出明显的不统一、不规范之状态。[2]
(一)司法审判中量刑需基准
通过实证研究可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环境犯罪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状,证明司法机关关于贯彻从严打击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成果,但在具体审判中反映出司法审判治理环境犯罪案件出现量刑不规范的现象。笔者以污染环境罪司法审判情况为例,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对X省的一审判决案件自由刑适用情况进行统计(一名涉案人员免除刑罚),其中被判处拘役的涉案人员占比44%;被判处为一年一下有期徒刑的涉案人员占比33%;被判处一年上三年以下的涉案人员占比23%,无人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在以上案件样本中出现自由刑相同但罚金刑分别为“五万”与“一万”之差的情形,且并未呈现自由刑越重罚金额越高的同步状态,虽然实务中影响二者状态的潜在因素较多,出现不统一的状态并不背离法律规定与秩序,但通常而言自由刑与罚金刑大体上应呈正比趋势,司法审判中量刑不规范,不能更好发挥“从严”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
(二)司法审判标准不统一
环境犯罪的判决书出现“严重后果”“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严重”的结果性要素词组频率较高,然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罪状并未对以上词组的具体概念规制统一、明确的法律标准。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3年和2016年先后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部司法解释,并于2019年2月印发了关于解决司法解释适用困境的文件——《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上述文件的出台对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司法适用起到关键性指导作用,但是遗憾的是以上文件对环境犯罪造成的结果评价并未形成具体、系统的评价标准,使得环境司法难以完全贯彻从严惩治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德国刑法学界威尔泽尔做过这样的阐述:没有法律就没有惩罚的真正危险并非来自类推,而是来自不确定的刑法规范。现实考量中,由于“从严”刑事政策实施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司法运行过程,实践中“从严”的把握具有鲜明的主观特征,司法工作人员的执法水平与理解能力又参差不齐,因此极易产生执行缺位的问题,从而与政策的制订初衷相悖,无法发挥政策应有的作用。[3]
(三)以罚代刑趋势明显
环境犯罪具有行政附属性的突出性质,刑法被视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在环境犯罪案件治理中,行政手段通常占有主导地位,即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链接不畅。两法衔接产生于我国违法和犯罪的“二分治理模式”,即对于违法行为由各级行 政机关及其部门进行处罚,对于犯罪行为由司法机 关进行制裁[4]。环境犯罪治理中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无法做到及时连接,案件移送困难,因此造成明显的“以罚代刑”趋势。环境刑事司法乏力的状态不但会影响环境刑事司法的效能,同时也会使环境污染犯罪行为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进一步表明了我国从严惩处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与打击决心,环境犯罪以罚代刑的现象与我国目前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精神相悖,需要平衡环境行政法和环境刑法的规制动态。
三、我国环境犯罪“从严”刑事政策司法适用改良思路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环境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理念与诉求应该在刑事司法中得到贯彻,对此问题应以转变司法观念为基础对司法适用进行完善。
(一)转变司法观念,提升生态思维
当前生态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环境法益已不再单纯为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法益观逐渐被吸收。当社会环境和发展背景发生变动时,刑事政策作为法律构建的影响因子也会推陈出新,审时度势地随之发生改变,进而指导司法活动的理性选择。在司法活动中须提高政治站位,司法观念应向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方向转变,促进理论成果与司法实践的相互转化,在环境犯罪行使司法审判中考虑案件对生态环境的整体影响和后续恢复的程度与可能性,结合案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综合进行处罚,科学量刑规范。
(二)贯彻从严惩处刑事政策,坚持有罪必罚
鉴于环境刑事案件往往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环境犯罪的处理过程中往往会受到“隐形”因素影响,如司法人员失职渎职等情况。从严惩治环境犯罪首先要做到有罪必罚,体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双重作用,因此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创新改进。
首先提高环境犯罪案件司法审判人员的专业性与工作自主独立性,建立环境司法案件办理的监督制度,增强案件办理的公开性透明性。
其次加大环境犯罪司法科技投资力度。环境犯罪行为本身具有专业性和隐蔽性,同时结果显现缓慢,因果关系证明相对复杂。[5]在智慧司法工作推动的背景下,鉴于环境犯罪案件的复杂性,采用科技手段可提高案件结案效率。例如构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网络共同办案平台,跟踪案件进程;对于案件涉及的专业性知识,可以考虑引进专业设备抑或与相关企业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加强环境犯罪司法审判的能动性与专业性。
(三)提高行刑衔接能力,考虑推广多元共治的联动机制
基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客观事实,我国各地区环境犯罪的主要类型和特征并不统一,针对各地区环境犯罪态势的因应剖析,可考虑在地区开展多元共治的联动机制,环境犯罪审判机关可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政和执法部门进行配合协调,多管齐下共同发力。如我国首例非法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就采用了由生态环境、公安、应急、检察、属地政府共同联动治理的模式,该案件的治理全过程采用多部门联动机制,达到了公平惩处的良好效果,是一次具有极强借鉴性与参考性的司法实践。
四、结语
环境犯罪“从严”刑事政策通过指导刑事司法,使“从严”政策精神转化为刑法制度与审判模式,环境犯罪司法适用要将“从严”刑事政策作为目标进行发展运作,持续转变司法观念,坚持有罪必罚的司法原则,建立信息共享、联合共治的司法机制,用法律手段保卫生态底线,为犯罪治理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建设美好生态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