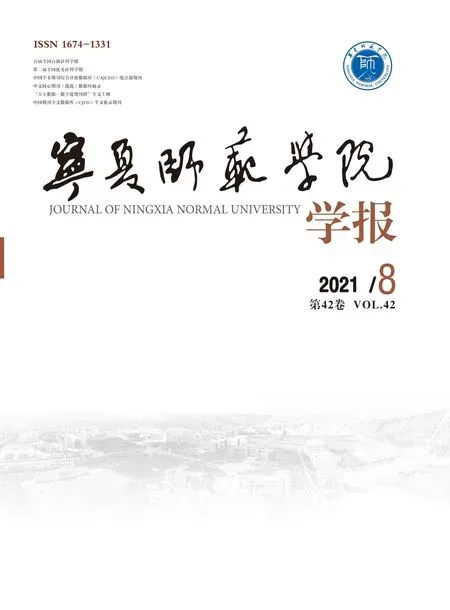《禁房情变》与《柳暗花明》的互文性解读
张海峡
(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宁夏 固原 756099)
《禁房情变》(ReflectionsinaGoldenEye)是由约翰·休斯顿改编自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小说《金色眼睛的映像》(1941)的一部电影,于1967年在美国上映,又名《春色撩人》《金丝雀》等。影片上映时,作者刚满50岁,《纽约时报》刊载了作者的巨幅肖像,题为“弗兰淇(作者另一部小说中具有自传色彩的主人公)五十岁了”[1]。作者在世时,其作品就被改编为电影呈现在观众面前,由此可见作家以及这部作品魅力不俗。事实上,这部电影在改编过程中对主题的深度把握和捕捉表现出了它对小说原作相当高的忠实度,这使得作为影像艺术的影片在艺术内涵与伦理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为剧情-伦理类型的影片《柳暗花明》(AwayfromHer)也是这样一部电影。它是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小说《熊从山那边来》的电影版,于2006年在加拿大上映,又名《远离她》。由于受到影像时间容量和受众的审美差异等因素影响,观众对艺术主题的领悟同电影的表达之间存在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艺术初衷的实现和传播效果。而经过对两部电影的互视和比较,发现二者在男性人物凝视的展现和电影音乐的性别气质与结构内涵两个方面形成突出的互文关系。一方面,镜头对男性凝视的强化揭示了凝视从实施权力欲望走向两性交流的生态轨迹;另一方面,电影音乐在性别气质与结构形式上的巧妙用心突出了影片内蕴的女性意识的主题,尤其开放性结局对两性间感情生态可能性的探讨富有建设性启示。
一、凝视的呈现
凝视作为一种专注的看视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福柯从医生、警察、精神病院管理者等人的视角发展这一概念时认为,凝视行为对被注视者而言是一种监禁,显示了主体的权力具有隐蔽性和规训性。[2]凝视因而成为一种具有投射欲望意义上的霸权行为。而随着女性的发展与女性意识的不断成熟,女性的斗争与反抗造成了男性的焦虑,这反过来又促成了男性的反思,使凝视行为开始向交流的方向发展。通过对两部影片的互读,其凝视镜头的呈现在实现和消解权力的双重层面表现出较深的意义。
(一)实施权力欲望的凝视
两部电影开始时的镜头都与凝视相关。《禁房情变》在用音乐与字幕预先铺垫了电影气氛后,首先展现的便是二等兵威廉姆斯迈着漫不经心的步子,带着麻木的表情在夜幕下走向营房的镜头,目光专注。这个镜头与其说是将电影人物刻意置于观众的凝视之下,不如说是将主人公的凝视行为突显在观众面前。威廉姆斯是和平时期在美国南方一个偏远哨所服役的士兵,沉默寡言,甚少社交。他自小便被长辈灌输了女人的身体有毒的观念,因此一直对女人心存警惕,从不靠近。有一天晚上,他漫步经过潘德腾上尉的家门前。上尉家灯火通明,窗帘没有拉下来,他看到了上尉的妻子利奥诺拉在同上尉吵架后脱得一丝不挂的身体。从此,他展开了对女性身体的想象,这一想象连同先前偶然的户外窥视一起导致了后来他多次的入室偷窥。影片中男性人物的凝视有两条线,这是其一。其二是在威廉姆斯的凝视背后,具有微妙的两性气质的潘德腾上尉逐渐注意到了他,对他产生欲望,时时关注他甚至最后跟踪他,对他展开凝视。作为第一条有关凝视的线索,二等兵威廉姆斯对利奥诺拉的凝视从无意中的室外窥视到有意地入室偷窥,从实现窥看欲望和私自侵犯两个方面表明他这一行为是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欲望促使威廉姆斯擅闯他人的私密空间,满足个人情欲,对女性实施男权。在第二条凝视的线索中,潘德腾对威廉姆斯的迷恋之深使得他对威廉姆斯有了愈发强烈的控制欲,以至于潘德腾常常利用自己的军官身份对威廉姆斯实施权力控制。
《柳暗花明》亦是以男主人公为中心,强调凝视的影片。剧情之初,先是男主人公格兰特一边开车,一边盯着手里的一张纸条核对地址,然后镜头便对准了他回忆里的妻子年轻时的形象。接着是夫妻二人在厨房里的情景,在他的凝视下,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妻子的记忆出了问题。镜头在“现实——回忆——现实”的轨迹里切换,加强了男性主人公的视角。影片中格兰特的“凝视”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影片开场所展现的画面,即凝视年轻时的菲奥娜。那个时候男主人公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虽对菲奥娜心存恋慕却没有大胆表白,直到后来菲奥娜开玩笑似的向他求婚,他们便结婚了。而他的风流本性在婚后便显露出来,他在学校常和女学生们暗自暧昧,甚至惯于利用教职身份引诱女学生。在纵览全片的高度上,回忆式的镜头中他对菲奥娜的凝视暗示着他对女性的权力实施。第二阶段是菲奥娜住进疗养院后,他在每一次探视中对菲奥娜乃至于其他病人所实施的凝视。此时,他以身体健康的探视者身份对疗养院中的菲奥娜和其他病友进行凝视,颇具有福柯式的权力意味。
(二)走向两性交流的凝视
然而,《禁房情变》中威廉姆斯的窥探行为有明显的悖论存在:一方面,他对利奥诺拉的窥探仅限于看的行为,而没有将其发展为真正对欲望的实现即身体接触;另一方面,他行使男权却也藐视和反抗男权。以前,除了女人的身体,他从不畏惧什么,比如父亲、上尉。如今,他似乎也不畏惧女人的身体了。随着剧情推进,故事以二等兵对潘德腾妻子身体的凝视和潘德腾对二等兵身体的凝视为递进,显得越来越文艺,其内涵也越来越不似一部单纯的凶杀案那么简单。这两个递进的视角成为深入理解影片内涵的关键。二等兵既是凝视者也是被凝视的对象,也就是说,既是权力发送者,也是权力的承受者。从入室偷窥败露被枪杀的结局来看,二等兵威廉姆斯总体上是一个霸权的受害者。较之潘德腾,他的凝视更多地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想要揭开一个关于女人有毒的谎言,这使他对利奥诺拉的侵犯在罪行层面以外增添了不同的意义。
在《柳暗花明》中,格兰特作为凝视行为的主体,事实上也充当着被凝视者的角色,也在体验被凝视的不自在感。第一阶段的凝视反射体现在他在梦中被那些有怨气的女学生们所凝视;第二阶段则是他在草地湖疗养院被护士和院长凝视。两个阶段里都充满着格兰特的男性焦虑。第一阶段里,出于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所隐约感到的威胁,她与菲奥娜及其家庭有距离感。这解释了他在婚后甚至感到妻子对他的不轨行迹有所掌握的情况下仍与女学生们暧昧,是在焦虑感中努力维护男权自尊的行动,不过在他后来遭到风波离校后就再没有发生过。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凝视,是格兰特男性凝视下对女性的欲望投射,显示的是男性对女性的消费与控制,那么比起他先前对女学生和这之后对奥布里的妻子玛丽安的凝视,这第二个阶段里的“看”的行为少了权力的色彩,更多的是无言的观察。他在欲望与焦虑的双重压力下,选择用心走近妻子,逐渐试着卸下一部分权力的生硬,寻求精神和解,这赋予探视一种观察与自省的意义。该变化在于,格兰特既害怕妻子得知自己过去的劣行,又担心妻子因患记忆障碍症而遗忘过去,他此刻的观察是在双重焦虑中了解病人,同病人沟通,以此去除权力性凝视行为。这一走向平等的交流为后面他以丈夫的身份为妻子带来她思念的恋人的行为作出铺垫,为他匪夷所思的行为给出了有关人性复杂的解释,即徘徊与挣扎在欲望与救赎的两端,欲望甚至充当着罪与赎的双重功能。
二、电影音乐的气质与形式
作为画外音乐,“电影音乐”这一术语指的是“剧情元素,是一个叙述的结构形式”[3],有时候同“电影中的音乐”共同出现,有时候单独出现。“在电影接受中,电影音乐与视觉元素相比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电影音乐在大多数时候是不被意识到的,但是它也非常重要……通常来说电影音乐能够渲染电影情节潜在的感情。”[4]电影音乐是电影叙事除图像和对话以外最重要的表达元素,与主题构建密切相关。两部影片不约而同地都将电影音乐作为必要的表达元素,尤其在片头和片尾巧妙地发挥出制造叙事与建立形式的作用。
(一)音乐的性别与性向模式的叙事效果
音乐的性向模式是音乐性别气质的基本取向,以音乐的方式无声地为主题的展现奠定基调。卡森·麦卡勒斯是一个极有音乐感受力的人,她的作品总会在内容或结构上有音乐元素的参与。
《金色眼睛的映像》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禁房情变》后,电影的音乐叙述同卡森小说的音乐性形成呼应。影片开始时以字幕的方式交代剧情,伴随着由沉重而富有金属感的声调构成的电影音乐,激愤铿锵、刚劲有力,仿佛是悲剧的结局将每一个音符撩拨得跳动不安,在听觉上给人一种男性气质的印象。凶杀的主题,令人不安的紧张氛围,受到自己双性气质折磨的主人公难以抑制的焦虑情绪都被音乐叙述出来了。电影音乐在瞬间唤起观众持续关注的紧张与不安的同时,将它所强烈暗示的悲剧原因也引向了男主人公这一方面,即音乐的侵略性力量与引发男主人公潘德腾上尉焦虑的力量——男权主义思想交相呼应,成为观众进一步理解影片内涵的有力依据。
《柳暗花明》中响起的钢琴曲则浑厚深沉而不失优雅,舒缓绵延的曲调中流淌着回忆的静谧感和生活的永恒感。电影以这样的音乐作为开始,逐渐展开了男主人公格兰特拿着写有地址的小纸条驱车去往目的地的画面,与此同时也开启了他的旁白。此时,观众随着镜头的移动进入故事,耳边似乎仍回想着方才的音乐。音乐十分动听,仿佛在款款诉说着既体验了风花雪月也经历了风霜与沧桑的岁月一路走来仍不失优雅与温暖的气度。抒情风格的音乐颇具女性气质的细腻敏感与包容力,先入为主地为观众在后面反思婚外的欲望与婚内的救赎的伦理内涵打下情感基础,深入人心,引人深思,与强调悲剧性不同的是它的启迪性。相比《禁房情变》中电影音乐的侵略性,抒情性音乐为《柳暗花明》营造了更富有沉思感的氛围。在电影音乐的性别气质对比中,《柳暗花明》富有女性气质的电影音乐使得影片的主题内容富有启发性和探讨性。
(二)音乐结构的形式意义
结构以其形式的存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禁房情变》的片头音乐令人不安,富有警示性,在片尾重现并与结尾的凶杀案结局相呼应,将权力欲望的控制力与毁灭性充分展示出来,叩击人心,触及灵魂,形成了电影的封闭结构;《柳暗花明》首尾音乐节奏统一,从故事的开头到结尾,一直以舒缓的节奏渲染着观众的情绪,直到结尾处也没有收住的意思,营造了一个没有结局和终点的故事,将影片置于一种开放性当中。开放性的结局意味着,一段携手走过40余载婚姻生活的老年夫妻,面对欲望与背叛、遗忘与救赎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并非一个拥有简单答案的问题,并且提供答案也不是影片创作的目的。开放性的音乐叙事的意图之一是对该问题的可能性作更多探讨和设想。“结构越是不确定,越是含糊,越是不可预见,越是不规则,信息就越会增多。所以,信息被理解为交流的可能性,即可能秩序的始动性。”[5]结构的开放性将语义置于不确定性当中,为信息在量上的积累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这将造就以交流为基础的秩序的不规则性。在封闭结构的确定性与开放结构的可能性之间,电影音乐所提供的信息着重指向了这样的意义,即具有开放结构的电影能够更有力地预见女性意识要求冲破父权秩序的自觉。由此可以见得,较之《禁房情变》的相对封闭性,《柳暗花明》在思考当代婚姻伦理、探讨权力话题方面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作为故事元素的音乐“可被用来表达与特定人物有关的思想”,“也可被用来追踪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和价值观”,其戏剧价值在于:“一旦设立了象征,随后每一次提到都能暗示变化。”[6]两部影片都将电影音乐作为主题表达策略,以其流动暗示情节趋势,生动描绘主人公挫败和焦虑的心绪、复杂人性的意识流动以及伦理思考。
三、结语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1975)一文中用精神分析法阐释了电影魅力得益于预先存在于个人主体以及形塑他的社会魅力的范式。在阐释男权思想无意识构建电影形式的过程中,她指出:“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悖论在于它依靠被阉割的女性赋予其世界以秩序和意义。”[7]女性作为形象为男性的注视快感提供支持。这主要表现在男性在对女性身体的注视下或凝视中,获得了原始欲望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进而为其自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种具有强烈父权制色彩的观念在社会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紧紧地束缚着女性,使她们同男性的依附关系更加牢靠。叙事电影也常常通过这种范式,潜在地满足着绝大多数观众的无意识的文化期待。然而,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女性越来越独立,她们对父权制思想的反抗最终使她们对男性的依附减弱,这与男性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焦虑与失落情绪一同,构成了艺术文本中男性“远离她”的交际景观。作为文艺色彩浓厚的叙事电影,《禁房情变》和《柳暗花明》在速食主义文化背景下显得晦涩难解,然而通过对比两部电影,发现二者在电影视角与电影音乐方面的互文性,两部影片都采取了突显男性人物的凝视来揭示当代社会男权思想对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社会人的压抑以及交际现状,用电影音乐的性别气质和结构形式来暗示男权压力下感情生态构建的可能性的影视艺术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