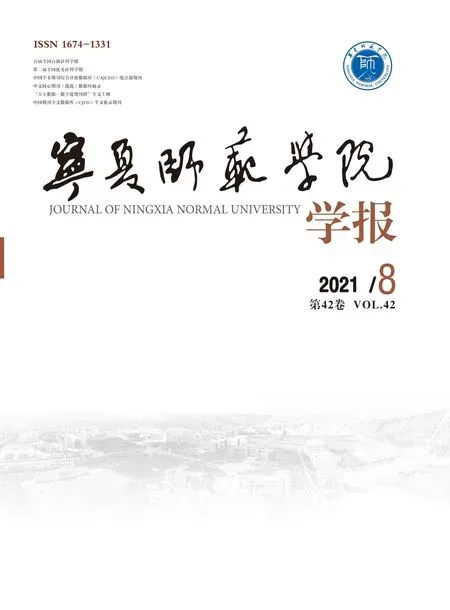唐代气候变化背景下河套地区城市发展与生态变迁
保宏彪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竺可桢先生通过对中国古史所载物候信息的长期研究,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指标,将中国近五千年历史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认为唐代属于第三个温暖期[1]。这一时期的气候总体温暖,变化趋势是由暖入寒,以 780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气候温暖,后期逐渐转寒,严寒事件增多[2]。结合《旧唐书·五行志》《新唐书·五行志》和相关人物传记来看,781—850 年间共有36个寒冬,平均每两年出现一次极寒天气,气候整体寒冷[3]。气候的冷暖变化对农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在深受温带大陆性气候影响的河套地区,以农业生产、牧业生产、城市发展为代表的人类活动呈现出与之相合的历史轨迹。温暖湿润的气候不但为河套地区开展大规模屯田提供了优越条件,促进了农业繁荣与城市发展,而且为河套地区畜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各游牧部族获得稳定生活保障后选择与唐交好,农牧业分界线相对固定。随着唐代中后期气候转寒,河套地区逐渐呈现降雨量减少、自然灾害频发等不利局面,对当地农牧业生产造成巨大冲击,屯田规模缩小、牲畜大量死亡成为典型现象。
一、唐代前期温暖气候下的城市与生态
(一)城市发展
自古以来,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离不开有利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唐代前期,温暖湿润的气候为河套地区农业生产提供了适宜温度和丰富降水,大规模屯田如火如荼。贞观四年(630),唐朝在攻灭东突厥汗国后推行羁縻府州制度,在学习隋朝固边经验基础上,通过重要军镇和普通军城的相互协同构筑外、内两层河套防线,有力维护了河套地区的稳定。在这一背景下,河套地区出现安定统一的大好局面,长期存在的对峙、对抗氛围一扫而空,随之出现的是农牧业生产的空前繁荣。温暖湿润的气候推动了河套地区水利建设的蓬勃发展,丰沛降雨为黄河带来了充足水量,一些荒废的水利设施得到恢复并重新用于农业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灌区。持续扩大的农耕区与各羁縻州内的牧区交错分布,奠定了半农半牧的新发展格局。河套地区的农业发展不仅保障了当地人民生活,而且大规模屯田为河套边防体系提供了充足给养,唐朝不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运送粮草。这样既解决了军粮需求问题,又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这一时期河套地区的城市发展以夏、灵二州和天德军最为典型,以六胡州为代表的羁縻州县也是一大特色。
1.夏州
夏州的治所位于朔方县,是一处水草丰美之地。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北游契吴,叹曰:‘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4]契吴山在朔方县境内,环境优美、生态宜人是赫连勃勃将大夏国首都统万城选址于此的重要原因。唐朝初年,唐太宗出兵征讨割据夏州的梁师都时曾将其困在朔方城中,为断绝城内粮食供给而“出轻骑蹂其稼”[5]。由此可见,唐初夏州地区生态环境良好,适合开展农业生产。收复夏州后,这里不但是唐朝在河套南部最为重要的屯垦区之一,而且是羁縻府州的主要设置地区,城市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2.灵州
在唐太宗规划的羁縻府州体系中,灵州是安置突厥、铁勒、回纥、粟特、吐谷浑、党项等部族民众的主要地区。麟德年间(664—665),崔知温担任灵州都督府司马之职,“州界有浑、斛薛部落万余帐,数侵掠居人,百姓咸废农业,习骑射以备之。知温表请徙于河北,斛薛不愿迁移,时将军契苾何力为之言于高宗,遂寝其奏。知温前后十五上,诏竟从之,于是百姓始就耕获。后斛薛入朝,因过州谢曰:‘前蒙奏徙河北,实有怨心。然牧地膏腴,水草不乏,部落日富,始荷公恩。’拜伏而去”[6]。因为宜农宜牧的灵州生态良好,所以吸引数万浑、斛薛部众聚于此地放牧。这些以游牧业为生的漠北部众眷恋灵州的丰美草场,对崔知温将其“徙于河北”的建议颇有怨言。在崔知温的一再坚持下,数万浑、斛薛部众被迫迁出灵州。不过,得益于唐初温暖湿润的气候,即使黄河以北也广布适宜放牧的丰茂草场,所以斛薛才对崔知温由怒转喜,在途经灵州入朝时向其表达感恩戴德之意。崔知温此举不但消除了干扰灵州农业生产的社会因素,而且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拓展了灵州农业的发展空间。开元七年(719),“河流渐逼(会)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团练兵起作(黄河堰),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没”[7]。黄河顺会州北上进入灵州,黄河堰的修筑完善了灵州水利设施功能,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据成书于开元末年的《唐六典》记载,当时灵州共有屯田 67屯[8],可为河套防线驻军提供充足的军粮储备。
3.天德军
在温暖湿润的气候作用下,就连黄河以北的天德军也成为适宜屯垦之地。天宝八载(749),“木剌山始筑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诏(郭子仪)即军为使。俄苦地偏不可耕,徙筑永清,号天德军,又以使兼九原太守”[9]。因为天德军利于屯垦,所以唐朝将横塞军从木剌山徙筑于此。天德军靠近黄河,水利灌溉为发展大规模屯田提供了充足水源,有利的光热条件则是开展农业生产的基础,足够的光照和合适的温度为农作物茁壮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得益于此,以黄河北岸的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为主体,众多烽燧为辅助的河套外层边防体系才能建立,天德军、振武军、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等军政机构因而成为维护河套北部稳定、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巩固民族团结的有机载体。
4.六胡州
调露元年(679),唐高宗在灵州境内设置鲁、丽、塞、含、依、契六州安置粟特部落,史称“六胡州”。长安二年(702),位于河套南部的六胡州遭到后突厥汗国袭击,御史李峤奉命监筑被毁城池。竣工之际,李峤赋诗《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一首。“驱车登崇庸,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马牛被路隅,锋镝销战场”[10],形象描绘了六胡州地区草原辽阔、植被茂密的优良自然条件,反映出一幅牛马蔽野、道路繁忙、牧业兴旺、 安宁祥和的繁盛景象[11]。长安四年(704),六胡州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设兰池都督府,下辖六县[12]。
(二)生态变化
虽然唐朝气候的总体特征是温暖湿润,但期间也曾出现一些波动,间歇性发生旱、蝗、雹等自然灾害,为河套地区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
武德六年(623),夏州发生严重蝗灾[13]。众所周知,对中国农业生产危害巨大的蝗虫种类主要为东亚飞蝗和亚洲飞蝗。飞蝗喜欢栖息在地势低洼、易涝易旱或水位不稳的湖滩,尤以大面积荒滩或耕作粗放的生有低矮芦苇、茅草、盐篙、莎草等嗜食植物的荒地居多[14]。因为隋末以来的长期战乱,漠北和河套北部草场植被遭到大规模破坏,出现局部荒漠化。从东亚飞蝗和亚洲飞蝗的生活习性分析,干旱年份有利于蝗虫生育,宜蝗面积增加带来蝗虫数量的几何式增长,从而酿成严重蝗灾。贞观四年(630)秋,丹、延、北永等州遭遇冰雹灾害[15],对秋粮收获造成一定损失。这种短时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虽然具有一定偶然性,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套地区气候在总体温暖背景下的小波动,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当地农牧业生产。
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灵州河清”[1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海晏河清”成为歌颂太平盛世的重要象征和文化符号。结合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在灵州会见漠北各部首领并被尊为“天可汗”一事来看,“灵州河清”现象的出现具有颂扬盛世、彰显天意的深刻意味。不过,如果考虑到灵州在贞观四年以后成为唐朝安置突厥、铁勒等漠北各族降户主要地区这一背景后,就会认识到在灵州境内羁縻州县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各部牧民的放牧行为对恢复当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相对于农业来说,畜牧业对土地的破坏程度较轻,只要不采取过度放牧、破坏草场等极端方式,草皮的固定土壤、涵养水源能力会大为增强,从而减少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现象。
从《新唐书·五行志》相关记载来看,唐高宗时期河套地区气候出现了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变冷过程。永徽二年(651),“绥、延等州霜杀稼”[17]。从“霜”这一信息推断,灾害的具体发生时间应该是秋季。这场发生在绥、延等州的秋霜带来了大范围降温,骤寒对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一定损失。调露元年(679),“突厥温傅等未叛时,有鸣鵽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警曰:‘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兆也。’至二年正月,还复北飞,至灵夏已北,悉坠地而死,视之,皆无头。”[18]“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兆也”反映了以游牧业为生的突厥部众缺乏抵御旱灾、寒灾等极端灾害能力的事实,在饥寒难耐、牲畜大量死亡的境况下不得不大举南下“犯塞”。调露二年(680),大批突厥雀北飞至灵、夏二州以北后坠地而死,这应该与飞行路线遭遇极端严寒有关。
河套北部虽然遭遇极端严寒气候,但是得益于农牧业生产的因地制宜和水利事业的有序发展,丰州在调露二年出现“河清”现象[19]。随着河套北部严寒气候的持续,旱灾接踵而至。“永淳中,岚、胜州兔害稼,千万为群,食苗尽,兔亦不复见”[20]。永淳年间(682-683),胜州出现大量野兔啃食庄稼的现象。野兔的主要栖息地在漠北高原,受严寒和旱灾驱使南下进入河套北部和山西北部,对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开元五年(717),河套北部遭遇旱灾,“榆林关有虸蚄食苗,群雀来食,数日而尽”[21]。“虸蚄”是黏虫的一种,幼虫头褐色,成虫习惯迁飞,对农作物具有一定危害。根据现代科学研究,虸蚄的生活习性和东亚飞蝗类似,常在旱灾之后大量繁殖。“榆林关”位于胜州,“在(榆林)县东三十里。东北临河,秦郤(却)匈奴之处。隋开皇三年,于此置榆林关”[22],故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东部城坡村故城[23]。
二.唐代中期气候转寒背景下的城市与生态
(一)城市发展
大约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唐朝气候开始逐渐转寒,降雨量随之减少,河套地区农牧业生产因自然灾害频发而遭受巨大打击,农牧业分界线大幅南移。因为土地承载能力下降,传统屯垦区的粮食产量不断减少,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从集约走向粗放,耕种方式严重退化[24]。河套地区畜牧业遭受重创,大量牲畜在严寒中冻饿而死,深受荼毒的游牧部族南下侵扰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日益扩大。寒冷干燥的气候使黄河水量逐年下降,湖泊数量和面积不断缩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套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个别地区的水利设施因水源不足而荒废。在这一背景下,唐朝为加强河套南部边防,不但扩建了夏州的城市规模,重筑了遭到吐蕃破坏的盐州城,而且迁移了因黄河侵蚀而损毁的东受降城。
1.夏州
根据历史文献分析和考古调查研究,唐朝可能在贞元八年至九年之间(792—793)增筑夏州外廓城[25]。外廓城平面为不规则的长四边形,南墙中部、北墙东部均有钝角状弯折。东墙切近台原边缘,依地势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300米,宽9.2米。北墙长约2000米,宽9.2米,东段呈弧形,西段为直线形,距离两座内城门的北墙100-150米,终于西内城西北侧[26]。南墙长约2100米,平面呈“V”形曲折线,转折点以东段南墙紧邻高达40余米的无定河北岸台原边缘,转折点以西段南墙呈直线斜向西内城,距两座内城南垣不足100米,止于西内城西南侧。
2.盐州
安史之乱以后,严重外患迫使唐朝不断强化京西北布防,京西北藩镇建设成为这一时代要求的必然产物。“盐州正处于农耕和游牧部族汇合的地带,吐蕃占领盐州地区后,北方可以隔断天德、振武两镇同京师的联系,南下可以通过鄜坊镇进入关中,西面可以对灵州形成合围之势[27]。由于盐州地理位置重要,当吐蕃进攻泾、陇、邠、宁诸州时,盐州可以“围魏救赵”之策出兵袭击吐蕃以解关中之困。在这一背景下,唐朝在贞元九年和元和十五年两次修筑盐州城。
贞元九年(793)二月辛酉,“诏复筑盐州城”。《唐大诏令集》收录了唐德宗颁布的这道重筑盐州城的诏书,强调了盐州的战略意义与重建城池的紧迫性:“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备无据。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甚勤。若非兴集师徒,缮修壁垒,设攻守之具,务耕战之方。则封内多虞,诸华屡警,由中及外,皆靡宁居。深惟永图,岂忘终身!顾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复前古之封、致四裔之守,与其临事而重扰,岂若先备而即安。是用思久远之谋,修五原之垒,使边城有守,中夏克宁。”[28]这是安史之乱后唐代最大规模的筑城活动,几乎动用了京西北所有军事力量[29],“令左右神策军及朔方河中绛邠宁庆兵马副元帅浑瑊,朔方灵盐丰夏绥银节度都统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邢君牙,夏绥银节度使韩潭,鄜坊丹延节度使王栖曜,振武麟胜节度使范希朝,各于所部,简择马步将士合三万五千人,同赴盐州。左神策将军兼御史中丞张昌,宜充右神策军盐州行营节度使,权知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杜彦光,可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应所板筑及缘修城杂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二旬之后,重筑的盐州城全面完工[30]。
唐德宗在积极筑城的同时,还布置兵力加强协防,“其余将士皆列营布阵,戒严设备,明加斥堠,以警不虞”。唐德宗为防范吐蕃出兵北上阻挠筑城工作,部署兵力进行牵制,“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朔方都虞侯杨朝晟戍木波堡,由是灵、夏、河西获安”[31]。重筑盐州城后,唐德宗对参与筑城工作的军士给予丰厚赏赐,“其修筑板筑功役将士,各赐绢布有差,其盐州防秋将士,三年满与代,更加给赐,仍委杜彦光具名闻奏,悉与改转。其防遏将士等,毕事便各放归,仍赐布帛有差。其诸军吏士,都赐帛七千匹”。在修筑盐州城池的同时,唐朝还注意加强周边军镇建设,积极强化盐州的协防能力。贞元十九年(803),唐德宗在盐州境内设保塞军[32],同年十一月“以盐州兵马使李兴幹为盐州刺史,许专达于上,不隶夏州”[33]。
经过20多年风雨侵蚀,盐州城到唐宪宗时期已经破败不堪。元和十四年(819)冬,“吐蕃节度论三摩等将十五万众围盐州,党项亦发兵助之。刺史李文悦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经过长期激战,盐州城防损毁严重。击退吐蕃围攻后,唐宪宗认为加强盐州防守迫在眉睫,下诏修复盐州城。“(元和)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宁节度使。时盐州为吐蕃所毁,命李文悦为刺史,令(李)光颜充勾当修筑盐州城使。”重筑盐州城后,元和十五年六月庚辰“加邠宁节度使李光颜特进,以城盐州之功也” 。太和五年(831)五月,唐文宗为加强盐州守备,下诏颁赐盐州驻军一批军械,“内出陌刀一百五十口,马甲一百领,器械一百万,斫刺刀一百口,赐盐州”[34]。
3.东受降城
在气候转寒的背景下,河套北部农业生产日渐艰难,大量屯垦区开始荒芜。长期耕作的土壤丧失植被保护,在干燥寒冷的环境中易为风力、雨水侵蚀,引发水土流失。随水而下的泥沙沿着各支径流进入黄河,加大了河道淤积和改道风险,为沿河各军镇、城堡带来水灾隐患。元和七年(812)正月,“振武界黄河溢,毁东受降城”。次年春天,“黄河泛滥,城南面毁坏转多,防御使周怀义上表请修筑,约当钱二十一万贯。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密陈便宜,以西城费用至广,又难施工,请修天德旧城以安军镇,其大略曰:‘伏以西城是开元十年张说所筑,今河水来侵,已毁其半。臣量其事势,不堪重修,若别筑新城,所费殊广,计其人功粮食及改屋宇,比及事毕,不下三十万贯钱,此但计费,犹未知出入之处。城南面即为水所坏,其子城犹坚牢,量留一千人,足得住居。天德军士,合抽居旧城,岂可更劳版筑,虚弃钱物。若三城是国家盛制,仁愿旧规,亦须得天德添兵,然后有人修筑。按天德旧城,在西城正东微南一百八十里,其处见有两城。今之永清栅,即隋氏大同旧城理,去本城约三里已下,城甚牢小,今随事制宜,仍存天德军额。北城周回一十二里,高四丈,下阔一丈七尺,天宝十二载安思顺所置。其城居大同川中,当北戎大路,南接牟那山钳耳嘴,山中出好材木,若有营建,不日可成。牟那山南又是麦泊,其地良沃,远近不殊。天宝中安思顺、郭子仪等本筑此城,拟为朔方根本,其意以中城、东城连振武为左翼,又以西城、丰州连定远为右臂,南制党项,北制匈奴,左右钩带,居中处要,诚长久之规也。寻属禄山有事,子仪留老弱于此城,身率大众河北讨贼,为贼将宋星星所破,纵火焚烧,遂移天德军永清栅,别置理所于西城,只缘添兵未得,且因循并在一处,力所不足,实非远图。臣久访略已计料,约修此城,不过二万贯钱。今若于天德旧城,随事增饬,因有移换,仍取城隶于天德军,别置使名,自为雄镇,以张声势,可詟殊邻。’诏从之,于是复移天德军理所于旧城焉”。在宰相李吉甫的建议下,唐宪宗放弃了重修东受降城的想法,将其治所迁往天德军旧城。这一举措有效加强了河套北部边防,“先是缘边居人,常苦室韦、党项之所侵掠,投窜山谷,不知所从。及新城施功之日,遂有三万余家移止城内。初,议者又虑城大无人以实,及是远近奔凑,边军益壮,人心遂安”[35]。
(二)生态变化
气候转寒和自然灾害频发加剧了河套地区农业经济的凋敝,严重破坏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兴元二年(785)夏,蝗尤甚,自东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经行之处,草木牛畜毛,靡有孑遗。”[36]这次严重的蝗灾席卷黄河流域,以夏州、灵州、天德军为代表的河套地区传统农业遭受重创,生产陷入困难,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唐德宗时期,夏州开始出现土地沙化问题。贞元十三年(797),唐德宗命夏绥银宥节度使韩全义率军前往夏州驻扎。“诏未下,军中遍知之,谋曰:‘夏州沙碛,无树艺生业,不可往’”[37],征调军士因恐惧夏州恶劣的生存条件而发生哗变。20多年后,夏州的土地沙化现象更为严重。长庆二年(822)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38]。咸通年间(860-874),进士许棠途经夏州时写下“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39]的诗句,感叹昔日的秀美山川已成满眼黄沙,悲凉之感溢于言表。在生态环境恶化过程中,粗放式开垦应该是主要因素。虽然大规模屯田不会直接导致自然灾害,但在环保观念淡薄和科技水平落后的唐代,屯垦过程普遍带有强烈盲目性和功利性,使农业生产者转变为生态环境破坏者。中古时期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共有两条,一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二是扩大耕地面积。鉴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最为便捷的方法就是扩大耕地面积,只能通过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极端手段向森林、湖泊、沼泽、山地、草原拓展[40]。不合理的、过度垦殖活动对河套地区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因开发不当而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水土流失、洪水、泥石流、土地荒漠化、沙尘暴等灾害频发。
唐代黄河流域大范围屯垦造成的水土流失导致黄河水患,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体现在水患发生地与屯垦集中区的地域关联。黄河上游的决溢共有四次,其中两次在西受降城,一次在振武军,一次在灵州怀远县。黄河依次流经怀远(治今宁夏银川市)、西受降城 、振武军(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怀远县的上游是青铜峡,黄河流出峡谷后进入开阔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这里是唐代河套地区主要屯垦区,大规模屯田造成大量泥沙通过风力侵蚀和水力冲刷进入黄河。因为河道平缓,流速较小使河水所携泥沙易于沉积,逐渐抬高河床,暴雨或凌汛后引发决溢,对两岸地形平坦地区造成巨大破坏。
元和七年(812)正月,“振武河溢,毁东受降城”。振武军的治所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地处黄河上中游分界点。正月“河溢”只能是凌汛现象,上游甘肃河段气温变暖之时,振武河段尚在冰封之中,大量河水裹挟冰块流至振武军造成河道壅堵,引发黄河决溢。“防御使周怀义上表请修筑,约当钱二十一万贯。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密陈便宜,以西城费用至广,又难施功,请修天德旧城以安军镇”[41],建议东城守军回迁天德旧城。这一提议遭到户部侍郎卢坦坚决反对,认为“城当碛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丰草,边障所利。若避河流,不过退徙数里,奈何徇一时省废,堕万世策耶?天德故城地壤硗瘠,北倚山,去河远,烽候无所统接,虏骑唐突,势不容知,是无故而蹙地二百里,故曰非便”[42]。从“天德故城地壤硗瘠”这一信息来看,唐代中期天德军的土地已经盐碱化,不再适于农业耕作。东城防御使周怀义作为当地守将,也对卢坦的意见表示支持,印证了天德军“地壤硗瘠”确为实情。
晚唐时期,灵州地区生态环境也开始恶化。宣宗年间,灵武节度使裴识上奏“灵武地斥卤无井”,说明当地已经出现土壤退化、地下水位下降现象。“在黄土高原地区,从生态环境看,它既是宜农宜牧的,又是十分脆弱的,所以当政府的有关举措或政策导致农牧生产比例有所偏移,就会造成生态环境优劣的变化。”[43]唐代在重农思想影响下推行农业扩张政策,大水漫灌造成土地盐碱化,传统的农作方式使土地在秋收后完全裸露,疏松的黄土在风力、水力作用下遭到严重侵蚀。在山区开荒垦田时,肆意伐木除草的生产方式加剧了贫瘠土地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又反过来加重土壤贫瘠,陷入“越垦越荒、越荒越垦”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