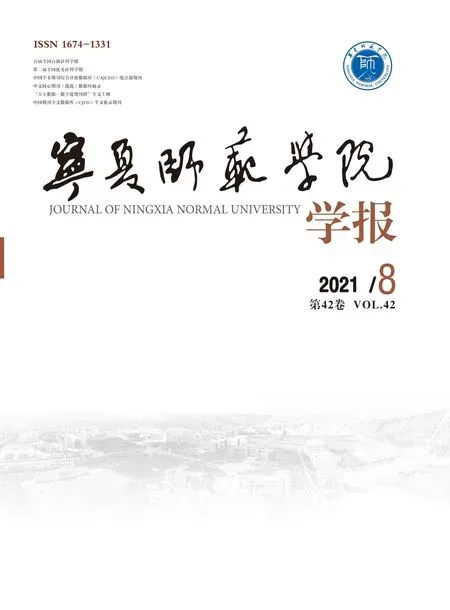盖茨的黑人知识分子身份与其文学批评思想的关系研究
段丽丽
(石河子大学 外国语学院,新疆 石河子832000)
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1950—)是著名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他从黑白两种视角审视美国非裔文学文本的审美特征。具体来说,追溯黑人土语传统、借鉴当代西方理论是盖茨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的两大支柱。但是,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孤立、彼此绝缘的,而是既各自独立,又互相配合,奏响了盖茨批评思想的双重奏。如果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这种结合体现出盖茨作为黑人知识分子既确认黑人传统又靠拢主流体制的两难困境。他所侧重的美国非裔文学的形式主义研究与主流机构对非裔文学批评的期待有着契合之处,这自然会引起黑人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在一些学者看来,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要么反抗,要么顺从。盖茨在顺从中反抗的立场反而更容易让人诟病其自觉让渡了黑人民众的权利。
盖茨的黑人知识分子身份为我们深入理解其批评思想提供了思路。一方面,他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与白人机构的干预密不可分。盖茨构建的喻指理论自身强大的阐释力是它获得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则是主流社会的接受和支持使之更强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主流机构的助力,喻指理论不会产生如此规模的影响。另一方面,盖茨也借机证明了美国非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进一步促使学界认可并接纳美国非裔文学及文学理论。鉴于上述两方面的思考,本文从“共识下的异议/冲突”“盖茨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在主流机构中的处境”和“黑人知识分子的两难选择”等方面入手,立足于盖茨的黑人知识分子身份探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
一、共识下的异议/冲突
盖茨的批评思想不但体现出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的自身需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时代的发展并迎合了主流社会对非裔文学的研究兴趣。20世纪80年代,美国形势发生变化。较之先前,黑人的生活状况有了一些改善,黑人知识分子对黑人文学和文化的阐释让人们重新认识到黑人研究的独特之处和它的重要性。盖茨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及理论构建虽然一再强调淡化政治,但是这一行为本身及其造成的影响仍不可避免地将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和政治诉求推向了研究的前沿。法比奥·罗哈斯(Fabio Rojas)在《从黑人权力到黑人研究:激进社会运动如何成为学术科目》(From Black Power to Black Studies:How a Radical Social Movement Became an Academic Discipline,2007)一书中指出:“有不少关于种族研究的历史记载,黑人研究尤其如此,但很少有研究者考虑黑人研究如何成为运动政治的产物,以及该领域如何融入高等教育体系。”[1]如果说,美国黑人研究出现在学院或学术机构是黑人抗争的结果,那么它在相应机构中的发展则取决于其与主流社会的合作与博弈。
迈克尔·贝鲁贝(Michael Bérubé)从“异议/冲突与共识”的角度分析了美国非裔研究在大学或学院中的处境:
自1985年《大学里的批评》(Criticism in the University)出版以来,格拉夫(Gerald Graff)一直是学院的首席发言人。他主张:只要我们能想象出一种不依赖于知识共识的理想的课程组织形式,我们跨学科和学科内的异议就会有非凡的教学价值。在1992年的《超越文化战争:冲突教学如何重振美国教育》(Beyond the Culture Wars:How Teaching the Conflicts Can Revitalize American Education)一书中,格拉夫表示,迄今为止,美国大学通过“掩盖事实”,通过简单地在课程中增加有争议的新领域,同时允许其他人照常开展工作,化解潜在的造成——或者说是激发——分裂的知识分子的冲突,设法阻止富有成效的内部辩论。当然,这种附加模式对知识分子也有好处,即在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者的反对时,允许创建妇女研究或美国非裔研究项目。[2]
可见,对于美国主流社会来说,回应种族文化冲突的方式,不仅仅是直接对其进行否定和排斥,而是转变为吸收和消解少数族裔的文化威胁。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认为:“甚至像哈佛大学这样的精英机构也在忙于制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学生被当作脆弱的儿童,必须保护他们不必面对智力分歧和冲突所构成的危险。”[3]在这种背景下,盖茨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颇具深意。不可否认,在主流价值观的框架内,他对黑人历史文化的阐释更具对话视野、更显多元性;同时,这也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美国非裔文学和文化的价值。但是,他如何在主流“共识”的影响下阐释美国非裔文学的独特性就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哈罗德·克鲁斯(Harold Cruse)在《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Negro Intellectual,1967)一书中指出:“美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在其中的地位,使得黑人知识分子发挥着特殊的作用。黑人知识分子必须同时与白人的权力结构、文化机构和黑人世界的内在现实密切接触。但是,为了成功地发挥这种作用,他必须敏锐地意识到美国社会动态的本质,以及它如何监控美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因素……因此,黑人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他不能与黑人或白人的世界完全分离。”[4]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黑人知识分子之一,盖茨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思想体现出体制内的抵抗,他的理论是在机构允许并倡导异议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盖茨的理论构建路径可以看出,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的“个性”取决于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许可他在“共性”的前提下谈“个性”。比如,作为其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的关键方法,重命名白人术语的策略既彰显了西方批评标准的普遍性和包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盖茨由外在显性地抵抗西方理论霸权滑向对西方现有体制的隐性维护。同时,“机构的作用是孤立和保护成员不受外界影响”[5],这就可能会造成主流机构中的美国非裔文学研究有脱离非裔民众的倾向。
二、盖茨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在主流机构中的处境
盖茨意识到当代美国非裔文学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所取得的成就与学院机构的支持密不可分。他曾这样说道:“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有一句著名的评论:知识分子可以被定义为合法化的专家,而今天的学院是一个合法化的机构,它确立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文化。在当今学院对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最激烈的抨击中,有一句古老的打油诗:我们是大学的主人/我们所不知道的,不是知识。”[6]事实上,盖茨很清楚自己的美国非裔文学研究最终要走向何处。在《黑色的象征》(Figures in Black:Words,Signs,and the “Racial” Self,1989)一书中,他就注意到“文学制度”(institution of literature)(1)有关“文学制度”的更多内容,参见[美]威廉斯(Jeffrey J. Williams):《文学制度》,李佳畅、穆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的重要性,并明确表达出他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致力于对非裔文学研究和当代批评研究作出贡献的目标,即“通过面向‘两种风格’的读者——关注黑人文学的读者和那些关注当今文学制度的读者——有助于美国非裔文学和当代批评的研究”[7]。
2008年,也就是在盖茨的理论专著《喻指的猴子: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理论》(The Signifying Monkey: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1988,以下简称《喻指的猴子》)出版20周年之际,乔伊斯(Joyce A. Joyce)结合时代发展,突出盖茨在主流学院的声望,重新反思了盖茨批评思想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她指出:“从1966年到1987年,黑人文坛发生了许多事情。到1987年,虽然黑人的比例仍然很小,但是,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机构的英语系,黑人学生的数量已经增加了。与此同时,少数黑人文学批评家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和黑人大学接受训练,开始享受舒适的薪水,并在他们的部门成为黑人文学问题的‘内部’权威。”[8]值得注意的是,西奥马拉·桑塔玛莉娜(Xiomara Santamarina)认为像盖茨这样的黑人知识分子在白人机构中起到了代表黑人种族的作用。同时,她也看到学院内的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客观上促进了非裔文学和文化的接受与传播。她表示,“尽管存在保守的阶级政治,但似乎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必须在学院内才能使黑人文学受到尊重”[9]。
学院内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取得的成就与机构干预密不可分。在桑塔玛莉娜看来,《喻指的猴子》在一定程度上是机构成功。她指出,“今天,《喻指的猴子》会引发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或者应该——将这本书的美学价值与机构成功区分开来。该书25周年纪念版是否仍然与我们的未来相关;尊崇一种过时的理论起源的叙述会不会仅仅是一种怀旧的做法?”[10]一方面,白人主流机构中的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彰显了非裔文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种研究也受制于白人机构的引导。特别是在一些受到白人支持的黑人学术精英的带领下,单维度的黑人传统研究难免受阻。这也就是桑塔玛莉娜所说的,“通过将黑人文学研究纳入学院,那些受益于盖茨杰出编辑地位的学者们已经提出了各种关于著名或不著名的黑人文本的解释框架。这表明单一的黑人‘传统’或黑人土语研究势必会受到排斥”[11]。
桑德拉·阿黛尔(Sandra Adell)指出了学院内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面临的尴尬境遇:“我们在学院的处境迫使我们‘掌握大师的语言’,我们作为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的处境迫使我们严格地审视‘美国非裔文学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12]的确,在主流机构的干预下,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很难做到既迎合主流偏好,又不牺牲自身特点。学者们对主流机构中的非裔文学研究的相关思考也引发了他们对盖茨在《喻指的猴子》中所提出的喻指理论的质疑:“鉴于批评的异质性,我们如何才能重新构建《喻指的猴子》的批评能力呢?是历史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对盖茨的非时间恶作剧者转义的挑战使‘黑’(black)的特殊性过时了,还是最近的批评干预使‘黑人性’(blackness)的研究变得无关紧要了?”[13]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在主流机构的发展相对应,学者们强调“从黑人视角出发”进行非裔文学研究的呼声也不容忽视。这种对立的研究态度在乔伊斯与盖茨等人的论战(2)有关这次论战的具体内容,参见王玉括教授《非裔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后结构主义之争》,载《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195-206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提升种族与顺从主流:黑人知识分子的两难选择
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在主流机构中的处境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对于美国黑人民众而言,黑人知识分子作为“十分之一杰出人士”还肩负着种族提升的责任和使命。
1903年,杜波依斯在《十分之一杰出人士》(The Talented Tenth)一文中这样说道:“与其他种族一样,黑人种族将被其杰出人士所拯救……他们可以引领民众远离污秽和死亡”[14]。在杜波依斯看来,从一开始,就是由受过教育并且有智慧的黑人领导和提升民众。颇有意味的是盖茨等人在《种族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Race,1996)一书的序言中明确表示:“作为一位领袖并不一定意味着被爱;爱自己的社区意味着在短期内敢于冒与该社区疏远与不和的风险,以打破我们长期处于的贫困、绝望和无望的循环。”[15]可见,盖茨等人意识到“十分之一杰出人士”在履行种族责任时必须要关注黑人面临的严峻形势,不能回避黑人问题。与此同时,为了种族的未来,他们也做好了短期内被误解的准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盖茨作为黑人知识分子的处境之难更多地体现在他摇摆于提升种族与顺从主流这样两种选择之间。盖茨位居黑人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他的“黑皮肤、白面具”症候主要体现在他的美国非裔文学研究植根于非洲文化传统,批判西方主流社会对黑人的错误认知和宰制,为非裔文学及文学理论发出黑人的声音;同时,他又在主流机构的支持下,借鉴当代西方理论,探讨美国非裔文学的西方传统,避免文化民族主义者对非裔文学的极端认知。
盖茨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既关注种族因素,又考虑到主流社会的接受程度及其产生的学术影响。他在批评实践及理论构建中主要遵循了两个原则:第一,坚决突出黑人特征,立足土语,有针对性地强调黑人文学的研究需求。第二,借鉴当代西方理论,寻找并确定非裔文学批评与主流理论的通用规则。不可否认,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在提升种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盖茨积极倡导黑白之间的对话,让公众有机会更多地了解黑人文学和文化。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强烈的批判意识是黑人知识分子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但是,盖茨更多的是在反思以往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的弊端,而不是重点批判历史上曾经遏制黑人发展的外部主流体制。他是黑人中的名流,与白人机构联系紧密,拥有各种社会荣誉和让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然而,“盖茨的批评者,尤其是一些非裔美国知识分子中的批评者,认为他的卓越声望并非来自本人的学术深度,而是他颇具争议的政治态度”[16]。就像巴克斯特·米勒(R. Baxter Miller)所指出的那样:“黑人批评家要么会有失去主流认可的风险,要么为了获得超越的普遍性而压抑种族自我。”[17]
不难看出,在盖茨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中,他尝试从“文化杂糅”的立场出发构建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理论。然而,一方面,他很难被主流机构完全接纳,无法有机融入白人社会;另一方面,他的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又难逃脱黑人民众的指摘。尽管盖茨宣称要代表美国非裔民众的利益,但是他无法解决知识分子所属阶层的精英特质与种族提升抱负之间的矛盾。他游走于黑白两个世界,试图为种族和自身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可是,他与其中任何一方的结盟都很难做到令人满意。
四、结语
作为著名的黑人知识分子,盖茨自觉探索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的变通之路,为种族提升铺路。通过分析盖茨的黑人知识分子身份,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比如,盖茨在种族提升与被主流接受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却又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就像任何一种批评思想的出现都离不开直接的内部因素和潜在的外部缘由那样,盖茨美国非裔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有其内外两个维度。就喻指理论而言,它既是非裔文学研究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对前辈非裔文学批评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同时,该理论也受到当代西方理论的影响,与外部社会体制密切相关。如果说,盖茨的批评思想在美国非裔学者们的论争中彰显出非裔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的内在诉求;那么,美国主流社会的政策支持和机制导向则推动了喻指理论与当代西方理论的交流对话,并扩大了喻指理论的影响力。也就是说,这种内外因素的合力促进了盖茨美国非裔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