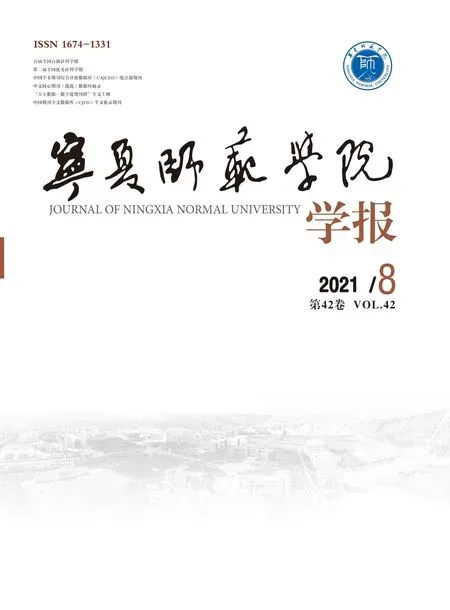理想与激情: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城市书写
王兴文
(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宁夏 固原 756099)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对此后的中国和世界影响广泛而深远。在整个80年代,国家制定的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使国家经济力量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时期的中国城市宛如缓缓启动随后逐渐加速的列车,带动整个国家进入经济快车道。大都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形成一个先后踏上由市场和计划共同配置资源的发展序列,向现代化的方向稳健迈进(1)整个80年代城市化逐渐加快,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2年的27.63%。见王廉《中国城市化教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变化,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迅速传导到文化领域,改变了文化领域重精神而轻物质的旧有范式。80年代是充满了理想与激情的时代,这种被释放出来的文化精神充满了时不我待、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信念,深深烙在80年代的文学中。
如果以城市书写为中心考察整个80年代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作为社会发展的“镜子”,这一时期的当代小说对城市的关注,并非出于一种文化自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遮蔽了城市书写的声音。但在整个社会挣脱束缚、释放潜力的大背景下,文学不可避免地“遇见”城市,80年代小说书写了改革时代城市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领域中的积极进取的精神,记录了城市空间不断被生产的过程,铭记了特定时代的城乡差异,也在新旧交替的城市景观中重构了城市记忆,在现代城市气息渐浓的时候书写了城市消费与欲望的同构关系。“文变染乎世情”,尽管80年代的城市书写呈现出多副面孔,但都受到了充满了理想与激情的时代精神的浸染,与社会发展、经济变化,以及人们的观念变化形成一种“共振”。
一、牵引经济增长的城市
城市是经济增长的机器,它通过聚集周边乡村的各种资源并实现重新配置,加快流动性,借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说,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会推动城市发展。1979年到1984年,是中国城市化的恢复时期,城市发展总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这一时期的经济变化主要是城市工业化改革和小城镇乡镇企业推动的。80年代小说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息,以近乎纪实的笔法,书写整个社会发生重要转折时期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塑造了一系列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人物形象,铭记了历史。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1],是“改革文学”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此后,蒋子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柯云路《三千万》《新星》、张洁《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5号》、张贤亮《男人的风格》等都涉及城市中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但这种近于“当代社会生活史”的城市书写也出现一种不平衡,这些小说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书写并不是一一对应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这样的序列,而是以蒋子龙的改革文学为先声,然后经过贾平凹的小城镇书写的铺垫,才出现张洁《沉重的翅膀》这样的巨著。这也是当代作家在书写城市时先有激情与理想,而后才有深思熟虑的沉潜之作的写照。
按照保罗·诺克斯的说法,“推动和塑造城市化的核心动力是经济变化。”[2]而中国城市经济的变化,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实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恢复生产带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这个意义上说,蒋子龙、柯云路的小说对国有企业书写,更多具有特定时代重要事件的纪实的特点。《乔厂长上任记》以某市重型机电厂为写作中心,通过塑造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开拓者乔光朴这个形象,聚焦20世纪80年代政治生活中的改革与守旧之间的斗争。柯云路《三千万》的主人公丁猛是某省轻工业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针对维尼纶厂建设十年还没有竣工的“胡子工程”,丁猛亲自到厂里调研压缩预算,进而解决三千万的烂账。两部作品都塑造了改革英雄的形象,但前者采取了“改革”+“恋爱”的模式,后者触及的官场关系网、人情网更为复杂,虽然没有深入揭露维尼纶厂党委书记张安邦及其背后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更为丑恶的一面,但对政治生活的复杂性的表现,却更胜一筹。两部作品都以理想人格的塑造,来表达特定时代的新旧斗争的主题。
在这一时期,中小城市的发展也极为迅猛,虽然戴维·哈维所说的当时中国“显著的增长率绝大多数都得力于集中化了的国有部门之外的部分”[3],可能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2)1984年底,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大5208万人,几乎是70年代末的10倍。见武晓鹰《人口城市化:历史、现实和选择》,《经济研究》1986年第11期。,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3)1978年到1984年间,农村收入惊人地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贾平凹的一系列作品,便敏锐捕捉到了乡村和小城镇经济发展中的新旧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腊月·正月》中,王才和韩玄子之间的新旧经济思想的交锋,其实是全国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矛盾的反映;在《鸡窝洼人家》中,贾平凹塑造了回回与禾禾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用以代表商业选择和农业选择在特定时代的冲突;《浮躁》以金狗和小水的爱情为主线,写改革时代经济发展。显然,乡村经济模式的转变来自城市经济的影响和国家层面的引导,只不过,在城市工业改革领域,这种冲突更加剧烈。
《沉重的翅膀》是改革文学的扛鼎之作,也是“我国文学反映经济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4]。即便是在40年后的今天重读这部小说,也不能不为作家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对风口浪尖做出各种选择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所叹服。《沉重的翅膀》所书写的城市生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政治生活。《沉重的翅膀》聚焦于改革开放初期重工业部和所属工厂的整顿改革,塑造了副部长郑子云、曙光汽车厂厂长陈咏明,以及车工组长杨小东和他的伙伴们等拥护改革的人物形象,也塑造了重工业部部长田守诚、副部长孔祥等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反改革派人物形象,还塑造了李瑞林、万群等生活艰难的普通工人形象,通过人物的行动,勾连起一幅改革时期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矛盾冲突迭起的社会生活画卷。其二是涉及那个时代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第四节写叶知秋拜访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在楼道里听到的音响:“楼道里传来的一切音响全是不顾一切的、理直气壮的,仿佛都在宣告着自己的合理:剁饺子馅的声音,婴儿的啼哭的声音,弹钢琴的声音……热闹的星期天。” 在第十二节,叶知秋和贺家彬从电报大楼走出来,看到了五光十色的街道风光:汽车、人群、指挥交通的警察、电器商店播送的电子音乐,交汇成日常生活的交响曲。张洁把所有声音和街道风光都描写出来,预示着这个时代即将拉开快速飞奔的离合,速度政治即将到来,并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三,小说已经把消费提上日程。小说中消费时代的代表无疑是郑子云的妻子,她的银嵌的、深灰色的大衣,从英国买来的提包,闪着珠贝一样色泽的拖鞋,绣着两只暗红的凤凰的白色丝绸睡衣,以及一头用乌发乳染黑、用阿莫尼亚水弄卷曲了的头发,虽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但是,这却是夸耀性消费的典型表现。其四,小说也写到了年轻一代的追求自我的意识,如郑圆圆对自由爱情的追求等。
80年代的政治小说虽然触及城市上层建筑中的官场生活,但大多把矛盾集中在新旧思想的交锋、路线之争上,理想与激情过剩,而对人性的挖掘不够深入,对城市经济发展与人的关系书写过于简略,对城乡人口、资源等配置的不合理也较少涉及。但无论如何,这些小说对政治、经济重大题材的开拓,应该是上承茅盾的社会科学家式的写作模式,下启90年代及21世纪之后的官场小说,算得上是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生活史。
二、生产空间差异的城市
1984年1月5日,国务院正式颁发《城市规划法》,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便提上历史日程。80年代初期下乡青年回城、农民进城,使得城市人口激增,加上出生于60年代、70年代的一批儿童正成长为青年,这些人的就业、结婚、生育的问题也成为城市的新问题。如何从政策层面改变如此巨大的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也是大城市必须解决的问题。城市空间的规划已经迫在眉睫。建造新的住宅区、改变堵塞的交通、合理规划利用城市功能区,与其说是城市规划的结果,不如说是人地关系紧张的产物。居住在城里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前途与更大范围的土地的前景息息相关”[5]。
人的生存与居住空间的矛盾表现在方方的《风景》中,也表现在池莉的《烦恼人生》中。池莉发表于《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的《烦恼人生》,是从民间角度对城市住房面积小、交通拥挤、工作繁忙进行了书写。方方的《风景》(《当代作家》1987年第5期)以写人的生存状况闻名,但实际上,也写到“棚户”这种特殊的空间对人性的压抑。如果说方方和池莉的小说是提出了问题,那么铁凝《永远有多远》、苏叔阳的《傻二舅》和陈建功的《放生》都涉及市民由胡同里的平房乔迁至现代高楼,则表明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是解决问题。如《永远有多远》一开篇就落笔于北京的胡同,而小说主人公白大省所居住的驸马胡同面临拆迁,则意味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虽然80年代的经济模式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但对城市空间的规划,已经透露出权力、资本以及公众利益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关系。这一点在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果说张洁《沉重的翅膀》紧紧把握住了改革初期复杂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话,那么《都市风流》就是在解决了生产和经营问题之后,一个城市的资源如何重新配置的问题;如果说刘心武的《交叉立交桥》中的城市空间的改造只是个引子,那么《都市风流》就是正经八百地书写立交桥的设计、建设。尽管小说的巧合太多,情节过于紧凑,但小说中弥漫的悲情氛围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还是非常感染人的。小说围绕中心事件——中国北方某大城市的旧城中心普店街的交通改造——展开,塑造了阎鸿唤、杨建华、曹永祥、老队长等积极开拓进取,努力建设光明立交桥的群体形象,也塑造了高伯年这样的虽然想为人民办实事,但不了解实际情况,脱离实际,仍然带有极左思想的领导干部,更是塑造了只为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埋头苦干的柳若晨、徐力里,以及投机取巧阿谀奉承的张义民、官二代徐援朝。《都市风流》由于跨越了改革与现代城市发展的阶段,所以它的城市书写体现出特定时代的特点。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都市风流》书写了城市规划、城市改造。特别是市长阎鸿唤上任以来,建起了三个大居民区,解决了该市住房问题:“又一个半年,市区两条主干线道路拓宽,这个城市第一次有了两条三十米宽的道路,又一个半年,三百多个商业网点建立起来了,市民们买菜、买粮、买煤难的问题冰释了。再一个半年,四座大型污水处理厂、三座发电厂,又相继建成……城市建设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大发展。”尤其是立交桥的设计与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应该是跟上了世界水平的建设。其二是小说所书写的权力腐败,已经出现苗头,利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的思想已经出现。比如市委书记高伯年的妻子沈萍在给自己的女儿高婕举办婚礼的时候坚持要办出一个大场面,并且为市委原书记徐克的儿子徐援朝的犯罪开脱,“徐援朝他们无非是想多弄点钱,现在社会上谁不想着钱?”实际上,徐援朝利用父亲市委书记的名头套购物资、倒买倒卖、走私文物,已经触犯了法律。其三是小说所涉及的物质的逐渐丰富所引起的人的迷失与腐化。小说中,罗晓维诱惑张义民时说:“中国人的观念发展趋势,我以为目前乃至将来就只有一个:从务虚到务实。何为虚?何为实?虚便是所谓的荣誉,实便是物质,金钱。说白了,钱就是一切。”罗晓维的观点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充满了庸俗的物质主义,但是,不幸被她言中的是,市场经济的施行和城市化的发展,确实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动摇和被越来越丰盛的物质盛宴所异化。其四是消费社会的征兆与人的欲望的书写。与《沉重的翅膀》相比,《都市风流》中的性已经出现,虽然作者都只是以暗示的方式提及,但由于这样的场面较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性观念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小说中,高婕未婚与音乐家黄炯辉同居怀孕,并且自以为自己的行为是追求艺术,这与后来的欲望泛滥似乎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贞操观念已经开始被消解。
80年代小说对当代中国城市的空间生产的书写,和人的基本生存状况贴得很近,也更多关注政治层面的权力斗争,对空间生产所牵涉的复杂的权力、资本以及资源配置等问题并未深究,对空间意义生成的根本原因,如“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6]也较少涉及,这与80年代作家受时代精神影响较大,来不及沉潜有关,也与当时市场经济不充分有关。直到90年代之后,当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之后,资本对空间生产的控制力量逐渐加大之后,空间的生产才成为当代作家批判城市的代名词。
三、进城叙事中的城市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数量巨大,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类人,一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的返城就业,二是赶上城乡贸易开放的列车进城从事各种商贸活动的农民,三是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通过积极参与到国家各项事业之中,而成为城市发展的建设者、推动者。由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建设既要偿还过去城市建设的欠账,还要向前发展,所以这一时期需要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甚巨,城市对人口的虹吸效应逐渐产生(4)由于这一时期国家实行“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政策,因此,大部分的进城人员,相当大的一部分其实是流动到中小城市了。。但由于国家对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限制,能够进城的人,还是极少数。况且,城市资源远胜农村,所以“进城”,其实就意味着个人命运的根本性改变。
在80年代小说中,梁晓声的《陈焕生上城》简单触及城乡差别,谌容《弯弯的月亮》、李杭育《山坡上那只风筝》、陈世旭《惊涛》等小说中的人物都把城市当作梦寐以求的天堂;张一弓《挂匾》、刘庆邦《到城里去》、陈敦德《女工牛仔》书写了形形色色的进城形象;铁凝《哦,香雪》、路遥《人生》,则把城市当作知识与文明的象征。虽然这一时期的进城叙事中丑化城市的主题不是很多,不同于《骆驼祥子》以及21世纪之后的进城叙事模式,但城乡二元对立的分明,也表现了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当然,人们对城市的理想化认知,也是80年代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时代精神的产物。
在这一时期的进城叙事中,最经典的作品应该是路遥的《人生》。《人生》以高加林、刘巧珍的爱情和高加林的进城两条线索结构故事,展开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阔的社会背景,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观念的迅猛变化,以及新旧思想之间的冲突。由于主题涉及面广,又夹杂着传统道德的审判力量,文本因而具有了多重意蕴。高加林的城市向往,是那个时代所有农村青年的理想,但从《人生》的具体描写来说,不管是高加林还是路遥本人,对城市的认识依然是停留在城市是实现自己理想的空间,城市能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这个层面。路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但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乡村的巨大区别,虽然他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
他们穿着游泳衣,一到中午就去城外的水潭里去游泳。游完泳,戴着墨镜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傍晚,他们就东岗消磨时间;一块天上地下的说东道西;或者一首连一首地唱歌。黄亚萍按自己的审美观点,很快把高加林重新打扮了一番:咖啡色大翻领外套,天蓝色料子筒裤,米黄色风雨衣。她自己也重新烫了头发,用一根红丝带子一扎,显得非常浪漫。浑身上下全部是上海出的时兴成衣。
黄亚萍对高加林的服装的改造,是从身体的层面将高加林“城市化”,黄亚萍给高加林提供的“罐头、糕点、高级牛奶糖、咖啡、可可粉、麦乳精”,以及进口带日历全自动手表,则是从物质层面把高加林“城市化”,黄亚萍带高加林去游泳,则是从生活方式上让高加林“城市化”。值得注意的是路遥对黄亚萍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按照小说中的提示,黄亚萍属于高干子弟,生活优裕。是从黄亚萍追求高加林的过程来看,她有自己的主张,自我意识非常明确,她接受的是现代思想的熏陶,要比高加林对现代生活的接受更加彻底。
《人生》中的进城叙事夹杂的对于知识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城市作为知识与文明的象征了。高加林和黄亚萍见面后,高加林大谈国际政治形势,黄亚萍则罗列各种能源知识,高加林和黄亚萍的这段交谈,表现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关注国际局势、关心国家大事,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的心态。当然,这个心态也是当时的青年普遍具有的心态,是一种时不我待,渴求知识,渴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家富强的集体无意识。但是,所有这一切,只是进城青年高加林的理想,是他把城市想象为实现自己理想的空间,是他把城市生活想象为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的结果,至于如何将知识转变为变革社会的力量,如何生产知识,如何通过生产知识推动社会发展,则是他所不明了的,当然,也是那个时代充满热情的相当一部分青年所不明了的。无独有偶,在《钟鼓楼》的结尾,刘心武花了不少篇幅讨论时间,时空弯曲、黑洞、时间旅行等概念在穿越小说与科幻小说盛行的今天早已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个时代还是别有意味的。当然,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人们渴望知识的心态在很多小说中都有表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学英文单词,比如贾平凹的小说《满月儿》里面就有“我”教月儿学英文的细节,《钟鼓楼》中的张秀藻和荀磊的第一次见面,也是荀磊手里捧着一本英文书。这些不经意的对书本知识渴求的细节,表现了一代人对知识的尊重与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城市这个概念是与知识联系在一起的。
路遥对城市是偏爱的。在塑造了高加林这个进城失败的形象之后,他还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了进城成功的孙少平的形象。尤其是路遥还不止一次书写到城市,如《平凡的世界》第四十章,写田福军狠抓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解决城市最迫切的问题,以至于“到处都在清洗路面,建筑花坛,改换刷新门面”。第四十八章,路遥借王满银的眼睛,展示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繁华情景,在这段描写中,路遥表达了他对上海的看法,其实也是那个年代人们对大都市的看法,这种城市书写虽然充满理想与激情,但是不无遗憾——80年代的进城叙事对城市还是很隔膜的,这些作家对城市内在的精神和气质缺乏深刻了解。
80年代的进城叙事中,除了路遥的小说深刻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关系的复杂之外,大多数作品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叙事:城市资源丰富但城市人虚伪、高傲,乡村资源匮乏但乡村人性纯洁、朴实。城市之恶的主题,直到90年代在《废都》《米》出现之后,才逐渐被拓展为一个重要的城市书写主题。
四、承载文化记忆的城市
早在发表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中,刘心武就已经写到了城市,只是这个城市作为背景被淡化了,读者只能从街道、花园、家庭居室等简单描述中重建模糊的城市印象。此后,刘心武《钟鼓楼》、汪曾祺《安乐居》、邓友梅《那五》《烟壶》、冯骥才《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神鞭》《俗世奇人》、陆文夫《美食家》,以及80年代末叶兆言《状元镜》《十字铺》《追月楼》等,都不约而同落笔于城市建筑、街道,以及栖居于此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惯,乃至他们命运的悲欢离合,开启了北京、苏州、南京等城市记忆的书写。刘心武、汪曾祺、邓友梅等作家对城市记忆的书写,其实也使得那些即将被历史淹没的城市经验和记忆媒介化了,这种媒介化的城市记忆,不但使人与城的相互依存的线索再次显露出来,而且开启了城市记忆多向流变,使城市记忆在此基础上再媒介化。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独有的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街道、自然景观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质性文化符号,它们构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呵护场所[7],人们的记忆也因“借助于象征物为群体所共享”[8]。80年代的当代作家关注较多也因而引起人们的城市集体记忆的“象征物”,有北京的四合院、小胡同、天桥,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小巷等,其中以北京的城市记忆书写最为充分,刘心武、汪曾祺、邓友梅、陈建功等都从不同侧面书写了北京的建筑、街道与自然景观。刘心武的《钟鼓楼》对北京地安门附近的地理环境、建筑、街道都有细致书写。在小说第二章第10节,刘心武描述了地安门附近的地理位置状况,然后对后门桥附近的闹市景象进行了描写;在第五章第19节,刘心武展开议论,认为“四合院,尤其北京市内的四合院,又尤其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国封建文化烂熟阶段的产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研究封建社会晚期市民社会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建筑艺术、民俗演变、心理沉淀、人际关系以及时代氛围的绝好资料。”接下来,用了极大的耐心对小说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的发生地——这个典型的四合院进行描写,对四合院的整体形状、院门的建筑式样,以及院内的影壁、前院、里院、垂帘门、东西厢房,都进行了介绍。尤为重要的是,刘心武还附带介绍了明清之际不同阶层之间住宅的区别。尽管刘心武认识到了四合院的文化价值,但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语境,《钟鼓楼》的重心并不在文化记忆方面。作者的落脚点是现在和将来(5)在《钟鼓楼》的结尾,刘心武畅想时间的相关概念,表现出美好未来的向往,无疑具有理想和激情的成分。,而不是过去,所以,刘心武笔下的城市建筑、街道,与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物存在某种背离。也许赵园所说的“《钟鼓楼》也非纯粹的京味小说”[9],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
城市的建筑、街道、自然环境等物质性文化景观,都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这些物质景观也因而会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塑造生存于其中的人们的文化性格、生活习俗,乃至道德、礼仪、信仰和价值观念。尽管汪曾祺、邓友梅、陆文夫对城市记忆的书写更贴近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更能惟妙惟肖地刻画出特定时代和城市环境所塑造的典型性格,但由于作家站在一个崭新时代的起点上,不免会被时代精神所感染,因而,在他们的笔下,这些生活在城市下层的普通人的身上,总是带着“陈旧”的思想观念,如陆文夫笔下的朱自冶,带着旧阶级的寄生虫式的生活习惯;汪曾祺笔下的安乐居中的人物,虽各有其性格,但都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普通人;邓友梅笔下的那五,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再如《钟鼓楼》对北京市民的职业状况和行业历史、从业人员的考证,以及第六章第26节对钟鼓楼下东墙根下“负暄”的老人们的书写,等等,更像是以社会科学家的姿态研究作为“他者”的社会存在。当代作家在书写城市生活时刻意把这些具有“旧”的特征的人物作为书写对象(或者说视角“他者化”),与其说是对城市历史的记忆,不如说是以新的立场与观念,重建过去。这种城市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现在的环境对过去进行重建。”[10]
80年代作家对城市记忆的书写,抓住了那些具有象征特征的城市意象,也精细刻画了宛如旧时代活化石的人物形象,但由于理想与激情的时代精神指引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所以这一时期的城市记忆其实是不完整的,变异的,是“借助叙事结构、象征和隐喻等审美形式编码”[11]的结果。直到80年代末,叶兆言创作了的秦淮河系列小说出现之后,这种俯视视角才得以改变。而90年代之后,在怀旧大纛下掀起上海摩登的书写潮流中,城市记忆则又矫枉过正,变成了对过去的无条件膜拜。
五、表征消费和欲望的城市
现代城市的一大特点便是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2],与消费、欲望和日常生活密切交融(6)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等作家就已经描绘出了上海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与浮华奢靡。。在经历了80年代初期的生产有序化改革、流通环节(交通运输尤其是道路)的建设之后,对被生产出来通过流通交换的商品的消费,逐渐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形成了所谓的第二次消费浪潮(7)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第二次消费浪潮。这一阶段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冰箱、彩电、洗衣机是标志性消费品,这次消费升级带动了中国家电产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期,城乡居民所面对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商品的更新换代,使得这一时期的城市体验完全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在这一时期,录音机和电视机作为最紧俏的商品,进入千家万户,与录音机和电视机同行的,则是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剧,《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在传播开放的观念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性观念。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就描绘了这一时期录音机的流行:
城里平添了一百架录音机,日日放着港台和大陆的歌星的歌唱,亦不知是流行歌曲推广了录音机,还是录音机推广了流行歌曲。新店铺开张之际,门口放着录音助威,毫不相干地咏叹着无常的爱情。出丧大殓、送殡的队伍里播着录音,唱的也是关于爱情。流行歌总也逃不了爱情的主题,就如流行的人生总也逃不脱爱情的主题。小城在爱情的讴歌里失去了宁静,变得喧闹了。轮船却还是每日两次靠岸,捎来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录音机和邓丽君,还比如,那一种失踪已久的半边黑半边白的骨牌。
这段文字是那个年代人们日常生活与录音机之间关系的真实记录。作为消费品,录音机由于能够随时随地播放音乐,占据了人们空闲时间,使人们的情感更加直接地释放出来。作为载体,录音机播放的港台地区和大陆歌星的歌曲,尤其是邓丽君的歌曲,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内容的同时,也把流行文化传播开来。当然,作为20世纪80年代较为大胆地表现性的女作家之一,王安忆的“三恋”曾引起众多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安忆的小说触及了一度被压抑的性,释放了焦灼与紧张。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先锋派小说,学者们大都从文学试验的角度分析,但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我们或许也可以把先锋派小说解读为进城青年欲望的表征,比如格非《褐色鸟群》对欲望的晦涩表现,再比如马原、洪峰、苏童、余华等人小说反复出现的与欲望有关的意象,其实都是一种释放。铁凝的《玫瑰门》对性的书写,也是如此,是那个时代人们某种集体无意识的表征。
其实在《沉重的翅膀》《都市风流》《大上海沉没》等小说中已经出现关于城市欲望与消费的书写,电视机作为紧俏商品在这两个文本中都有提及。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电视机的大量售卖,电视机所承载的电视剧与电影一同把港台地区的文化,以及最新的政治经济事件与文化事件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每一寸国土,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启蒙的话,那么这种启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颠覆了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正宗地位,加之通俗文学的渐次繁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金庸、古龙等武侠作家小说的涌入),纯文学的地位已经出现了岌岌可危的状态。这种可以统称为通俗文化的东西,迅速填补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精神消费空缺,也大面积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的改变不仅表现在普通民众的身上,也表现在当时的天之骄子(大学生)的身上。具体而言就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与颠覆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流行。
个人主义的表现,在《沉重的翅膀》中也有表现,比如郑圆圆的爱情,已经摆脱了家长的束缚,而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则涉及个性与共性的区别,但直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的出现,个人主义才唱出了最强音。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极富才能的学生李鸣不止一次地想退学,马力每次上课都睡觉,孟野每门功课都是5分却被劝退学。刘索拉所描写的这一代青年的心态,是多元的、消极的,虽然没有徐星笔下的“我”那么颓废。徐星在《无主题变奏》中说,“老Q!我只想做个普通人,一点儿也不想做个学者,现在就更不想了。我总该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和保持自己个性的权利吧!”考虑到这篇小说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对名、利、权的抵制与否定态度,文本这里所说的“普通人”其实并不普通,因为从文本中所透露出来的消极、颓废的思想来看,文本中的“我”在精神上是与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垮掉的一代一脉相承,至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即便不为实现 “封妻荫子”的人生追求,人生的另一种追求也应该是“独善其身”的。显然,《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是西方存在主义、荒诞派等思潮影响下的文化婴儿。
这种个人主义更多地以叛逆的方式出现。如陈建功的《鬈毛》中的卢森,反抗以家庭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在都市的街道上“自由”地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再如王朔笔下的“顽主”们,消费青春,以追求世俗的生活乐趣为目标,蔑视崇高,消解正常的生活方式。刘毅然《摇滚青年》中的“我”同样拒绝程式化的海鸥舞,而喜欢能够自由发挥的霹雳舞,为了坚持自己的个性不惜辞职。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反抗社会固化模式的思想尝试,是力图突破世俗观念和传统思想的牢笼,进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尝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一时期,随着城市物质生活的丰盛,原有的精神生活,那种近乎僵化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青年人的心理需求了。
80年代末期作家对城市消费与欲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生命个体的自觉意识的书写,其实是对现代城市人的城市生活与城市精神气质的表现,虽然80年代作家努力表现个体生命对传统集体意识的反叛,但总体来说,理想与激情的时代精神还是主导了这种反叛。因此,即便是刘震云的《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如何琐屑,即便王朔笔下的顽主如何类似于嬉皮士,他们依然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没有沦为90年代之后完全不顾道德底线的城市“新人类”。
六、结语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与激情的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活力,促使整个国家挣脱旧有范式的桎梏,城市发展很快。由于计划经济尚未完全向市场经济转变,城乡人口流动仍受限于户籍制度,城乡之间的壁垒依然分明,尽管城市经济在工业化带动下向前发展,乡村经济在乡镇企业带动下兴盛,但实质上并未能“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格局,全面调整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进化”[13]。作为时代发展的晴雨表,80年代小说创作表征了整个国家渐次融入全球经济大潮前的复杂社会状况,折射出了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显示了因城市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书写内容的倾斜(受时代精神和社会事件较大的题材多被关注,反之则较少关注)。另外,作为一种书写,80年代小说的城市书写也受到作家个人主观精神气质影响,受到文化传统制约,不自觉地将道德与乡村联系,遮蔽了城市某些方面的特征。但无论如何,80年代的城市书写从多个侧面表征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时代精神,为90年代及后来的城市书写开拓了思路,提供了写作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