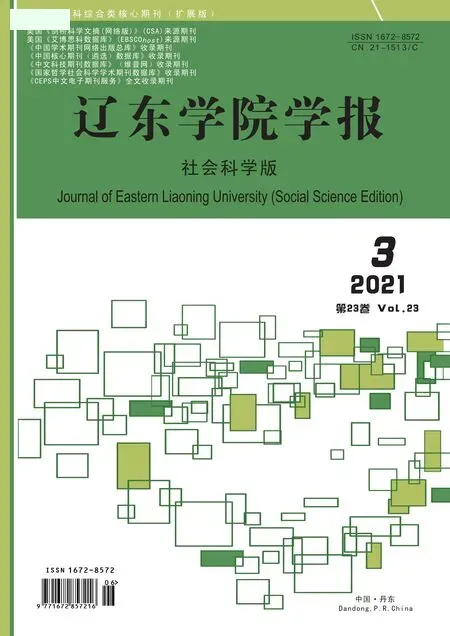宋玉赋对纵横家辞令铺陈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李 霖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引 言
“铺陈”是语言艺术的组合形式,常围绕一个描写中心,分别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语句、调动富丽的辞采,呈放射性展开,呈现出圆形的几何特征。战国纵横家游说诸侯,尤重铺陈之手法,造就了“富赡宏肆”的语言风格。宋玉赋(1)按:本文所谓的“宋玉赋”,是指宋玉辞赋。过去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传世的宋玉赋几乎全部被断定为伪作,怀疑的主要理由是战国时期不可能产生散体赋。但随着宋玉散体赋佚篇《御赋》的出土,使怀疑宋玉散体赋为伪作的推断不攻自破。根据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重新考察,现在我们可以断定宋玉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微咏赋》《御赋》《对楚王问》共14篇作品(关于宋玉作品真伪的考证,可参吴广平《宋玉著述辨》,《文献》2003年第3期;《宋玉著述真伪续辨》,《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又载于中国屈原学会编《中国楚辞学》第八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190页;《宋玉研究》上编第五章“著述的真伪”,岳麓书社,2004版,第86-111页)。笔者即根据这14篇宋玉赋来对“宋玉赋对纵横家辞令铺陈手法的继承与发展”进行研究分析。描摹自然山水、描写女子形貌、绘田猎、叙鬼怪,亦多全方位、形象化、层次分明、细致入微的铺陈描写。据“铺陈”之“铺陈中心——铺陈角度——铺陈语句——铺陈辞采”这一极富层级性的概念特征,可以看出宋玉赋对纵横家辞令的铺陈手法有一定的继承与发展。
一、宋玉赋对纵横家辞令铺陈手法的继承
章学诚曾言:“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1]117他认为,赋体的诞生,不仅与《诗》《骚》、诸子散文有关,与纵横家辞令亦有一定的关系。章太炎《国故论衡》言:“纵横者,赋之本”,“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2]91。章太炎亦认为赋体由纵横家辞令发展而来。从宋玉创作实际来看,其辞赋创作既吸收了纵横家辞令“恢张声势”的语言风格,也继承了纵横家辞令注重多角度、多侧面描写的铺陈手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铺陈结构的继承
宋玉赋的铺陈手法多继承纵横家辞令“对问”的结构技巧。关于“对问”,前贤曾有论及。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言:“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3]254“一个‘造’已暗示出虚问实对、设词抒怀之意。”[4]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指出,对问乃“设辞以自慰者焉”[5]49。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亦认为对问之言,“反覆纵横,真可以舒愤郁而通意虑,盖文之不可阙者也”[5]135。以上诸说,皆阐明了“对问”结构的设置目的及艺术功用。结合创作实际来看,宋玉赋继承纵横家辞令的铺陈结构,于“问”中展示问题的表象,于“对”中多角度、全方位进行铺叙,确可更好地“申其志、抒其意”。
纵横家辞令之铺陈手法多运用于对问结构中,问者多为君王,对者为纵横家,所对多为计谋,为使计谋被采用,对中多含辩驳之成分、铺陈之手法。如《战国策·楚策一·威王问於莫敖子华》一篇,楚威王发问:“是否有不追求爵位俸禄而忧虑国家安危的大臣?”莫敖子华遂以此为对答中心,罗列铺陈忠良贤臣形象。一般而言,《战国策》中的铺陈结构,“问是引子,对为主干。问是起,承、转、合都由对来完成”[4]。但有两篇较为特殊。其一为《战国策·齐策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一篇,虽含对问结构,但铺陈之语出现在问者之辞中。赵威后围绕“民”字连续7问,通篇记言,逐步铺叙推理,阐释出鲜明的民本思想。其二为《战国策·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一文,开篇无发问之语,只交代秦楚大战,楚国大败,楚顷襄王派黄歇游说秦昭王这一背景,全篇以黄歇的游说为主,旁征博引,向秦昭王排比铺陈了攻楚之优劣。虽无问者之辞,言说对象——秦昭王、言说中心——劝秦放弃攻楚则是确定的,故黄歇之运用“铺陈”亦有其特定的言说目的与言说功用。
以一定的对问结构作为基础,意味着交代了特定的言说时空或言说场景,点明了特定的问、对主体,并限定了言说中心,而对者为说服或娱乐问者,必尽可能使对答中心全面充分,故而“铺陈”手法便成为必不可少的言语手段,“铺陈”之运用有其存在的必要,符合一定的行文逻辑。宋玉赋继承纵横家辞令的铺陈手法,亦多以对问结构为依托,以问为首引,以对为主体,以问为抑,以对为扬。如《风赋》中,楚顷襄王以“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6]313发问,宋玉以“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为对答中心,从风的发生过程和各种态势等角度层层渲染、多角度铺陈,使得“其所托者然,则气与风殊焉”[6]314的道理得以展现。又如在《对楚王问》中,楚顷襄王责问宋玉有不好的行为,宋玉遂以“普通民众无法理解圣人的‘瑰意琦行’”为阐述中心,分别从音乐中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鸟类中的凤凰与篱晏鸟,鱼类中的鲲与泽鲵展开对比铺陈,淋漓尽致地表现其孤高之情。
宋玉赋继承纵横之法,在“对问”中展开铺陈,推进了事理的阐述与情志的表达,“对问”结构是“铺陈”手法之“不可阙者也”。
(二)铺陈角度的继承
在具体的铺陈中,宋玉赋继承纵横家辞令的铺陈角度,常依空间与事理等角度来对言说中心展开描写。
依空间铺陈,即据天地四方、高低远近、上下左右等空间方位铺陈。如《战国策·楚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楚威王》一文中言:“苏秦为赵合纵,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7]787以“西有……东有……南有……北有……”等四方铺陈,从而凸显楚国四方之优势。宋玉《招魂》一篇“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对天地四方六极的恐怖世界进行了详尽的铺陈描写:东方“长人千仞……十日代出”[6]288-289;南方“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6]289;西方“流沙千里……五谷不生”[6]290;北方“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6]291;天上“虎豹九关……一夫九首”[6]292;地下“参(三)目虎首,其身若牛些”[6]293。又如宋玉《笛赋》一文,亦从阴、东、南、西四方出发,铺叙了笛之生长环境。
由事理铺陈,即以事物发展逻辑、事物发生类别为向度,铺叙展开事物所有可能的发展结果。如《战国策·赵策四·五国伐秦无功》一文,苏秦为制止赵国的连横举动,数说了各王公诸侯彼此事奉秦国的各种可能性及方案,得出与秦国讲和并无益处的结论,遂说服了奉阳君。宋玉赋亦注重从事理角度来对事物进行铺排陈述。如其《风赋》一篇,将风分为两类,细致地描绘风从形成、扩展至平息的全过程,并详尽铺叙风吹物袭人的种种情状。又如《对楚王问》一篇中,从《下里》《巴人》到《阳阿》《薤露》,再至《阳春》《白雪》,依音乐高低,分别依序对唱和者人数进行铺展。
宋玉赋继承了纵横家辞令空间与事理的铺陈角度,而因其描写题材、言说背景等的不同,其铺陈角度比纵横家辞令更为丰富,更为精细,这一点将在后文进一步论述。
(三)铺陈技巧的继承
宋玉赋在运用铺陈手法时,也继承了纵横家辞令之排比、比喻、夸张的修辞技巧。如果说空间与事理的铺陈角度有助于描述事物的概貌,那么排比、比喻、夸张等铺陈技巧的运用,则有助于具体细致地展现事物的内部特质。
铺陈注重多方面、多角度的刻画,这便不可避免地常采用排比句式。如《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一文中,司马错在铺陈“先攻蜀国的好处”时言:“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7]202接连排比,逐步推进,较有感染力。如《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一文中,苏秦为突出秦为“天下之雄国”,采用大量排比句式将秦可攻可守的地利条件、兵多将广的人和条件、兼并诸侯的天时条件一一铺陈,言辞气势逼人,极富震撼力。宋玉赋亦然,如《高唐赋》中,对山水草木之铺陈描摹,无不借助于排比的修辞技巧。如“濞汹汹其无声兮,溃淡淡而并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6]326整齐的排比,突出刻画了“百谷俱集”的宏伟场面,富于气势,蔚为壮观。
在多角度、多侧面的铺陈描写中,也很多采用丰富的辞藻,展列多连串的夸张,较有冲击力。如《战国策·齐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一文,借“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7]539之扩大夸张,生动又深刻地铺陈渲染出了临淄的繁盛。又如《战国策·韩策一·苏秦为楚合纵说韩王》一文,苏秦为说服韩王合纵抗秦,故而大肆渲染韩国武器、士兵的优势,并极力夸张臣服秦国的屈辱。宋玉赋亦继承此铺陈技巧,如《对楚王问》中,为突出凤凰在鸟类中的独特,遂用夸张手法以铺陈之:“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6]423《大言赋》中为铺陈“大”,指出斗士之舌伸长达“万里”:“锯牙云,晞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6]375,尽显夸张之态。
在多角度、多侧面的铺陈描写中,也很注重比喻修辞的运用。运用比喻,即注入了感性因素,含蓄形象,更易于说服人、打动人。对于君王这一言说对象而言,不宜直接陈言,故为达到说服的效果,纵横家与宋玉皆于铺陈处注重曲喻旁譬。如《战国策·赵策三·赵惠文王三十年》一文,赵奢为说服田单,借干将之剑作比,铺陈了“用兵多”的好处,较为生动。如《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一文,庄辛为劝醒荒淫的楚顷襄王,以蜻蜓被粘捕、黄雀被射、黄鹄被杀、蔡灵侯被捆缚,最终着眼至楚顷襄王本身,暗喻其放荡淫乐必遭亡国之祸。接连的比喻,铺陈“淫乐不知忧患”的种种后果,形象充分。宋玉亦多借助比喻手法以铺陈,如其《登徒子好色赋》一文,言东家之子“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6]354,将东家之子的形貌与翠羽、白雪、细绢、贝壳等相联系,使得东家之子的美在比喻铺陈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又如《高唐赋》《神女赋》中,也多用比喻对神女外貌进行铺陈描摹,形象可感。
2.4 临床指南认知与应用影响因素分析 505名受试者人均认知情况总值为13.7分,仅占总分值57.1%;505名受试者人均应用情况总值为11.1分,仅占总分值74.0%。
(四)铺陈句法的继承
铺陈之语,往往是几句话表达同一个意思,用骈词俪句来重复一个中心,但不显拖冗,亦不显呆板。纵横家辞令即注重于铺陈处杂以“排偶句法,夸张其词”,如《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一文中,苏秦为使秦王接受自己的计策,以骈语的错综变化来层层铺叙:
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橦(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7]142
骈偶句式张弛有度,由疏而密,语气遂由缓而急,词锋犀利,且多三言短句,富紧张感,增添气势,又清晰简洁,易于理解。此外,《战国策·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战国策·赵策二·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战国策·韩策一·苏秦为楚合纵说韩王》等篇亦多骈词俪句,铺陈并列,条理清晰。
宋玉赋亦多调动骈俪句以铺陈,如《登徒子好色赋》中,针对襄王质问自己“好色”,宋玉遂以铺陈描述、烘托渲染的表现方法,塑造出东家之子与登徒子之妻两个人物形象,对登徒子诬陷自己“好色”进行了巧妙的辩解与反击。其句式骈散相偕,于散句中穿插骈句,整齐错落,表现自然:
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齿只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6]354
此外,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对楚王问》等篇中亦多骈俪之语,以工整、流畅的骈偶句式,更好地推进了铺陈的展开。刘熙载言:“用辞赋之骈俪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8]14即对宋玉赋多骈俪之辞进行了肯定。
二、宋玉赋对纵横家辞令铺陈手法的发展
由于宋玉与纵横家在言说身份、言说场景、言说对象、言说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故而宋玉赋在继承纵横家辞令之铺陈手法的同时,亦有一定的变化、发展。纵横家辞令多为游说之言,重在说理,体现出功利主义本质。宋玉赋则以描写为主,或隐喻说理,但重在娱君,审美性较强。宋玉赋对纵横家辞令铺陈手法的具体发展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游说性铺陈到娱君性铺陈
言说主体总是以一定的当下身份在言说[10]77。言说背景与言说主体的身份决定了言说的目的与风格,宋玉与纵横家言说背景与身份的差异,决定了两者言说目的的差异,决定了其具体言说时所采用的铺陈手法的差异性。
纵横家这一群体诞生于无统一之国家、无统一之思想、无被公认之诸侯国、“邦无定交,士无定主”[11]760的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皆渴求高层次的游说者为之献计献策,秦孝公甚至对于“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尊官,与之分土”[12]254。在这一政治背景下,纵横家奔走于各国朝廷之上,唯利是图,以智取胜。“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13]1005,成为纵横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与能力。为说服人主采纳自己的计谋,纵横家多在言语技巧上努力,在语言的铺张扬厉中直陈利害。正如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中所言:“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14]61要之,纵横家注重“铺陈”,其鲜明的目的即在于成功游说。
宋玉因友人的推荐而成为楚顷襄王的文学侍从,即宫廷里的职业作家。这一身份意味着其言说主要是为了迎合君王的审美喜好,而非纯粹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文心雕龙·时序》言:“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3]671-672可知屈原、宋玉所处之时,楚国已有图议国事、论艺读书的场所——“兰台之宫”。“兰台之宫”的文士多善辞令,在君王游乐之时常应景赋诗,以求得君王赏识。楚顷襄王注重声色享乐,虽然国力日衰,但楚国宫廷娱乐风气较为炽烈。襄王的无心国事,使兰台文士较少施展抱负的机会,更多的是为君王娱心助兴。且“襄王好乐而爱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周·宋玉》),作赋是宫廷娱乐的重要部分。宋玉的辞赋创作即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他随襄王游于云梦、兰台,参加大、小言竞赛,为迎合君王,他骋才助兴,铺采摛文,层次分明而又细致入微地或铺陈描摹自然山水、或描写女子形貌、或绘田猎、或叙鬼怪。故而宋玉的言说是一场娱君的言说,其铺陈是为娱君的铺陈。
(二)从说理性铺陈到描写性铺陈
纵横家的游说辞令多与特定的政治事件有关,其铺陈是一种说理性质的铺陈,讲求逻辑严谨,目的性较强。而宋玉娱君的创作行为下,其铺陈则是一种描写性的铺陈,讲求细致具体,抒情性较强。
从铺陈中心来看,纵横家辞令多围绕一件事的某种特征、某种结果,多方面铺陈,虽会涉及山岭关塞、农桑猎牧,但不会进行重点描摹,所铺陈的题材对象只是为议论服务,只是为全面充分的展开说理。如《战国策·韩策一·苏秦为楚合纵说韩王》中,苏秦对韩国地利、兵强等的铺陈,是为了强调韩国合纵的优势,而不是纯粹地铺陈描摹韩国地之杰、山之美。宋玉赋的铺陈范围较为广泛,不仅铺陈事物,还扩大至人物、景物,且皆对其进行精细详尽的铺叙。也正因为宋玉赋之铺陈不是为政治性的说理,而是重文学性的描写,故而其成功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形象,如《登徒子好色赋》中的东家之子,《神女赋》中的高唐神女,《高唐赋》中的巫山景色,《风赋》中的大王之风,无不令人赞叹。
从铺陈角度来看,宋玉赋虽继承了纵横家辞令空间、事理的铺陈角度,但宋玉赋在依空间、事理进行铺陈时,往往描写得更为精细。比如同是据空间铺陈,纵横家辞令多为“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这般简单的“罗列”,而未对西、北、南、东展开具体的描写,因为其铺陈不是为了形象的塑造,而只是通过陈述秦国东南西北的方位优势,从而更好地说理,更好地说服秦王。宋玉赋则不然,其按空间铺陈时,往往对各个空间方位又展开具体的铺陈。如其《高唐赋》一文,按“登巉岩而下望”“中阪遥望”“登高远望”“上至观侧”不同空间高度来铺陈,并非简单罗列景物,而是分别对各个高度的景观进行详尽的描摹刻画,从而将巫山整体的面貌和特色的景致都展现出来。此外,据刘刚老师总结,宋玉赋的铺陈不仅从空间与事理的角度来进行,还包括时间、物象、人体、博物全知等铺陈角度[15]。这是宋玉赋重描写、重精细刻画的发展结果。
(三)从功利性铺陈到审美性铺陈
借由铺陈之手法,纵横家更好地实现了其功利性目的,而宋玉赋通过使用铺陈手法,达到了一定的审美功用。
纵横家本身是功利主义者,其言说观受《鬼谷子》理论之影响较深。不同于正统思想界“修辞立其诚”(《周易·乾·文言》)的修辞观,《鬼谷子》认为论辩乃出于特定的目的,为达到功利目的须借助一定的言语手段。如其《权篇》中所言:“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16]101又指出:“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16]101认为说服他人要注重修饰语言,修饰语言即调整增减语言。铺陈,是修饰语言的一种手法,是对语言进行增益,但不是盲目的堆砌与重复,而是可以增强言说的感染力,从而更好地说服人、打动人。故铺陈是纵横家为达其功利性目的而采用的重要言语手段。纵观《战国策》,借由铺陈之手法,纵横家之辞令实现了一定的“功利”性功用。如张仪、苏秦在说服君王采用“连横”“合纵”的政治谋略的过程中,在言辞上大肆渲染,极尽夸张,最终大都成功说服君王。借由铺陈之手法,作为言说主体的纵横家亦由此实现了其自身的功利性目的。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鲁仲连等,凭自己重铺陈的言说,其政治主张被君主采纳,遂被委以重任。正如《资治通鉴》所载:“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曰犀首,亦以谈说显名。其余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纪。而仪、秦、衍最著。”[17]99-100
宋玉赋之铺陈是娱君的铺陈,是描写性的铺陈,是审美性的铺陈。“中国人的美意识,简单地说,在其初期阶段,一般是起源于味、嗅、视、听、触所谓五觉。”[18]18宋玉赋的铺陈,即围绕“五觉”大肆描摹,提供了多角度的美感享受。宋玉赋铺展色相,既使用了如白、红、青等显色词,也运用了如雪、沙、纂、缟等事物本身具有视觉色彩的隐色词。通过铺展颜色词,宋玉或使神女唇色特征鲜明化;“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神女赋》);或使衡山以东日出后红霞满天的情景图景化:“其东则朱天皓日,素朝明焉”(《笛赋》),从而形成鲜明的视觉触感。宋玉赋捕捉声响,通过使用双声叠词而增添了声韵美。如在描绘波涛澎湃、撞击巨石的盛状时,“汹汹”“淡淡”“洋洋”“湛湛”“潼潼”“澹澹”“淫淫”等叠词的使用,形象刻画出涛声之大和水势之高。宋玉赋铺陈触觉美、嗅觉美,最典型的是《风赋》中对风吹袭人感觉的铺陈:“邸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状直惏慄憯凄,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6]316宋玉赋铺陈味觉美,最典型的为《招魂》篇中对楚宫饮食的渲染:“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6]300通过对色、声、香、味、触等的多层渲染铺陈,宋玉赋在女性形象的塑造、山水自然的描绘等方面皆实现了一定的审美功用,取得了不朽的文学成就,正如清人程廷祚《骚赋论·中》评论宋玉赋所言:“穷造化之精神,尽万类之变态,瑰丽窈冥,无可端倪。其赋家之圣乎!后之视此,犹后夔之不能舍六律而正五音,公输之不能捐规矩而成方圆矣。”[19]67
结 语
宋玉赋继承纵横家辞令“对问”的铺陈结构,空间与事理的铺陈角度,排比、夸张、比喻的铺陈技巧,骈散相偕的铺陈句法,是对纵横家辞令中文学性元素的挖掘与延续。同时,宋玉赋发展纵横家辞令之铺陈手法,不再突出说理的逻辑力量,而是立足于文学形象的塑造,则完成了铺陈手法由政治辞令向文学言说功用的转变。铺陈是赋体重要的表现手法,且对问的体制、强烈的语气、骈俪的辞藻,正是后世赋家所追求的行文效果,故宋玉赋继承、发展纵横家辞令的铺陈手法,在赋体的艺术构成乃至赋体的创始上均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