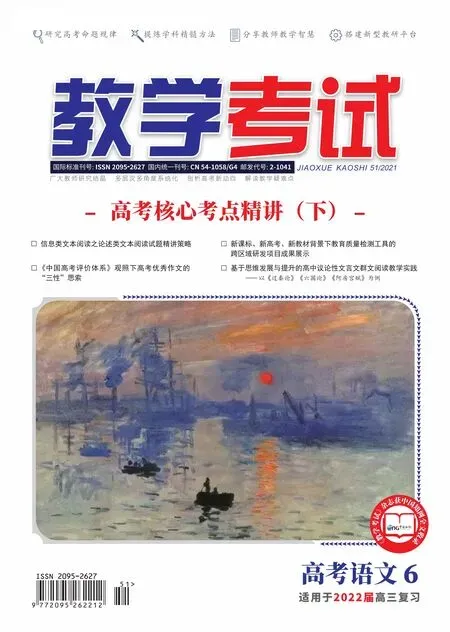节奏、张力、深度
——重复叙述的作用分析
浙江 晏 铌
“叙述”是近年来高考的热门考点之一。2021年新高考Ⅰ卷文学类文本阅读第8题:“王木匠讲石门阵时,多处使用反复手法,这种讲述方法有什么效果?”该题考查的就是叙述技巧中的重复叙述。
叙述是叙事性文本必不可少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包含了叙述角度、叙述人称、叙述腔调、速度控制、叙述顺序、叙述技巧等知识点。其中,叙述技巧包括重复叙述、多重叙述、层层铺叙、渲染、用对话的方式展开小说、叙述过程中多用对比手法等。本文拟对其中的“重复叙述”进行简单梳理。
一、厘清基本概念
先厘清两个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概念——多重叙述和重复叙述。
多重叙述又叫复调叙述,是一种在同一叙事中并行着两个甚至更多声音的叙述方式。换句话说,故事可能通过多人之口来讲述,叙述视角是多元的。这种复合型多元视角使得视角呈平行或交错状态,打破了单一视角叙述、单线条历时性叙述以及传统的全能叙述模式,各个视角的叙述相互补充,使事件更加完整、立体,比如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马尔克斯继《百年孤独》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它有两个叙述层次:一是“我”回乡调查寻访圣地亚哥·纳萨尔被杀一事,二是小镇人对凶杀案的回忆和看法。小说采用复调叙述的方式,让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或同一时间内发生的事件进行多次讲述。因为立场、身份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说法虽然相互补充印证,但也不免彼此矛盾。如此,小镇的社会环境氛围、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主要表现为集体冷漠和失语)等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
各个视角的叙述还会相互颠覆,比如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该小说以在公堂上审讯犯人和证人为背景展开,相关的七个人对同一“事件”的讲述却大相径庭,矛盾百出。在叙事的迷雾中,唯一能确定的是武士死了,其妻真砂被强盗多襄丸凌辱,而案子的关键问题——武士是怎么死的却被悬置。
不管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还是《竹林中》,都因多重叙述而营造了多维的叙述空间,也给文本带来了多义解读的可能。
鲁迅的名篇《祝福》也采用了多重叙述的手法,不仅“我”在讲祥林嫂的故事,卫老婆子也在讲(“现在是交了好运了”“她真是交了好运了”),祥林嫂自己也在讲(“我真傻,真的”),这三重叙述相互补充、彼此印证,既完善了情节,丰满了祥林嫂的形象,又深刻地揭示了小说主题。
2014年全国卷Ⅰ文学类文本阅读《古渡头》也是双重叙述。小说既有“我”的讲述,也有渡夫的讲述,其中渡夫的叙述为小说的主要内容。
重复叙述又可以称为反复叙述,是对同一对象的多次叙述,有时候也表现为用相同的语言模式去表述彼此联系的事物。这种手法并不罕见,《庄子》有“重言”的特点,比如《逍遥游》中就有两段大同小异的叙述: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庄子采用重复叙述的方式是为了向读者强调他所讲事情的真实性——许多文献资料上都有记载,也在于阐述事物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祝福》中,祥林嫂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地诉说“我真傻,真的”也是重复叙述的一个典型。这种叙述表明祥林嫂已经陷入儿子死亡的阴影中无法自拔,精神完全麻木,甚至崩溃。同时,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和多次哭诉不仅没换来镇上人们的一点同情,还遭到深深的厌弃。这不但丰满了祥林嫂的形象,而且多角度地渲染了社会环境氛围,从而更深刻地凸显了主题。小说中还有多处此类的重复,比如祥林嫂的四次外貌描写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二、分析效果作用
一般来说,重复叙述的作用有:控制叙述节奏、加强叙述张力、丰富小说内容、丰满人物形象、深化小说主旨、感染小说读者等。
下面,笔者以卡尔维诺的《牲畜林》、鲁迅的《祝福》和2021年新高考Ⅰ卷文学类文本阅读《石门阵》为例,逐一分析重复叙述的基本作用。
《牲畜林》的情节很简单:贪婪愚蠢的德国兵在牲畜林中一再地想抓住各种牲畜,最终却在村民朱阿拙劣枪法的“恐吓”下和野猫同坠石崖丧命。简单来讲,这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反映战争背景下人们命运的故事。卡尔维诺巧妙地运用了“延迟”的手法,六次让朱阿摸到扳机却直到最后一次才扣响。小说中的“延迟”是通过“重复”来实现的。这里的重复是情节上的类似,它故意延迟小说的进展,竭力给故事设置障碍,既增加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又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张力。小说中的重复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采用多种手法使六次重复各有声色,毫无重复啰唆之感,小说内容也因之而丰富;情节在这种重复中推进,从而挖掘了叙事深度;同时,五次延迟,使整个小说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在朱阿紧张的情绪中让人感觉到一阵阵轻松,别有幽默感和喜剧色彩。
诚如丹麦民俗学家阿克塞尔·奥尔里克所认为的那样:“在每一叙事作品中,都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景,而且,故事的连续性允许重复这一场景。它不仅对于创造紧张气氛,而且对于使叙事文学丰满起来都是必要的。虽然有强化重复和简单重复之分,但关键是,离开了重复,叙事就不能获得它的完整形式。”《牲畜林》中的这些重复既加深了读者对故事中相似情节的记忆,让读者可以轻松掌握故事的逻辑脉络,同时又促使读者注意到重复中的变化,并且明了重复中的变化、程式化中的差异其实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因素。殊不知,高比例的重复反而使人更容易注意到这些差异。因此,作品中的重复一般都不是机械化重复,而是以简单灵动的方式提升故事的丰富性。
卡尔维诺的作品多富有寓言式、童话般的色彩,《牲畜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具备了此类文学形式,尤其是民间文学的一些特点。而民间文学的叙述规律之一即是重复叙述,这跟民间文学来自口头传承有很大关系。
口头文学采取重复叙述的方式,与话语生成过程的特点有关。瓦尔特·翁认为,把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意思重复几遍,是为了适应思维的延续性而在口头表述上呈现的古老传统。他说:“由于口头说出的东西转瞬即逝,心智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供回顾,因此心智就必须把步伐放慢,紧紧盯住已处理的大部分注意焦点。冗赘和重复刚刚说过的事,恰恰能使讲话人和听话人都跟着思路走。”
口头文学通常在生产生活中即兴创造,一边说一边编,没有充分的构思时间,如何保持表述的流畅性和情节的连贯性是故事讲述者面临的主要困难。重复同一个情节(也包括言词、段落等),或者说固定的词语、固定的框架使讲述者可以轻松完成故事各部分间的衔接。所以,重复叙述适应于口头表达的特点,既能满足表述流畅的要求,又能满足情节连贯的要求,重复中又有次数、方位、人物等情节因素的置换变化,不是单调刻板的。也就是说,通过重复已讲述的内容,可以为讲述者赢得话语计划和情节思考的时间,保持话语的流畅性;而其中夹杂的变化则承担着推动故事情节前进的作用,使故事在重复的框架下仍然可以得到连续发展。
在卞之琳的《石门阵》中,最主要的情节就是木匠王生枝给乡亲们讲故事。这一情节就具备了民间文学或儿童文学(童话寓言)的一些特点,尤其接近于中国传统的“说书”。
“那条小街上有人吗?没有。
那个院子里有人吗?没有。
那堆小树丛背后有人吗?没有。”
诸如此类的语言结构和形式的重复,小说中一共有五处。这样的重复,既契合了听故事人的身份特点和他们当时的心情,抓住村民的注意力;还可以引导村民的思绪,让他们跟着王木匠的节奏走;又让内容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使听故事的村民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通过重复手法的运用,塑造了擅长讲故事的王木匠形象,他和他的讲述占据了该场合中的绝对主导权,牢牢抓住了村民的心。
当然,在具体分析重复叙述的作用时,还需要从重复的内容入手,再根据具体内容进行相关解读。比如,《石门阵》中的重复既是故事情节内容的重复,又是王木匠语言的重复。因此,在分析重复的效果时,需要先分析这是什么情境下的语言。
这篇小说中,人物是作为群体形象出现的,他们的身份是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村民,王木匠则是群像中的突出个体。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是王木匠和村民、讲故事人和听故事人之间的关系。就好比《祝福》中,祥林嫂语言的重复是她面对不同身份的鲁镇人的重复。
鲁镇人在小说中可以简单分为三类:封建地主——鲁四老爷和四婶,雇工——善女人柳妈、长工等,普通鲁镇人——老女人、女人、男人、孩子们。祥林嫂的诉说是命运悲戚的雇工向有地位有身份有文化的主家的自诉遭遇,是一个遭遇凄惨的底层妇人对一群命运悲惨的底层人的倾诉。祥林嫂反复向不同的人讲相同的故事,讲述的方法却因听众的身份、讲述的场合不同而有着细小差异。祥林嫂第一次回忆阿毛的遭遇是在鲁四老爷和四婶面前,第二次则是对着镇上的人们。前后两次讲述的时间、场合、对象都不相同,祥林嫂的语气、语调、感情心理也有所不同。祥林嫂对鲁四老爷和四婶讲述的时候说“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对镇上的人说“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相较之下,对镇上人讲的时候现场感比较强烈。祥林嫂面对主家,不敢“放纵”自己的悲伤,所以她说“我叫阿毛”,语气相对平缓。对镇上的人就少了一些顾忌,感情流露得更自然强烈一些,所以她说“我叫”,停顿一下,再强调说“阿毛”。这是一种还原性的回忆,它透露出祥林嫂内心巨大的痛苦,极具感染力,鲁镇人也不免“陪出许多眼泪来”。

——祥林嫂的悲剧原因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