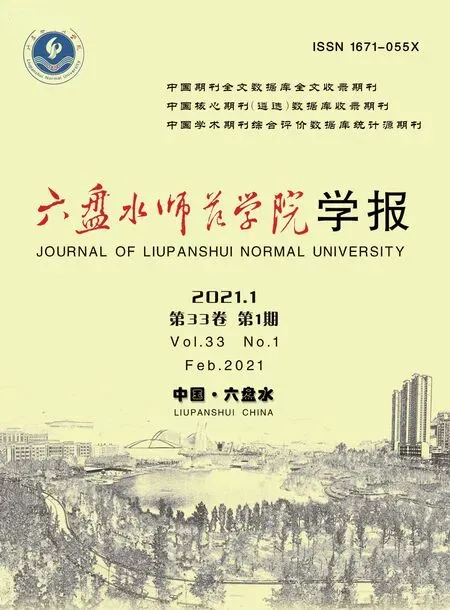《紫颜色》中的男性气概及身份建构
黄艳玲
(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20世纪60年代,美国非裔文学在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与女性、族裔、同性恋文学一样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裔文学的书写主题众多,主要包括黑人形象、黑人性、种族身份、种族歧视与压迫,暴力创伤等,男性气概也是其中之一。正如美国著名的男性气概研究学者凯斯·克拉克(Keith Clark)所说,“黑人男性作家对男性气概和主体性的关注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1]3。学界普遍认为,这与美国黑人的特殊历史遭遇和种种惨痛经历息息相关。然而不仅黑人男性作家对男性气概和身份建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度,学者隋红升认为,“黑人女性作家对男性气概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佐拉·赫斯顿(Zora N.Hurston)的《她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的《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格洛利亚·内勒(Gloria Naylor)的《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The Men of Brewster Place)、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生》(The Third Life of Grange Copeland)和《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都是男性气概书写的典型”[1]3。《紫颜色》向读者展示了“暴力”这一现代男性气质的评判标准对两代黑人男性的误导和摧残,及其在这种暴力倾向诱导下黑人男性做出的种种残暴、血腥和丧失本性的行为。该作品深刻揭露了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影响下黑人男性气概建构的认知错误以及黑人由此遭受的人格扭曲和异化的漫长之路,这不仅阻碍黑人男性自身发展,而且破坏家庭和两性关系的和谐。《紫颜色》的出版打破了长久以来黑人男性作家对男性气概建构研究的话语权,从女性角度书写男性气概,丰富和拓展了当时人们对男性气概和身份建构的认知和性别研究视野。
自1982年出版以来,《紫颜色》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国外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叙事策略、主题、象征和隐喻的运用。美国黑人文学学者泰特(Tate)评论了这部书信体小说叙事策略的运用。在她看来,“沃克放弃了书信体小说传统的欧洲文学叙事风格,给了西莉通过书信来叙述自己经历的机会”[2]37。在《<紫颜色>中的种族、性别与民族》(Race,Gender,and nation in“The Color Purple”)一文中,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通过对小说叙事风格的分析,揭示了小说中的民族认同、种族压迫、性别压迫。他认为,“在这个修订后的自传体故事中,种族主义继承了叙述中的性别歧视,成为社会暴力的原因”[3]839。琳达·塞尔泽(Linda Selzer)在她的论文《紫色的种族与家庭生活》(Race and Domesticity in the Color Purple)中主要关注小说的叙事策略,她认为,“沃克的家庭小说通过两种重要的叙事策略来处理种族和阶级问题,发展一种嵌入式的叙事线,提供一种后殖民主义视角的行动,使用‘家庭关系’或亲属关系作为对种族关系的精心阐述的文本比喻”[4]82。关于小说的主题研究,亚当·古索(Adam Gussow)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芝加哥评论》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小说的主题是女性友谊”,他还指出,“在美国黑人民间传说和文学中被认为是失乐园的非洲,实际上和美国一样具有压制性的父权制”[5]124。对小说的符号和隐喻的研究方面,1991年,杰奎琳的《黑人女性作家的神话和隐喻》一书为我们分析了沃克对隐喻的使用。
然而在国内,学界更多地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小说。陈琳从马克思主义女性视角对小说做了研究,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是争取女性解放的关键因素”[6]76;焦立冬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紫颜色》,他提到,“民族身份异化带来的失重感、来自白人种族社会的歧视加上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思想使黑人妇女的地位双倍甚至三倍的边缘化”[7]262;而杨何则从生态女性意识出发研究小说,如她所说,“《紫颜色》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的内在联系”[8]69。除此之外,学界还从叙事视角、解构主义视角、文学伦理学视角、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多重文化视角和成长小说视角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进行分析。总之,国内外学者对该小说的研究角度层出不穷。然而,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小说中几位黑人女性的成长,尤其是主人公西丽的成长,对小说中黑人男性的成长却颇少关注,小说中黑人男性成长过程中的男性气概及身份建构更是被忽视,少有学者对此进行相关研究。
鉴于此,本文采取文本研读的方式,对《紫颜色》中的典型男性人物形象展开分析,试图探讨作品中的黑人男性如何实践真正男性气概及个体身份建构。同时,反思现代男性气质的种种弊端,把真正的男性气概与社会中残存的种种刻板印象和流俗区分开来。
一、辨析“男性气概”与“男性气质”
“男性气概”(manliness),又称男子气概或丈夫气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同时,它也是很多文学作品一贯书写的主题,深受美国非裔男性作家青睐,有着深厚的书写传统。“男性气概”和“男性气质”(masculinity)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男性气质是由传统男性气概演变而来,但两者在定义范围和评判标准等方面已有所不同。尽管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于男性研究领域的这两大概念并未做详细区分,仅把它们当成在表达习惯上有所差别的概念。除此之外,要么一律使用男性气概要么一律使用男性气质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在对男性气概建构做进一步的研究之前,辨析男性气概和男性气质的区别已不容忽视。
在定义范围方面,传统男性气概是一种以勇敢和坚强为核心的人格品质,代表了男性的一种美德;同刚毅、意志力、责任感、自控力、忠诚、自信和正直一样,男性气概是一种内在品质;同时,它还是一种内在力量,能够帮助人们摆脱困境、抵抗压力、焦虑与恐惧,促成善心善举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正如曼斯菲尔德所言,男性气概就是一种“德性”“它是勇敢或绅士风范(gent l emanl iness)的德性”[9]5。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大众的文化价值观发生蜕变,男性气质由此进入人们视野之中。不同于男性气概,男性气质更多关注的是男性的外在表现,如对权力、财富、地位、性能力和体貌等的痴迷和过度追捧。而且,在男性气质的诱导下,男性把暴力手段和对女性的绝对征服看作是其男性气质的展现方式,致使其陷入霸权性男性气质危机中无法自拔。男性越想表现自己、证明自己就越陷入男性气质危机中,因此男性气质带给男性的只有越来越多的压力、自我怀疑、焦虑甚至人格异化。综上所述,男性气质忽视和淡漠传统男性气概对男性内在意志品质和精神力量的培养,实际上是对传统男性气概的一种曲解。
在褒贬评判和价值取向方面,传统男性气概是积极的、褒义的,因此属于积极性男性气概,它给予男性面对一切的力量和勇气;男性气质则是消极的、贬义的,它的出现使得外在的行为举止取代了男人的内在品质,使男性陷入自我和身份危机中,因此是一种消极性男性气概。这种消极性男性气概仅是一种男性气概流俗和刻板印象,并非真正的男性气概。就价值取向而言,“男性气概具有内在导向型比较强调男性的人格尊严与道德品质;而男性气质具有外在性,非常关注男性的外在表现与他者的评价”[9]47。综上所述,传统男性气概具有内在性、精神性和灵魂性;男性气质则是外在性、虚伪性和表演性,因此一定程度上,现代性男性气质被看作是对传统男性气概的一种误读。
尽管如此,黑人男性寻求这种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欲望从未消减,且这种外在性男性气质常常以暴力的方式展现,而且,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俨然成为很多现代男性,尤其是黑人男性证明和建构其男性气质的重要途径,如小说《紫颜色》中的“某某先生”和其儿子哈波就是该霸权性男性气质建构下的典型人物。
二、霸权性男性气质腐蚀下主人公人性的异化
长久以来,白人社会拥有且占据一切话语权,而黑人甚至连自己的生存权利都无法掌握。在这样一个以白人主流媒体为主导的畸形社会,白人社会极力宣称男性必须统治、控制一切思想。他们既需要女性支持自己的雄风,也通过贬低女性获得先天的优势和良好自我感觉;他们反对男性具有柔弱、爱美、需要保护、体贴等特质,却将暴力作为解决问题、向世界证明自我的基本方式,且试图通过金钱和性的成功建立男性气质霸权,排挤蔑视那些“失败者”。在这一霸权性男性气质神话的推动下,白人社会一边贬低黑人男性,认为他们幼稚、懦弱、愚蠢、野蛮、懒惰,并且讥讽地称呼黑人男性为“boy”,一方面白人媒体又以男性气质的种种规范来要求黑人男性。在这种“双重标准”的压迫和“霸权性男性气质”之梦的误导下,黑人男性极其渴望实现其被阉割的男性气概,他们不得不盲目追随主流社会大肆宣扬的“男性气质”来迎合白人,试图以此得到认可,并证明黑人也同样拥有被神话了的霸权性男性气质。
小说中,“某某先生”揍西丽(Celie)就跟揍孩子一般,不管西丽是不是按照他说的做。当年幼的哈波(Harpo)问父亲为何揍西丽时,他说道:“因为她是我的老婆,还有她太倔了。”[10]18在“某某先生”眼里,老婆不仅是他发泄性欲的工具,而且还是用来揍的。在“霸权性男性气质”之梦的误导下,“某某先生”始终把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当作其男性气质的一种体现并冥顽不灵地践行着。因此,当成年后的哈波求助父亲如何管教索菲亚时,“某某先生”只是问了一句:“你打过她吗?”[10]26父权制社会中,男人控制一切、统治一切的思想根深蒂固,尤其表现在对女性的绝对征服。对人格已经严重扭曲的哈波而言,不能对女性为所欲为便是男性的一种耻辱。见此情形,“某某先生”向儿子传授“经验”道:老婆都像孩子,驯服她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地揍一顿。人格扭曲的“某某先生”不仅自己把白人主流社会宣扬的暴力手段奉为教条,把残忍凶暴、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当作具有男性气概的表现,而且还唆使自己的儿子以他为榜样,对女性任意妄为,以此来彰显父子俩缺失已久的被压抑的面目全非的男性气概。
其实,暴力和凶残并非黑人男性的本性。年幼的“某某先生”和大多纯真无邪的孩童无异,小说后半段他自述道:“我小时候常和妈妈一起做针线活,大家都笑我,可你知道我喜欢做针线活”[10]90。但成长在暴力横行的国度最终使他不可避免地沦为暴力的拥戴者,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所言:“在黑人男子还未涉及暴力之时,他就出生于将暴力当作社会控制手段的文化中。”[11]140作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深受父权制思想牢笼禁锢的黑人男性在成年之后极度渴求像一个正常男性一样拥有尊严和地位。这种想象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使他们麻木不仁,对弱小儿童和妇女的压迫与欺凌便成了他们展现尊严和男性雄威的唯一途径,迎合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也成了他们证明男子雄风和男性气概的仅有出路。殊不知,黑人男性却因此遭受了漫长的人性扭曲和异化之路。
长期生活在种族歧视和父权制思想文化的阴霾下,这种人格的异化也发生在哈波身上。哈波刚和索菲亚结婚时成天忙个不停,“他喜欢做家务事,喜欢做饭、收拾屋子,他好像生下来就会这一套”[10]26。但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腐蚀下,哈波开始效仿霸权父亲的一举一动。他开始羡慕西丽对父亲的唯命是从,又因为索菲亚不受他的控制而恼羞成怒。思索再三后,哈波企图依靠暴力制服索菲亚。然而首次暴力尝试却以失败告终,他反被高大的索菲亚打得鼻青脸肿。尽管如此,哈波还是想方设法地想骑在索菲亚头上作威作福。当西丽再次见到哈波时,他眼睛肿得如拳头一般大,面对西丽的询问,哈波不但没有丝毫悔意,反而理直气壮道:索菲亚是我老婆,老婆就该听话。由此可见,哈波和其父亲已然沦为男性气质神话的牺牲品,他们贬低女性,对女性恣意妄为,他们的人格早已残缺。
多次暴力尝试未果的哈波最终失去索菲亚的爱,而哈波对此并无悔改。相反,他重新找了个黄皮肤小个子女友,并给她取外号“吱吱叫”。和高大结实的、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索菲亚相比,“吱吱叫”不仅个子矮小,最重要的是她和西丽一样对男性百依百顺。这是他在索菲亚身上从未体验过的,而这恰好能实现对哈波自卑心理的补偿,满足他对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幻想,以此彰显他早已扭曲的男性尊严和男性气概。
三、“男性气质”之梦的幻灭与传统男性气概的回归
“某某先生”和哈波始终执迷不悟地奉行美国主流社会男性气质的种种规范,给西丽和索菲亚的身心造成双重伤害,最终她们愤然离家。男性权威首次受到挑战的“某某先生”怒不可遏,但不可否认的是,西丽的大胆反抗恰好为他重新审视两性关系提供契机,帮助他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对其男性气概的回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丽的离开是“某某先生”男性气概的回归与主体身份建构的重大转折点。西丽走后,“某某先生”开启了一段自我反思之路。他努力信教,不仅辛勤劳作、卖力干活,而且像女人一样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转变表明“某某先生”骨子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已经悄然改变。不仅如此,“某某先生”还学会照顾和关心家人,他挖空心思给生病的小孙女做好吃的,而以前他对自己的子女则是不闻不问。从冷漠无情到学会关爱幼小,“某某先生”异化的人性逐渐复苏,他开始像正常人一般拥有责任感和爱心。除此之外,他甚至能够听取别人的建议了。西丽离开后,哈波建议父亲把他故意藏的耐蒂(Nettie)的信寄给西丽,他也真的照做了。这一转变证明他已经开始倾听家人的声音,并懂得健康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当西丽再次回归时,她发现“某某先生”现在喜欢搜集各种各样的贝壳。收集贝壳需要耐心,同样地,要建立互敬互爱的父子关系与和谐友爱的两性关系,男人也需要耐心,去倾听和交流,而不是用暴力让孩子和女人沉默。通过学习,他关注和提升自己的内在品质,逐渐抛弃以暴力为首的白人主流媒体号召下的外在性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与此同时,西丽惊奇地发现跟他讲的话他好像都听进去了,她甚至觉得只有“某某先生”才能真正地懂她。改变后的“某某先生”不仅实现了个体人格的矫正和重塑,而且建立了和谐的家庭和两性关系。这是“某某先生”男性气概的内在性回归和个体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此时小说的叙事也迎来一个重大转折,原来一直没有名字的“某某先生”终于有了名字——艾伯特(Albert)。从给子女命名来看,学者罗虹认为,“在非裔美国黑人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非洲的名字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2]21。众所周知,姓名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和民族文化的标志,而且“非洲黑人对名字极为重视,并认为一个人的名字是其人格的重要成分,甚至是灵魂的一部分”[12]21。但小说中西丽、索菲亚等女性一直不愿以他的真名相称,只称他“某某先生”,这表明在长期受其奴役和压迫的女性眼里,“某某先生”早已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的完整人格。学者隋红升、陈吉也认为“命名(naming)是一个重要的叙事策略,是人物身份的重要符码”[13]93。个体身份的缺失,究其深层原因,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影响身份的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等也对身份和认同起着决定的作用”[14]6。这种个体身份的缺失也是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种族歧视与压迫盛行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因此,要想建立主体身份,黑人男性必须摒弃对美国主流社会男性气概模式的盲目崇拜,从黑人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实现像黑人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男性气概回归后的“某某先生”整个人都变了,如他自己所言,“我现在心满意足,我第一次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世界上”[10]180。
由此,建立主体身份对个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某某先生”的转变赢得了西丽、索菲亚等女性的一致认同和尊重,并最终赢得自己的名字,这标志着其男性主体身份的最终确立。重塑个体人格和拥有个体身份后的艾伯特开始思考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价值,他越琢磨这些就越爱大家,同时他还惊奇地发现大家也都很喜欢他了。此时的“某某先生”已经彻底从男性气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实现从对外在性霸权男性气质的追求到向传统男性气概的内在性回归。他不但学会尊重女性、自我控制、拥有责任心和意志力,也不再把暴力当作征服女性的武器。由此、传统男性气概是一种内在性的精神品质,也是一种宝贵的内在力量,能够帮助黑人男性抵抗来自白人主流媒体方方面面的压力、焦虑和恐惧。
综上,健全、完整的个体人格和两性关系的和谐是主人公男性气概回归的重要推手,这同样体现在哈波身上。在“某某先生”度过的那段糟糕日子里,哈波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好些个夜里他甚至把父亲搂在怀里安慰。索菲亚察觉到哈波的这些转变才又对他产生感情,这表明个体健全的人格对于自身、家人和两性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哈波也正是在索菲亚刚毅、坚强、自立自强精神的感召中逐渐放弃了暴力。因此,“自我主体意识的确立不仅对黑人女性的成长有着重要意义,对黑人男性来讲,也是一种宝贵的精神感召”[13]92。从此,哈波不仅卖力工作,还帮忙做家务、带孩子,并无条件支持索菲亚。他摒弃了“老婆就是用来揍的,老婆就该听话”这一深入黑人男性骨髓的错误观念,重新理解、尊重和爱护女性。这一颇具仪式性的一幕标志着哈波男性气概的彻底回归。这种男性气概显然是建立在尊重、沟通而不是暴力的基础上。
四、结语
《紫颜色》是一部长篇书信体小说,也是一部极富思想的作品,小说在关注黑人女性自我发展的同时,又深入探讨了黑人男性气概的建构历程。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我们发现黑人男性气概建构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没有名字的“某某先生”到男性身份确立后的艾伯特,从霸权性男性气质腐蚀下的暴力分子到摆脱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束缚后的哈波,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旨在警示黑人族群要想建构真正的男性气概,必须从现代男性气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男权思想的禁锢中脱离出来,跳出男尊女卑思想的羁绊,回归真实自我。只有将黑人男性气概的建构与黑人男性个体身份建构、和谐友爱的两性关系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新型男性气概的构建,实现以勇气、尊敬、自我控制、自信、忠诚、坚毅等为核心的传统男性气概的回归。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现代男性气质模式不仅使黑人男性的人性遭受扭曲和异化、还给黑人女性身体和心灵带来巨大伤害,因此,关注男性内在品质的发展,把真正的男性气概和种种残存的男性气概流俗和刻板印象区分开来,从而实现传统男性气概的内在性回归、使之真正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