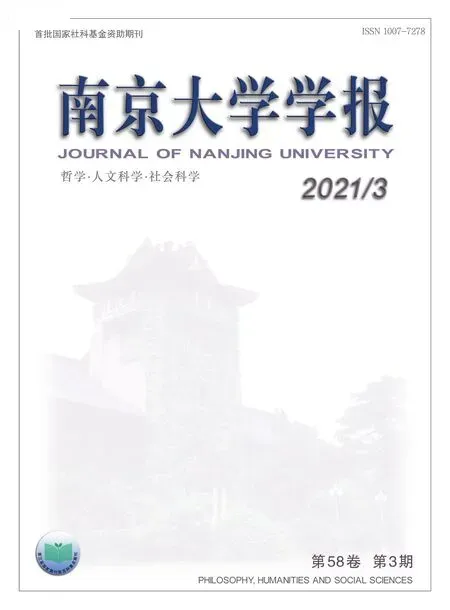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的思维学考察
张 晶 唐 萌
(1.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24;2.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9)
命题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项开创性工作,由吴建民、张晶等人发起,渐为学界所重。近年来,在大量范畴研究、命题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开始展开深层次的命题研究。相比范畴研究而言,命题研究对于探索古代文论思想系统、开发古代文艺思想资源、创建中华思想文化的话语体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曾提出:“要在中国美学理论建设上有突破性进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仅停留在范畴研究的层面上已经难以充分发挥古代文艺理论的资源功能,难以承载这样的历史使命了。”(1)张晶:《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研究的意义何在》,《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1期。现有的范畴研究在理论阐发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要进行命题研究,不应驻足于“命题”的理论阐释层面,而是需要对“命题”生成的内部机制,包括命题的思维类型与思维程序,以及命题的外部功能,包括文论体系的建构功能、文论思想的阐释功能以及文化风俗的引领功能等深层机理性问题有自觉的认识。
从现有研究论著看,学界对“命题”本身已经做了基本辨析,涉及命题的内涵与外延以及范畴与命题之间的关系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应进一步向纵深拓展。在举出经典命题范例之后,还应继续总结命题的一般性特征;认识命题的发展与流变之后,更要了解命题的生成过程;注意到命题与范畴的形式区别之后,还应关注命题相对于范畴的独特功能。作为意识的模型、思维的外显,命题深受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命题反映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表述形式的命题背后是不同的思维形态。鉴于此,本文拟从思维学角度对古代文论命题进行综合考察,以揭示古代文论命题深层的学理依据。
一、古代文论命题的定义、形式与构成
吴建民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由命题构成,命题借助于名词概念即范畴来表达。三者的关系是:范畴构成命题,命题组成体系,命题与范畴是构成古代文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因素。”(2)吴建民:《命题与古代美学理论之建构》,《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1期。其中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命题的表达形式,二是命题与范畴的关系。这两个问题是认识古代文论命题的关键。
要认识命题,必先了解“范畴”,因为命题与范畴关系密切。何为范畴?
从“范畴”一词的起源看,最早使用“范畴”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其《范畴篇》对范畴的语言形式进行界定。亚氏称:“所说的东西中一些是按复合说的,一些则无复合。因此,那些按复合说的例如人跑、人赢;而那些无复合的例如人、牛、跑、赢。……不按任何复合方式说的东西中的每一个,或者表示实体,或者表示数量,或者表示性质,或者表示关系,或者表示何处,或者表示何时,或者表示姿态,或者表示具有,或者表示施为,或者表示遭受。”(3)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6页。质言之,亚氏将范畴的语言表达形式分为“复合”与“非复合”两类。姚爱斌说:“根据亚理士多德的理解,范畴应该是‘非复合词’(即词)。而不应是‘复合的’语言表达(即句子)。”“按照现在的说法,‘复合的’表达相当于或长或短的句子,‘简单的’表达则相当于词。”(4)姚爱斌:《“范畴”内涵重析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对象的确定》,《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我们可以确认,从语言表达的形式来看,“范畴”是非复合概念,相当于语词,而非或长或短的句子。
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对范畴进行了全面研究。他总结了“范畴”的定义:“范畴是英文category的汉译,指反映认识对象性质、范围和种类的思维形式,它揭示的是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中合乎规律的联系,在具有逻辑意义的同时,作为存在的最一般规定,还有本体论意义。正是基于这种特性,它被人用作精神操作的工具,进而确认为思维特有的逻辑形式。”(5)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简单说,范畴是关于事物特征与关系的基本概念,它能够揭示事物之间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具有逻辑意义、本体论意义及特有的逻辑形式。在古代文论范畴中,有“道”“气”“象”这样的元范畴,有“神思”“妙悟”等创作范畴,有“风骨”“雄浑”“冲淡”等风格范畴,还有“体势”“意脉”“格律”“肌理”等体式范畴,等等。从内涵上看,范畴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众体文学的特征及规律;从形式上看,范畴则表现为不同概念的集合(6)关于“概念”与“范畴”的关系问题,张岱年认为,在概念之中,有些可以称为范畴,有些不是范畴。如表示存在的统一性、普遍联系和普遍准则的可以称为范畴,而一些常识性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马等,不能叫作范畴。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4页。张岱年从哲学范畴立论,与本文所探讨的文学理论范畴仍有区别,可做参考。。
这里周延出“概念”一词。“概念”是人类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把所感知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进行抽象概括的一种语词表达,它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一般认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靠的是逻辑思维。事实上,人的思维不只有逻辑思维这一种类型,也有非逻辑思维,感性认识即偏重于非逻辑思维或称前逻辑思维。这就是说,概念是思维的产物,既含有逻辑思维也不乏非逻辑思维的参与。概念的集合又以某种形式组成了范畴,所以,范畴具有比概念更高一级的思维属性。汪涌豪说:“范畴是比概念更高级的形式。……概念是对各类事物的性质和关系的一种反映,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单一名言,而范畴则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是关于一类对象的综合性名言,它的外延比前者更宽,概括性也更大,在许多时候能统摄一连串层次不同的概念展开事理的推演和论列,故具有最普遍的认识意义。”(7)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第7-8页。
在对“范畴”的形式和内涵进行一番简要梳理后,回到本文的核心议题“命题”。既然范畴是命题的基本单位,命题由范畴构成。那么,命题的形式是什么?古代文论中哪些形式可称为命题?吴建民认为:
“命题”本是一个逻辑学概念,其基本形式是“判断的句子”或“陈述句”,也可以是一种单纯的“判断”;其基本内涵是“判断”或“陈述”一种道理、观点。这种解释基本适用于解读古代文论中的命题。按照“命题”的这些特点,古代文论中的“诗言志”“知人论世”“立象尽意”“诗无达诂”“发愤著书”“神用象通”“文已尽而意有余”“不平则鸣”“以文为戏”“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思与境偕”“文以载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体物而得神”“文,心学也”等都是典型的命题。(8)吴建民:《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页。
通过以上列举的命题范例可以看到,所谓“范畴构成命题”的形式特征即命题包含范畴。具体而言,命题是以某种特定的逻辑位序进行的范畴串联,它表达对某些范畴的经验性或逻辑性的体认以及范畴之间的诸种联系。比如,明末公安派袁宏道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命题。其中,“性灵”“格套”作为基本的文论范畴,一属风格,一属体制,常见于古代文论。在这里,袁宏道对性灵、格套两个范畴提出了具体要求,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种要求与明代文坛拟古风气有关。明代文坛复古之风大盛,文学创作受格式套路的束缚甚剧。对此,袁宏道提出这一命题,饱含着袁氏追求独创的文学观念。显然,袁氏重自由抒发、追求独创的思想观点是通过对“性灵”与“格套”的态度表达出来的,而表达这一态度的语言形式就是命题。可见,命题与旨在描述、体现、反映某种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范畴”不同,它还肩负着表达某种意向(包括思想、观点等)的话语职能。关于古代文论命题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借助近代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概念与范畴》一书中对作为哲学概念的“命题”的定义来参照理解,柏林对“命题”的定义是:“命题指的是向人表达某事是或不是怎么回事的句子。句子指的是遵守一定语法规则的词语组合。”(9)以赛亚·柏林著、亨利·哈代编:《概念与范畴:哲学论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19页。柏林对哲学命题的定义直观地阐述了命题的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命题表达是非判断;其二,句子是命题的表述形式;其三,表述命题的句子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
无论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命题,还是作为逻辑学概念的命题,二者对“命题”这一概念的内容与形式特征的论述基本一致。根据这些论述以及与范畴定义的比较,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文论命题做出基本的界定:中国古代文论命题是指能够表达文学观点、阐发文学思想的复合型长短句,它体现着是非判断或对事实的认定,具有阐释文学思想与指导创作实践的意义,比如“诗言志”“文以载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
二、古代文论命题的思维特质与思维类型
从整个文学批评理论的大系统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术语、概念、范畴、命题何其之多,不可胜数,但它们始终离不开古人的知觉活动、想象活动、情感活动和思维活动。无论是术语、概念、范畴还是命题,都是对古代文学创作、批评经验的特定视角的言说,本质上都是一种话语形态。而不同的言说方式、多元的话语形态,归根到底都是思维问题。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甚为密切,一方面,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需要借助语言来表达;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决定着言说方式,有什么样的思维就有相应的言说方式与之配合。中国文学文论的诗性表达反映着中国传统的思维特征。正如袁行霈在《中国诗学通论》中强调的,要研究中国诗学,“就要了解中国诗学的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10)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14页。。的确,思维是开启中国诗学、中国文论研究的门径,因此,研究古代文论命题也须从思维入手。
思维学是一门周延广泛的学科,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脑生理学、符号学等都有从本学科视角对“思维”进行界定及建构的相关理论。然而,这些界说大多遵循逻辑思辨的分析方式,难以涵盖前逻辑思维阶段即原始宗教思维类型。为此,思维学家赵仲牧提出新的思维界说,今从之。赵仲牧提出:“思维是运用符号系统、遵循一定的运作程序,从不同的领域去发现或构造各种秩序和规范的意识活动。思维具有符号、程序、秩序三个基本要素。”(11)赵仲牧:《赵仲牧文集 第1卷 思维学、元理论和哲学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6-186页。他根据思维的构成要素与整体结构对思维进行了分类,分为原始—神话思维、审美—艺术思维、思辨—分析思维、体悟—直觉思维、计量—运算思维、日常—综合思维六类。应当承认,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以直觉、感性为主,相比西方的辩证思维、逻辑思维而言,直观性和整体性确乎是中国传统思维的显著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人没有抽象化、概括性、思辨性的理性思维。从“命题”这一特殊视角统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述,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学、文论并非只有感性直觉的体认、诗性的表达。除感性直觉的体认、诗性的表达之外,审美—艺术思维、思辨—分析思维、体悟—直觉思维三种思维并驾齐驱,诗性言说、理性论述、体悟式表达迭相而出,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表达模式。
(一)审美—艺术思维类命题
审美—艺术思维类命题是基于审美—艺术思维而创设的文论命题。此类命题是由作为思维主体的人和心所具有的“情”与作为思维客体的天和物表现出的“景”,二者相磨激荡而生成。物与天呈现出的“景”寄寓着人心之中的“情”,天人之间、心物之间的关系借由情景相融而呈现,这是审美—艺术思维创作审美意象的实质。有研究认为,文论范畴、命题具有逻辑思辨性,是逻辑思维的产物。此论只揭示了范畴、命题的一种特征,或者说是某一类范畴、命题的特征。如机趣、韵致、通变、阴阳一类范畴是古人对客观现象、文学规律的抽象概括,确实富有思辨性。但是,诸如“文”“诗”“人”“心”这类范畴则是一种文体或本体的概念指称,并未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意识。范畴如此,命题亦是如此。应该看到,并非所有范畴都是逻辑思维的产物,也不是所有的命题都只有逻辑思维的参与。审美—艺术类思维是建构文论命题的重要思维类型,它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让抽象的规律呈现出形象的言说形态,从而使得文学理论既有“理性地”说也有“诗性地”说,如“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神用象通”“杼轴献功”等。
此类命题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形象化的语言面貌。从语言表达方式与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来看,中国古代语言往往带有一种泛化的诗性色彩。古人善于运用形象化的、感性的、直观的语言来表情达意,而这种语言形态所表征的正是“审美—艺术思维”的基本程序。赵仲牧说:“审美—艺术思维的思维程序是通过形象去表现情意的思维程序,这是一种运用想象、移情和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等方式去创造审美意象和表现感情意念,并着力梳理和描述与此相关的深层秩序的思维程序。”(12)赵仲牧:《赵仲牧文集 第1卷 思维学、元理论和哲学卷》,第181页。以“杼轴献功”说为例,《文心雕龙·神思》云:
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1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95页。
“杼轴献功”是刘勰针对文学构思而创设的理论命题,理解这一命题须联系上下文语境。首先,“杼轴献功”说是一种隐喻。刘勰将文学创作喻为织布,将文章构思喻为织布的经营组织。所谓“杼轴”,亦作“杼柚”,是指织布机上的两个部件,即用来持纬(横线)的梭子和用来承经(竖线)的筘。织布的经营组织与文章的构思具有内在思理的相通相似,这是刘勰以前者隐喻后者的前提。织布隐喻文章构思在《文心雕龙》中很常见,如“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文心雕龙·情采》),“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文心雕龙·正纬》)等,都是以经纬经营隐喻文学创作。对此,古风、闫月珍等人总结过《文心雕龙》乃至中国古代文论所具有的“以器物隐喻文学”的特点。从表面上看,“器物喻文”是一种话语言说形态。而进一步从语言背后的思维角度看,器物喻文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借助形象表达事理的思维程序。就“杼轴献功”而言,其中,既有刘勰对“织布”过程中的杼轴、丝麻等织布器物、织工程序的形象认识,也有对文学中情辞关系与创作规律的深层体会。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对于二者之间共通性的大胆联想。基于此,刘勰才能够以艺术化的语言来描述文学构思的深层秩序。此说之意为拙辞、庸事常蕴含着巧义与新意,犹如布出于麻。文章构思与织布经营一样,只有善于经纬相配、精心加工才能制造珍品。可见,“杼轴献功”命题以具有隐喻意义的艺术性语言为思维符号,展开于“文学”与“器物”的类比联想的思维程序中,最终表达了文章构思、语言加工的深层秩序。
如“神用象通”“衔华佩实”“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等命题大抵如此,都是以形象化的语言(思维符号)、类比式的想象联想(思维程序)来表达文学创作的某种规律(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命题都是审美—艺术思维作用下的文论命题。尽管这些命题未脱离感性的语言形式,甚至还粘连于具体的物象描述,“取一种感性直观的姿态”(14)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第61页。,但它们的感性形式及所勾勒的经验世界,最终指向某种客观理性秩序,这是作为文论命题的真正价值所在。将理性的规律诗性地表达,个中展示着中国古代文化最生动鲜活、最具人文色彩的文化品格。可以说,此类命题是最具中国传统思维特色的一类文论命题。
(二)思辨—分析思维类命题
19世纪以来,西方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非实证主义论者提出两种认知路径,因而形成两种哲学命题:关于可能经验的直接陈述的“经验命题”与用理性把握材料的“逻辑命题”。前者忠实于直接经验,以直接经验的获得作为认知真理的途径;后者强调逻辑推理,以间接经验的获得作为认知真理的途径。两者各具优势,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认知对象、不同的认知条件。两种认知途径代表着两种思维类型,如果说此前所论审美—艺术思维类命题接近于哲学上的经验论,那么这里要谈的思辨—分析思维类命题则近似于唯理论。
根据思维学对思辨—分析思维程序的定义:“这是一种运用演绎、归纳或假设、求证等方式并根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推导或解析自然、社会和心理领域中深层秩序的思维程序。”(15)赵仲牧:《赵仲牧文集 第1卷 思维学、元理论和哲学卷》,第182页。这一思维程序与我们通常理解的逻辑思维甚为接近而有别于形象思维(16)关于思维分类方法,现有三分法即“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灵感思维”。赵仲牧反驳此说,认为形象思维的确定以是否有“象”为分类标准,逻辑思维以是否具有逻辑分析为标准,二者标准不同,不足以区分不同的思维模式,故提出思维的六分法。。随着人的思维能力的提升,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客观世界的形象化描述而开始尝试以现象作为基础,通过演绎、归纳、推断的方式进一步解释某一领域的深层秩序。这时,思辨—分析思维走向成熟,在文学批评领域即表现为从经验范畴向逻辑范畴,从经验命题到逻辑命题的转变。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颇具代表性的思辨—分析思维类命题。若按现代学科分类看,这并不是文学理论命题,而是艺术学领域的绘画理论命题。但以古代大文艺观视之,画论与文论同属于古代文艺范畴,同样能够反映古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观念。这一命题载录于《历代名画记》,由唐代画家张璪所提。
“张璪,字文通。吴郡人。……尤工树石山水,自撰《绘境》一篇,言画之要诀,词多不载。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璪所受。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于是阁笔。”(17)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201页。“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命题中包含三组具有辩证关系的范畴,分别是:外与中,师与得,造化与心源。在张璪看来,绘画应有所师法而非闭门自悟。究竟师法于何人何处?他提出师法“造化”。事实上,“师造化”这一观念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由画论家姚最提出,其云:“天挺命世,幼禀生知,学穷性表,心师造化,非复景行,所能希涉。”(18)姚最:《续画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所谓“师造化”就是取材于自然。姚最强调“心”师造化,心即是师法的主体。在心师造化的过程中,画家之心被造化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心也是师法造化的客体。所以在姚最这里,心与造化的分际尚不明显,心物之间的辩证关系亦不突出。到了张璪,他将造化界定为外部条件,“外”可以理解为“向外”。既然有“外”,势必有“内”,“内”又指什么呢?答案就在这个命题的后半部分——中得心源。向外,师法造化;向内,求诸内心的情思营构。姚最的心师造化强调“心”对造化的师法,忽略了心对造化的改造。而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方面承认了向外“师造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更强调艺术家内心的情思营构之关键。毕竟,自然造化不能自觉地成为艺术美,由自然到艺术还需要人“心”之源。所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命题,从创作过程看,有“求之于外”与“得之于中”的分际;从艺术构思看,有师法与自得之别;从主客关系看,有造化与心源之分。应该说,张璪对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构思、主客关系、心物关系的思考与分析已经越过了实践经验层面,走向理性思辨的境域。
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的思辨性取式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先秦哲学系统中的“有无”“阴阳”“动静”“神理”等大量的哲学范畴无不体现着辩证统一的思想,沾溉于此,古代文论的很多范畴、命题亦表现出同样的思辨性。从“心”“造化”“师法”的单一范畴到“心师造化”的独立命题,再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命题的生成,这一过程经历了由心物不分到物我之别、由主客一体到主客分际、由单一到辩证、由粗朴到精细的多重转变。究其实质,是古代文论思维由实践的直观经验向抽象的理性思辨的进步。这一进步,决定着命题相对于范畴在创作实践方面的普遍指导作用,奠定了命题作为成熟的理论话语的自在品质,并孕育出贯穿整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的精神活力。
(三)体悟—直觉思维类命题
直觉体悟作为把握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历来为古人所重。先秦儒家的“思通”、道家的“玄览”、宋代理学家的“静观”以及禅宗讲求的“顿悟”,都是体悟—直觉思维的映现。与审美—艺术思维和思辨—分析思维有所不同,这一思维具有更强的内向性、更注重体验性,也更具有心灵化和个性化特征。受其影响,古代文论家在对文学现象的思考与阐发中也善于运用体悟—直觉思维,并创设了一系列体悟—直觉类命题。
“体悟—直觉思维的思维程序主要是比喻说理的程序。这是一种运用体察、内省或领悟、直觉等方式,选择特定的事象作为比喻,去说明或论证心物之间和天人之间以及相关领域中的深层秩序的思维程序。”(19)赵仲牧:《赵仲牧文集 第1卷 思维学、元理论和哲学卷》,第183页。文学出于人心巧思,描绘大千世界众生图景,常有“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文心雕龙·神思》)的精微之处。刘勰说“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即言精微境界中不可言说之妙。这一“妙”,不能直接感知,亦不能用概念表述,只能借助比喻加以描摹。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提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20)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页。严羽以参悟禅法的方式领悟诗道,在他看来,诗道与禅道一样都有不可说破之妙处。诗道如何妙?严羽这样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1)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第26页。
诗有别材之妙,有别趣之妙,这些妙处与读书论理无关,但是不读书不论理又难以达到至妙之境。不沉耽于论理,不落于语言之束缚,才是诗之上等之妙。盛唐人的妙,妙在兴趣,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妙,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像空中的声音、形貌中的色彩、水中的月亮、镜中的成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既然诗之妙不可凑泊,又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为上,那么,对诗之妙的刻意言说注定徒劳无功。所以严羽并没有对“妙”进行过多的理论辨析,而是采用了“比喻”式的描摹。他说:“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这段描摹诗之“妙”的文字,在形式上构成了一个命题。这一命题正是严羽以“体察、内省、领悟、直觉”的方式,以音、色、月、象为喻体,去描摹“妙”这一深层秩序。由于这种深层秩序——精微之妙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叙述中严羽借助了象喻的方式,通过象喻的形象性来悟解义理的精微。这也说明,体悟—直觉思维是一种形象与理辩相互关联交替而行的思维模式。
体悟此类“不著痕迹”“不可说破”“不立文字”的精微妙境需要实现两重超越:其一,超越感性经验;其二,超越理性思辨。一旦陷入事物的有形之象或个别事物的殊相,必然很难上升到“体道”的层面。道家讲“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22)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1页。,这既是对“道”的特征的概括,也有对体道方式的提示。禅宗讲“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23)张岱年:《中华思想大辞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0页。,也是讲求不依经卷、不涉文字,唯以心灵契合之“心传”为参禅之法。沾溉于斯,古代文论中的很多范畴直接得益于传统哲学。严羽“以禅喻诗”就是极为典型的一例。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与文学思维的迭相参照。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形式上极为相似,都少有完备的逻辑推衍系统、缺乏严整的推理体系,并呈现出零散化、个性化、心灵化的理论面貌。当然,从另一角度说,这些特征也为体悟—直觉思维的诞育与发展开辟了天地。
综上可知,思维并非一个不可解构的笼统概念,思维有不同的类型,思维对象互有分界,不同类型的命题有不同的思维特质。审美—艺术思维重“象”,此类命题以文学形象的观察、想象、联想为出发点,以再现、描绘、刻画形象的规律为落脚点;思辨—分析思维重“概念”,此类命题以演绎、归纳、求证文学活动的本质规律为出发点,以思辨析理为旨归;体悟—直觉思维重“喻理”,此类命题以体察、内省文学思想的精微之理为出发点,以喻理言说为要义。很明显,不同类型的思维创设着不同的命题,用于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艺术思维类命题“杼轴献功”,到唐代思辨—分析思维类命题“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再到宋代体悟—直觉思维类命题“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有两条甚为清晰的线索呈现于前:一是中国古代思维发展的脉络,二是中国古代文论命题演进的理路。思维作为命题生成的智能基础,决定了命题生成的思维程序与结构形式;命题这一语言形式作为思维的工具,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思维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解析事理规律、建构天人秩序过程中的独特魅力。思维对于文字、语词、范畴、命题的组创,开拓了古代文论饶有意味的表现形式与无穷的理论空间,使其得以长久地照鉴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演进。
三、古代文论命题与文学秩序的建立
作为思维的产物,命题具有思维的功能属性。思维所具有的重要功能特性就在于通过对深层秩序的梳理来解释各个层次的秩序,最终把客观世界中各种可观察感知的秩序以及相关的事象解释清楚。如前所述,审美—艺术思维借助形象梳理秩序;思辨—分析思维以思辨析理表现秩序;体悟—直觉思维通过喻理言说表达秩序。尽管运用的思维方式不同,但它们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共同的旨归——推进了文学秩序的建立。对于古代文论命题而言,其所论广涉古代文学的各个层面,但总其归途,文论命题建立文学秩序分别在形式秩序、思想秩序、价值秩序三个层面推进。
(一)形式秩序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始,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学界一直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论有无体系?学术界形成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认为,古代文论有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体系完备的论著,因而具有体系性;另一种认为,古代文论多零散性、自发性、点评性表达,缺乏严整的理论体系(24)梁实秋的《近年来中国之文艺批评》说:“中国文学里,本来有文学批评这一类的作品,但大半不过是些断简残片,没有系统的叙述,亦没有明确的主张,例如诗话一类的作品,里面也不是没有一点半点的批评的材料,但未经整理与译述之前,简直不能算作正式的批评。”见梁实秋:《梁实秋散文集》第3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64页。郭绍虞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并无特殊可以论述之处,一些文论诗话及词话、曲话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统的材料,不是记述闻见近于史料,便是讲论作法偏于修辞;否则讲得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页。蒋寅说:“中国古代有系统的文学理论吗?或者说有一个文学理论体系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古代没有产生一部真正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见蒋寅:《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从文心雕龙谈起》,《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承认古代文论具有体系的论者众多,故不列举。。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如实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特征,因论者视角不同,加之对于“系统”一词的标准各异,各有其道理。但若从命题视角重新审视古代文论,不难发现,文论命题所具有的衍生性与系列性,在形式层面建构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体系。
从前文分析可知,命题的基本单位是范畴,作为范畴的组合体,命题与范畴具有某些共同属性,如衍生力及统序性。尤其是单体范畴,具有极强的衍生力,它能与其他范畴搭配组合,形成若干新范畴。比如,“韵”这一单体范畴,可与“神”这个范畴组合生成“神韵”,还与“气”这个范畴组合生成“气韵”,还能进行内涵更丰富的组创,衍生出“气韵生动”“神韵冲简”等涵容更大的范畴或命题。与范畴一样,命题也具有这种衍生性与序列性,在不同的逻辑位序串联组合下,单个命题衍生出命题组序。比如,由“诗”到“诗言志”,再到“诗缘情”,再到“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等,这就是一个关于“诗”文体范畴的命题组序:
诗言志。(《尚书·尧典》)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诗所以合意。(《国语·鲁语》)
诗无达诂。(《春秋繁露·精华》)
诗者,志之所之也。(《毛诗序》)
诗缘情。(《文赋》)
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文心雕龙·明诗》)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
这些命题都围绕某个范畴衍生而成,正是这种衍生性形成了命题组序。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文论命题组序纵贯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之中,反映着历代文人意脉相连的文学思想。自上古至近代对“诗”的理解,形成了一个内在体系。《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认为诗是用来表达情志的。春秋之际,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总结了诗的四种功能。战国时期,《国语》又提出“诗可以合意”。汉代以降,董仲舒又对解诗有新的看法,提出“诗无达诂”。《毛诗序》作者继承“诗言志”说,强调诗的情感意志属性。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文学的自觉,文论家对诗的认识得到空前解放。陆机别开生面,提出“缘情”说,一改此前对诗的传统认识。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也认同了“诗能表达情性”的观点,提出“持人情性”一说。唐宋以后,讨论渐多,亦渐成熟。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一命题已有总结前人成说之功。以“诗”为中心,在历代文论家的思想“加持”下,众多讨论“诗”的命题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组序,呈现出“诗”这一文体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发展流变脉络。若将视域继续扩大,古代文论史上不仅有“诗”,还有“象”“清”“韵”“气”“体”“神”等文体序列、创作序列、审美序列的相关范畴,这些范畴所衍生的命题汇聚成一个庞大而完备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由此而言,以古代文论命题的衍生性与系列性所决定的这一形式秩序,最终指向了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二)思想秩序
如果说命题的形式秩序是一种呈现于“外”的秩序,那么,命题的思想秩序则是一种归属于“内”的秩序。对于古代文论家而言,或许他们还没有自觉建构文学的形式秩序的明确意识,但他们怀有建构文学思想秩序的强烈愿望。在古代文论史上,没有哪一位论者的论述是凭空而论、为论为论,所论必定基于对文学现象的切实体悟与深刻理解,甚至很多古代文论家都是一流的文学家,其论皆为亲历创作的甘苦之言。应该说,无论是理论著述,还是零散点评,甚或不同编选意图的选本,无不寄寓着古人的文学思想与文学理想。
就文论命题的内容而言,它是某种观点的表达或理论的阐发。表达观点、阐发理论的过程无异于思想秩序的建构过程。赵仲牧说:“各种解释活动和解释模式均在不同程度上以可观察感知的秩序为根据,用不同的方式去梳理和描述不可观察的秩序,并力图用后者解释前者。”(25)赵仲牧:《赵仲牧文集 第1卷 思维学、元理论和哲学卷》,第113页。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与既有的观点,文论家渴望以其独到的理解树立某种新的理念。比如,“象”范畴的发展流变。
观物取象。(《周易·系辞》)
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
铸鼎象物。(《左传·宣公三年》)
澄怀味象。(《画山水序》)
神用象通。(《文心雕龙·神思》)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二十四诗品·雄浑》)
“象”范畴最早作为哲学范畴出现于《周易》,意为对物的模拟,“象也者,像此者也”(《周易·系辞》),其意义在于反映古人对宇宙运行规律的思考。《老子》继承了“象”概念并提出“大象”的新概念,以象喻道,赋予“象”本体论意义。《左传》中也出现了“象”,“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此处“象”有模拟之意,仍作为手段而言。及至魏晋,画论家宗炳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提出“澄怀味象”命题,刘勰以“象”作为贯通精神与物象的方式,提出“神用象通”命题。从“物象”“取象”到“大象”“象物”,再至“味象”“意象”,“象”作为一个基本范畴表现出了多面性,从哲学拓展至文学、艺术、美学等众多领域,从方法意涵演变为本体论再变为艺术鉴赏范畴。这种多面性反映出古人借助“象”表达对世界本原、文学创作、艺术鉴赏等不同领域的深层秩序的自觉体认。
一方面,规律的总结植根于可观察的、已有的秩序;另一方面,总结规律的目的更在于呈现新的秩序。如前所列与“诗”有关的系列命题,所呈现的就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文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先秦时期的“诗言志”是对“诗”的内容界定;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综合说明;“诗无达诂”是对“诗”义理解的一种观点;“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是从文体角度出发,对“诗”的文体性质进行的定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则是根据创作实践,对“诗”体裁、内容的全面概括。后者往往以前人的观点为基础,或继承之,或反驳之,或另辟视角提出新的论说,总之,不会完全因袭前人之言,而是试图革新成说或集前人之大成。因此,对“诗”的理解才有了历时的发展。从内容到功用、到意义、到性质、到体裁,从不同的方面,对“诗”进行界定、说明、论证、定义、概括,从而创成新说,由此成就了系列性的文论命题。这其中无不体现着论者对于建构“诗”这一文体秩序的努力。
共时地看,每一种观点、每一个命题都反映着论者以个体视角建构的思想秩序;历时地看,每个时代、每个时期的主流思想则代表着某个时代的思想秩序。“诗言志”“兴观群怨”“诗所以合意”是先秦时期重功用的文学观念的体现;“诗无达诂”“诗者,志之所之也”是汉代儒家诗教观念的体现;“诗缘情”“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是魏晋南北朝重艺术特征、重情性的体现;“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则是中唐写实尚俗文学观念的体现。通而观之,这些命题所揭示的某种秩序都烙印着论者的思想,各自呈现出鲜明的学术特点。作为古代文论发展的历史性成果,它们更是时代思想的印记。
(三)价值秩序
在形式秩序与思想秩序之外,古代文论家还着意于价值秩序的建构。价值秩序广涉于作品、作家、鉴赏各个领域,是与事物的好坏、是非、对错、真假、善恶、美丑等价值相关的秩序。价值秩序更能体现古代文论家的个性化观点。
纵观古代文论发展史,历代都有论者“热议”的话题,都有各自推崇的风尚,如汉魏“风骨”说、南朝“声律”说、“滋味”说、唐代的“兴寄”说、宋代的“法度”说等。当论者或以客观陈述、或以褒贬态度高频次地评说某一现象时,预示这一现象即将上升为“现象级”的焦点。尤其是在当世文坛宗主的引领之下,声浪更甚。比如,清初诗坛的叶燮在《原诗》中所提的一系列诗学命题,颇具价值导向。
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
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
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
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
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26)叶燮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9页。
叶燮是明清易代之际的诗人、诗论家,晚年隐居于太湖横山,开坛设教,弟子甚众,沈德潜、薛雪皆从其学。清初诗坛,叶燮主张破除明人“诗必盛唐”的偏窄诗论观念,有意拓展诗歌的多元化取向,重视诗人的主体性,渐开风气之先。叶燮提出,创作主体应具有“才、识、胆、力”四种质素,指出四者之中当以“识”为先。他还进一步论述了“有胆无识”“有才无识”“有力无识”三种弊端。很明显,叶燮从“才、识、胆、力”四个方面对创作主体进行考察,无论对于“学诗者”还是“诗作者”来说,都是十分明确的要求。换言之,在叶燮看来,“才、识、胆、力”是衡量当世诗人的“价值标准”。叶燮之后,门人沈德潜、薛雪等人继承其诗论主张,宣扬成说,也提倡以诗人的“胸襟、人品、才思、学力”作为考察诗人诗作的标准。
不惟叶燮在诗学领域的主张,历代诗文流派的创作主张、文坛口号、审美风尚无不体现着鲜明的价值导向。殷璠《河岳英灵集》中主张的“神来,气来,情来”,元白诗派宣扬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实、尚俗、务尽”,韩愈主张的“以文为诗”,西昆体标榜的“雕润密丽”的形式美,江西诗派讲求的“无一字无来处”,明代复古派主张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及清代的“肌理”说、“神韵”说、“性灵”说等,都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各自流派或个体的理论主张,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意味。与一般的理论观点不同,具有价值导向的观点往往裹挟着论者尖锐的批评立场与鲜明的褒贬态度,对作品、作家的品评影响更大,使得这些导向甚至冲破文学的界域,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形态。刘熙载所提“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诗概》)已由诗歌品级上升到人之德性,反映了对品德的崇尚。司空图所提“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二十四诗品·典雅》)由诗风之雅丽引向了典雅人格的追求。刘勰指出“风末气衰”(《文心雕龙·通变》)的文坛风尚已经内在地透射着社会与时代的衰颓。诸如此类,文学批评之于人生、社会、时代的功用已不止于“再现”,更在于超前的洞悉与价值的引领,这无疑是某种价值秩序的内在建构。
综上,古代文论命题为文学秩序的建立开示了门径。文论命题的形式秩序决定着古代文论体系之建构,有力地回应了中国古代文论是否具有体系这一重大论题。文论命题的思想秩序对应于文学规律的总结及理论的阐发,昭示着古代文论并未停留在对文学现象的描述,而是进阶到思辨论理的思想秩序的建设层面,即从所谓“从事象立言”发展到“从事理立言”的高度。文论命题的价值秩序呈现于对文风、人格、世风、时风的文化引领中,绾结着各个时代的人文精神与世相风貌。形式秩序、思想秩序、价值秩序所导向的体系建构、理论阐发、文化引领,可以说是古代文论命题三种独特的文化功能。我们只有跳脱出古代文论本身的理论内涵,从文论命题的外部功能来考量,对古代文论命题独立的理论品格与高标之理论地位方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四、结 语
文论命题的生成与发展反映了文学内外诸要素的矛盾运动,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古代思维的发展与嬗变。作为思维的产物,命题的生成与思维的演变息息相关。不同的思维方式组创着不同类型的命题,不同类型的命题阐释着不同视域、不同层面的理论问题。丰富的思维类型决定了文论命题多元而丰富的理论形态,由取象到析理、由个体到整体、由局部到统观、由感性直观到理性思辨的多重转变,既符合人类思维进化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对命题发展过程的描述。在中国古代文学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文论命题不满足于对文学现象的描述、对事实的认定,而是以精谨的语言、鲜明的观点、理性的思辨揭示着文学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阐释着文学发展的深层秩序,以此不断强化着文学批评的话语地位,最终建构了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对话语权。
命题就是这样一种语言形式,这一形式在理论的确定性与言说的不定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张力。一面是语言对理论的把控,一面是理论对语言的挣脱,两相作用之下使得语言对理论的言说总有着或多或少的失落。也正因此,被言说着的理论将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