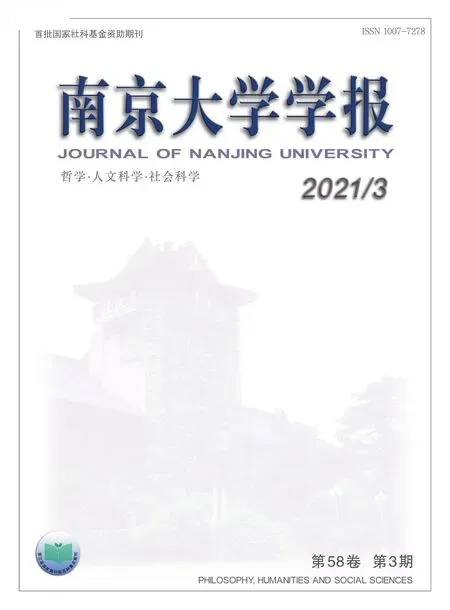流动民工的男女平权与代际父权制再生产——基于大都市医院“双薪护工”劳动与微信沟通实践的分析
曹晋 曹浩帆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女性主义研究的前沿正从聚焦妇女在教育、就业等领域的平等抗争扩展到关注男人的父权制如何被削弱、甚至瓦解的宽广领域,将家庭夫妻平等关系和情感维护纳入研究视线(1)蔡玉萍、彭铟旖:《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18-119页。。通过观察进城务工的双薪护工在都市面临的种种张力及其家庭内部互动关系、情感纽带和个体能动性的施展,笔者发现这些流动至都市进行共同劳动和生活实践的农村家庭,正是女性主义研究苦苦追寻的男女家庭平等关系的经典案例。本文通过关注共同进城务工的“双薪夫妻”的劳动实践和微信沟通,不仅再现了农民工家庭的都市生存压力,而且也反映了由此带来的社会性别权力的局部改变。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究三个问题:首先,通过对进城务工的医院夫妻护工的劳动实践及日常生活的在场观察,丰富农民工双薪家庭都市打工的主体性经验;其次,探究跨越城乡的夫妻在都市边缘谋求生存时所遇到的张力与困境,分析其在共同参与护理劳动和家庭事务的过程中如何开创夫妻平权的生活新貌;最后,探究护工微信沟通联络代际关系与护工经济收入去向如何重构农民工的代际父权制。
本研究试图通过传统民族志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路径洞察农民工护工在都市的生活压力以及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化。笔者父亲于2011年和2019年两次住院,在陪护期间,笔者雇请了一位护工帮助护理,前后共计十周。在此过程中,笔者以“妇女帮助妇女”的视角,与护工家庭充分互动,为她们排忧解难,践行一种介入式行动主义的理念。在这种介入式的行动主义实践中,笔者逐步从“经验相远”(Experiences Away)的“局外人”(Outsider)转变为“经验相近”(Experiences Near)的“局内人”(Insider)。
本研究涉及的两位女护工为来自安徽农村的亲姐妹,各自丈夫也均在这家医院工作。他们年逾半百,在城市贡献出自己的青壮年劳动力之后未能融入城市,继续留在都市边缘出卖老年的体力,目的是为自己赚得养老积蓄,以及为后代偿还债务、积聚财富。本研究以这两个裙带家庭为个案研究对象,虽然在数量上难以对广大农民工双薪家庭打工现状形成“代表性”和“普遍性”,却直指问题的核心:说明农民工在都市务工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个人在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里的挣扎和困境(2)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
二、文献综述
(一)客工:被边缘化的异乡人
国际学界以“客工”(Guest Workers)指代外籍劳工,这个概念源于“外籍工人”(Foreign Workers)、“移民工人”( Immigrant Workers),他们均指迫于生计而离开祖国、在异国他乡从事体力劳动的雇佣工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这一特殊群体便受到关注,但相关讨论多在法律和经济学领域,聚焦于以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为主的外籍雇佣工人的涌入对于本国经济的发展或者本国工人生活的影响(3)Hall, P. F.,“The Federal Contract Labor Law,”Harvard Law Review,11(8), 1898, pp.525-535; Millis, H. A.,“Some of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Japanese Immigr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4), 1915, pp.787-804.。“客工”一词的正式使用最早见诸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的研究中(4)Windolf, P.,“Strategies of Enterprises in the German Labour Market,”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5(4), 1981, p.351.。20世纪下半叶,战争、冷战和全球化先后构成了德国三波难民与移民潮的动力背景,这缓解了德国战后劳动力匮乏的困境,这些年纪在20岁到40岁的单身男性劳动力预期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返回祖国,然后由新人替代,因而被称为“客工”(5)吴强:《德国难民政策的演变:从客工到欢迎文化》,《文化纵横》2015年第6期。。“客工”这一概念,可以囊括那些漂泊于异国他乡、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弱势打工群体。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劳工接收国。有学者研究了早期在美国开设洗衣店的华裔移民,这些洗衣工几乎不和所在的社区发生任何生意之外的联系,只和自己同种族的人交往,他们也没有体现出人格撕裂感,而是固守中国传统。作为“离家乡绅”,他们是家乡经济最坚定的贡献者和文化传统的捍卫者(6)Paul C. P. Siu., John Kuo Wei Tchen,The Chinese Laundryman: 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New York: NYU Press, 1988.。美国政治学家伊曼纽尔·内斯(Immanuel Ness)系统地调查了在美国的客工情况,认为经济全球化中的美国企业主们为了降低劳动成本和扩大利润,打着填补劳动力短缺的旗号,为低技能工作岗位招揽外籍劳工。在客工们遭受雇主剥削的同时,美国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也减少。由于工人迁移和外来工人计划削弱了输出国和接收国的劳动力组织力量,他呼吁保护美国工人和外来工人的利益(7)Immanuel Ness,Guest Workers and Resistance to U.S. Corporate Despotism,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1.。
基于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城乡之间的鸿沟,中国农民工的异地迁移研究可以与国际学界的“客工”形成对话。离开经济水平相对落后、观念传统较为保守的农村,进入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从事低收入、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工成为中国本土化的“客工”。他们服务于都市建设却难以融入都市,游离于以经济实力和专业素养为标准的社会评价体系和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劳动力奉献结束就收拾行囊返回家乡,在城市没有容身之地,这反映出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工遭到排斥的现状。
(二)代际父权制:家庭权力关系的轴心
家庭最初的定义是“‘共同使用火(厨房)’,也就是一起吃饭的共同体”(8)上野千鹤子:《近代家庭的形成与终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页。。“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基于性别、年龄等确定家庭成员的等级划分及功能分配,共同完成规训、养育以及传递历史等功能,在中国农村家庭中表现为男人是“一家之主”的“男主外、女主内”格局之下的父系继承。在传统的从夫居、父系和父权三重支柱的支撑下,妇女婚后被嵌入到“支配—从属”的父权制主导的家庭权力关系之中(9)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在“三从四德”的传统规约下,被囿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约束之中,并以男孩偏好的生育和提供免费家务劳动的形式在巩固和提升自己的家庭地位的同时对父权制进行维护和再生产。
进行生育以传宗接代是中国农村组建家庭的首要目的。李慧英通过6个省的实证调查发现,中国男孩偏好观念下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父权制的三大要素:一是从夫居的婚居制度,二是父子相承的财产继承制度,三是父子相传的姓氏继承制度。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不仅仅是文化观念,更是强制性的资源分配制度安排(10)李慧英:《男孩偏好与父权制的制度安排——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性别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2期。。除了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婆媳关系也是亚洲社会经典的家庭关系之一。笑冬提出,婆媳关系的实质是父权家族制度中妇女等级制的体现。她剖析了婆媳之间存在辈分、年龄、社会性别的苛刻等级,指出两代妇女之间冲突的实质是竞争和控制养老资源,而且这种竞争和控制方式由男人占统治地位的家族制所默认和普遍化(11)笑冬:《最后一代传统婆婆?》,《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随着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家庭结构的调整,农村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发生了局部变化。蔡玉萍和彭铟旖敏锐地指出,夫妻共同离乡进城从根本上改变了从夫居的实践,家务劳动的参与、都市经济压力以及公共福利资源的排斥等导致男性农民工的妥协(12)蔡玉萍、彭铟旖:《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第11页。。但金一虹认为,“流动瓦解了家庭的父权制”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叙事,她将举家外出或家庭重心在外的家庭称为离乡式流动家庭,指出虽然从理论上看,这种新居方式将对传统父权家庭制度构成直接挑战,但观察发现,在从夫居消失的地方仍然能够生产出男人支配、妇女从属的权力关系以及父权制意识形态——即使妇女家庭成员获得比男人更高的经济收入,在解构和重建的交错过程中,父权制家庭仍然在变动中得以延续(13)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三)流移工人的信息传播技术使用
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深刻影响着各行各业的生活与工作,其中也包括护工这一群体。技术的使用在他们寻求信息及情感支持、维系人际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使用数字媒体技术对于护工们更好地完成护理工作具有积极意义。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通过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面临相似问题的护理人员可以建立起关系纽带,使他们产生归属感,这将对他们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产生积极影响(14)Namkoong, K., et al.,“Creating a Bond Between Caregivers Online: Effect on Caregivers’ Coping Strategies,”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17(2), 2012, pp.125-140.。如网络论坛为护理者们提供了信息支持以及情感支持,能够有效缓解他们的压力,提升他们的幸福感(15)Tanis, M., Das, E., Fortgens-Sillmann, M.,“Who Gives Care to the Caregiver: Effects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 Groups on Wellbeing of People Taking Care of Others?”, Conference Paper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9, pp.1-22.。
与此同时,先进的通信技术也方便了跨国迁移护工联络家庭情感、维系家庭关系。有学者通过研究在我国香港工作的菲佣对手机和因特网的使用,探讨了现代化信息沟通技术与母职建构之间的关系,发现频繁且便利的远程通信使得跨国母亲们能够克服地理隔绝带来的不便,为她们的孩子建构一种母亲的“虚拟在场”。通过这种“虚拟在场”,跨国母亲们从情感和道德两个层面履行其母亲职责,为“母职”一词提供了新的诠释(16)彭铟旎、黄何明雄:《信息沟通技术与母职:一项关于香港菲佣的实证研究》,《社会》2012年第2期。。学者金(Kim)发现,移民妇女们的生活经由数字媒体被中介化,形成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刺激了她们身在贫困家乡的女儿们,这种欲望推动了新一辈妇女移民流动并加入护理行业,却使她们陷入远远低于预期的困顿生活之中。由此他指出,人们对数字媒体的体验及其带来的影响,并不直接由技术本身的强大力量或使用者本人决定,而会被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情况建构和引导(17)Kim, Y., “Digital Media and Intergenerational Migration: Nannies From the Global South,”Communication Review,20(2), 2017, pp.122-141.。
对于中国大陆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对互联网的“工具”性已有清晰的认识,但也仅仅停留在娱乐、简单的人际交流和查找信息的层面,而对于互联网所具有的其他更为强大的功能,如学习业务技能、扩展职业人际圈、表达自身权益等,他们尚无意识或鲜有使用。
农民工夫妻一起到都市打工的共同流动,使得核心小家庭脱离了农村传统大家族的场域,暴露于都市快节奏的现代化进程之中,遭遇生存压力以及新技术、新观念的冲击,这是护工双薪家庭在都市打工的整体语境。在此背景下,新居制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与家庭内部的平权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种平权能否延续和保持?新媒体技术对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嵌入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既有文献中鲜有涉及的问题,本文将展开这方面的研究。
三、双薪护工医院劳动的田野考察
护工是指在医疗机构中由患者或其家属聘用,为患者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人员。2011年和2019年,笔者父亲两次住院,均受到护工兰姐(化名)的照顾。在与护工们朝夕相处的几十天里,笔者意识到病房的方寸之间就是最好的田野场域,很自然地开始近距离与护工接触,不必像人类学家格尔兹那样,要为迟迟不能与巴厘岛的当地村民沟通相处而苦恼(18)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412-530页。。
在泌尿科住院部的护工有四位,均来自安徽,平均年龄58.75岁。笔者重点考察的是来自安徽省庐江县下属某乡村的一对姐妹,姐姐芳姐(化名)生于1961年,妹妹兰姐生于1968年。兰姐1993年来到上海,成为三甲医院的一名护工,熟悉环境后,她先后将姐姐、姐夫和丈夫介绍进了这家医院。1995年姐姐和姐夫来沪,姐姐成为与妹妹同一科室的护工,姐夫老李(化名)由于年龄较大,在手术大楼承担保洁工作。兰姐的丈夫老吴(化名)2007年也来到这家医院,负责护理外国人的病房。就此,两个农民工双薪家庭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跨地迁徙。
(一)护工的护理劳动实践
护工不属于医院的弹性用工类型,由医院指定的第三方公司管理,护理费用每天每人100元,但患者或家属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调整。除了每天照顾固定的病人,护工们要轮流每两个月看护一次其他病情较轻或是受限于经济条件不雇请护工的病人。比起一般的保姆和病陪,护工具备更专业的基本护理、康复护理以及特殊病人的生活护理等知识和技能。在泌尿科,护工们在手术前会告诉患者家属必须购买的护理用品,如袜子、腰带、成人尿不湿等;手术后帮助患者进行术后恢复,如通过观察手术后排出的膀胱冲洗液体颜色来判断病人是否需要进食,测量病人心率、血压,关注伤口是否感染等,从而可以密切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
泌尿科护工们一天的工作从凌晨四时开始。4时30分许就有病人起床,护工们也要及时起身,扶病人如厕、洗漱。5时许起床的病人陆续增多,护工们要迅速帮病人整理床铺。5时30分亮灯,她们须给病患取早餐、辅助用餐,等待医生查房。主治医生查房时,护工们站在整个医护队伍的外围,静静听取主刀医生的观察结论和对病人的要求。查房结束后,她们须根据病人尿袋的颜色以及医嘱随时调整病人的饮食,给予相应护理。接下来的一整天,除了照顾病人,她们还要辅助护士铺床、规整病房的各类医疗器物。
晚餐之后,护工们要帮助病患做就寝准备,包括帮病人洗脚、换袜子乃至擦洗身体。21时30分之后,病人们大多入睡,病房里也逐渐安静下来。在住院部八楼的走廊上,护工们将两张椅子拉开一定距离,把自己预先准备好的一块木板搭在上面,铺好被褥。这张简单的床就是她们忙碌一天后的临时睡床。半夜陆续有病人需要如厕或者喝水,她们须起来搀扶,直到病人不再有任何诉求后才能躺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的睡眠是碎片化的,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二)服务和情感的商品化
2019年笔者父亲再次住院且病情更为严重,主刀医生的评价不甚乐观。整个病房有十张床位,兰姐负责照顾包括笔者父亲在内的四人。在料理完其他三人后,她就坐到笔者父亲的床边,密切观察心率仪器测量的数据变化,并帮父亲解决胃胀问题。除此之外,她还主动给父亲按摩腿脚,促进他的血液循环。面对笔者和其他家属的沉重心情,她利用休息间隙讲述了一个暖心故事:去年一个重病患者在医生妙手回春的手术治疗之后安然无恙出院,现在还和家人出去旅游。她的劝慰信手拈来、不着痕迹,却犹如阳光一样照亮笔者身处住院部灰暗的心境。
国外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从事护理工作的妇女移民容易沦为全球化的受害者,成为承受“关怀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care)、“剥削”(exploitation)和“无存在感”(invisibility)的被压迫的“全球妇女”(global woman);但也有一些护工在与雇主的关系中不一定是被压迫的一方,双方有可能形成一种“拟制亲属”(fictive kinship)的关系,在情感和物质上相互支持,这不仅让被照顾者感觉更舒适,也提高了护理人员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并鼓励他们做出更多超出工作范围的事情(19)Richter, C.,“My American Grandma: Theorizing Fictive Kinship and Affective Visibility in the Lives of Immigrant Elder Care Workers,” Conference Papers,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8.。中国护工们作为家属之外与病患接触最为亲密的照顾者,加之携带着中国农村中“人情社会”和“关系社会”重情谊的传统观念,与国外妇女移民护工相比,在提供身体劳动服务的同时,更易形成情感的卷入。其身体的劳动和情感的付出相互交织,在商品化的过程中也与病患及家属形成了较为亲密的情感连接,所以在中国大陆本土经验中的医院护工区别于国外从事护理工作的作为纯粹“被压迫”商品的妇女移民。
但另一方面,城乡有别的观念也深深镌刻在农村护工们的意识之中。尽管安徽护工姐妹与笔者的交流已经十分热络,但一些言辞之中仍透露出她们的自卑感,如将自己与笔者、上海人以及上海这座城进行了严格的划分,小心翼翼,不敢逾矩,甚至将自身进行矮化和贬低。兰姐甚至说:“和您(笔者)相比,我们就是讨饭的。”
由此,城乡的差别与阶层的差距相互交织,在护工与雇主之间划下不可逾越的鸿沟。病患家属或者患者一般也不会主动与护工亲近或者添加微信,在劳动力与雇工费用的交换过程中,其个人价值以劳动力价值的形式被再现出来。当临时性的雇佣结束,彼此的关系便终结。她们的服务与情感投入难以跨越这一鸿沟与雇主形成更亲密的情感连接,最终不得不回归商品化的尺度衡量和临时性的雇佣关系。
(三)医院:都市中的孤岛
由于需要长时间陪护在病人身边,女护工们的吃穿住行几乎都锁定在医院。对她们来说,医院提供了工作场所并整合了部分家庭功能,从而成为她们在繁华都市中栖身的孤岛。她们囿于其中,为都市的欣欣向荣贡献力量,却鲜有机会离开医院去体验都市生活,遑论融入城市。
具体来看,护工们与都市生活的剥离有两个因素:
一方面,工作要求以及医院的便利条件形成引力。病人对护工们具有极强的依赖性,护工们须随侍在侧以满足其不时之需,不能频繁或者长时间离开医院。医院也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包括一间专供护工们存放日用品的储物间、洗漱间以及免费WiFi,这可以满足她们生活的基本需求。由此,医院成为护工们工作空间和家庭空间的融合空间。
女护工们与丈夫共同饮食等具有家庭仪式感的行为都是在医院完成的。兰姐的丈夫老吴会在用餐时间来到病房,与她一起帮病房的餐车负责人发放餐食,之后两人一起进餐。15分钟简餐结束后,两人会帮忙洗刷餐车。餐车负责人是一个50多岁的上海本地女工,她很乐意接受护工夫妻的帮助,如果有多余出来的饭菜,就会送给他们食用。在这个过程中,病房成为护工夫妻们完成工作、履行家庭职责以及人际交往等多种行为的交汇地。
在午餐结束后的两三个小时内,大多数病人会午休,病房里的需求相对较少,工作空间再次转化为家庭的娱乐和休闲空间。一些护工会用手机或者其他移动设备观看电视剧。芳姐喜欢用平板电脑追剧,她看完会主动和笔者评论剧情。其他护工或午睡,或洗澡、洗衣服,或去附近购买自己所需的日用品,但都不会远离病房太久。对于她们来说,在医院以护理为主的生活几乎成为她们在都市生活的全部。
另一方面,对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都市生活的恐慌形成斥力。即使有空闲时间,护工们也不愿远离医院去接触城市的其他地方。来自农村以及低学历的身份镌刻在她们的自我认知之中,使其在光怪陆离的繁华都市中产生格格不入之感,从而进行与都市的自我隔绝。此外,都市中盛行的消费主义与其勤俭节约的观念和打工赚钱的目标相悖,加剧了这些护工对都市生活的排斥。对于她们来说,城市生活是遥不可及的,她们理应待在医院一隅,尽量减少花销。 如芳姐就说:“就在医院里待着,到外面逛什么呢?像我们文化又不高,往哪逛呢?逛街就要花钱,呵呵,逛街你看到好看的东西总归是要买的。”
护工们为医院的正常运转、为持续老龄化的都市的繁荣发挥着微小却重要的作用。他们秉承着从农村带来的勤劳质朴的观念,客居于城市,将自我封闭于医院这座孤岛上。对于未能经验的其他人生选择的可能性,以及未能体会到的美好物质生活,他们虽有所遗憾,但又任劳任怨,他们是漂泊在都市中的中国本土“客工”。
四、“流移都市”的困境与家庭内部的平权
农民工在被城市平等接纳以及保障自身权益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这使其在家庭内部形成共同对抗生活压力的合力。在家庭外部,护工们面临来自病人、护士、医院以及第三方管理公司等关系的多重张力。在这些层层权力关系共同交织的场域中,护工们作为雇佣关系中的受雇方、医护人员层级中被遮蔽的人群以及管理关系中的被管理人员,成为病房里被迫切需要但维权和议价能力弱势的一方。而在外部重重困境之中,漂泊无依的核心小家庭内部夫妻之间“报团取暖”,打破了传统家族制中男人主导的权力关系模式。
(一)雇佣关系中的弱势群体
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对于中国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以劳动力换取工资的经济过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个使农民工获得“素质”的社会过程(20)Yan H.,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6.。外来农民工常被认为缺乏现代性和主体性,在病房的护理劳动中,缺乏医科专业素养的护工是雇主和医护人员“改造”的对象,他们的言行举止要受到雇主要求以及医院制度的“规训”。
对于病人来说,除了家属之外,护工是与其接触最频繁的人。一方面,他们对护工具有强烈的依赖心理,另一方面,这些依赖和需求会转换成对护工的压力,稍有不慎便成为病人与护工之间的矛盾滋生点。整个医院的运转是一个复杂系统,医疗资源调配、医护人员职责分配等环节都可能出问题,这些会导致病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矛头往往指向护工。
医院负责人:病人要经常换衣服,但有时候医院的供给是不够的,护工拿不到衣服,病人会不满意,相互之间有小矛盾。
如果说病人与护工关系紧张给护工带来的负面情绪,是他们获得护理费应该承受的风险和后果,那么护士带给他们的负担和责难则容易使其感到委屈。护工的工作以病人为中心,但有时也会应护士之请提供帮助,甚至做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护人员以外卖方式就餐,一些护士则支使护工们将餐食从医院外卖架上取回。
兰姐:外卖堆得像山一样,瞪着眼睛都看不清,要一个一个地比对,好多人(护工)在那里翻这样,翻那样,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的苦啊!
虽然护工们几乎24小时在医院上岗,但他们的人事关系并不属于医院。医院曾设隶属于医院的护工管理处,但只负责简单整理一些资料,对护工们护理操作实践的管理是开放式的。2004年上海市卫生局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加强对医疗机构内为住院病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生活护理及简单基础护理的社会人员的管理(21)《关于加强上海市医疗机构护理员、护工管理的通知(修订)》,http://wsjkw.sh.gov.cn/yzgl1/20180815/0012-58805.html,访问时间:2020年9月26日。。由于护工并不属于医院的编制,护工管理处改由第三方护工管理公司设立,对护工群体实施专门化的管理。护工与第三方管理公司签订协议,第三方管理公司负责护工的招聘、培训以及平时工作的监督,护工则须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
事实上,对于这些已经从业20多年的护工们来说,其护理经验是长时间积累形成的,她们后来也并未接受专业部门或者医院工作人员的培训。对于她们来说,第三方管理公司的介入管理并没有让她们感受到任何实际好处,但她们却要多付出高额的管理费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第三方公司管理费从之前的每年一万元上涨到每年三万元,她们也不得不接受并尽数缴纳。其部分原因如芳姐所叹息道的:“这把年纪和能力不在医院做工,还可以在哪里打工攒钱呢?在这毕竟每个月还能挣三千多(元)。”
虽然护工们不接受医院的直接管理,但是医院也有权处罚甚至拒绝护工上岗。根据医院负责人的介绍,若护工们不按照医院规定保持个人卫生的整洁,或损坏医院公共财物,或不能按照要求为病人提供相应护理,将面临教育、再培训、处罚乃至开除的风险。所以护工们认为医院和第三方公司是联合起来欺压她们的共同体。芳姐曾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说:“(医院和第三方管理公司)他们是一伙儿的。”
在与医院和第三方管理公司的三角关系中,护工们作为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一方,一方面要受到另外两方的双重管理,另一方面在交出高价管理费用后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权益保障。对于护工们来说,第三方公司成为剥削他们的新工具。值得注意的是,从2020年开始,医院通过租赁大巴车或者报销火车票的方式送务工人员返乡,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护工们的生活,其所彰显出的“城市主人”对“异乡客人”的馈赠与款待,反而加剧了护工们对城市的异域感。
(二)外部的生存困境与家庭内部的平权
中国传统社会中男人对妇女的支配,基于一套严格的性别分工系统,即男人主导公共领域,而妇女则被隔绝在外而局限在家庭领域。在双薪农民工家庭中,妇女及其丈夫同在都市社会中参与劳动,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改变了这种支配关系。对于这些背井离乡、在陌生城市漂泊的农村夫妻来说,相互慰藉与支持是共同对抗都市劳动力市场重重压力的生存法则。妇女薪资水平的提高以及男人们在都市打工生活中对男性气质的全新阐释,使得在这个迁移的核心小家庭内部男女社会性别关系产生变化。
对于农村打工者来说,背井离乡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差距。在乡村收入微薄,远不能满足他们对于更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即使城市生活体验对护工们来说是苦涩的,但这里有限的收入就家乡的生活水平而言也相对丰厚。所以他们宁愿以在都市苦行僧式的生活,换取在家乡的“体面”。以芳姐夫妻为例,芳姐以简易板床长期驻扎医院,丈夫老李在附近以一千元每月的租金与人合租弹丸之地,两人每月伙食费严格控制在一千元以下,但他们在家乡盖了阔气的“小洋楼”,也帮儿子在老家所在的县城买了房子。
芳姐:“在城市比在家里种田好一点,家里种田没有钱,就搞点吃吃,就是在这里能赚到钱,就是为了钱,才跑到这里来了。因为我们家里没有厂,如果有厂,我们也不会跑出来了,在厂里打打小工,种点田干点活,在老家多美,晚上好好睡一觉。在这里睡眠短一点,睡不能好好睡,你吃饭的时候,人家一叫你,就要走了。”
对于妇女们来说,离开农村进入都市,她们从免费的家务劳动和传统的性别体系中解放出来,进入都市的劳动力交换体系。虽然收入微薄,但她们的劳动力以计时、计件的形式得到偿付,她们以劳动为核心树立女性的自信和能耐,劳动创造的价值以市场上的经济收益体现,提高了自身在核心小家庭中地位。芳姐在女儿三岁时离开家乡,丈夫留在家中承担起“带孩子、种田、养猪、养鸭”的职责,这直接提升了她在家庭中重大事项的决定权,20世纪90年代末家乡安装电话线路,就是她拍板决定的。
芳姐:“那时候农村里时兴通电话嘛,我们家乡是统一拉贷款通电话,我老公在家里,他说家里拉贷款通电话,我说通,拉贷款也通!”
客居都市的过程中,她们的女性气质和母职的履行主要以在外省吃俭用和给农村家庭汇款的方式来实现。除了获得经济报酬,她们在医院打工所积累的经验和人际关系网络也使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同乡亲友进城就医,基于对医院流程的熟悉以及有限人脉,她们可以介绍相熟的医生帮忙,有效提高亲友们看病的效率,这提高了她们在家乡社会网络中的身份地位,使其得到同乡人的肯定和礼遇。兰姐曾带朋友的儿子到医院检查,省掉了其他医院因误诊而要求的十万治病费,她说:“我跟泌尿科的医生很熟的,待了二十多年了,就带着他挂了号,然后找这个医生看了一下。熟人嘛,朝里有人好做官,熟人好办事!”
而对于男人们来说,在农村家庭中“男主外”的男子气概被瓦解:一方面,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城市是由商业精英或者专业精英引领的,他们所建立的城市男子气概让农村男人们产生被边缘化的挫败感;另一方面,这些农村男人在经济收益以及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各方面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均处于被排斥的地位。
老李:“现在没有保险,老家里就是农保,她们(安徽姐妹)没到60岁没有呢,我一个月120块。在上海什么保险钱都没交,现在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一个月几千块,交了保险日子怎么过啊。”
具体来看,在都市医院中,农村男人们的妥协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主动帮助妻子分担工作职责。安徽护工姐妹的丈夫们都会在工作闲暇之余来到病房帮女护工们照料病人。妹夫老吴时常在泌尿科病房,协助妻子给病人泡脚。其二,主动承担家务劳动。由于男人们不需要像护工姐妹一样睡在医院,老李和老吴各自以每月一千元在医院附近合租老式住宅,他们休息的时候会做好饭菜带给仍在医院忙碌的妻子们。其三,女人们掌握了家庭中最重要的财务大权及实际话语权。老李每月薪水4 000元,扣去房租和一些少量的烟酒费,余款如数交给芳姐保管。老吴每月收入约7 000元,扣掉房租和日常打牌娱乐的钱,都交给兰姐保存。而不善表达且不擅使用新媒体的他们很少主动与家乡的家人进行视频或语音通话,妻子们成为利用媒介与其余家人远程沟通的主要亲情维护者,掌握家庭的话语权。可以看到,共同游走于都市社会边缘的经历和压力激发夫妻间相濡以沫的亲密情感,提升了男人们帮扶妻子的责任感,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于妻子的依赖感,妻子发挥起家庭的“主心骨”作用,树立起自己在核心小家庭中的权威。
兰姐:“挣得不多怎么办呢,我在这里我老公他们安心一点……如果我要回家了,他一个人也待不住了,也要回家了。”
护工和其他都市工人一样在经济与符号意义层面都受到结构性压制,在市场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在此背景下,他们对原本以男人权威为基础构建的男性气质进行了重新诠释,将其建立于男人供养和关爱家庭、使家庭成员感到快乐的努力和责任之上(22)蔡玉萍、彭铟旖:《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第118-119页。。他们通过劳动来捍卫自己作为丈夫以及父亲的身份和尊严,而在城市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遭受的挫败感让他们贴近家庭、回归家庭,紧密地与妻子达成“统一战线”,共同应对在都市的压力,在此过程中父系权威被压缩了。其他阶层妇女没有实现的平等景观(23)Orgad, S.,Heading Home: Motherhood, Work, 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Equali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却在最底层的乡村双薪护工家庭工作和生活的逼仄病房空间内局部地实现了。
五、微信沟通与代际父权制的重构
(一)微信沟通、异地母职与家庭情感的维系
农民工们从乡村迁移至都市并非意味着与在农村的家族隔绝,而是借助通信技术维系着与农村的关系纽带。21世纪以前,手机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奢侈品,彼时他们与家庭保持联系非常困难,借由城市和农村的公用电话进行沟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高,但沟通效率却非常低。
芳姐:“那时候农村里又没有电话,要么是发电报,要么是写信。我们家隔壁村庄里有一个人开小店,他们家里通电话,打电话和他约好的,说叫我老公明天中午几点钟来接电话。那时候电话很贵的,三块五毛钱一分钟,很贵的。”
21世纪以来手机逐步普及,尤其是当代信息和传播技术(ICTs)的飞速发展,智能手机以其强大的功能以及大众化的价格迅速普及,到2021年4月我国手机上网用户数达到13.63亿(24)工信部数据,《2021年一季度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https://www.miit.gov.cn/jgsj/yxj/xxfb/art/2021/art_162cf3f6f9314d49a6b736ac6cb16326.html,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日。。廉价且便捷高效的语音和视频通讯成为农民工们与家庭沟通的首选,这也为农民工异地履行母职和父职、联络家庭情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这个过程中,妇女们表现出较强的对新媒体技术的学习能力和利用手机进行沟通的能力,在维系亲情中占据绝对优势。相比传统的乡村家庭,丈夫乃是家庭要事的裁定人,但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的普及,沟通方式悄然发生变化。笔者在医院的观察发现,老李并不擅长用新媒体,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处于被动的收发信息状态。而芳姐灵活使用平板电脑或是智能手机,熟练地用微信视频与家人交流,掌握了远程沟通的唯一通道,借由媒体近用权进一步巩固了家庭话语的权力。
一旦有空闲时段,女护工们就会拿起手机与子女或其他亲属联络,其中微信视频是护工们与异地的家人进行联络的主要路径。晚饭后陪病人散完步,到病人睡觉之前会有短暂的休整时间,她们一般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与家人视频通话。儿子是芳姐最频繁的联系人,每周两到三次。每当儿子一家出现在镜头前,芳姐便会笑逐颜开,双方彼此寒暄期间,孙子会在儿子和儿媳的引导下,亲昵地向奶奶问候。不仅如此,微信还成为护工夫妻之间以及同乡护工之间交流的重要工具。但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以及追求沟通的效率,他们很少通过文字交流,而是直接发送语音或者语音实时通话。除此以外,借助微信的便捷支付功能,护工们与异地家人之间越来越多的金钱来往转移至微信。
从微信沟通的内容与时间分配来看,其最大功用在于:其一是协助了女护工异地履行母职,因为不能亲自帮助儿子育儿,又担心一年才回老家与子孙团聚而疏离了母子和祖孙情感,于是定期和老家县城的小家庭保持密切的微信视频交流。其二是协助完成家庭内部事务的裁决,两个家庭之间的重大决策可以经由微信沟通来互相知会以及形成共商共量的虚拟空间。其三是,维系了在都市的陌生化场景中,夫妻护工和乡里乡亲的同舟共济和情感体验的共享。其四,通过微信转账,微信卷入经济层面,对护工们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更深刻的嵌入。
微信由此成为护工们(主要是女护工)在都市中维系原有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表达情感的载体。微信不仅将两个家庭结合起来,同时也将城乡接合起来,经由此桥梁,符号意义、情感以及资金形成源源不断地传播流动。最重要的是,妇女作为新媒体技术的掌握者,成为这个过程的“把关人”。
(二)代际父权制的重构
虽然医院护工夫妻共同外出打工带来的新居制,实现了妇女在小家庭内部的自主和家庭关系的平等,但这是都市打工阶段性的应对方略。事实上,这种“共患难”的经历所带来的双薪农民工家庭平权,是为繁荣其家族后代的生活而服务的。也就是说,局部小家庭内部的平权实际上隐性地强化了在更大范围内以父系继承为主导的代际父权制。
这种代际父权制体现于两个方面:
其一,父系继承作为代际父权制的核心,导致“重男轻女”观念仍在延续。虽然已经脱离保守的传统观念主导的农村,但父系继承的宗族观衍生出的偏好男孩的生育观根植于护工们的内心。一方面女护工们自身曾是“重男轻女”思想的受害者,在其成长过程中家庭资源集中于同辈中的兄弟。芳姐小学没毕业,常遗憾于自己没能多读些书:
我们那个时候重男轻女……农村里是男孩子念书,女孩子是人家的人,不能念书,念书念坏了,呵呵呵……我和我妈说,你就偏心,应该给我念几年书,让他们少念几年。
但另一方面,这一流弊并未在她们这一代消失,仍以隐蔽的方式存在着。芳姐平时娱乐或者与家人视频的平板电脑是女儿所赠礼物,但它的使用多集中在与儿子家庭进行微信视频对话,孙子的成长乃是其关注的核心,与外孙的视频通话频次明显少于孙子。她平时也很少谈论女儿家的事情,更不会为已婚女儿支付任何费用,她认为“女儿嫁出去了,就不用再操心了”。相比之下,她会把打工的大部分收入用于儿子的房贷。更为吊诡的是,由于不能亲自照顾孙子,兰姐夫妻要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每个月支付参与照顾的亲家母三千元,因为“儿子是我家的,孙子也是跟老公的姓”。这种方式将看护孙子划归为奶奶的天职,而外婆与外孙的血亲关系被此种变相“雇佣”的关系取代,母系一方被阻隔在家族传承之外,维护着父系继承的权威性。
其二,财产继承规则作为代际父权制的外在显著要求,为双薪护工家庭带来巨大压力。农村护工们以传宗接代和保障子嗣的良好生活为己任,而延续宗族以缔结婚姻为前提,所以中国社会的高房价、高彩礼以及婚后的高生活压力,经由财产继承链条反向传递给已经步入老年的护工们,他们身为父母的哺育和供养职责并不止于儿子们的成年或者自己的退休年龄。以芳姐夫妻为例,虽然老李已年过花甲,芳姐也年逾半百,儿子已经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但由于儿子在县城的房贷还未偿清,儿媳全职在家照顾孩子,所以在体力可支的岁月,他们仍要帮助儿子还贷款、支持儿子哺育孙子。但对于芳姐自身而言,她为能够帮助儿子在县城买房安家、并继续支持儿子养育孙子感到满意和骄傲。而这种老年时代继续制造财富、为家族传承做贡献的现象在农村也以不同方式成为普遍现象:
芳姐:“农村里基本上都是老的在外面打工,如果实在不能,就老的在家带小孩。基本上就是老头和老太太在外面打工。”
此外,女儿们被排除在财产继承规则之外,但平等观念的局部传播使得她们要越来越多地担负实际的赡养责任和义务,这进一步加剧了代际父权制。对于安徽姐妹来说,她们婚嫁时虽然没有得到与兄弟们同等的财产支持,但对于目前尚在的老母亲,她们要承担相同的赡养费用。与此同时,身处于这种不平等的格局而认为理所应当,而对此境况自愿接受的态度也出现在其女儿身上。芳姐自知对女儿没有太多投入,在养老方面“全凭她(自觉)”,但芳姐十年前第一部手机和现在使用的平板电脑都是女儿买的,对母亲的关怀和物质支持远超儿子。由此,子嗣财产继承制被当代“懂事的”女儿们持续巩固着。
六、结 语
由医院双薪护工家庭的劳动与生存情境可见,他们在都市里处于客居状态:他们从远方来,随时可能离开;他们在经济上是城市建设的贡献者,在结构上是城市共同体秩序的维护者,但大部分人最终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他们是都市里或远或近的“陌生人”(25)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1-348页。。农村双薪夫妻通过在医院“有做有得,不做不得”的计件式勤苦劳作,仅仅为了获取短期经济利益。他们的根基和过往都不在都市,而医院护工的身份并没有让他们忘却乡土,昔日乡村的血缘、地缘关系仍然是流动到都市之后的重要社交纽带。无论在都市面临何等艰辛、压抑与张力,他们都有一套自我释怀的生存逻辑鼓舞彼此坚持下去:他们以努力攒钱、供养子孙为坚定信念,至于护工生涯中是否有机会改变社会地位,或者是未来与都市产生何种关联,他们不抱太多希望。他们身在都市,但一切组织生活的原则都以过去乡村的惯习为基础,家乡亲人和乡村生活的烙印是支撑护工家庭在都市困难重重时刻的坚强源泉,并最终召唤他们回到农村老家。
每一位病人的出院意味着这段雇佣关系的终止,病人们的生活回归正轨,护工们的相应职责就此完成而被遗忘;而对于医生护士来说,护工是辅助他们工作的“工具性存在”,对其生活和个人感受则鲜有关注。他们像在美国的洗衣工一样,以赚钱为目的客居异乡,将自己囿于一隅,几乎不与工作领域以外其他地方和人群发生联系,因为他们所客居的社会不是他们借以获得自身认同的社会和空间。城市仅仅是他们挣钱养家的地方,而真正的家远在农村(26)瑞雪·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流动到都市的护工家庭运用微信联络化解了离乡背井的远程乡思和异地履行母职、父职的困境,攒钱回乡的理念是他们长期苦苦在都市打工挣扎的精神支柱,他们主动迎合了当下中国阶段性存在的城乡鸿沟结构性体系,营造了市场经济转型期都市经济的繁荣与整体生活品质的提升,他们是中国大陆语境下都市中的“客工”。而从家庭内部来看,从乡村到都市的农村夫妻迁徙,局部改变了小家庭的传统居住和沟通方式、收入分配以及权力结构,进而引起家庭情感、代际父权制的局部变化,这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一代进城务工者的生活情境。
一方面,农村男人的核心权力在迁移到都市之后面临挑战,男人们面临经济资源和社会保障资源匮乏的现实问题,于是配合妻子去共同劳动、存钱以履行父职,以扶持家乡县城的另一个小家庭的生存。笔者聚焦研究的两个医院夫妻护工家庭,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奋斗在都市三甲医院的第一线,双方分担家务,并对儿孙家庭给予支持,妇女们掌握财权,在小家庭内部获得丈夫的支持和帮助,并在大家族中的权威也逐渐增加。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村劳动力大规模向都市的流动,的确瓦解了农村建立在辈分、年龄、社会性别等轴心层面的原生家庭传统权力结构的最后阵营。
另一方面,代际父权制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在新的家庭模式中重构,并以更隐匿的方式继续存在,给妇女们带来新的制约。通过微信沟通,医院农村女护工们进行家庭情感的维护与母职的履行。微信将流移于城市中、实现内部平权的核心小家庭重新嵌合到农村的大家族之中,使得农村传统父系继承观念继续宰制小家庭。女护工们对父系家庭中儿子的支持以及孙子的青睐,与具有同样血亲关系的女儿家庭的去经济化支持形成鲜明对比,女护工自身承受着新型代际父权制的压迫,履行赡养义务的同时得不到财产继承权利,同时将这种压迫继续传递给自己的女儿们。妇女们难以摆脱传统代际父权制烙印于家庭传承的陈旧父系继承以及财产继承观念,并通过身体力行再生产新型代际父权制,认为其理所当然而不自知,这是女护工劳苦一生的沉重压力。
在流动农民工家庭的新居模式下,妇女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已经不是完全取决于妇女的生育,而是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以及夫妻共同进城务工而具有的双薪条件和养老资源的自我储备。但局部的核心小家庭的内部平权,仍然没有弃绝维护更大范围内的整个农村家族的传统代际父权制的陈旧理念,甚至为其服务,成为其新型且隐性的存在。许多老人曾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一旦失去体力和年龄优势而无力进入城市市场经济体系,随即处于失去家庭权威的边缘,只能仰赖看护孙辈来获得子女的物质帮助。
由此,男女平权的愿景出现在进城务工的双薪护工家庭,都市情境中妇女的劳动与男人的身份压力共同导致男性妥协。但需要注意的是,“男性气质的妥协为移民家庭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具体的男性气质的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27)蔡玉萍、彭铟旖:《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第179页。。也就是说,这种平权是语境化的、功利性的、暂时性的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