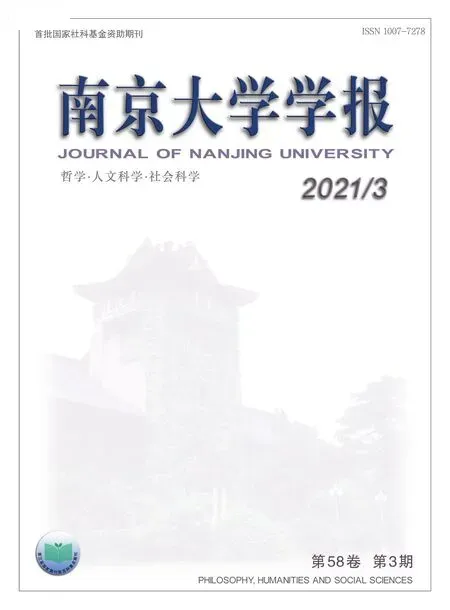论“代理权滥用法理”之滥用
王 浩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1600)
一、绪 论
关于现行法上的“代理权滥用”,有学者总结为四种,即“职责违反型”“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型”“自己缔约型”“双方代理型”。(1)参见胡东海:《论职责违反型代理权滥用》,《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后三种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禁止(第154条、第168条),而对于“职责违反型”,《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只是规定代理人应就本人的损害承担责任。所谓“损害”,似专指本人因不得不承受代理行为之效果而产生的损害。(2)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1页。换言之,《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暗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即违反职责的代理行为仍可对本人有效。(3)参见徐涤宇:《代理制度如何贯彻私法自治》,《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近来越发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违反职责的代理行为仍属有权代理,仅在相对人对代理人违反职责非善意时,代理行为才作为“无权代理”而效力待定,由本人决定是否追认代理效果。(4)参见汪渊智:《代理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0页;朱庆育:《民法总论》,第351-352页;谢鸿飞:《代理部分立法的基本理念和重要制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吴香香:《滥用代理权所订契约之效力》,《中德私法研究》第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 245页;胡东海:《论职责违反型代理权滥用》,《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殷秋实:《论代理人与相对人的恶意串通》,《法商研究》2020年第3期;迟颖:《德国法上的禁止代理权滥用理论及其对我国代理法的启示》,《河北法学》2020年第11期等。可是,即便代理行为有转为无权代理之可能,是否就当然适用《民法典》第171条之规定,不无疑问。该条所针对的,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的情形,此与代理人单纯“违反职责”有无差异,需先予澄清。
实际上,所谓“职责违反型的代理权滥用”究系何种情形,本身就不乏争议。关于“代理人不履行职责”,传统见解认为是指代理人在处理受托事务时未尽善管义务或忠实义务。(5)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 年,第212 页;江帆:《代理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年,第 87 页。近来有学者认为,如下事例也应适用代理权滥用法理:委托人指示受托人以不低于10万元的价格出卖二手车,受托人却以低于10万元的价格出售了该车。(6)参见胡东海:《论职责违反型代理权滥用》,《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迟颖:《德国法上的禁止代理权滥用理论及其对我国代理法的启示》,《河北法学》2020年第11期。此外,无论根据《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还是传统见解,代理权滥用的典型特征就是代理行为“损害或违背本人的利益”。与之伴随的一个问题便是,代理权滥用之成立,究系只要客观上有害于本人即可,抑或代理人主观上还须有损害之“故意”。过往的文献中,有将代理权滥用等同于代理人“故意”损害本人利益的(7)参见佟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有将代理权滥用理解为代理人之“过失”的。(8)参见梁慧星:《读条文 学民法》,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第43页。近来则有学者提出,只要客观上代理行为不当,即构成代理权滥用。(9)参见吴香香:《滥用代理权所订契约之效力》,《中德私法研究》第15卷,第 247页;胡东海:《论职责违反型代理权滥用》,《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另外,还有学者一度主张“代理人是否具备主观过错在所不问”(10)参见迟颖:《意定代理授权行为无因性解析》,《法学》2017年第1期。,后又改称代理人有主观故意是代理权滥用的构成要件,与此同时却认为“代理权的滥用不以客观上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为必要”。(11)参见迟颖:《德国法上的禁止代理权滥用理论及其对我国代理法的启示》,《河北法学》2020年第11期。
综上,关于职责违反型的代理权滥用,虽然现行法上不无规定,但解释论上仍有诸多不明,学说中则不乏混乱和矛盾,若不加以逐一澄清,所谓的代理权滥用法理恐有被滥用之危险。
二、代理权滥用还是越权代理?
视违反指示或限制之代理为代理权滥用而非越权代理者,主要是受德国法的影响。德国法的文献中,与之相应的名言即是,“内部原因关系决定代理人在法律上被允许做什么,代理权决定代理人在法律上有能力做什么”(12)参见 von Tuhr, Allgemeine Teil, Bd. II/2, München u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1918, S. 385.。但必须指出,内部指示之所以无关代理权范围,皆因德国法上存在所谓“不可限制的代理权”以及“代理权外部授予”这两种特殊制度。而我国代理法上是否也存在类似制度,不无疑问。
(一)不可限制的代理权?
1.代理权不可限制说的形成
众所周知,代理权抽象性理论的形成归功于德国学者Laband。他当时主要强调的,正是委托等内部关系与代理权授予之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代理权范围的不可限性。Laband认为:从《德国商法典》的规定看,代理权的范围可以比本人的委托或指示来得大。(13)这些规定基本为现行德国商法典及公司法所继承,具体内容参见《德国商法典》第50、54、56、126、151、495、531条,《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7条,《德国股份法》第82条。比如董事、经理、合伙人、清算人等的代理权范围由法律统一规定,本人无法限制;即使施加了限制,也不能对抗哪怕是知晓该限制的第三人,除非第三人与违背义务的董事、经理、合伙人等故意缔结有损本人利益的合同。(14)参见Laband, “Die Stellvertretung bei dem Abschlußvon Rechtsgeschäften nach dem allgem. Deutsch. Handelsgesetzbuch,”ZHR 10,S. 223f.又比如船舶管理人、船长的代理权范围也由法律统一规定,本人虽可施加限制,但该限制只能对抗知晓该限制的第三人,且本人需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该限制。还比如商业代办权人、店员等的代理权范围虽来自于当事人的合意,但法律对这些权限的范围作出了推定,故当这些代理人在法律推定的范围内与第三人缔约时,本人不能以内部的限制对抗第三人,除非本人可以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些限制。(15)参见Laband, “Die Stellvertretung bei dem Abschlußvon Rechtsgeschäften nach dem allgem. Deutsch. Handelsgesetzbuch,”ZHR 10,SS. 220f,221f, 224.
Laband总结到,代理权已经从委任也即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中脱离了出来,成了一种独立的交易资格(Verkehrslegitimation),从而无论是促进还是侵害了本人的实质利益,代理人都被赋予了得向第三人行使本人权利之权限。 Laband并为此举了一例:A授予B向C购买马匹的代理权,同时委托中指定买白色马匹,花费不得超过100帝国塔勒。后B从C处以200帝国塔勒购入了一匹黑马,但C仍获得了基于买卖合同的对A的诉权,而A只能基于委托合同要求B损害赔偿。Laband认为,一种“形式化的代理权限”正在现行法中生成,因为“对于今日之经济生活中的交易而言,必须用各种形式化的标准去取代有关实质性权限的调查,资格(Legitimation)必须取代权限(Berechtigung)”。(16)参见Laband, “Die Stellvertretung bei dem Abschlußvon Rechtsgeschäften nach dem allgem. Deutsch. Handelsgesetzbuch,”ZHR 10, SS.230-241.
如果代理权范围真有Laband所谓之不可限性,那么确实可说代理行为即使违反了委托时的特定指示也仍属有权代理,至多只是代理权滥用。然而如上所示,此种代理权不可限性理论的产生,源于德国商法上有关某些代理权范围之特别规定。事实上,对于那些法律未特别规定范围之代理权,Laband自己也说代理权范围只能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依据通常的解释规则进行认定,代理权范围存有争议时仍须由第三人举证证明代理人的行为确实在权限范围内。(17)参见Laband, “Die Stellvertretung bei dem Abschlußvon Rechtsgeschäften nach dem allgem. Deutsch. Handelsgesetzbuch,” ZHR 10,S.224.那么,我国法上是否也存在关于类似的“不可限制之代理权”的规定?
2.权利外观说的优越性
近来确有一些学者试图将《民法典》第61条第3款、第170条第2款、第504条[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0条]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第37条(对合伙人的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也表述为有关不可限制之代理权的规定。(18)参见朱广新:《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徐深澄:《〈民法总则〉职务代理规则的体系化阐释》,《法学家》2019年第2期;杨秋宇:《融贯民商:职务代理的构造逻辑与规范表达》,《法律科学》2020年第1期;尹飞:《体系化视角下的意定代理权来源》,《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刘骏:《再论意定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交大法学》2020年第2期;迟颖:《德国法上的禁止代理权滥用理论及其对我国代理法的启示》,《河北法学》2020年第11期;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1207页。但是,这些学者似乎忽视了一点,即德国法(特别是《德国商法典》第50条、第126条、《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7条、《德国股份法》第82条)要么规定对代表权等的限制对任何第三人均不生效力,要么直接规定代表权等不得受限。而我国《民法典》《合伙企业法》不仅从未规定过代表权等不得受限,且明确规定对代表权等的限制仅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民法典》第504条更是明确写着: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多数学者认为,该规定的原理基础即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外观法理(所谓“表见代表”)。(19)参见温世扬、何平:《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与“表见代表”规则》,《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李建华、许中缘:《表见代表及其适用》,《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张学文:《董事越权代表公司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石一峰:《商事表见代表责任的类型与适用》,《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杨代雄:《公司为他人担保的效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朱庆育:《民法总论》,第473页。《民法典》第61条第3款也多被认为与原《合同法》第50条一脉相承,同样体现了权利外观法理。(20)参见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上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第261页。《民法典》第170条第2款则多被视作《民法典》第172条(表见代理)的特殊规定。(21)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下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第765页;耿林:《〈民法总则〉关于“代理”规定的释评》,《法律适用》2017年第9期;聂卫锋:《职权代理的规范理路与法律表达——〈民法总则〉第170条评析》,《北方法学》2018年第2期;冉克平:《论商事职务代理及其体系构造》,《法商研究》2021年第1期。
实际上,关于德国商法中的上述规定历来就有不同解读,Laband的“代理权抽象性(不可限性)”说只是其中之一。因 “表见代理权”(Scheinvollmacht)理论而扬名的德国学者Seeler在《代理权和表见代理权》一文中就指出:Laband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违反义务的代理行为也能对本人产生效力,但Laband将此归因于代理权的授予则有悖于事实。 实际这与代理权问题完全无关,而是涉及那些基于外部事实认为代理权存在的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问题。(22)参见 Seeler,“Vollmacht und Scheinvollmacht,” ArchBürgR 28,SS.2,9f.Seeler认为,正是因为表见代理的概念在当时尚未明确,才有了代理权抽象性的构想,于是那些本应属于表见代理范畴的问题都被有权代理教条吸收了。故不同于Laband将不可对抗第三人的代办权、店员权理解为无关委任的“真正代理权”,Seeler将有关代办权、店员权的《德国商法典》第54条、第56条视为针对权限范围的特别“表见代理”规定。(23)参见Seeler,“Vollmacht und Scheinvollmacht,” ArchBürgR 28,SS.9,45ff.这一认识如今看来似乎是更有力的。(24)参见卡纳里斯:《德国商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388页、第398页。
就代表权等概括性的商事代理权而言,是否有必要像德国商法那样规定内部限制对外部任何第三人均无效,其实也不无疑问。最近有学者提出,德国法上的经理权规则真正体现了代理权之抽象性,并非表见代理规则可涵盖,因为第三人即使知晓经理权存在内部限制,只要不与代理人串通损害本人之利益,就仍可主张代理之有效性。(25)参见刘骏:《再论意定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交大法学》2020年第2期;刘文科:《商事代理法律制度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205-208页。但是,如果法律对经理权范围予以特别规定的现实意义仅在于“满足商事交易快捷、安全的需求,且在商事交易中并不允许相对人探究内部的基础关系”(26)参见刘骏:《再论意定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交大法学》2020年第2期。,那么为何“知晓内部限制”的第三人仍值得保护?实际上,由于如今的德国学说和审判实践对于代理权滥用,往往不问代理人是否有加害故意(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故超越内部限制行使经理权、代表权的行为今天大多可构成代理权滥用,从而那些单纯知晓内部限制的第三人未必可主张代理之有效性。当然,在特定情形下,知晓内部限制的相对人仍可能值得保护。比如,X的代表人A从事一定金额以上的交易需得到X的董事会批准,交易相对人Y对此知情,但是Y基于A所持的董事会决议等认为A已经获得了批准。不过,此时Y需被保护的已不是有关代表权不受限制的信赖,而是有关A得到了个别授权的信赖,仍属于表见代理的一般情形。总之,正如德国学者Beutien所指出的,经理权等商事代理权的特殊性仅在于法律对权限范围作出了强制划一的规定,目的还在于保护和加速商事交易;而在此之上强调代理权抽象性的特殊商事规定并不存在,而且也无必要,因为商事登记公示和民法典上一般的权利外观规定已足以照顾到须被强化的交易保护。(27)参见Beutien, “Gilt im Stellvertretungsrecht ein Abstraktionsprinzip?” 50 Jahre BGH: Festgabe aus der Wissenschaft, Bd. I, München: C.H. Beck, 2000, S.102f.
必须指出,就代理人违背特定指示或超越内部限制的事例而言,表见代理制度的确已足够保护代理相对人,无需上升到代理权的抽象性。Laband之所以强调代理权的抽象性(不可限性),如上所示,无非是想让代理相对人免去针对内部关系的实质审查。而表见代理制度的宗旨正在于:只要本人的言行举止态度(包括将行为人置于某种地位、给予某种头衔)充分表明行为人有代理权(即“代理权通知”),那么即便相对人未调查实际的内部关系,本人也不能以实际的内部关系对抗相对人。换言之,形式化的“代理权通知”取代了代理权,成为建构双方法律关系的基础,相对人由此免去了针对内部关系的实质审查。(28)参见王浩:《“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重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另外,有学者认为,从代理权抽象性出发建构相对人保护的机制,比之表见代理更有助于相对人保护,理由是表见代理的成立需相对人证明其有合理信赖(29)参见迟颖:《意定代理授权行为无因性解析》,《法学》2017年第1期;尹田:《论代理制度的独立性》,《北方法学》2010 年第 5 期。,但此种认识显然不当。表见代理规定实际上有一般和特别之分,在相对人保护要件和证明责任分配这些问题上不能一概而论。就表见代理的一般情形(涉及代理人是否就某一事项得到了特别授权)而言,的确应由相对人证明其有合理信赖的评价根据事实。(30)参见王浩:《“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重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但就《民法典》第61条第3款、第170条第2款、第504条而言,作为表见代理的特别情形,应由否定代理效果的本人证明权限逾越以及相对人非善意。(31)参见冉克平:《论商事职务代理及其体系构造》,《法商研究》2021年第1期。因为此处的代理人是得到“概括授权”的代表人或“高管”,而权限受限则是例外。相反,若将所有超越内部限制的代理均原则上视作有权代理,则会导致一般情形也被“特别”对待,从而不当地减轻相对人的证明义务。譬如,相对人知晓章程不允许代表人从事一定金额以上之交易的场合,如相对人与代表人缔结了该金额以上的交易并主张该交易有效的,则相对人本应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该代表人就对外担保这一事项被特别授予了代理权。如上所述,此种事例仍属于表见代理的一般情形。
(二)代理权的外部授予?
即使无代理权的授予,委托人委托时也可能对受托人设定特定的行为义务,比如要求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出售委托人的二手车时定价不得低于10万元。若委托的同时又有代理权的授予,则此类义务设定是否构成代理权的范围,属于授权行为的解释问题。按本人的意思,其“允许”代理人做的,才是代理人“能够”做的,也即委托时的义务设定自然应构成代理权的范围。但依据《民法典》第142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应从“相对人的角度(相对人如何理解)”来解释。所以,授权行为的“相对人”是谁、其是否知或应知本人为代理人设定了行为义务,对于代理权范围的认定至关重要。
《德国民法典》第167条规定:“意定代理权的授予,以向……代理应对之发生的相对人的表示为之。”(32)本文中《德国民法典》的条文中文翻译均参考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据此,代理权的授予可通过本人向代理交易的相对人所作之表示而实现,此即所谓的“代理权外部授予”。此种授权行为的相对人是代理交易的相对人。由于身处外部的代理相对人往往无从知晓本人内部的义务设定,故依据上述解释规则,此种义务设定就与代理权范围无关了;即使代理人违背了特定指示,代理行为始终还是权限内的行为。此外,《德国民法典》第170条规定:“意定代理权以向相对人做出的意思表示授予的,意定代理权对该相对人保持有效,直至授权人将意定代理权的消灭通知相对人。”据此,即使内部关系已经消灭,只要本人未向相对人通知代理权消灭,代理行为就仍属有权代理。可见对于德国民法而言,正是因为有了“代理权外部授予”,自然而然代理权就有了隔绝于内部关系的所谓“抽象性”。有德国学者甚至认为,Laband的代理权抽象性理论正是以外部授予的代理权为基础形成的。(33)参见弗卢梅:《法律行为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006页。而我国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代理权范围一般具有抽象性,也恰因他们总是以“代理权外部授予”作为立论的出发点。(34)参见迟颖:《意定代理授权行为无因性解析》,《法学》2017年第1期。
然而在我国,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还是《民法典》,均只规定了“代理权的内部授予”。就内部授权而言,授权行为的“相对人”就是代理人,而代理人作为受托人自然应当知晓本人的义务设定。所以,依据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确定代理权范围时,本人的意思反而具有决定意义,本人所做的具体指示通常就构成代理权范围的限制。难怪弗卢梅说,内部授权之下通常不会出现代理人对外“能够做的”与本人“允许(代理人)做的”之间的偏离。(35)参见弗卢梅:《法律行为论》,第1005页。
或许有人会说,我国民法虽无明文,但依私人自治原则,似不禁止代理权的外部授予。然而,与德国民法将代理权授予明文规定为本人的“单方行为”不同,我国民法传统上将代理权授予看作一种类似于委托合同的“双方行为”。比如意定代理被称为“委托代理”、委托代理又被表述为“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民法典》第163条第2款)、有关复代理的规定(《民法典》第169条)则完全复制了合同编中有关转委托的规定(《民法典》第923条)等,皆为明证。之所以代理权授予是“合同”,也即代理权须得到代理人之同意方能产生,皆因我国民法中的代理权实际仍是代理人基于其意志发生变动的主观地位,而非本人单方面的“资格认证”。《民法典》第173条第2项(代理权因代理人辞去委托而消灭)其实就表明了这一点。总之,诸如本人与代理相对人之间的行为亦可发生代理权这样的构想在我国民法上似无立锥之地。另外,本人关于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所作之表示,对绝大多数代理交易的相对人而言,与其说是一种设权行为性质的“意思表示”,毋宁解读作“已经授予了行为人某种代理权”、也即“观念通知”更加自然。当然,基于此种通知而信赖代理权存在的相对人同样需被保护,不过如前所述,这一任务已交由表见代理制度来完成了。在此意义上,我国恐怕也无必要引入代理权外部授予的概念。
(三)小结
的确,我国《民法典》仿照德国民法将“代理”单独置于总则之中,且在很多人看来,这意味着委托与代理权授予的分离。(36)参见尹田:《论代理制度的独立性》,《北方法学》2010年第5期;陈华彬:《论意定代理权的授予行为》,《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2期;梁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238页;汪渊智:《代理法论》,第83页。但是,在代理权的性质认识、代理权授予行为的性质认识等方面,我国显然异于德国,也因此,在代理的具体问题上不能一味依循德国法的语境去构建规则。就违反内部指示之代理而言,由于我国法从未承认、也无必要承认“代理权不可限性”和“外部授权”,故应属越权代理的范畴。对于越权代理,依据表见代理制度即可保护代理相对人,无须言及代理权滥用法理。
三、客观滥用还是主观滥用?
需适用代理权滥用法理的,其实是如下情形:代理人虽未违背内部指示或超越内部限制,但代理行为损害了本人的利益。需进一步明确的是,此种代理权滥用之成立,应否需代理人主观上故意(所谓“主观滥用”),抑或代理行为客观上有害于本人即可(所谓“客观滥用”)?譬如,A委托B全权出卖甲房,并及时根据行情调整价格;随后B一直未关注此事,半年后房价上涨,但B并未及时调整价格,导致甲房标价比市场价低了45万,C见此报价便马上与B缔约购入了甲房。若持客观滥用之说,则A尚有主张代理权滥用以对抗C之可能。若持主观滥用之说,则无论C是否知晓报价有误,A都要接受代理效果。
(一)不同立场
我国学者近来之所以提倡客观滥用,还是因为德国法的影响。德国学者认为代理权滥用事关相对人的信赖保护,故重要的是相对人的主观样态,而非代理人的主观意图。(37)参见弗卢梅:《法律行为论》,第944页;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835页;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730页;布洛克斯、瓦尔克: 《德国民法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3 -244页等。德国联邦法院如今也越发倾向于客观滥用。譬如在2006年的一个判决中,德国联邦法院就明确提出,代理权滥用无需代理人有滥用之故意。(38)参见BGH NJW 2006, 2776. 另参见Krebs, in:MünchKommHGB,München: C. H. Beck, 2021, Vor § 48 Rn. 75;Schmidt,in:MünchKommHGB,München: C. H. Beck, 2021, § 126 Rn. 21;Stephan / Tieves, in:MünchKommGmbHG,München: C.H. Beck, 2019, § 37, Rn.181;Spindler, in:MünchKommAktG,München: C. H.Beck, 2019, § 82, Rn. 64.
不过应看到,德国学者所谓的代理权滥用包括了超越内部限制或违背指示的代理。上述联邦法院的判决所涉及的,正是公司董事行使代表权时逾越了早前内部决议对代表权所施加的限制。如果从权利外观法理来看,那么这类事例中代理人有着何种主观样态本就不重要,甚至代理行为客观上是否有害于本人也不重要。而在与德国民法渊源颇深的日本,代理权滥用理论基本都是在“主观滥用”的语境下展开的,审判实践中的代理权滥用案件几乎也只涉及主观滥用。(39)参见平山也寸志:《代理権濫用の研究》,东京:信山社,2018年,第196页。至于法人代表超越内部限制之类的事例,在日本往往被视作“越权代理”或“代理权部分消灭后的代理”;针对此种事例的日本一般法人法、公司法中的善意第三人保护规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也被视作表见代理的特别规定。(40)参见佐久間毅:《民法の基礎 1》,东京:有斐阁,2018年,第364页。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修订的《日本民法典》第107条明确将代理权滥用限定在了“主观滥用”上。该条规定:“代理人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之目的而于代理权范围内所作之行为,相对人已知或可知其目的时,其行为,视为无代理权之人所作之行为。”(41)本文中《日本民法典》的条文中文翻译均参考王融擎编译:《日本民法:条文与判例》上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
(二)“主观滥用”的规制必要性
我国的情况似与日本更相像。首先,就超越限制或违背指示的代理而言,如前所述,在我国也应归入越权代理的范畴,不适用代理权滥用法理。其次,如果只是因代理人实施的行为有害于本人,本人就可在相对人非善意时拒绝承受代理效果,那么实在过于优待本人了。因为相对人与本人直接缔约时,本人并无此待遇。例如某人自身疏于关注市价导致自己以低价出售了房屋的,他当然无法借口自己的过失来否定售房合同的效力。既然如此,为何在某人通过代理人缔约时,却允许他借口代理人的过失来否定售房合同的效力?代理制度只是让代理人的行为可以像本人自己的行为一样归属于本人,而不是让本人在交易中变得更有利。换言之,无论直接交易的相对人还是代理交易的相对人,均应有同等的获利机会;只要在契约自由的框架内,相对人就可以利用本人一方(包括代理人)的过失或决策失误,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否则,相对人更愿选择与本人直接交易,而极力回避代理交易。总之,代理制度的存在本身即表明“过失乃至完全无过失 的代理权‘滥用’始终属于生活经验之范畴,对此本人只能予以忍受”(42)参见Leptien,in: Soergel BGB,Stuttgart: Kohlhammer, 1999, § 177 Rn. 17.。
代理法需规制的,其实只有代理人故意损害本人利益的场合。此种场合下,即便允许本人拒绝代理效果,也未让其比之直接交易获得更多优待。因为本人亲自缔结法律行为时,根本不可能存在本人故意侵害自身利益之类的情况。亲自缔结法律行为时本人“故意”实施的任何异于早前的利益安排的行为,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实质都只是本人对自身利益的重新定义而已。(43)参见Vedder,“Neues zum Missbrauch der Vertretungsmacht,”JZ 2008,S.1079.需注意的是,不能仅因诸如代理人有意识地以显著低价出售本人财物之类的情节,就认定代理人有损害本人之故意。譬如,虽然代理人有意识地以显著低价出售了本人的房屋,但原因可能仅是代理人误以为本人想以低价出售,代理人是否明知其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有悖于本人的利益安排,才是认定“故意”与否的关键。此种明知往往可通过以下事实来认定:代理人非为本人的利益,而是为其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实施代理行为。比如,本人指示代理人以不低于10万元的价格出卖其二手车,后有人出价12万元向代理人求购该车,但代理人还是以10万元价格将该车出售给了自己的朋友。
据此,我国法语境下的代理权滥用法理应主要针对代理人违反忠实义务的事例。仅代理行为客观上有害于本人(包括代理人因过失实施了有害于本人的行为),即使相对人对此知情,也不应允许本人拒绝代理效果。
四、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国的代理权滥用法理应适用于何种情形,已基本得到澄清。问题是,就代理人违反忠实义务的事例而言,既然与违反指示或限制同为本人不允许的代理行为,为何不可直接作为“无权代理”来处理?
(一)抽象原则何去何从?
如果像Laband 那样强调代理权范围的抽象性,那么即使违背指示的代理也可属有权代理;反之,如果代理权范围与内部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具有一体性,那么所有不被本人允许的代理行为都可能是“无权代理”。 在我国,近来不少学者就极力主张在代理权授予行为的效力等方面应放弃抽象原则,并由表见代理制度来保护交易。(44)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第240页;汪渊智:《代理法论》,第131-132页;朱庆育:《民法总论》,第345-346页;叶金强:《论代理权授予行为的有因构造》,《政法论坛》2010年第1期;冉克平:《代理授权行为无因性的反思与建构》,《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殷秋实:《论代理权授予与基础行为的联系》,《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等;刘骏:《再论意定代理权授予之无因性》,《交大法学》2020年第2期(不过,刘骏认为在商事代理领域应坚持抽象性原则)。不过,此种观点主要是针对代理权抽象性的一个方面,即代理权的效力不受内部基础法律关系无效、被撤销的影响。代理权抽象性当然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代理权的范围与内部基础法律关系上的义务无关。
就后一意义上的代理权抽象性而言,质疑的声音也从未停止过。前述学者Seeler就认为,代理权就是来自于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契约或其他类似的“事务执行契约”,这种契约既在本人与代理人之间创设了权利义务,又产生了代理权,代理权作为本人对他人干涉自我权利领域的许可,是此类契约的必要组成部分。在Seeler看来,一旦代理行为欠缺了与本人关系上的正当性就变成了无权代理,因为代理权是基于本人的意思而产生的,且无人会愿意接受一个非己所欲的、已被自己禁止的法律行为。而所谓代理权授予是单方行为、独立于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之说是不自然的。(45)参见Seeler,“Vollmacht und Scheinvollmacht,”ArchBürgR 28,SS.4ff.,9,9f,12f.Frotz更是直截了当地认为这种不自然的观念完全无视本人的形成自由:“代理人的权限是否受制于义务,原则上非法律事先所能定,而是首先交由本人来决定。……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愿授权他人实施违背义务的行为,任何一个理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也都会认为授权者不会如此不理智,即使他在授权表示时未明说将代理权的范围限定在与义务相符的行为。故在任何一个授权中,代理人能够做的显然都因意定而受制于其被允许做的。”(46)参见Frotz, Verkehrsschutz im Vertretungsrecht, Frankfurt/M: Athenäum, 1972, S. 264.
然而上述论点未必击中要害。将法律行为孤立于基础行为或原因,也即所谓的“孤立化方法”(Isolierung-Methode),仅是法律行为理论的一种技术化。该技术化使得法律行为摆脱了附着在原因之上的风险,为法秩序带来了安定性与明了性,而安定性和明了性正是法秩序不可欠缺的要素。(47)参见Egger,“Missbrauch der Vertretungsmacht, Beiträge zum handelsrecht,”Festgabe zum 70. Geburtstag von Carl Wieland, Basel: Helbing & Lichtenhahn, 1934, S.47f.反之,如果只强调形成自由,那么几乎已成通说的动机错误理论(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甚至也可能被否定。因为将动机与法律行为分开,所体现的正是“孤立化方法”。(48)参见Egger,“Missbrauch der Vertretungsmacht, Beiträge zum handelsrecht,”Festgabe zum 70. Geburtstag von Carl Wieland, S.47.或许此种技术路线在一些人看来“不自然”,但“不自然”尚不足以否定该技术路线。只有其他貌似更自然的技术路线也能满足同一功能时,才能宣告旧技术路线的寿终正寝。但是否真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表见代理这一技术路线就能在代理交易保护上全面取代代理权抽象性理论?
(二)有权代理说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对于代理人违反内部限制或指示的事例而言,并无强调代理权抽象性之必要,表见代理制度已足够保护代理相对人。但是,对于代理人客观上未违反内部限制或指示,只是故意违反忠实义务的事例而言,表见代理制度可否依然发挥作用,不无疑问。因为“代理权通知”只是本人的一种举止态度,从中无法读取代理人有无“不忠”的内心意图;实际连本人自己都不知代理人的内心意图,即便询问本人,也可能毫无意义。比如当本人的举止态度表明代理人得以“不低于10万元的价格出售小汽车”,而代理人恰以10万元价格出售该车时,谁也无法断定代理人“不忠”;只有事后发现代理人因买家是其友人而放弃了以更高价格出售该车之机会时,代理人内心的“不忠”才为人所知。要之,代理相对人无法仅凭“代理权通知”就相信代理人是忠于职守的。在此意义上,表见代理(本人的举止态度给相对人以“误解”)与代理权滥用(本人未能成功防止代理人背信行为的发生)完全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强以表见代理规则去应对代理权滥用,也只是为了保护相对人而假托一个规则罢了。
不过,既然不能过多要求相对人去调查本人是否在内部对代理人作出了特定指示或限制,那么就更无理由过多要求相对人去调查代理人是否不忠。毕竟,代理人的内心意图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在代理人客观上未违反特定指示或逾越内部限制的前提下,想要继续核实其内心意图,显然更加困难。既然如此,则相对人对于代理人忠于职守的信赖就应得到——比之对于代理人未违背指示或逾越内部限制的信赖——更多保护。所以,与其假借表见代理规定,不如直接以“有权代理”作为处理代理人单纯违反忠实义务问题的出发点。必须承认,忠实义务这种内部关系上的固有义务并不构成对代理权范围的限制,仅在这一点上本人“允许”代理人做的与代理人实际“能够”做的仍不同。正如Beutien所说,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大”的代理权抽象性,而是一个 “小”的代理权抽象性。(49)参见Beutien,“Gilt im Stellvertretungsrecht ein Abstraktionsprinzip?”50 Jahre BGH: Festgabe aus der Wissenschaft, Bd. I, S. 99f.
实际上,我国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也倾向于从“有权代理”的角度来处理代理人违反忠实义务的问题。譬如,银行信用卡部的工作人员通过发行信用卡侵占客户资金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呼军系建行太原分行信用卡部的工作人员,其与黄陵信用社协商办理信用卡事宜,应属职务行为,建行太原分行应对呼军的行为后果承担民事责任。”(50)参见“中国建设银行太原市分行与山西省太原市南郊区黄陵信用社存款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1998)经终字第201号民事判决书》。又比如银行信贷部负责人通过吸收存款侵占客户资金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信贷部原负责人梁斌以信贷部的名义吸收江城营业部人民币1 000万元的储蓄存款,并在吸收存款时向江城营业部出示了有关证明,其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信贷部清算组,应依存单约定向江城营业部承担兑付责任,但双方约定的高息部分不予保护。”(51)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咸宁市支行与三峡证券有限公司江城营业部等存单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1997)民终字第112 号民事判决书》。还比如储蓄所主任开具存单为自己债务核押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许开泉是新街储蓄所的负责人,其对外以新街储蓄所的名义所为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且空白存单系由作为新街储蓄所业务员的许开泉之妻李淑琼从该所套取,存单表面要件齐全,作为质权人华信公司营业部有理由相信质押存单是由新街储蓄所开具。”(52)参见“中国工商银行莆田市涵江支行与福建省华侨信托投资公司营业部等存单质押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1) 民二终字第163 号民事判决书》。尽管有学者认为审判实践未很好区分表见代理与“职务行为”(53)参见杨芳:《〈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规则)评注》,《法学家》2017年第6期。,但很多时候审判实践正是要借“职务行为”一词说明行为人被赋予了“履行该职务所应当具有的权限”。(54)参见刘文科:《商事代理法律制度论》,第85页。而在近来的“湖北金华实业有限公司与苏金水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苏金水案”)中,针对代理人出售本人的房产并截留购房款之举,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如一审法院那样认定为代理人个人的行为,而是根据代理人、本人间的《包干销售合同》定性为有权代理,并指出代理人所违反的只是“内部约定”。(55)参见“湖北金华实业有限公司与苏金水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抗字第24 号民事判决书》。
(三)“人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金水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特别提及一点,即“选择和监督委托代理人的经营风险不得转嫁于”合同相对人。代理权滥用对交易当事人而言的确是一种“风险”,确切说就是所谓“人的风险”。(56)参见 Frotz, Verkehrsschutz im Vertretungsrecht, S. 605.意定代理的场合下,此种风险根源于本人动用了私人自治意义上的形成力,也即本人为缔结法律行为而推出了代理人。如若本人选择直接与相对人缔结法律行为,则本来不会有此等风险。另就防控此种风险的有效性而言,与其要求相对人在交易时多加注意,不如要求本人在选任和监督时谨慎小心。在此意义上,意定代理的场合下“人的风险”的支配者是本人,非相对人,故而当“人的风险”成为现实之际,本人比相对人更应负担相应的责任。
(四)相对人不值保护时“效力待定”?
以“有权代理”作为处理代理人违反忠实义务问题的出发点,只是为了保护相对人。于是,当相对人不值得保护时,基于“目的性限缩”否定代理权之抽象性(57)参见Prölss,“Vertretung ohne Vertretungsmacht,”JuS 1985, S.577.,以“无权代理”来定性违反忠实义务的代理行为,似未为不可。但是,在此基础上,是否当然适用《民法典》第171条之规定,不无疑问。 根据《民法典》第171条第1款,无权代理人缔结的法律行为“效力待定”,这意味着,只要相对人未行同条第2款规定之催告、撤销(比如相对人始终不知无权代理),本人也从未明示或默示追认过,则自法律行为缔结起无论经过多久,本人都可主张该法律行为对自己不生效力。如此一来,即便本人不知代理权滥用而履行了合同,由于尚不构成默示追认,本人也总有“反悔”的可能。在《民法典》第145条中,也能见到法律给予限制行为能力人类似的优待。但是,《民法典》之所以这般优待本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牺牲法律关系的安定性,只是因为法律行为发生在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代理权消灭”或仅具“限制行为能力”的场合,也即当事人不仅自己未做出相关意思表示,也未授权过他人做出相关意思表示,或者只是在没有辨识能力的状态下做出了意思表示。简言之,当事人并无相应的可责性,不能仅因时间徒过就受法律行为之终局拘束。
形成对照的是基于重大误解、受欺诈等实施的可撤销意思表示。由于这些意思表示均是有辨识能力之当事人亲自作出,只是存在意思瑕疵,故撤销权会因除斥期间届满而消灭,当事人仍可能受法律行为之终局拘束。(58)关于效力待定的行为与可撤销的行为在这一意义上的区别,参见Lorenz, Der Schutz vor dem unerwünschten Vertrag,München: C.H.Beck, 1997, S. 52f.至于代理人未违反指示或逾越内部限制,只是单纯违反忠实义务之场合,究竟系更像通常的“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还是有“意思瑕疵”之法律行为,殊值讨论。如后文所示(本文之第五部分),代理人单纯违反忠实义务之事例,在利益状况上与“第三人欺诈”之事例颇为相似,故本质上不同于《民法典》第171条第1款所规制之情形,本人并非没有可责性。基于不同事物不同对待的原则,本应拒绝适用《民法典》第171条第1款于代理权滥用。
五、规则续造之基础:诚实信用、真意保留抑或第三人欺诈?
由此可见,针对违反职责型的代理权滥用,现行法上其实尚无完备的制度规范;关于我国的代理权滥用法理,还需借助法秩序内的其他评价标准,进一步加以续造。
(一)向诚实信用原则的逃逸
首先想到的是民法一般原则的适用。德国的审判实务界传统上就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建构代理权滥用法理的。比如1964年3月25日的联邦法院判决即认为,在代理权滥用问题上应延续帝国法院的“恶意抗辩”(die Einrede der Arglist)理论,也即关键需考虑,相对人向本人主张合同的效力,而该合同恰是代理人基于代理权滥用与相对人缔结的,是否为诚实信用原则所禁止。(59)参见BGH WM 1964, 505.
相对人非善意却仍向本人主张代理效果的,属援引不诚实获得之权利地位,的确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但是,诚实信用原则毕竟只是内容空洞、缺乏明确要件构成的一般条款。譬如对于本文所关注的如下问题,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本人得知代理权滥用后,是否总是可以拒绝代理效果;如自本人知道代理权滥用或自法律行为缔结时起经过一定期间,本人就不得拒绝代理效果的,则这一定期间究竟是指多久,等等。诚如Kipp所说,一般条款的直接适用,大多属于具体规定缺失时无奈采取的“应急措施”,而在有可得适用之具体规定时,这样的“应急措施”是没有必要的。(60)参见Kipp,“Zur lehre von der Vertretung ohne Vertretungsmacht,” Die Reichsgerichtspraxis im deutschen Rechtsleben, Bd. 2,Berlin: de Gruyter, 1929, S. 288.
(二)真意保留法理的类推适用?
除了一般原则外,法秩序之中,究竟有无得以作为规则续造之基础的具体规定?对此,日本的代理权滥用法理值得一观。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代理人企图为自己或第三人谋利而实施权限内之行为的,倘若相对人知或应知代理人的这一意图,则可类推适用《日本民法典》第93条但书之规定,本人无须就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61)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1967年4月20日判决民集21卷3号”第697页。修订前的《日本民法典》第93条规定:“表意人知道其意思表示并非真意时,亦不因此而碍其效力。但相对人已知或可知表意人之真意时,其意思表示无效。”这就是有关“真意保留”的规定。类推适用该规定于代理权滥用事例也渐成日本学界的多数说。(62)参见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I 新订民法总则》,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322页;近江幸治:《民法讲义I 民法总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5页。
我国民法上并无真意保留的规定,不过由《民法典》第142条可知,表意人内心之真意与表示不一致,且不被相对人所知或应知时,意思表示的内容应依相对人所理解之含义而定。若此种不一致是表意人故意而为,则不构成重大误解,故表意人须受到法律行为之终局拘束。据此,我国《民法典》实际上也肯认了真意保留法理。(63)关于真意保留法理与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关系,参见纪海龙:《真意保留与意思表示解释规则》,《法律科学》2018年第3期。
不可否认,类推适用真意保留法理相比适用笼统的诚信原则更具要件构成上的确定性。但正如一些日本学者所言,代理权滥用事例实际并不存在类推真意保留法理的基础,因为即便是代理权滥用,代理人的行为客观上表现的内容与他的实际意思也并无二致,都是“行为的法律效果归属于本人”,故与真意保留的情形之间无相似性可言。(64)参见四宮和夫:《民法総則》,东京:弘文堂,1982年,第252页;佐久間毅:《民法の基礎》,第293页。判例之所以类推适用(假托)真意保留规定,仅因为《日本民法典》中唯独这一规定最接近于如下结论:代理人滥用代理权时,其行为的效果原则上仍归属于本人,除非本人可以证明相对人知或应知代理人有不当意图。(65)参见谷口知平、石田喜久夫編:《新版注釈民法(1)》,东京:有斐阁,1981年,第108页;四宮和夫:《民法総則》,第252页。
(三)以“第三人欺诈”规则为参照
本文认为,代理权滥用的利益状况毋宁说更类似于《民法典》第149条所规定的“第三人欺诈”。
1.利益状况上的相似性
众所周知,民事欺诈的实质,就是他人故意侵害表意人在法律关系形成上的自我决定。而本文所谓之代理权滥用,如上所述,专指诸如“代理人为其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而实施有损本人利益的代理行为”之类的事例。必须看到,基于意定代理形成的法律关系虽有他主(代理人)决定的一面,但本质上仍属本人自我决定的范畴。(66)参见王浩:《论代理的本质》,《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所以,当代理人为其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而实施有害于本人的代理行为时,实际上本人的自我决定就受到了故意侵害。此外,就第三人欺诈表意人而言,第三人虽非合同关系之当事人,却不诚实地利用了自己对表意人的影响力(滥用了表意人对诚实告知信息的信赖),致表意人实施了于己不利的法律行为。代理权滥用的场合下,代理人也非合同关系之当事人,却同样不诚实地利用了自己对本人的影响力(滥用了本人对诚实行使代理权的信赖),使本人不得不接受一个于己不利的法律行为。可见,代理权滥用和第三人欺诈在利益状况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有学者认为意思瑕疵问题上的法律诉求不同于代理法,前者不注重相对人信赖的保护。(67)参见殷秋实:《论代理人与相对人的恶意串通》,《法商研究》2020年第3期。但是,在“第三人欺诈”的问题上,法律偏偏注意到了这样的诉求。《民法典》第149条规定,仅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表意人受欺诈时,表意人才得否定法律行为的效力。如上所述,代理权滥用原则上仍属有权代理的范畴,仅相对人不值保护时才构成“无权代理”。可见法律在“第三人欺诈”问题上的诉求并未与代理法有明显不一致。所以,在代理法的续造上,现行法围绕“第三人欺诈”问题所形成的规则群(如《民法典》第149条、第152条)恐怕不能被无视。
另有观点认为,相比受第三人欺诈的表意人,本人应获得更多的保护,故而即使相对人无过失地不知代理人滥用代理权,本人也可否定代理行为的效力。理由在于,表意人通过核查欺诈者的虚假陈述,尚可能于意思表示作出之前阻止侵害;而本人则无可能在代理人滥用代理权时阻止侵害,因代理人握有将代理效果直接归属本人的代理权。(68)参见Vedder, “ Neues zum Missbrauch der Vertretungsmacht,”JZ 2008, S.1082.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观点更像是将代理权滥用类比“第三人胁迫”。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50条,表意人受第三人胁迫的,无论意思表示的相对人是否知悉胁迫,表意人总能撤销法律行为。原因正在于,相比欺诈,胁迫对于表意人的自我决定侵害更严重,表意人更无可能阻止受胁迫。(69)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471页。但就代理权滥用而言,其对自我决定的侵害程度未见得比欺诈更严重,且前已述及,代理权滥用的风险根源于本人自身,观念上本人尚可通过审慎选任更称职的代理人,来管控代理权滥用的风险。在此意义上,代理权滥用中的本人完全不同于受胁迫的表意人,并无理由比受欺诈的表意人获得更多保护。
2.无权代理之特则
据此,代理权滥用更类似于存在“意思瑕疵”的法律行为,而与《民法典》第171条所谓之“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之间则有较大差异,故应参考《民法典》第149条、第152条,形成专门针对代理权滥用问题的无权代理之特则。具体而言,代理人滥用代理权的场合,本人一般不得以“无权代理”为由拒绝代理效果,惟代理相对人知或应知代理人滥用代理权时,本人方得主张“无权代理”;但本人知或应知代理权滥用之日起1年内,或者自代理人缔结法律行为之日起5年内未表示拒绝代理效果的,不得再行拒绝。此外,本人得拒绝代理效果之场合,因代理相对人非善意,故即便受有损失,也无法根据《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请求代理人承担法定特别责任;至多只能以代理人有过错为由请求代理人承担侵权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但代理人仍可根据《民法典》第171条第4款主张责任之减轻。
3.“应当知道”的判断标准
如上所述,本人得以“代理权滥用”为由拒绝代理效果的前提是相对人知或应知代理人滥用代理权。《民法典》第149条中的“应当知道”,是指“因过失而不知”。(70)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总则详解》下册,第648页;石一峰:《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问题是,就代理权滥用而言,代理相对人的过失究系指轻过失还是重大过失?
若指轻过失,则意味着代理相对人在代理交易时须尽可能地调查核实代理人有无滥用代理权。但如前所述,之所以区隔内部关系上的忠实义务与代理权范围,目的就在于让相对人在代理交易时无需投入过多的成本在核实代理人是否忠于职守上;又如前所述,之所以让本人而非相对人更多承担代理权滥用之风险,是因为在意定代理之中本人比相对人更易支配该风险,人们更应期待本人在选任监督代理人时更加谨慎小心,而非期待相对人在交易时进行广泛的调查核实。所以,关于相对人是否“应当知道”,不应根据相对人是否尽到核实义务来判断。
要求代理相对人对滥用权限负担核实义务的立场,于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权的场合尤其不合适。《民法典》第61条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通常认为,与代表人交易时,相对人并无义务核实代表权有无内部限制,除非代表人超越权限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只要不是熟视无睹就不可能不知道。(71)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上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425页。如上所述,滥用权限(内心意图的问题)比之违背内部指示或超越内部限制更为隐蔽、更难从外部察知。既然相对人对于代表权的内部限制都无核实义务,则对于滥用代表权就更不应负担核实义务。
那么,具体如何判断“应当知道”(有无重大过失)?本文倾向于近来多被学者提及的“显见性”标准。(72)参见汪渊智:《代理法论》,第240页;朱庆育:《民法总论》,第352页;吴香香:《滥用代理权所订契约之效力》,《中德私法研究》第 15 卷,第 245页;胡东海:《论职责违反型代理权滥用》,《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迟颖:《德国法上的禁止代理权滥用理论及其对我国代理法的启示》,《河北法学》2020年第11期等。所谓“应当知道”,即指代理权滥用的嫌疑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稍加注意便可知晓代理权滥用。滥用的嫌疑是否明显,不能仅看交易价格是否明显低于市价、相对人与代理人是否为亲友之类的因素(73)有观点认为基于这些因素便可推定相对人知或应知代理权滥用,比如殷秋实:《论代理人与相对人的恶意串通》,《法商研究》2020年第3期。, 而应根据交易惯行,结合交易的具体内容(比如代理行为是否有害于本人而有利于代理人)、相对人的具体属性(比如作为专业人士的相对人比一般相对人更易察觉代理权滥用)等综合研判。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总刻意区分“应当知道”与“显见性”,好像一旦改称“应当知道”,就意味着代理相对人负上了高度的调查核实义务。(74)参见吴香香:《滥用代理权所订契约之效力》,《中德私法研究》第15卷,第 247页;胡东海:《论职责违反型代理权滥用》,《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迟颖:《德国法上的禁止代理权滥用理论及其对我国代理法的启示》,《河北法学》2020年第11期等。这种认识可能也是受到某些德国学者的影响,比如弗卢梅:《法律行为论》,第941页。然而,在我国法上,“应当知道”一语与有无此等注意义务之间并非对应;即使当事人不负此等注意义务,也可能由于“应当知道”而得不到保护。比如《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规定代理相对人只要“善意”就可请求无权代理人承担特别责任,这表明代理相对人并无义务调查核实代理人的主张是否真实;而根据同条第4款,“应当知道”的相对人并不能主张上述特别责任(只能在与代理人分担损失的前提下主张一般的侵权责任)。该条所称“应当知道”,正是指不知但有“重大过失”的情形。(75)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总则详解》下册,第773页。实际上,所谓相对人不负调查核实义务,非指任何时候都不需调查核实;如从交易内容等来看有明显可疑,则相对人基于诚信原则之要求自应调查核实,否则即构成“重大过失”。在此意义上,“应当知道”“重大过失”与“显见性”之间并无实质差别,“显见性”不过就是用以判断是否“应当知道”、有无“重大过失”的一介标准。
六、结 论
关于代理权滥用法理,本文认为需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违反内部指示或超越内部限制的代理属越权代理,与表见代理有关,但无关代理权滥用法理。代理权滥用法理的主战场应为代理人违反忠实义务、故意损害本人利益的情形。由于表见代理制度不足以保护此种情形下的代理相对人,故应切断忠实义务与代理权范围之间的联系,违反此类义务的代理原则上属有权代理的范畴时构成无权代理。第二,但是,关于此种意义上的无权代理,《民法典》第171条尚不足应对,仍需借助法秩序中其他的评价标准来续造规则。第三,鉴于代理权滥用与第三人欺诈之间的相似性,可从《民法典》第149条、第152条出发形成这样的特则,即代理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权人滥用代理权时,本人得在一定期间内以“无权代理”为由拒绝代理之效果。至于“应当知道”的判断,则不应以相对人有较高的注意义务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