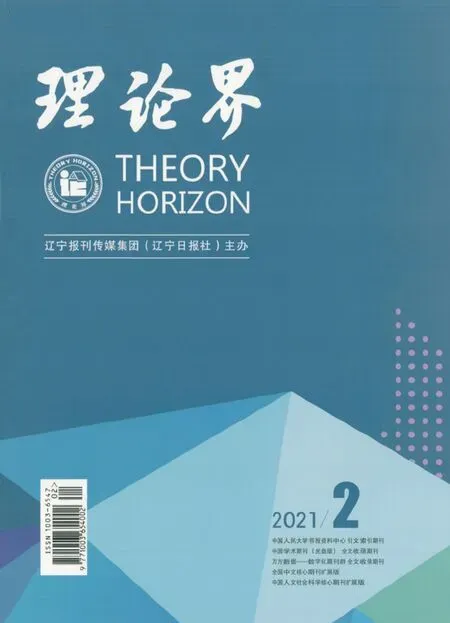民族志视野下的北宋使辽诗
刘炳辉
一、问题的提出:北宋使辽诗是民族志
一般而言,“民族志是关于民族/族群社会文化的记述与描写,其研究对象就是民族(Nation/Nationality) 或 族 群 (Ethnic Group)”。〔1〕为了最终完成和呈现某个民族和地方的文化文本,最重要的环节是开展田野调查。向丽其在文章中对民族志书写与田野调查的关系这样界定:“民族志旨在通过对研究对象所在‘田野’知识进行考察、收集,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知识进行分析、比较和阐释,以获得关于此文化的形态与意义的更为繁复而细致的知识谱系。”〔2〕也就是说,民族志书写是人类学研究从田野到文本的转向,既包括对田野调查的文字记述,也包括田野调查后的继续研究。追本溯源,英国人哈登在《人类学史》中提出,人类学发展有三个主要阶段:“首先,是一个杂乱的事实或猜想,是历史学家、冒险家、传教士的遗物,它乃是各种认真程度不同的业余学问家所喜欢涉猎的地方。其次,我们看到从混乱中产生了秩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许多建筑物,但却有着不稳定性和不完美性。最后,它们为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性整体所取代。”〔3〕作为人类学的分支,民族志无疑可以被看作是民族学家对被研究的民族、部落、区域的人的生活文化的描述与解释。它的产生与发展显然也经历了杂乱无章的描述、粗犷的采集与叙述以及渐趋系统化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三个阶段。也就是说,民族志概念及其方法论的提出要远晚于民族志文本的形成,因此,世界各国有关异民族的记载都可以被算作民族志的一部分。而这些记载中,中国的史料文献无疑是最早最系统的。早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文献中,就已开始记载周围各民族的动态。《诗经·鲁颂·秘宫》中有对戎狄的明确记述:“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4〕二十四史中更是有北狄传、大宛传、匈奴传、突厥传等少数民族传记。特别是20 世纪中后期,以写诗的方式或者直接以诗歌文本的形式来写田野调查报告,是西方文化诗学、人类学诗学以及民族志诗学等流派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方式。而这些以诗歌来抒写田野调查的方式,其实在中国古代早已朦胧出现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没有率先提出“民族志”及其相关概念,但是我国的民族志资料已经积累了几千年,早已具备民族志的书写基础和文本形态。所有有关他民族的记述和诗歌等创作,都应该被纳入民族志的范畴。
理清了民族志概念及其早期形态,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北宋人使辽的创作目的。使辽诗不仅记录着北宋使臣的出使感受、沿途见闻、辽地风俗和民族情感,甚至还会窥探辽国动向,评估对辽政策。苏耆曾两度出使辽国,苏舜钦《先公墓志铭》称:“诏使契丹,初出疆,每舍必作诗,山漠之险易,水荐之美恶,备然尽在。归而集上之,人争布诵。”〔5〕苏耆使辽,显然是以诗歌来代替使辽观察笔记,时人竞相传诵。随着宋辽两国频繁通使,大到疆域地貌和风俗人情,小到身在异国他乡的情感波动,皆可入诗,既体现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优越情怀,又符合“赋诗言志”和“兴观群怨”的诗学传统。情韵兼备、诗意盎然的使辽诗因为符合大众需求,能引领社会风尚,不足为奇。
我国悠久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各民族之间交流、交融和沟通的民族融合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6〕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尽管宋辽政权是对立的,但是各民族之间的情感是相亲相近的。北宋使臣出使辽国不只是对辽国的文化产生了影响,辽国的民俗文化同样对北宋使臣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使辽诗是宋辽对峙时期民族融合的产物。我们将其放在民族志视野下,不但能准确反映北宋使臣的创作目的,而且更能体现民族交流交融的双向互动,对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大有裨益。
二、北宋使臣有意识的诗歌创作和无意识的民族志书写
北宋使臣进入辽国虽然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是在创作欲望驱使下,他们当中有不少文士如欧阳修、王安石、苏颂、苏辙、王珪、余靖、彭汝砺、陈襄等,创作了大量见景生情、为人传诵的使辽诗篇,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辽代社会历史和风土人情的宝贵文献。
宋辽两国设有陪同人员,专门迎送双方使节于边境,史称“伴使”或“馆伴”。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初,王安石曾伴送辽国贺正旦使回国,途中曾写下一组诗歌,编为《伴送北朝使人诗》。其《涿州》诗云:“涿州沙上望桑干,鞍马春风特地寒。万里如今持汉节,却寻此路使呼韩。”〔7〕“桑干”即桑干河,亦名卢沟河(今北京市南郊的永定河)。《辽史·地理志四》:“(宋)王曾《上契丹事》曰:自雄州白沟驿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刘李河,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8〕白沟是宋辽边境的界河,在今河北省白沟镇附近,而桑干河即卢沟河,距离燕京六十里,是辽国的腹地。路过白沟,王安石有《白沟行》诗云:“白沟河边番塞地,送迎番使年年事。……棘门霸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7〕在这首诗中,王安石明确表示白沟是宋辽边境线,并对对辽政策表达了强烈不满。其《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亦言:“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语言之不通,而与之并辔十有八日,亦默默无所用吾意。时窃咏歌,以娱愁思,当笑语。鞍马之劳,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诸戏谑之善,尚宜为君子所取。故悉录以归示诸亲友。”〔7〕根据这篇序言和现有史料,王安石很可能未曾真正出使过辽国,只是作为馆伴或伴使到过宋辽边境。因此,这首《涿州》,诗人应该只是站在泛指的涿州之地,远望“桑干河”,并未深入辽地。
辽廷为宋使食宿方便,在境内设有驿馆,使辽诗对此多有描述。遇到比较繁华的驿馆,辽国馆伴甚至还会以美酒和契丹歌舞来助兴。王安石作为馆伴,就曾在边境驿馆受到过这样的款待,其《出塞》诗云:“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泪落,蒙蒙吹湿汉衣冠。”〔7〕蒙蒙细雨中享受契丹歌舞虽然非常惬意,但是诗人始终不肯忘却他的身份和使命。相比之下,真正深入辽国腹地的王珪创作的使辽诗更能令人深切感受涿州之景,其《涿州》诗云:“涿州亭下柳依依,谁折长条送客归。晓月未消燕戍酒,春云初拂汉台衣。玉堂社燕宜先入,沙碛晴鸿已半飞。回首青山欲千里,行人犹自马騑騑。”〔9〕在诗人笔下,杨柳依依,明月美酒,这样的良辰美景即使身处中原也不过如此。相同的鹿儿馆,诗人的情绪不同,笔下的景色也是千差万别。王珪《戏呈唐卿》诗写出了鹿儿馆的艰险和高峻:“行到鹿儿山更恶,八千归路可胜劳。……晓磴云浓藏去驿,阴崖冰折断前桥。”〔9〕刘敞《朱桥》诗则写出了鹿儿馆的风景秀丽和自己的无限留恋之意:“朱桥柳映潭,忽见似江南。……犬声寒隔水,山气晚成岚。留恨无人境,幽奇不尽探。”〔10〕苏辙使辽,有《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渡桑干河》诗即描述了辽国“馆伴”于边境送宋使出境的情形:“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11〕正是得益于契丹民族对北宋政权的友好情感,这才出现了“胡人送客不忍去”的动人场景。在诗中,倔强的苏辙终于对辽人的习俗生活表达了适当理解。而这种情感其实在《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诗中已有流露:“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其三),“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其四)。〔11〕刘跂到达辽国后,受到的也是友好盛情的款待。其《使辽作十四首》十一云:“今日朝元仗,千官两掖门。从容鱼藻宴,供奉柏梁尊。厌服貂裘敝,愁看桂酒温。谁知广文淀,水面箔为藩。”辽廷设国宴招待使臣,君王亲自出席,“千官”陪同,盛况空前的酒宴使人耳目一新,倍感亲切。于是,诗人以平和的心态欣赏着辽人的风俗人情。其十二云:“置酒穹庐晓,僧山合管弦。应缘地褊小,难遣舞回旋。风急皮毛重,霜清湩酪膻。君看东向坐,贵重尽童颠。”〔12〕无论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恰似江南的风土人情,甚至是契丹人的热情款待,虽然观察的视角以诗人心情为主,但是它们都是朴素的民族志书写。
民族志田野调查具有科学、专业、准确的特征,也必然带有写作者个人的情感、风格及立场,这种情感、风格及立场创造了民族志的文学性,即“民族志具有文学品质”。〔13〕换句话说,由于北宋使臣的创作动机和抒情范式不同,或缘事而发,写情纪实,或应酬而作,拟情造景,或通过政治修辞表现大国情怀,使辽诗必然会存在个人描述与客观现实的差异,从而呈现千姿百态的文学性。更进一步讲,虽然北宋使臣无意对辽朝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进行田野调查,并且有意对使辽诗进行修辞润色,但是因为涉及所见所闻、心得体会以及对不同文化的感知,并不妨碍这些使辽诗成为田野调查文本,成为民族志。
三、辽国的自然风光和生活环境
宋辽和平相处,不仅让两国人民摆脱了战争之苦,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还加速了契丹族的汉化,促进了民族融合。进入燕云之地,展现在北宋使臣面前的是一幅“青山如壁地如盘,千里耕桑一望宽”,〔14〕“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14〕的人民安居乐业的美景。看到雄伟的燕山,苏辙不禁惊呼“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中开哆箕毕,末路牵一线”,进而称赞燕地之民“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上论召公奭,礼乐比姬旦。次称望诸君,术略亚狐管。子丹号无策,亦数游侠冠。”〔11〕其《木叶山》诗云:“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冰霜叶堕尽,鸟兽纷无托。”〔11〕木叶山在今内蒙古东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诗人不但对辽国的地理环境有所描述,而且对当地百姓耕种贫瘠之地也表达了同情。张舜民《秋日燕山道中》诗更是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燕山:“燕山秋更好,况复新值晴。一径幽花闹,千岩晚瀑明。寺危迂路入,水漫信船行。尝栗皱初破,开梨颊未頳。松萝扶斗上,剑戟插沙平。”〔15〕在郑獬笔下,辽朝的冬天狂风怒号、寒冷逼人,其《回次妫川大寒》诗云:“地风如狂兕,来自黑山旁。坤维欲倾动,冷日青无光。飞沙击我面,积雪沾我裳。”〔16〕
苏颂两次使辽,先后写下使辽诗五十八首,是其诗歌中最为亮丽的篇章。当他跨过白沟河,看到绚丽多彩的北国风光,顿时为“青山如壁地如盘,千里耕桑一望宽”〔14〕的壮丽山河倾倒。即使一路跋山涉水,面对“山路萦回极险屯,才经深涧又高原,顺风冲激还吹面,滟水坚凝几败辕,岩下有时逢虎迹”〔14〕的困境,他依然感到惊异和陶醉:“天险限南北,回环千里山,客亭依斗绝,朔地信偏悭。”〔14〕甚至认为这里的冬天也很有特色:“薄雪悠扬朔气清,冲风吹拂毳裘轻”,“朔风増凛冽,寒日减清晖。”〔14〕《过土河》诗更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画:“长叫山旁一水源,北流迢递势倾奔。秋来注雨弥郊野,冬后层冰度辐辕。白草悠悠千嶂路,青烟袅袅数家村。”〔14〕苏颂不仅对风格迥异的自然风光惊叹不已,还会用大量诗篇描写辽地人民的生活。在他笔下,经过多年的和睦相处,昔日落后荒凉的辽朝已今非昔比,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恬静怡然:“山谷水多流乳石,旃裘人鲜佩纯绵。服章几类南冠系,星土难分列宿缠。”〔14〕在《契丹马》一诗中,苏颂还对相比中原更加剽悍的契丹马进行了考察:“边林养马逐莱蒿,栈皁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材驹事力豪。略问滋繁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14〕辽阔草原上,“风寒霜雪”中放养的契丹马自然是比温室中喂养的中原马耐力持久,这是诗人得到的养马真经。
沙漠是使辽诗描绘较多的地方,苏颂有两首诗道尽沙上行路的艰难,其《沙陀路》云:“上得陂陁路转艰,陷轮推马苦难前。风寒白日少飞鸟,地迥黄沙似涨川。结草枝梢知里堠,放牛墟落见人烟。”〔14〕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依然有人烟,读来不禁令人暗自捏把汗。其《和过神水沙碛》更是着眼沙漠之险:“沙行未百里,地险已万状。逢迎非长风,狙击殊博浪。昔闻今乃经,既度愁复上。”〔14〕如果说苏颂笔下一望无垠的沙漠令人望而却步,那么彭汝砺笔下危险且易使人迷失方向的沙漠则令人胆寒。《大小沙陂》诗其二云:“大小沙陁深没膝,车不留踪马无迹。曲折多途胡亦惑,自上高冈认南北。大风吹沙成瓦砾,头面疮痍手皴折。下带长水蔽深泽,层冰峨峨霜雪白。狼顾鸟行愁覆溺,一日不能行一驿。”〔17〕沙陁即沙漠,狂风卷沙,道路难辨,在它面前,人类是那么的渺小和不堪一击,即使是熟悉当地环境的契丹人也得小心辨认。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当地人依然在此从事农业生产。《大小沙陁》其一云:“南障古北口,北控大沙陁。土地稻粱少,岁时霜雪多。”〔17〕其《宿金钩》诗更见辽国地广人稀、沙地较多:“绝域三千里,穷村五七家。云深无去雁,日暮有栖鸦。雾拥云垂野,霜远月在沙。”〔17〕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使辽诗人以自然环境入诗,使当时燕云之地的生存状态得以保存下来,充分体现了“以诗补史”“诗史互补”的特色,也符合民族志真实记录观察对象的要求。
四、辽人的习俗信仰
燕云之地入辽,尤其对于北宋使臣来说,这里是誓要夺回的故土,肯定要投入更多挑剔的目光。但是经过近距离观察,北宋使臣的态度逐渐有了变化,除了描写辽朝的自然山水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他们更多的是将笔触转向异域的风俗人情、君臣关系、生活方式、婚姻习俗及契丹语等,一切新异的事物都是他们的创作素材,极大地开拓了边塞诗的书写范围。
对于契丹族跟随季节和水草迁徙的生活习惯,以及居住的帐篷,苏颂也是不吝笔墨。其《辽人牧》诗云:“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14〕《契丹帐》诗云:“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酪浆膻肉夸希品,貂锦羊裘擅物华。种类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14〕牛羊成群,逐草而徙,辽朝人民努力生活、自给自足的形象已跃然纸上。辽人的居住方式尤为变通,既崇尚中原帝王威严的宫殿楼宇,又保留了在山林间射猎游牧的传统。其《观北人围猎》诗则对辽人的围猎习俗进行了刻画:“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画马今无胡待诏,射雕犹惧李将军。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14〕寥寥数语,众人骑马分围,弓矢齐发,锣鼓喧天,群兽逃窜的热闹场景便出现了,光是读诗都能令人热血沸腾,更何况诗人身临其境,视觉冲击想必更加强烈。尽管在诗人笔下,辽人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但是今天我们读来反而更能直观感受到契丹人当时的风俗习惯。正是得益于民族融合,契丹人的饮食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单一的肉食转向了荤素搭配,野味、野菜和野果都是上等的待客佳品。
辽朝有四时“捺钵”的习俗。“捺钵”即行宫,是辽朝皇帝在渔猎地所设行帐的契丹语称。苏辙使辽《虏帐》诗对冬“捺钵”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舂粱煑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我来致命适寒苦,积雪向日坚不融。联翩岁旦有来使,屈指已复过奚封。礼成即日卷庐帐,钓鱼射鹅沧海东。秋山既罢复来此,往返岁岁如旋蓬。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甘心五饵堕吾术,势类畜鸟游樊笼。”〔11〕彭汝砺《广平甸》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诗序详细描述了辽朝皇帝行宫的布局结构和装饰风格:“广平甸谓北地险,至此广大而平易云。初至单于行在,其门以芦箔为藩垣,上不去其花,以为饰。其上谓之羊箔门。作山门,以木为牌,左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总谓之‘蓬莱宫殿’,曰‘省方殿’。其左金冠紫袍而立者数百人,问之,多酋豪,其右青紫而立者数十人。山棚之前作花槛,有桃杏杨柳之类。前谓丹墀,自丹墀十步谓之‘龙墀殿’,皆设有青花毡。其阶高二三尺,阔三寻,纵杀其半,由阶而登,谓之御座。”〔17〕契丹贵族“四时捺钵”,普通民众则冬季定居避寒,夏季逐草游牧。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曾言:“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11〕
使辽诗对辽朝皇宫也有所涉及。韩琦曾参加过辽兴宗皇帝“永寿节”的庆典活动,其《使回戏成》诗云:“专对惭非出使才,拭圭申好敛旌回。礼烦偏苦元正拜,户大犹轻永寿杯。欹枕顿无归梦扰,据鞍潜觉旅怀开。明朝便是侵星去,不怕东风拂面来。”〔18〕深受汉人春节拜年习俗的影响,契丹元日的拜礼也不简单。苏颂对辽朝皇宫也有描写,其《广平宴会》诗云:“辽中宫室本穹庐,暂对皇华辟广除。编曲垣墙都草创,张旃帷幄类鹑居。朝仪强效鹓列行,享礼犹存体荐余。玉帛系心真上策,方知三表术非疏。”〔14〕如此隆重的宴会,虽然以契丹礼仪为主,但是也融合了汉族礼。
辽朝崇佛贵僧,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其二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11〕苏颂使辽曾到中京镇国寺游览,并有《和游中京镇国寺》诗记述该寺的宏伟和辽人信佛的盛况:“塔庙奚山麓,乘轺偶共登。青松如拱揖,栋宇欲骞腾。俗礼多依佛,居人亦贵僧。纵观无限意,记述恨无能。”〔14〕深受佛家文化影响,辽朝妇人有颜色者谓之“细娘”,面涂黄谓之“佛妆”。彭汝砺《妇人面涂黄而吏告以为瘴疾问云谓佛妆也》诗,曾对辽朝妇女的“佛妆”这样描述:“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人怪见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17〕他还对辽人的孩子有过细致描述,其《奚奴》诗云:“秃鬓胡雏色如玉,颊拳突起深其目。鼻头穹隆脚心曲,被裘骑马追鸿鹄。出入林莽乘山谷,凌空绝险如平陆。臂鹰緤犬纷驰逐,雕金羽箭黄金镞。争血雉兔羞麋鹿,诡遇得禽非我欲。”〔17〕可见,此次使辽,彭汝砺做了充分准备,对契丹人与汉人之不同,甚至是小孩样貌、服饰都有细致描绘,这显然是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
入乡随俗,有人甚至学会了契丹话。余靖曾三使辽朝,他在欢送宴上曾用契丹话写就《北语诗》一首:“夜筵设罗(侈盛)臣拜洗(受赐),两朝厥荷(通好)情干勤(厚重)。微臣稚鲁(拜舞)祝若统(福祐),圣寿铁摆俱可忒(无极)。”〔19〕辽朝皇帝听罢余靖的契丹语诗,非常高兴。刁约使辽,亦作契丹语诗,描述辽廷为他饯行酒宴及赐赠辽地特产貔狸鼠:“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20〕“移离毕”,契丹语官名,“貔狸”,辽地特产,形如大鼠,味如豚肉而脆。
在将燕云十六州纳入版图后,契丹立即采用了崇尚儒学、重用汉人的同化政策,成功实现了对燕云地区的统治。在这里,汉、契丹、奚、女真、渤海等族人杂居在一起,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碰撞在一起,燕云之地既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又是辽人学习中原文化、不断封建化的试验田。诸多因素纠结在一起,恰好给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民俗盛景。在此背景下,两种民俗文化兼收并蓄、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既儒雅沉稳又豪放洒脱的多元性民风习俗。相应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了,契丹与汉族的融合水到渠成。
五、结语
由于澶渊之盟是宋辽两方都认可的条约,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所说,“北宋对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21〕所以使臣们可以用从容的心态去审视辽朝的自然风光、民情风俗和社会文化,甚至带着嘲笑和鄙视。对于一贯主张“以和为贵”、睦邻友好的北宋朝廷来说,辽朝的所见所闻和文明进步恰恰是儒家文化同化异域民族的力证,自然值得他们大书特写。虽然北宋使臣无意对辽朝人民生活的地方和文化习俗进行系统描述,但是他们对被观察目标进行了深入、细致和全面的描述,既有客观的观察和判断,也有主观的体验和认知。正因如此,这些记录着我国北方民族融合和辽朝封建化进程的使辽诗,无疑是相对客观和公正的民族志。以民族志的视角重新解读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宋辽对峙时期辽朝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而且对于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国策真正融入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中,也是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