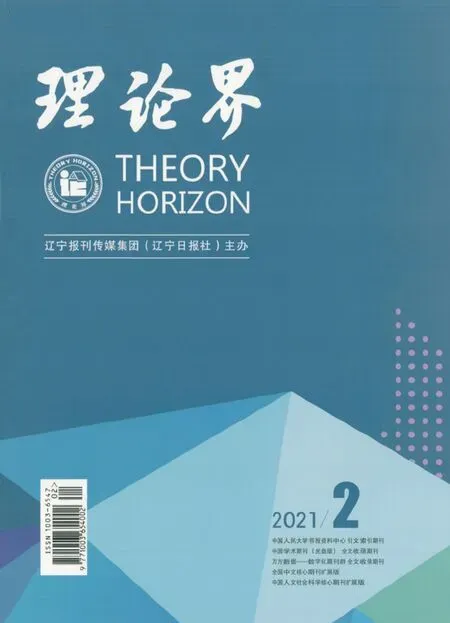任昉“兰台聚”与梁初政坛及文坛
何良五
魏晋南北朝一般被称为贵族制社会或门阀制度社会,然而学界一般的观点是,门阀制度至南朝为一大巨变,门阀势力减弱而皇权政治加强。高门贵族所自恃的门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在政治、社会上的优势随之减小,而次等士族以文学才能得到皇室赏识,得以与高门士族交往,甚至以平等的姿势并驾齐驱。概括来讲,南朝时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过渡,门第作为政治资本的效力逐渐减弱,而文学(文化)成为接近、取悦、臣服于皇室的工具,逐渐成为新的政治资本。这一转变在刘宋时便已开始,至南齐永明年间已相当明显。至梁武帝时,大力引进文学之士,锐意改革贵族制度,形成了一种新的贵族主义。任昉在南朝政治、社会变革过程中,凭借杰出的文学才能,一度成为文坛领袖,然而很快被外放为新安太守。任昉在梁初的得势与失势,其实与梁武帝的意志有关。
一、任昉何以成为文坛领袖
任昉为乐安博昌人,其先世在两晋时期未见特出者,门第不高,在普遍讲究门第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仕途前景并不乐观。《梁书》载任昉“幼而好学,早知名”。〔1〕《南史》本传记载较详:“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2〕说明任昉确实在幼年便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褚渊曾谓其父曰:“闻卿有令子,相为喜之。所谓百不为多,一不为少。”〔2〕史称褚渊“少有世誉,复尚文帝女南郡献公主”,宋明帝即位后,“深相委寄,事皆见从”。〔3〕可见,褚渊在当时政治、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另外,任昉从叔晷称其为“吾家千里驹也”。〔2〕任昉幼年之时便以文学才能得到名流褚渊及叔父任晷的赞赏,由此“早知名”。
《梁书》称任昉被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刘秉任丹阳尹在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任昉时年十五六,如此年轻便被权臣刘秉辟为丹阳尹主簿,主要还是因为“早知名”所起的作用。然而任昉“以气忤秉子”,“久之,为奉朝请,举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迁征北行参军”。〔1〕当时的秀才对策“主要重视的是才学文采”,〔4〕任昉得以举秀才,也由于其具有非凡的文学才能以及颇高的名气。其时任征北将军者为建平王景素,史称建平王景素“好文章书籍,招集才义之士,倾身礼接,以收名誉”。〔5〕任昉得以入建平王征北府,也由于其文学才名。永明二年(484),王俭任丹阳尹,引任昉为丹阳尹主簿。《南史》载“(王)俭每见其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且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2〕又令任昉改正己文。王俭如此夸赞任昉,当在士流当中具有一定影响,使得任昉声名更盛。此后,任昉迁司徒刑狱参军事,转入竟陵王萧子良府,又转司徒记室参军。子良高选僚佐,其府僚实为清贵之职,任昉得以迁为竟陵王子良府记室参军,说明其文采应该得到相当高的认可。又任昉长于文笔,史称“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1〕“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说明任昉文名已盛,并在王公贵族之间流传;而为王公代笔,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交游手段。〔6〕
萧衍克建康后,任昉以昔日旧友的身份得为骠骑记室参军。此后任昉“专主文翰”,“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1〕因文笔之才而得以运用。然而,任昉政治眼光、野心不如沈约,政治才干又不如范云,因此,虽同为西邸旧友,任昉在齐梁革命中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入梁后,其仕途升迁亦远不及沈、范二人。任昉在齐末官至中书侍郎(九班)、司徒右长史(十班),入梁后转吏部郎(十一班),掌著作;天监二年出为义兴太守,次年还都,重为吏部郎,参掌大选。居职不称,不久迁为御史中丞(十一班),在任时间大致为天监三年至四年,〔7〕五年为秘书监(十一班),六年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七年卒于任上。从官班来看,任昉在梁代的仕宦较为顺利,但是晋升过程相当平稳,最终班次也不高,仕途并不显达。然而,任昉在梁代文坛一度成为领袖人物,却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士林领袖出现于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有所谓名士一流,在社交界占据重要地位。东晋末年,刘裕通过打击以谢混为代表的士林领袖人物,使得贵族社交界一度黯淡下来,贵族高门为士林领袖、评骘人物的风气逐渐式微。〔8〕至南齐时,王俭一度振兴这一风气,同时以竟陵王子良为代表的皇室势力崛起,出现贵族与皇室双峰鼎峙的局面。〔9〕至此之时,贵族门第的影响力下降,而个人才学的作用增大,宋时主要以门第高下为交往之尺度,此时突破门第的限制而以才学多少为交往之标准。是以沈约、任昉等门第较低者,能与王融、谢朓等高门共同游处,号曰“八友”。并且在永明年间,沈约、任昉等人既获大名,在社交界具有一定影响力,普遍形成互相交游、提携后进之风。如《南史》载:“(谢)朓好奖人才,会稽孔觊粗有才笔,未为时知,孔珪尝令草让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简写之,谓珪曰:‘士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余论。’其好善如此。”〔2〕可知谢朓等人有意识地通过称赞后辈以为其树立名声。任昉结交、称赞后辈,亦自南齐始。如任昉在南齐时与到洽、到溉、到沼相善,称到洽“日下无双”,〔1〕申拜亲之礼。到溉“早为任昉所知,由是声名益广”,〔1〕任昉称赏延誉之功不可没。王僧孺出为县令,任昉赠诗大赞其文史之才;又称赞王籍、伏挺等人。总之,任昉在永明年间便已热心交游、称赏后辈,获得“有知人之鉴”〔1〕的评价。
入梁之后,武帝有意大举引进文学之士,《梁书·文学传》称“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1〕便是对这一情况的概括。又称“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殊”。〔1〕也就是说,不以官位高下为区别,有文才者皆加以拔擢。除永明年间便已成名的西邸旧友外,梁武帝、沈约、任昉等人尤其重视后进才士。而后进才士如何达于帝听呢?这时成名文人的延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任昉在齐梁革命过程中担任萧衍霸府记室参军,专主文翰,“禅让文诰,多昉所具”,沈约甚至略用心机而得以参制文笔,可见霸府文笔的重要性。任昉专主霸府文翰,其文学声名当进一步扩大。又“(任)昉好交结,奖进士友,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好”。〔2〕今存史料尚载任昉直接嘱托吏部尚书王瞻起用刘之遴,之遴因之得以除太学博士。〔1〕因此种种,任昉得以在梁初成为文坛领袖,形成煊赫一时的龙门之游。然而,任昉入梁以后在政治、文坛上的表现和遭遇,其实与梁武帝的意志是分不开的。
二、任昉的遭遇与梁武帝的意志
如前所述,萧衍称帝后大力引进文学之士,梁初文学因此大盛。与此同时,梁武帝通过举行公宴赋诗、诏敕文士写作并予以奖惩、授予文学之士以优职等手段,将政治权力介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企图获得政治、文学上双重霸主的地位。〔10〕在此过程中,永明年间便已成名,且与梁武帝关系较好的任昉实际上处于中间人的位置。《梁书·文学传》载梁武帝“引后进文学之士”,有彭城刘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等人,而所谓“兰台聚”则有刘孝绰、刘苞、刘孺、陆倕、张率、殷芸、刘显及到溉、到洽等人。受到梁武帝赏识的后进文学之士,基本上都受到任昉赏识;或者说,正因为得到了任昉的延誉,后进之士才得以受到梁武帝赏识。彭城到氏适为其例。彭城到氏本非士族,到彦之本以担粪自给,后随刘裕征战,以功封侯,到氏由此发迹。至第四代,到氏政治、社会地位已趋衰落,到溉、到洽自王国常侍起家,从父弟到沆自后军法曹参军起家,大致处于士族中下层。史载到溉、洽兄弟“少孤贫”,“早为任昉所知,由是声名益广”。说明溉、洽兄弟之所以成名,正是因为得到了任昉的称赏。《南史》载“(到溉)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资,为二儿推奉昉”。〔2〕又载任昉与到洽申拜亲之礼。可知到氏熟知任昉在社交界的地位,有意交结,企图获得任昉延誉。天监二年,任昉出为义兴太守,与到溉、洽共为山泽之游;次年还都迁为御史中丞陆倕赠诗曰“既有绝尘到,复见黄中刘”。〔2〕可知到氏兄弟经过任昉之交游、赏誉,声名已盛。梁初,到溉、洽、沆皆以文才被引见给梁武帝,帝御华光殿,令到氏兄弟与萧琛、任昉等赋诗,且对任昉称赞曰“诸到可谓才子”。任昉对曰:“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1〕梁武帝之所以对任昉称赞到氏,是因为他知道任昉与到氏兄弟非同寻常的关系,而任昉的回答,一方面肯定了梁武帝的称赞,另一方面则恭维武帝之得人。到氏兄弟正是通过任昉的延誉,得以进入宫廷文学圈,仕途大开。其他如刘孝绰、王僧孺、张率等人,与到氏兄弟类似,皆因任昉之赞誉而得知于武帝。在梁武帝掌控、主导文坛的过程中,任昉起到了一个中间人的作用,任昉在梁初得以成为文坛领袖,兰台聚、龙门游得以形成,背后暗含了梁武帝的意志。
任昉入梁后拜黄门郎,转吏部郎,这是与其以前仕历相称的职位。二年出为义兴太守,次年返都,“重除吏部郎中,参掌大选,居职不称”。〔1〕《梁书·王泰传》称“自过江,吏部郎不复典大选,令史以下,小人求竞者辐凑”。〔1〕东晋以后吏部郎虽不典大选,但其地位不断上升,反映在梁代官班中,就是吏部郎在十一班,班位高出尚书左、右丞,而其他尚书侍郎在第六班。任昉第一次担任吏部郎,更多的意义是经过这一官序,提高其政治地位。第二次任吏部郎,参掌大选,则其选官权力进一步扩大,其意义在于发挥铨选职能,若表现突出,很可能累迁至吏部尚书。然而,《梁书·任昉传》继而称其“居职不称”,不久即转为他职。关于任昉“居职不称”的原因,大约有两种说法:杨赛认为原因是任昉“狂放”,且“大力提拔南方士族和寒族,为当时北方士族所不容”;〔11〕郑雅如认为,“任昉将自己的交游作风带入选举公务,造成选举不公”,〔6〕与梁武帝的用人准则产生冲突。以上说法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最切中要害者,恐怕还数第二种说法。如前所述,梁初文人之所以争相与任昉结交,正因为“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又如前述任昉请托吏部尚书王瞻提拔刘之遴,可以想见任昉在吏部郎(参掌大选)任上,应当会按照自己的喜好选用士人。又史称“不附之者亦不称述”,〔2〕如裴子野为任昉之从中表,因不造请任昉,久之方得除官;二者之间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但显示出任昉好恶之心较强。此风若长,很有可能造成选举不公。
任昉居吏部郎不称职,随即转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本为高门士族不愿担任的官职,〔12〕然而梁武帝极为重视此职,张绾为御史中丞,武帝宣旨曰:“为国之急,惟在执宪直绳,用人本不限升降。”〔1〕此外,又提升御史中丞的班位。可知梁武帝以任昉为御史中丞,实际上是给予重用的。御史中丞一职既要执法严正,又要长于文笔,任昉二者皆得,留下了非常优秀的奏弹案例和奏弹文。然而,任昉在御史中丞任上,更为突出的是其作为文坛领袖的地位。史称任昉迁为御史中丞后,“后进皆宗之”,号为“任君”,比东汉之“三君”。范晔释“君”为“一世之所宗也”,〔6〕可见时人将任昉比照“三君”,说明时人将其视为士族领袖。以任昉为中心的“兰台聚”“龙门之游”,一度振兴了久已沉寂了的士族交游界;若此风延续,则以某一特定士人为领袖的士族交游圈或将形成,东晋时期活力十足的士族文化或将重现。然而,任昉担任御史中丞大约两年后,转为秘书监,不久出为新安太守,次年卒于任上。徐摛因为创作宫体诗影响萧纲的名声,〔13〕被梁武帝外放为新安太守,武帝谓之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卧治此郡。”〔1〕从武帝的话来看,新安太守事务不多,且有大好山水,似为优遇之职;然而,徐摛实际上是因事被外放,出为新安太守并非乐意为之。任昉之出为新安太守,或许亦有隐情。
如前所述,萧衍称帝以后,有意加强在政治、文学上的控制力,欲在政治、文化两方面称尊。任昉凭借之前的名声和奖掖后进的热心,一度成为文坛领袖,在士族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曹道衡先生认为,任昉出为新安太守是因为他“并无做官的才能”。〔14〕然而其后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梁武帝有意将其黜出京师文坛,维持皇权独尊的文坛地位。任昉在新安太守任上,作《落日泛舟东溪诗》,诗曰:
黝黝桑柘繁,芃芃麻麦盛。交柯溪易阴,反景澄馀映。吾生虽有待,乐天庶知命。不学梁甫吟,唯识沧浪咏。田荒我有役,秩满余谢病。〔15〕
此诗前四句写东溪美景,五、六句表达乐天知命的想法,自我安慰。后两句用典:诸葛亮高卧隆中时,好为《梁甫吟》,有见用之冀;“沧浪咏”见于《孟子·离娄》,为孺子之歌,《楚辞》中渔父歌之,遂有隐逸之意。“不学梁甫吟,唯识沧浪咏”二句,表达任昉不求见用,安心隐逸的心境。结尾两句更显悲观,即秩满之后谢病辞官,不再出仕。此诗表达的不是老、庄那种超然物外的隐逸之情,背后潜藏的是强烈仕进之意破灭之后心如死灰的自我喟叹。“我有役”“余谢病”二句连续喷出,乃是作者表达自我圆满、不求于外的决心。“外”指的是谁呢?其实是梁武帝。结尾两句看似任昉抒发自己期望隐逸的心理,实际上隐藏着对梁武帝的强烈不满,甚至不妨视为一种挑战。史称任昉“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辞讼者,就路决焉。为政清省,吏民便之”。〔1〕然而这种不理郡事、颇为颓唐的形象,不正与《落日泛舟东溪诗》表达的意志类似么?任昉离开建康后,“兰台聚”自然解体,京师后进亦不必“宗之”,昔日文坛领袖的风光一时落寞。至任昉死后,其子乃至“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下场可谓凄凉。关于刘峻《广绝交论》一文的讽刺对象及用意,历来颇多异见。有学者认为,刘峻借到洽兄弟为幌子,实际上是“抓住萧衍有负旧友一点作文暗讽”;〔16〕也有人认为,此文并非针对到氏兄弟,而是针砭“齐梁时期的炎凉世风”。〔17〕《广绝交论》讽刺的是受任昉恩惠而不回报其子嗣之人,到洽等人难辞其咎;然而,此文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任昉昔日旧友亦未曾接济其子。梁武帝身为一国之君,最有能力提携任昉子嗣,竟亦无任何举动。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来看,任昉子嗣沉沦不显,都与梁武帝的意志有关。任昉离开建康后,昔日盛极一时的士族交游圈一度冷清;至其死后,陈郡殷芸与到溉书曰:“哲人云亡,仪表长谢。元龟何寄,指南何托?”〔1〕以文坛领袖为中心的士族交游圈不复存在了。稍后不久,梁武帝诸子渐长,皇子府的地位大大提升(反映于十八班制中),以皇子(包括太子)为中心的交游圈再度形成,皇族夺得了士林、文坛的主导权,梁代皇子文学集团因此大盛。在这一过程当中,任昉既是显赫一时的功臣,也是一名牺牲者,而其后则体现了梁武帝隐秘的意志。
三、参与“兰台聚”者的身份及新的贵族主义
参与“兰台聚”之人为: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彭城到溉、到洽,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这些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没落或门第较低的北方士族(陈郡殷芸,沛国刘显);(二)刘宋以来凭借军功起家,其后转向文化家族者(彭城刘氏、到氏);(三)沉寂已久的东南士族(吴郡陆倕、张率)。这些家族在门阀贵族时代,在政治、社会上的建树会受到很大影响。晋宋之时,门第的界限非常严格,高门占据政治、文化的顶端,不屑与低等士族交往。至南齐时,社会风气稍变,低等士族以文化为资本,逐渐走向政治、社会中心。《南史》在述及任昉交游圈时,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即“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2〕“贵公子孙”指的就是高门贵族子弟,也就是说原本门第是决定交游的首要因素,而此时门第的作用减弱,首要的是文化尤其是文学。这一变化实关乎东晋南朝政治社会之大变,即传统以门第为标准的贵族制经过宋齐时的发展,在梁代出现了新的贵族主义。梁代文学之发展、兴盛,实与这一变化紧密相关。
梁代贵族制的变化,首先与武帝的意志有关。旧的贵族主义主要以门第为衡量标准,出生在高门之家,便可称为贵族。与此相应,贵族的起家官、升迁途径皆有一定程式,甚至有些官职专由贵族担任。梁武帝的改革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承认贵族门第的作用,但要求其具备与贵族身份相对应的才能;其二,选任某一官职的标准不是门第,而是担任者的实际才能。第一点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梁武帝即位后,十分重视教育。天监四年,开五馆引进寒门人士;七年下诏“大启痒斅,博延胄子”,令“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入学就业。且将学业与仕宦相联系,下令“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1〕如此则自宗室至高门贵族,皆热心向学,门第之外,人才(学术)成为重要的因素。第二点主要体现在梁武帝的用人观念上。太子洗马为尤清之职,梁前皆用甲族有才望者,武帝以庾於陵、周舍为太子洗马,并宣言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1〕也就是说,官职的清浊不取决于门第高下,而决定于担任这一职位者的才能。这一观念与旧有的贵族主义是不相符合的。又,武帝以张率为秘书丞,谓之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1〕武帝打破了旧的用人模式,实际上也就是破除了旧的贵族主义,提倡一种以才能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新的贵族主义。
此处以彭城刘孝绰为例,略作说明。彭城刘氏崛起于刘勔,其父、祖并为郡守,门第不显。刘勔在宋时以军事立功,明帝临崩时,以其为守尚书右仆射、中领军,成为左右政局的关键人物之一。刘勔死于宋末战乱,其子悛在宋齐革命中投靠萧齐,且与萧赜关系密切;悛弟绘历任萧道成、萧嶷参军,亦党同萧氏。因此,刘悛、绘兄弟在南齐权位转重,而刘绘又以文义见长,成为当时的后进领袖。孝绰即刘绘之子,年幼时善属文,当时号为神童。“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1〕当时的社会风气一般是后进造请前辈,而沈约等人竟然造访年幼的刘孝绰,可见其才名之大。诸人之中,任昉尤其赏好刘孝绰,天监初,孝绰为《归沐诗》以赠昉,任昉回诗大加劝勉。武帝令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得引见。“尝侍宴,于坐作诗七首,武帝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1〕孝绰得预宴幸,很可能是沈约、任昉称之于武帝。武帝嗟赏其文,竟使刘孝绰“朝野改观”,这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也就是说,刘孝绰以文学才能受到了武帝的独特赞誉,在士族当中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朝野改观”,说明一种新的因素受到了社会的关注,那就是文学才能及其所起到的作用。此后,刘孝绰转为秘书丞,如前已述,秘书丞为天下清官,一般只由高门贵族担任。武帝谓周舍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1〕说明武帝用人不仅考虑门第,更注重个人才能,另外说明刘孝绰极得武帝赏识。此后孝绰转为太子宫僚,时东宫人才济济,而昭明太子尤重王筠、刘孝绰二人,“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1〕王筠门第高而刘孝绰门第低,但二人之所以得幸于太子,与门第无关,而是由于二人文才超常。刘孝绰等人以文学才能得到梁武帝、昭明太子的赏誉,担任以前仅由高门贵族独占的部分清职,成为众人欣羡的对象,表明一种新的贵族主义出现。
刘孝绰仅为一例,到溉、张率等人莫不因此致贵,“兰台聚”实际上拉开了梁代新贵族主义的序幕。这些次等士族在门阀政治时代本无出头之日,经过齐梁之发展尤其是梁武帝的大力革新,得以由政坛前辈、文坛领袖荐之于上。武帝对这类文士大加称赏、破格拔擢,在政治、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气,亦即新的贵族主义。而这种贵族主义得之于皇权,缺少旧贵族所具有的“自律性”,天生表现出对皇权的臣服。梁武帝试图“突破传统‘社会贵族主义’之限制,建立以君权为主的‘国家贵族主义’”。〔18〕《南史》称兰台聚“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实际上,贵公子孙亦“不须预”,因为贵族门第的作用还在。然而仅仅依靠贵族门第,已被抛弃于梁代新贵族潮流之外。王筠与诸儿书,夸耀的不再是其门第高贵,而是七叶之中“人人有集”,〔1〕即文学才能,这反映了旧贵族向新贵族主义靠拢的倾向。梁代文士之多、文学创作之盛,应当结合这一皇权主导下的新贵族主义来理解。
总之,梁武帝致力于改革贵族主义,在门第之外,强调个人才能的重要性。参与“兰台聚”者门第较低,在梁武帝的统治思想下,凭借文史之才得到皇帝赏誉,出任清要之职,形成一种新的贵族主义。梁代文士之多、文学创作之盛,当结合这一政治、社会变化来理解。另外,皇帝从士族领袖手中夺回文坛盟主的位置,成为政坛与文坛的最高统治、评判者;皇子作为皇权的延续,在地方上统治士族文人,从而形成皇子文学集团,梁代文学的整体结构大致形成。因此,梁代文人从骨子里皆臣服于皇权,皇帝也给予优厚的政治回报,梁代文学因此大盛。然而正因为如此,梁代文人缺乏个人独立性,文学个性不足,纵使千诗百赋,其面如一。这是梁代文人之大幸,同时也是梁代文学之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