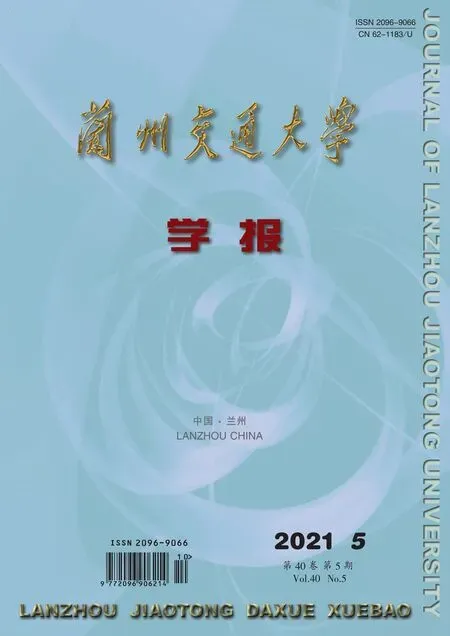超脱的倾情书写
——论民间审美视野下的《生死场》
荣斯柔,潘黎勇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3)
《生死场》是萧红创作初期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作品,完成于一九三四年九月,由鲁迅为之作《序言》,胡风为之作《读后记》,并且与叶紫的《丰收》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作为《奴隶丛书》系列而一同出版,问世于上海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文坛。
萧红是沿着鲁迅的创作之路前行的,虽说她坚持站在启蒙的立场上去揭露民间生活的愚昧、落后和野蛮,然而展示出的却是透露着原始之气的生命。所以,冯骥才说:“生命之美是民间审美的第一要素。”民间审美是建立在民间文化这个“源”的基础之上,具有自发性,这种“自发”直接来自生命本身,具有生命的本质。民间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体系,包括审美语言、审美方式与审美习惯。民间审美视野作为一种视域角度,从审美视角出发突出表现民间特色。而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风格是指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相区分。审美视野中的民间特色和文学中的现实性可以等同,二者都是对某一特定场域中特色的强调。所以在这种独特的民间审美视角下审视萧红的《生死场》,生命一方面展现的是鲜活的、激情的、生动的,是充满着原始之气的,另一方面更独特地展现了生命的本真。亦即陈思和所言:“《生死场》写得很残酷,都是带血带毛的东西,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冲撞、在呼喊。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才真是珍品!她的生命力是在一种压不住的情况下迸发出来的,就像尼采说的‘血写的文学’”。
一、生的艰辛与挣扎
人之所以得以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着生命的活力。《生死场》中写到:在乡村生活的人们永远不知道,永远无法体验灵魂,他们只是用现实中存在的物质来充实他们。第十三章写到了二里半,人们因为抗日要杀二里半的羊来进行宣誓,可是二里半却舍不得,最终找了一只鸡来代替这只羊。我们可以想到这只羊对于这些人而言只是一只普通的羊,但对于二里半而言,却是他的“灵魂伴侣”,是他情感的依托。所以他才找了一只公鸡代替山羊,随后他牵着自己的山羊回家去了。可以说这是一幕对于生存之道非常细腻的描写,其间充斥着人和动物的特殊感情。在乡村的民间社会中,劳动人民所看重、所在意的仅仅是自己能否生存下去,这个是居于第一位的。或许我们因此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国民落后性的深刻展现,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不是一种朴实真诚的实用主义的独特展示呢?他们关注的首先是自己的生存空间,联系到的是自己的实际生存之道。同样的对于二里半来说,他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在这个动乱不堪的时代中生存下去,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生存。这种念头就是民间的生存法则,因为只有人能够活着,有生命力,才会有力量去实现别的东西。可以说在民间生活着的人们,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也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的生存看的比其他都重要。
在第二章《菜圃》中写到:发育完全的青年汉子,带着姑娘,像猎犬带着捕捉到的猎物似的,走下高粱地去……这是对月英和成业第一次结合的描写。这些原始而放肆优美的习俗在这里持续着,又在这里一圈又一圈轮回着。在后面作者又写到:“我知道给男人做老婆是坏事,可是你叔叔,他从河沿把我拉到马房去,在马房里,我什么都完啦!”在其间他们或许会想到道德的束缚,但是在生存之道的选择之下,道德似乎已经不再是约束人行为的绳索。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诉说着生的艰辛。生之所以为生,就是要为生命不断注入鲜活的生命力,来维持生命的基本特征。这种场景我们依稀可以在《诗经》中找到相似之处,很早之前的先民们也在用相似的方式做着类似的事。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诉说生的本能,这或许已经变成这个古老民族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在这种充满原始之气的生命历程中,展示的是他们充满了粗犷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尽情释放着生命的能量。无论是受古老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还是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展现出的都是一种自然的美。这种古老而优美传统一直在轮回着,轮回着生,轮回着死,轮回着独特的结合。这是一种放肆而狂荡的原始生命之美,这更是一种生命充沛之美的象征,这是一种在原始力量涌动中的一种动态之美。
第三章《老马走进屠场》中又写到:王婆回过头来,马走在后面;马什么也不知道,仍想回家。这是一个充满感情的场面描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婆对于他所爱的马有太多的不舍。因为她和马已经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她此时此刻对于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人与马的关系,而是给它赋予了人的些许性格,将其人格化、人物化、感情化。而这种感情是基于马陪着她走过了无数个春秋,可是她为了能够生存,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它卖掉。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死场》中萧红把自身童年时代的生活体验和对大自然特殊生命力的独特感悟融入到个人创作之中,通过动植物的一些特征来展示人身上类似特征,或是通过它来表现人的生存际遇。这种人与动物间深沉的感情,是来自于生命的本原,是穿透种种文明的遮蔽,抛开贫穷、卑琐、愚昧的人生不堪。人跟土地、跟生命的原始状态,是一种原始生命活力勃然喷发,是人不同于动物的丰厚、细腻的情感流淌。这种“爱”更是一种单纯而无私的美,是一种源于自然的对一切生命的坦诚相待。在这个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村子里却出现了一种淳朴而真诚的爱,一种展示人和动物之间恋恋不舍的真情之美。
我们可以看到,在萧红的笔下,农民首先是对于土地、对于动物的热爱之情。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半为了找羊变得如同发疯一样。我们也能看到王婆牵马上屠宰场那种依依不舍的沉重复杂之情。这所展现的并非简单的人与动物的感情,更是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因为土地养育了他们,他们把土地作为自己的对于动物的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一种超越生命本质的一种原始的发自本能的热情。我们或许可以说,在那个年代,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相似性体现出一种很原始的生存状态,看似无能为力,却也包含着对人生和命运的反思与抗争。生活永远都是这样,贯穿着一个无法改变的选择,那就是弱肉强食。尽管有着再多的不舍与爱,那也是徒劳的,在一个基本物质生活都得不到满足的时代,不可能要人放弃物质上的需要而去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孔颖达在研究《诗经·七月》曾说:“民之大命,在温与饱,八章所陈,皆论衣服饮食”。人的生存之道高于一切,也许这便是萧红写这篇作品的主旨吧!
二、活的自然与和谐
和谐是一种生活的最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且展现在人与物之间的无限亲近上。《生死场》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展现的却是一幅富有诗意的田园生活图景。在小说的开头,萧红便写到: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树根。用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开始写生命的自然之美,有孩子在捉蝴蝶,有太阳普照大地,有高蓝的天空,有碧绿的菜田。这可以说是一幅浓缩了的乡村农家自然生活景致,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所有的人和物都在最自然的状态下镇定自若的生活场景。《礼记·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者谓之和。”我国古代的传统认为人是天地的主宰,人的情感如果都能够得到恰当的控制,世间的万事万物的秩序也能因此得到保证。这反映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和谐之美。《论语·八佾》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孔子看来,文学艺术中表现的感情要受到理性的制约,追求理性与感性的融合,讲究中庸、适度、平和的原则,不能过于泛滥,这表达的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而萧红究其一生是颠沛流离的,在经历了早年失家、病痛折磨与爱情创伤之后,她开始对人生世相呈现出了一种消极悲观的认识,幽深孤独的内心世界使她的文字抒写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苍凉孤寂的格调,写人运的不幸与生存的艰辛。但是她也并不总是竭力暴露痛苦,而是以一种平静淡泊的笔调,舒缓自如的节奏,在文字间呈现出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美。
《生死场》不仅仅让我们一饱眼福人与动物的和谐,同时也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生死场》第一节《麦场》和第二节《菜圃》中,就生动展示了农业在乡村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作者的笔下蔬菜和谷子在乡村人的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它是生活在下层的劳动者的生命之本。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离开了土地与农业,那也就如同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法则,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文中麻面婆把麦粒看得比孩子还重要,金枝的娘把菜棵看得比女儿还重要。第三章《老马走进屠场》、第五章《羊群》所着力描写的都是老马和羊群,它们都是作为乡民们生活的必须品,而乡民将其视作命根子一样看待。萧红对于这样的生活是非常了解的。她在这部小说中没有将人物作为故事的中心,因为在萧红看来,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不仅仅只有人类,人物并非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人物是做不了主人的。《生死场》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由自然主宰的自然王国,在萧红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只有月份,却没有年份。如果说年份仅仅是指向人文的,那么月份则是指向自然的。对于那些生活在乡下的村民而言,他们是无法听见历史前进的脚步声的。他们所看见的只是季节的轮回和转换,他们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停滞的,十年如一日,甚至千百年也没有多大变化。我们可以在《生死场》中看到的他们,与《诗经·七月》中表现的农村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三、死的从容与淡定
《生死场》中,作者描写了大量的富有哲学色彩的死亡。死亡是一种归宿,一切事物都是从生开始,然后渐渐走向死亡,死亡的存在说明了生命存在的弥足珍贵。小说中描写的村里最美姑娘月英的死,就诉说着一种死的恐怖与淡然。月英患了瘫病,在十二月的寒冬,夜夜听见她那歇斯底里的呐喊。三天以后,人们把她葬在了荒山脚下。《罪恶的五月节》一章中写老王婆的服毒自杀,可怕的死亡之气紧逼着王婆,人们把棺材准备好并且掘坑的铲子也不再翻扬,当一切准备就绪时王婆却大吼了两声从嘴角吐出了一些黑血,在人们不知所措地喊着死尸还魂的同时,他的丈夫赵三用自己手中的扁担刀一般地切在王婆腰间,弄了一身血。王婆被视为死尸般地被最亲近的人蹂躏着如虫蚁,如草芥,即将被抛入另一个冰冷的世界。大家都觉得她必死无疑了,然而就在快要钉棺材盖的时候,她说了句“我要喝水”,又活过来了。或许读者可以理解为赵三用扁担压王婆的时候把肚子里的毒素清除了,但对于垂死挣扎中的人来说,显现的是顽强而坚忍的生命力,在生与死的较量中勃然喷发,生命最本质的一股力量显露出来,震撼着人的心灵。当王婆的女儿冯丫头因为当胡子的哥哥死了,生活无所着落而回来投奔父母,看到垂死的母亲时,“一阵清脆的泰裂的声浪嘶叫开来。”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灵魂的呐喊,是一种原始生命本能的母女之情的迸发,这种哭喊带着一种埋藏于心灵深处的力量穿透了大地与山林。这种哭与女性常有的哀哭是绝然不同的,她展示给人的更多的是一种生命呐喊的力量。
“死人死了!活人算计着怎样活下去。在这里,冬季的女人们准备夏季的衣裳,男人们考虑明年的耕种”。尽管这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他们依然在死亡的气息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人的眼里,死亡似乎变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在他们的眼中生是一种从容的姿态,死又何尝不是呢?《罪恶的五月节》一章中写到,这里时刻都充斥着死亡的气息,这种死亡的气息让人觉得可怕,让人觉得悲凉,更让人觉得淡定。这正如胡风在《生死场·读后记》中所说到的一样:“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了粮食,养出了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在这种独特的生存环境中,人们世世代代繁衍着,在痛苦的生命面纱之下却涌动着原始生命的活力。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自古以来,生存与死亡总是相伴而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作者笔下的乡村,人和动物们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死亡是无可逃避的,但对于死亡的态度展现的却是对待生命的尊重与敬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虽然说这种气息有点压抑,但是这种死亡之气所展示的却是一种近似从容的、淡定的、泰然自若的、毫不吝惜的一种状态。萧红笔下这些在乡间生活的乡民们更多的是保留了自然的原始特性,而这种自然原始特性更多的表现在乡民们对待生与死的冷漠与漠视。在他们的眼中,死亡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死亡就如同出生一样,是一种对于大自然的自然回归。
整部《生死场》似乎给我们所呈现的只有生与死,而且生与死似乎都在一直轮回着,都在循环往复。也许人们大都会觉得死亡是最无意义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而且它吞噬掉了人之所以得以生存的根本意义。但是,在乡间生活的人们始终明白一个道理,人之生必然相伴于死,每个人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便开始步入了走向死亡的旅途,从生到死仅仅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所以他们在生的过程中体验着死亡,沉思着死亡。可见在他们这里“死”的存在并不会使“生”毫无意义,而是更凸显出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对于“死”有更深入的探索,才会懂得“生”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萧红对于人生的理解与探索,更多地集中在她对农民命运以及他们生存方式的深切关注之中。她对于乡间生存的人们,给予的不是只看到他们的愚昧与落后,而是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与同情,这或许源于她对于乡间民众的特殊之情吧!
四、结语
通过对萧红作品的民间视野之下审美意蕴的发掘,让我们得以深入地挖掘出萧红作品民间视野之下的审美特质,也让我们不得不欣羡这位天才女作家感受美与抒写美的创作才能,指引着我们在理解美与感受美的路途中找寻到艺术的魅力。从作品的内涵角度来说,其作品中积淀的民间视野之下的审美意蕴,是她面对生命的苦难亦或是面对生活的苦难,并没有沉浸于生活的“苦汁”中而就此沉沦,而是审视、领悟、感受人性中光辉的一面。她的一生虽然遭际坎坷,但她却始终能以一种审美化的人生态度看待生活。她终其一生追寻着属于女性的自由天空,始终坚持独立写作,为弱者发声,追求文学超越阶级性的美学理念。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