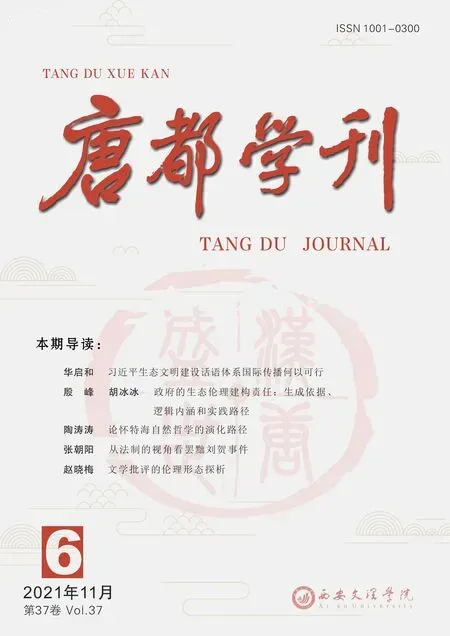从贽见礼等级序列辨析《左传》昭公四年“竖牛”的身份
黄文慧
(高雄师范大学 经学研究所,台湾 高雄 802311)
《左传》昭公四年的“竖牛”是鲁国史上家臣叛主事例的要角之一,历代注疏从杜预《春秋释例》以降皆载“庚宗妇人”为“叔孙豹外妻,生竖牛”,“竖牛”为“叔孙豹子、氏叔仲”[1],及其昭公五年注曰:“昭子不知竖牛饿杀其父” ,至此以降多半认为“竖牛”即叔孙豹早年奔齐过庚宗之地所留下的私生子。又叔孙豹奔齐回归鲁国的时间点并未见载,因此注疏家们同时也利用“竖牛”作为“竖”的这个身份所对应的年龄,来推测叔孙豹归鲁的时间点。笔者因而发现,在注疏家历代承衍“竖牛”作为“竖”这个身份理解的基础上,可以对“竖牛”此人本身的身份细节作进一步探究。而其中关于“奉雉”的部分,与贽见礼的等级序列相关,笔者希望藉由先秦社会礼制习俗的角度对“竖牛”的身份进行辨析,再回顾此身份对文本解释作用的意义。以下先将《左传》昭公四年“竖牛”的原文附上,再分析讨论:“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适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鲁人召之,不告而归。既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政。”[2]
一、妇人献雉
首先关注注疏家如何推断庚宗妇人与叔孙豹的关系?成公十六年叔孙豹避侨如之祸奔齐,过庚宗遇妇人,妇人私为食而宿焉,并哭着送别了他,在这个故事背景下,于是有了认为竖牛就是叔孙之子的可能。但仅就这个文献描述的背景还是有不明确之处,可以再思考。
庚宗之地乃今日山东泗水县东南,据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春秋齐鲁的部分(1)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再配合山东地形图来看,北面以西都是小山地丘陵,以东有一连串的湖泽地带,而庚宗就位在一连串山东丘陵中尼山与蒙山所夹的廊道之间,就春秋鲁国的政区地理而言,即是曲阜以东、廊道北口与季氏平邑之间。叔孙豹无论从曲阜或是叔孙采邑郈奔齐皆需经此廊道而往,据邑而叛的鲁国家臣们,如竖牛本人、郈马正侯犯,尤其以廊道南口为主的费邑家臣,如南蒯、公山不狃,皆从此奔齐。《左传》成公十六年传:“召叔孙豹于齐而立之”,杜预注:“近此七月,声伯使豹请逆于晋,闻鲁人将讨侨如,豹乃辟其难,先奔齐。”再对应“使私为食而宿焉”,可以了解到这一次叔孙豹的出奔是避难,而庚宗是必由之路。临时求助于一位妇人而暂有食宿安顿是有可能的。但如文献所言,这暂时的食宿应该不会太久,临时收留个人,妇人问其详,也是人之常情,哭而送之,则有很多种情感上的可能。叔孙豹据史书所记是一位知礼并有抱负,拥有外交政治才华的人,“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应是妇人得知了叔孙豹的处境,或欣赏或生男女之情,才会在其离去时泪别,也不尽然要有男女之实。
其次,叔孙过庚宗时应有一定的年纪,《左传》文公十一年传,叔孙得臣“败敌于咸,获长敌侨如。……以命宣伯”,杜预注:“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侨如,以旌其功。”又从《正义》中可知道叔孙得臣有三个儿子侨如、虺、豹,并说明三子未必同年,也可能事后才出生。《礼记·曲礼下》载:“子于父母,则自名也”,郑玄注:“名,为父母所为也。”[3]假使文公十一年为叔孙侨如出生的下限,而成公十六年侨如为祸,叔孙豹奔齐,这年叔孙侨如应至少有40岁了,那么叔孙豹也应有差不多30岁的年纪,正好符合《周礼·地官司徒·媒氏》所载“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4](2)参见孙晓春《周代婚年辨析》,载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适齐时取了嫡妻生嫡子孟丙,是有礼可循,知叔孙豹从礼如善,如其德性有所偏差,《左传》作为史家者言,应有所指出。
再次,何谓“妇人”。《礼记·曲礼下》载“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 ,庶人曰‘妻’”,对应《左传》桓公十五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此“妇人”所指即为雍纠的妻子雍姬。又《国语·晋语六》:“大其私昵而益妇人田”,韦昭注曰“妇人,爱妾也”[5]。《论语·泰伯》:“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6]又《说文》:“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段注:“妇主服事人者也。大戴礼本命曰: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7]可见“妇人”于先秦而言,是已嫁做人妇、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并且掌管家中职事的女子。依此,与叔孙豹不应有男女之实。
由上可见,庚宗妇人见叔孙豹“献以雉”。《礼记·曲礼下》记载:“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童子委挚而退。野外军中无挚,以缨、拾、矢可也。妇人之挚,椇、榛、脯、脩、枣、栗。”妇人献雉明显不合礼仪文献之记载。然根据上述对“妇人”的了解,结合《左传》这段记载可以解读为,妇人有其职能,而其子竖牛长亦能执事,知叔孙豹之善于为政,又立于叔孙氏,故而前来投靠为臣。
晁福林先生对于春秋委质之研究有提及,“春秋后期,随着士的兴起,委质为臣成为一种风气。”[8]《孟子·滕文公下》:“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8]又《礼记·郊特牲》载:“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故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又《礼记·杂记上》载:“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以上可以推知庚宗妇人之丈夫身份级别为士,竖牛从其父,故而用雉。此处妇人献雉,当结合后面“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也就是母亲带着孩子与礼物上门求职,而主要求职者为竖牛,故而献雉。
二、子长能奉雉
要探讨竖牛的身份,需要先厘清竖牛的年纪与叔孙豹去齐归鲁的时间是不是有必然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看到《左传》成公十六年“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孔疏曰:“此时七月也,至十月而侨如奔齐。……乃云宣伯奔齐,穆子馈之,则似豹在其多年,侨如始往,故服虔以为叔孙豹先在齐矣,……杜不然者,若豹以前在齐,则非复鲁臣,……今传言声伯使豹,明在鲁军,得为声伯使耳。……二子之生,必在侨如奔后。豹之还鲁,虽无归年,而襄二年始见于经,竖牛已能奉雉,故杜以为此年去,彼年归。”可以看出在孔疏之前有两种看法:其一是服虔认为叔孙豹奔齐,在成公十六年以前甚至数年;其二是杜预提出叔孙豹出奔于成公十六年,透过叔孙豹与竖牛之间亲子关系的认定,推断其归鲁于襄公二年。
据《左传》昭公四年载“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杜注:“襄二年,竖牛五六岁。”孔疏曰:“穆子还鲁,传无归岁。襄二年始见于经,疑是其年新还也。……成十六年出奔,襄二年始还,凡经五年,故竖牛五六岁,能奉雉也。计竖牛至襄二年,四岁也。杜言‘五六岁’者,竖牛见穆子,未必即以还年见之。”成公十六年孔疏显然是据昭公四年的杜注进一步阐释,然而,孔颖达跟从杜预肯定两者的亲子关系之外,还需考虑竖牛未必在叔孙豹归鲁当年上门拜访。综此二注疏可知,其一因叔孙豹归鲁时间不定,于是有了竖牛为叔孙子的可能解释的产生;其二确实竖牛之长,未必与叔孙归有必然的关系。
在注疏之外,可以看到《韩非子·内储说上》有关于“竖牛”的记载,其言:“叔孙相鲁,贵而主断。其所爱者曰竖牛,亦擅用叔孙之令。叔孙有子曰壬,竖牛妒而欲杀之”[9],在韩非子看来,并不认为竖牛是叔孙豹之子,“有子曰壬”说明竖牛与叔孙嫡出第二子仲壬并无兄弟关系。又联系前面孔疏所引之服虔,似乎也没有特别提及这方面的论述,或为杜预以后方有之。
对应到昭公四年,在叔孙豹问其姓号其名,之后用其为竖,“有宠,长使为政”,杜注:“为家政”,然而无论家政或外政,在先秦的礼制中应具有一定的年纪,《礼记·冠义》:“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江美华先生有相关研究认为:“《仪礼》记载士礼多项,篇首为《士冠礼》,因冠礼乃成人之始,通过冠礼后,加冠的年轻士人始成为宗法社会接受的‘成人’。”[10]在此连结庚宗妇人奉雉,又谓其子长能从而奉雉,也就是说庚宗妇人遇叔孙时竖牛尚未成人,过庚宗只言遇妇人,妇人又有幼子,可见此妇人为士之寡妇,知叔孙豹之才,为其子往后谋得一职。
如果依照杜预注:“襄二年,竖牛五六岁。”那么可以推断,昭公四年竖牛饿杀叔孙豹时,已经近四十岁了。其所职掌有类《礼记·文王世子》载:“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此处“内竖之御者”,与竖牛职权上非常相似。而前面也提及孔颖达认为竖牛在哪一年见叔孙豹未知,如果不把竖牛作为叔孙豹子看待,昭公四年的竖牛一定比杜预所预测的年纪更大一些,担任“内竖之御者”,又长于叔孙豹嫡子数岁,让自身的权力来到高峰,非常有可能。因此笔者更倾向判断庚宗妇人带竖牛见叔孙时,竖牛已经成年。
而关于士级别的见面礼,《仪礼·士相见礼》:“始见于君,执挚,至下,容弥蹙。庶人见于君,不为容,进退走。士大夫则奠挚,再拜稽首,君答壹拜。”[11]杨宽先生在谈及贽见礼时,“如果是小辈初次见长辈,臣下初次见君上,则将‘贽’安放在地上不亲授,即所谓‘奠挚’以表示身份低下。”[12]另有《礼记·曲礼下》:“童子委挚而退”,郑玄注:“挚之言至也。……童子委挚而退,不与成人为礼也。”《正义》曰:“童子见先生,或寻朋友,既未成人,不敢与主人相授受拜伉之仪,但奠委其挚于地而自退避之。”可以从此二种进而讨论竖牛的动作“奉雉”。
上述提及的还有“奠”“委”,不妨先看看这三者的区别。首先《说文》:“奉,承也。”[13]古文字看来像两手捧玉状。而“奠”,《说文》:“奠,置祭也。”在甲骨文中作此形“”,像酒尊置于地上,可以想见我们在扫墓时将祭品放置于坟头前的空地上,也如同传统祭祀土地神。往后金文的演变,字形上有了改变,作“”“”,已经不是单纯放在地上而是有一块丌案,有一定物质文化上的转变,同时也影响人与人之间交往礼仪的转变(3)参见李圃《古文字诂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35页。。“委”,《说文》:“委,委随也”,其同时也有放置的意思,例如《战国策·燕策三》载:“是以委肉当饿虎之蹊,祸必不振矣。”[14]因此,从上述看来,这些动作是有所差异的,“奉”是双手亲自捧交,而“奠”“委”是为了显其卑而间接奉上。可以更确认地说,庚宗妇人带竖牛见叔孙豹时,用的是成人礼,并且是以士这样的身份级别前往。
而竖牛所奉的“雉”,有相关学者研究(4)参见宋洁、陈戍国《士婚礼用雁问题及上古家、野禽之分野考论》,载于《求索》2014年第2期;在此篇文章之前,有李衡眉《古代婚礼执雁新解》,载于《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胡新生《〈仪礼·士昏礼〉用雁问题新证》,载于《文史哲》2007年第1期。,“雉”虽然在文献中通做野鸡之说,但也不能说一定是野生的,还需要考虑每个词汇在每一时代的流转过程,也许这些禽类最早是野物未被驯化,但是在人类最早农耕畜牧的社会里也是一个递进过程。礼书之所以记载贽见礼的级别,也是为了表明不同身份的人,会对应着不同的经济能力。
由此,笔者对于竖牛“奉雉”提出两种思路:其一,竖牛“奉雉”加上庚宗妇人献雉,妇人从其夫,无夫则从子,然无论从夫从子,都显示其父子对应的身份地位,即为礼书所载的“士”。其二,从上述学者研究来看,家禽比野物可能更好,也许有一种可能即是,当时有身份地位的人有相应的家产田邑,对他人拜访可以从家中直接取用,而身份越低下的人,则没有私产,要想拜访别人,尤其拜访有身份地位的人,总不能空手,只能去野外取些野物来。因此,若“雉”作家禽,那么竖牛拥有的身份应该高一些,透过贽见礼的级别,可知竖牛有“士”一级的可能。
三、未问其名而号之
从上面两点分析,笔者倾向庚宗妇人与其子竖牛,应该算“士”一级别的人家。但还是要回归问题的原初,究竟竖牛是不是叔孙豹的私生,如此叔孙豹与竖牛的互动是不是有迹可循?在庚宗妇人献雉时,“问其姓”,见竖牛如梦中救命之人,则“未问其名,号之曰:‘牛’”,竖牛也马上“曰:‘唯’” 。也就是叔孙豹未问竖牛之名,而直接给予名字。此处可以参见日本尾形勇的著作(5)参见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9-140页。,称名于先秦有其特别意义。在不同身份相应之下,会有不同的应答。
《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而冠,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郑注:“对至尊,无大小皆相名。”又前面曾提及的《礼记·曲礼下》载:“子于父母,则自名也”,郑玄注:“名,为父母所为也。”如依照前述推论,叔孙豹若非竖牛之父,如何能为竖牛起名?依据尾形勇的理解,称名的意义在于名是父母所起,因此不能随便使用。而笔者据此进一步理解,在《左传》中称名的例子确实非常地少,而男子二十而冠并且有字,也就是说当一名孩童成长为大人,要参与的公众事务渐多,而名为父母所予,并不能随意使用。这个疑点,或可以从先秦策名之俗进行理解,郭政凯先生对委质称臣进行研究时(6)参见郭政凯《“委质为巨”仪式初探》,载于《史学集刊》1987年第3期。,引用了唐嘉弘先生的推测(7)参见唐嘉弘《试谈周王和楚君的关系——读周原甲骨“楚子来告”札记》,载于《文物》1985年第7期。,认为委质为臣的制度可能与收养习俗有关,在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或技术能力受血缘关系束缚,因此通过收养习俗来确认被收养人向收养人的家族绝对效忠,这是突破血缘关系扩大统治基础的一项作法。如同朱凤瀚先生认为异姓家臣与宗主之间需要存在拟制的亲族关系(8)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型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而关于策名制度,即是入职于某处或效忠于某人时,记载于名册,如今日之户籍,而收养之俗正连结了这两项要素,职务上的需求与纳入血缘体系的忠诚。
如此,进一步演绎,这场委质称臣的仪式中,叔孙豹对竖牛进行了赐名。赐名的研究,黄修明先生指出:“与姓氏赐予的情况相比较,无论哪一种形式或类型的赐名,都具有如下一些与赐姓完全不同的显著特征。”[15]赐姓可以针对多人甚至受赐者家族,然而赐名往往针对受赐者本人,名有其专指,通常具体指其人品行为、个人特殊表现,甚者为君主主观寄意,竖牛的情况即属于此类。
近年来,曹大志先生对于商周族徽研究(9)参见曹大志《“族徽”内涵与商代的国家结构》,载于《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认为族徽为亲属职衔称谓,出现的形式为称谓加私名,或连续二至三个称谓后再加私名,有些甚至只有称谓,这个现象主要由于商文化的形式更趋向职能性的分工,因此在受命官员上,更在乎职称大于私名,而一个人在社会中表达自己的身份地位时,职衔也相对重要。周朝有周人不用族徽一说,这是随着铜器铸造技术的下传,加上贵族阶层的壮大,私名渐能表达个人身份地位,故而族徽标志意义衰弱。而在先秦策名的意义也着重在职能,所以可以看到在先秦职位相对较低,身份上不如贵族可以以其名立于社会者,仍然承袭用职称加上私名。竖牛之称即属于此类。
总之,透过贽见礼中的士相见礼与童子之礼相比较,可以确认竖牛本身应是承继士身份的年轻人。另外,叔孙豹与竖牛的整个互动,即是策名的一个过程。从以上两点,再回归“问其姓”,杜注:“问有子否”。后世注疏也从此说,如杨伯峻注曰:“古礼,士执雉,此妇人献雉,示其有子矣,故穆子问其子。”从妇人执雉的角度肯定了叔孙豹之问姓,即问其子,以下更提出几则姓即子的考证。《左传》中“姓”有其多样的内涵与社会功能(10)参见王学凯,王寒《〈左传〉中姓、氏来源及其文化內涵与社会功能》,载于《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问其姓”针对庚宗妇人本身也应该是可以的,先秦的女性之名,往往是丈夫氏名或国名,加女子母族之姓,如此问庚宗妇人,其所答也同样象征着她孩子的身份。如此,叔孙豹“问其姓”的行为并不必然连结竖牛为其亲子,如同求职者上门了解其身份。
四、委质为臣
在贽见礼的研究中,杨宽先生之贽见礼研究同竖牛故事,皆包含了两个礼制的内容,贽见礼不仅是礼仪级别与身份地位的体现,同时透过委质为臣的过程,两种制度交互发生在每个阶层,可以看做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确立与定位的重要一环。而委质的内容物也随着委质之人的身份不同而不同,而不同的内容物,也就说明你为主上带来的责任义务大小的区别,可见贽见礼在整个社会的作用。
伴随着历代注疏家对“委质”不同的认识,进而对整个社会关系互动类型的意义上造成区别。《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杜预对“策名委质”的看法,注云:“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则不可以贰。”其后《正义》云:“质,形体也。古之仕者,于所臣之人,书己名于策,以明系属之也。拜则屈膝而委身体于地,以明敬奉之也。名系于彼所事之君,则不可以贰心。”除此之外,《国语·晋语九》韦昭注:“质,贽也。士贽以雉,委贽而退。言委贽于君,书名于策,示必死也。”又《集解》引清人惠栋所言:“孟子滕文公赵注云:‘质,臣所执以见君者也。’内传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服虔注云:‘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君也。’质,读为贽。死质,谓雉也。”
由上,可归纳两种对于“委质”的看法:一者认为“委质”乃是所臣之人的躯体做出臣服的姿态;二者则以为“委质”是以死贽象征所臣之人本身,请求其主接纳。而关于“屈膝而君事之”,笔者参看郭伟涛先生对于中古策名委质的研究,其认为在中古时代“‘策名委质’只是‘称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并不存在所谓登录己名于君主名籍的仪式”[16]。也就是说,注疏家所处的时代对此仪节并不熟悉。
关于“质”的本身为何,从晁福林先生的研究看来变动性是存在的,身份、场合、事件的不同,都会造成差异。对于“策名”是否等于“策死”,也是关于委质称臣常有的讨论主题。有学者主张,委贽礼是平常表示诚恳友好的平等关系,后来逐渐变化成政治性礼仪(11)参见项晓静,任建库《“策名委质”新探》,载于《安康师专学报》2005年第10期。。于此开展关于质与信之关联,委质之初兴于统治扩张至春秋末,大夫与士阶层崛起,更有能力触及统治核心,于是在与统治者之间渐取得更为平等的信义关系。《礼记·曲礼》中的“疑事无质”,《左传》隐公三年,“信不由中,质无异也”,《论语·颜渊》“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皆将质与信义连结。又如《管子·四称》中很明确说到有道的委质之臣当是如何,其中也很明确提到事君有义:“昔者有道之臣,委质为臣,不宾事左右,君知则仕,不知则已。若有事,必图国家,徧其发挥。循其祖德,辩其顺逆。推育贤人,谗慝不作。事君有义,使下有礼。贵贱相亲,若兄若弟。忠于国家,上下得体。居处则思义,语言则谋谟。动作则事,居国则富。处军则克,临难据事,虽死不悔。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临官则治,酒食则慈。不谤其君,不毁其辞。君若有过,进谏不疑。君若有忧,则臣服之。”[17]
郭政凯先生也强调,委质的状况,也存在于宗主与异族人之间。其引《白虎通·文质》:“子见父无贽何?至亲也,见无时,故无贽。臣之事君,以义令也,得亲供养,故质己之诚,副己之意,故有贽也。”结合以上质与信义之说可以确认,无论是贽见礼与委质,其本身都带有取信于人的意味,非必有死之别。通过现代学者对于委质称臣的研究加之古文献的映照,可以从这个角度推测,竖牛与叔孙豹并非父子。竖牛“奉雉”的行为,是一名士级别的异姓拜见、求职宣誓效忠的表示,如同《孟子·滕文公下》载“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18]
综上,可以归纳如下:其一,庚宗妇人也许本身只是一名有身孕或独自抚养小孩的寡妇,并且其原本的丈夫可能为“士”一级别的人物;其二,竖牛的身份透过贽见礼的视角来看,“竖”这类人不尽然身份卑贱,竖也不等于小童,能奉雉为政,足见其已成年;其三,透过先秦策名、赐名、姓名、职称等,说明竖牛与叔孙豹有不必然成为父子的条件;其四,透过历代注疏家对“策名委质”的理解,结合今人对西周末春秋初的社会发展状况研究等,可以推测“委质”乃作为贵族中最低的级别,没落贵族之“士”, 在大时代动荡中取信求职于主家常见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