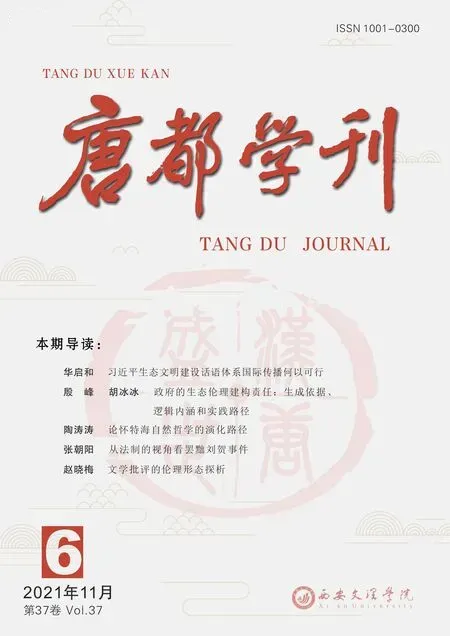“吏民” 再论
华迪威,刘 蓉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西安 710127)
“吏民”(1)关于“吏民”的代表性论作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刘敏《秦汉时期的社会等级结构》,收入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高敏《〈吏民田家莂〉中所见“馀力田”“常限”田等名称的涵义试析——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三》,载于《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王素《说“吏民”——读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札记(一)》,载于《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27日第7版;邱立波《关于两汉史籍中的“吏民(人)”问题》,载于《史林》2003年第5期;黎虎《“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载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黎虎《原“吏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收入《祝贺朱绍侯先生八十华诞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黎虎《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载于《文史哲》2007年第2期;黎虎《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载于《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黎虎《原“吏民”之四——略论“吏民”的一体性》,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刘敏《秦汉时期“吏民”的一体性和等级特点》,载于《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一词常见于秦汉史籍,在明清之时仍有沿用,可见其指代的群体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关于“吏民”具体定义、政治地位、享有权利和应尽义务等问题,学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吏民”与爵制关系、“吏民”与编户齐民关系、“吏民”是否具备一体性以及其究竟是复合词还是一体词等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本文拟对“吏民”称谓的特点及其指代的群体等问题进行重新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吏民”称谓的丰富性
学界对“吏民”问题的研究,通常只集中于史籍中出现的“吏民”一词,往往就“吏民”而谈“吏民”,对与其含义接近或完全相同的其他词语缺乏关注(2)侯旭东举出“编户”“黎庶”“黎元”“庶民”“民庶”“庶人”“百姓”“平民”等词汇,对这些词汇与“吏民”的联系并未涉及,参见侯旭东《北朝朝廷视野中的“民众”》,收入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乡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00页。,因此遗漏了不少重要史料,不利于认识“吏民”称谓的丰富性。在使用语境基本相同时,可认定其与“吏民”具备同样的含义。
第一,吏人。《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上闻,迺赦赵、代吏人为豨所诖误劫略者,皆赦之。”[1]2640《史记·高祖本纪》载此事云:“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1]387可知“吏人”“吏民”指代同一群体。“吏人”之使用更常见于《后汉书》,如《窦宪传》:“徙封罗侯,不得臣吏人”[2]820;《吴汉传》:“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2]683。同样语境下《后汉书》也用“吏民”,如《马防传》:“租税限三百万,不得臣吏民。”[2]588
第二,民人、人民。《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曰:“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1]2694《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3]527,则“民人”即为在户籍中之人口也,《三国志·苏则传》云:“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4]491,盖“民人”“吏民”同义,皆为在籍人口也。“人民”一词也在同一语境下出现,如《三国志·陈群传》云:“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裴松之案语云:“《汉书·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户口最盛,汝南郡为大郡,有三十余万户。则文景之时,不能如是多也。”[4]636-637“民人”“人民”“民”与“吏民”同义可知也。
第三,士民。《汉书·王莽传》云:“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3]4048;《宣帝纪》载:“赐诸侯王以下金钱,至吏民鳏寡孤独各有差”[3]239;《王莽传》有“公卿大夫士民同心”[3]4130;《平帝纪》排序为“三公、卿大夫、吏民”[3]353,可知士民、吏民所指代皆为普通平民,往往位列等级中之最下等。《后汉书·耿纯传》有“德信不闻于士民,功劳未施于百姓”[2]761,士民、百姓、吏民所指皆同。且“士民”“吏民”往往带有地方性、区域性特征,如“巴蜀士民”“秦士民”“凉州士民”“益州士民”“代地吏民”“南阳吏民”“邺吏民”“济北吏民”等,可知其实为一方之土著。
第四,庶人、庶民、民庶。《史记·平准书》太史公曰:“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1]1442《汉书·食货志》中师丹建言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俞困。”[3]1142可知庶人、吏民同义。而“免为庶人”“免为庶民”之记载亦常见,人、民二字可以互相替代;庶、民之先后顺序不同也代表同义,如《后汉书·顺帝纪》云“太原郡旱,民庶流冗”[2]269;《后汉书·杨彪传》:“民庶涂炭,百不一在”[2]1786。庶人、庶民、民庶皆与“吏民”指代相同。
第五,士庶、士庶人。《汉书·货殖传》载:“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货有余。”[3]3681士庶人之职责在于务农,《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有“听受吏民士庶上书”[4]115,又有“闾里士庶”[5]2356,“群黎士庶”[5]3211,群黎与士庶同义。《汉书·东方朔传》注引孟康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上阶为天子,中阶为诸侯公卿大夫,下阶为士庶人。”[3]2851形成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三层的等级次序,《后汉书·荀悦传》云其“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2]2062;《风俗通义》有“上欺天子,中诬方伯,下诳吏民”[6]。可知士庶、士庶人与吏民皆指代社会最基层民众也。
第六,百姓。《后汉书·桓帝纪》载:“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贷十分之三,以助廪贷;其百姓吏民者,以见钱雇直。”[2]300杨树达先生在其《积微居读书记》中认为“王侯吏民”之“吏民”为衍字,而“百姓吏民”之“百姓”二字为后人添加以与“王侯”相对[7]。按“百姓吏民”史亦有载,《三国志·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载张茂上书云:“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4]105百姓吏民便是黎民百姓之义,并无特殊之处,而《续汉书·百官志》载:“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得臣其所食吏民。”[2]3630所谓“王侯吏民”就是供养王侯食邑的吏民而已,杨树达先生之误可知也。《宋书·裴骃传》载其“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8]701。前后对应,可知百姓、吏民同义也,荀悦《汉纪》中有“令吏民百姓上长安城”[9]也可为证。
第七,齐民、编户民、家人、匹夫。《史记·吕太后本纪》载“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1]403,《南齐书·晋陵文宣王子良传》则曰“百姓齐民”[10],《魏书·李安世传》载“一齐民于编户”[11],则百姓皆被统一编户管理;《晋书·翟汤传》有“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5]2445。则编户民即为百姓、齐民也。《汉书·栾布传》载:“彭越为家人时,常与布游”,颜师古注曰:“家人,犹言编户之人也”[3]1980。则家人可等同于齐民、编户民、百姓,由此也可知辕固生说窦太后所好老子书“此是家人言耳”[1]3123时为何引得窦太后勃然大怒,因为辕固生这是讽刺窦太后格调不高,所好与百姓并无二致。《汉书·外戚传》中颜师古再注家人曰:“家人,言凡庶匹夫。”[3]3960匹夫与家人、百姓、编户民等词语同义,也就是吏民。
第八,蒸庶、众人、烝民、蒸人、元元。《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汎爱蒸庶”[1]3090,《汉书·武帝纪》载:“劝元元,历蒸庶”[3]167,元元与烝庶同义。《汉书·元帝纪》载“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颜师古注曰:“蒸,众也”[3]279;又在《中山靖王刘胜传》注云:“蒸庶,谓众人也”[3]2424。众人,即普通平民百姓也,如《史记·赵世家》:“年谷丰孰,民不疾疫,众人善之”[1]1817,民与众人同义;韦贤自作诗云:“忽此稼苗,烝民以匮”,颜师古注云:“言众人失此稼穑,以致困匮”[3]3103,可知众人、烝民、烝庶、蒸人皆指平民,也就是吏民。
第九,黔首、黎民、黎元、黎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更民曰‘黔首’”,《集解》引应劭注云:“黔亦黧黑也”[1]239,此为秦朝对于民的称谓。《汉书·鲍宣传》颜师古注引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3]3090此明确指出黎民、黔首、民之同义。《汉书·贾谊传》云“百姓黎民”[3]2249,可与上文论及之“百姓吏民”相对应,证明黎民与“吏民”之同义。而“黎民”又与“元元”相结合,有称“黎元”者,与“庶民”结合称为“黎庶 ”者,皆为百姓、吏民之义。
第十,平民、布衣。《史记·平准书》云:“齐民无藏盖”,《集解》引如淳曰:“齐等无有贵贱,故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1]1417。则齐民、平民同义也。《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云刘邦“起布衣”[1]2043,太史公云“绛侯周勃始为布衣”[1]2080,《史记·高祖本纪》载:“诸将与帝为编户民”[1]392,可知布衣与编户民同义,皆为统一受编于户籍之中的平民百姓,也就是吏民。
以上梳理了可以确定与“吏民”基本同义的称谓,使用这些词汇时将其代替为“吏民”也完全不影响原意,可见“吏民”称谓的丰富性。由上述史例可知,“吏民”是编制于户籍之内的平民,构成了社会结构最基础的部分,是各类征伐、劳役的主要承担者。
二、“吏民”与爵制关系再讨论
学界关于“吏民”的研究是从探讨其与爵制的关系开始的,有关对“吏民”爵位限制的几条记载启发了相关研究者,但在是否存在“吏民爵”以及军功爵与赐爵制关系等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今试析之。
(一)是否存在“吏民爵”?
贺昌群先生首倡“吏民就是庶民之有爵者”一说,观其核心史料依据,仅为《续汉书·百官志》“关内侯”条李贤注引刘劭《爵制》曰:“吏民爵不得过公乘”一则[12]。在其认识中,“吏民”群体所能拥有的爵位就是“吏民爵”,而“吏民”属于庶民范畴,只是因为有爵而得以与其他庶人区分开,“吏民”是一个具备一体性的群体。但史料中出现“吏民爵”一词时,却分明体现出其并非一体、等同。如《汉书·昭帝纪》云:“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3]223;《汉书·成帝纪》云:“赐天下吏民爵,各有差”[3]309。可知“吏民爵”中存在等级差异,而这与“吏民”群体同等的政治地位并不符合,故“吏民爵”称谓之合理性值得怀疑。
朱绍侯先生认为汉代“民爵、吏爵有严格的区别。由五大夫至关内侯是吏爵,公士至公乘为民爵……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13]。这一看法延伸开来,便是拥有五大夫至关内侯爵的便是属于“吏”的范畴,公乘及以下爵的拥有者则只能是民。但据《汉书·景帝纪》载:“三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如淳曰:“虽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数有赐爵”[3]150。则官、爵在一定时期内不匹配盖为常事,但总体而言,多次赐爵还是一种试图让官吏群体官、爵匹配的方案。
《汉书·宣帝纪》载,元康元年(前63)三月:“其赦天下徒,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颜师古注曰:“赐中郎吏爵得至五大夫。”[3]254《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中郎秩比六百石”[3]727,在此次赐爵之后,中郎才得以爵至第九级的五大夫,可见在此之前很多比六百石的吏并未获得公乘以上爵位,因为吏之迁转与赐爵级位之调整并非同步,官方的赐爵存在滞后,且往往一次性进行大规模赐爵,但对于具体的个人,并不会因为其官职上升或下降而立即为其调整爵位。
这样的普遍赐爵也使得“汉代没有爵的编户民似乎是不多的”[14]。但除却少数特殊时期纳粟得高爵的例子,绝无普通吏民能拥有公乘以上爵者,而官吏中确有暂时未获得与其匹配的爵位者,这足以说明民、吏之间在赐爵中是存在的,只是并非完全不可逾越。从多次赐爵中也可以看出吏与民的差别极大,如《汉书·宣帝纪》有赐爵“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3]254;《汉书·王莽传》有“赐吏爵人二级,民一级”[3]4114,即便是吏员群体中最底层的佐史,也在赐爵中享有高于民一级的优待,吏、民爵自然有鲜明分野。《昭帝纪》此条“中二千石以下”还有八百石吏、六百石吏等多个级别,他们不可能被排除在普赐民爵之外,故此处之“吏民爵”断然不会是赐给“吏民”阶层以爵,而是赐给中二千石以下的某些级别吏员及普通平民以爵;《成帝纪》此条当点为“赐天下吏、民爵,各有差”,如此则与吏爵、民爵鸿沟明显的史实相符合。因此,就赐爵制的实践来看,并不存在单独的“吏民爵”,此为吏爵与民爵之合称。
(二)军功爵与赐爵制的关系
刘劭《爵制》中“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者,得訾于子若同产”[2]3631。这一观点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作为探讨军功爵的重要依据。然其文本身便有诸多疏漏,如其曰:“有功赐爵,则在军吏之例。”盖获得军功而获得赐爵之人就属于军吏,则军吏便是军中有功而获得赐爵之人,《史记·张丞相列传》载:“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1]2681,则是指汉初当朝的将相公卿皆是从高祖起义而有军功之人。然军功爵共二十等,《爵制》却曰:“公乘者,军吏之爵最高者也”,此判断前后矛盾,《爵制》前文便载:“八爵为公乘,九爵为五大夫,皆军吏也”,九爵都依然为军吏,为何八爵的公乘却成为了军吏的最高爵?《爵制》又有“自左庶长已上至大庶长……皆军将也”,然《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有“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1]2336,《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有“五大夫绾伐魏”[1]2410皆为五大夫,而独领一方面军,则五大夫也可为军将也,非独左庶长以上能为耳。故刘劭此作虽早出,却多与军功爵相关史料有矛盾抵牾之处,不能将其内容全部作为讨论军功爵制的理论依据。
关于“爵不得过公乘”,有如下几条记载:“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于子若同产、同产子。”[2]96“赐民爵,人二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三级,脱无名数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级,爵过公乘得移于子若同产子。”[2]129“赐民爵,人二级,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于子若同产、同产子。”[2]220“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于子若同产、同产子。”[2]259
纵观以上诸条,并不涉及军功赐爵,皆为天子赐民以爵。朱绍侯先生指出最晚在武帝时期,赐民爵八级制已从为战争而设的军功爵制中游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奖赏体系[15]347-355。在两汉频繁的赐爵中,如不加以限制,普通民众确实容易因年龄而累积到很高爵位。而若是立下军功,则自然不被局限于八级公乘之内。刘劭《爵制》很可能未能辨明两种不同的爵制体系,故其文字前后存在不少与史实相抵牾之处,这说明早在三国时,人们就已经混淆了军功爵制与赐爵制。朱绍侯先生指出,刘劭对二十等爵的解释“都适用于秦和汉初,当赐民爵(即非军功赐爵)形成定制和卖爵之风盛行之后,就完全与三家的解释对不上号了”[15]413。这是非常精当的认识。但同样可以看到赐爵制中高于公乘的情况,如《汉书·宣帝纪》“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此说明公乘及以下爵的拥有者中也有尊官,但国家致力于对此问题的调整与解决,试图让尊官与高爵相匹配,而匹配的措施就是先让他们都普遍拥有高于八级公乘的第九级爵——五大夫。说明在赐爵制中,中二千石至六百石的官员,在理论上至少都应当超过“爵不得过公乘者”的限制,六百石及以上官员并不在“吏民”的范畴之内。钱大昭云:“自公士至公乘,民之爵也,生以为禄位,死以为号谥。凡言赐民爵者即此。自五大夫至彻侯,则官之爵也。”[16]西嶋定生指出“公乘以下之爵,可授与一般庶民及未达秩六百石之官吏;五大夫以上,则是秩六百石以上之官吏可受的爵。”[17]昭示出赐吏、民爵与官爵之别,官即为六百石以上吏也。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有“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18]之记载,则编户齐民不会拥有五大夫及以上高爵,这对于我们认识“吏民”的身份有启发作用。
因为两汉广泛的赐爵行为,编户民普遍拥有爵位,而他们在赐爵之前早已拥有“吏民”的身份,并非因为赐爵才拥有这样的身份。且综上所述,公乘以下爵位的拥有者并非尽如贺昌群先生所谓“与庶民无异”,故其“吏民就是庶人之有爵者”一说并不能成立。
赐爵制与军功爵制存在区别,而人们对两种制度的认知很早就出现了混同的趋势,刘劭《爵制》前后记载的矛盾便是这种趋势的体现。一般而言,在赐爵制中“吏民”不能累积获得公乘以上的爵位,而在军功爵制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限制。但是,“不得过公乘”“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等皆为对“吏民”享有权利和身份等级层面上的一种限制,而非对其本身下的定义。
三、“吏民”的相对性
“吏民”的使用不仅具有丰富性,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此相对性突出表现在与长吏相对时,也与使用者的身份和场景有关。
(一)相对于长吏而言的“吏民”

上条之“皆长吏也”提示我们关注长吏与“吏民”之关系,那么“六百石以上”才属于长吏范畴吗?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颜师古注曰:“吏,理也,主理其县内也。”[3]742长吏似指代县中之主理政务者,如县令、长、丞、尉皆在其中。六百石以上吏皆为长吏,但长吏并非皆在六百石以上。邹水杰认为“长吏”的含义有过变化:秦及西汉时期大致指县令长、丞尉等县级官吏,但西汉有时也仅指县令长;到东汉时期则转为郡国守相和县令长等地方行政首长,而不及其佐官[19]。张欣则指出长吏在秦汉时期有泛指高级官吏的用法,但不是所有高级官吏都可称作长吏,长吏还具有实指的一面,即主要用作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一种代称[20]。
按张欣之说更为精当,我们可以从史料中一窥长吏与地方民众之关系,如陈涉起义时“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1]349。“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1]1953,“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1]2573,地方郡县造反时,皆先杀其长吏而不及其余。“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1]2967,“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3]54,“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徒四十万口,摇荡百姓”[3]2198。可见,郡县长吏皆为中央所派遣,代表着皇权和中央的意志,起到教化民众之作用。而“长吏”之作为与“摇荡百姓”直接相关,可知长吏以下皆属百姓之列,受到其直接管辖与治理。
而“长吏”并不完全代表地方百姓的利益,往往与地方百姓矛盾深刻。如董仲舒云:“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3]2512他将群生、黎民所遭遇的困苦皆归于“长吏不明”。《史记·滑稽列传》有“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3]3213,可知长吏以下即是“民人父老”之列。唐人孙樵《梓潼移江记》:“恨所在长吏不肯出毫力以利民”[21],将其所在长吏与吏民百姓们的对立展现得淋漓尽致。
前文已论民人、黎民、民与吏民同义,则长吏以下尽属吏民的判断可以成立。那么,何以长吏以下尽为吏民呢?顾炎武有“守相命于朝廷,而自曹掾以下,无不用本郡之人”[22]之判断,严耕望详细论证了“凡中央所任命之地方官,上自郡国首相,下迄县令、长、丞、尉、边侯、司马,均用非本郡人”[23]347的观点,盖长吏皆为中央所任免,非所任职地区之本地人也。严氏同书也有力论证了“汉时掾属无不用本郡人者”[23]351的观点,则长吏以下皆为本地人也。陆九渊有“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24]的认知,则官人为长吏,吏人为本地人。前文已论吏人与吏民同义,则吏民就是相对于地方长吏而言的本乡之人、本地之人也。《三国志·夏侯玄传》云“今之长吏,皆君吏民”[4]297,则“长吏”相对“吏民”为君也,陈直先生指出“汉代大官僚对朝廷称臣,人民对长吏亦称臣”[25]。故“吏民”或可释为“长吏之民”,即相对长吏而言的臣民也,长吏代表中央,“吏民”代表被控制被裹挟的基层民众。
以上观点也可以得到出土简牍资料的印证,《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中有以下几种身份的人皆被归入“吏民”范畴:男子、大女、州吏、郡吏、县吏、州卒、郡卒、县卒、军吏、复民、士[26]。黎虎先生指出:“所谓‘吏民’并非单纯指普通农民和政府机构中的吏员, 实际上包含了乡里基层编户中的各种各类人员,就目前所见吴简而论,除了普通农民和州郡县吏之外,还有军吏、州郡县卒、复民、士等不同身份的人。可以说凡编制于乡里基层之中的编户均属‘吏民’的范畴。”[27]其说可从。此处涉及州郡县之吏皆为长吏以下之掾属小吏,因地方长吏户籍皆不在其任职之地,故在本地入籍之吏皆为长吏以下,若“吏民”包含有县令、长、丞、尉等,《吏民田家莂》不可能对拥有这些身份的人无载,故可知长吏均非“吏民”也。而中央派遣的长吏以下的地方掾属、小吏与各类职业、身份的普通平民一起编织入户,王夫之云“统吏民而壹之,则无差等也”[28],亦可见“吏民”与编户齐民之同一性。王素指出汉代户籍或可名之为“吏民籍”[29],张荣强指出吏民的“骨干和基础则是一般民众和下级吏佐”[30],二说皆较为符合历史事实。
(二)不同使用场景下的“吏民”
《史记·孝文本纪》载:“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1]426则济北王以下之吏与民皆为被其裹挟,造反非其本意,故被赦免,此处之“吏民”指代济北国王以下所有人也。《汉书·武五子传》中载燕王刘旦造反不成,“有赦令到,王读之,曰:‘嗟乎!独赦吏民,不赦我。’”[3]2758此处之“吏民”也是指代燕王之下所有吏与民。
《汉书·循吏传》载汉宣帝“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3]3624,相对于太守为一郡之长吏,其余郡县官吏及百姓皆为其治理者也,故太守以下一郡之吏与民皆为其吏民。《资治通鉴》:“彭州长史刘易从……任孝忠谨,将刑于市,吏民怜其无辜,远近奔赴,竞解衣投地曰:‘为长史求冥福。’”[31]则此处之“吏民”实为长史以下之吏与民的合称。此为相对郡守、长史而言的吏民,而相对天子而言,百官、百姓皆为其“吏民”也。《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载张茂上书云:“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则天子之下皆为其“吏民”也。
由此可知,“吏民”在使用场景不同和使用者身份不同时,其指代的具体人群也有不同,“吏民”之称谓在丰富性、普遍性之外,还具有相对性。
四、“吏民”群体的基本特点
“吏民”为中国古代史籍中常用且意义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的一个词汇,与其含义接近的词汇有吏人、庶人、庶民、民庶、士庶、士民、民人、人民、平民、布衣、编户齐民等二十余种,反映出其称谓的丰富性和普遍性,而从这些称谓及其指代群体所拥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出发,可以作为考察“吏民”身份的重要依据。在赐爵制中,六百石以下吏及平民一般不得拥有超过公乘的爵位。六百石以上官员被要求“符合吏体”,与民众要有明确的身份界限以区分,而长吏以下则并不被作此要求,说明六百石以下吏并不被皇帝认为是与民有明显等级差别的人。由于地方长吏由中央任命,故其代表皇权和中央的意志,未必能够对地方利益予以充分照顾,故在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时,长吏往往首先成为基层民众的攻击对象。而“吏民”群体皆为本乡之人,对地方及个体利益十分关注。经过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走马楼三国吴简的考察,基本可以将“吏民”界定为长吏以下吏及平民或相对长吏而言的臣民,他们被共同编制入户籍为编户齐民,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代表着本乡人的利益。“吏民”是郡县制及大一统逐步确立进程中的产物,地方与中央的纠葛,民众与皇权的合作与矛盾,皆是其生存的历史背景。除此之外,“吏民”在使用场景不同时,其指代的群体有所区别,反映了“吏民”称谓的相对性。
就此而言,“吏民”群体整体上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吏民”被统一管理、编制入户口。《史记·项羽本纪》载刘邦入关后秋毫无犯,却最先进行了“籍吏民”[1]312的工作,可见“吏民”的统一管理被视为在一个地区统治得以展开的头等要事。《汉书·礼乐志》载:“民人归本,户口岁息”[3]1075,《宋书·武帝纪》载:“繁殖生民,编户岁增”[8]38,可知“吏民”人口变动直接影响户口数量。其二,“吏民”承担国家赋税和徭役。《汉书·谷永传》载:“务省繇役,毋夺民时,薄收赋敛,毋殚民财,使天下黎元咸安家乐业”[3]3449,《汉书·贾谊传》有提到“其吏民繇役往来长安者”[3]2261,可知“吏民”的主要义务便是承担赋税和徭役,故政府对这两项进行减免就被视为仁政。其三,“吏民”内部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汉书·武帝纪》有“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3]177;《汉书·龚遂传》载“吏民皆富实”[3]3640;《汉书·食货志》载哀帝时“累世承平,富豪吏民訾数矩万,而贫弱俞困”[3]1142;《贡禹传》载“富豪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3]3071,而与此同时也常见有“吏民困苦”[3]1254之记载。可知“吏民”中有富豪,有能假贷贫民者,也有贫穷之人,如果“吏民”皆为相对富裕之人,史籍中也就不必多以“吏民富实”作为地方官的政绩进行赞扬了,更无必要对能假贷贫民者以特殊之礼遇了。而有的“吏民”甚至会因为种种原因丧失其原本之身份,《汉书·高帝纪》载“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3]54;《商君书·错法》言“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32];《汉书·武帝纪》注引李奇云:“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贫民”[3]180;《淮南子·齐俗训》云:“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33]。杜正胜先生指出:“财富之外,权势和气力都会使齐民不齐。”[34]木村正雄则有力指出:“民田制是一种私有制,因而它就必然包含着弱肉强食即一方兼并土地而另一方丧失土地的契机。于是各王朝的极盛期一过,就出现了作为王朝衰退原因的民田兼并和耕地偏颇的现象。”[35]“吏民”群体有着国家层面上同等的政治地位,但经济、权势之别都会使得贫富和强弱差距明显,不能将“吏民”都统一视为富裕的阶层。
综上所述,“吏民”问题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点,对“吏民”称谓丰富性与相对性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吏民”群体,而在“吏民”问题的研究中辨明赐爵制与军功爵制的区别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笔者希冀在这些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