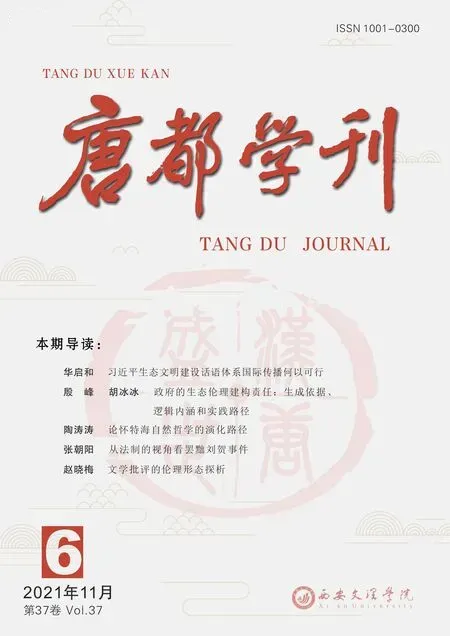河、湟归唐与晚唐诗歌研究
傅绍磊,郑兴华
(宁波财经学院 a.象山影视学院;b.人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东侵,河、湟沦陷,关中与安西、北庭的联系被切断,失去战略屏障,长期遭到吐蕃侵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广德元年(763),连长安也一度沦陷。虽然贞元、元和年间,德宗、宪宗都有复河、湟的意图、甚至付诸行动。但是,长庆年间,随着姑息、苟安的政治主张逐渐占据上风,唐朝与吐蕃会盟,正式承认吐蕃所侵占的唐朝土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中年间。“大中三年正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七月,三州七关军人百姓,皆河、陇遗黎,数千人见于阙下。上御延喜门抚慰,令其解辫,赐之冠带,共赐绢十五万匹……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玭奏收复秦州……九月,西川节度使杜悰奏收复维州……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泽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以义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1]621-629这就是大中年间的河、湟归唐事件,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深刻影响到大中、甚至咸通年间的士风、文风,却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颇为遗憾。本文梳理河、湟归唐对晚唐诗歌,特别是边塞诗的影响,分析原因,从而为认识晚唐诗歌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角度。
一、河、湟归唐诗歌表现
河、湟归唐以后,士人纷纷遥想盛唐,将盛唐的绚丽图景投射到现实之中,有生逢盛世之感,从而将大中与开元、天宝相提并论,河、湟归唐成为当时朝野内外争相歌颂的事件。崔铉《进宣宗收复河湟诗》:“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芳洽凯歌。右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遇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白敏中《贺收复秦原诸州诗》:“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天山千里锁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植《奉和白敏中圣道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眀呈上》:“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圣功。四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弢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扶《和白敏中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铉等人身为朝廷重臣,诗歌为礼制上的应酬之作,但是,在盛情歌颂的过程中很难说没有真情的流露。
更多的是许多士人的声音,薛逢《八月初一驾幸延喜楼看冠带降戎》:“城头旭日照阑干,城下降戎彩仗攒。九陌尘埃千骑合,万方臣妾一声欢。楼台乍仰中天易,衣服初回左衽难。清水莫教波浪浊,从今赤岭属长安。”刘驾《唐乐府十首》:“唐乐府。自送征夫至献贺觞,歌河湟之事也。下土土贡臣驾,生于唐二十八年,获见明天子以德归河湟地,臣得与天下夫妇复为太平人,独恨愚且贱,蠕蠕泥土中,不得从臣后拜舞称于上前,情有所发,莫能自抑,作诗十章,目曰唐乐府,虽不足贡声宗庙,形容盛德,而愿与耕稼陶渔者歌田野江湖间,亦足自快。”张祜《喜闻收复河陇》:“诏书频降尽论边,将择英雄相卜贤。河陇已耕曾殁地,犬羊谁辩却朝天。高悬日月胡沙外,遥拜旌旗汉垒前。共感垂衣匡济力,华夷同见太平年。”当时薛逢在长安任职弘文馆,刘驾为应举士人,而张祜则为布衣,虽处不同的阶层,但对河、湟归唐却都表示出了极大的欢喜和兴奋,说明河、湟归唐影响的广泛性。
值得注意的是,河、湟归唐影响几乎持续整个大中年间,《新唐书·礼乐志》:“宣宗每宴群臣,备百戏。帝制新曲,教女伶数十百人,衣珠翠缇绣,连袂而歌,其乐有《播皇猷》之曲,舞者高冠方履,褒衣博带,趋走俯仰,中于规矩。又有《葱岭西曲》,士女踏歌为队,其词言葱岭之民乐河、湟故地归唐也。”[3]478
安史之乱后,河、湟沦陷,唐朝中衰;大中五年,河、湟归唐,对大唐士人而言意味着盛唐时期的太平盛世已经到来。
二、河、湟归唐与晚唐边塞诗的新变
会昌以来,随着回纥、吐蕃的衰弱,唐朝边境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资治通鉴》卷247:“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之先备器械糗粮及诇吐蕃守兵众寡。”[2]7999-8000河、湟归唐是会昌年间边境军事胜利的继续,是当时唐朝边境形势的重要转折点,为大中、咸通年间,唐朝对党项、南诏的军事胜利奠定基础,从而大大激发士人文化自信,推动边塞诗在晚唐出现全新的面貌。
第一,歌颂唐朝武功,渴望立功边塞的豪迈情怀再次成为主题。唐朝边塞诗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高潮,在盛唐武功的激励下,士人纷纷从军边塞,歌颂将士英勇,表达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边境大幅度收缩,军事力量衰弱,特别是面对吐蕃强大的军事压力,边塞诗不但数量锐减,而且因诗人情绪低落,厌战、思乡成为普遍主题。会昌以来,唐朝在边境由守转攻,吸引越来越多的士人前往边塞,在频繁的军事胜利激励下,边塞诗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马戴《出塞词》:“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诗中石雄大破乌介可汗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少有的边境胜利,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在诗歌语境中堪比盛唐武功。
河、湟归唐引起唐朝西部边境形势剧变,直接推动唐朝对党项的军事胜利,而且时间与河、湟归唐相隔不久,从而使得河、湟归唐的影响更加持久。开疆拓土呼声在当时边塞诗中逐渐高涨。马戴《关山曲二首》:“金甲耀兜鍪,黄金拂紫骝。叛羌旗下戮,陷壁夜中收。霜霰戎衣月,关河碛气秋。箭疮殊未合,更遣击兰州。”“火发龙山北,中宵易左贤。勒兵临汉水,惊雁散胡天。木落防河急,军孤受敌偏。犹闻汉皇怒,按剑待开边。”许棠《送李左丞巡边》:“狂戎侵内地,左辖去萧关。走马冲边雪,鸣鞞动塞山。风收枯草定,月满广沙闲,西绕河兰匝,应多隔岁还。”张乔《再书边事》:“万里沙西寇已平,犬羊群外筑空城。分营夜火烧云远,校猎秋雕掠草轻。秦将力随胡马竭,蕃河流入汉家清。羌戎不识干戈老,须贺当时圣主明。”击破外敌,开疆拓土,安定边境,是晚唐边塞诗的内在逻辑,因为河、湟归唐让士人有了生逢盛世的幻觉,从而顺理成章地在盛唐武功的语境中形成特定的表达范式,“犹闻汉皇怒,按剑待开边”,已经与盛唐边塞诗相差无几。盛唐武功主要是在西部边境获得,从而晚唐边塞诗主要的地理审美空间对应的正是以河、湟为中心的区域。
第二,强烈的纪实性。会昌以来,因为边境形势的好转,大量士人乐于从军边塞,零距离地感受边塞,所以,晚唐边塞诗就包含了更多纪实的价值和诗人直观的感受。
许棠就因为身在边塞而亲身经历河、湟归唐的整个过程,《塞下二首》:“胡虏偏狂悍,边兵不敢闲。防秋朝伏弩,纵火夜搜山。雁逆风鼙振,沙飞猎骑还。安西虽有路,难更出阳关。”“征役已不定,又缘无定河。塞深烽砦密,山乱犬羊多。汉卒闻笳泣,胡儿击剑歌。番情终未测,今昔谩言和。”《出塞门》:“歩歩经戎虏,防兵不离身。山多曾战处,路断野行人。暴雨声同瀑,奔沙势异尘。片时怀万虑,白发数茎新。”河、湟归唐在长安是君臣同庆的热烈气象,在边塞却是“胡虏偏狂悍,边兵不敢闲”。所以,身在边塞就是在亲历真实的历史,豪迈却不失深沉、厚重。《题秦州城》:“圣泽滋遐徼,河堤四向通。大荒收虏帐,遗土复秦风。乱烧迷归路,遥山似梦中。此时怀感切,极目思无穷。”河、湟归唐突如其来,虽然是重要的军事胜利,但是,毕竟难以在短时间里再现“太平盛世”,荒凉的边塞有着强烈的审美感受,只有零距离面对边塞才能够有所感受,《春日乌延道中》:“边穷厄未穷,复此逐归鸿。去路多相似,行人半不同。山川藏北狄,草木背东风。虚负男儿志,无因立战功。”《成纪书事二首》:“东吴远别客西秦,怀旧伤时暗洒巾。满野多成无主冢,防边半是异乡人。山河再阔千余里,城市曽经一百春。闲与将军议戎事,伊兰犹未绝胡尘。”“蹉跎远入犬羊中,荏苒将成白首翁。三楚田园归未得,五原歧路去无穷。天垂大野雕盘草,月落孤城角啸风。难问开元向前事,依稀犹认隗嚣宫。”当时唐朝边境形势颇为有利,边塞风土人情在许棠的诗中虽然苍凉却不乏刚劲,将士少了几分怨恨,多了几分悲壮。许棠虽然在诗中还是难免惆怅,但更多的是昂扬之情,对唐朝的信心,对自己立功边塞的渴望,这些都建立在最真实的边塞感受基础之上。
《旧唐书·高骈传》:“骈,家世仕禁军,幼而朗拔,好为文,多与儒者游,喜言理道。”[1]4703高骈作为晚唐名将,用诗歌记录晚唐边塞历史,表达家国情怀。《旧唐书·高骈传》:“会党项羌叛,令率禁兵万人戍长武城。时诸将御羌无功,唯骈伺隙用兵,出无不捷,懿宗深嘉之。西蕃寇边,移镇秦州,寻授秦州刺史、本州经略使。”[1]4703高骈的戎马生涯始于在西部边境平定党项叛乱中表现出的高超军事才华,从而获得重用,拉开建功立业的帷幕,谦逊之中分明是一份踌躇满志的自信。《言怀》:“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主圣扶持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咸通年间,南诏攻陷安南,唐朝南部边境危急,高骈南征,收复安南,战功赫赫,《南征叙怀》:“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回期直待烽烟静,不遣征衣有泪痕。”《赴安南却寄台司》:“曾驱万马上天山,风去云回顷刻间。今日海门南面事,莫教还似凤林关。”《过天威径》:“豺狼坑尽却朝天,战马休嘶瘴岭烟。归路崄巇今坦荡,一条千里直如弦。”凤林关和海门一带分别是高骈对党项和南诏作战的主要战场,都是高骈立下赫赫战功之所,天威径对于高骈而言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进骈检校刑部尚书,仍镇安南,以都护府为静海军,授骈节度,兼诸道行营招讨使。始筑安南城。由安南至广州,江漕梗险,多巨石,骈募工劖治,由是舟济安行,储饷毕给。又使者岁至,乃凿道五所,置兵护送。其径青石者,或传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3]6392
乾符年间,南诏进犯剑南,高骈再次出征,对南诏几乎产生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力。“南诏寇巂州,掠成都,徙骈剑南西川节度,乘传诣军。及剑门,下令开城,纵民出入。左右谏:‘寇在近,脱大掠,不可悔。’骈曰:‘属吾在安南破贼三十万,骠信闻我至,尚敢邪!’当是时,蛮攻雅州,壁庐山,闻骈至,亟解去。骈即移檄骠信,勒兵从之。骠信大惧,送质子入朝,约不敢寇。”[3]6392《赴西川途经号县作》:“亚夫重过柳营门,路指岷峨隔暮云。红额少年遮道拜,殷勤认得旧将军。”正是因为有了长期在边塞建功立业的亲身体验,所以,高骈的边塞诗豪迈之中更多真切、自然。
征战的艰辛、将士的悲苦、闺妇的哀怨,也都是高骈边塞诗中常见的主题。《塞上曲二首》:“二年边戍绝烟尘,一曲河湾万恨新。从此凤林关外事,不知谁是苦心人。”“陇上征夫陇下魂,死生同恨汉将军。不知万里沙场苦,空举平安火入云。”《叹征人》:“心坚胆壮箭头亲,十载沙场受苦辛。力尽路傍行不得,广张红斾是何人。”《寓怀》:“关山万里恨难销,铁马金鞭出塞遥。为问昔时青海畔,几人归到凤林桥。”《边城听角》:“席箕风起雁声秋,陇水边沙满目愁。三会五更欲吹尽,不知凡白几人头。”《闺怨》:“人世悲欢不可知,夫君初破黑山归。如今又献征南策,早晩催缝带号衣。”边塞是征人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也是冤魂萦绕不散的无情坟墓,更是佳人黯然伤情的梦中他乡。
保家卫国的豪迈与生离死别的哀伤缠绕交织是高骈边塞诗的最大特点,代表了晚唐边塞诗的特点。高骈作为晚唐名将,久经沙场,屡立战功,名震边塞,深为唐朝所倚重,高骈边塞诗创作将晚唐边塞诗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获得了不同于盛唐边塞诗的独特意蕴。
三、河、湟归唐与晚唐诗歌再评价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4]孟子的“知人论世”反响强烈,逐渐与政治挂钩,形成以政治评价文艺的范式。《毛诗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5]政治兴衰直接影响文艺创作,在“治世”“乱世”“亡国”等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就有相对应的文艺创作状态,导致不同审美风格的形成,“诗”成为“世”的反映。《文史通义·文德》:“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6]章学诚是在“世”与“诗”之间注意到“人”的作用,但本质上并没有超越“知人论世”的理论范畴,只是进一步完善而已。后世对于晚唐诗歌的评价也深受“知人论世”的影响。
南宋以来,晚唐诗就受到贬抑,严羽《沧浪诗话》:“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严羽所说的晚唐诗不仅是一个时代范畴,更是一个审美范畴,所以“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入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7]。严羽对于晚唐诗的贬抑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黄子云《野鸿诗的》:“晚唐后专尚镂镌字句,语虽工,适足彰其小智小慧,终非浩然盛德之君子也。韩、柳之文,陶、杜之诗,无句不琢,却无纤毫斧凿痕者,能炼气也;气炼则句自炼矣。雕句者有迹;炼气者无形。”[8]贺贻孙《诗筏》:“中、晚唐人诗律,所以不及盛唐大家者,中晚人字字欲求其工,而盛唐人不甚求工也。”[9]139吴乔《围炉诗话》:“晚唐多苦吟,其诗多是第三层心思所成。”[9]591
《唐才子传》:“观唐诗至此间,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双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10]晚唐诗人普遍苦吟,晚唐诗也就难免雕琢过甚,辛文房归因于国运衰弱,辛文房的观点引起后世不少学者的认同,陈子龙《安雅堂稿》:“大中而后,其诗弱以野,西归之音渺焉不作,王泽竭矣。”[11]因为晚唐是衰亡之世而贬抑晚唐诗,属于典型的“知人论世”,在整个唐代历史与唐代诗歌发展史中,可备一说。但晚唐与晚唐诗之间也不可能通过政治形成笼统而简单的关系,笼统地认定晚唐是衰亡之世所以简单地贬抑晚唐诗而不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更为具体深入的认识,有失偏颇。
后世对于晚唐诗歌的评价基于对整个晚唐政治走向的全面认知,而晚唐士人不可能全面认知整个晚唐的政治走向,他们多是通过特定政治事件判断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
晚唐国运日蹙,会昌、大中年间,唐朝攘除回纥,河、湟归唐主要原因是回纥、吐蕃的衰弱,而不是唐朝的强大,甚至对党项、南诏的军事胜利也并不意味着唐朝军事实力已达至盛唐。但当时的士人不可能深究其中的原因,故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太平盛世的印象,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文学创作(1)陈铭、方然、余恕诚等人对晚唐诗歌评价更加客观,但也是基于晚唐是衰亡之世的前提,认为晚唐诗歌代表的是不同于盛唐诗、甚至是中唐诗的具有时代衰落感、回避现实的消极的审美风格,还是“知人论世”的范式。虽然晚唐是衰亡之世,但是,因为出现了河、湟归唐等特定政治事件,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衰亡之世的特征被掩盖,甚至在当时士人的观念中消失,那么,对于晚唐诗歌也应该有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评价。参见陈铭《晚唐诗风略论》,载于《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方然《关于晚唐文学发展规律的系统探讨》,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余恕诚《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其风貌特征》,载于《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河、湟归唐等政治事件与当时的发展趋势并不一致,士人的太平盛世的印象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有着较大的偏差,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说明将晚唐诗置于整个唐代诗歌甚至更为广阔的文学创作背景中加以研究固然不错,但是,设身处地地认识当时士人所经历的特定的政治事件、所具有的创作状态,再以此为角度对晚唐文学进行研究,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