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章 为人楷模”的著名学者张恒寿
夏明亮

张恒寿
张恒寿,字越如,1902年3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官沟村(今属阳泉市郊区),1991年3月7日在石家庄逝世。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研究院,先后执教于国立北平艺专(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北平文法学院、辅仁大学、河北师范学院等高校,曾任河北师院历史系名誉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河北省委委员、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务,为我国现代著名的庄子研究专家、哲学史学家。
作为一代著名历史学家,张恒寿在中国传统史学哲学研究中造诣高深,新见迭出,成果丰硕;作为人师,张恒寿一生推重人伦,道德与学问交相辉映,其嘉言懿行,为现代和后代学人所推崇。
乱世之中的求学生涯
张恒寿出生于一个旧式农商家庭。父亲张士林是当地著名士绅,曾积极参加光绪末年山西爱国士绅抵抗清政府出卖山西采矿权的“保矿运动”,为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之一,民国期间,山西省政府赠予其“急公好义”匾额予以表彰。张士林喜爱读书藏书,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培养。1909年,他不惜重金从平定州城聘请两位学识渊博的儒生,办起家族私塾,张恒寿遂入私塾读书。
在私塾中,张恒寿读完了《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还学习了《名贤集》《朱子治家格言》和清朝学部编译馆编辑的《国文》和《算学》课本。11岁时又到离家三里远的赛鱼村上高小,接触到一些数学、历史、地理知识。1916年夏张恒寿高小毕业,年迈的父亲不想让幼子远离,又请了一位饱读古籍的老先生,于是他在家里学读《左传》《孟子》及唐诗等,并开始文言文和旧体诗方面的写作练习,同时还读了父亲的藏书《呻吟语》(明代吕坤著)、《书目答问》(清代张之洞著)等。并以《书目答问》为线索,翻阅了多种学术典籍,尤其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三位集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于一身的硕学鸿儒特别敬慕。少年时代长达十年的古代传统文化学习经历,使他在义理、考据、词章等方面都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920年,18岁的张恒寿进入太原市第一中学学习,开始接触新文化,读了陈独秀、胡适之的许多文章。1921年,他亲耳聆听了哲学家梁漱溟的演讲后,“颇受感动,但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于是撰写了一篇评论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文章,发表在平定留省学生季刊上。一个中学生,竟敢向全国一流学术权威提出质疑,这种有胆有识之举轰动了山西学界。时任太原一中校长崔梦禹在多个公开场合自豪地表示:“我们的张恒寿,不但是太原一中建校以来的第一才子,就全市各校来说,也是首屈一指!”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更使张恒寿认识到,在国学之外,还有一个充满奥秘、博大精深的西学世界,若像之前那样故步自封,将会落伍于时代。
中学时代,张恒寿还结识了新文学作家高长虹和石评梅,读了一些新文学作品,尤其对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最为喜爱。这时,他的视野开始越出校园,列强在华夏大地上肆虐横行,军阀之间混战不已,百姓生活朝不保夕,这些凄苦的现实,使他内心十分苦闷。国家的出路何在?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他彷徨四顾,无所适从。
1925年,张恒寿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班。不料家中祸事接二连三,继母、结发妻子和父亲相继染病,又相继病故,使他难以专心就学。直到三年后,他才得以返回北平,升入北师大英文系本科。读了一年英文专业,根据自己的兴趣,他又转入历史系就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掀起抗日热潮。张恒寿与小学同学甄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山西大学校长)及郭绳武、董书芳等联络山西同学回乡在平定中学成立了“平定青年奋进社”,被推举为社长。他们举行演讲会,募捐款项创建流动图书馆,并创办了《平定评论》《奋进》等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张恒寿撰写了《中国现状和中国青年》《论罗素哲学》《科学在自由教育中的地位》等论文,并在县城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及其影响”“平定与中国”的演讲。这些活动,在宣传群众、激发青年奋起抗日的斗争中发挥了启蒙作用。
1932年大学毕业后,张恒寿先后在太原平民中学、成成中学、山西大学附属中学任教。目睹国家陷于内忧外患,自己却不能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尽一份力量,他决定继续读书深造,从中外历史中寻找救国之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清华大学中文研究院的招生广告,结果一试即中。1934年秋,他走进美丽的清华园,开始了研究生学业生涯。
非常幸运的是,在读研究生期间,张恒寿得到了几位学术大师耳提面命的点化。他的导师刘文典长于校勘学,是国内少数几位有独到见解的庄子研究专家之一。他跟着刘先生做了三年《庄子》研究的考证工作,完成了十二万字的《庄子研究》文言文初稿;他选修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佛教翻译文学》课程后,撰写了《六朝儒经注疏中之佛学影响》的学年论文;他選修陈寅恪先生的《<世说新语>及魏晋哲理文学》课程后,完成了《读<世说新语>札记》的学期作业;他选修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课程后,撰写了《庄子与斯宾诺莎哲学之研究》的学年论文;他选修闻一多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课程后,完成了《共工洪水故事和古代民族》的学年论文。上述论文都经过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三位学术大师的指导和批阅,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视为张恒寿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上的初步贡献。
1937年6月,张恒寿完成了研究生学业,经过笔试和口试,他被清华大学留聘为大一国文教师。正当准备论文答辩之际,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张恒寿颠沛流离,辗转于家乡平定、太原和北平之间。为避免日伪迫害,他在北平埋名隐居,艰难度日,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才结束了这段身心俱疲、近乎“亡国奴”的精神炼狱。
狂风面前的淡定学者
1946年,应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之邀,张恒寿加盟国立北平艺专,担任国文教师。之后,经冯友兰先生推荐,他又在北平文法学院兼任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师;经陈寅恪先生介绍,在北平辅仁大学兼任国文课程教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张恒寿调入河北师范学院,从此在这所大学任教近40年,直至去世。
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张恒寿始终坚持学者操守,不说一句违心之语,不做一句违心之论。他一生的著述数量不多,但他绝不作凑数之文,应景之章,每一部每一篇都有新见,皆为心血之作。正如著名史学家胡如雷先生为其撰写的挽联所云:
德高望重,澹泊明志,终生贵操守;
学广识博,未轻落笔,一贯尚精深。
1955年冬,全国开展批判胡适的运动。当时国内各大报刊发表的大批判文章有一些共同特点:政治帽子多,学术水平低,结论多,论据少,有些文章干脆就是人格攻击甚至谩骂。这时,张恒寿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发表了《胡适“反理学”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实质》一文。他把学术批判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在文中他不但研究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历史和思想,而且对胡适本人的身世和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通篇不见政治帽子,行文中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势,即使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人读来,仍可见其学术价值。
张恒寿治中国思想史,不是单纯局限于思想史的范围,而是追寻到决定某种思想倾向的社会基础之上,把唯物史观建立于扎实的社会条件之上。鉴于这种史识,他的思想史研究又拓展到古代社会史和古代哲学史领域。
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张恒寿作了一个重要发言,引起哲学史界的广泛关注。他指出,在唯物唯心斗争和阶级斗争二者的关系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认为宇宙论上的唯物主义者在社会政治上都是代表进步的,唯心主义者都是落后反动的,不能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他认为,确定一个哲学家的阶级性,应该以其社会理论为主,而不应以其自然观为主。因为前者的反映是直接的,后者的反映则是间接的。对于少数在自然观上是唯心论而在社会政治观上是反对统治压迫的哲学家,则应该分析他的政治理论是怎样得出来的,两者间的矛盾应该怎样解析,绝不能以简单的公式曲解事实。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要有一定的哲学学识和造诣来支撑,在当时过分强调阶级性的政治氛围中,更要有过人的政治勇气。与会的《人民日报》记者当即约请张恒寿将这一发言整理成文,1957年2月4日《人民日报》正式刊出了这篇题为《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从方法论上提出的见解,划清了宇宙观与阶级立场的界限,遭到一些思想左倾人士的批判和围攻,但张恒寿坚持认为此乃自己集数十年研究所得,始终未改变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不做学术上的“风派”是他一生坚守的学术道德底线。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是20世纪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前后发表的论文专著,数以几百万字计。而张恒寿发表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首篇的《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一文,被著名史学家胡如雷先生称之为“确为其中的奇葩,犹如鹤立鸡群,独放异彩”。
当时,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议而未决。张恒寿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只是要圆满解决这一问题,难度颇大,必须等待理论上、材料上圆满解决的时机。正在这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商调张恒寿到该所担任研究员,河北师院不愿舍掉这面学术旗帜,只同意他兼任该所研究员。哲学大师冯友兰时任该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同意张恒寿将河北师院的论文题目作为哲学所兼职研究员的题目,于1957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会议上列席讨论。后来,应《历史研究》编辑部之约,将原文进行压缩,登载在该刊1957年第9期上。文章发表后,受到史学界、哲学界高度评价,被誉为“代表了当时汉代社会性质研究的最高水平”,推动了多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张恒寿虽沧桑几度,但他不谄笑以取悦,不曲言以负心,宁肯保持沉默,也不写一篇批判文章。他沉痛地说:“我不能写,也不想写,因为我不能说违心的话。”1974年,友人介绍他为北京师范学院编注“王船山法学思想论著”的学员们上课,讲解《船山遗书》。他指着文集中的《老庄申韩论》,对听课的学员们说:“说王船山是唯物论者,相当容易;说王船山是法家,你们这任务可不容易完成啊!”用这种方法提醒学员们把进步哲学家都说成法家这种简单化推理的荒谬。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学院等高校合编《中国古代史》讲义,他分工写思想史部分,因预料到大家不会接受他的观点,便提前声明:“我只能这样写,如果不合适,请诸位改,我是改不了。”在全书统稿时,编写组要求加上“评法批儒”的内容,他毅然拒绝。后人称其“不被形势所左右,不为功名而躬身”,是兼具史德、史才、史识的真史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迈入暮年的张恒寿迎来了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在他人生最后的十余年間,他发表了《论春秋时代关于“仁”的言论和孔子的仁说》《论子产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孔子评传》《略论理学的要旨和王夫之对理学的态度》《论宋明哲学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说》《顾宪成学术思想散论》《浅谈“二程”思想的异同》《章太炎对“二程”学说的评论》《王船山天人学说探微》等多篇论证缜密、严谨求实、篇篇落地有声的论文,结集为《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于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花山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诗集《韵泉室旧体诗存》。

张恒寿著作《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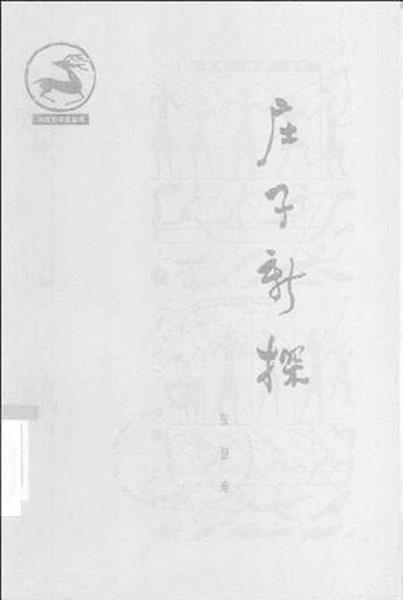
张恒寿著作《庄子新探》
庄周的后代知音
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庄子新探》是张恒寿半生学术心血的结晶,成就了他作为我国现代庄子哲学研究的权威地位。哲学大师张岱年称该著“探赜索隐,盖多发前人所未发,堪称名著”。
张恒寿研究庄子肇始于1934年初入清华大学中文研究院时,就写作时间来说,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从青年到耄耋,几乎绵亘了一生。
张恒寿初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从自己的文史哲兴趣出发,选了一个与文学思想和哲学思想都有关系,而自己又比较熟悉的庄子作为研究课题。这时的张恒寿不满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又找不到拯救国家的路径,于是感觉庄子对统治阶级的消极反抗与自己当时的政治态度十分吻合。在跟随导师刘文典先生考证研究《庄子》的过程中,越来越对这位颇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化和智慧的圣哲产生了思想深处的共鸣。三年研究生阶段完成《庄子》考证部分的文言文初稿,之后随着学养的积累和阅历的丰富,不断加以充实完善,终于在年过八旬之后完成了这部反映自身学术风貌的代表性专著。
关于张恒寿和他的《庄子新探》,著名史学家赵俪生有一段生动形象、准确到位的评述:
他的学术风貌究竟是指什么呢?照我说,应该叫大考证,落落大方的考证,大关节目上的考证。说起考证,自清朝乾(隆)嘉(庆)以来,特别以长江三角洲地带为典型地区,人们把这门学术越做越琐细了,有时我对其中一些令人不耐卒读的作品私下里对自己的研究生说过一句刻薄的话“鸡零狗碎之学”,足见我一生对此积愤之深。可是恒寿先生的考证却丝毫不沾这种边。我常说,读他的庄子考证,如同进入一座宏大的手术室,人们静悄悄地,只听见钳子、剪子、镊子的轻轻碰响,主治医生对应切除什么,缝合什么,心中井井有数。恒寿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手术师,来给庄周动手术,他把《庄子》书中33篇总共二百余个段节一一加以精心的料理。
33篇原本分三类:内篇、外篇、杂篇。当初这么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人们通过这种划分,反映这些篇章之可靠性的等次。但这又不是铁板一块的。有时内篇文章中会出现一些与庄周不合的思想,或者说是较庄周本人要晚出的思想;有时外、杂篇中会出现一些好像是庄周本人或者当时的思想。这些情况,清朝人不是一点也没有接触到的,但动大手术来切除什么,缝合什么,却是恒寿先生的业绩。我说“落落大方”,是指恒寿先生做这些考证不像三角洲人们那样挑起一个针鼻子大小的事就大动干戈,不惜繁征博引以炫其腹中之富,而到头来于主题毫无补益。张先生处理庄子是从思想实质出发,经过足以说服人的论证,又回到思想实质上做出结论;有时,也举一些同时前后的子书(如《吕览》《韩非子》《孟子》《荀子》《淮南子》等等)作比较,但具体比较过程往往留在“暗”处,而只把比较得出的结论拿到舞台上来,令人有台面干净利落之感。有时,也在《庄子》本书不同篇、不同章段之间作比较,同样也是作得毫不繁琐。须知,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叫乾嘉以后的人写,写几十卷,出一套书也写不完的,而恒寿先生却只用二十几万字,这是一种本领,十分高强的本领。
《庄子新探》分上、下篇。上篇是考证,考证《庄子》书中可靠性的等次。这是一种奠基工作。我常常这样想,假如每部先秦古籍都有人做做这种大手术,该多么好呀。下篇是分析,在这里又显示出恒寿先生的另一种能力和能量,那就是理论的能力和能量,这是只有经历了多年精心阅读和体会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黑格尔、康德、斯宾诺莎等人哲学专著才能获得到的水平。没有这种水平,是驾驭不住庄子这匹骏马的,而恒寿先生若无其事地驾驭住了,像家常唠嗑样地把庄子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一一分析出来了。在书尾,他又像诗集末尾一样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结束语”(张恒寿在《韵泉室旧体诗存》这部诗集后面附了一篇篇幅不長的《后记》,阐发了自己对文史哲方面的精辟见解——引者注),在其中提到了庄周“不与当权者合作”的传说,他的“未改狷者型”,又一次地彰显了出来。
《庄子新探》一问世即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1984年第11期《哲学研究》载文评说该书是庄学研究中的新突破;1985年,该书荣获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86年第1期《中国哲学史研究》载文,称该书是一部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的高水平学术论著。1985年夏,日本研究中国道家哲学的专家池田知久专程拜访张恒寿,对《庄子新探》赞叹不已,特意索书回国向日本同行推介。
范仲淹、顾炎武的精神传人
张恒寿被学界誉为皎洁有操守的“大雅高人”,在他清心玉映的一生中,无论是面对何种境遇,都不屑时荣,不曲学阿世,透射着中华民族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格光辉。
张恒寿在一首四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宇宙万物,人号最灵。
须重教育,方称此名。
教有两轮,知识德行。
知贵运用,德为本根。
昔在北宋,有范文正。
曾留名言,后世称颂。
“后天下乐,先天下忧。”
志气远大,可贯宇宙。
明季顾君,垂教立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行已有耻,博学于文。”
此言虽简,可行终身。
愿我同志,师法两公。
志高行健,方称英雄。
早在弱冠之年,面对军阀混战,国忧民难,张恒寿忧心如焚,慷慨悲歌:
可怜神州风云晦,
手无斧柯奈若何?
书生空谈无长策,
且复劝酒对嫦娥。
不知他年将如何,
只怜今宵明月多。
愿洗人心如月净,
爱我祖国矢靡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恒寿恨自己一介书生,不能为国分忧,为民纾难:
利剑不在手,
四境多妖氛。
斯民悲涂炭,
何用徒攻文!
张恒寿寄希望于能出现一个全力挽救时局的抗日势力,1933年“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建的成立,使他极度兴奋,未承想这一抗日势力很快被分化瓦解镇压下去。这位怀着炽热爱国之情的年轻学者找不到救国出路,只能埋头于学术研究之中,以笔为剑,为真理而献身了。
1937年冬,华北沦陷,大片国土被日军践踏。当时张恒寿正乡居平定县故里,因他在当地颇具声望,日伪方面用恐吓、诱骗等方式“请”他出来担任伪职,他毅然拒绝。日伪县政府派人去抓他,他逃到偏僻的塞山槽、神堂咀山庄躲避,乡亲们久不闻他的音信,以为他凶多吉少,因而当地百姓中间误传出他已被害的消息。
后来,局势稍为平静,他携夫人刘桂生返回北平,隐居起来。他改名张永龄,留起胡须,蛰居斗室,在忧愤中艰难度日。为了生计,他给富家子弟做家庭教师,夫人给别人誊抄稿子,加上老家卖地寄些钱,生活勉强得以维持。即使生计再艰难,他依然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和傲骨,绝不肯“下海”到日伪掌管的大学教书,宁肯什么也不做,也不向敌方屈服。在日据时代的北平,他结识了张东荪、王桐龄、邓以蛰等不同日伪合作的文化界前辈,互相砥砺,坚守情操。他还与张岱年、翁独健、王森、张遵骝、韩镜清、成庆华、王葆元等知名学者组成“三立學会”,每隔两三周相聚一次,探讨一些哲学思想和时局变化等问题,成为北平文化界“一个保留民族气节、促进哲学研究的集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频繁的政治运动,张恒寿积极参加学术辩论,但他始终坚持真理,绝不随风附和,不做违心之论。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浮夸风、“共产风”和“文革”中的影射史学,张恒寿不以为然,决不仰承鼻息作推波助澜之文。在“批林批孔”的狂浪喧嚣正炽之际,他以学者的正直和良心,坚持对待孔夫子必须一分为二,在当时的反孔“大合唱”中,此论此举,可谓石破天惊。
张恒寿故去后,国学大师季羡林用极为简洁又恰如其分的八字评语为之盖棺定论:
“道德文章,为人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