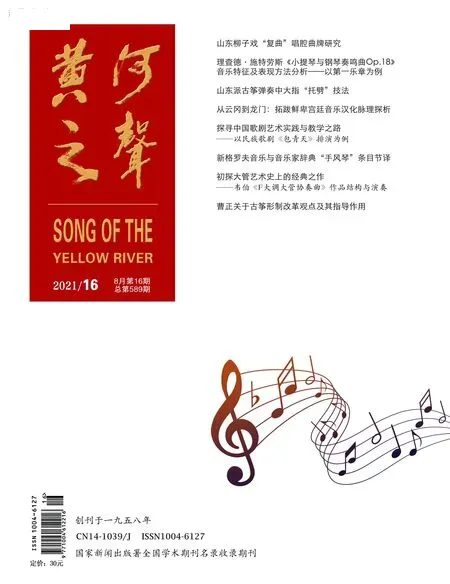关于曾侯乙镈钟的几点思考
梁 玉
1977年9月,一支部队在湖北随县(今称随州)擂鼓墩山头,偶然发现一座大型墓葬,经考究为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距今约两千四百多年。次年6月,曾侯乙编钟悉数安全出椁。这套编钟共计64件,外加一件镈钟,作为战国时期的随葬乐器是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音律最全,其音域可达五个八度,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套大型编钟。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在世界早期音乐中占有不可小觑的分量,甚至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一、关于礼乐制度与曾侯乙
礼乐制度始于西周,盛于西周,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礼乐制度受到一定的打击,削弱了对其王侯、士大夫等阶级的制约作用,从《论语·八佾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对于季氏(大夫阶级)在家中享用天子规格的乐舞队列极为不满。足以体现这一时期礼乐制度遭到一定的破坏,不过这不是绝对的。
曾侯乙虽处战国时下葬,但从出土的墓葬来看,其依旧遵从礼乐制度中诸侯的下葬标准。黄敬刚曾在《曾侯乙墓椁室形制与宗周礼乐制度》提及到中室和东室是曾侯乙墓的主体。而墓中的音乐文物主要集中于墓葬的东室和中室,特别是中室。除编钟外,中室存放的音乐器物中还包括编磬、建鼓、笙、瑟、十弦琴等百余件乐器,可能也与他爱好音乐并制作大量“金石之声”的礼器入葬有关。
虽然也有国内学者曾质疑过曾候乙墓中的部分器物过于奢华,有僭越礼制的嫌疑,例如墓中的“九鼎八簋”也属于礼乐仪式中的“重器”,有且只有天子才能享受这个等级,“显然超越了礼制等级规范”;但是在《吕氏春秋·节丧》:“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不可胜其数。”中也提及到只要经济富足雄厚,厚葬也是可以被允许的,符合一定社会风俗。《节丧》篇又言:“世俗之行丧,载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云偻翣以督之,珠玉以佩之……苟便于死,则虽贫国劳民,若慈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大意为世俗之人举行葬礼,用大车载着棺椁,打着各种旗帜,棺柩之上点缀着珠玉,军法指挥送葬行列等既美观又奢侈的场面,但用这种葬礼为死者求安宁,却是不行的。如果这样做真有利于死者,那么即便使国家贫穷、人民劳苦,作为慈亲孝子也在所不惜去做;在《曾侯乙墓椁室形制与礼制考》中也清楚地叙述了这一观点的不可能性,并认为:曾侯乙逝世,年近四十有余,这时候正是他年富力强的时候,曾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同时代的巅峰,其伟业应该在继承先帝基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更快,为汉东称雄打下一定基础。战国时,曾国可能与楚国关系匪浅,楚王送给曾侯乙镈钟可证曾(随)国被尊为汉东诸侯强国的地位。又据《左传·僖公·僖公四年》:“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译为:凡是诸侯在朝会时死去,葬礼加一等;为天子作战而死的,加二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用天子的礼制入殓。在《从曾侯乙编钟看古代曲悬与轩悬制度》中也表达过相似疑问。
因此,是否可以大胆猜想,曾侯乙的死确实由于“薨于朝会”或为国作出重大贡献而捐躯亦或是护驾有功等原因,使得在追葬时受到了最高等级的待遇。
在出土的曾侯乙镈钟上刻有31字的铭文:“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楚王从西阳返回朝中后,听闻曾侯乙逝世在西阳的消息,悲痛之至为他坐了一件镈钟,送回西阳随曾侯乙入葬。至于他们在西阳是否参与战争,是否为楚王作战,从而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曾侯乙的死亡,目前并无此类相关的文献记载,无从考究。但可以结合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来看,镈钟上的铭文也是侧面证实了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的可能性。这也解释了曾侯乙墓中随葬品的奢靡豪华的另一原因,同时也对是否僭越礼制给予一定考究。
二、关于《周礼·小胥》孔颖达疏“天子、诸侯悬皆有镈”,而“卿大夫、士,直有钟磬无镈也。”中思考天子诸侯等级的墓葬是否必备镈钟
(一)关于“乐悬”制度与曾侯乙编钟、镈
在礼乐制度中,“制礼”谐音可以理解为“治理”(国家),是通过制度对人们行为上的规范;“作乐“更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约束。在《孝经》中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从音乐史角度来说,周朝的礼乐制度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佾”和“乐县”。“佾”是礼乐制度中歌舞乐队的使用行列;“乐县”,“县”通“悬”指悬挂乐器,这里的乐悬制度指的是悬挂乐器的使用规格。《周礼·春官·小胥》记载:“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意思是:天子使用四面排列的悬挂乐器,诸侯用三面排列的悬挂乐器,卿大夫用两面排列的悬挂乐器,士阶级用一面排列的悬挂乐器。说明周礼在音乐、乐舞中各阶级所使用的规格是不同的,并且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阶级所使用的音乐规格都有明确的划分,而曾侯乙编钟就是“乐悬”中“轩悬”的具体实物,即诸侯所用规格。(详见图1)

图1
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编钟共计65件,编钟由64件纽钟和甬钟组成,外加1件镈钟,悬挂于底层中间位置,形制与所排列的编钟风格迥异,经国内学者李纯一先生考究确实不是同一套乐器。
(二)思考天子诸侯等级的墓葬是否必备镈钟
据《周礼·小胥》孔颖达疏“天子、诸侯悬皆有镈”,而“卿大夫、士,直有钟磬无镈也。”由此,对于王侯墓室中是否必备镈钟这一说,可以从礼乐制度的视阈下对于曾侯乙编钟及镈进行思考:
其一,这一文献记载无疑是对曾侯乙诸侯等级身份的肯定,也是楚王对于曾侯乙生前所做出的贡献予以肯定,在此镈钟上并有铭文加以证实。在《太原晋国赵卿墓铜编镈和石编磬研究》中认为:“太原赵卿墓编镈,为豪华的镈钟形式,规模达19枚之巨……若按‘轩悬’’的制度来加以考虑……构成‘曲悬’的形式,加上编磬一列,正成‘三面、其形曲’的‘轩悬’’之制”,因此,“将该墓出土乐器的乐悬确定为轩悬之制应是可信的”。因此,《周礼·小胥》这段话再次证实李纯一先生所认为的观点,曾侯乙墓是符合乐悬制度的。那么是否必备镈钟这一说,来区分王侯与士大夫之间墓葬等级标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考量。
其二,单看王侯墓室中是否必备镈钟,从而体现的等级制度这一问题。可以确定的是从普遍意义上讲,这是不够准确的。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讲“周礼”在西周时期王权高度集中时提出,所以实行效率较高,效果显著,而随着时代变化,在分封割据的战国时期,当权力不在集中专一于天子时,权力的削弱势必会带来制度的毁坏;从微观角度讲这时期的礼乐制度逐渐在发生衍化,而再次传到楚地时,已然逐渐衍生似周礼而又有其不同宗周制度,笼统称之“楚礼”,当然各地藩国的随葬制度也随之出现了一定区别。但是就曾侯乙墓来说他仍遵循周礼的随葬规格,已然与大多楚墓出现了差异。在《荀子·正论篇》也有所提及:“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认为其楚地在当时较为特殊,不完全受礼乐制度的约束。由此看来,这个问题只能单纯就曾侯乙编钟进行个案分析。在邵晓洁《楚乐悬钩沉》中也对这一观点有明确的图文赘述。
其三,不同时期关于镈的所属等级、功能、大小等,在徐蕊《周代以降钟镈诸问题探究》中对历代有关镈钟这类问题进行溯源与分析。可以看出钟镈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使用制度也不尽相同,形制、大小、功能更是变化丰富的,在这方面的文献记载都证实了是有一定的区别。
其四,目前我国的古代出土乐器中已有特悬,单个使用,体积较大,猜测可能是作为节奏型的乐器,也有编组使用的乐悬,大小不一,使得音域不再单一,演奏形式也更加丰富。而在马自树《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一级品·上卷》中记载:曾侯乙编钟的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千克,是迄今为止出土墓葬中最大的一套编钟。在《礼记·礼器》中说到的“礼有以多为贵……以大为贵……”。在《楚乐悬钩沉》又言:“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乐器体量的大小,特别是青铜乐器的重量或耗铜量,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拥有者的等级相关。”,由此不仅可以确定曾侯乙编钟里的镈钟合乎礼乐等级关于诸侯的所属等级,并且可以推测出“天子诸侯皆有”的可能是大型的单个特镈,而非小型的编镈。由此,对于乐悬制度中,是否必备镈钟是可以给予一定考究的。
综上所述,从现有的已经出土的周代墓室中看,王侯并非全部都配有镈这一乐器,同时在士大夫阶级的墓葬中也有配镈钟。“卿大夫、士,直有钟磬无镈也。”[出自《周礼·小胥》]这一说也就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能以偏概全,将曾侯乙墓及其出土的音乐器物进行个案分析,它又是合情合理的。说明“礼乐制度”虽然遭到一定的破坏,但是在王侯之间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曾侯乙所推崇的祖制正是这种具有强化等级的制度-即礼与乐的融合,使得他死后也希望后代尊崇更高等级的制度为其下葬,若是不推崇宗周制度,后人是否会按照他应有的礼制进行下葬,便又成一难题。
结 语
关于在曾侯乙与礼乐制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曾侯乙虽地处战国时期的楚地,礼乐制度遭到一定的破坏,且楚地根据”周礼“已衍生了”楚礼“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从墓葬中依旧可以考究出曾侯乙墓葬是符合礼乐制度的,墓中的随葬品虽奢靡豪华的另一原因,但并无僭越礼制,并可以看出他生前极度热爱音乐,其墓葬中发现不仅铸造了大量的青铜乐器,还都专门为其篆刻铭文,即“曾侯乙持终”,同时对字符进行别出心裁的创新将:“作”创制为“音乍”字样,将音与礼直接上升到精神层面,尊崇周制将礼与乐紧密度融合在一起。并且通过上述实例,再次印证了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典型性的合乎“周礼”的诸侯墓葬,未有僭越的嫌疑。
关于乐悬制度中是否存在《周礼·小胥》中提及到的;王侯皆有镈”,而士、大夫,直有钟磬无镈这一说因此也得到了准确的答案,文章从制度、等级、功能、形态的四点考究,可以确定,这句话并不具备”普遍性“的意义,不能以偏概全适用于所有的下葬等级的标准,且无法作为区别王侯与以下等级的葬制。但是仅从曾侯乙钟镈来看它又是合情合理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印证了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典型性的合乎“周礼”的诸侯墓葬,这句话仅用于曾侯乙墓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