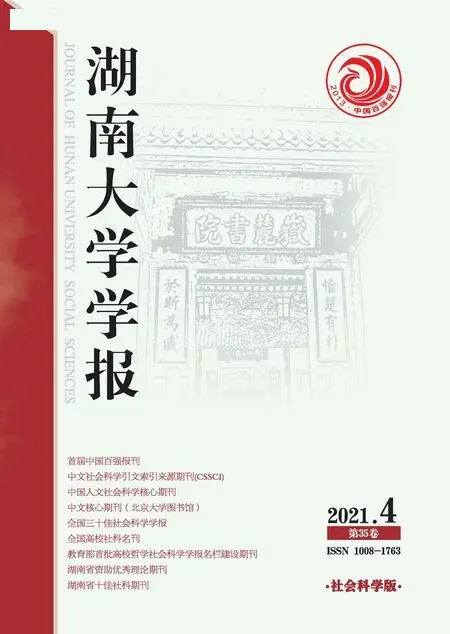日本近代“公德” 发展与“法治”关系探赜*
史 少 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 710126)
日本近代 “公德”发展与“法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民“公德”的快速提升,其背后是“法治”的强大协力。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公德”状况受欧美人讥讽、耻笑,甚至侮辱,到明治时代后期“公德”状况极速改观,“公德”水平飞跃式地进入了世界前列。探究日本近代“公德”水平的飞跃式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公德”关联的“法治”推动,“公德”飞跃式发展的背后是相关“法治”的强大推力。即,日本近代国民“公德心”的拥有、“公德”意识的快速提高,乃至精神风貌的极大改观。这不仅仅是政府进行国民公德教育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与“公德”发展相对应法治的健全与有效运用的结果。诸如日本自古以来至明治初期,日本国民的随地吐痰、街头巷尾乱扔烟头、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乘车时挤上挤下、遛狗随地大小便等等顽疾的治理,不仅仅是通过“公德”教育,而主要是通过相应的“法治”取得了重大成效。故而,日本近代 “公德”发展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 日本近代强制性治理“不公德”顽疾的“法治”意识提高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法律是统治者统治国民的手段之一。“法”一般包括宪法、刑法、民法等。日本近代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行了改革。日本近代出版的著作《国民读本》中指出:“凡是叫做国家的,一定都有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政府支配在其国的众多国民,……我国自建国以来,是君臣定分、万世一系、天皇列相承统治国家的纯全君主国家。”(1)[日]普通教育会编:《国民読本》,东京:国民书院,昭和九年版,第2页。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重大政治改革,建立明治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在法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模仿西方国家,施行一系列的“变法”。 “宪法是国家统治的根本法则。”(2)[日]文検受验研究会:《文部検定修身科教案提要》,东京:启文社书店,大正十四年版,第225页。宪法是一个国家至高至上之法。明治宪法,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颁布。明治二十三年明治政府制定了旧民法典,明治三十一年制定了新民法典。“民法是关于父子夫妇主仆之间的事项,即关于父子夫妇主仆之间的人事、财产、契约等全部民间私事的规定。”(3)[日]峰是三郎:《国民教育资料》,东京:东京同文馆,明治三十二编版,第83页。明治三十二年,明治政府制定了明治商法,“商法是关于商人事业之间关系的条例”(4)[日]峰是三郎:《国民教育资料》,东京:东京同文馆,明治三十二编版,第84页。。明治四十年颁布新的刑法。明治时代日本对刑法进行了大的改革。“刑法是诸法律中其保护范围最广,即我们的生命、身体、财产、名誉等生活必要的全部事,都依据刑法受到完全的保护。为了我们安全地生产、安全地寝食、营造快乐的家庭,实际上是国家为了保护我们而制定的此刑法。然而旧刑法,相对于今日显著发达的国家、显著富裕的国民来说,日益显现的缺点颇多,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众的利益,因此实施改正。经过议会的协赞,明治四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布,明治四十一年十月一日开始实施。”(5)[日] 法律専攻会 编:东京:《改正新刑法注解》,柏原奎文堂,明治四十二年版,第1页。明治时代,明治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完善了法律体系。
“法治”就是依法律治理。法律自产生之日起,就是国家统治国民的工具。在蒙昧时代,没有法律的概念,法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伴随国家的出现才产生的。“法律是依据国家的权力产生的,而道德是以人格的发达为条件;法律是外部的,道德是内部的;法律尊形式,道德尊内在心情;道德比法律更具积极性与根本性。随着法律的进步,会接近法律道德,通过道德上的原理达到与法律的统一……道德依据法律被补充,法律是通过道德性原理达到统一的基础。”(6)[日]国汉文研究会:《受験的作文と文法の実际》,东京:三宅书店,昭和四年版,第315页。法律能强制性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能强制人们做什么,也能强制人们不做什么。“一个标准是法律所规定的一种行为尺度,离开这一尺度,人们就要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7)[美] 罗斯科 ·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令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9页。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日本明治四十四年出版的《臣民读本》中指出:“臣民对国家有绝对无限服从的义务,有遵守法律命令的义务。”(8)[日]嵩山堂编辑局 编:《臣民読本》,东京:嵩山堂,明治四十四年版,第44页。法律也是保障国民正当权利的工具,同时国民也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以正义为基础,为国民防邪除恶而制定。吾等必须遵守之,如果违反之,破坏人伦道德、损害安宁秩序,国家就会对其处罚。”(9)[日] 足立栗园 :《公民讲话》,东京:富田文阳堂,第68页。任何国家,对于国家的治理,对人民的管理,一般都运用德治和法治手段,有的国家侧重以德治国,有的国家侧重于以法治国,更多的国家在治国方面既重视法治,也重视德治。也有国家某个发展时期、发展阶段侧重以德治国,在另一发展时期、发展阶段侧重以法治国。
明治时代以前的日本,也是非常注重德治的国家,一直重视国民忠君、孝亲、对朋友信等“私德”修养。近代意义上的“公德”概念,日本明治时代福泽谕吉给予了界定,并且与“私德”概念相对阐释,日本学界对“公德”“私德”概念也从多角度进行了阐释。明治时代普通教育会编的《国民读本》中这样论述:“公德是对社会的德义,即重视公众的卫生、尊重社会的规律,爱护公众的物品等,时刻考虑众人的利害而从事行为的德义。不弄脏市街、道路,不乱涂、损害神社、佛堂的建筑物。折公园里的花、折树枝等,都是缺乏公德的表现。”(10)[日]普通教育会 编:《国民読本》,东京:国民书院,昭和九年版,第305页。明治初期,学界一致认为日本自古以来,“私德”发达,“公德”缺乏。正如日本近代坪内孝、草刈融所说:“由来东洋的道德对特定的人发达,对广大的社会公众不特定人的道德(即公德)缺乏。对特定人的道德即对君尽忠节、子女父母间尽孝养、朋友交信、夫妇有别。君父朋友夫妇都是特定人,自古以来关于对特定人的道德,反反复复地叮咛教导其道,唯独对于社会公众不特定人的道德,何等教导都没有。”(11)[日] 坪内孝、草刈融:《常识修养录》,东京:松华堂,大正三年版,第44页。日本当时缺乏公德的表现:“有人在道路上极其喧噪给人造成不安、有人喝醉了横卧在大街上影响国家的体面、有人在乘车时推挤别人……严重缺乏公德之心。”(12)[日] 坪内孝、草刈融:《常识修养录》,东京:松华堂,大正三年版,第48页。日本近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改革、文化的提升,国民“公德”水平的提升势在必行。日本近代《国民读本》中写道:“立宪政体下的我国臣民,不仅仅具备私德,还应当具备公德是极其重要的。公德是对社会公众之道德,提升国民的公德,对于增进国家的福利、保持社会安宁,是无上无比的政策。”(13)[日] 普通教育会 编:《国民読本》,东京:国民书院,昭和九年版,第306-307页。因为人都具有自然属性、社会性的二重性,人的自然属性中都不同程度地或多或少有贪婪性、自私性;然而每个人还具有社会性,都是生活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社会中,并且每个人都不可能孤立地、脱离社会而存在。因此,由每个人组成的社会需要秩序井然,需要相互协作,需要相互支撑,更需要相互之间各自的克制。每个人在有秩序的、和谐的社会中共处,需要自制力,也需要公德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克制力、自制力、公德心。明治时代教育家、理论家汤本武比古认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是德教的国家,不是法治的国家……日本法治习惯缺乏,可以说遵法之心淡薄,其结果导致某些人不守公禁,而没有公德心。”(14)[日]読売新闻社 编:《公徳养成之実例:附·英人之気质》,东京:読売新闻社,明治三十六年版,第126-127页。
日本近代“法治”意识提高。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国际交往也日益频繁,在与欧美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日本人当时的“公德”状况,尤其受到了欧美国家的鄙视与耻笑。日本明治时代的峰是三郎认为:“人的品性,分为个人品性与国民品性……我国国民品性缺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其主要表现为,其一,共同性的思想缺乏……其二,社交中猜疑之念强……其三,理性薄弱容易感情用事……其四,独立独行思想缺乏……其五,公德缺乏。”(15)[日]峰是三郎:《国民教育资料》,东京:东京同文馆,明治三十二编版,第49-50页。尤其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公德”缺乏,日本学界以及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日本政府痛下决心改变社会公德现状,鼓励学界学者揭露日本人在公德方面存在的问题,列举日本习俗中“不公德”行为的顽疾,把丑陋的一面展现出来而后摒弃,难以改正的“不公德”陋习用法治强制性地修正。“公德”教育不是万能的,有时候仅仅依靠“公德”教育不能提高全体国民的“公德”素质,只有借助于法律,依法强制性地对“不公德”行为的顽疾进行惩治,才有可能强制性地修正某些国民的“不公德”行为陋习。明治时代,日本学界许多理论家认为日本自古以来,不是法治健全的国家,为了适应日本近代的发展,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健全、完善国家的法律,使社会得到有效治理。在日本近代,“法律的制定,首先向议会提出法律案,在议会决议的基础上,给予天皇裁可,然后公布,对臣民检束产生效力”(16)[日]普通教育会 编:《国民読本》,东京:国民书院,昭和九年版,第55页。。
日本近代与“公德”发展相应的“立法”开始。明治政府于明治四年(1871年)颁布了《散发脱刀令》,修正男子的发髻习惯,允许人们散发、短发,改变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交往的形象。明治五年,日本司法省颁布了《违式诖违条例》,同年东京率先实施,陆续在日本全国各地实施。“‘违式’的语义具有违反一定法式的意味;‘诖违’在词典中没有这样的词汇,‘诖’有错误、欺骗、妨碍之意。明治六年七月十九日,《地方违式诖违条例》为单行法,太政官第二五六号以单行法形式公布。《违式诖违条例》总则五条,违式罪目三十七条,诖违罪目四十八条,合起来共九十条。”(17)[日]松谷武一.:《ひながたとかぐらづとめ―国家権力の弾圧と近代法制史料》,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98年版,第104-105页。《违式诖违条例》具有法律效力,其中为国民规定了诸多关于“公德”方面的行为规范、规则,法律本来就有命令性、强制性,国民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违背《违式诖违条例》,一旦有人违背《违式诖违条例》,就会受到处罚、制裁,按照《违式诖违条例》的规定条目,严格执行处罚。《违式诖违条例》规定得很细致,对于妨碍他人的种种行为、损害公共财物之行为等有关“不公德”“悖公德”的表现都进行了列举,并且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或被罚款、或被拘禁等。日本近代“公德”发展的历史证明:《违式诖违条例》在推进国民“公德”迅速提升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依“法”治理社会,依“法”规范国民的行为习惯,依“法”强制性地扭转国民的不良习俗、陋习,即强制性地扭转国民不良习俗、陋习中的“不公德”行为,从而使国民从心理上反复强化法律意识、公德心。《违式诖违条例》是明治政府制定的法规性公文,具有法律效力。《违式诖违条例》对于扭转当时日本国民某些违背“公德”的陋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国民的“公德”素质快速提高,不仅仅是日本政府号召的道德教育的结果,主要的是因为重视制定有关促使国民“公德”素质提高的法律有关。政府对国民具有支配力,“这种支配力是直接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是通过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施加这种压力是为了迫使他尽自己的本分来维持文明社会,并阻止他从事反社会的行为,阻止不符合社会秩序的行为”(18)[美] 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令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页。。为了社会有秩序、和谐地不断发展,国家有权利利用法律等手段对社会进行控制,以保证绝大多数人的正当利益,从而为国民谋幸福。人人都有欲望、自由、权利,同样也都有义务。人的欲望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损害其他人的正常合理利益。所以,自国家建立以来,每个国家都会制定法律,以此维护国民的正当利益,以求社会有秩序、文明地发展。法律是非常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促使国民根据法律塑造新的风尚、新的习俗的重要手段。“在一个复杂而又人口众多的社会中,法律履行着一种不可缺少的职能。”(19)[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7页。故而,《违式诖违条例》对于日本国民形成高 “公德” 水平的新风尚、新习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促使日本国民的行为习惯得到很快改观,公德意识迅速提高,社会风貌焕然一新。
二 日本近代具有法律效力的《违式诖违条例》落实与“公德”提升
《违式诖违条例》发布后,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落实、执行是体现其效力的显现。《违式诖违条例》在社会实践中运用,需要公正“司法” 、严格“执法”。
“司法”是司法机关或司法公职人员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定职责,按照法律对民事、形式案件进行侦查、审判的专门活动。“执法”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执法就是指法律的执行,即国家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按照法律程序实施的活动。狭义的执法是指国家执法机关及法律授权、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对于犯罪者依据法律落实相应制裁的活动。日本近代学者坪内孝认为:“我国是立宪政体国家,我们是立宪治下的国民……裁判所有司法裁判所和行政裁判所两种……司法机关即司法裁判所裁判民事刑事的诉讼。”(20)[日] 坪内孝、草刈融:《常识修养录》,东京:松华堂,大正三年版,第52-73页。对于任何违反法律的制裁,一般来说是由国家司法和行政部门执行。“凡缺乏组织强制力之直接并即时支持的事物都不是法律。”(21)[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北京:商务印书局,2015年版,第21页。明治时代学界的一些理论家认为,扭转当时国民缺乏“公德”或违背“公德”的一些陋习、顽疾,必须利用法治的强制力才有可能改观,否则迅速提升全民“公德”水平的愿望会落空。明治政府在学界的推动下,也非常重视有关“公德”法律条例的制定,如《违式诖违条例》,并且非常重视有关法律的严格执行。
“法律内在道德要求有规则,这些规则为公众所知以及它们在实践中得到那些负责司法的人士的遵循。就法律的外在目标而言,这些要求也许看起来具有伦理上的中立性。但是,正像法律是良法的前提一样,根据已知的规则来行动也是对司法作出任何有意义评价的前提条件。”(22)[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8页。每一国家的“公德”提升,来源于每个国家各方面的努力,当然离不开警察的努力。无论一个国家的“公德”多么发达,但也会有个别人出现“不公德”的行为,当违背“公德”的情况出现,此时,我们不禁会想到警察、会期望警察的出现来制止或监管“不公德”行为。当然,国民如果凡事都能做到有“公德”,那就不需要警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公德”水平越高,需要警察维护公众“公德”行为的地方就越少。例如,某一国家的国民“公德”素质非常高,任何公共场合的排队秩序等都不需要警察维护就会井然有序。警察在维护公共秩序的时候,要执法有度,切不要知法犯法。国民有关的“公德”行为,警察有监督、监管的职能,所以必须保障警察的正义、正当、公正、严于律己。为此,日本近代出台了关乎“公德”的“警察犯处罚令”。“警察犯处罚令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宁秩序而发布的规则,此规则中处罚公德违犯条项很多,其列举的事项如果违背的话,会处以拘留或者科料刑。警察胆敢违反公德的这些条项,就必须受到法的强制,如果对违反公德之事放任自流,就会给广大的社会公众造成麻烦,违背有损国家体面的公德,也是犯罪,必须受到惩罚。”(23)[日] 坪内孝、草刈融:《常识修养录》,东京:松华堂,大正三年版,第49页。警察在处理关于“公德”的有关条例的过程中,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秉公“执法”。
如果一个国家制定了完备的与“公德”提升有关的条例、法律,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严格执法体系,否则即使制定了完备的与“公德”有关的条例,也会成为一纸空文。例如,《违式诖违条例》规定:“第二十二条:往河川、沟渠、下水道投掷尘芥垃圾、瓦砾等而妨碍流通者……第四十三条:乘马车在狭隘小路奔走者……第四十五条:不考虑状况而驾驶马车疾驰给行人造成困扰者……第四十七条:死禽或脏物乱扔弃者……第五十条:扫除的人搬运没加盖的粪桶者……”(24)[日]《违式诖违条例》,东京:庆应义塾图书馆写真版,昭和六年,第1-18页。《违式诖违条例》规定的诸多行为都有相应的制裁,或被罚款、或被鞭笞、或被拘禁等,但是如何对违背“公德”的诸多行为进行监控,又如何做到对每一个违反条例的行为都得到相应的制裁,这是一项复杂、艰巨并且细致的工程。《违式诖违条例》与明治颁布的其他法律联合执行,确保《违式诖违条例》在实际生活中的解释落实,避免成为一纸空谈,避免《违式诖违条例》规定的规则、规范与现实中的实行脱节。当然,一个国家的政府,颁布的任何法律条例,与其国家的道德目的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一国民的合法、合理的利益。“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找不到任何理性的根据来主张一个人负有道德义务去遵守一项不存在的法律规则,或者一项对他保密的规则,或者一项在他行动完之后才颁布的规则,或者一项难于理解的规则,或者一项被同一体系中其他规则相抵触的规则,或者一项要求不可能之事的规则,或者一项每分钟都在改变的规则。一个人或许并不是没有可能去遵循一项为负责执行该规定的人所无视的规则,但这样的守法在某一刻必定会变得徒劳无益。”(25)[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7页。优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违式诖违条例》,是“法治”的本质要求和体现。《违式诖违条例》颁布的时候,明治政府也颁布了诸多其他的条例、规则,在落实、执行《违式诖违条例》时,与其他条例一同实行。明治十三年,出版的《罚例类纂》中列举了诸多条例、规则等,其中有“出版条例、新闻报纸条例、报纸杂志法……邮便罚款规则、电信条例、铁道略则、写真条例……天然痘预防规则、检疫停船规则……遗失物取扱规则、卖药规则、药用阿片买卖及制造规则、鸟兽猎规则……保释条例、监狱则……官吏惩罚戒例……巡查惩罚例……府县条规违反罚则、卖淫罚则、禁令”(26)[日]大分県警察本署编:《罚例类纂》,东京:大分県藏版,明治十三年,第113页。。法律条例的落实、执行,需要民众的配合,需要各界人士的协助,需要严格的执法程序,需要执法部门毫无私心地公正执法,杜绝执法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行为,才能使法律条例有很高的效力。
三 日本近代 “公德教育”与“法治”有机结合推动“公德”快速发展
日本从古代开始就重视“道德”教育,但只是重视的“私德”教育,而忽视“公德”教育。日本自古以来可以说是以德治为主的国家,一直到明治时代以前都不能称为“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学界一般认为,明治时代以前,从古代至奈良时代,日本具有“德治”的色彩。“推古朝一直到奈良时代,道德感化的功果非常多是不容置疑的……日本是具有浓厚色彩的以德治国的国家。”(27)[日]高楠顺次朗:[财団法人启明会]讲演集. 第97回》,东京:启明会,昭和十五年版,第53页。日本近代学者佐藤纲次郎也曾论述:“西洋国家以法治为主,东洋国家以德治为主。……特别是我国的国体是彻头彻尾地以情构成的,即使皇室和臣民的关系,也是崇尚‘义为君民,情兼父子’,义理和人情相结合,其他一般社会关系也是以情为根本。耶稣之爱、佛之慈悲、儒之仁等,是我国的特色。”(28)[日] 佐藤纲次郎:《军队と社会问题》,东京:成武堂,大正十一年版,第17-20页。随着明治时代对国外的开放,日本汲取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及文化精华,重视依法治国。“到明治时代,锁国的梦被打破了,开创了‘向世界求知识’的新世界,汲取西洋文化,使与从来文化不一样的推理性文化开花结果……日本法治国的态势、色彩显现。”(29)[日]高楠顺次朗:[财団法人启明会]讲演集. 第97回》,东京:启明会,昭和十五年版,第60页。由此,日本近代依法治国就开始了,正如佐藤纲次郎所说:“立宪政体下的我国是法治国家。”(30)[日] 安芸喜代香:《 通俗教育道话. 第6》,东京:大日本雄弁会,大正七年版,第4页。其实,依法治国并不是摒弃依德治国,而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协同发挥作用。日本近代思想家中柴恵洲指出:“现在人们一开口就说近代的日本是法治国家……然而,法律实际上是道德一部分的成文化,只不过是强制万众实行……今日作为进步社会规范的道德和法律,都蕴含体现在风俗习惯中……由于社会的进步,各种关系复杂化,紧紧依靠不成文的法则、规范,圆满地处理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团体与团体之间关系等变得困难,作为成文规范发布成为必要,于是法律出现。法律是外在的规范,道德是内在良心的规范。”(31)[日] 中柴恵洲《日本国民に告》,东京:瑞景阁书院,昭和五年版,第65-66页。
自明治时代开始,日本不再仅仅重视“私德”教育,而且还非常重视“公德”教育。家庭、社会、学校全方位的“公德”教育体系在日本逐渐形成。明治时代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进行了改革,德育的教材中都增加了“公德”教育的内容。日本近代开始也不再只是重视以德治国的国家,而且还是依法治国的国家,重视“法治”与“德治”二者的紧密结合。因为“德治”与“法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不仅仅是“法治”与“德治”在功能上的互补,而且二者目的都有相同的趋向。“法”也是符合道德的良“法”,“德”也是符合法律之德,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故而,明治时代开始,日本的“公德”教育,与惩治“不公德”相应的“法治”紧密配合,相互协力。日本近代,自明治时代采用《违式诖违条例》的“法治”与“公德教育”的目的具有一致性,二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协同共同起作用。国家用政令训导国民,借助于法律治理社会。“法治”目的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益,惩治危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构建和谐的社会;“公德教育”的目的也是维护每个人的利益,维护优良的社会秩序,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道德早于法律而产生,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有国家权力时候才出现,法律的制定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为了维护人们的正当权利不受侵犯。“法律是通过国家权力而实现,道德是以人格的发达为条件;法律是外部的,道德是内部的;法律尊外在的形式,道德尊内在的心情;道德比法律更具有积极性和根本性。”(32)[日] 文検受验研究会:《文部検定修身科教案提要》,东京:启文社书店,大正十四年版,第315页。“法治”是依靠法律而治理社会,“德治”是通过道德而治理社会。只不过“法治”与“德治”的范围不同,“德治”的范围比“法治”的范围广泛,并且“法治”具有强制性而“德治”不具备强制性。道德教育是劝导人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法律是强制人必须不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然而“法治”与“道德”又是紧密联系的,“法律面向国内是保护各个人的权利,这些权利首先是正义的,而什么是正义的问题也是道德的问题,法律和道德是紧密联系的”(33)[日] 井上哲次郎 (巽轩):《巽轩讲话集.初编》,东京:博文馆, 明治三十五年版,第514页。。日本明治时代的《违式诖违条例》,是提升全民“公德”水平有关的条例,其法律效力是正义的,也是根据当时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内在要求而制定的,是符合国民和国家利益的。“国家是文化的国家,依法实现自身,也依德实现自身,任何国家也会依靠权力技能实现自身……法治和德治是文化国家的两大原理。然而我们如何思考什么是法治、什么是德治以及法治和德治关系?我们回答此类问题依据国家的本质才能明确。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在东洋,我们看到一般是把道德性的东西乃至宗教性的东西作为宇宙的本源,由此看出考虑政治重视德治的立场。”(34)[日] 长田新:《国家教育学》,东京:岩波书店,昭和十九年版,第186页。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效仿西方国家重视依法治国。日本近代在全体国民“公德”提升方面,也借助了“法治”,并且把重视对“不公德”的“法治”与“公德”教育有机结合,“法治”成为日本近代“公德”快速提升的强大推力。
当然,重视“法治”,也不忽视德治,是近代日本提升全体国民“公德”素质的国策。无论任何国家,教育是必要的,道德教育也是必要的,当然道德教育中的“公德”教育也是必要和重要的。“教育对于国民来说是必要的……须对少年国民进行普及教育,是一个国家坚固的根蒂,也是文明的本旨。教育分之为三,一曰庭训(即家庭教育),二曰普通教育,三曰高等教育。对人有智育、德育、体育之别。”(35)[日] 普通教育会 编:《国民読本》,东京:国民书院,昭和九年版,第303页。“公德教育”属于“德育”的一部分,一个国家不断走向更加文明,需要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尤其需要“公德”意识的不断提高,故而“德治”离不开“公德教育”。“公德教育”在提高国民“公德”素质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每一国民的秉性存在差异,每一国民的内在德性存在差异,每一国民自律性存在差异,由此通过“公德教育”,提高国家的“公德”整体水平,对大多数国民来说会有成效,但“公德教育”对个别人不起作用,只有通过“法治”才能扭转个别人“不公德”的恶习、陋习,此种状况下,“法治”予以提高国家的“公德”整体水平以强大助力。日本近代《文部検定修身科教案提要》指出:“道德通过法律被补充,法律是以道德性原理为基础而统一。”(36)[日]文検受验研究会:《文部検定修身科教案提要》,东京:启文社书店,大正十四年版,第315页。在日本近代,日本利用《违式诖违条例》的“法治”与对国民自少儿起就进行的系统的“公德”教育密切结合,使日本国民“公德”水平得以迅速地提高。
四 余 论
“‘公德 ’是处理个人与一般人关系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规范与社会准则。”(37)史少博:日本近代道德论的流变《世界哲学》,2019年第6期,第75页。国民“公德”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大力倡导社会公德, 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38)陈来:《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文史哲》2020年第1期,第23页。“法律”是“道德”中一部分的成文化,并且是强制性要求国民践行“道德”中的那一部分,故而“法治”与“德治”密不可分,倡导“公德”、发展“公德”需要“法治”的协同和保驾护航。“政府有规定条例的权力,同时享有对违背条例、规范的行为强制处罚的权力。提高全民的公德意识,提升全民的公德水平,只凭借理论家的呼吁和道德的约束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强制力量的护航。”(39)史少博:《明治时期西村茂树“公德论”之建树》,《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20页。日本近代“公德”由被欧美国家的人耻笑、侮辱,到日本“公德”受到世界赞誉的飞速发展,其背后都是因为日本近代制定了有关促进“公德”发展的细致“法治”条例作支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近些年的“公德”虽然取得可喜的进步,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更好地发展,相关“公德”建设的“法治”条例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日本近代重视采用“法治”促进“公德”发展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