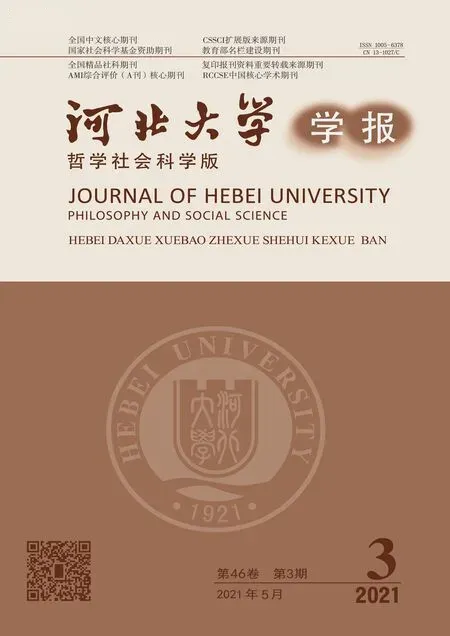清末民初公共卫生体系发展视域下的伍连德抗击东北肺鼠疫再探究
程丛杰
(莱斯特大学 国关、政治与历史学院,英国 莱斯特 LE1 7RH)
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刺激了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伍连德作为此次疫情防治的关键人物备受学者关注。现有研究多为三个方向,各国对疫情所采取的防控方法[1],伍连德取得防疫主权过程的考证[2],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进一步探究[3]。以上成果对本文提供了学术支撑,但就伍连德与此次疫情对中国建设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的推动作用这一角度仍有讨论的空间与必要性。例如,清廷为何会如此信赖身为西医的伍连德?完善的公共卫生有怎样的政治作用?伍连德个人的阅历与人脉是如何助力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发展的?本文拟以伍连德治理1910—1911东北肺鼠疫为链接点,运用中英文献,探析伍连德对中国建设公共卫生体系的积极影响,希冀呈现晚清至民初以来不同社会与政治情境下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演变。
一、晚清社会转型中公共卫生的引入
中国发展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公共卫生引建于西方。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及后续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签署,西方势力开始影响晚清社会的各个层面,西式的公共卫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华进行更多商业活动的同时,将中国通商口岸城市的公共卫生建设上升为国际性问题,屡次要求清政府从中央层面对西医应用进行制度化构建[4]。另一方面,随着大量西方人来华定居,他们建立的卫生机构影响着地方民众对西医和公共卫生的认知。
不同于西方由官方主导的公共卫生制度的设置和行政理念的推广,中国民间在官方渐次施行公共卫生举措前已通过传教士对西医有所接触。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教会开始以西医作为传教手段。管治权并不在清廷手中的澳门于1827年成立澳门眼科医院,美国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35年在广州开设中国大陆最早的西医诊所——眼科医局[5]22-25,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该诊所在早期免费为当地民众治疗,本为眼科医生的伯驾应病人请求也治疗疝气、肿瘤、麻风等疾病。伯驾的资助者是第一个海外美国基督教归正宗传教机构,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下的公理会差会,资助伯驾的主要目的就是以西方医学作为证明基督教优于原住民信仰的一种手段[5]47。至1877年,美国在华的41个传教点已经建立16家规模不等的医院以及24间诊所,每年累计接待70 000名左右的患者[5]227。此外,传教机构在华的医疗活动还包括建立医学堂,如1899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在上海先后创立的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即同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前身[6]。以上医学院都得到过欧洲传教组织的资助,并在成立早期免费为患者提供治疗甚至培训医师,使得西医逐渐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
由西医引申发展的公共卫生也影响着地方政府。租界作为近代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各种公共卫生条例先在租界施行,华界随后效法。上海法租界早在1869年便发布《肃清街道之规章》,禁止乱扔垃圾和随地大小便。租界街道的逐步整洁使得一墙之隔的华界民众看到“上海人多地狭易集污垢,华人无预防之智识”[7],华、洋两界的卫生状况渐有“一洁一污如上下铺”之别[8]。上海县衙于1872年颁布《示禁随路便溺》,明昭“重罚任意便溺者”[9],并仿照租界的粪秽股成立上海垃圾局,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出台公共卫生相关措施的先例[10]102-105。如传教士建立的医院一样,大多数公共卫生规定仅在通商口岸城市颁布,华界效法的规定亦多为告示性质的示谕,缺乏行政制度的保障与约束,效果与执行力度都不尽如人意。上海华界在1890年代仍是“大街尚属清洁,小巷堆积如故”[11],因而这一时期并未改变整体中国民众对西医和公共卫生的认知。
与此同时,清廷也开始着手组建国有的医学院和公共卫生机构,这属于清末新政效仿西方国家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在文教改革中倡导建立国有的医学院。1902年11月,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以徐华清为总办,聘请日本驻军医院院长正平贺精次郎为总教习,在天津成立北洋军医学堂,即“中华民国国防医学中心”的前身,这是中国第一所采用西医教学的军医院[12]。而公共卫生行政制度的构建则源起于警察制度的改革。1905年,北京裁撤五城御史,效仿日本成立巡警部,警察卫生作为警察制度的组成部分被建构起来。巡警部下属的京师内外城警察总厅下辖卫生处分为清道、防疫、医学和医务四科,负责管理北京城的公共卫生事务。次年,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扩建为卫生司,具体负责公共卫生、筹建医院、药品检测等事务[13]。北京公共卫生行政化改革起到示范作用,公共卫生从民众接触,地方改良,逐渐演变为全国范围的制度性推广,各地如广东等省份意识到“卫生机关欠缺,卫生行政急需扩张”“中法西法俱优,应相辅用于军中”[14]。浙江巡抚冯汝骙直接效法北京,在全浙设立卫生科,拨经费组建卫生警队,负责街道清洁、贫民就诊等公共卫生事宜[15]。
“西医东渐”是晚清社会整个西学东渐转型过程的一部分。这一时期西方的医学与卫生体系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虽然无论是清廷还是传教医生建立的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多集中在大城市。但中央、地方和民间层面的现代医学观念已有所提升,能逐渐认识到西医的实用价值,整个晚清社会已经逐步开始从中医到西医卫生系统的行政理念和制度设置的转型。
二、伍连德归国与早期政、医人脉的积累
身为新马华人的伍连德在晚清社会转型期归国,至东北肺鼠疫暴发前已官至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已是当时顶级医学院的核心职位。这一过程中反映的文化情思和身份认同,既有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也与伍连德在工作学习中结识的人际网络的助力密不可分。
归国前的伍连德从没有与祖籍国发生文化与情感上的脱节。1902年,伍连德在意曼纽学院完成硕博学业,为剑桥大学史上首位获得医学博士的华人,于次年返回马来西亚开设一家诊所[16]255。工作时间以外的伍连德投入到新马华人社会的改良运动中,返乡不久后成为《海峡华人杂志》的主编之一。该杂志由新马华人宋旺相和林文庆创办,主要选题围绕华人的民俗改良、民族认同与反歧视等内容[17]。伍连德曾以英文文章在该刊上呼吁西方对所谓的“黄祸”应该“以渊博的知识给予对方深入的了解”。伍连德还组建雪兰莪文学辩论会,定期在华人社区举办提倡改俗的相关演讲和辩论会,举办过提倡女校建设、鼓励男子剪辫易俗、杜绝鸦片赌博和酗酒、改良华人传统婚葬中的陋习等主题活动[16]230-233。同时,伍连德还对国内事务积极关注,这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1904年美国政府要求续签限制旅美华人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从而引发东南地区的民间反美运动[18]。伍连德随即在滨州的华人会馆中呼吁海峡华人声援上海等地的抵制美货运动[19];二是清廷于1905年派出考察团赴欧美日等国考察宪政,当第二组考察团转道槟城时,伍连德组织当地华侨迎接,向考察团了解国内状况并介绍当地侨情。伍连德在这次活动中遇到他的伯乐——施肇基,施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学校,后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16]278-281。相似的教育背景使两人很快成为朋友,二人的友情持续一生。
正当伍连德在家乡的事业蒸蒸日上时,一件事改变了他的命运。1906年,伍连德参加马来西亚禁烟运动,因积极向民众宣传吸食鸦片的危害而遭罂粟园主记恨,被反诬藏有医用鸦片而被当地法院判决制裁。正当伍连德意志消沉时,前文提到袁世凯创立的北洋军医学堂邀聘伍出任帮办,经过短暂的考虑与准备后,伍连德参加完1907年伦敦禁鸦片烟会议后,于次年5月到中国履职[16]303-304。
伍连德归国初期建立的人际网络对其日后发展起到很大作用。1908年5月伍连德前往天津途中转船上海,虽然只停留十天,却结识一批拥有相似教育背景、随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的外交次长颜惠庆、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推动基督教发展的曹福庚等人[16]276,并且加入了由西方在华医学传教士于1886年成立的中国博医生。抵达天津后,伍连德拜会当时的“御医”,北洋医学堂总办屈永秋医师,并结识其助手全绍清和学生邓松年与陆存煊[20],初步建立回国发展的政治与医学关系网络。在随后的东北肺鼠疫中,就是施肇基推荐的伍连德,全绍清、邓松年与陆存煊则前往辅助。伍连德经常参加博医会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年会,结识了更多的同行,这些人都多少助力伍连德的医疗卫生事业,如医博会会员王吉民就和伍连德共同编篡了《中国医史》[21]。
这里要说明的是伍连德最终上任并非一纸任命这样简单,得益于其早年生活与学习中结识的人脉。向袁世凯举荐伍连德的是时任北洋营务处会办的程璧光,二人因伍连德任海军军官的二舅林国祥而相识。1896年林国祥与程璧光、谭学衡、杨联甲、卢守孟、陈镇培六位海军将领前往英国监造订制的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程璧光和谭学衡与正留学剑桥的伍连德结成忘年交。当伍连德于1908年11月初抵达天津准备进京谒见袁世凯时,清廷中枢发生突变,慈禧与光绪在11月14日和15日先后去世,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随即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旨“开缺回籍养疴”将袁世凯贬回河南老家。伍连德或将受到连带影响,此时已升任陆军部海军处副长官的谭学衡为其奔走,向顶头上司陆军部尚书铁良举荐伍连德。谭学衡为伍连德准备朝服和假辫,反复排练面试礼仪与预设问题[16]106-108。伍连德最终得到铁良的赏识,被授予回国后的第一个职位——陆军军医学堂帮办。
从伍连德完成学业返回家乡到最终选择回到祖籍国发展的经历,反映出那个时代海峡华人对中国近代以来发展与改革的关切,也呈现出伍连德所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为自己的族群做出一份贡献,渴望被需要的共识。最终在历史的偶然必然间,伍连德在多层关系人士的助力下在天津开始了三年教学时光直至东北疫情暴发。
三、东北肺鼠疫背后政治与医学的博弈
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既是中国公共卫生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反映出完善的医疗卫生在捍卫国家主权中的政治作用。1910年10月25日,疫情最早暴发于满洲里,随后沿中东铁路传播,至次年一月已蔓延东北全境乃至京冀鲁地区,在短时间内造成总计52462人死亡[22]。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已争夺中东铁路多年的日俄两国却将此次疫情视作一次契机,都派出本国的细菌专家,借掌控疫情治理权向东北扩张势力。
东北肺鼠疫对中国造成潜在的主权危机不亚于疫情的扩散。除日俄两国外,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也在疫情暴发前一年提出“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和“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意图出资为中国赎回东北各段铁路,从而将美国的势力引入东北[23]。疫情的扩散则加剧局势的复杂化,1911年1月疫情扩散到南满铁路日本势力范围后,关东都督大岛义昌迅速在旅顺和大连成立防疫指挥部,加派军警挨户对华人居民进行强制检验,俄国一面在疫情暴发后对铁路附近华人施行粗暴隔离,一面向诺克斯建议由俄国医生主导疫情的防治,并向东北中心地区增派军队[24]4。俄国的实际目的是想以医官接管东北各地,这场疫情演变成各个列强争夺中国领土主权的筹码。
伍连德便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奔赴东北的。早期疫情防治工作的失利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形成国家力量大规模介入地方疫情治理的行政理念。负责哈尔滨疫情治理的吉林省西北路兵备道道台于泗兴,便认为防疫应主要由社会力量负责,官方提供经费。地方政府聘请的中医却成为此次疫情罹难者中按职业划分占比第二高的人群,仅次于负责搬运病患的医工[16]42。同时期哈尔滨俄管区的疫情控制相对较好,使得地方官逐渐认识到防控需要西医。当时哈尔滨全城竟没有一名西医,东三省总督锡良只从奉天找到两名中国西医和一名日本医生,并致电清廷中央加派西医专家[25]1122。在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力荐下,1910年12月21日伍连德与好友全绍清被派往哈尔滨调查疫情[26]。负责统筹防治工作的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务部,也表明清廷对东北政治局势的关注。
各国医生对疫情的调查是医学与政治的双重竞争。伍连德抵达哈尔滨后立即解剖一具患者的尸体进行细菌培养分析。在当时认定这是某种鼠疫,但伍连德认为它不是常见的腺鼠疫,而是一种新型的芽孢杆菌[16]13。伍连德的迅速分析证明了中国人的医学能力,得到俄国铁路管理局总办霍尔瓦特将军的认可。俄国在此时转变策略,决定在防疫问题上联合中国共同对抗日本。美国也采取类似的态度,总领事费舍尔向日本专家北里柴三郎指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各国应共同抗击疫情,日本对东北情势的了解不会高于中国政府”[27]32。加之施肇基在朝廷内为伍连德各方奔走,最终伍连德在多方医学与政治双重角力下被赋予防治此次疫情的全权。
同时,清廷中央逐渐与哈尔滨地方政府进行紧密的合作以尽快遏制疫情,责令内阁各部对东北地区予以支持,强制关闭部分铁路段,并沿铁路线设置隔离站,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先后拨银30万两,并允许东北地方政府向交通与大清银行再借款30万两,为抗疫提供资金保障,并紧急成立京师防疫局和哈尔滨防疫局[28]。哈尔滨地方当局在伍连德的指导下制定有效的防疫措施。伍连德首先发明一种简便实用的口罩,这种口罩医用纱布即可简单制作,口罩的佩戴对防止医护人员感染起到非常重要的效果,被公认是N95口罩的鼻祖之一[29]。此外,伍连德将哈尔滨内的疫区进行分区隔离,调配1700多名军警控制各区人口流动,防止交叉感染,所有医护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消毒。还向东清铁路租借车厢对咳嗽、发热等早期症状的人员和接触者进行7天的隔离观察[16]25-26,这便是沿用至今“疑似病例”概念的来源。最后,伍连德发现患者尸体是重要的传染源,病死者本在棺木中下葬,随着疫情的扩大加之哈尔滨正值寒冬,死者激增且冻土挖掘困难,大量尸体就被放置在墓地周围甚至家中。伍连德克服巨大的伦理困难,说服哈尔滨地方官员上奏朝廷对尸体进行集体火葬。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用火化的方式集体处理受病毒感染的尸体[30]。此后,俄日辖区和东北各地也开始对死者尸体进行集体火葬。经过努力,死亡数字从1911年1月31日开始下降,至3月1日,记录最后一个新增病例[16]46-48。中国随后宣布召开具有对疫情总结性质的万国鼠疫研究会,标志次此肺鼠疫的平定。
万国鼠疫研究会是伍连德个人的高光时刻。这场会议于1911年4月3日举行,历时20余天,邀请来自美国、英国、日本、俄国等12个国家的24位专家[32]7-11。伍连德在会议上发表多篇报告,对此次肺鼠疫的传染源、中国的防治措施、具体的病理学分析、经验与不足等做出透彻的分析[29]83-85。为表彰伍连德,清廷授予伍陆军少校加医科进士,摄政王载沣亲自代表年幼的宣统皇帝授衔。沙俄政府也授予伍连德二等勋章[16]498。 后来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陈垣在所著《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称赞伍连德“致力于国家医学,受命于外国威胁……为吾国后起之英,学术品德为世人所推重”[32]17。
东北肺鼠疫的成功治理不但挽救无数生灵以及捍卫中国的主权,还直接推动中国医疗和公共卫生的进一步革新。中国的社会风气也被注入一股新气象,正如锡良在鼠疫研究会的致辞:
鼠疫为中国近世纪前所未有,一切防卫治疗之发,自当求诸西欧。但恃内国陈方,断难收效。……各国明哲所发明最新最精之医理,吾民又焉可阙焉不讲?……本大臣服膺是语有年,中国医术卫生,近亦渐知研究,将来之力求进步,并对于卫生上之若何注重,当全力一致行之。[32]1-4
锡良的话表达清廷官方的态度,承认公共卫生体系在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作用,这次疫情也让官方意识到完善卫生体系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会议进行期间的1911年4月17日,近代中国第一部国家级卫生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颁布[10]117,明确统一了各地方省份的具体防疫措施,全国性科学防疫体系已初见端倪。虽然伍连德此行是医疗目的,但他通过身体力行协助解决中国的外交危机,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还改良了民间传统与伦理文化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在解剖尸体、发明口罩、施行隔离、集体火葬等许多方面开启风气之先。
四、中国常设性医疗卫生组织的逐渐建立
1910—1911东北肺鼠疫直接从宏观层面推动了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持续发展,而伍连德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具体体现在两点:一是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后,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下简称“总处”)作为全国性常设医疗卫生体系的一部分正式成立;二是伍连德在平定疫情后几乎成为中国在国际医学交流上的代言人,致力于推动中国发展自主的医学机构,包括建立国有医学院和落实海关检疫自主化等。东三省总处的成立开启中国建立常设性防疫机构的先河,有别于临时性机构的京师防疫局和哈尔滨防疫局。出任总督察的伍连德除负责研究并管理各种传染疾病,还策划改革中国医疗和医科教育。虽然清朝在肺鼠疫平定的当年就覆亡,但继续自主发展现代公共卫生已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这也是伍连德随后的事业方向。
东三省总处在当时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家级卫生防疫机构之一,代表着中国公共卫生学的先进理念,伍连德将全部心血投入其中,利用自己的人脉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总处的运行。总处隶属于外务部,伍连德在归国初期结识的好友颜惠庆此时已官至外务部左丞,在行政上给予诸多便利。总处的运行费用来自海关税和地方拨款,拟定年经费为七万八千卢布[33]7。但中国的海关被用于抵押庚子赔款和外债而由北京外交使团掌控,伍连德刚到职便与哈尔滨海关税务司梅因斯·沃森交好。沃森为人干练,对中国建立现代化医疗体系深表同感,在3天内便完成一份详细的备忘录,计划总处年预算为关金60000两,设总处总院于哈尔滨,分院在满洲里、拉哈苏苏、三姓和大黑河,还为总处提供一间办公室[33]5。但辛亥革命爆发打乱了总处的建设进程,较为独立的哈尔滨海关税收被外交使团节流,拒绝提供原定的经费。伍连德为此亲赴北京,颜惠庆引荐其拜会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在安格联的积极斡旋下,伍连德先后拜见各国公使,并最终说服外交使团恢复拨款[33]64-67。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伍连德短时间内在东北地区建立起包括医院、实验室和检疫站的卫生网络,聘请到在剑桥的学弟陈永汉和陈祀邦、学生陆存煊林家瑞和邓松年、奥地利细菌专家伯力士、英国细菌学家雷诺兹等专家。事实上,总处的人事基本上全是他的“关系户”,但伍连德反而更注重职工专业素养的提升,与沃森协定另拨出经费为总处的医官做出国深造之用,这就保障了人才与医学技术的不断更新[34]。伍连德的努力很快在实践中取得效果,在1910—1911年肺鼠疫之后,总处先后迅速参与防治了1918年晋绥鼠疫、1920—1921年东北第二次肺鼠疫、1926年东北霍乱、1928年通辽鼠疫等,上述地区再未发生第一次肺鼠疫那样的惨重伤亡。尤以在应对1926年霍乱时表现突出,哈尔滨此次霍乱仅有280例,总处下辖的滨江医院收容患者的救治率高于苏联的东清铁路中央医院[35]。
另一项代表总处成果的是伍连德主导的一系列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以定期报告的形式记录在案,代表中国在国际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言,最早在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上发表的关于疫情分析报告就被《柳叶刀》转载。肺鼠疫结束后伍连德带领陈祀邦、俄国专家萨伯罗尼教授等组成的中俄联合考察队前往中俄边境考察旱獭间鼠疫流行状况,这次调研结果被伍连德以《旱獭与鼠疫关系的调查》于1913年第二次在《柳叶刀》发表。1911年和1913年,伍连德还两度代表中国参加海牙万国禁烟大会,从1923年开始参加两年一度的远东热带病医学会议,并于1924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委员会的医学研究基金,该项基金专门授予世界性的杰出研究人员[16]517-522。在此期间,伍连德发表诸如《论肺炎疫》(1926)、《结核病与鼠疫的混合感染研究》(1926)、《华北鼠疫状况》(1926)、《鼠疫手册》(1932)等专业性论文,出版《世界鼠疫暴发记录》(1932)、《已知或疑似感染鼠疫之啮齿动物》(1932)、《中国医史》(1932)等医学史类的文章和书籍[16]98-102。具体到公共卫生行为,伍连德呼吁改进传统就餐方法,1915年发表《中国卫生餐台》号召每人一副公筷一副私筷,并制作一种可旋转的餐桌以减少配菜时的接触,这便是今天旋转餐桌的来源[36]。伍连德的文章、书籍和总处的年度报告全以英文形式发表,这些成果获得更多国际认可的同时,也引来国外专家和资本对中国卫生体系的关注。伍连德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争取各方投资先后参与建立了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21所各类院校,共计床位2387张[16]407。
九一八事变前后伍连德的工作重心由于东北的沦陷而转向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全国海港检疫处。对于海港城市的防疫管理,既关系到医疗公共卫生,也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伍连德任职东三省总处时已经对中国的海港检疫极为关注,在1920年便主导成立营口海港检疫所,又考察十余座中国沿海城市检疫状况,先后发表《远东之检疫问题》《中国1930年之前的海港检疫》和《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历史》等文章供卫生部参酌[37]。甚至在申报公开发文向国民政府呼请收回海港检疫权,将检疫权的归属上升到关乎民族健康的高度[38]。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28年10月4日做出成立全国海港检疫处总部的决定,并于1929年7月26日向国联卫生部发电,邀请派团来华考察医疗和协助建立海港检疫[39]。国联卫生部在1930年1月份派出考察组,其中专门负责传染病检疫的帕克医生(C.L.Park)发表有利于中国的报告——《上海港建立海港检疫之必要》,提议应将上海特别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三处的检疫机构进行整合,由中外各方都能接受的伍连德博士统一管理[40]58-59。1930年7月1日,海港检疫处总部在上海成立,下属总务、医药、防疫、消毒四个部门,分处包含广州、厦门、汉口、秦皇岛、天津等地,伍连德任处长兼管总务科,其余所有政医主管全由中国人担任[40]6。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于国民政府卫生部,统筹全国检疫行政业务,标志着中国正式收回海关检疫主权。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与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是伍连德推动中国常设性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的集中体现。以这两个机构为立足点,伍连德在致力于医学研究的同时,促进着中国医疗现代化和公共卫生体系的普及,还代表中国在世界科研领域发言,吸引国外力量对国家医疗卫生建设的关注,兼具了学术与务实。伍连德在这个两个机构虽主要为专业性职位,但与政治却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视作其学术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相辅相成,证明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对国家构建的重要作用。
五、结 语
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是清末民初社会与政治文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暴发前夕,中国正在经历从民众、地方到中央渐次对西医的接受与发展,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制度建立到雏形阶段,而非一片空白。这种时代背景为伍连德返回祖国施展提供了平台,因其所具备的医学知识是晚清社会改革所需要的,其独特的身份背景也是中西文化最能接受的。而伍连德个人在学习、工作与归国过程中集结了不同维度的人际网络,这些网络又涉及其他的资源、知识、资本与医学技术的流通,与所掌握的西医科学知识一并将其引入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科学的核心,使得可以将伍连德个人与中国民族现代化发展加以同步研究。
到东北肺鼠疫的暴发,日俄均以中国现代防疫能力与公共卫生制度不完备为由企图进一步蚕食东北。此次疫情演变成为涉及中国主权的国际性问题,迫使清政府以现代医学应对外交压力,这更是伍连德的专业知识被朝廷所更加仰仗的因素。中国最终在伍连德的指导下成功地遏制住疫情,度过一次政治危机,展示现代医学与国家主权的紧密联系。而对中国整体“西医东渐”的转型而言,疫情的成功治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疫情结束后,由国家层面倡导的公共卫生机构与制度的建设促进了专业实验室、医院、卫校的建立以及学术期刊、研究组织的创立,这些都推动着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普及。伍连德一直到抗战爆发后返回马来西亚都为这一过程做出突出贡献。集西方资源和技术以及民族身份于一身的伍连德以医学研究为当时主权沦丧、民众缺乏自信的中国提供获得国际认可的一面,在实质意义上除促进公共卫生发展外,也体现出现代医学在提升民族自信,构建国家形象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