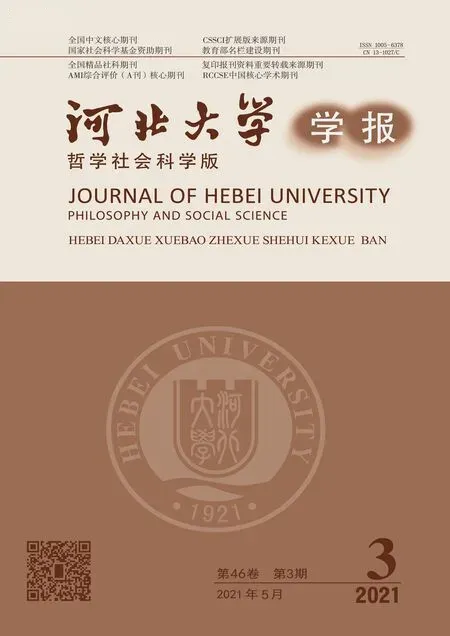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
——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黄仕坤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国内学界对“知行合一”的解释,主要着眼于其日常伦理实践的内涵,且解释路径大概可分为三支:其一,以“知行合一”之“知”为道德意识,认为“知行合一”指道德意识转化为实践行为,如吴震言“‘知’主要是指德性之知,‘行’主要是指道德实践”[1];其二,以陈立胜、方旭东为代表,将“知”理解为“意志”[2]或包含意志于其中的“意向”[3],而“行”则涵盖念动至外在道德行为的整个过程;其三,以陈来为代表,将“知”解为“道德意识”“一般知识活动”“意识、意念、意欲”和“良知”等意[4]110-125,这又大概可归纳为道德意识、意志、一般知识活动三者,而“行”则被定义为“心理行为”和“物理行为”[4]117。这些解释路径,对于“知行”的界定或有所不同,但共同之处在于皆主要从伦理道德实践层面讨论“知行合一”,并且将知行主客二分化了。海外学者方面,亦存在类似情况。如成中英认为“知行合一基于意”,这与将“知”认为是道德意识或意志的解释路径相类似,其阐释仍然主要是围绕伦理道德[5]。又如Xiaomei Yang在其论析“知行合一”的文章中将知或良知界定为 “moral knowledge”, 或其在文中讨论的Julia Ching,Weiming Tu和Antonio S.Cua等学者对“知行合一”的阐释,这些学者的观点虽有不同,但亦主要域于伦理道德范围[6]。
就伦理道德实践来指点“知行合一”,确实是王阳明在论述“知行合一”时的侧重之处。然而,“知行合一”不仅涉及道德,而且关乎存在。因为,王阳明之“知行合一”承“心外无物”的蕴旨而来,并以对治主客二分的理解路径造成的知行二分为目标。因此,将“知”与“行”分别理解为作为主体的道德意识、意志与对象化行为,不仅无法触及“知行合一”的存在内涵,而且将道德主客二分化了。
一、心外无物
王阳明之“心”作为本体与现象不同,既非有“自性”的存在物,也不是事物的普遍本质。因此,王阳明曰:“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7]119这意谓“心”在大化流行之存在中显现自身,故不可将其当作现成存在者。因此,作为非现成存在的“心体”超言绝相而不可见,但现实存在物则可用语言论述之。王阳明论之曰:“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夫有而未尝有,是真有也;无而未尝无,是真无也;见而未尝见,是真见也。”[7]279“心即道”[7]23,“心”作为道,无形无象,非现成的经验存在但又非空无,所以其不可成为理性的对象,不可落于言诠。如此,“心体”不可以肉眼得见,而只能以心证之,故见而未见。王阳明喻之为:“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7]40可见,这种由体证而来的道,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通过理性思维推理而有之“noumenon”并不相同。
王阳明之“心”作为道,并非只是伦理道德的根据,更是万物存在的本体。因此,对王阳明而言,“物”非冷冰冰的主客二分的自在之物,而是心体之开显。王阳明论“心外无物”曰:“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7]6“意之所在便是物”,并非指意着于物,而是意使物“存—在”①“存—在”旨在突出“存在”一词的动词含义。后文类似的构词法皆本此意。此构词法受张样龙“缘—在”构词法启发。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1.出来。换言之,心、意、物一体不分,物之存在即是意,而意便是心或良知。因此,王阳明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7]115。心物一体,良知灵明使人与天地万物得以自然地开显为如其所是的存在,但心体又是不离万物的,故王阳明曰:“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7]136。可见,王阳明认为,存在的真实情状是“心外无物”的“万物一体”之一体性存在。正因存在一体不分,故人的良知即是草木的良知。王阳明曰: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7]118
并非有人与外在之草木瓦石两种存在,真实存在的只是一个存在,即人与草木瓦石一体不分的存在,而此存在的本体即是良知灵明,故王阳明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换言之,良知因其开显的无限性使物不断新生而无自性,并使物开显为一体化生的存在。正是基于物的“一体化生”性,王阳明将“物”称为“事”——物的存在即是良知的发生事件,是一体性存在关系的显现。
综上而言,万物皆以“心”为体,但心非存在物,故心不可以理性知而只能以心证。因此,对良知心体的“知”,不可能是主客二分式的。此外,心与物体用一如,并呈现为现实存在的一体不分,即人之意念、身行与人之在、万物之在一体不分。而正是这真实存在的一体不分,使“知行合一”之“知”与“行”皆获得了超越主体伦理道德的存在意涵,并成为“知行合一”之“合”的存在实情。
二、知行本体
将“知行合一”之“知”解释为“道德意识”,无法保证其必然转化为道德实践,且未能解释王阳明以“念”为“行”之意。例如将“知”理解为意识,认为意识(“念”)是整个行为的第一个阶段,则“知”与“行”之间仍然存在着“同质的时间差”[2],故还不是真正的同一。因此,陈立胜将“知”界定为“意志”,认为知行“是同一行动中交互渗透的两个向度”[2],即意志发动行为并在整个行动中照看着行为。然而,这种“‘照察意义’上的合一”[2],仍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未能将“知”与“行”真正同一;而且将“知”理解为“意志”,与王阳明为说明“知行合一”所言的“知痛”“知饥”之“知”不通。另一方面,将“知”理解为“一般知识活动”,而以类似“知痛”之语为讨论知识来源于实践,亦无法说明王阳明为何用知识起源于实践的例子,去论证所谓的道德之知必然转化为实践行动;而且在这类知识论诠释中,知行或可言不离但亦难同一。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诸论将“知行合一”之“知”与“行”主客二分化了,进而将“知行合一”之“合”理解为主体与对象行为的符合,并将其内涵主要限于主体的伦理道德实践范围内,以致遮蔽了知行的本然。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对治知行二分的功夫,其“知”与“行”皆应从存在层面理解,因为知行的本然指向着作为万物本体的良知。王阳明在《答陆原静书》中曰:“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7]75此处之“本体”就本然讲。“知行”之本然是良知,即“知行”皆为良知心体之开显。这意指“知”与“行”虽以功夫论,但二者之实质则为良知开显之“用”。
再者,王阳明曰:“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7]106。“发动”意指“开显”,这表明良知开显之“几”——意念之萌动,已是良知之“行”。可见,“行”在王阳明那里包含着念、视、听、言、动等人的意念、身行。又因为,“心外无物”之“心”非主体化之心,“物”亦非现成自在之物,即真实的存在乃是心物一体化生之在——人之意念心知、视听言动与万物的开显相融一体、无有间隔,故而人之心念乃至视听言动作为“行”,皆关涉人与物能否如其所是地开显自身。换言之,就真实的存在而言,人之“行”即是人之“在”,同时也就是万物之存在,而没有意念与身体,或人与物的区分,只有“存—在”——不断涌现着的存在。因此,“知行合一”之“行”的最深远的意蕴乃指向“存—在”,即指向万物之良知本体的开显本身。由此可明,以“念”为行并非将“行”的概念内涵泛化,即如王夫之或后来有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是把外在客观的行与心理活动相混淆。相反,这恰揭示了“念”的真实内涵——念即存在:一念之起即是良知之开显,世界之生化,类似佛家之“一念三千”。
另一方面,“生知”之“知”作为良知之“用”,指向良知明觉之自知,其就人而言则称为“体知”。良知作为明觉与“体知”表现为体用关系。因此,“生知”意指不虑而知,这缘于良知本体自然能知,即良知明觉自然发见而知良知自身。又因为良知是万物之本体,不离万物而在,所以良知明觉之发见即是存在的开显。因此,“知行合一”之“知”,指良知开显“心物一体”的存在而抵达自身。而“行”作为“安行”则指良知自然而然地要开显、澄明自身为“心物一体”的存在。因此,“知”与“行”实为同一个存在的两个面向,即良知明觉之发见与良知的开显是二而一的。换言之,就真实的存在而言,存在是明觉通透、充满光明的存在。就人之存在言,心道为一之圣人,良知自然开显,无所思虑而自然地“存—在”。由此,对于得道之人,“知行”作为功夫,即是随顺良知开显光明通透的存在,而明觉良知自身。
可见,“知”与“行”一体不分,知即行,行即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7]46。若知行二分则“已被私欲隔断”[7]4,即人已因私欲而脱离良知开显的“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而使明觉不得完全开显,导致“知”非真知,“行”非真行(良知真正地开显)。换言之,“知行”二分,缘于良知开显的一体性存在断裂——主客二分化,致使“知”成为对象化的知识,“行”成为对象化的行为。相对地,正因“知”与“行”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一体性,王阳明将“知色”“知孝”“知痛”“知寒”或“知味”“知路”之“知”与“知行合一”之“知”相关涉。如《传习录》记载王阳明举例论真知行曰:
《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7]4
“见好色”之“见”,既意味着存在之开显,又意味对存在的证知,否则即为无所见。这意指,人亲身处在心、意、目、色的一体性“存—在”之中,并对此“存—在”有着前概念的、非主客二分的,或前理性反思的体证、领会——对存在的肯定(“好”)与否定(“恶”)。这即是良知之知“是”知“非”,故“见之”即“知之”。又因存在之是非与良知是体用一如的,故“知”既是良知之知“是”知“非”,又是良知明觉发见而是(存在为)其所“是”、非(存在为)其所“非”①朱刚细论了良知之自知、是非、善恶、好恶的内涵与关系,并关涉知行。不过,不仅是非之知如其言不限于伦理善恶,且好恶之行也不域于道德实践,如王阳明此处所言。参见朱刚.“自知”与“良知”: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相互发明——从耿宁对王阳明“良知”的现象学研究谈起[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96-109.,所以“知之”即“好之”“恶之”,意即“知之”即是念起,是良知之开显,是是非存在的开显,是“行”。因此,“见好色”“知好色”和“好好色”是一个,而“闻恶息”“知恶臭”和“恶恶息”亦是一件。这意味着,“知”首先是以存在的形态出现的:知道一个东西,即是开显一个东西,抵达一个东西,故知行同出而名异。
又如“知孝”,并非有一个抽象、固定的“孝”之道理待人去“知”,有如常识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孝之为孝,只有作为当下的呈现才能抵达。也就是说,真正的“知孝”,乃是人通过戒慎恐惧、语默动作不断地开显孝之为孝的存在。而孝之为孝的存在即是“心物一体”之存在,因为“孝”即是这“一体性”生命关系的生发。因此,“知孝”即是开显或抵达人与他者、他物的切己相关的“一体性”存在。如此,知孝的过程,就是使良知活生生地涌现的过程,即良知“行”的过程。由此亦可见,对王阳明而言,伦理道德并非主体的产物;相反,“心物一体”才是伦理的本然。换言之,对王阳明而言,一切存在皆是“伦理”的“存—在”,因为一切存在皆是良知开显的心物一体之存在。因此,就真实存在而言,“知行合一”既是伦理的又是存在的,因为存在原是“心物一体”的存在。
与“知孝”同理,“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意谓人对痛的“体知”,必然要亲身寓于痛的存在之中,即人只有亲身处于良知之开显中,乃能抵达(自觉)此良知开显的存在及良知本身。若将人与存在分开,即在亲身的实存之外或将“痛”“寒”“味”“路”对象化,人皆无法“知”之,而只具有空洞的概念知识。因此,王阳明又曰:“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7]46。“欲食之心”作为意,即是念起而为“行”,是从欲食到食用完毕整个良知开显过程的开始。或者说,“欲食之心”指向“知—味”,即“知—味”之“意”构成了“行”的目的或起因,而“知味”则在具体的食之“行”中得以实现。另外,“食”作为人之动,并非只关乎“口”,且包含着当下人之视听言动,是未反思地亲身投入到人的全身心、食物乃至周遭存在的“一体性”关系之中,而食所得之味,正是良知开显自身所呈现出的这“一体性”的存在意蕴。因此,对食物味道之知,必在食之行中,在良知之“行”中。同样,人对“路”的知亦须亲身践履,但这种“践履”并非常人所认为的主体之行走,而是人之心身与路融为一体之“游走”。因为“真知”非主体对对象物之知,而指“知味”和“味”的存在或“知路”与“路”的存在,在原初的存在处是一个。换言之,只有一个存在,即“心物一体”之存在,故知之即存在之:良知明觉之发见与良知开显为真实存在是二而一的,二者只是称谓不同而已。如此,“知”与“行”原是良知明觉开显的“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的两面,故王阳明言“未有知而不行者”[7]4。这即是知行的本然。
总而言之,“心外无物”而万物一体,故心知即意,意即念,念即行,行即物,物即身:知、意、念、身、行、物皆为良知心体的开显而一体不分。王阳明谓之为:“身、心、意、知、物是一件。”[7]100因此,就知行本体言,“知”与“行”皆为良知之开显,是良知开显的心物一体之存在的两个方面:“知痛”“知寒”“知孝”“知味”“知路”之“知”与“知行合一”之“知”皆为良知明觉之发见,而明觉之发见即是良知开显原初的存在,即是“行”,故“知行合一”。由此,“真知”与“真行”,与主体或对象化的行为无关,更不限于主体的道德之域,而指向无限的生命存在境域。
三、知行功夫
良知虽开显知行,但其又须在知行的功夫中呈现自身,这即所谓本体即功夫,功夫即本体。王阳明曰:“《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7]1048这表明,王阳明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相通相融:“知至”之“知”指向“体知”的功夫,指体证良知,而体证良知并与之为一,即为“知至”——抵达良知;“行”为开显良知的功夫——致良知,故“行”的过程即是开显、达至良知的过程。由于良知非存在物又与存在一体不分,且真实的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体知”非对象化地认识良知或把持良知,而是必须进入良知呈报自身的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中与良知同一,始能居留于良知之乡。因此,“知”良知即是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的过程即是“行”的过程,“知”与“行”不过是对致良知之同一功夫的不同称谓。
若将“知行”或致良知分而论之,则可以说“知至”是“至之”的目的,而“至之”是“知至”得以实现的现实途径。换言之,抵达良知是致良知的目的,而推致良知是抵达良知的手段。“知行”的这种关系,王阳明论之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7]5。“主意”指方向,意谓“知”是“行”的方向或“行”的目的是为了“知”——抵达良知。“行”是“知”之功夫,强调的是人之“行”或“存—在”对抵达良知的意义。因为良知唯有在人之“行”(意念、身行等人之存在)中,在人与物一体不分的存在中,乃能真的开显而被证知。这与王阳明所言“‘惟一’是‘惟精’的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7]14相似:“惟精”的目的是“惟一”,而“惟一”则须靠“惟精”的功夫来实现,如尊德性是道问学的目的,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或者说,无论是学问思辨还是致知格物,无不是“惟精”之功或“道问学”之功,即无不是“行”;而学问思辨或致知格物又无不是为了抵达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故而亦是“惟一”或“尊德性”之功,是“知”之功。因此,“惟一”与“惟精”或“尊德性”与“道问学”或“知”与“行”,本是同一个致良知功夫,但因描述角度不同而称谓有异罢了。
由此,“知是行之始”的“始”并非简单地指向开端,而与“主意”之旨相似,指向起因。换言之,“知—至”是“行”的原因,即开显良知并抵达良知是“行”的原因;反过来说,就“行”为良知之开显言,良知的自我抵达(知)是良知开显的原因。然而,“知”又唯有通过人之“行”或人之“存—在”、万物之“存—在”,乃能得以“至”,此即“行是知之成”。这意指,人时刻做诚意、致知、格物的功夫,始能使良知得以完满开显自身,而为人所证知。可见,王阳明反复论说,皆意在指明:“知”在“行”中,“行”在“知”中,“知”与“行”是同一个开显良知功夫的两面。
正缘于“知”与“行”的同实而名异,故王阳明曰:“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元来只是一个工夫”[7]222。“知之真切笃实”指良知明觉自知之真切笃实即是良知开显得真实无妄,这即是“知至至之”,故“知”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指良知开显并明觉其自身而为真知,即良知开显得光明通透,这即是“至之知至”,故“行”即是“知”。这意味着,在真实存在的意义上,王阳明不仅将“知”与“行”合一,且将功夫与本体合一,即将良知与体知,及良知与良知之开显合而为一。如王阳明曰:“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7]92良知与良知明觉之发见是一,即是良知与良知之开显是一,或良知与存在为一。由此,体用之分及物我之别皆被泯除,而只有心物一体的存在,故“知行”功夫只是一体性地去“存—在”,这即是知行功夫的本然。
因此,“知行合一”作为功夫,“真知”即是在心物一体的存在中抵达良知——成为明觉,而“真行”即是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光明地“存—在”。如此,若良知开显不能明觉通透,即不是真的开显,则“行”为冥行,如心意发动而不善;若良知之明觉发见不能真切笃实,即是良知没有得到真实地开显,则“知”是脱离良知开显的真实存在而“知”,即非亲身实证之“真知”而为“妄想”——脱离良知开显之真实存在的抽象思维,如主客二分的概念知识。因此,知行是一个功夫:就“开显”而言为“行”,就开显得明觉通透为“知”;知之即是开显之,二者同时发生而皆指向致良知之功。
然而,“知”与“行”的这种存在关系意味着,“行”的断裂即是“知”的终止,反之亦然。王阳明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7]132良知即是明觉,良知自能知是知非,故“容易”;只是人不能切实用功致良知,故是行难。而“行”之难即是良知真实开显之难,即良知明觉发见之难,故又是“知”之难。因此,良知之“知”与“行”是既容易又艰难:“知行”之容易因“良知”自然涌现,即“知”即“行”即存在;“行”之难在于“人”推致或维持这种光明通透的存在之难,故又是“知”之难。具体论之,就常人而言,常人对良知的体知并未即能精明通透,而须在万事万物上推致良知,始能期开显臻至圆满的存在而达至真知;就圣人而言,即使圣人对良知之知能圆满无碍,但若不能不断地推致扩充之,则意味着良知开显的中断,即真实存在的终止,因而良知之“知”亦会中断而不能至。可见,对王阳明而言,真知与真在是一体两面的,且“知至”须在无限的“致知”中实现,所以“知”与“行”的合一是一个无限开显一体性存在的过程。或可反言之,“知行合一”既是心物一体存在的本来面目,又是得道之人始能达至的真实存在,故是一个需要切实用功始能成就的功夫。
总之,功夫与本体一体不分,本体开显功夫,功夫达至本体。因此,就功夫言,“知”良知指抵达良知,即是良知明觉之发见,是良知明觉真切笃实地开显;而“行”指开显良知或使良知明觉呈现自身,即是良知开显得光明通透。因此,“知”与“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二者称谓不同但皆指开显良知、抵达良知,即诚意、致知以开显万物一体之真实存在而达至良知本体。如此,“知行合一”作为功夫,并非指作为主体的道德意识或意志转化为对象化的日常伦理行为,而指良知开显为真实的存在或开显良知为心物一体的存在,这即是“知行合一”之功夫的本然。
四、存在的分裂与知行二分
前文分析已表明,正是“心外无物”的存在一体性,使“知”与“行”的合一成为可能;相反,存在的分裂,不论程度如何,皆会造成“知”与“行”的二分。因此,王阳明曰:“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7]47。心物二分,故先向外求知天理然后再按照天理来行,则“知”与“行”被二分。相对地,“心外无理”则指向“心外无物”:心之理即是物之理,故心物一体。“求理于吾心”表明,“知”与“行”之功夫皆是以心体良知为标的。然而,真实存在的“一体性”意味着,既没有存在之外的主体来知,又没有作为认知对象的心体,而只有良知开显之“心物一体”的存在,所以无往不是良知之“行”,又无往不是良知明觉发见之“知”。因此,“求理于吾心”非把持一个主体之心,而是要进入或开显心物一体的真实存在以使这存在的灵明呈报出自身,这即是天理明觉发见处。如此,“知”与“行”无非是良知明觉开显的“心物一体”之“存—在”的两面,而“知行合一”之“合”即在于“存—在”之“一体”。
基于此,不仅主客二分的理解无法达至“知行”的本然,而且对“心外无物”蕴旨理解的丝毫偏差,亦会造成“知行”的分化。例如,林丹虽探讨了“知”在体知内涵下与“行”之间的关系,并论及“知”“行”与存在的关联[8]131,但因未达至真正的存在一体性,而未能完满地解释“知”与“行”的合一关系。如其将“念”归属于“知”[8]142,以“身行”界定“行”[8]130,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之“一念”乃是粘连着“行”的[8]142,即念自然引起身行。可见,“念”与“行”之间仍然存在着嫌隙,因为念是念,行是身行,而念并未即是行。换言之,“知”与“行”只是粘连而未同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林丹将王阳明之“心”境域化或时间化为“知觉领会”[9]。正由于作为根源的良知本体的缺失,使其无法将“知”与“行”同一为良知之开显,即无法将“知”与“行”同一为一个“存—在”。换言之,“心体”的缺失或仍可达至存在的“相关性”,但不能真正由心体建立生命的“一体性”存在,即充满光明的存在,而将“知”与“行”统一在这“存—在”中。如一念之行即是光明之发见,是生命一体存在之开显。因此,存在的丝毫裂隙,皆是遮蔽,皆会致使人错失“知”与“行”合一的存在根据而使之二分。
类似地,Warren G.Frisina基于过程本体论,对“知行合一”的理解亦存在相似的问题。他认为王阳明之心与万物一体不分,皆处于永远的运动过程中。因此,其将“良知”解释为“primordial experience”[10],即原初的体知,而此体知即是思想活动,是一种最基本的行。再者,由于心物的一体相关,其认为心之活动与道之创生活动不相分离且是“one aspect of the dynamic creativity”[10]。如心对一事物的反应(“知”),同时也就是与之建立一种存在关系,因而“知”也就是宇宙创生之“行”的一个方面。可见,Warren G.Frisina亦将“知”和“行”存在化了。然而,其并未将“心”界定为生化之本,心之活动只是宇宙创生力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创生本身。相应地,其对“知行”之“行”的讨论主要限于“mental activity”[10],虽偶有论及“心行”与“身行”乃至宇宙运行不相分离,但始终未直接将“身行”纳入“行”的范畴,并将“行”扩展为整个宇宙的创生活动本身,即指向整个宇宙的物之“存—在”。因此,Warren G.Frisina也因未能将“心”或良知真正本体化而获得真正的一体存在视域,进而将“知”与“行”完全存在化为道之开显,揭示出“知行”的本然。
概言之,“知”与“行”的合一基于“心外无物”,即“知”与“行”是良知开显的心物一体真实存在的两个面向,故对“知行”的理解,既不能离开作为万物本体的良知,又不能离开物的一体性存在。相对地,主客二分的理解范式,或对心物及其关系把握的任何偏差,皆会使存在断裂,而对“知行”造成不同程度的分化。
五、结 语
王阳明以“心外无物”为真实的存在:人与万物皆为良知心体的开显,故人之念、视、听、言、动与万物之在一体不分。这意味着人之意念、身行等作为良知之开显,即是存在之开显。因此,王阳明以人之意念、身行为“知行合一”之“行”,即是以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为“行”。同样,基于“心物一体”,“知”非对象化之知,而是体证之知,指向良知的自我抵达,即良知明觉之发见;而良知明觉之发见即是良知之开显、存在之开显,因为只有一个存在,即“心物一体”之存在。由此,就知行本体言,“知”与“行”皆为良知之开显,表现为良知明觉之发见与良知开显的一体不分,故“知”与“行”是对同一存在不同面向的称谓。而就功夫言,“知行合一”之“知”与“行”为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面:“知”指使良知明觉切实发见而抵达良知,“行”指开显良知为光明通透的存在而抵达良知,故二者皆指向开显良知为心物一体的存在以达至良知本身。因此,“知行合一”功夫指“心物一体”地“存—在”,而“合一”之旨即“一体”之精神。
另外,正是“真知”与“真行”因“心外无物”而有的一体不分之存在向度,使王阳明将“知行合一”之“知”与“知痛”“知路”等“知”相关涉。相对地,无论是将“知行”主客二分化并进而限于主体的道德之域,还是从知识的角度理解“知”及“知痛”等语,皆是割裂“心物一体”之存在而造成知行二分。再者,即使论者已经明确了“心物一体”的理解路径,但若不能精准把握“心外无物”的蕴旨,则是仍处于分裂的存在而未抵达“知行合一”的存在。因此,知行二分对应着分裂的存在,正如知行合一对应着一体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