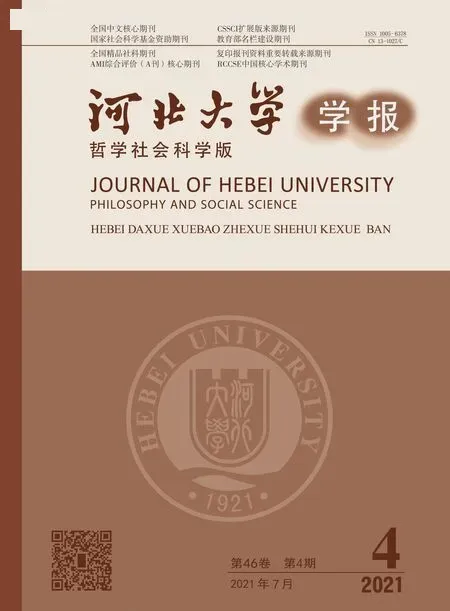“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
——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许春华,许 嫘
(1.河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清华大学 五道口金融学院,北京 100083)
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问题,是中国哲学史的重大问题,甚或说是研究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淮南子》称:“根本不美,枝叶茂直,未之闻也。”(《淮南子·缪称训》)从中国哲学史来看,自从先秦诸子哲学产生以来,战国至汉代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如庄子、荀子、班固等,就把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问题自觉纳入其学术视野,这是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第一次研究思潮从战国中晚期至汉代,涉及的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史记·太史公自序》《淮南子·要略》《汉书·艺文志》《抱朴子·百家篇》和桓谭《新论·九流篇》等。本文以对中国哲学思想史影响较大的《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性文本,对战国至汉代第一次研究思潮进行探讨。
一、《庄子·天下篇》
以庄子、荀子为代表的战国中晚期思想家,在探讨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时,不仅彰显先秦诸子的创构与贡献,以言简意赅的方式概括了先秦诸子的主旨,而且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发源,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先看《庄子·天下篇》第一部分: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1065-1069
《庄子·天下篇》提出先秦诸子哲学起源于“古之道术”,这种“古之道术”亦即先秦诸子发源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其总体宗旨“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种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从承载的文献来说,即是西周至春秋时代的《诗》《书》《礼》《乐》,且明确“《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明分”。这是对“六经”①关于“六经”产生的时间,学界并未完全达到共识。本文仅限于《庄子·天下篇》的文本进行探讨。主旨最早的概括,所谓“道”,指“达也,通也”[1]1068。从思想阶层来说,即“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指能明理《诗》《书》《礼》《乐》之思想家群体;从其思旨趣来说,是一种争奇斗艳、纷纷蜂起的“百家之学”,“称而道之”即是说他们均不同程度地传承、接纳了“古之道术”这种思想世界。“道术”潜存于“物”的世界,先秦诸子则是对“物”的世界一种顺承与接纳,而非对“物”的世界的宰制与分割,如墨翟、禽滑釐是“不靡于万物”;宋钘、尹文是“不饰于物”;彭蒙、田骈是“趣物而不两”,“于物无择”;关尹、老聃是“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惠施是“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逐万物而不返”;庄周是“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在《庄子·天下篇》中,“物”并非纯粹客观存在的自然之物,而是一种生命世界的展现,思想家与这个“物”即生命世界相通,即生发某种思想观念,由此来说,“物”的世界亦是一种“思想经验”。通过对“物”的世界的接纳与反思,达到对整个宇宙、世界、人类的一种哲学理解,是《天下篇》的特点。
《庄子·天下篇》对先秦诸子的价值判定有臧有否,褒贬结合,其否定性向度主要体现在先秦诸子是对世界整体性、纯粹性的割裂,“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其肯定性向度是在明确“道术为天下裂”的前提下,仍然对先秦诸子“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给予充分的肯定。此处“裂”指分裂,而非断裂,“断裂”乃是一种对“古之道术”的割断、悬隔,是对《诗》《书》《礼》《乐》传统的断裂;“分裂”则是从“古之道术”统一的、整体的、一元的思想世界,分化、裂变为多元的诸子思想世界,是对《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与接纳。在《天下篇》作者看来,先秦诸子犹如一曲之士,各自传承古代整体思想世界之一部分,此可谓“方术”。“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皆有所明”之“明”与“明于本数”之“明”同义,与“贤圣不明”“暗而不明”之“明”亦同义,乃明道、明体之义。“本”应指“内圣外王之道”,故“皆有所明”“皆有所长”“时有所用”,指先秦诸子对古代思想世界所承载的“内圣外王之道”,各自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以“明体达用”,各自以自己的思想路径对《诗》《书》《礼》《乐》传统进行价值判定。所以《天下篇》在谈到每一个先秦诸子学派时,均指明“闻其风而悦之”,“风”即思潮、学派之义,“闻”即内在融入之义,犹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之“闻”,“闻其风”即融入“内圣外王之道”之古代思想世界,“悦”即接纳与顺承之义,指传承《诗》《书》《礼》《乐》传统所承载的思想世界。尽管学界对《庄子·天下篇》的作者争议不断,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探讨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上的首屈一指的学术地位,《庄子·天下篇》首次明确了春秋时代《诗》《书》《礼》《乐》思想传统与先秦诸子哲学的渊源关系,“庄子不但是中国轴心时代的开创者之一,参与了那场提升精神运动的大跃动,而且当时便抓住了轴心突破的历史意义”[2]14。
二、《荀子·非十二子篇》
《荀子·非十二子篇》也是对先秦诸子思想主旨进行探讨的一篇优秀作品。可以视之为中国哲学思想史较早的一篇论著。其开篇即云: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浑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3]89-91
先秦诸子之论,皆为一种“言”“说”。如它嚣、魏牟之“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陈仲、史之“忍情性,綦谿利跂”;墨翟、宋钘之“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慎到、田骈之“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惠施、邓析之“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子思、孟轲之“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此“十二子”之“言”“说”,在荀子看来,均为一种“邪说”“奸言”。这就从价值属性上给予一种否定性判定。在另一处荀子亦指明,先秦诸子之思想主张皆为“道之一隅”,乃“一曲之士”之所见,故而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想困境,“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荀子·解蔽》)。此文诸子之“蔽”亦即浑然一体之“道术”裂变的结果,荀子揭示了先秦诸子思想主张的非正当性,均斥之为“邪说”“奸言”。
《庄子·天下篇》与《荀子·非十二子篇》对先秦诸子的价值判定,虽然各有千秋,褒贬不一,但总体上是对产生于春秋晚期“百家争鸣”思想现状的一种否定性反思,亦是对战国末期天下一统大势的思想反映。相对而言,《荀子·非十二子篇》对先秦诸子的否定性判定更为激烈。这种否定性判定不仅体现于上述思想内容上的非正当性评价,而且对于其表达方式、社会价值也进行了否定性评价。所谓“矞宇嵬琐”,郝懿行注曰:“矞,满溢也。宇,张大也。嵬,崔嵬,高不平也。琐者,细碎声也。此谓饰邪说,文奸言,以欺惑人者。”[3]90这种表述方式的隐晦、曲折、琐碎,与明白、通畅、简易的表述方式正好相对,表述方式的隐晦、曲折、琐碎,也映衬出先秦诸子思想主张的“邪”“奸”。先秦诸子之为“邪说”“奸言”,不仅仅表现于言说方式上,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于其对天下秩序的扰乱和社会风气的摇荡。“枭乱”,犹浇漓,“混然”,无分别之义。“枭乱天下”是说这些“邪说”“奸言”,使社会风气轻浮薄弱,“天下混然”是指天下秩序混乱,“不知是非治乱”是指在真假、对错、善恶这些根本性问题上缺乏普遍、客观的原则,以致使维系社会恒常的价值观念混乱,维护天下秩序的礼法准则缺失,此之谓“天下浑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之义。
在对先秦诸子进行否定性判定的同时,荀子也充分肯定了《诗》《书》《礼》《乐》《春秋》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对早期儒学的价值,“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是矣。向是者臧,倍是者亡。向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荀子·儒效》)。“管”,“枢要也”[3]133。“是”,“皆谓儒也”[3]134。《诗》《书》《礼》《乐》之归宗在于儒学,其“志”“事”“行”“和”“微”之旨趣,承载着儒学的“天下之道”与“百王之道”,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向”与“背”,亦即决定着儒学的“臧”与“亡”。
对于先秦诸子的哲学论证方式,荀子统一评定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郝懿行注曰:“故者,咨于故实之故,谓其持论之有本也;成理,谓其言能成条理也。”[3]91如果撇开荀子对先秦诸子之思想旨趣“邪”“奸”之评定,荀子对这种论证方式的充分肯定,不失为一种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探讨的基本规范要求,这与荀子追求客观普遍的规范准则的思想主旨是一致的①杨国荣曾以《规范与秩序》为题,对《荀子·非十二子》的思想进行了哲学诠释。参见《规范与秩序——〈荀子·非十二子〉的哲学诠释》,载于氏著《哲学的视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90-311页。。
三、《汉书·艺文志》
汉代对先秦诸子思想源流的探讨,以《汉书·艺文志》最为鲜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撰有《七略》,其中《诸子略》收录于班固之《汉书·艺文志》: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掌观象授时);……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掌刑狱);……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掌仪节);……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掌守宗庙);……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掌使节往来);……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掌谏议);……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掌农事);……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一种小官)。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4]
在孔子时代之前,学在官府,各种知识最初都掌握在官府中,同各种官守之职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知识与品质教育只在贵族阶层中进行,各项专门的技艺在王官执掌的职业内部传承,“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所谓“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艺文志》提出,先秦诸子之思想主张虽然“各推所长”“各有蔽短”,但从其思想发源之处即“合其要归”来说,乃“六经”之“支与流”,故可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刘歆在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农家等诸子百家之渊源进行界定时,并没有做出一种完全肯定的判断,而是在每个流派前均以“盖”字说明,所谓“盖”,即表示只是一种或然判断,对何种王官与何种先秦诸子学派之思想渊源,不是十分肯定或非常明确,或者说是认为仅仅存在一种或然性的联系。这与《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先秦诸子“闻其风而悦之”,在思想理路上存在着相似之处。
近代章太炎认为,“古之学者多出王官”(《诸子学略说》)。“是故九流被出王官,及其发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国故论衡·原学》)章氏之说传承了《汉书·艺文志》的主张,认为“九流诸子”皆出于王官。胡适则与之相反,认为《汉志》所云与章氏所论,“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而后之学者乃奉为师法,以为九流果皆出于王官。甚矣先儒之言之足以蔽人聪明也!”[5]593并逐条进行驳斥:第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也。第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也。第三,《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也。在驳斥章氏观点的基础上,胡适得出结论:“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5]598其所云之“救世论”,实源于《淮南子·要略》:“专论诸家学说所自出,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
从先秦诸子的思想发源来看,“诸子出于王官”之论,无论《艺文志》及章太炎的肯定性意见,还是胡适的反对意见,并没有切入到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根本。因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出”,是指先秦诸子产生的一种历史根源,而不是思想的逻辑根源,所以这种“出”只是一种松散的纵向历史根源论,不是对先秦诸子思想发源的学理论证。所以章氏顺承《汉书·艺文志》所说“诸子出于王官”论,仅仅是对诸子哲学一种历史根源的了解,并没有达至“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荀子·非十二子》)。同样,胡适反对“诸子出于王官”之论,是按照“逻辑理路”来进行驳论,认为先秦诸子思想不可能产生于王官职业,也就是说,胡适之认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出”应该属于逻辑之“出”,而“诸子出于王官”之论属于历史根源的探讨,即历史之“出”,或者说这种观点存在一种“先天不足”,胡适的错误就在于把这种历史根源当作逻辑根源来进行驳斥,把本来非常松散的历史根源当作严格的逻辑根源来看待,所以只能以一种横向的社会根源论去反对章氏纵向的历史根源论,殊不知,这两种都属于一种先秦诸子哲学产生的“外缘”论。从历史根源上来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产生,属于一种“外缘”论,同样,从社会根源上来判定先秦诸子哲学的产生,亦属于一种“外缘”论,这两种观点并非绝对错误,但是没有切准先秦诸子哲学产生的根源。牟宗三认为,《汉志》包括章氏所论与胡适之说,“这不是诸子的因,那只是它的缘。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说社会出问题,民生有疾苦,这也是诸子的缘”[6]。二者的共同缺陷在于从外在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来推测先秦诸子哲学之起源,显然没有深入到内在的本质的思想根源。当然,章氏、胡适之主张并非完全没有学术价值,他们从不同侧面触及先秦诸子之学对《诗》《书》《礼》《乐》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的传承与突破,“如果说,‘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从一个侧面触及了诸子思想的历史继承性,那么,肯定‘诸子不出于王官’,则意味着确认诸子之学包含对以往文化思想的突破、超越这一面”[7]。
四、“地方性知识”视域
第一次研究思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从上述三个文本来看,他们对先秦诸子各个学派与春秋时代的《诗》《书》《礼》《乐》传统的对应性关联,并没有坚持非常明确、完全肯定的观点,但是对《诗》《书》《礼》《乐》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作为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发源之地,却都坚持非常明确、完全肯定的主张。这说明《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存在一个共同的突出的特点:他们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探讨,其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这种探讨是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的,故而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恐怕是所谓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诸子哲学“地方性知识”最为根本的体现。所谓“地方性知识”,并非指某种知识、思想产生于某个地域,因为所有的知识和思想均源自一定的时空即某个“地方”。“地方性知识”的旨趣在于,这些“知识”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时代、现实的文化传统之中,应对其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①关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参见陈少明:《中国哲学: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以各民族之“诗”为例,在原始初民的精神世界中,“诗”以其独特的情感语言,占据着世界各民族文明的最初源头,成为人们理解宇宙、世界、人类的最为主要的表达方式。“要理解宇宙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发现这个方法——以语言为中介而不是以物理现象为中介的方法——那我们就找不到通向哲学的道路。”[8]143为此,古希腊智者十分重视语言作为“最有力的武器”之作用,“正确地运用语言并不断地加以改进和磨炼,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为了这个目的,智者们创立了一个新的知识分支:不是语言学也不是词源学,而是修辞学成为他们的主要关切对象”[8]146。“修辞学”占据了古希腊哲学传统的中心位置,修辞学成为西方逻各斯传统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逻各斯则形成了西方语言哲学的原动力,由此可说,“修辞学”是西方诗学和哲学的“地方性知识”,与逻各斯共同“呈现古希腊哲学的‘地方性’特征”[9]。与此不同,中国“诗学”传统或者中国哲学的“地方性”,则是更为强调其“教化”——道德教化与审美教化之价值功能,“故圣人始教,以《诗》为先。《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10]。
对于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问题,惟有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加以理解,才会更加准确把握先秦诸子哲学产生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的基本特质,从而切中先秦诸子哲学的根脉,“强调诸子之学与地方性知识的联系,不只是有助于今日对其所包含的‘非哲学’部分的恰当的理解,而且可以更好地突出中国哲学尊传统,重人事的历史文化性格”[9]。这种“地方性知识”展现于两个维度,一是历史维度,二是时代维度。其一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自殷周之际以来,尤其是在春秋时代经历了一次“重构”或“阐释”。所谓“阐释”,是将原本隐性的解释为显性的,如《诗》《书》中的道德意识,通过“礼”化、“乐”化成为春秋时代政治伦理与美德伦理的一种重要资源;所谓“重构”,即将原本已有的思想观念重新构建,如《诗》《书》中的正义(情)感,通过礼之“义”化转换成为一种判别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规范,即正义原则。这种“重构”或“阐释”使《诗》《书》成为礼乐文明一种最为根本的经典,“《诗》《书》所代表的文本的权威化和经典化的形成,是在春秋时代。而这一经典化的特色在于,它是文明的经典,而不是宗教的经典”[11]217。虽然《诗》《书》《礼》《乐》并非完全的哲学经典,但是说它们是先秦诸子哲学的源头活水则无疑义,“诸子之学,其根底皆在经也”[12]。其二时代维度,是指《诗》《书》之“礼”化、“乐”化过程,使之溢出了《诗》《书》原在的文学、艺术、政治、宗教领域,随着礼乐制度“成为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成为维系春秋时代宗法社会、政治秩序、日常生活的价值规范,成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撑。《诗》《书》《礼》《乐》凝聚而成为春秋时代一道靓丽的思想风景线,是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这种传统一直到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哲学时代,甚至延伸到秦汉之际的经典文本如《礼记》,“先秦儒家文献中固然开始把‘子曰’的德性论述作为经典,但诗书的经典地位并不受影响,传承诗书、解释诗书,在话语中称引诗书,一直到汉代前期仍然如此”[11]218。征引、阐释、重构《诗》《书》,这种传统成为我们理解和解读先秦诸子尤其是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的思想背景。
强调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地方性知识”,要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先秦诸子的多元哲学形态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世界,礼乐传统的精神气质、思想品格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型塑于先秦诸子哲学形态之中。余英时认为,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墨、道三家,“都是在礼乐传统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而它们之间的思想分歧也源于对待‘礼乐’的态度各不相同”[2]17。脱离春秋时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来理解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问题,只能滑向一种“抽象的理解”。其二,先秦诸子哲学均是原创性的思想体系,自有其“知识来源、问题渠道、思想方式,这是别人无以代替的。忽视这一点,就忽视了中国思想原创的专利权”[13]。切莫机械地步一些近代学人的后尘,急不可待地在概念、框架、范式等方面以西方哲学为模板,要防止陷入一种“格义式论证”的“陷阱”。所谓“格义式论证”,即努力证明中国哲学中的某一范畴、命题或观念系统能在西方哲学中找到对称物,尽管它与西方哲学相比略有逊色。这种论证方式的要害之处在于完全抹杀了中国哲学的原创性,“把中国哲学合理性或价值高低,完全系于所选择的西方框架……结果都是把中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附庸,其任务只是等待西方新思潮的出现。哲学原创性的任务交给西方哲学家,我们都是搭顺风车的思想游客”[14]。其三,先秦诸子哲学是在充满动荡的剧烈转型时代,在应对天下、世界、人类的生存危机时,把自己最切实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智慧,转化为一种人道关怀与理性思考,这是哲学自身普遍性品格所致。我们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不应忽视先秦诸子哲学尤其是儒道两家,对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哲学层面的揭示与阐释,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