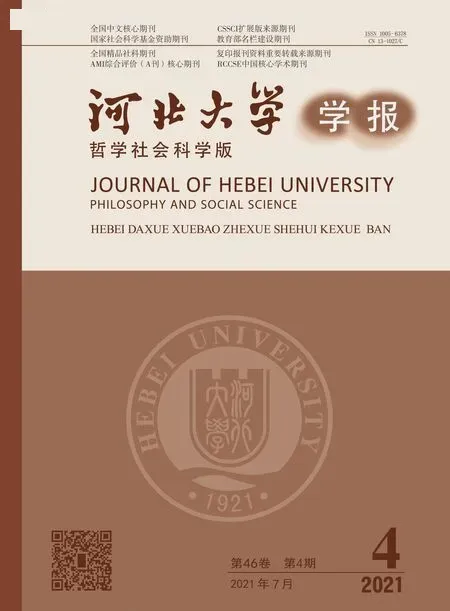西汉文学叙说
刘跃进
公元前206年冬十月,亦即秦历时年的岁首,刘邦至霸上,西入咸阳。此前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故欲王关中。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其《入关告谕》一文,实一代文章之本。这一年,刘邦51岁。西汉纪年由此而始,西汉文学史亦由此而始。
公元25年,即淮阳王刘玄更始三年夏,长安城被赤眉军樊崇等部所毁。六月,刘秀称帝于河北(鄗),改年号为建武元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西汉王朝至此结束,前后延续231年。
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汉代辞赋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而汉代文章则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一、“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辞赋
汉代文学的正宗是大赋。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3他的看法代表了传统的认识。
(一)辞赋的含义
赋,其本义是敛。何时冠以文体之名,其确切含意又是什么,历来歧说不一。概括起来主要有四说∶
其一,《汉书·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2]1755-1756由此看出,赋之产生在《诗》淡出之后,是“贤人失志之赋”,是诗学范畴之外的一种文体。赋有两类,一是诗人之赋,二是辞人之赋。而《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类:一是以屈原赋为首,二是以陆贾赋为首,三是以孙卿赋为首,四是《主客赋》为首,作者定义为杂赋。因为《汉书·艺文志》大都承袭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而来,所以,有人认为此语出于刘向。刘向生活在西汉后期,就是说,他就生活在大赋兴盛的当时,因此,这恐怕就是当时人给大赋下的定义。
其二,左思《三都赋序》:“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先王采焉,以观土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3]80就是说,赋出于《诗》的“六义”之一,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含义是铺陈,即《文心雕龙》所说的“铺采摛文”。对此,班固在《两都赋序》也说过类似的话“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
其三,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4]117即原本于《诗》《骚》,出入战国诸子,从文体特性上看,具有战国纵横家文的色彩。
其四,“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故《汉志》叙纵横家,引‘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之文,以为大戒。诚以出使四方,必当有得于诗教。”[5]126姚鼐《古文辞类纂》、刘师培《论文杂记》并主此说。
(二)辞赋的分类
《汉书·艺文志》分辞赋为四派,即: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刘师培《汉书艺文志书后》认为最后一类是荟萃众家之作的总集,而前三类则是个人的创作,屈原赋为缘情托兴之作,陆贾赋为骋词之作,荀卿赋为指物类情之作①刘师培《汉书艺文志书后》:“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余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词之作也。聚事征材,旨诡而词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类之大略也。班志所析,盖本二刘。自《昭明文选》析赋、骚为二体,所选之赋缘题标类,迥非孟坚之旨也。”(刘师培《左盦集》卷八,民国廿三年宁武南氏校印本)。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屈原赋类: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这是西汉辞赋的主流。在汉代,尤其是西汉,《楚辞》的影响随处可见。黄伯思《校定楚辞序》认为:“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6]344-345譬如西汉文景时代,楚、吴、梁、淮南、河间诸藩国,文士济济,如枚乘、邹阳、庄忌、淮南小山等均以擅长楚辞而闻名于世。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类作品,如贾谊《吊屈原赋》《惜逝》、严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等,可以说都受到了《楚辞》的沾溉。在整个西汉前期,具体说,主要是汉武帝登基以前,赋体创作,主要是受到了《楚辞》的巨大影响。就是汉武帝之后,直至终东汉一朝,《楚辞》的影响依然存在,比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扬雄《反骚》《广骚》《畔牢愁》、刘歆《遂初赋》、班婕妤《自悼赋》、班彪《北征赋》、蔡邕《述行赋》等,依然可以看到《楚辞》的影子,只是没有以前那样明显罢了。所以《文心雕龙·时序》说:“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3]477除了大赋、骚赋以外,在两汉还有为数不多的抒情小赋,比如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穷鸟赋》、祢衡《鹦鹉赋》等,不用设问,篇幅短小,通篇押韵,或三言或四言乃至六、七言,咏物抒情,灵活多变,也可以看出屈原的影响,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先河。
陆贾赋类,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以扬雄赋为代表。汉景帝时发生了著名的“七国之乱”,这是诸侯王国和中央集权间的一次大的较量。这次战争的结果以吴、楚等国的彻底失败告终。这就大大地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使中央集权制大为加强。这种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汉赋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原来的辞赋家多半在诸侯王国进行创作,此后,则大部分都转到了朝廷中来。例如司马相如等人本来都在诸侯王国,后来先后来到长安。这是因为诸侯王国已被严重削弱,而景帝死后,即位的汉武帝又非常喜欢辞赋,他久闻枚乘之名,即位后就用“安车蒲轮”去迎其进京。可惜枚乘年老,在半途中就死了。在汉武帝周围,还集中了一批辞赋家,如枚皋、严助、朱买臣、主父偃等。进入京城后,这些辞赋家的创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原来他们的创作多少都还保留了个人的独立性。但是,到了这时,却多已成为文学侍从。其创作的目的主要是供皇帝阅读,所以多是歌功颂德之作。在体制上,铺陈排比,驰骋才学。其中,司马相如、扬雄是最典型的代表。“一般认为,枚乘《七发》是大赋形成的标志。”可以说,到了他们二人手中,汉赋的体制基本上已经定型。
孙卿赋类,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孙卿赋十篇。今存:《成相篇》《赋篇》五篇,《佹诗》一篇,凡七篇。若《成相》作五篇,则十一篇也。其中赋篇五篇分别写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以四言为主,半韵半散,问答相间。其表现手法是“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文心雕龙·谐隐》),近于隐语。西汉以后作者二十三家,可见创作之盛。此外就是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杂赋中有大量的杂咏草木器物之赋,说明咏物赋之起源甚早。
上述所列主要都是汉代的作品,但是多数已经失传,很难考察班固这种四分法的依据。而《文选》则根据标题与题材,将赋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15门类,共56篇作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对赋体进行“原始以表末”发展梳理时,将赋分为两大类:一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赋,一是“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的小赋。大赋的主题,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特征,这“体”与“经”为动词,而“国”与“野”相对照。也就是说,大赋的基本功能即全面描述整个社会的风貌,关涉一国体制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因而表现出劝百讽一、光明正大的文化特点。因而,我认为,刘勰用这八个字是很能概括出大赋的政治文化指向的。
二、积极关注现实的西汉文章
在古代,所谓“散文”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始终处在一种变化的状态。其本意原是文采焕发,与今天所说的“散文”原本无涉。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名称,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实际上在南宋才开始广为流传[7]。为了区别于韵文、骈文,而把凡是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概称散文。随着文学概念的演变和文学体裁的发展,在某些历史时期,又将小说与其他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歌。至于近世,则与诗歌、戏剧、小说相对,凡是前三者所不收者,都可以归之于“散文”类。因此,“散文”的含义最为丰富。换言之,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之外,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散文,清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文”包括了诗词曲以外的全部文体,即赋、骈文及一切实用文体均在其中。比如,宋玉的《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就在其中,但是,没有收录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大概以为屈原《离骚》诸作是诗。但是,《汉书·艺文志》将赋分为四家,其一就是屈原赋之属,则汉人认为屈原的作品是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3]80说明刘勰也将屈原的作品视之为赋。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以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赋。而姚鼐《古文辞类纂》有辞赋类,选屈原《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而不选《九歌》,大约以为《九歌》名之曰歌,归入诗类。这样,自秦汉以下,辞赋均可称之为广义的“文”。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文”或“文章”或“散文”的概念,与现代的散文概念有所区别。
众所周知,古代散文起源于上古史官的记事、记言,具有鲜明的实用特点。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写作,推终原始,恐怕已经是唐宋以后的事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仅根据现代文学理论观念,画地为牢,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而是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将中国散文的源与流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将应用文体与纯文学性的文体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将古人心目中的名篇佳作与现代学者判定的散文作品联系起来一起考察,这样,才能清晰地把握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线索。
依据这样的认识,秦代李斯的石刻文、《谏逐客书》等就有重新评价的空间。《谏逐客书》善于运用比喻、排比的句式,使语言富有形象性,音节铿锵有力,明显带有战国文章的遗风。另一篇奏议《论督责书》,近似于战国一些法家文风,峻峭刻板,长于说理而缺乏文采。
汉初的文学家继承战国诸子的传统,积极入世,关心国家大事,写下了许多带有政论色彩的文章。论其时代,推陆贾为第一人。从戎马征战中夺得天下的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后,他并不清楚该怎样治理天下,他以为靠自己指挥打仗那套本领,就能对付得了。所以,当陆贾经常向他宣传文化知识,介绍历史经验时,他竟颇不耐烦地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也不客气地回敬道:“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就是说,夺取天下与保卫天下,所处的形势是不同的,使用的办法也应不同。历史上商汤、周武王文武并用,所以能够长久;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一味极武任刑,很快就招致灭亡。如果秦在取得天下以后,能变刑法,行仁义,借鉴历史经验,你又怎么会得到他的天下呢?刘邦听了这既尖刻又中肯的意见,心中虽然不高兴,脸上却有惭色。于是叫陆贾把这些想法都写下来,“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8]2113。表现出要了解历史、借鉴统治经验的愿望。于是,陆贾写出了论文十二篇,进一步阐释历史兴亡的道理。据说每奏一篇,高祖无不称赞,命名曰《新书》。这部书至今还在流传。
从那以后,以总结历史经验,批判现实弊端的政论文纷纷问世,形成汉初文坛一大潮流。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推贾谊了。贾谊的代表作是《过秦论》和《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过秦论》,顾名思义,是总结批判秦国的过失、说明秦为什么灭亡的论文。
西汉前期的政论文,除了规劝皇帝之外,还有的作者由于生活在藩国,纷纷上书诸侯王,希望他们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在这些文人中间,以枚乘、邹阳规劝吴王不要起兵的政论文最为有名。枚乘《上书谏吴王》、邹阳《谏吴王书》,分析天下大势,纵横捭阖,既富有文采,同时又具有相当的逻辑力量。汉初的这些写政论文的作家与汉武帝以后那些醉心于歌功颂德的辞赋家形成鲜明的对照。
西汉中期,散文名家辈出。《文选》中收录的东方朔《答客难》,以主客答问方式联结成篇,抒发其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苦闷。后来文人迭相效仿,如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悔》、郭璞的《客傲》,以至韩愈的《进学解》等,都可以说是《答客难》的拟作,可见影响之大。《淮南子》虽然出自刘安门客手笔,但是其中确有相当部分与刘安有关。《文心雕龙·诸子》称其“泛采而文丽”,富有浪漫色彩和汪洋的气势。司马迁的《史记》 虽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然而其文笔之富丽,气势之磅礴,可谓前无古人。
西汉后期散文,王褒《四子讲德论》《圣主得贤臣颂》《僮约》、刘向《谏营昌陵疏》、扬雄《解嘲》等,都是传诵一时的著名作品。特别是扬雄的《解嘲》,在思想内容和写法上都深受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成为西汉后期最重要的文章典范。
三、西汉诗歌的四种类型
汉代诗歌,内容比较庞杂。如果从形式方面着眼,可以分楚歌、乐府诗、五言诗、七言诗四种类型。
(一)楚歌
楚歌,顾名思义,是楚地传唱的歌诗。用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的话说就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者[6]344,均可称之为楚歌。而在先秦,楚歌最典型的代表当然就是《楚辞》。从这里可以看出楚歌在形式上的特点,即句式比较自由,多有“兮”字。这类作品,除《楚辞》之外,还有《孟子·离娄》里面记载的《孺子歌》(又叫《沧浪歌》)。此外还有《说苑·善说》记载的《越人歌》等,都是楚歌的典型代表。这种形式到了楚汉之际达到顶峰,因为刘邦、项羽均为楚人,所以,他们均喜欢楚歌。项羽作《垓下歌》,刘邦有《大风歌》。从这两首诗就可以看出,汉初诗坛,整个是被楚地歌声所笼罩。楚歌仍然为上层人士所欣赏。从刘邦的儿子赵王刘友,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无不演唱楚歌。不仅帝王皇室好作楚歌,就是武将大臣也熟悉楚调。李陵与苏武身陷匈奴,汉朝请求放还,匈奴允许苏武归汉。苏武将行,李陵置酒饯别,因起舞而唱楚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随着汉武帝恢复采诗制度,一些民间诗歌被收集到宫廷中来,其中有不少是五言句式,影响日益扩大,而楚歌的影响则越来越小,到后来,五言诗取代了楚歌而成为诗坛的主流。但是,这已经是在汉朝建国一百多年以后的事了。
(二)乐府
《汉书·礼乐志》记载说:“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9]1043清代学者沈钦韩认为这是以后来的建制来追述前代事,而清代另一位学者何焯则认为这是班固把乐府与太乐搞混了。乐府令应是太乐令之误。其实,这种疑问,早在宋代就已有人提出过,如王应麟作《汉艺文志考证》就已经怀疑乐府并非始建于汉武帝时。《史记·乐书》:“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10]1177此明言惠帝、文帝、景帝时即有乐府。《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治“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又三十六年,“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11]257-259说明秦时宫廷有音乐供奉。1976年陕西临潼县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秦代编钟,上面刻有秦篆“乐府”二字①参见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陕西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和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等文。。这就为王应麟的怀疑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证据,证明至迟在秦代就已经有了乐府。不过,秦代虽然设立乐府官署,但并没有建立采集民间歌谣制度,多演唱前代流传下来的旧曲。
《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12]1123这是记载先秦时期的情形。武帝时,又恢复这种采诗制度,故《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9]1045这个时候的乐工,主要还是童男女,人数也就在七十人左右,常常是采诗夜诵,昏祠至明。
从唐代杜佑《通典》的记载中知道,在秦汉时代,掌管音乐的官职有两个,一是太乐,一是乐府,各有分工。太乐掌管传统的祭祀雅乐,归奉常主管;乐府掌管当世民间俗乐,归少府主管。创立乐府用以取代大乐官。故《汉书·礼乐志》:“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9]1070-1071据此知乐府设在上林苑中。
在汉代,乐府诗的最主要特点是入乐。当时从民间采集来的诗歌通常叫作“歌诗”,如“吴、楚、汝南歌诗”等,而贵族文人的作品一般只叫“歌”,如汉高祖刘邦有《大风歌》,还有汉武帝刘彻有《李夫人歌》等,这些诗歌都曾在乐府机关中合乐,而且又被演唱,所以后来的人们把这些歌辞称为“乐府”①其实,这已经是一种转变,即由原来的官署之名变为歌辞通称。魏晋以后,“乐府”又由歌辞通称变为一种诗体的专称,如《宋书·自序》载沈林子著述,除诗赋赞等文体外,别有“乐府”一类。《文选》《玉台新咏》除诗赋之外,均设“乐府”一门。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诠赋》外,有《乐府》专篇,明确称“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说明魏晋南北朝人仍然从音乐上着眼,用以辨析乐府。就是说,凡是能入乐的,或具有音乐特点的诗篇,均可称之为“乐府”。至唐代,“乐府”概念已渐渐脱离了音乐的特征,而更加注重其内容,有所谓的“新乐府”之称。至于宋元时所说的乐府,则多指词或散曲,如《东坡乐府》等,那离乐府的原来含义相去就更远了。。
《汉书·艺文志》记载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2]1756该书记载的西汉一百三十八篇民歌目录是以地域划分的,涉及的范围边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东汉依然有专掌俗乐的机关,依然采集各地民歌。可以想象,当时采集来的民歌一定不在少数。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汉乐府散佚情况非常严重,现存的也就是四五十首。而且就这几十首,古人在把它们编辑起来时,由于分类的需要,常常把它们分在各处,如果不对其分类有所了解,查找起来就会感到困难。
乐府诗的分类,种类很多。可以根据作者来分,因乐府中有民间作者,有贵族文人,也有配乐制辞的音乐家;还可以从体制上来分,有首创者,有模拟者;还可以从声辞上来分,有因声而作歌者,有因歌而造声者。上述分类,历代学者都有尝试,但总是不很理想。所以人们多所不取,而按乐曲的性质进行分类,基本上为历来学者所认可接受。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早在汉明帝刘庄时代就“定乐有四品”。《晋书·乐志》分为六类,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分为八类,把民间乐歌区分开,郭茂倩《乐府诗集》分为十二类:(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曲辞;(4)横吹曲辞;(5)相和歌辞;(6)清商曲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辞;(12)新乐府辞。我们所说的汉代乐府诗歌的精华,大都收录在“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中,是用丝竹相和,都属汉时的街陌讴谣,或用短箫铙鼓的军乐。而贵族文人之作主要见于“郊庙歌辞”中。此外,“杂歌谣辞”中也收录了不少汉代民歌,因为未能入乐,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这类乐府诗,与民歌有较大的距离。
汉武帝后期,乐府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有些乐人名倡还显贵于时,贵戚五侯之家也畜养乐工,甚至与皇室争女乐。《汉书·礼乐志》载,哀帝作定陶王时就已经对此状况非常不满,及即帝位,“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特下诏书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9]1072-1073其实,此前乐府已经一再精简。《汉书·宣帝纪》载,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春,宣帝就曾下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13]245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六月,以民疾疫,刚刚即位的汉元帝又一次减少乐府人员。尽管如此,成帝时的乐府依然壮观。当时,桓谭为乐府令,自云“昔余在孝成帝时为乐府令,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定精简乐府人员,详细论列了乐府的分工、人数史料,是乐府研究的重要资料②参见台静农《两汉乐府考》,收入《静农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出版。施蛰存《汉乐府建置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期。芳婷婷《两汉乐府研究》,台湾学海出版社1980年版。。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才秉承皇帝旨意,下决心奏减乐府。故《汉书·哀帝纪》载诏曰:“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14]335居延汉简有“丞相、大司空奏可省减罢条”[15]128,当即此事。
(三)五言
汉代五言诗的出现时间问题,目前还有较大的争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五言古诗的兴起大约是在两汉。根据现有资料看,两汉以前,五言古诗很少,《诗经》以四言为主,虽然不时也夹杂着五言;《楚辞》句式参差不齐,与五言古诗的关系似乎更少。当然,楚歌中也有一些近于五言,比如,《孟子》中记载的《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说明在两汉以前五言古诗已经在民间有所流传,但是很少,而且不十分成熟,所以现存的史籍记载比较稀见。《汉书·外戚传》载戚夫人《舂歌》是三五句式:“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16]3937虽然杂有五言句式,但不是完整的五言诗。《汉书·外戚传》载,汉武帝时代的李延年也作有一首诗近于五言古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16]3951
当然,西汉前期,主要还是骚体和四言诗的天下,尤以骚体为主。刘邦有四言的《鸿鹄歌》和骚体《大风歌》。这两首诗见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所以比较可信。项羽最有名的诗是《垓下歌》,也是骚体。这首诗也见于《史记》和《汉书》,所以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西汉前期,主要都是骚体诗流行于诗坛。但不管怎么说,在东汉以前,民间已经有了全用五言句组成的歌谣。秦代文学部分曾引晋杨泉《物理论》所载秦时民歌便是五言四句。楚汉相争之际,唯有一首题为美人虞的《和项王歌》。《史记·项羽本纪》只是记载项羽为歌,“歌数阕,美人和之”。未载其词。《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记载了歌词:“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作为五言古诗,它已经可以说相当的完整。虽然这首诗的真实性叫人怀疑。但是,它首先著录于《楚汉春秋》,这部书虽然失传,但曾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且唐代尚存。因此,还不能遽然否定其记载的真实性。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6年在位)时有五言歌谣《何以孝弟为》一首,共六句。此后成帝(公元前32年—前6年在位)时又有《邪径败良田》《安所求子死》和《城中好高髻》等五言的歌谣,长者六句,短者四句。从上述的情况看,五言歌谣在西汉已经流行。
此外,还有所谓的武帝时代苏武李陵诗的问题,习称“苏李诗”。《文选》所收旧题苏武诗四首、李陵诗三首。此外《古文苑》又收有李陵诗八首、苏武诗二首。相传是苏武归汉时,李陵与苏武的唱和之作。这些诗,历来评价较高,被作为五言古诗的代表。比如《文选》中李陵和苏武赠答诗第一首分别如下: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
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这两首诗均收入《文选》,因而影响久远。钟嵘《诗品》将李陵诗列为上品,以为其源于《楚辞》,“文多凄怨者之流”。不过,这些诗作的时代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前所述,在西汉前期,主要还是骚体诗的天下,五言古诗远未定型,而苏李诗则相当完整,所以难以取信于后人。故刘宋时的颜延之虽然承认其“有足悲者”,但同时也不能不对其真伪问题表示怀疑。《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庭诰》①颜延之《庭诰》:“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37页。、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②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苏轼《答刘沔都曹书》③苏轼《答刘沔都曹书》:“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统不悟。”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29页。、洪迈《容斋随笔》④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四“李陵诗”:“《文选》编李陵、苏武诗,凡七篇。人多疑‘俯观江汉流’之语,以为苏武在长安所作,何为乃及江、汉?东坡云:‘皆后人所拟也。’予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益知东坡之言可信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5页。以及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梁章钜《文选旁证》等都认为这组诗为后人伪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组诗出现在什么年代呢?逯钦立先生《汉诗别录》中列举了四个方面的例证,说明苏李诗系东汉灵帝、献帝时的作品:其一,诗中有“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其中,“中州”一语,西汉文章中极罕言之,到东汉后期渐渐习用,指中原地区;其二,“清言振东宁,良时著西厢”二句已经涉及清言,实始于汉末;其三,诗中所述习俗,多与汉末相合;其四,东汉末期,人伦臧否风气盛行,矫情戾志,互相标榜,品目杂沓,诗中所写多近此风。
梁启超、马雍则以为成于曹魏时代。李陵诗早在东汉以前既已流行,而苏武诗当出现在魏晋时代。《诗品》叙述中有“子卿双凫”一语,似指苏武之“双凫俱北飞”一首,但钟嵘此文历举曹植至谢惠连十二家,都以年代为先后,“子卿双凫”句在阮籍《咏怀诗》句之下、嵇康《双鸾》句之上,则子卿当为魏人,非汉代苏武。梁启超怀疑魏代别有一字子卿者,今所传苏武六首皆其所作。自后人以诸诗全归苏武,连其人的姓名亦不传。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将苏李诗与自汉迄晋诸作相比,寻求“通用之字,常遣之词,皆作之句,同有之境”,又具体考订了诗中称呼的变化证明此说。建安诗中间有称“子”,但多数称“君”。汉乐府及称为古诗的五言亦如此。今存苏李诗除了“愿君崇令德”外,其余之称作“子”。今考建安时代称“子”者凡四见,及太和、正始年间,称“子”渐多,已取代“君”字。阮德如《答嵇康》诗中凡八称“子”,苏李诗当晚不过此。阮氏生卒年无考,但必与嵇康同时,推想此诗之作当在正始(240年—249年)初年。由此而推,苏李诗当成于公元240年左右,为曹魏后期作品[17]。
甚至,还有认为这组诗是西晋末到东晋初年淹留北方的士人所作,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18]。还有的说是东晋以后江南士人所作。不过这种意见古直早就有所辩驳:“使果出于东晋以后,则至早亦延之同时之作耳。延之博学工文,冠绝江左,何以同时之作,不能分别,而归其名于李陵邪?且东晋以后,声律暂启,群趋新丽,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其时工于拟古者,无过谢灵运、鲍照、刘铄,今持其诗与《文选》李诗相较,则去之不啻天渊矣。使苏、李出于东晋以后,试问谁能操此笔也?”但是此说仍不能服人,百字之偶云云,是指其人本色之作,而并非指拟古诗。陆机、谢灵运、江淹的拟古诗,逼肖原作,难说有天渊之别。
在汉魏六朝诗歌发展史,这组所谓“苏李诗”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其真伪问题也困惑了无数博学之士,时至今日,也没有讨论出个所以然来。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一反历代成说,认为不仅诗是李陵所作,就连答苏武书也是李陵的作品[19]。而这个问题,凡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又无法绕过,所以也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旧话重提,激发人们探索的兴趣。
(四)七言
西汉文人已染指七言诗。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联句创作的《柏梁台诗》就是其中的代表。
《世说新语·排调篇》刘孝标注引《东方朔别传》:“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诗。”但未引诗。《艺文类聚·杂文部》引曰:“汉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20]1003皇帝与群臣联句赋诗曰:
日月星辰和四时(武帝),骖驾驷马从梁来 (梁王),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 (丞相),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
撞钟击鼓声中诗(太常),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
周卫交戟禁不时(卫尉),总领从官柏梁台(光禄勋),
平理请谳决嫌疑(廷尉),修饰舆马待驾来(太仆),
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
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农),徼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
三辅盗贼天下尤(左冯翊),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
蛮夷朝贺常会期(典属国),柱枅欂栌相枝持(大匠),
枇杷桔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
齿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全诗二十六句,八十二字(官名不计),遣词用韵,古朴重拙,似非后人依托之作。如果《柏梁联句》确为武帝等人于元封三年所作的话,那么,就可以证明七言诗早在西汉前期就已经出现。而且,作为一种诗体,“联句究当以汉武《柏梁》为始”[21]464。当然,专门记载汉代历史的《汉书》里并没有记载此事,所以历史上也不断地有学者对于此诗的年代问题提出种种疑问。特别是清代以来,学者们对此诗越发怀疑,而且辩驳颇为有力。比如乾嘉学派最为推崇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提出了五条强有力的证据认为世传柏梁台诗不可信。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看法。逯钦立先生在《汉诗别录》中仔细辨析了《东方朔别传》的内容,认为此书实成于西汉。《柏梁台诗》既出于此书,正可以证明此诗确系西汉作品。加之此诗辞句古朴,亦不似后人拟作。再就史实而言,元封年间建立柏梁台也确有其事。因此,柏梁台诗确实是汉代的作品。
事实还不仅如此。秦汉以后,七言句式已在世间流行。余嘉锡《古书通例》“明体例第二”云:“《东方朔书》内有诗。《朔本传》言‘《朔书》有七言、八言上下’,《注》晋灼曰:‘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22]208可见东方朔七言诗并非偶然为之。不过据李善所引东方朔七言“折羽翼兮摩苍天”来看,东方朔的所谓七言,与骚体颇有关系。《董仲舒集》也有七言。又刘向、刘歆父子七言句式尤多。刘向七言:“博学多识与凡殊”“朅来归耕永自疏”“山鸟群鸣我心怀”等。刘歆七言:“结构野草起室庐”等。东汉七言也多有记载,如崔骃七言:“皦皦练丝退浊污”。李尤《九曲歌》似通篇为七言,如“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壮士翻日车”“肥骨消灭随尘去”等,所有这些并见李善注《文选》所引。《道藏》中的经典《太平经》收录了许多韵语,以七言为主的句式尤其多见。如:“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蚑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柏梁台诗》在武帝时出现不足为奇。《文心雕龙·明诗篇》、旧题任昉《文章缘起》等都已言及此诗。《初学记·职官部》“御史大夫”条引《汉武帝集》曰:“武帝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座。御史大夫曰:‘刀笔之吏臣执之。’”宋代发现的《古文苑》卷八亦收录此诗,每句下称官位,与《艺文类聚》同。又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称连句“起汉武帝柏梁宴作。人为一句,连以成文,本七言诗。诗有七言始于此也。”[23]61上述材料都是唐代或是唐代以前的文献记载。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因此断定说“七言起于汉武《柏梁》”[24]48,并注“柏梁体”说:“汉武帝与群臣共赋七言,每句用韵,后人谓此体为柏梁体。”[24]69尽管目前关于此诗的年代尚有争议,但是从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看,完全否定也比较困难[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