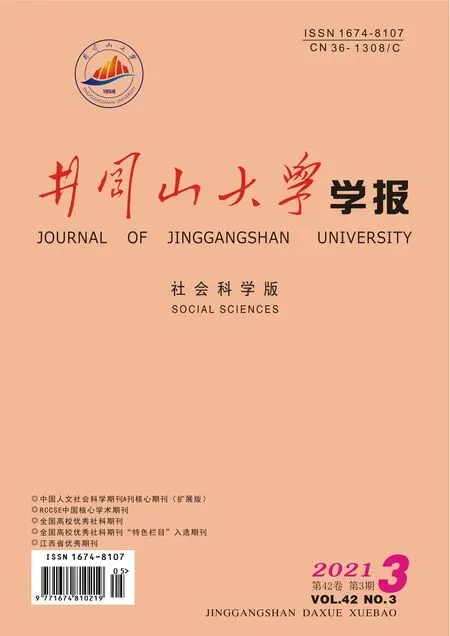“新左翼文学”三题
周平远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
21 世纪初,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新左翼文学”①首先以“左翼”为之命名的是季亚娅。在“新左翼文学”命名之前,出现过“新左派文艺”命名。由于1990 年代中期知识界出现了“新左派”概念,文学界顺势将这一概念挪移到文学批评之中。如吴义勤《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文艺研究》,2002,(5)),在文化批评中纳入了“新左派”批评;李新宇《新左派文艺批评抽样考察》(《走过荒原——1990 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勾勒了“新左派文艺批评”的轮廓和脉络;郑闯琦《中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北方的河〉》(《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6)),概括了包括“新左派”在内的4 种文艺史观,《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一条80 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1)),则对“新左派”文学史叙事进行了描述和阐释,等等。。有论者甚至断言:“新左翼文学”不但已经成为一种文学思潮,而且“已经构成了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1]
何为“新左翼文学”?
为何“新左翼文学”?
如何“新左翼文学”?
对这一度成为热点的前沿话题进行必要的反思与回应,具有一定的文学史研究价值。
一
一般认为,关于“新左翼文学”的命名,是从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开始的。曹征路发表于《当代》2004 年第5 期的《那儿》,描写的是改革开放背景中的国企工人的尴尬处境与艰难命运,以及他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这部正面描写工人命运及其精神风貌的作品,包含有“镰刀和斧头”以及“国际歌”等左翼文化符码,因而被视为一部恢复了“左翼文学”传统的作品。继而,《那儿》被认为“标志着左翼文学传统的复活”[2],也有被视为“左翼文学传统”[3]在今天的延续与当下中国“新左翼文学”的起点。[4](190)
在“新左翼文学”的讨论中,关于“新左翼文学”何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和“底层文学”的关系;二是它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把这两种关系梳理清楚,“新左翼文学”何为的问题便不难解决了。
“新左翼文学”是从“底层文学”中分化出来的。而直面苦难、勇于担当的“底层文学”,本身又是在与“纯文学”的长期博弈中脱颖而出以及应运而生。众所周知,1980 年代“去政治化”“非政治化”的文学思潮,经过“朦胧诗”“先锋文学”“新的美学原则”的浸淫而日益走向“纯文学”及“私人化写作”,伴随着1990 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然加速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分化,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但业已形成,而且给社会的公平正义与道德良知以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和道德压力,于是有了1990 年代中后期聚焦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并进而有了新世纪以来鼓吹“再政治化”“重新政治化”的“底层文学”乃至“新左翼文学”。
“底层文学”(包括“写底层”和“底层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正如有论者称,它既包括以1990 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为书写对象的“大厂文学”,也包括以农民离乡背井进城务工为书写对象的“打工文学”,甚至还包括沿袭都市文学和乡土文学传统而表现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百态的诸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式的“平民文学”或“市民文学”等,以致边界不清的“底层文学”,俨然成了一种“穷人文学”[5]。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4 年以来,“底层”和“底层文学”已成为文学领域的一个新热点,以致有论者称:“最近一年半的文学杂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说,都是将‘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选作基本的素材的。”[6]
由于侧重于书写苦难,所以才有了“底层文学”之命名。不过,“新左翼文学”的命名则不仅表现为它的直面苦难与直面当下,更表现为它的勇于担当与勇于批判。正如有研究者所称:“‘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7]换言之,最能体现“新左翼文学”之所以为“新左翼文学”的“新左翼精神”,即表现为它对于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
关于“新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的关系,有论者作过如此概括:“在关注现实、关注底层上,二者是相似的,而在思想资源与文学传统上,二者则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底层文学’的思想资源是人道主义,那么‘新左翼文学’的思想资源则是马克思主义,而在文学传统上则继承了‘左翼文学’的脉络,并在新的时期有所发展”[8]。
用“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区别“底层文学”和“新左翼文学”,是机智的,但语焉不详。将“新左翼文学”最为根本的特质概括为对于社会现实“见证与批判”的“新左翼精神”,则无疑要具体得多,也清晰得多。
对此,论者有详细论证与论述:“新左翼文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现象,便是很多作家将对社会现实和底层民众的精神与生存的“见证”与“记录”作为自己的追求。正是在对严酷现实触目惊心的“见证”与“记录”中,“新左翼文学”相当有力地对现实作了强而有力的揭露与批判。“新左翼文学”不仅“见证”和“记录”了资本强权的残暴与罪恶,而且还有力地戳穿和撕扯着它的伪善,它的欺世盗名的道德假面。由此可以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强权的嚣张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而戕害着底层民众并给他们带来苦难的,实际上还有权力体系中的败类和那些委身于资本强权的帮凶。在小说中,我们多次读到对于基层警察等“执法者”之“正义性”的质疑,读到作家对有关“执法者”和基层官员草菅人命的愤怒指控。其中最有新意的方面,还在于对资本强权和戕害着民众的某些基层权力的批判。实际上,这已经是对底层苦难的内在真相与社会原因的诘究与追问。尤为重要的是,“新左翼文学”还书写了以资本强权为主的权力压迫所导致的底层民众的个体反抗以及群体抗争,而这正是“新左翼精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新世纪以来,这样一种能够点燃我们怒火的作品不断出现。概而言之,“新左翼文学”中的“底层写作”就是这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见证”和“记录”着以资本强权为主体的权力压迫下底层民众的精神与生存,书写着他们阶级意识的初步觉醒和他们的勇敢反抗。而这种反抗与斗争在近年来的小说中已经越来越多,很多作品中这种人物形象已经组成了一个反抗者的形象谱系。显然,“新左翼精神”,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直面时代的战斗精神。[7]
从2005 年对“新左翼文学”命名的初步界定:“它以骨肉相亲的姿态关注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悲欢,它以批判的精神气质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不平等,它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呼唤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9];到2008-2011 年对“新左翼文学”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所提出的“主潮”论和“新左翼精神”论[7];再到2017 年带有总结性的理论概括:“新左翼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和阶级立场,站在社会底层的立场上,呼唤社会公平与正义,以毫无间隔设身处地的姿态,关注着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深入这些没有话语权的小人物的心灵世界,以现实主义的文学姿态直面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等[10];由此可以发现,批评者对“新左翼文学”的认知和评价,似乎越来越拉近了与现实主义文学的距离。
据此,是否可以认为: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表征的“新左翼文学”,其实就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而所谓复活了的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新左翼精神”,其实也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
二
现实主义文学最本质的内在规定性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它的真实性和批判性。
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植根于文学创作所包含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客体性与主体性这对矛盾范畴。由于倾向性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其中最具有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倾向性便是它的批判性,因此,现实主义最为基本,也最为根本的美学精神,便体现为它的真实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新左翼文学”所谓的“见证”与“记录”、“揭露”与“批判”,正是现实主义之所以为现实主义精髓的题中应有之义。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曾写道:“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于是“我搜集了许多事实,又以热情作为元素,将这些事实如实地摹写出来。”[11](p168-174)正基于此,巴尔扎克的小说有了某种经得起实证的文献学性质。对此,恩格斯强调指出: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汇集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2](p570-571)
显然,经典作家之所以对现实主义厚爱有加,首先就因为它以“见证”和“记录”为叙事方法的认识论价值和社会学意义。
唯其如此,马克思高度赞扬了“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3](p686)恩格斯声称:“我看到了《漂亮的朋友》生活中完全现实的一幕,现在我应当向吉·德·莫泊桑脱帽致敬。”[14](p588)反之,用思辨哲学抹杀了文艺真实性的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以及用唯心史观歪曲了历史真实的拉萨尔的《济金根》,则受到了他们的批评。马克思对夏多勃利昂更是写道:“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15](p102)而所谓“底层”,所谓“弱势群体”,所谓“左翼文学”传统对“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以及现实批判和对人民性的强调”[16],更是现实主义在经典作家心目中具有突出地位之根本原因所在。
早在英国宪章运动达到高潮后不久,1842 年11 月至1844 年8 月,恩格斯用21 个月的时间,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并根据亲自调查和考证的翔实资料,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认为,1835 年以来的宪章运动是反抗资产阶级的强有力的形式。1838 年的人民宪章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章派被恩格斯认定为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宪章派号召人民武装起来,甚至号召他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过去法国革命时代一样。对此,恩格斯写道:“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且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并进而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英国的工人政党将会完善地组织起来,足以很快地结束那两个轮流执政并以这种方式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的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17]
因此,对德国画家许布纳尔专注于“底层”和“弱势群体”的绘画作品《西里西亚织工》(1844),恩格斯作了如此评价:“它画的是一群向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对此,恩格斯指出:“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18](p589-590)“新左翼文学”论者曾引用钱理群的这一论述:“左翼作家(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由此而形成了其永远的批判性。”[19](p330)而“批判性”,恰恰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根基的现实主义之灵魂所在。正如马克思所强调: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0](p22)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首先体现为对人类历史传统、现实关系及意识形态等毫不妥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也就集中体现在它对现存事物的肯定性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否定性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正如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一样,现实主义“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此,所谓“新左翼文学”的批判性,不但是现实主义固有之义,也是现实主义力量之所在。
正基于此,恩格斯强调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力量和批判性锋芒的《西里西亚织工》,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出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12](p570)
当然,作为现实主义,它的批判性可以是鲜明的,也可以是隐蔽的:“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2](p545)
经典作家有关现实主义文艺的经典论述充分表明,无论是“新左翼文学”的“见证”与“记录”,还是它的“揭露”与“批判”,本来就存在于现实主义,至少是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和美学精神之中。
也许,正因为如此,“新左翼文学”论的质疑者强调了这一点:“左翼文学传统精神内里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从来没有在当代断裂,‘底层文学’的崛起不过是市场经济状态下现实主义精神的时代性表达。”[21]曹征路的《那儿》是他倡导现实主义的结果,只是由于特定题材、视角、情感立场的选择,使小说具有了某种“新左翼文学”的特征。与其将这视为左翼文学的复苏,不如说是作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22]而“新左翼文学”论的倡导者也承认:“新左翼文学”总体上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新左翼文学”也就是继承和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这一精神传统直面现实的文学。[7]概而言之,“他们本着朴素的直面现实的写作精神,道出民间的疾苦,控诉社会的不公,显示出曾在中国文学土壤中深深扎根的现实主义传统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22]
显然,认为“新左翼文学”其实就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应该不会是牵强附会空穴来风的。
三
如果“新左翼文学”究其实质乃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那么,在当下语境中,为何要特别标举“新左翼文学”的口号与旗帜?
我以为,以“见证与批判”为特征的“新左翼文学”,即不但具有社会文献的真实性,而且具有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现实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而不是长期以来所流行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伪现实主义”。由于各种各样的伪现实主义流行得太久,以至于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现实主义,包括1990 年代初以“冲击波”形态而名噪一时的现实主义,也被批评因为“分享艰难”而失去了现实主义“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本真形态与固有性质。
何况,在一个盛行以“后”为前缀命名的时代(如“后革命”“后现代”“后殖民”“后理论”“后……”等等),在一个多中心无中心眼花缭乱一片迷惘的新媒体或后媒体时代,如果一种声音不具有特别鲜明特别强烈的区分度与辨识度,它只能淹没在众声喧哗一片口水之中。也许,正是基于不拆屋就不能开窗之考量,“新左翼文学”口号才横空出世石破天惊。
无论如何,在文学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平庸化、消费化的语境中,“新左翼文学”引起了广泛关注是个不争的事实。就此而言,“新左翼文学”的批评策略应该是成功的。
应该肯定,“新左翼文学”有一共同特点,即聚焦底层苦难,关怀弱势群体,而且他们“对底层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也不是站在边缘把玩,而是以平民意识和人道精神对处于灰暗、复杂的生存境况发出质疑和批判,揭示底层人物的悲喜人生与人性之光。”[23]这种社会担当、道德良知与人文情怀,在商品拜物教和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私语化、快餐化、游戏化颓靡文风大行其道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而且,“新左翼文学”深入剖析当下社会生活中的敏感问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质疑与拷问,强而有力地重建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这不但对于历经了40 多年之久的改革开放目标的界定和确认,而且对于文学价值的重估和界定,对于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回归和中国左翼文学遗产当代意义的追寻,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对那些批评者保持应有的尊重与足够的敬意。
不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新左翼文学”是否可能,仍是个问题。
首先,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包括左翼文学运动,是伴随着具有世界性、国际化的共产主义运动——苏维埃运动而发生发展的。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运动,而是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一个分支、一条战线出现的。对此,笔者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同源性、同质性、同步性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整体风貌和历史过程,作过具体阐述详实论证,无须赘述。[24]
其次,从理论上说,笔者以为,左翼文艺之所以为左翼文艺,其最为根本的特质,不在于它的写实性而在于它的政治性,不在于它倡导的现实主义、平民主义,而在于它鼓吹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对此,国民党1933 年《查禁普罗文艺密令》关于普罗文艺特性的阐释,可谓一语中的:
盖此辈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用新写实派之技术,虽煽动无产阶级斗争,非难现在经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然含意深刻,笔致轻纤,绝不以露骨之名词,嵌入文句;且注重体裁的积极性,不仅描写了阶级斗争,尤为渗入无产阶级胜利之暗示。故一方煽动力甚强,危险性甚大;而一方又是闪避政府之注意。苏俄十月革命之成功多得力于文字宣传,迄今苏俄共党且有决议,定文艺为革命手段之一种,其重要可知也。[25](p360)
显然,普罗文艺之所以为普罗文艺,不在于它的“新写实派之技术”,而在于它“煽动无产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左翼文艺之所以为左翼文艺,关键在于“全系挑拨阶级感情,企图煽起斗争,以推翻现有一切制度”。因此,作为“文化剿匪”之重大举措,国民党一方面“严密查禁,以遏乱萌”,一方面以苏共、中共为楷模,制定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策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甚至鼓吹:“我们革命之能否彻底成功,就在文艺工作者之是否努力,是否尽了自己的职责!”[26](p84)应该说,国民党对普罗文艺、左翼文艺性质特点及其功能之认知与概括,是具有专业水准,符合文艺实际的。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便明确指出:“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27](p241)。冯乃超也强调:“文化问题就是文化领域上的阶级斗争问题”[28](p195),左翼文艺运动“也就是广大工农斗争的全部的一分野。”[28](p198)左联行动纲领的第一条便是:“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29](p185)。因此,“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29](p187)
1930 年8 月4 日,左联执委会通过了左联的第一个决议,便是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为号召:目前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转入积极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组织活动的时期。”[30](p203)由于目前的时代乃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因此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的斗争。苏维埃文学运动应该从这个血腥的时期开始。”“苏维埃文学运动应该为现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不能不是苏维埃文学运动的使命。”[30](p205)从此,“苏维埃文学”“苏维埃文学运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等代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新口号,频频出现于中国文坛。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才有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中的“两条战线”“两种围剿”之说,才有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支军队”“两个司令”①即“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之谓。
因此,只要注意到“左翼十年”所具有的上述性质,注意到中国左翼文学、左翼文艺所具有的政治性、阶级性、斗争性,不是一般的政治性、阶级性、斗争性,而是包含有极其鲜明极其强烈极其尖锐的党派性、对抗性、颠覆性的政治性、阶级性、斗争性。为了他们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美学理想,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身许志杀身成仁。
正因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文学话语与生俱来的阶级性、党派性、对抗性、颠覆性等质的规定性,是无法稀释更无法抹煞的。因此,在21 世纪的中国语境中,试图以“新左翼文学”的口号与旗帜来“激活”“复活”“复苏”“恢复”20 世纪中国左翼文艺传统是否稳妥,大可讨论。如果不加限定不设防火墙地鼓吹左翼文艺左翼话语,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险的。正如有论者断言:把左翼的激进情绪、革命立场和阶级斗争重新嫁接到当下,是不可能的;“新左翼文学”,只能是个“伪命题”。[31]
也许,正是基于左翼文学传统与现实政治语境存在不可调和的悖反与冲突,有论者另辟蹊径,对何为左翼文学传统进行了重新界定和阐释:“一种文学与政治的相关性,一种文学不只是为了文学自身,也不只是为了个人奋斗与个人审美,而是‘为……(如改造社会)’的目标,或者始终与‘为……(如改造社会)’为目标的视域相融合,也在此展现了新的可能——那不正是鲁迅时期的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吗?”[5]
如果将“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归结为“一种文学与政治的相关性”,而“新左翼文学”的特质也仅仅在于重新审视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时代的问题,那么,“新左翼文学”的命名是可能的。这比那种概括——“马克思主义赋予‘底层’的阶级性与斗争性”[4]似乎更“策略”些。
不过,问题在于,“中国左翼文学传统”能够被简单界定、概括为“文学与政治的相关性”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上世纪末,笔者曾经写道:文艺社会学的核心,是文艺的社会本质、社会过程、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而这,恰恰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与精髓,也是当下中国文艺实践和中国历史运动的强烈诉求,是全球化背景中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在走向开放与综合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趋势中,立足于把文艺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的文艺社会学,不但具有学术资源的本土性和学术价值的现实性,而且也具有学术视域的前沿性和世界性。[32]
本世纪初,笔者又曾写道:新旧世纪之交,在中国文论的“文化转向”中,出现了“走向文化诗学”和“重建文艺社会学”的呼声。它表明,20 世纪的文艺社会学传统和未竟事业,在21 世纪正在并已经获得了可持续发展。[33]
从1920-1930 年代左翼文学的“政治化”,到1980 年代纯文学所主张的“去政治化”,再到当下众声喧哗的“再政治化”,文学理论和历史似乎都陷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由此看来,尽管“新左翼文学”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也许只是一个神话,但文艺和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左翼文学”主创者之一,李云雷博士近年来又提出了“新现实主义”和“新社会主义文学”[34]口号。相对于“新左翼文学”而言,这似乎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与策略。
无论如何,它至少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与走向。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