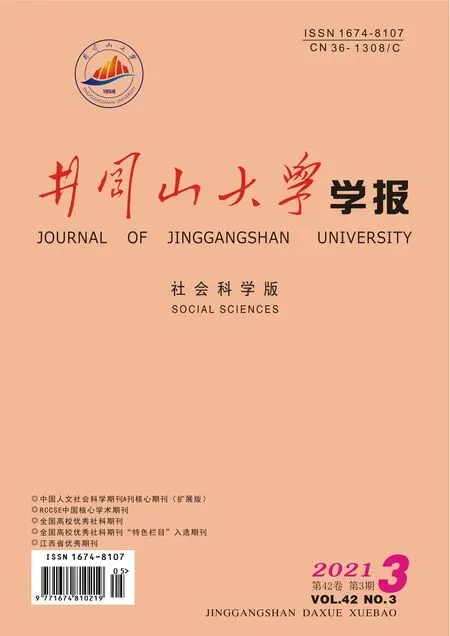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历史逻辑
易新涛,陈 霞
(1.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2.湖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65)
党性是一个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特征。加强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941 年7 月1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建党以来首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党内法规。《决定》要求全党加强党性锻炼,将党建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使全党成为在统一的意志、行动和纪律下的有组织的整体。以此为开端,在全党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增强党性的运动。马克思认为:“没有偶然发生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有其原因而且是由原因必然地产生出来的。”[1](P39)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极端困难之时,我们党通过《决定》,开展大规模的增强党性运动,绝非偶然。1941年底,时任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指出了作出《决定》时党所处的四种社会环境和条件。[2](P805-806)次年7 月,他在中央党校作增强党性的报告时曾谈到了四个原因。[3](P369)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决定》的研究文献中,偶有原因分析,但基本上没有超出,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在喜迎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全面分析抗战相持阶段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重温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把党性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着力思考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为什么要增强党性、如何增强党性等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一、在风谲云诡的抗战时局中勇担民族大任的现实选择
(一)武汉、广州沦陷后,日军开始调整对华的侵略方针及其相应的策略
其一,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早在1938 年1 月16 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如国民政府重新考虑而悔悟过来,诚意求和,则根据日本所提和谈条件进行谈判,否则,将扶助建立傀儡政权。[4](P258)同日,近卫内阁就发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占领武汉后,日本大本营认为:“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民国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5](P573)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了此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4](P259)的立场,公开诱降国民政府,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我方并不予以拒绝”。[4](P277)日本御前会议作出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提出:“制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合作的原则,特别要制定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的原则。”[4](P279)第三次“近卫声明”再次向国民政府伸出诱降之手,提出日满华“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4](P287)
其二,集中兵力,重点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称:“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6](P100)其参谋长笠原幸雄指出:今后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治安肃正的根本意义在于打破这个以地方武装为中心、以共军为背景且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6](P177)据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0 年“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6](P223)中提出,要“将各项工作有机地统一于剿灭共军的前提之下,继续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进行讨伐”。[6](P224)
其三,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1938 年7 月,日本五相会议制定的《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规定,“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4](P271)日本御前会议还决定,划蒙疆为高度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应按既定方针作为特别行政区域。[4](P280)随后,日本逐步形成东北、“蒙疆”、华北、华中等四大地区的殖民政权。12 月16 日,日本决定将管理占领区傀儡政府的统管机关“对华院”改称“兴亚院”,“在中国事变之际,担任处理在中国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有关确定政策的事务以及特殊会社之业务监督”。[7](P106)
(二)英、美等国继续奉行“绥靖”政策
1939 年7 月,英日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侵华为“合法”。1941 年3 月8 日到12 月8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举行了四、五十次谈判,企图使日本不以武力,“在道义上和行动上维护和保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8](P588)但是,日本逐步深入的侵华战争严重威胁着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在华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仅1937 年7 月到1939 年,美在华利益受日军侵犯的事件高达382 起,不到3 天就有1 起,但日本政府仅作答179 起。[9](P308)越来越多的美国朝野人士感到“绥靖政策是一条死路”。[9](P358)美国因此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其一,对日实行禁运。1939年1 月初,针对日本御前会议作出的“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和权益”“当然要受到限制”[4](P282)决定,罗斯福建议对日禁运军用物质且限制贸易,给中国提供1.7 亿美元贷款。4 月,调美国舰队从大西洋重返太平洋。7 月26 日,宣布废除《美日通商及航海条约》。从1939 年12 月到1941 年5 月的近一年半时间里,美国总统、国务院和联邦贷款署发表的近20 则公告和新闻宣布,钢铁、石油等重要物质对日实行禁运。其二,援华抗战。1939 年2月给予2500 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940 年4 月给予2000 万美元的滇锡借款。1941 年4 月1 日,美英通过《平准基金协定》分别贷给中国5000 万美元、500 万英镑,是自全面抗战以来中国收到的最大一笔英美贷款。[10](P483)5 月,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正式适用于中国,美国拨给中国物质总值达2600 万美元。[11](P148)英美对华政策的改变,无疑增强了中国战时经济和抗日能力,鼓舞了中国抗日士气,对于阻挡日本进攻,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战争部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或改变绥靖政策,而是为了自身利益,服从于“先欧后亚”、战后与苏联的抗衡战略等全球战略,客观上增强了国民党蒋介石积极反共的实力和基础。
(三)苏联的对华政策迅速转为“疏华联日”
随着德国的步步逼近,苏联认为“西面被认为是最危险的。预料敌人正是从那里实施主要进攻”,[12](P742)改变原来的“援华抗战”政策,转而实施“疏华联日”政策。其一,与日本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破坏中国主权。1941 年4 月13 日,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13](P303-304),以限制日本,维护其远东防线之重要环节外蒙古的安全,将大批力量抽调到西线参加反攻。其二,加紧渗透新疆。1940 年11 月,与盛世才签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锡矿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后,因盛世才“倒戈”国民党,并在新疆策动的反苏行动,苏联撤走所有的人员和设备,后将唐努乌梁海的最后一部分划入苏联版图。其三,停止对华援助。1939 年6 月13日两国签订的1.5 亿美元信贷协议,1941 年6 月停止执行,至此中方只用了0.73176 亿美元,不足一半,余额终未用。[14](P137)1942 年3 月,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苏联对华政策的改变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紧张和倒退,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抗战的困难,间接地加速了美蒋联合的步伐,促进了国民党政权的日益消极和反动。
面对日本的诱降、英美的劝降,加之国共力量的消长,国民党集团内部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日益发展。其一,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15](P273)“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15](P273)会议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15](P273)的反动方针,通过整理党务的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会后,秘密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全面布置了“政治防共”“军事限共”。1939 年冬到1943 年相继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二,与日本暗中接触,企图妥协投降。1938 年7、8 月间,蒋介石和何应钦派雷嗣尚通过箫振瀛与日本特务暗中密谋,后因武汉失守而不了了之。从1939 年11 月到1940 年9 月,日本开启旨在诱降国民党蒋介石的“桐工作”后,蒋日代表多次秘密会谈,终因“美国远东政策的强硬,英国大使的重庆之行,苏联、中共情况的活跃等内外形势,使一筹莫展的蒋介石发生了动摇”。[16](P125)其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于1938 年12 月29 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随后在南京凑成汪伪政权。可见,相持阶段后,“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17](P616)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共产党要担当民族的大任,切实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就必须首先增强党性,使自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团结成有组织的整体。只有这样,才能从民族存亡大局出发,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战直至最后胜利。否则,“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2](P443)
二、在抗战乃至于中国政治生活中引领民族未来的迫切需要
“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18](P804-805)与国民党观战避战形成鲜明对照,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深入敌后,依靠人民群众,创造灵活多样的斗争形式,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敌后战场1938 年抗击了58.8%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19](P95);1939 年抗击了62%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19](P97);1940 年日本对敌后战场作战的兵力47 万,占侵华日军的58%[19](P97);1941 年至1942 年,对敌后战场作战的兵力约40 余万人,占侵华日军的70%。[19](p97)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成为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否则,“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20](P140)因此,“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17](P535),党必须“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18](P945)
共产党“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21](P140-141)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全中华民族当务之急就是“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22](P759)1939 年7 月7 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政治口号,认为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是全中华民族继续努力的总方向。[23](P440)同日,在《致国民党书》中称:“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便成为目前抗战时局中的两种最大危险”,[23](P442)“而反共的活动,更成为日寇汪逆投降派借以挑拨全国,造成内部分裂中途妥协之最重要的关键,最实际的步骤。”[23](P448)9、10 月间,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的前途有两个,即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实行妥协、分裂、倒退;[17](P584)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唯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7](P591)1940 年,毛泽东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文章中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17](P763)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17](P745)“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17](P746)对顽固派的斗争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17](P750)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赢得了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部正义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坚持、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了自身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共产党“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21](P141)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宣传,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甚至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将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托之于蒋先生手中”,“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24]民族资产阶级尽管不满于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战前途心存疑虑,企图走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1939 年10 月到1940 年1 月,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抗战乃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前途和方向。同时,党还制定了包括“三三制”“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在内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领导广大军民广泛开展政权建设、工农业生产、“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灾荒救济和社会救助,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根除社会陋习,使抗日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社会文明的新社会。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7](P718)
毫无疑问,共产党已经成为抗战乃至于中国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力量。当然,要带领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引领民族的未来,就必须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正如毛泽东所说,从自己建党的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7](P652)而要实现这个政党建设目标,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党性锻炼。
三、在风险挑战中不断防范被瓦解危险的必然要求
共产党处于民族战争环境中,必须艰苦卓绝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相持阶段后,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中野蛮进攻的战略重点。“敌人不仅公开的在军事上围攻八路军,政治上破坏共产党,而且隐蔽的派侦探奸细混入我们的内部,来瓦解我们的军队与政权,破坏党的组织。”[23](P692)日本在华的特务机关规模庞大、机构繁多、密如蛛网。仅日本陆军省的军费预算支出就占日本全国行政(财政)预算支出的二分之一,而用来供给和组织情报的秘密费又占陆军省军费总支出的三分之一。[25](P4)这些特务机关异常猖獗,采取各种方式进攻抗日根据地。包括诱降下层,深入上层,作为一些军政长官的幕僚,从中拉拢;以开设货铺烧饭馆等作掩护,打入我政府机关,在根据地布置间谍,也即坐探;派遣流动的汉奸化装成邮差、小贩、公务人员、卖药的、乞丐等各种各样的人物出现,深入根据地进行活动;利用各种汉奸组织,通过派遣汉奸打入的具有封建结社性质的各种会门,如大仙道、长毛道、天门会、红枪会、白枪会、佛教会、九宫道、清水道、天仙道、老君会等,混入抗日根据地。他们侦探情报,窃盗文件,毒害将士,瓦解部队,混入后方机关特别是破坏伤兵医院,在日军进攻时指示爆炸目标,故意破坏军民关系。[26]毛泽东曾告诫全党,日本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党内,因而要“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17](P524)
党又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中,必须正视阶级矛盾的存在,防止阶级敌人的分裂瓦解。在这场全民族的自卫战争中,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一切必须服从于抗日的利益”。[17](P525)但是,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甚至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这就给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侵蚀我党以及影响我们的党员,又增加了一个可能性”。[2](P806)国民党一直视共产党为政治对手,始终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排斥打击。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各种反共摩擦,想尽办法削弱共产党。比如,利用我们某些党部与中央意见的不同,关系的不好,企图拉拢我们那些党部,来分裂共产党;企图分裂八路军和新四军,把新四军拉过去,或者造成共产党和军队的对立;采取许多办法打进我们党部和八路军、新四军里面来收买我们的人,瓦解我们。[3](P366)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后成立了反共的特务委员会,秘密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文件,提出要“加强特务工作,……打入共党组织”,[27](P323)“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27](P324)“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27](P324)在各地,国民党的反共特务活动日益猖獗。他们利用合法组织身份来掩护其在根据地的特务情报活动,或在根据地周围建立特务据点进行针对根据地的特务破坏活动,或利用土匪在抗日根据地发动武装暴乱,甚至千方百计在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内部建立所谓“高级内线”,从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国民党煞费苦心、处心积虑地将触角伸入边区,“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28](P207)耀县是军统特务对边区活动的中心,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由此潜入延安。[28](P208)对此,共产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六中全会特别要求全党提高革命警惕性,用锐敏的注意力,“严防日寇及其走狗——托洛茨基分子及一切汉奸和反共的分子们在共产党内部外部所进行的各种挑拨离间和破坏危害的阴谋诡计,以布尔塞维克应具的党性来揭发和反对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采取两面派方法的)反党的和危害党的分子”。[22](P764)1939 年8 月25 日,《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由于党的组织不巩固,“使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有了一些机会来进行破坏我党的阴谋”。[23](P579)10 月10 日,《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再次强调,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对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阴谋暗害工作,前所未有地加紧了,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最高限度的提高革命的警惕。”[23](P692)
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同时存在且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汉奸和其他反动分子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瓦解共产党。面对这样的复杂环境和艰巨任务,如果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存在违反党性的倾向,党内盛行严重的英雄主义、个人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和无组织状态,没有统一意志、行动和纪律,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机整体,无疑为中外反动分子分裂瓦解共产党提供了可乘之机。因而,“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的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3](P366)
四、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克服错误倾向、永葆生机活力的内在需求
(一)各种违反党性的倾向在滋生
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且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呈现出一些主要特点和特殊规律。中国革命必须长期立足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29](P49)长期处于独立、分散的状态;无产阶级人数少,“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30](P105);绝大多数来自于破产的农民,“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意识还未完全无产阶级化,还常常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甚至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2](P806),“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30](P105)。因此,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的小农意识弥漫于中国大地尤其是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党的建设,在党内容易滋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违反党性的倾向。1929 年12 月,古田会议指出,党内和红四军中存在着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其原因在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29](P85)而“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29](P85)1937 年9 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自由主义来自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是革命集体组织中的一种“腐蚀剂”,因而号召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它。[17](P361)
(二)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思想尚未肃清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反复出现了“左”右倾错误。其主要原因在于,党的理论准备不充分,没有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对中国国情认识不够,对革命发展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错误的估计;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因而,它不能为中国革命指出正确的前途和方向,不能很好地增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18](P800),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武器,从两个方面反对“左”右倾错误,从而“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的前提”。[17](P531-532)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既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更要反对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告诫全党:“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17](P532)
(三)大量发展的新党员迫切需要加强教育
为了适应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形势的需要,1938 年3 月15 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要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向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大胆地开门,“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22](P186)到1941年前后,党的规模由原先的4、5 万人迅速发展到80 万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群众性的党;就其领导骨干、党员的某些成分、革命工作等方面来说,“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17](P603)但是,新发展党员的来源和成分相当复杂。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党的理论知之甚少,对党的性质认识模糊;许多是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充满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高涨的抗战热情,但缺乏马列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革命实践的磨练,存在一些散漫、不服从组织纪律等不良习惯;有的存在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等错误思想意识;有的是地主子弟,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未完全入党,具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经不起残酷战争的考验,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更有甚者,某些地方党部追求入党数目,大搞突击运动,致使“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23](P579)这种状况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和党的组织巩固程度,模糊了党组织与群众抗日团体的区别,从而为敌人破坏共产党制造了机会。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23](P579)
(四)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不服从中央领导”、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甚至对立的态度、“党内独立主义”等党性不纯的问题时有发生
1935 年6 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依仗人多势众,拒不执行党中央继续北上的方针,坚持南下,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党和红军。全面抗战爆发后,尽管洛川会议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路线,但在长期分散、独立的战争环境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有些重大的问题,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3](P367)个别党部、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根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3](P368)他们表现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独立主义、思想上的个人主义。1937 年12 月,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挟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论断。随后,王明大闹独立性,凌驾于中央之上,到处宣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未作请示就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主张,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前总发布指示性意见。1938 年4 月,张国焘公开叛党。1941 年1 月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2](P68)“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常的程度”。[2](P68)2 月,分管妇女工作和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的王明又借《中国妇女》停刊之际,公然反对中央的停刊决定。因此,已经走向成熟的党清醒地认识到,加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党性,使全党成为具有统一意志、行动和纪律的有组织的整体,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毛泽东说:“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2](P70),“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31](P321)
总之,由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共产党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必须肩负新使命,加之日益壮大的队伍也需要加强建设,中共中央通过了《决定》,并在全党范围内迅速开展了增强党性的教育运动。它对于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增强党性,坚定信仰,加强组织纪律性,改造错误思想倾向,自觉维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团结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拥有9500 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同样正处于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肩负着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使命。因此,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新时代党性修养新要求,更加突出党性锻炼,不断增强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勇于自我革命,从而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在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经受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