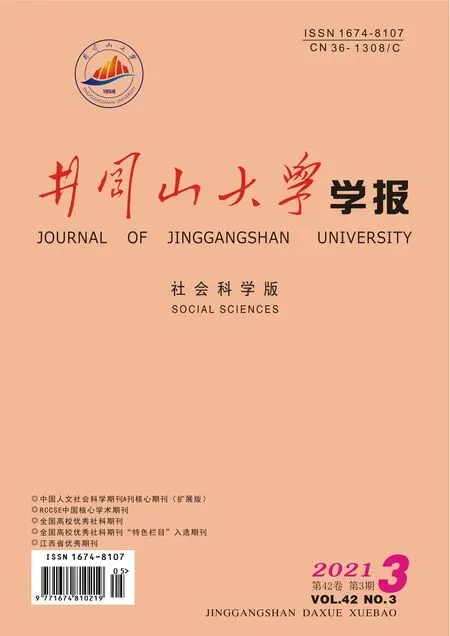从张太雷赴日看中共初创时的境况
——中共一大召开百年纪念
张劲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张太雷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又早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对他的研究和宣传因此相对较少。其实建党前后,张太雷的贡献和影响不小,如建党前夕就在莫斯科代表中共登上国际舞台;8 月回到上海,与中央的许多领导人一起工作;10 月又去东京一周时间,引发中央领导的第一次纷争。此事反映出当时中共面临的形势,以及许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相关人物品性的差异。张太雷日本之行的原因和过程,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订详细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认为:“尚有诸多不明之处。”[1](P299)可见,此事值得深入探讨和详细分析,并就此来看中共建党初期所处的困难境况和需要应对的复杂局面。
一、张太雷赴日前后
由负责中共北方地区建党的李大钊安排,张太雷1921 年3 月到达伊尔库茨克,担任刚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负责起草中国科的工作计划、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建党情况等。[2](P171-208)5 月,朝鲜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开会,张太雷代表中共发言致贺,还参与筹备远东大会①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针对将要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即在11 月开的太平洋会议,由美国发起并邀请英、法、日、意等国参加,有意孤立苏俄,签订了《五国海军条约》等。、起草呼吁书等。之后来到莫斯科,与俞秀松一起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书记处的达林在为张太雷申办代表资格时,评价张太雷工作认真之外,说“他在参加大会后将立即回国。”[3](P136)据此,当选少共国际执委会委员的张太雷,应该等到7 月23 日少共国际二大闭幕,从莫斯科启程回国,这样最快也需8 月中旬才能到上海,即便他提前几天离开会议,但7 月底也不可能在上海出现。因此,张国焘回忆一大期间,张太雷英译了党纲等,显然记忆有误。
回到上海,张太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除了向中共中央汇报共产国际三大等情况,任务还有整顿国内青年团组织、物色参加远东大会代表等。9 月中旬陈独秀到上海,接手中共中央工作,因与马林意见分歧,几乎不见面,这样,张太雷还得充当两者之间的协调人和联络员。10 月4 日,陈独秀被捕,5 日第一次庭审,6 日交押金获保释和在家候审,26 日结案:罚款释放。陈独秀这次被捕虽在狱中只呆几天,但案情前后拖了20 多天,行动自然不方便,情绪也不高。期间,张太雷去过一次日本。“这件事使陈独秀先生大为愤怒。他认为马林真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虽然被派任马林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需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4](P157)
此前,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负责组织、李负责宣传。还应选出过候补委员,其中有周佛海,不然难以解释他在一大后,负责中共中央的工作①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的回忆中说:在嘉兴南湖“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有我代理。”其中的“副委员长”一说,明显属于自我吹嘘。[5](P108)。而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准确说是在中共一大会场上出现过,因为他没有直接指导中共建党的任务和身份。[4](P142)中共中央建立后,马林建议作为中央领导人,应该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9 月上旬,陈独秀接受马林意见,辞去广东省政府的职务②1921 年9 月10 日《广东群报》“本省新闻”消息:“教育委员会欢送陈独秀……教职员特于昨日开饯行大会”;该报13 日消息:“陈独秀附轮返沪……”。,由上海派去接他的包惠僧陪同,离开广州回上海。囿于马林的身份限制及意见不一,陈独秀和马林很少见面,据周佛海回忆,两人是通过写信交流。中共一大后到上海的张太雷,还有召集远东大会代表的任务,并努力协调中共领导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期间,为召集日本参加远东大会的代表,张太雷得到周佛海、李达的同意和介绍,大约在9月底离开上海,10 月5 日抵达东京并见到了施存统,接触若干日本有关人士,12 日从横滨乘上“春日丸”回上海[6](P100)。这次秘密行动,虽然在日本时间不长,但事先没有告知陈独秀。
需要考察的是,陈独秀何时知道张太雷去了日本。现有的研究和资料,均不明确。按时间顺序推断一下,10 月1 日前,张太雷已经离开上海,陈独秀还不知道,否则已经生气、甚至加以阻拦;接着4 日下午,陈独秀在家中被捕,6 日出狱,此前自然无从知道也没有发怒的对象。保释候审回家,只能从前来探视的某人之口,陈独秀得到张太雷去日本的消息,于是发怒,因此也才有周佛海和李达又写信给在东京的施存统,而这封信张太雷12日离开日本之前已经看到。也就是说,陈独秀的发怒,是他出狱回家不久发生的事情。此时,确切知道张太雷行踪的,是周佛海和李达,其中一人把张太雷赴日告诉了陈独秀,这个人最有可能是周佛海,另外作为中央领导的张国焘也不能排除。从周佛海回忆来看,只说当时中共中央派人去各地,找人赴俄参加远东大会,而闭口不谈由他具体经手的张太雷赴日,似乎在刻意回避③周佛海回忆说:“记不清了,不知为一件什么事……仲甫是一条硬汉,一定要马林认错,才肯见面。而马林不肯认错,”到陈独秀被捕那天,几个人在陈家一起打牌娱乐,而后包惠僧来接替,周佛海则离开去约会杨淑慧,之后顺道去看马林,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让周佛海带信陈独秀,还说“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周佛海拿着信去渔阳里陈家,得知在陈家的五六人都被捕了。如果这一段回忆可信,说明:1.周佛海说记不清的事情,其实就是他把张太雷行踪告知了陈独秀,不料事情闹大了,就有意说记不清;2.这样,陈独秀就有可能入狱前,已知张太雷去日本,并愤怒地要马林认错;3.马林不肯认错,还写信告诉陈独秀,共产国际的命令都得服从,更让陈反感;4.陈独秀发怒,首先应该冲的是原来的中央负责人周佛海;5.周佛海的模糊叙述,不如非当事人的张国焘回忆详细,显然有问题。。倒是张国焘在回忆中却大谈此事,反而说明他没有顾忌(或是别有用心)。再说张太雷赴日,对陈独秀尚且保密,张国焘或许真不知道详情。这些情况,也反映中共建立之初,中央领导面临的险情和困难。
二、张太雷赴日并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决定
马林1922 年7 月11 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说共产国际二大之后,自己“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直到1921 年3 月我才成行。”这是马林来华的正式使命及具体任务。可是途中在维也纳被捕,护照上的入狱记录,使马林要去的国家,都拿不到入境的签证,4 月曾经打算经中国东北回俄国,由于日本控制着南满铁路而无法实现。结果由荷属印尼驻上海领事馆出面,马林于6 月来到上海,并利用公共租界的管理混乱、上海与各国交通和通讯等条件,能够“同中国、朝鲜、日本、爪哇和俄国的同志们保持联系。”此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伊尔库茨克成立,马林为成员之一,仍留在上海工作,故马林说:“我与伊尔库茨克书记处并无组织上的联系。”“只是名义上参加了书记处。我从未收到过伊尔库茨克来的任何文件……没有参与过书记处的决策和全盘工作。”而此时的张太雷正在书记处工作,包括筹备远东大会,此后张太雷去日本召集参会代表,其实正是这一工作的延续,不仅与马林基本无关,而且许多回忆也说张太雷赴日,代表的就是共产国际或者远东书记处。但马林在上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没有疑问。马林在报告中还自认为:“书记处的权限仅限于中国、朝鲜和日本,对我来说还有菲律宾、印度支那和荷属印度(尼)。”报告说到在上海开展工作很难,后来得到回国的张太雷帮助,“取得显著的成就”。远东书记处“下达的关于从中国、朝鲜和日本派出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后,当即同中国党的领导机关,就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做出安排。派同志到广州和另外一些城市去邀请那里的团体……张太雷同志被派往日本,邀请那里的同志参加。”[7](P223-227)其实,马林不仅去不了日本,而且在上海也被租界巡捕房监视,陈独秀回上海曾与马林有过两次短暂的见面,是导致很快被捕的原因,这也是中共一大会场出现密探的缘由。
马林报告的关键点:(一)马林虽然是共产国际代表,但没有指导中共筹建的使命;(二)远东书记处下达要找人开会的任务,张太雷回上海,马林又去不了日本,而且张太雷作为远东大会的直接筹办人,此事比马林更能够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处,更了解办会进程及对代表的要求等;(三)张太雷去日本,绝非马林个人的意图,并事先与周佛海等中共领导商定,决定时间应在陈独秀回到上海之前。
陈独秀怎么会认为是马林在指挥中共党员?并因此发怒,属于矛头错指。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当时集中体现在陈独秀与马林的交往。张国焘为筹备中共一大,1921 年5 月就到了上海,先是见李达,得知马林很难说话,后来与马林接触,“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一大后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佛海也回忆,马林致信陈独秀,“竟把第三国际代表头衔拿出来”,还表示“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可见,马林是以中共上级的姿态自居,行事方式又以势压人,没有尊重中共中央及领导。即便今天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作为共产国际的组织及成员,强调纪律和服从,马林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他并没有负责中共建党和指导中共中央的身份,中共也尚未决定加入共产国际[1](P246)。所以,马林对于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及领导人来说,不过是一个朋友和外人。而陈独秀针对的是马林没有权力命令中共党员,是想坚持中共的独立性,名正言顺,可以批评的只是态度有问题。
三、日本之行是张太雷勇于任事的表现
张太雷自1921 年3 月开始,在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8](P39)期间的任务就有参与筹备远东大会、起草呼吁书等。[6](P84-85)而后张太雷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8 月回到上海说是马林的助手,实际上还有召集远东大会代表等重要任务。马林报告中明确提到,由于日本警方的严厉控制,“几个月来我们在上海同日本的运动一直没有联系。”自己不能去日本,写信也被日本当局扣压,于是只能另外派人去日本,不二人选就是张太雷。马林还解释“格雷同志拿着一张英国护照于11 月中旬离开上海,11月22 日就在东京被捕。与他有联系的日本同志也在警察局招了供。”还好日本方面“在张太雷同志的帮助下,组成了一个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并建立起经常联系,“日本同志每半个月派一个信使到上海。”[7](P231-232)可见,张太雷的这次行动,促进了日共与共产国际及中共的关系,收获不少,应该肯定。而且是张太雷在远东书记处筹备远东大会时的工作直接延续,实际与马林关系并不大。张国焘不知详细内情,回忆中说张太雷先受李汉俊指派担任翻译、后受马林指派赴日,显然是凭想象或听传闻,加上对马林不满等。如果一大之后张国焘当时也是如此说法,想要坚持中共独立性的陈独秀听了,显然恼火。
据此可信,王一知的回忆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出的关于召开大会的宣言是太雷起草的……他还秘密去日本,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联系日本共产党派代表到伊尔库茨克参加远东人民大会。他在日本会见了堺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等人。”[2](P7)其实还转交了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值得注意的是,张太雷直接“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非马林派出的代表。周佛海也曾去长沙、汉口等地,物色赴俄的人选并发放路费,则是代表中共中央,故陈独秀没有异议。而张国焘回忆说张太雷就是受马林的指派,或许当时他也是这样对陈独秀说的,结果引得后者火冒三丈。张国焘的说法,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当时确实不知详情或后来记忆有误,二是别有用心,下文再叙。
张太雷自日本回国后,又为营救陈独秀奔忙,还说服马林用经费交罚款等,表明他非常关注和致力于中共的事务。陈独秀后来得知这一情况,对马林及张太雷的态度也有所缓和。其中反映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即经费的严重短缺。据张国焘、李达等人的回忆,也都谈到了这一点。年底,张太雷陪同马林到中国南方考察,与孙中山等接触,回上海后提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但建议当即遭到陈独秀的反对。表明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本质改善。
四、陈独秀对张太雷赴日发怒属于借题发挥
自广州回上海,接手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基于张国焘、周佛海、李达等提供的信息,陈独秀对马林也一直怀着不满的态度,甚至拒绝见面。而张太雷在协调两者关系时,明显倾向马林,陈独秀不可能乐意。张国焘和包惠僧的回忆也谈到这些情况。其实张太雷身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和少共国际执委会委员,日本之行是张太雷自身的职责所在,无可厚非。施存统就说:是“第三国际派张太雷去日本。”[9](P36)可以说即便没有马林,张太雷也要代表远东书记处去日本,因为他是这次大会直接筹办人。陈独秀借着马林指派中共党员一事发怒,细究起来,还真是有些无厘头。而周佛海、张国焘、李达,都有可能为息事宁人或者推卸责任,就说是马林指派了张太雷,还要求保密,似乎就瞒着陈独秀一人,结果只能愈发激其愤怒。
陈独秀发怒的缘由,首先是基于对马林及张太雷的不满,还有当时中央工作急需开拓而又经费短缺,加上被捕、出狱又没能结案,都是陈独秀借机发泄情绪的因素。后来陈独秀得知自己被捕之后,马林及张太雷为了营救,出钱出力不少,态度才有所缓和。但他对共产国际及马林的认识,并没有根本转变,直到中共二大之前,仍然对马林的许多意见持反对态度,只是碍于他们营救自己的情面,没有公开激烈与之抗争,但在致信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维经斯基,表现非常明显。[7](P222)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马林从莫斯科再次来上海,对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合作等,表示强烈不满并提议开会专门讨论。1922 年8 月底在中共中央西湖会议上,马林强调必须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并说明这是孙中山唯一能够接受的方式,结果遭到陈独秀及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反对,但因中共已加入共产国际,他们还是表示了服从的态度。不过陈独秀又提出一个条件,要孙中山取消加入国民党按手印及宣誓服从领袖等程序,否则即便是共产国际命令也反对。李大钊赞同陈独秀提出的条件,并劝阻大家避免与代表共产国际的马林争执。[10](P242)可见,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一直比较僵。
这些事实,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直接影响马林、陈独秀、张太雷,以及周佛海、张国焘、李达等人此后的工作。不过,从陈独秀发怒来看,其脾气性格及待人态度,确实存在不足。性格类似的鲁迅,与陈独秀曾经同事,却没能成为朋友,恰如他在《忆刘半农君》所说,虽然佩服率性直白的陈独秀,但更愿意亲近随和的刘半农。由于每个人的认识难免局限,尤其对待自己的同志和团体,如果个人情绪主导乃至意气用事,不仅无益而且不可能被容许。后来中共除名陈独秀,虽有共产国际及当时中共左倾错误的因素,但陈独秀的性格也有影响,使得他虽然认定方向时能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可作为文化名人,基于长期的知识积累和较多的问题思考,容易陷入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表现出来的是经常发脾气,也听不进任何告诫,不仅无法团结同志、维护团队稳定,还成为一批中共早期骨干不愿意与他共事的原因之一。
五、相关人物的不同表现
张太雷赴日和陈独秀发怒,导致“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争吵。在上海的同志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颇引以为忧。”[4](P160)此话不虚,因为这事对周佛海、张国焘、李达、李汉俊及施存统等中共早期重要人物,确实都有不同程度的直接影响,从中还可以看出这些人对此的态度及各自的品行。
首先是周佛海,作为留日学生党员的代表,一大后留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张太雷赴日经过他的同意,完全可以也应该为张太雷赴日之事进行辩护并承担责任,何况他自己也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到长沙等地找人赴俄。可陈独秀对此大怒时,周佛海采取了推卸责任的态度。就按周佛海回忆的说法:远东大会“中国方面要召集工人、农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六七十人,派去出席。时间非常倨促,而又毫无准备,急得我毫无办法。商量数次,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各大都市,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各大都市,都派人去召集,长江一带由我亲自出马,于是把营救仲甫的事,托付力子等人,乘直航长沙的轮船径赴长沙。”马林报告也提到:得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筹备远东大会,要中国、朝鲜和日本派代表参加,当即同中国党的领导就代表问题做出安排,派人到广州等地邀请……张太雷去日本。有意思的是,马林报告中对此没有用其他事情表达此时的“我”如何,而是说“共产国际的代表为此事”[7](P227-228)如何,可能一是想表达远东大会与“我”无关,二是共产国际代表除“我”之外,还另有其人——张太雷。简单地说,就是共产国际要找人去俄国开会,中共代理书记的周佛海不仅知道而且卖力执行,陈独秀回上海刚接手中央工作就被捕,按说周佛海不应离开,但面对可能的被捕险情和陈独秀发怒,却借机开溜,甚至致信在日本的施存统,不要理睬张太雷,这可是陷同志于险境的举动,更不能原谅。从中可见周佛海的人品,一旦有事和要负责任,其见风转舵、投机取巧的本性便会暴露。
再看张国焘,是中共一大后负责中央的组织工作。张国焘与张太雷非常熟识,但他对陈独秀因张太雷之事发怒,说是“也不愿多表示意见。”一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实际上却包藏浑水摸鱼的心态。张国焘回忆写道:陈独秀入狱后说过,“国焘等似乎未被捕。他虽有些地方顾虑不周,但他是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的。他有主张有办法……如果大家都赞成的话,可以由我代理书记的职务,那末,他纵然在监狱里住上几年,也就安心了。”[4](P164-165)还说这话是包惠僧告知的。可是,与陈一起入狱的包惠僧说:“陈独秀被捕后张国焘做了一件坏事。张国焘散发传单,题目是《伟大的陈独秀》或《陈独秀的生平》,说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张国焘的用意是想包揽党的事情,让陈独秀在牢中当书记。”[11](P369)张国焘的回忆和包惠僧的回忆比照一下,张国焘内心的如意算盘可以想见。联系此前马林曾经鼓动张国焘取代陈独秀,[4](P161)包惠僧的说法更可信。而且张国焘这种唯恐党内不乱的心态,也反映在他对代理书记周佛海的态度不善,说周在老家已经娶妻生子,在上海又与杨淑慧谈恋爱,其影响“对于这位代理中国共产党书记的青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将这件事当作笑谈的资料”,就是要让周佛海难堪、尴尬。[4](P155)
还有李达,1920 年8 月自留日归国,就在上海参与建党筹备,主编《共产党》月刊等。1921 年6月,与来上海的马林见面,并联系广州的陈独秀,决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达当时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表,承担了通知各地、组织会议、起草文件及会务工作,直到转移嘉兴南湖,都由他和夫人王会悟安排。张太雷赴日,李达作为中共中央当时在上海的主要成员,与周佛海一起,联名写介绍信给在东京的施存统。陈独秀知道后很生气,李达自然无趣。虽说负责理论宣传工作,担任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主编,编出一批马列著作,可是工作中也难免有思路不合,与陈独秀相处久了,李达提出辞去中央的职务,应毛泽东之邀赴长沙,任自修大学校长并创办《新时代》。李达后来回忆,1923 年暑期到上海,又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意见不同,“我的理由还未说完,他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好像要动武的样子……我当时即已萌发了脱党的决心。”[12](P18)脱党后,李达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保持了真理追求者和宣传者的执着。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的李达,对毛泽东也数次当面表达了不同看法甚至批评意见,难能可贵。
接着是李汉俊,留日回国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发起筹建中共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5 人之一,对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党组织的建立,都有直接贡献,董必武就回忆说他是自己接受马列主义的老师。中共一大开会也在李汉俊的住处,可见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颇多。可是1922年春,性格比较随和“从不与人争吵”[4](P141)的李汉俊,也因为与陈独秀及张国焘等意见不合,回湖北继续宣传马列主义和投身工人运动,可惜1927 年在武汉被军阀杀害。李汉俊与张太雷的交集不多,不知张国焘为何回忆:中共一大前,因为张太雷“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实际上张太雷一大之后才到上海,何况一大之前李汉俊也无权指派自共产国际回国的张太雷。
另一位直接受影响的是施存统。1920 年8 月中共最早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5 人,施存统也在其中,后去日本留学并治病。张太雷到东京,带着周佛海和李达写的介绍信,找到施存统,并通过他联络日本共产党人、转交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等。而后施存统又收到周、李的来信,说不要理睬张太雷,自然是莫名其妙又头痛无比,于是就把来信给张太雷看了,两人只能面面相觑。而张太雷与施存统的联系,石川祯浩根据日本的史料,认为早已在警方掌握之中,作为中共秘密党员,“施存统浮出水面,只不过是时间问题……12 月20 日,施存统被捕”,入狱10 多天后驱逐出境。[1](P300-301)回上海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由代表少共国际的张太雷直接指导,施存统接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恢复工作。1922 年5 月5 日,团的一大在广州召开,施存统当选团中央书记,张太雷、俞秀松、蔡和森等为团中央委员。由于严重的神经衰弱,施存统不久即辞去职务。1923 年秋施存统到上海大学任教,瞿秋白被当局通缉离校,他继任社会学系主任,1927 年登报脱党。
六、结语
张太雷赴日引发陈独秀愤怒,事情不大可是影响不小,表明中共初创之时,就需要应对许多困难的情况和处理非常复杂的关系,值得分析总结和深入思考的内容也很多,这里集中说两点。
首先,陈独秀的愤怒,其实反映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矛盾。而当时处于中央领导层中的周佛海、张国焘、李达等人,对此则态度不明或者干脆躲避,事后也没人再提沟通讨论、分析原因和汲取教训,使得中共最初就没能抓住与共产国际建立较好关系的机会,尤其是助长了陈独秀的执拗和任性,既贻害他的一生,也无益于党的事业。陈独秀从不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开始,到反对共产国际的诸多指示,再到不顾党的组织和纪律而被除名,仍然固执于自己的见解和小团体,乃至终身对共产国际及斯大林抱着批评态度,虽说其理由并非一无是处,但追根溯源,不能说与中共一大后中央领导层的这次矛盾没有关系。
其二,即便处于环境恶劣、形势严峻的年代,上下级之间、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仅仅一味强调服从并不够,上级组织和领导如何听取并尊重下级及个人的意见,同样也有必要。因为,下级组织甚至某个同志,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形势,以及认识问题和采取行动的过程及理由。姑且不论共产国际及代表,自居上级一直对中共指手画脚甚至越俎代庖,带来的危害众所周知。具体就张太雷去日本这件小事而言,他身为中共党员,又肩负共产国际的使命,还征得过中央负责人的同意赴日,而新领导陈独秀来后,没能了解详细情况和分析原因,就横加指责,结果引发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第一次矛盾。再说一个成功的事例,朱德1922 年在上海申请入党被拒绝,不能说陈独秀没有理由或脾气问题,因为对一个刚离开旧军队的将领,其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党的认知,显然没有把握,故凭感觉给予拒绝,应该说陈独秀这个上级和领导的决定,有其合理之处。后来朱德到柏林,结识周恩来,双方通过深入交流,得知朱德的身世、经历、追求之后,周恩来决定介绍其入党。如果作为下级的周恩来,只会服从或拘泥于上级的决定,此类明显利党的情况,也就很难发生,而尊重全体党员的主体作用和发挥党员的积极性,或许就只能停留在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