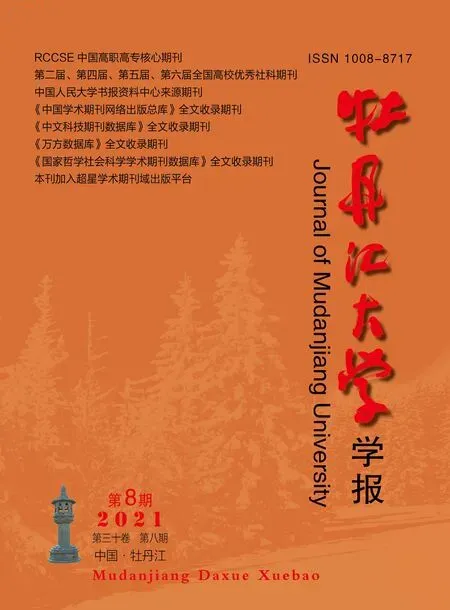被抑制的卑微
——考琳·麦卡洛小说中的同性恋主题
徐 梅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北京 10140)
“同性恋”(homosexuality)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有的一种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现象,而且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在动物界亦存在同性恋现象,英国著名性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认为,“男风”一般指男性同性恋现象或活动,而“同性恋的现象在动物生活史里就有它的地位”[1]。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在她的《性文化研究报告》中指出,“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无论是在21世纪,还是在远古时代。”[2]103源于对恋爱对象、情感产生原因、恋爱模式、恋爱内涵等不同要素的理解,专家学者们对“同性恋”内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在国内,《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对“同性恋”的定义是,“在正常生活条件下,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对同性成员持续表现性爱倾向,包括思想、感情及性爱行为;对异性虽可有正常的性行为,但性爱倾向明显减弱或缺乏,因此难以建立和维持与异性成员的家庭关系。”[3]在此之前,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张北川教授提出了“同性爱”概念,主张用“同性爱”替代“同性恋”,并对判定“同性爱”的标准进行了阐释:“在对性伴侣的选择拥有充分自由的条件下,一个性成熟的个体如果具有明显或强烈的指向同性的性欲或同时存有主动的同性性行为,方可视之为同性爱者。假如个体仅有偶然的同性性行为,但有关性定向的自我意识模糊,可视为同性性行为,而不宜简单地判定其为同性爱者。”[4]李银河教授则对“同性恋取向”和“同性恋者”进行了区分,她认为,“同性恋性取向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同性恋者则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5]在国外,专家学者们对同性恋的认知与阐释也不尽相同,法国著名同性恋史研究专家弗洛朗斯·塔玛涅(Florence Tamagne)强调的是“性吸引”指向,他认为同性恋是一种性吸引指向同性别人的性爱形式。[6]英国性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在判定同性恋时侧重的是“性冲动”,他认为性冲动的对象是同性而不是异性时就可以称为同性恋。[7]美国生物学家、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则认为同性恋是“性别相同的人所建立的性关系,既指肉体关系,又指精神关系。”[8]
在考琳·麦卡洛的小说研究中,同性恋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Colleen MuCullough:A Critical Companion》一书曾强调:《一个下流的痴迷》在情节层面上一个明显的主题是同性恋。[9]102除了这本书,她的《恺撒大传·十月马》《摩根的旅程》《遍地凶案》《荆棘鸟》《罗马第一人》《呼唤》《特洛伊之歌》《班纳特小姐的自立》等多部作品均对同性恋现象进行过呈现,对同性恋话题进行过探讨,综观中外专家学者对同性恋的不同界定和理解,考琳·麦卡洛笔下的同性恋现象既包括同性恋倾向,也包括同性爱。在她的作品中,她在对同性恋者的边缘化地位进行客观性呈现的同时,也对同性恋行为的自发性、原生态的美进行了赞誉,为同性恋者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进行了呐喊,但是,她笔下的同性恋者从未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而奋起斗争,也没有去争取自己行为的合法化,这固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是作者个人对同性恋行为的纠结态度使然。
一、被边缘化
李银河教授认为“大量已有的研究表明,同性恋者虽然在整个人口中占少数,但其绝对数量并不少;尤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跨文化而普遍存在的现象”。[2]113同性恋是一种性文化现象,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更是一种性文化现象,因为它涉及观念、风俗、科学知识和法律等诸多问题。从历史上看,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除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中外历史上,这一行为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非议和漠视。在同性恋发展史上,中世纪时期的同性恋受到了最为坚决的禁止和严酷的打击。此后,同性恋也一度被列入“犯罪”“疾病”之列。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快,人本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们也开始理性化地审视同性恋现象,同性恋也逐渐从“犯罪”“疾病”等“罪名”中挣脱,但即使是转变,同性恋问题仍处于社会问题的末端,所以同性恋问题至今仍是各国的边缘化问题,其原因如中国同性恋史研究专家张在舟所强调的:“他们把一般的同性恋置于社会问题中的末要位置,认为只需要民众去进行反应性的自发调节即可,而不必用系统高深的理论去加以研究,做出规范。”[10]
作为一名热情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和现实主义作家,考琳·麦卡洛通过小说创作,通过多个视角展现了社会强加给同性恋者的心理创伤,呈现了同性恋者作为边缘群体的边缘感。考琳·麦卡洛之所以对同性恋者的人本需求被抑制之苦进行书写,主要源于考琳·麦卡洛对同性恋者不幸生活的见证和感悟。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作家,不管是在澳大利亚生活时期还是在英国、美国游历时期,考琳·麦卡洛目睹的都是同性恋被禁锢、被抑制的事实。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同性恋仍然被视为罪恶。《Colleen MuCullough:A Critical Companion》指出“在1945年的美国,同性恋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变态……同性恋等同于耻辱和内疚。”[9]103在英国历史上,同性恋者的处境也曾非常悲惨,迫害同性恋者的丑闻不断发生,最著名的丑闻便是迫害“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在初创时期,几乎是全面移植英国文化,其中包括对同性恋的禁锢和压制,直至2017年12月,同性恋婚姻才在澳大利亚取得了合法化。出生于澳大利亚、受英国文化影响、在美国游历期间见证了石墙事件的考琳·麦卡洛对同性恋者被边缘化的悲剧进行了真实呈现。在她的作品中,无论是在几千年前的古罗马时期,还是在英国向澳大利亚倾倒罪犯的18世纪,抑或是在美俄对峙的冷战时期,同性恋都是一个被规避的存在。
考琳·麦卡洛以上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的美国小镇为背景的转型作品——《遍地凶案》呈现了当时社会的动荡、混乱、阴郁政治对人性的抑制,其中包括同性恋者所遭受的排斥和疏离。此期的考琳·麦卡洛在美国进行神经病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她对当时主流社会文化对同性恋者的压制及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呼声有着直接的感触,因此,《遍地凶案》中的同性恋者由于遭受主流社会文化的驱逐而普遍呈现出猥琐状态:他们有虐恋倾向、奸尸,与犯罪相关,属于边缘群体,过着阴暗、离群索居的生活,遭受主流文化疏离。考琳·麦卡洛在《遍地凶案》中,通过珀维这一人物形象来呈现同性恋行为不为社会认同,需要掩饰、遮蔽的现实。正如艾丽卡·达文波特博士所言,当时的同性恋者为了获得传统文化的认同,不得不乔装打扮,掩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以便释放自己的本能需求:“他装成男人中的男人——从一方面讲,又是男人中的男人们不太愿意追求的对象。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同性恋,对装扮成女人的青年有一种强烈的爱好。”[11]132该作品中史密斯的观点则代表了当时社会舆论对同性恋者的普遍仇视态度。史密斯不仅对妓女、同性恋者、诱使自己女儿堕落的迪伊·迪伊进行诽谤、诅咒,而且,对于自己手下职员中的同性恋者也充满毫不掩饰的敌意:“探长,他是个同性恋,我不喜欢同性恋的人。于是就把他流放到外蒙古去了。”[11]280虽然作为社会正义力量的化身——侦探,卡尔米内曾公然反驳史密斯对待同性恋者的敌视态度:“……可我不同意你关于同性恋的看法。对一些男性来说,这是种天生的特殊情况,不能和我遇到的性犯罪混为一谈。”[11]281但是,他也难以逃离当时社会文化的浸染,对同性恋现象进行无意识的疏离,对于自己儿子的名字,卡尔米内竭力排斥能让人联想到“女人气”“同性恋”的字眼——“朱利安”“西蒙”等,尽管他的妻子戴斯迪莫娜理性地提醒他不要对同性恋抱有偏见,但是,卡尔米内强调不得不面对社会和世俗的压力。
考琳·麦卡洛的《恺撒大传·十月马》通过盖尤斯·马略因为同性恋而被诛杀的故事和提图斯·庞玻尼乌斯·阿提库斯的政治前途在同性恋这个话题上无疾而终的悲剧,真实呈现了当时同性恋者在仕途上遭受冷遇的现实和同性恋者的自我被隐匿的痛楚:“可惜阿提库斯内心的爱情已经萌生了……他害了一场足以置他的政治生涯于死地的病症,这就是爱情。而且他爱的都是那些面貌俊朗、性情娇弱的小伙子,这在罗马的上流社会是不被接受的……”[12]345
考琳·麦卡洛于2003年出版的第二部家世小说《呼唤》,以19世纪英国移民潮、澳大利亚淘金热、澳大利亚工业初创期为背景,在这部作品中,她也谈到了在主流文化的审视中同性恋是造成家庭、婚姻不幸的罪魁祸首:“琼的丈夫非常喜欢年轻男人,这在爱丁堡几乎无人不晓。可怜的琼,难怪她一直没有孩子。她喝酒太多,待人冷淡。”[13]考琳·麦卡洛用同性恋者的家庭悲剧呈现了当时社会文化对同性恋的否定态度。《班纳特小姐的自立》(《傲慢与偏见》的续篇)以19世纪初期的英国为背景,在该作品中,考琳·麦卡洛通过父亲威廉·达西对儿子查理同性恋传闻的愤怒态度,表明了当时社会对同性恋的极度厌恶情绪和同性恋者的人本需求被囚禁的现实。
二、人格的卑微
埃利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讨论了一种特殊的逃避机制,也就是现代人为了逃避由于个性化而导致的孤独和焦虑而采取的一种趋同机制,这种趋同机制在考琳·麦卡洛笔下的同性恋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同,刻意抑制个人的同性恋倾向,遮蔽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在这种对自己本能需求的特殊逃避机制中,“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这正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14]123但是在变得与其他人一样的过程中,他放弃了自我。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言,“人放弃个人自我,成为一个机器人,与周围数百万的机器人绝无二致,再也不必觉得孤独,也用不着焦虑了。但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那便是失去了自我。”[14]123考琳·麦卡洛笔下的同性恋者为了使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得以安放,他们不得不以自我异化为代价,以卑微的姿态存活于被当时社会视为“常态化”的异性恋之间。
在《摩根的旅程》中,考琳·麦卡洛塑造了一个外在条件、人品和政治地位都非常优越的同性恋者:亚历山大号上的四副——斯蒂芬·多万纳:“他个子很高,很苗条,长得挺英俊,甚至可以说漂亮……他眼睛的颜色是像矢车菊一样的蓝色,眼神里充满了快乐。”[15]271但是,在作品中,相对于理查德·摩根这位被当时社会认同的异性恋者,斯蒂芬·多万纳的人格是卑微的,他祈求得到流放犯理查德·摩根的爱,可是遭遇了理查德·摩根的断然拒绝。虽然理查德·摩根与斯蒂芬·多万纳的社会地位是颠倒的,但是,他理直气壮地拒绝斯蒂芬·多万纳的同性爱示意,表明了当时社会规约对异性恋的肯定、对同性恋的否定态度。在这部小说中,考琳·麦卡洛还通过约翰尼·利文斯顿这一同性恋者形象表达了当时同性恋者沦为掌权者的玩物、在主流话语面前无法获得自我的悲剧。“约翰尼·利文斯顿身材苗条,举止优雅,一头金色的卷发,一双大大的、充满生机的眼睛长着长长的黑睫毛。他非常漂亮……”,但约翰尼·利文斯顿的命运却是“注定要成为众多海军军官喜欢的玩物”[15]424。
在《恺撒大传·十月马》中,考琳·麦卡洛中还提到了渥大维和马尔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之间敞亮的、自然萌发的同性相惜之情,但出于时代因素的考虑,恺撒从政治家的必备素质出发,强烈建议渥大维通过异性恋、结婚、生子等形式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进行掩饰,进而将对马尔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的倾慕之情扼杀在萌芽状态:“在一个人的仕途中没有什么比畸形的嗜好以及道德堕落更能把他拉下水的,你一定要将我的警告铭记于心。”[16]恺撒对渥大维的“警告”代表了当时社会对同性恋的定位,在当时同性恋属于“畸形嗜好”“特殊癖好”之列,同性恋群体更是一个卑微的存在。
三、天性的流露
对苦痛的见证和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的担当意识让考琳·麦卡洛在创作过程中担负起呈现苦难历史、维护同性恋者人本需求的重任。但她不仅对同性恋者被边缘化的悲剧进行真实呈现,而且还对同性恋行为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同时,她还对同性恋者之间自然萌发的情感予以肯定、赞美,对同性恋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给予了充满人性温暖的关注。考琳·麦卡洛笔下的同性恋行为是自发的、稳定而独立的情感,它的存在与异性恋并不矛盾,在她的笔下诸多人存在双性恋行为。在她的作品中,同性恋倾向是一种自发的、无法治疗也无需治疗的自然感情,它们以一种文化的姿态存在,自然而然,并不迫于环境的压迫或者异性的缺失。考琳·麦卡洛通过对同性恋行为自发性唯美的阐释,表达了对同性恋倾向的敞亮态度,表达了对同性恋现象的尊重。
考琳·麦卡洛享誉全球的家世小说《荆棘鸟》通过克利里家一对双胞胎兄弟之间的同性恋行为所遭遇的异样目光和嘲笑呈现了同性恋者在20世纪40至50年代的澳大利亚仍然被排斥的窘境。詹斯和帕西之间无意识的、发自本能的同性恋关系虽然招来了周围人善意的玩笑和异样的目光,但是,考琳·麦卡洛通过詹斯和帕西之间无意识的同性恋行为强调了同性恋行为的合理性,考琳·麦卡洛还进一步强调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慰藉、抚摸带来的巨大的身体愉悦和满足感。《荆棘鸟》中帕西和詹斯这对孪生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他人眼中就是“黏糖”,但是,他们之间的亲昵行为毫无传统文化描绘的同性恋者之间的猥琐之态,他们的亲昵仿佛来自于身体内部的本能渴求,随着生命的诞生而诞生:自然、原始、充满生命本能的热望。这种真实、原始的感觉让他们感受到了自我存在的真实:“他们肩并肩地走着,比一般男人们之间允许的程度要近乎得多。有时他们愿意互相抚摸,他们并没有发觉这一点,只是觉得像一个人抚摸着自己的身体……似乎使他们肯定了自己的存在。”[17]考琳·麦卡洛将詹斯和帕西之间发自本能的同性恋行为用诗意的语言呈现在读者面前,其实就否定了当时社会规约对同性恋进行边缘化处理的可悲之处。
1969年6月27日,美国爆发了同性恋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石墙运动。石墙事件终于让同性恋者不再沉默,更让他们意识到,唯有自己去争取,才会被尊重。[18]但是在考琳·麦卡洛的笔下具有同性恋倾向或者同性恋者并没有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抗争,更没有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发起挑战。在考琳·麦卡洛的笔下,同性恋者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他们是无辜的、卑微的,但是,他们没有进行抗争,没有捍卫自己的权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考琳·麦卡洛对同性恋现象的纠结态度:一方面,作为一名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和一名离散型作家,考琳·麦卡洛以广阔的视野倾注着对同性恋者的人性关怀,对同性恋者的关怀、同情自然而然流露笔端,汩汩而出;但另一方面,考琳·麦卡洛又难以逃离传统文化的影响,致使她作品中的部分同性恋者呈现出猥琐状态,他们人格卑微,处于社会边缘,自我被社会舆论淹没。
考琳·麦卡洛也许在同性恋者的自我拯救和同性恋被边缘化问题的解决方面还缺乏相应的探讨和思索,但是,她能通过小说创作真实呈现了同性恋者被边缘化的悲剧,能通过作品有力表现同性恋美好的一面,相对于她所处的时代来讲,不能不说拥有了一种前瞻性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