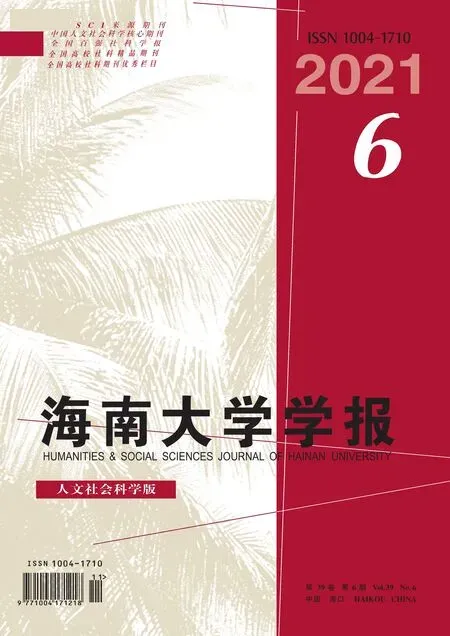王夫之罪情论发微
——兼论其对情的界定及省察治情之道
高阳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211189)
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情不仅被提升至形而上的高度,而且形下意义愈加凸显。时至明末,诸如泰州学派等阳明后学以情为性、即性即情的思想直接导致了情泛滥风气的形成。然而,王夫之并未受到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他把情从至高的神坛下放以探究不善的来源,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罪情论。王夫之认为情是不善的来源,故而情应当承担不善的罪责,“其能使为不善者,罪不在情而何在”①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66页。,此即王夫之罪情论。已有的研究成果②周兵《王船山罪情论》梳理了王夫之对传统将才、气、物以及物欲作为不善之根源说法的批驳,进而指出王夫之将不善归罪于情的主张;王林伟《王船山之情论发微》讨论了王夫之对情的界定,明确了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进而从理欲关系的角度阐明情的正当性。以上研究虽肯认罪情论的存在,但对于情如何为不善以及如何发挥情的积极作用未能展开详细论述。同时,学界也不乏王夫之贬情的评价:陈来《王船山论“恶”的根源——以其孟子诠释中的罪情论为中心》认为王夫之心性情论具有“尊气贬情”特点;陈丛兰《船山性情观刍议》则指出王夫之对“尊性贬情”唯理主义的认同。此外,孙钦香《船山论“情”》在对情的疏解及功罪分析的基础上也认同王夫之贬情的倾向。肯认王夫之罪情论的存在,然而,对于情如何为不善以及如何向善未能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同时,学界针对罪情论亦不乏王夫之贬情的定位。深入理解罪情论不仅在于明确“恶自情出”“归罪于情”的价值判断,还需要对王夫之关于情范畴独立性的界定、情之不为善的生成以及如何治情以向善等问题做具体而微的考察。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试陈管见,期以展现王夫之罪情论的全貌,进而探究其在儒家情论史中的价值与意义。
一、情:“变合之几,成喜怒哀乐之发而为情”
情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在先秦时期尚未成熟。在孔孟思想中,情通常指涉情实③情实指真实情况,“实”是事实意义上的确实,而非科学意义上的真理,是事物的真实展现。虽然早期的情更多指情实,但情的情感义也逐渐产生。情感与情实存在差异,情感偏向指人,情实偏向指事、物,但情感义没有完全背离情实义,在某种程度上情感义是情实义在人格化层面的发挥。情实义与情感义有相通之处,情感表现的是人真实存在的特质或属性,从情实到情感即从事物之真实推广至人之真实。可以说,情的情实义与情感义均基于真实,情实反映了事、物的客观真实,而情感反映了人的主观真实。情感义不仅延续了情实之真,而且这种真还被赋予价值判断的意味。如荀子所言,“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百姓有爱憎的情感,却没有表达欢喜愤怒的恰当形式以宣泄心中的爱憎,则会发生混乱。需要注意的是,早期文献对情感的讨论多从喜怒哀乐等进行描述,这表明虽然情之情感义的产生不早于情实义,但古人对情感的关注却早已存在。,包括客观事物与人性本然的实情。情“不具有实体性,而是一个功能性的、作用性的、关系性的、相对性的概念”①陈昭瑛:《儒家美学与经典诠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如《论语》“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②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中的情指实情,《,《孟子》“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中的情则指人性本然为善的实情③“乃若其情”是孟子回答公都子之问的内容,公都子转述了他人对人性的三种看法,性无所谓善与不善、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以及性善与否因人而异,进而向孟子请教这些观点。尽管孟子以性善论著称,但他并未直接言性善,而是提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可知此处的情与性密切相关。“乃若”是发语词,无实际意义。孟子言“其情”而非言“情”,可知“其情”针对公都子所言。公都子表面上在转述他人对性善与否的观点,实际上也陈述了人性的种种实情。以上种种对应“其情”,情似乎可以理解为人性的实情。然而,联系“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人性的实情有为善的表现所以说人之性善,这样的理解无法契合孟子性善论。公都子转述的人性实情确然,但孟子认为这些内容皆无法推翻性善。孟子指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以水喻性,水往低处流是水之本然,而人之性善“犹水之就下”,善即人性之本然。尽管人性无有不善,但现实之势驱使下的人性表现有为不善的可能,此之一如水受外力干扰而流向高处。由此可知,孟子从人性本然的角度来论证性善,而性之实际情形因受外在影响会有善与不善的不同表现。进一步讲,告子等所说的人性指受到现实之势干扰的人性,即人性之实然,而孟子所论则是未受外势影响的人性,即人性之本然。根据“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的逻辑,“乃若其情”探讨的中心仍然是性,此处的情即人性本然为善的实情。。此外,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多次提到情,“道生于情,情生于性”④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⑤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第29-30页。。虽然《性自命出》中的情在不同语境内涵不同,但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大都与人性的诠释相关。从情范畴的推进看,孔孟及《性自命出》不曾对情持批判态度。到了荀子,情增加了情感、情绪之义,“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⑥张觉:《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29页。,情之为恶的倾向开始凸显,“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⑦张觉:《荀子译注》,第294页。。由此观之,先秦儒家思想中有关情的论述通常伴随着对人性的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世有关情的讨论逐渐成为探究人性及性情关系的附庸,如董仲舒“性阳情阴”、刘昼“情出于性”、王安石“情者,性之用”之论,情作为独立范畴的意义不够凸显。相较之下,王夫之构建了独立、完整的情之体系,情不仅成为具有实体性的独立范畴,而且与性分际甚严。
(一)情的独立性:“:“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动则化而为情”
性情关系作为解读情的传统径路,虽然有助于理解情的意涵,但也造成了情之独立性的缺失,情作为独立哲学范畴的全貌难以窥见。王夫之对情范畴诠解的贡献在于从形而上的角度对情做出了界定,情的本质、生发机制、内容表现与特点无不涉及。
首先,情的本质是阴阳变合之几。王夫之表示,“情者,阴阳之几”⑧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89页。。《易传》有“几者动之微”⑨王弼,韩康伯,孔颖达等:《周易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的说法,王夫之在此基础上提出“几者变之微也”⑩王夫之:《周易内传·船山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55页。,“几”指事物发展的微小变化。作为王夫之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几”时见于其阐释情的本质,“情者……吾之动几与天地之动几相合而成者也”⑪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7页。,“几”的内涵还包括事物间彼此作用时互动的情境。进一步讲,情的本质就是阴阳二气氤氲互动的产物。之所以称“情元是变合之几”⑫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6页。,原因在于“吾之动几与天地之动几”互动往来存在相应或相异两种可能,相应为“合”,相异为“变”。此外,由于互动的产物不是固有的存在,故而王夫之以“变合”称之。
其次,情产生于人心与外物相取相合。王夫之分析情的本质时就注意到了情的生成,“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⑬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三册)》,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23页。。情产生于人心与天地之产互动相应之几,相对于外物,心处于内,情的产生必有外物与之相应,即“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倘若仅有外物,则有情的生成与不生成两种可能,即外有其物而内既可能有情亦可能没有情。换言之,情物不离,情是内外交成、互动相取⑭“相取”的意义可借鉴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二者(情、景)交互为用,水乳相投,就叫做‘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相取”即两者交互为用、水乳相投,意在强调彼此间相互因依的密切关系。的结果。王夫之又指出,“盖吾心之动几,与物相取,物欲之足相引者,与吾之动几交,而情以生。然则情者,不纯在外,不纯在内,或往或来,一来一往,吾之动几与天地之动几相合而成者也”①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7页。。吾心属内,但情的生发却“不纯在内”。虽有外物相引,情的产生也并非“纯在外”,而是成于内外往来相取。这样,较前人“情生于性”②如刘昼“情出于性”、李翱“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等。之论,王夫之从情本身出发来还原情的生成机制,确保了情范畴的独立性。
再次,情表现为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王夫之指出,“夫情,则喜、怒、哀、乐、爱、恶、欲是已”③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5页。。情具体表现为人的喜怒等七情并非王夫之首创,早在先秦时期,荀子赋予情以情感义,韩愈、李翱更是明确指出情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④韩愈《原性》“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李翱《复性书》“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王夫之与韩愈等人的区别并不在于将七情之“惧”替换为“乐”,而是基于本质分析情自生成后的具体表现,同时明确七情形成的渐进性,“情元是变合之几……情之始有者,则甘食悦色;到后来蕃变流转,则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种种者”⑤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6页。。情作为阴阳变合之几,生成后最初表现为简单、朴素的情感,随着变化流转则逐渐表现为人的七情。无论是诠释情的生成机制还是内容表现,王夫之一直秉持着从情之本质出发来构建情范畴的原则,从而确保了情作为哲学范畴的独立性。
最后,情具有已发的特点。王夫之认为情既生成则表现为喜怒等七情,而人之所以能感知七情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情具有已发性,“非犹夫喜、怒、哀、乐之情,当未发时,虽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乐,而实无喜怒哀乐也。发而始有、未发则无谓之情”⑥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4页。,这意味着喜怒哀乐之情未有发出、未有表现时并不是情。换言之,情之已发才成为情,“变合之几,成喜怒哀乐之发而为情”⑦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9页。。同时,情的生成机制也决定了其已发的特点,情生于内外交成相取,情的生发不全然在内,表明情必然于外有所发见,即情具有已发性。人们对显而易见之象容易察觉,对性体实理可能全然不晓,“普天下人只识得个情,不识得性”⑧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6页。。因此,王夫之认为性精微藏秘而不可闻,情则粗表易显可验,即“性不可闻,而情可验也”⑨王夫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62页。。
王夫之多番辗转力求明确情的精义,情不再是人性论或性情关系的附庸。所谓“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动则化而为情”⑩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6页。,情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哲学范畴,自有其生发机制:情的本质是阴阳变合之几,产生于人心与外物相取相合,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欲七种,具有已发的特点。
(二)性情之分:“情自情,性自性”
强调性情有别并非王夫之首创,但前人之论大都从性情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体用关系申发性情之分,如荀子“情也,性之质也”⑪张觉:《荀子译注》,第331页。,二程“只性为本,情是性之动处”⑫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情作为性之用,通常处于性情关系中的低位。与前人不同的是,王夫之从情的独立性来凸显性情之分。同时,王夫之的性情分际非常严苛,近乎保守,主要表现在对朱熹“性情已发与未发之分”“四端皆情”等观念的批驳。
朱熹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属于情,“四端,情也,性则理也。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⑬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10页。,即“四端皆情”。诚如学者陈来认为,“朱熹所谓情发于性的学说,情是包括四端、七情都在其内的”⑭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将四端归入情范畴原因在于朱熹认为性情一致,差异主要在于未发与已发的不同,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⑮朱熹:《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0页。。与朱熹不同,王夫之认为性不存在已发和未发之分,而情只有已发性,“未见孺子入井时,爱虽无寄,而爱之理充满不忘,那才是性用事的体撰。他寂然不动处,这怵惕恻隐、爱亲敬长之心,油然炯然,与见孺子入井时不异”①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4页。。爱是情,爱之理根源于性,性不因物之来感与否,实理一直充满其中。寂然不动的内心状态是“性理用事”的状态,未见与见孺子入井的内心状态并无不同,说明性不存在已发与未发之分。由于情具有已发性,故而不能如性一样有“充满不忘”之理,性情之分甚严。
性情之分的坚定立场让王夫之对混淆性情的“四端皆情”之说颇多指斥,“以怵惕恻隐之心为情者,自《集注》未审之说”②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5页。。他认为“四端皆情”与孟子本义相去甚远,“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也’云云,明是说性,不是说情。仁义礼智,性之四德也。虽其发也近于情以见端,然性是彻始彻终与生俱有者,不成到情上便没有性!性感于物而动,则缘于情而为四端;虽缘于情,其实止是性”③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4-1065页。。四端与四德皆属于孟子论人性的范畴,四端作为性之四德的见端,虽然其表现与情相近,但其从来都是与生俱有的。性彻始彻终与生俱有,但“不成到情上便没有性”,性有感于外物触动而有所发,即性之见端“缘于情”,故而其本质仍然是性。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性隐情显,性必须凭借情而昭著,“性自行于情中”④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6页。,性寄托并运行于情中,即仁义礼智四德的显发需要依凭情。四德凭借情而发见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要此四者之心,是性上发生有力底。乃以与情相近,故介乎情而发。恻隐近哀,辞让近喜,羞恶、是非近怒”⑤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46页。。四端显发虽缘于情,但仍然是性。王夫之进而以布衣卿相、花果为喻,“如人自布衣而卿相,以位殊而作用殊,而不可谓一为卿相,则已非布衣之故吾也。又如生理之于花果,为花亦此,为果亦此,花成为果而生理均也;非性如花而情如果,至已为果,则但为果而更非花也……故以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性也,而非情也”⑥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4-1065页。。人从布衣平民成为卿相官宦,二者固然地位悬殊,于社会之用亦存在不同,但不能因成为卿相就否认其最初为布衣,一如四德“缘于情而为四端”仍旧是性,花果生理亦如。因此,王夫之认为“朱子未析得‘情’字分明”⑦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0页。。
王夫之认为“四端皆情”不仅导致朱熹未能析得情之分明、混淆四端与七情,而且错误地将恻隐之心视为爱。朱熹指出,“四端皆是自人心发出。恻隐本是说爱,爱则是说仁。如见孺子将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爱这孺子。恻隐元在这心里面,被外面事触起”⑧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四册)》,第1564-1565页。。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而四端则是仁义礼智之性的展示,即四端是人之性的客观化表现。具体来说,恻隐之心是一种爱的情感,而爱本质上指向仁,如同见到孺子坠井而出手相救,这是心中怜爱孺子的表现。简言之,孺子坠井等外物外事的触动促使恻隐之情有所发见。王夫之认为,将恻隐之心视为爱将沦为告子之流,“乍见孺子入井之心,属之哀乎,亦仅属之爱乎?非有爱故……学者切忌将恻隐之心属之于爱,则与告子将爱弟之心与食色同为性一例,在儿女之情上言仁……恻隐是仁,爱只是爱,情自情,性自性也”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5-1066页。。王夫之反复强调性不存在已发与未发之分,“未发时之怵惕恻隐与爱亲敬长之心,固性也;乍见孺子时怵惕恻隐之动于心也,亦莫非性也”⑩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3页。,未发时的怵惕恻隐、爱亲敬长之心,与见孺子坠井时已发的怵惕恻隐之心都是性。见孺子入井之心并不是爱的缘故,而是人性使然,将恻隐之心当作爱无异于混淆性情,甚至错误地从儿女之爱(情)寻得人性之仁。因此,王夫之坚持爱属于情,“‘爱未是仁,爱之理方是仁’,双峰之说此,韪矣……夫爱,情也;爱之理,乃性也”⑪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59页。。
王夫之严守性情之分,认为诸如朱熹“四端皆情”的观点不仅没有明确何为情,甚至也无法正确理解何为性,“若昏然不察,直将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与喜怒哀乐作一个看,此处不分明,更有甚性来”⑫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5页。。可以说,王夫之不仅要析得情分明,也要析得性分明。那么,王夫之强调情的独立性、对性与情严加区分的目的何在?实际上,王夫之旨在通过情的独立性与严格的性情之分来阐述人性之善而人有为不善的原因,继而提出罪情论。
二、罪情:“性无不善而才非有罪,决以罪归情”
王夫之在确保情的独立性、严守性情分际的基础上将不善归罪于情,然而,有关情恶或情之不善的价值判断早已存在。从荀子“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①张觉:《荀子译注》,第294页。起,到韩愈论情亦分“三品”②韩愈在“性三品”的基础上把情亦分为上、中、下三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品。,乃至李翱“情本邪也,妄也”③李翱:《李文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情为不善的倾向逐渐凸显。与前人不同的是,王夫之罪情论具有辩证性与系统性,他不仅注意到情既可以为善也可为不善,而且探讨了情如何为不善的生发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王夫之希冀通过审视情来探寻不善的来源。他驳程朱视物欲、才作为不善之来源的观点,在剖析性情才之为善与否的基础上,明确了情是不善的唯一来源。
(一)情可以为善:“:“情之为善,专就尽性者言之”
对于情为善与否的价值判断,王夫之通过性情对比得出,“唯一善者,性也;可以为善者,情也”④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三册)》,第332页。。肯认性善直承孟子,但王夫之并没有承认情善的确定性。王夫之诠释《孟子》时指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可以为善,则亦可以为不善也。唯其不能即善,故曰‘可以为善’。如固然其善,则不待‘为’而抑不仅‘可’矣。若恻隐等心,则即此一念便是善,不但‘可以为善’也”⑤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4页。。王夫之认为情“可以为善”包含为善与为不善两个方面,原因在于情“不能即善”。“即善”的是恻隐等四端,“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也’云云,明是说性,不是说情”⑥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4页。,恻隐等四端是性,而性作为“唯一善者”,故四端即善。可知“即”是确定的,情“不能即善”说明情善并不确定。进一步讲,“唯其不能即善,故曰‘可以为善’”,“可以为”包含成就与不成就两种可能,因而“可以为善”说明情有为善与为不善两种可能。王夫之继而指出,“如固然其善,则不待‘为’而亦不仅‘可’矣”,如果情同性一样固然是善的,则情无需待“为”,也不会被称为“可”善,表明情善与不善是“为”的结果,即“情待为”善或不善。
情既可以为善亦可以为不善的观点强化了性情分际。“或人误以情为性,故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今以怵惕恻隐为情,则又误以性为情”⑦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5页。。在王夫之看来,有的人把情当作性,继而认为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而把四端看作情,则犯了以性为情的错误。再者如朱熹,“情者,性之动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47页。。王夫之表示,按照朱熹由情善推知性善的逻辑,情之为不善则将推出性之不善的结论,“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则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将以知性之不善与”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5页。。王夫之继而指出,由于朱熹这种逻辑存在偏颇,所以孟子论性善从四端说起,而不从具有多种可能的中节者(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的情)验证性善,“此孟子所以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见端于心者言性,而不于中节者征性也。有中节者,则有不中节者”⑩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5页。。
王夫之强调性情之分的同时注意到了性情和合,这也是情之为善的前提。虽然性与情是两种不同的范畴,“性,道心也;情,人心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道心也;喜、怒、哀、乐,人心也”⑪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473页。,但二者关系密切,“斯二者,互藏其宅而交发其用。于恻隐而见有其喜,于恻隐而见有其怒,于恻隐而见有其哀,于恻隐而见有其乐。羞恶、恭敬、是非之交有四情也。于喜而有气恻隐,于喜而有其羞恶,于喜而有其恭敬,于喜而有其是非,怒、哀、乐之交有四端也。故曰互藏其宅”⑫王夫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二册)》,第262页。。性情既分际甚严又彼此相需,于四端而有喜怒哀乐,于喜怒哀乐而见四端,性情相需而交发其用,“互藏其宅”①“互藏其宅”指在两方事物中,一方所藏是另一方的宅所,强调彼此间的关系密切。这一思想较早见于《周易参同契》:“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日魂,阴神月魄。魂之与魄,互为宅室”。“互为宅室”后为张载传用,其多以“互藏其宅”称之。《张子正蒙注》言:“互藏其宅者,阳入阴中,阴丽阳中,坎、离其象也。太和之气,阴阳浑合,互相容保其精,得太和之纯粹”。坎卦(☵)所藏为离卦(☲)的宅所,而离卦所藏是坎卦的宅所,故称“互藏其宅”。后王夫之多次引用,最为著名的是用以阐述诗歌情景交融理论,“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互藏其宅”。反映了性情和合的状态。鉴于性情和合,那么情之为善就在于性能够规范与约束情,“性固行乎情之中也。情以性为干,则亦无不善”②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5页。。性行于情中,性因之能导情为善,即情以性为导向,故而促使情之为善。王夫之论诗有“诗道性情”的说法,强调性对情的规范与引导,“尽其性,行乎情而贞,以性正情也”③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三册)》,第429页。,诗歌应当抒发贞正之情,唯有性的约束、引导,情方称得上是性之情,而性之情就是为善之情。这样,王夫之在主张性情分际的同时实现了性情和合,并由此明确了情之为善是“专就尽性者言之”④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0页。。
(二)情可以为不善:“能使为不善者,罪不在情而何在”
王夫之“情以性为干则无不善”似又回到了朱熹“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的逻辑,实际不然。朱熹认为“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23页。,情作为性见于外之绪故而为善。可知朱熹通过强调情的中节之用来肯定情,侧重体对用的中节,体现了由体言用的思维。
相较之下,王夫之认为情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发而始有、未发则无者谓之情,乃心之动几与物相往来者,虽统于心而与性无与。即其统于心者,亦承性之流而相通相成,然终如笋之于竹,父之于子,判然为两个事物矣”⑥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4页。,情具有已发性,成于心物往来相取,虽然性情统于心,但“性自性,情自情”,好比笋与竹、父与子各自有不同的属性。换言之,情固然受性的影响,但情自产生后能“自为藏”,“情受于性,性其藏也,乃迨其为情,而情亦自为藏矣。藏者必性生而情乃生欲,故情上受性,下授欲”⑦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三册)》,第327页。。“情受于性”并非情生于性,而是情的发用受性的影响,即“受有所依”;而当情“授有所放”,则能生欲。因此,“情亦自为藏”的意义在于“情受性而既成之后,即亦自为一系统,自有其生发之机能,而可顺其机能贯之性,以离性而盲动”⑧曾昭旭:《王夫之哲学》,台北:远景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自为其藏”表明情是一个具备生发机能的系统,既能“顺其机能贯之性”而为善,又能授欲以行,离性盲动而为不善。
王夫之又以风喻情说明情为不善的可能,“情如风然……恻隐等心行于情中者,如和气在风中,可云和风,而不可据此为风之质但可为和,而不可以为极寒、暄热也……喜怒哀乐之发,岂有节而无无节者哉”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0页。。四端于情显发犹如和气充满和风,但不能据此认为风只能是和风,而不能成为寒风、暖风。又如喜怒哀乐之发既可能有节也可能无节,无节之情即“下授欲”之情,授欲以行之情因缺乏中节而为不善,“离性而自为情,则可以为不善”⑩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5页。。
然而,王夫之并未止步于承认情可以为不善,而是经由情来探寻不善的来源。从性情关系讲,情之为不善印证了情是不善的来源,“大抵不善之所自来,于情始有而性则无”⑪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5页。。同时,王夫之认为其对不善之来源的理解是对孟子的变通,“孟子言‘情则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也’,专就尽性者言之。愚所云为不善者情之罪,专就不善者言之也。孟子道其常,愚尽其变也”⑫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0页。。王夫之将不善之来源锁定于情,情应当承担不善的罪责,故而提出罪情论,“才不任罪,性尤不任罪,物欲亦不任罪。其能使为不善者,罪不在情而何在”⑬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6页。。王夫之归罪于情的同时,否定了才、物欲作为不善之来源的其他观点。
视物欲为不善之来源的代表是朱熹,“人之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47页。。对此,王夫之表示,“《集注》云‘乃物欲陷溺而然’,而物之可欲者,亦天地之产也。不责之当人,而以咎天地自然之产,是犹含盗贼而以罪主人之多藏矣。毛嫱、西施,鱼见之而深藏,鸟见之而高飞,如何陷溺鱼鸟不得?牛甘细草,豕嗜糟糠,如何陷溺人不得”①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6页。,“物之可欲者”是天地的产物,而“天地无不善之物”②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3页。。将不善归咎于物欲是没有归责恰当之人的表现,无异于将盗窃罪归咎于被盗人家财物众多。他进而又举毛嫱、西施之美而不陷溺鱼鸟与牛甘草、豕嗜糟而不陷溺人的例子,反复论证物欲并非不善的真正来源。
除了物欲,才也进入讨论善恶的范畴。程颐表示,“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③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4页。。王夫之承认才有为不善的表现,“人之为恶,非才为之,而谁为之”④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0页。似与程颐观点相近,亦与其罪情论有所冲突。实际上,才虽然存在为不善的表现,但仅有表现不能成为其作为不善之来源的缘由,更不能认为才承担不善的罪责,“唯其为才为之,故须分别,说非其罪”⑤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0页。。才为不善却不承担罪责,原因在于为善与否的焦点在于情,才有为不善的表现源于不正之情。对于情才关系,王夫之归结为“情以御才,才以给情”⑥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980页。,情驾驭才,才受控于情,故不善的来源在于情。情支配才,才只是为善与否的载体。王夫之进而以人用兵器杀人为喻论之,“如刺人而杀之,固不可归罪于兵,然岂可以云兵但可以杀盗贼”⑦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1页。。造成死亡的直接原因在于杀人兵器,但兵器的主导是人,此之一如情是才为不善的主导。
王夫之继而从性情才三者关系说明情是不善的来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本在性,而其灼然终始不相假借者,则才也……若夫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虽细察之,人亦自殊于禽兽,此可以为善者。而亦岂人独有七情,而为禽兽之所必无,如四端哉!一失其节,则喜禽所同喜、怒兽所同怒者多矣。此可以为不善。乃虽其违禽兽不远,而性自有几希之别,才自有灵蠢之分,到底除却者情之妄动者,不同于禽兽。则性无不善而才非有罪者自见矣。故愚决以罪归情,异于程子之罪才也”⑧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2页。。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性,而区别的表现在于才(形色)。同时,由于人之情可以为善,故而人与禽兽之情差别较大。然而,情失其节制则导致人的行径近于禽兽,以至于为不善。虽然情失其节导致人“违禽兽不远”,但人之性与禽兽之性本就有差别,人之才与禽兽亦本有灵蠢之不同,唯有情作为“妄动者”存在使人“违禽兽不远”的可能。简言之,情是导致不善的唯一来源。至此,王夫之关于性情才之善与否得以明晰,“故唯一善者,性也;可以为善者,情也;不任为不善者,才也”⑨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三册)》,第332页。。
(三)情如何为不善:“铄情不善,率才以趋溺物之为”
基于对情的界定以及性情才为善与否的分析,可知王夫之肯认情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并将不善归咎于情,“情之不能不任罪者,可以为罪之谓也”⑩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2页。。需要注意的是,情之为善或否不仅是情最终呈现的结果,而且包含着善与不善的生成。换言之,情为善与否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为善与否的结果以善与不善的生成为前提。
王夫之以铄情归纳情之为善或否的生成过程:“唯其为然,则非吾之固有,而谓之‘铄’。金不自铄,火亦不自铄,金火相构而铄生焉。铄之善,则善矣,助性以成及物之几,而可以为善者其功矣。铄之不善,则不善矣,率才以趋溺物之为,而可以为不善者其罪矣”⑪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7页。。“铄”出自孟子,“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⑫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仁义礼智之性皆为人所固有,并非由外在因素渗入而成,可知“铄”意味着外在的影响。王夫之发展了“铄”指受外在影响的含义,“铄”引申为彼此间的互动,金、火皆不能独自成“铄”,只有金与火相搆相擩才称得上“铄”。以“铄”称情之为善或不善,原因在于情的产生本就是人心与外物相互作用的结果,故而理解其成善与否也应当从内外互动处着手。王夫之表示,铄情的结果有二:一方面,铄情成善,情善则能助性以成、体物之几。情助性以成是“情以显性,故人心原以资道心之用”①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473页。“循情而可以定性”②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三册)》,第353页。的相同表达。换言之,助性以成之情应理解为“善情”或者“性情”,而资道心之用就是情之为善的表现。另一方面,铄情成不善,不善之情将导致才的趋敝乃至陷于物欲之流,故而为不善。
“率才以趋溺物之为”表明,在性情才三者中,情是才与性的中间环节。王夫之指出,“才之所可以尽者,尽之于性也……才本形而下之器,蠢不敌灵,静不胜动,且听命于情以作为辍,为功为取,而大爽乎其受型于性之良能”③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7页。。性需要借才以成用,才虽为形下之器却能为功为取,“若才之本体,则为性之所显,以效成能于性中之经纬,而何罪哉”④王夫之:《四书训义下·船山全书(第八册)》,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699页。,才本是可以“协助仁义之性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的”⑤孙钦香:《王夫之论“情”》,《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33-39页。,从而成为为善的助推。表面上看,才效于性而应成为善才,然而,才处于居静待用的状态,其听命于情或作或辍。王夫之继续分析,“才之所可尽者,尽之于性也。能尽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尽其才者,受命于情而之于荡也。惟情可以尽才,故耳之所听,目之所视,口之所言,体之所动,情苟正而皆可使复于礼。亦惟情能屈才而不使尽,则耳目之官本无不听、不明、耽淫声、嗜美色之咎,而情移于彼,则才以舍所应效而奔命焉”⑥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7页。,“才之所可尽”即发挥耳目口体之职来实现尽之于性的功用,才受不正之情的影响则舍其“应效”于性之用。具体而言,由于才受控于情,故而情之正而能尽其才,耳目口体皆能实现尽性的功用;相反,情之不正则屈才而使之不能尽性。简言之,铄情不善则支配才无以尽其性而为不善。
三、治情:“知几审位”
王夫之认为铄情产生善与不善两种结果,情之为善则是善情,情之为不善则是不善之情。然而,无论是善情还是不善之情,二者都属于情,只不过不善之情作为“情之下游”而存在,“若夫情之下游,于非共所攸当者而亦发焉,则固危殆不安,大段不得自在……唯无根故,则始终异致,而情亦非其情也”⑦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473页。。情既可发于其所攸当处,也可以发于非攸当处。由于为善之情能“助性以成”,故而发于攸当的标准是尽性。相较之下,发于非攸当处的情“危殆不安,大段不得自在”,沦为境界卑下的“下游”,王夫之称其“无根”“亦非其情”。“亦非其情”不是说其不是情,而是强调其不是善情或性之情。由于此情非性之情,因而无法尽性以为善。虽然情是不善的来源,但王夫之并没有像李翱一样主张去情,而是肯认情存在的必要性,并藉由情的对治来探寻向善的径路。
(一)不善与恶的关系:“只不善便是恶”
在王夫之看来,情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进而将不善之来源归罪于情。人们一般将善的对立面理解为恶,王夫之却将不善作为善的对立面。他认为不善即是恶,“天下别无恶,只不善便是恶”⑧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6页。。由此观之,情可以为不善似乎表明情可以为恶。情可以为恶的说法能否成立,这里还需要梳理王夫之对不善与恶之关系的理解。
王夫之认为恶生于不得其宜,“六十四卦之变动,皆人生所必有之事,抑人心所必有之几;特用之不得其宜,则为恶”⑨王夫之:《周易内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78页。。“几”就是事物发展的微小变化,王夫之以卦象为喻阐述“几”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并藉由此说明人必然经历种种变化,人心相应地也有起伏。王夫之又指出,“阴阳之位有定,变合之几无定”⑩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2页。,虽然阴阳自有其定位,但变合之几具有不确定性。又“特用之不得其宜,则为恶”,说明当“几”的发生不合适、不恰当时则有恶的产生。回溯王夫之对情为不善之来源的理解,人心与外物“于非共所攸当”而有不正之情,此不正之情即“不得其宜”之情。王夫之认为此“不得其宜”之情“可以为不善”,而根据“不得其宜则为恶”推之,王夫之论情“可以为不善”意在说明情“可以为恶”。
王夫之不仅通过“不得其宜则为恶”来辗转说明不善就是恶,而且直言“只不善便是恶”。“天下别无恶,只不善便是恶……不善已著而人见其可恶,(,(去声。)便谓之恶……言外之物、内之性,无一不善,但交互处错乱杂揉,将善底物事做得不好尔”①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6-967页。。天下本没有恶,外在之物与内在之性无一不是善的。然而,物我交互往来间错乱杂糅就有产生恶的可能。换言之,不善者并不意味着本然不善,其之所以为不善在于与物相引而不得其宜、错乱杂糅,“凡不善者,皆非固不善也。其为不善者,则只是物交相引,不相值而不审于出耳”②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3页。。恶的生成被限定在物我往来交互的作用处,将本应为善的物事做得不恰当则生恶。“天下别无恶,只不善便是恶”道明了恶的本质,恶意味着善的缺失,不善就是恶,而情可以为不善则说明情可以为恶。这样,王夫之不仅明确了情是恶的来源,而且确保了人性之善:人继善成性,性乃“唯一为善者”;虽然人之性善确定无疑,但人有为不善的可能;物我往来不当位之几而有不得其宜之情,铄情而成不善。
恶就是善之缺失的观点不仅化解了人性之善与情可以为恶的冲突,而且坚定了王夫之“决以罪归情”的立场。那么,王夫之提出归罪于情,视情为不善的来源,这是否意味着他主张去情、灭情?事实上,王夫之不仅没有主张消灭毁弃情,而是肯认情存在的必然性及其价值,进而藉由情来探索去恶向善的径路。
(二)罪情而不去情:“人苟无情,则不能为恶,亦且不能为善”
王夫之思想的出发点和终极理想是“立人极”,“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圣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极也”③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850页。。“人极”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立人极”即以人为出发点来建构世界,意在强调天道等“只能由人按实践需要去加以把握”④萧箑父:《船山哲学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从这一角度讲,情之为善与否本质上是人为善与否。人继善成性,行为应当向善。然而,物我往来相取之几仍可能铄情不善,故而人有恶行。因此,王夫之表示,“慕天地之大而以变合之无害也,视情皆善,则人极不立矣”⑤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2页。,“视情皆善”有违“人极”,更无从“立人极”,明确情不能皆善是“立人极”的必然。虽然王夫之将不善归罪于情,但他并不主张去情、灭情。在他看来,无情之人虽不会为恶,但其也丧失了为善的可能,“人苟无情,则不能为恶,亦且不能为善”⑥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9-1070页。,因而不去情、灭情也是发挥情之为善的前提。
然而,在王夫之以前,去情、灭情的主张并不少见,李翱“去情复性”是典型代表。李翱表示,“水之性清澈,其浑之者沙泥也。方其浑也,性岂遂无有耶?久而不动,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鉴于天地,非自外来也。故其浑也,性本勿失,及其复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犹水之性也”⑦李翱:《李文公集》,第10页。。李翱以水喻人性、泥沙喻情,指出人性之善如同水之清澈。水本具有清明之性,但泥沙的存在及搅浑让水失去了清明。然而,只要长时间不去搅动,泥沙便会自沉,水会再度清澈明净。同理,情的昏乱导致人性之善被蒙蔽。鉴于此,李翱主张去情以复性,“问曰:尧舜岂不有情耶……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⑧李翱:《李文公集》,第6页。。圣人之情不同于普通人之情,圣人有情却能彰显善性,原因在于圣人之情不发挥任何作用,就像没有情的存在一样,因而不会受到邪情惑乱的影响。普通人却因受情惑乱以至无法复见善性,“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⑨李翱:《李文公集》,第6页。,故而应去情以达到“未尝有情”的状态。
表面上看,李翱论情昏乱惑人的观点与王夫之罪情论相近。然而,王夫之论情明确表示,“若论情之本体,则如杞柳,如湍水,居于为功为罪之间,而无固善固恶,以待人之修为而决导之,而其本则在于尽性”⑩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0页。,情如同变化浮动的流水、杞柳,其本身无善无恶。情之所以为恶而成为不善的来源,深层原因在于人的修为,人的修为最终呈现为情为善或不善。因此,二人对情之为不善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李翱更多关注情对于性善的昏惑蒙蔽,而王夫之既注意到情为恶也不忽视情为善的功用,即情之于尽性尽才而为善的必要性。由于王夫之充分注意到了情之为善的功用,故而反对去情、灭情,肯认情之存在的必然性。同时,王夫之认为通过去情来防止恶的产生将流于佛道二家“无情”的异端之说,“情既可以为不善,何不去情以塞其不善之原,而异端之说繇此生矣”①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9页。。这样,王夫之在肯认情之存在的必然性、不去情灭情的基础上,希冀通过对治情来实现向善。
(三)去恶向善的工夫:“省察以治情”
情是吾心之几与物之几内外互动相取的结果,王夫之希望对治情以向善,表明他试图通过物我之几的互动相取探索向善的实践工夫。王夫之指出,“天地无不善之物,而物有不善之几。非相值之位则不善。物亦非必有不善之几,吾之动几有不善于物之几。吾之动几亦非有不善之几,物之来几与吾之往几不相应以其正,而不善之几以成”②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3页。。物本身不是不善的,也并非一定存在不善之几。但之所以说物可能存在不善之几,原因就在于“化之相与往来者,不能恒当其时与地”③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2页。,“当其时与地”指恰当的时间与地点,即物之几与人(吾)之几没有在恰当的时间与地点互动相取。在这里,王夫之对物我互动提出了时空要求,只有双方于恰当合宜的时空互动往来,才能达到彼此和合、互相匹配的定位,即“相值之位”,进而成善。相反,彼此互动未能发生于恰当的时空,则产生不善。同理,人(吾)并非一定存在不善之几,然而,当物之几与人(吾)之几的往来互动发生于时空不相宜之位,双方互动则不匹配相应、不能成其正,故而有不善之几。
鉴于善恶与否源于物我互动之几,故而王夫之认为唯有“知几”才能明确善恶,进而以去恶向善,“故唯圣人为能知几。知几则审位,审位则内有以尽吾形、吾色之才,而外有以正物形、物色之命,因天地自然之化,无不可以得吾心顺受之正”④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3页。。“知几”源于《易》,指认知事物变化的隐微征兆,《,《系辞下传》“知几其神乎”可知“知几”之大用。王夫之援引“知几”以向善:一方面,“知几”意味着正确认识物我往来互动相取之几,通晓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据,确保吾之几与物之几能于“当其时与地”相应匹配,如此则成其正、成其善;另一方面,“知几”是“审位”的前提,先知而后审。“位”即物我互动“当其时与地”的定位,有“得位”与“不得位”之分,“得位”则“物不害习而习不害性”⑤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3页。,“不得位”则“物以移习于恶而习以成性于不善”⑥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63页。。因此,只有在“知几”的基础上明辨得位与否,方能确定何为物我各当其位的正情,进而尽形色之才、正形色之命。
圣人能真正做到“知几审位”,而普通人因不能确认何为“得位”“得宜”之情而有不善之举,简言之,人无知而有不善。尽管普通人不能全然如圣人,但王夫之认为,“若论情之本体……以待人之修为而决导之”⑦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70页。,由于人拥有能动性,故而人应成为向善的践行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向善。换言之,普通人应向圣人学习,提高认知物我的能力。具体而言,人虽不能完全把控何物、何时、何地与人心互动相感,但人可以于情上用功,审视、省察其情,“功罪一归之情,则见性后亦需在情上用功……既存养以尽性,亦必省察以治情,使之为功而免于罪……省察者,省察其情也,岂省察性而省察才也哉”⑧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9页。。省察就是明审、辨析,省察其情就是人“知几审位”的实践工夫,而省察的最终目的在于治情以向善。鉴于情既可以为善亦可以为不善,故而治情亦需从以上两方面辨证着手。
治情以向善首先在于发挥情可以善的功用,王夫之指出:“不善虽情之罪,而为善则非情不为功。盖道心惟微,须藉此以流行充畅也。如行仁时,必以喜心助之。情虽不生于性,而亦两间自有之几,发于不容于已者。唯其然,则亦但将可以为善奖之,而不须以可为不善责之”①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9页。。由前之所述,情具有生发机能,故道心(性)藉由情的生发机能以流行充畅,诸如仁之显发需凭借喜心(情)助成。情虽不生于性,但性情相需,性之显发离不开情,此即应“奖情”而不能“责情”的原因所在。不仅如此,情的生发机能速度迅捷、力量强大,能充分发挥向善的功用,“盖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其体微而其力亦微,故必乘之于喜怒哀乐以导其所发,然后能鼓舞其才以成大用。喜怒哀乐之情虽无自质,而其几甚速亦甚盛”②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7页。。性隐而情显,性之四端“体微而其力亦微”,故而四端发用需乘之于喜怒哀乐之情,进而鼓舞才以成用。简言之,喜怒哀乐之情虽无固善固恶之质,但其生发易动的向善机能迅捷而力强。
在发挥情为善之功用的基础上,王夫之继而强调“治不道之情”③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三册)》,第416页。。不道之情即为不善之情,其作为负面、消极之情而存在。王夫之没有主张去不道之情,他认为首先要做的是不奖为不善之情,“审乎情,而知贞与淫之相背,如冰与蝇之不同席也,辨之早矣。不奖其淫,贞者乃显”④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328-329页。。省察其情可明辨为善之贞情与为不善之淫情,而不鼓励、不助推淫情,贞情则可以发挥“存养尽性”之用。
除了不奖不道之情,王夫之还主张通过舒气调剂不道之情,逐渐消散其负面能量,助长情之为善的动力,“治不道之情,莫必其疾迁于道;能舒焉,其几矣……情附气,气成动,动而后善恶驰焉……待其动而不可挽。动不可挽,调之于早者,其惟气乎”⑤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三册)》,第415页。。消极、为不善之情通常无法迅速回归为善的状态,王夫之主张通过舒缓引导的方式对不道之情进行规治。情之所发附于气,气之动则情之善恶运衍、传播。由于气之已动则不可挽,故而应在情附气成动之前调气。王夫之又指出,“气之动也……其能舒也,则其喜也平,其怒也理,虽或不惠,末之很矣……是故欲治不道之情者,莫若以舒也。舒者,所以沮其血之躁化,而俾气畅其清微”⑥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三册)》,第416页。。舒气意味着舒导所发之气,让气保持在清微的状态。舒气不仅能够阻遏血的躁动,还能使欢喜之情趋向平和有度、愤怒之情逐渐有理有节。换言之,不道之情在从容不迫的舒气调节下,逐渐消散了负面能量而得以匡正,进而重新获得清畅的生发机能。这样,王夫之在没有去情的前提下,既发挥了情之为善的生发机能,又践行了治不道之情的工夫,实现了由不善之来源的对治以去恶向善的理想。
四、余论
回到文章开头关于贬情的存疑,虽然王夫之视情为不善的来源,不宠、不奖为恶之情以下放情的高度,但他没有贬损情之为善的功用,更没有主张去情,而是希冀对治情以向善。简言之,王夫之罪情而不贬情。诚如其所言,罪情论“尽破先儒之说……不宠情以配性,而使性失其节。窃自意可不倍于圣贤,虽或加以好异之罪,不敢辞也”⑦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68页。。肯定情之为善的价值,同时将不善归罪于情是对先儒(李翱、程颐、朱熹等)之说的反拨,不仅避免了过度抬高情之地位的倾向,而且化解了人性固善与情之为恶的冲突。
王夫之论情,特别是其罪情论与省察治情之道在儒家情论史上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王夫之论情彰显了情范畴的独立意义。一方面,王夫之论情严守性情之分,否认“四端皆情”“性情一物”,而是坚持情就是情,性就是性,析得情之分明的谨慎态度凸显了情范畴的独立意义;另一方面,王夫之充分挖掘了情的生发机能。传统性情论重在以性节情,但王夫之论情不仅注意到情的生发机能,而且试图通过情以显性、人心以资道心之用来实现向善的积极意义。其次,王夫之论情丰富了传统性情论,客观地定位了情在性情关系中的位置。情范畴是讨论性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诸多哲学家眼中,情通常处于性情关系中较低的位置,如董仲舒“性阳情阴”、李翱“去情复性”。虽然王夫之承认性是“唯一善者”,但其罪情论并没有因肯认性善、情是不善的来源而贬抑情,而是客观、全面地阐述了情尽性而为善的意义。再次,罪情论及省察治情之道探索了去恶向善的新路径。在王夫之看来,实现去恶向善的关键在于情,只有对治情方能尽性尽才以向善。藉由情去恶向善首先在于省察其情,在明辨情之善恶的基础上,既发挥为善之情率才以尽性的生发机能,又能规治不道之情而不为恶,最终实现向善的理想。此外,罪情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晚明重情思潮所带来的情之泛滥的负面影响。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与发展,晚明重情蔚然成风,然而“王阳明的逻辑势必导致以情为性,性情不分”①蔡鍾翔:《明代哲学情性论的嬗变与主情论文学思潮》,《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3期,第82-89页。,特别是泰州学派等阳明后学以情为性的思想直接导致了情的泛滥。王夫之在全面审视情的基础上,将恶的来源归罪于情,辩证地降低了情的高度,修正了阳明后学私情泛滥的流弊。
——探《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