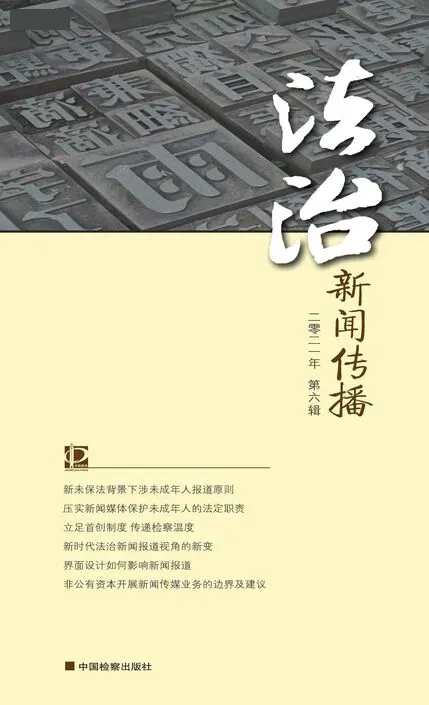刑法第308条划定法律红线
■印 波 唐淑臣
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是其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形式,各国都注意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赋予媒体重要使命,即发挥媒体的监督制约功能。但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新闻报道时,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媒体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国外的传媒业在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方面有比较严格的行为规范,我国新闻媒体同样受各种有关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法律法规约束,不可逾越涉未成年人报道的法律红线。
新闻报道的法律红线
大家应当注意到,“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是悬在法治调查媒体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刑法修正案(九)将“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作为妨害司法罪下的罪名,在刑法第308条之一中予以规定。其与前款罪名“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在行为对象、侵犯客体、主观心态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同时在犯罪主体、行为方式和危害结果等内容上又具有差别,二者属于法条竞合关系。
在犯罪主体方面,“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是身份犯,该罪名中规定了特殊主体,用以规范直接参与案件审判的相关人员,即只有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才可以构成本罪,其他主体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则不成立本罪。“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则没有主体限制,不论是掌握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的记者、编辑,还是了解案情的网友,或者是其他发布信息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①都可能成立本罪。在犯罪客体方面,两罪名作为妨害司法罪下的具体罪名,其保护的主要是司法秩序,立法者增设两罪的首要目的在于打击扰乱司法机关正常诉讼活动的行为,以维护司法审判秩序。但又因两罪名还涉及诉讼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两罪名侵犯的客体均为复杂客体,即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以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②
从犯罪行为来看,“披露、报道”不同于“泄露”。“披露、报道”倾向于面向多数人发布或透露,“披露”是指一般主体将处在保密状态下的信息公之于众,“报道”是指通过一定的媒介将信息公之于众,而“泄露”则是指向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的人传递了信息。这也直接导致两罪的犯罪结果有所不同: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要求达到“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危害结果,而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需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结果。“造成信息公开传播”,主要是指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以及互联网上公开传播本罪所规定的信息,本质上是信息为公众所知悉;而“其他严重后果”则包括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严重干扰司法审判活动,严重侵犯他人隐私、商业秘密等。
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的“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
涉未成年人案件报道中“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包括两种,一是未成年人作为公民与生俱来的隐私权利,二是未成年人作为特殊主体所享受的特殊隐私权利。
“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隶属于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指的是法律规定不应该公开审理的案件。我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3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有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姓名、影像、住所、就读学校以及其他可能识别出其身份的信息,但查找失踪、被拐卖未成年人等情形除外。刑事诉讼法第285条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57条也规定,开庭审理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对依法公开审理,但可能需要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不得组织人员旁听;有旁听人员的,应当告知其不得传播案件信息。这是未成年人作为特殊主体所享受的特殊隐私权利。
此外,法律还规定了未成年人作为公民与生俱来的隐私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规定,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案件和当事人申请的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民事诉讼法第134条在上述几类案件之外,增加了当事人申请的离婚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以及“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不公开审理。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法律另有规定的和当事人申请的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根据上述规定,涉未成年人案件中“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范围非常宽泛,包括并不仅限于未成年人的姓名、影像、住所、就读学校等,一切其他可能识别出其身份的信息都属于“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凡是披露、报道后造成严重后果的,都有可能触犯刑法。
涉未成年人案件报道中的注意事项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推进,媒体报道借助互联网更深层次地融入到社会发展的轨道中,部分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也在信息化浪潮中被披露报道,严重干扰了司法机关正常司法秩序并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案件作为社会热点类问题,其本身的报道更能吸引公众眼球,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猎奇”内容,但这类报道中的案件信息因涉及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更引发了新闻伦理问题,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合理报道限度引起关注。③
对于未成年人为被告人的案件,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已经对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新闻记者对此类案件进行报道时,对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的案件信息应该予以保护。对于未成年人为被告人的案件,不涉及被害人隐私信息的,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而披露的,属于违法阻却性事由,不构成犯罪(指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④未成年人为被告人的案件并非禁止报道,结合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封存的是曾有过犯罪记录的犯罪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并不是要对整个刑事案件进行封存,因此对于“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应当加以限缩——并非全部涉案信息都属于“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对于案件中与被告人身份信息联系不大,不能将案件事实与被告人个人信息进行对应的信息,媒体可以进行适当报道。所以说,对于未成年人为被告人的案件,并没有完全排除新闻媒体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进行报道的可能性,但要确保无法通过报道的信息反推出具体未成年人。
对于未成年人为被害人的案件,媒体抓住社会对保护未成年人话题关注的心理,对犯罪行为以及被害人的身份信息进行公开,存在过度报道的现象,引起社会关注,这显然涉嫌侵犯被害人的个人隐私,造成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虽然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未成年人为被害人情形下需要不公开审判,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报道除了需要遵守刑事诉讼法不公开审判的一般规定外,还需要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对未成年被害人案件进行报道,信息公开传播导致严重后果的,也存在触犯刑法的可能。尤其是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等案件,其作为涉个人隐私案件,法律规定不公开审判,其信息自然属于不应公开的信息范畴。因此,媒体在报道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时,应当尽量避免一切可能识别出特定未成年人身份的信息披露,尤其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案件,则更要进行脱密报道。比如2019年发生的凤凰少女性奴案,湖南凤凰县检察院通报一起该县50岁单身男子在自家房屋地下挖洞囚禁16岁在校女生为性奴的案件,女生被囚禁24天后被警方解救。检察院对于事件的通报内容进行了相应的细节隐藏,但是之后有多家新闻媒体通过联系当事人、就诊医院乃至公安部门,对了解到的具体细节内容进行报道,而这些报道相继曝光后,对回到原生活环境的当事人造成了伤害。这种报道明显超越了边界,涉嫌违法。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不论是未成年被害人还是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都应当得到必要权利保障。新闻媒体在信息披露与未成年人信息保护之间应当做好利益权衡,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进行价值取舍,坚持适度报道、适度公开、有底线地公开,守好涉未成年人案件报道的法律红线。
注释:
①雍自元:《“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评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②臧铁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249页。
③唐献玲、张成飞:《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失范与规范》,《新闻战线》2015年第8期。
④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439页。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