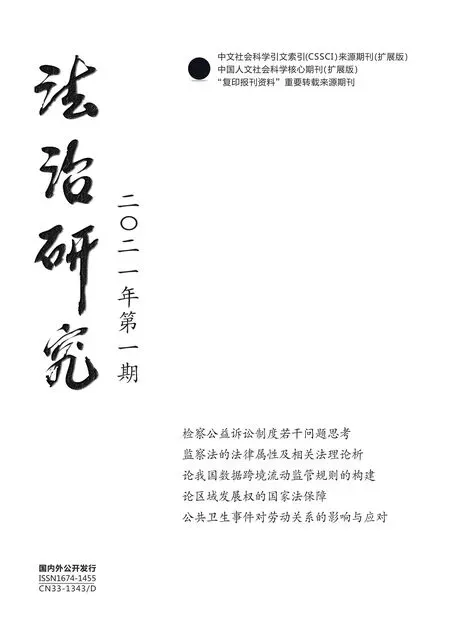《民法典》立法资料的法治意义与实践方式*
刘志阳
一、《民法典》适用中的二次造法问题
我国《民法典》生效后将面临如何解释和适用的问题。在众说纷纭的现状下,如何对《民法典》进行权威解释,以免司法恣意,并带来二次造法问题,这将是《民法典》生效后的重大挑战,特别是立法机关还将面对制定司法解释的挑战,对法典的解释能否保持立法原意将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比如,我国《民法典》第1221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如何确定存在争议。由于本条是继受《侵权责任法》第57条而来,在该条立法中,《侵权责任法(草案)》曾规定:“判断医务人员注意义务时,应当适当考虑地区、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但是后来考虑到诊疗行为的实际情况很复杂,这一规定又被删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认为,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规定了诊疗行为的具体要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一般都应当遵守,不应当因地区、资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诊疗行为属于基本性操作,不一定要考虑这些具体要求。有的诊疗行为也需要结合地区、资质等因素来判断是否履行了“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但是采用地方特殊标准说的观点认为,应依据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资质以及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对此,最高人员法院作出的《医疗损害责任解释》第16条规定:“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进行认定,可以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个体差异、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此解释中的内容确立了一些主观标准,即需要参照地域差异、医疗机构等级差异等因素。②参见杜万华等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解释规则精释与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但是这一观点是否为《民法典》立法原意值得怀疑,因为黄薇在其主编的民法典释义中认为,这一客观标准的认定需要依据医疗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来确定。但是对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存在适用全国统一标准还是适用地方特殊标准之争。对此,黄薇明显采用全国统一标准说:这些对于医疗水平要求的抽象性规范应当在全国得到普遍遵守,在认定医务人员是否符合“当时的医疗水平”时不能因地域差异和医疗机构的等级差异而适用不同的客观标准。③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11页。
我国《民法典》颁布后,解释民法典的各家各派观点林立,但是由于缺乏权威的立法资料佐证,各种学术观点造成了《民法典》适用的混乱,难免会有二次造法问题存在。立法资料,特别是立法理由,是解释《民法典》的重要依据。因此,我国如何对立法资料进行管理值得研究。鉴于此,本文将结合大陆法系一些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来分析,试图寻找适合我国的相应路径。
二、成文法系的经验及做法
成文法系各国及地区一般面临着法典颁布后的二次造法问题。比如《德国民法典》颁布之前,德国民法存在共同法、巴伐利亚法、法国法、萨克森法和普鲁士法等多个法适用区域,德国面临着如何避免《德国民法典》解释中的恣意问题。奥地利学者克莱默认为,法律解释传统上被区分为原本的解释和法官法,而对成文法系来说处于基础地位的是对法律原本的解释。④参见[奥]恩斯特·A.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2页。对于法律原本的解释需要借助立法资料,这涉及立法资料的管理和使用。从成文法系各国及地区的应对措施来看,各国及地区所形成的经验归类如下。
(一)立法文献的整理与公开
为了在法律颁布后能够让相关人准确地理解《民法典》的立法原意,大陆法系各国对立法的原始文献保存都十分完善,并在整理后公开出版。比如《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材料涉及对第一草案进行修改、变动的立法会议原始过程进行记录的《德国立法会议记录》以及据此编纂的《〈德国民法典〉立法动议》。奥地利的《奥地利一般民法典》原始草案和咨询意见记录⑤Ofner, Julius, Der Ur-Entwurf und die Berahungs-Protokolle des Österreichischen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Band 1, Detlev Auvermann KG/Glashütten im Taunus, 1889, Vorrede.、瑞士关于《民法典》的草案、说明以及讨论记录,都被完好地保存并公开。今天瑞士的《伯尔尼评注》将这些资料汇编成三卷本,置于该评注之首。⑥Hurni, Christoph/Reber, Markus/Hofer, Sibylle, Materialien zum Zivilgesetzbuch, Band I, II, III, Stämpfli Verlag AG Bern, 2009; 2007; 2013.鉴于篇幅,本文下面着重介绍德国的相关资料文献。
首先,《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立法理由被整理在《〈德国民法典〉立法动议》之中,该《立法动议》的官方版本由古藤塔克出版社(J. Guttentag)于1988年正式出版。官方版本(Amtliche Ausgabe)根据《德国民法典》体例共分为总论、债法、物权法、家庭法与继承法五卷本。德国立法动议对每个具体条文立法过程的详细阐述和论证,包括立法目的与对该条文的理论争议以及立法者所采用的立法选择以及论证理由等,这些都记录在了《立法动议》之中,这些属于立法的最原始材料,而出版的每本《立法动议》都对每个法条的立法理由的原始材料作了呈现。⑦Motive zu dem Entwurfe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Band I.-V., Berlin und Leipzig: Verlag von J. Guttentag, 1888.
其次,为德国民法典立法会议记录。较早成书的是第二起草委员会整理的《立法会议记录》,该《立法会议记录》由帝国司法部委托Achilles, Gebhard,Spahn.J.Guttentag等汇编而成,主要涉及《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德国民法典第三草案》的立法原始文献,里面还包括了讨论时各位立法者对民法典各条文讨论的过程记录,包括讨论中的不同意见以及讨论的具体结果。这真实地记录了立法的详细过程,对采纳意见的理由分析以及对摒弃意见的理由分析也颇为详细,这对后来理解法条的制定过程以及立法者的原意提供了原始材料依据。⑧Protokolle der Kommission für die zweite Lesung des Entwurfs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Band 1-5, Berlin: J. Gutentag Verlag, 1897-1899.
二战后,对于民法典的修订,德国、奥地利、瑞士的联邦议会在《联邦法律公报》(Bundesgesetzblatt)中公布修订后的法律以及详细的立法理由。比如对《德国民法典》修订后的《债法现代化法(草案)》《病人权利保护法》以及针对每个法条列出的详细的《修订理由》就收录在《德国联邦法律公报》之中,这一官方的立法资料公布形式使得立法资料更加权威。同时,联邦议会议员对于法律修正案的讨论内容也会被真实详细地记录下来,并公开发布于《德国联邦议会会议报告》(Deutsche Bundestag Sitzungsbericht)之中,这一官方公布的立法会议记录对于了解后来研究法律变动的原因和过程具有重要帮助。
(二)立法资料的实践价值
奥地利学者沃夫那(Ofner)在其主编的奥地利民法编撰的立法资料前言中一开始就对会议记录对于《奥地利一般民法典》解释的权威性作了强调。⑨同前注⑤。在成文法系国家,立法文献的科学管理对法律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法教义学、司法与法律修订之中。
1.民法教义的基础
民法教义构建于对法律的权威解释之上。立法原始文献真实地记录了立法理由与立法过程,使得后人对法条变迁有了直接客观的理解,对于正确把握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更有利于正确理解法条的本意。《奥地利一般民法典》颁布后,帕夫(Pfaff)和霍夫曼(Hofmann)在其评注中就充分利用了会议记录,以探究法条本意。⑩同前注⑤。《德国民法典》颁布不久后的德国教科书、法典评注等,学者撰写的对法条的内容理解基本都以《立法动议》和其他立法材料中公布的内容为基础,并进而奠定了德国民法法教义学发展的基调。比如Hugo Reumann对《德国民法典汇编》(Handausgabe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所作的注解⑪Reumann, Hugo, Handausgabe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Berlin: Verlag von Franz Vahlen, 1903. S. 11ff.,厄尔特曼(Paul Oertmann)的《债法》(Das 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⑫Oertmann, Das 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 Berlin: Carl Heymanns Verlag, 1899, S. 4ff.,《索艾格民法典评注》等法典评注中早期的内容主要还是以立法理由中的立法者观点为基础。⑬HKK/Harke,§ 311 II, III, Rn. 11f.当然,对于《〈德国民法典〉历史评注》(Historisch-kritischer Kommentar zum BGB)而言,在论述制度发展中立法者的观点时对原始立法文献的引述更是随处可见,意义非凡。
当然,法教义学研究同样会遇见疑难问题,这时立法文献对于疑难争议内容的理解特别具有助益。比如,对于缔约过失(culpa in contrahendo)和信赖损害赔偿的立法模式问题争议的探讨就需要探究立法理由中的论述。一方面,德国民法典起草者是否引入了耶林发展而来的缔约过失责任,还是在《德国民法典》中设计了一个不同于耶林的模式?后人依据《立法动议》认定,起草者明确放弃了合同缔结中过错的一般条款模式,并将之限定于特定损害赔偿规范之中。⑭HKK/Harke,§ 311 II, III, Rn. 11f.而对于《德国民法典草案》立法是否采用了不同于当时著名私法学者也是第一草案起草者之一温特沙伊德的观点问题,学者根据当时的立法材料认定,温特沙伊德确立的是一个客观的赔偿责任和强制性的私法规则,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并未将之确立为规则,而只是将第122条、第179条第2款和第307条作为具体的方案,但《立法动议》将立法理由作了详述,使得后人得以了解规则制定的详情,从而为法教义学的建构提供了依据。⑮Mot. II S. 216 = Mugdan, Bd II. S. 119.
2.司法的参照
德国方法论著名学者吕克特(Rückert)认为,判决也是论证的过程,而从论证法学角度来看,立法者决定的历史主观上的理由在论证中具有优先性。⑯Rückert/Seinecke,Methodik des Zivilrechts - von Savigny bis Teubner, Nomos Verlag, 3. Auflage, S. 590.但是,在成文法国家,基于权力分配与制约这一宪法原则,法院的司法活动要受制于法律。比如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2款第2句将权力分立为“专门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审判权”,这赋予了司法一个明确的角色。它应该以法律和法为标准来控制其他权力,而非自己设定的标准。在现实中意味着:议会决定立法的标准,政府和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司法机关则关注合法性。因此,法官仍然受法律的约束。同样,对于所谓的法的标准中的漏洞也很少仅仅交由法官来处理,法官对法条的正确理解是司法正义的前提。⑰同前注⑯,Rn.39.因此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能够正确地理解法律,必须要掌握立法者对具体条文的立法意图,特别是在涉及争议案件之时,比如对物权变动的模式选择以及理由。在德国司法审判中,引用立法原始文献来分析法律争议的情况更是常态,并将之作为首选。⑱RGZ 61, 207ff;RGZ 65,17ff.
对于立法理由作为司法判决论证依据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1905年7月8日帝国法院在对合同缔结中被代理人因代理人的欺诈行为是否承担一般赔偿责任问题进行论述时就直接引用了《立法动议》第一卷中关于第117、118条的立法理由:“对于代理人在行使代理权时所作出的违法行为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忽略针对法人规定的特殊条款)被代理人只在第711、712条(现第831条)规定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被代理人是否为代理人在作出法律行为中的过失(缔约过失)负责,取决于该行为中是否存在被禁止的行为,还是只是涉及违反了法律行为的义务——这一问题在上文(第20页)已经论述过。”帝国法院依此立法理由中的立法者的论述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认为符合立法者观点的结论。⑲RGZ 65, 207, 212.
但是,德国法院经常遇到法律解释的争议问题,有的争议由于很难从保存至今的立法文献中寻得立法者的原意,这就使得问题的争议在司法中一直存在,也使得司法机关难以作出统一的判决,理论界对司法机关的判决也会批判不断,造成了法律上的混乱。如1985年联邦普通法院对一个关于租赁合同的标的物一开始就客观履行不能时的赔偿责任问题进行分析时,就对是否与立法者的观点相冲突进行了论证。⑳BGHZ 93, 142,145.而在联邦普通法院2014年判决的著名主持人亚历山大(Peter Alexander)诉某杂志侵犯其名誉权要求金钱赔偿案件中,对于因侵犯人格权的金钱赔偿请求权是否可以继承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非常大,联邦普通法院在判决中写到,对于这一争议难以从立法文献中寻找到确切的立法者原意,因此只能根据理论加以分析。21BGH,Urt.v.29.4.2014-VI ZR 246/12(KG).但是判决出来以后并未平息争议,反而招致了更多的批判。比如施匹克霍夫(Spickhoff)教授就对联邦法院的判决作出了批判,他认为这一判决不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也未必符合立法者原意。22LMK 2014, Nr. 359158.因此,要作出权威的符合法律的解释,立法文献中所记载的立法者的本意对解释法律相当重要,如果缺失则会造成司法的混乱。
而对于《民法典》后来新修订的立法理由的原始资料的引用在联邦法院的判决中也是论证的有力依据,因为这对于论证法律的变化带来对案例事实评价的变化很是关键。同样,还有其他原始立法文献,比如2007年联邦普通法院在关于不动产买卖中损害赔偿请求权案件中对于联邦立法资料BT-Drucks. 14/4722号文件的多次引用。23BGHZ 173, 24, 31ff.以及联邦普通法院在案件中对专利程序的目的进行论证时对立法文献的引用24BGHZ 165, 163, 164; BGBl. 1980 II S. 1105.等。
3.法律修订的参照
正确理解之前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是法律修改的前提。《德国民法典》修订时也要探究立法者原初的立法初衷,领会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并为修订法律提供参考。同时,也将修订法律的立法理由以及立法过程公布于众。《德国民法典》在2002年债法改革时就将修订理由公布于联邦议会的官方公开出版物中,即载于第14届、第6040号《联邦议会文件》中否认《关于〈债法现代化草案〉的说明和理由》(2001年5月4日联邦议会党团的草案)。2002年德国债法改革后联邦议会的修法原始文献BT-Drucksache 14/6040无疑是德国法典评注、教科书与各法院判决最权威也最常引用的立法原始材料。这一共有288页的联邦议会立法原始文献对立法修订的理由逐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证,无疑就是一本权威的教科书。25BT-Drs. 14/6040.而对于之前讨论的非物质损害赔偿,2002年7月,关于损害赔偿法的第二修正案在《德国民法典》第253条增加了一款。该新增的条款是在第847条条文的基础上改动而来,修订时同时删除了第847条。依据第253条第2款,痛苦抚慰金不仅适用于侵权法领域,而且还适用于违约和危险责任领域。据此,痛苦抚慰金请求权在法典体系中具有了新的位置,且具有了一个更大的适用范围。但是该次法律修订并未完全跟随法官造法的趋势,而是继续保持了19世纪德国民法典立法者们所划定的谨慎范围,并未彻底改变基础性的原初思想。虽然存在学者的批评,但是仍然如之前的德国损害赔偿法一样,被侵权人的亲属仍不享有痛苦抚慰金请求权。26BT-Drs. 11/4415; vgl. Lepa, Die Wandlungen des Schmerzensgeldanspruchs und ihre Folgen, in FS Müller (2009), S. 113, 116.在该次法条修订之中,修订者们首先探究了立法者的原意,而探究立法原意的重要参考依据就是原初保存下来的立法原始文献。如果没有这些立法原始文献,修订者对立法原意的探究就不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对立法修订的权威性构成威胁。
总之,德国民法的立法动议为立法的原始文献,其详细记录了立法草案中每一个法条的立法理由,并且对之后该法条修改变动的立法理由、意见分歧以及修改过程作了详细真实的原始记录,全面客观地反映了立法的全貌,为后来正确理解立法提供了权威的依据,解决了立法后对该法条正确理解的难题。并且立法者也界定了立法原始文献与立法解释之间的区别,赋予其辅助地位的工具价值。随着立法技术的发展,法律条文已经与立法解释、法律理论有了明晰的界分,将法律文本与法律文本辅助资料分开已经成为当代立法的模式。德国模式很好地体现了该立法技术的发展,作为立法文本出现的法典已经具有独立、权威的地位。但是德国模式还注重立法文献的保存,这体现了当代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为法典的正确使用提供了直接、权威的辅助资料,这些资料对法典的运行提供了标准与参考,对法典的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我国立法资料管理的问题与方向
(一)我国立法资料管理的问题
成文法系国家及地区对于立法文献的管理都形成了严格的制度,并严格依据立法资料的管理制度管理,这使得直到今天仍可以看到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我国台湾地区等早期立法的立法理由和会议讨论记录。这对于今天的法律适用具有重要影响。立法资料的管理方式对于该资料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我国台湾学者黄茂荣认为“这些资料,以公诸大众为限,始能被引用”。27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页。总体来看,我国不存在上述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立法资料。从我国的立法文献编撰、管理来看,所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非全面性。从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民法典》立法资料来看,主要涉及民法典的各个草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等。从内容上看,关于民法典草案并未给出详细的制定理由,对于草案修订也并未列出详细的修改理由。
第二,非正式性。我国《民法典》生效后各种解释法典的著作层出不穷,但是唯独缺乏立法机关整理的原始的立法资料。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主任黄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解读》,28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副主任石宏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解与适用》,虽然编著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工作人员,但是内容并非直接、原始的立法材料,而是立法后对已经生效规范的解释说明。29参见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立法资料正式性体现在为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民法典条文时形成的历史文件。中国尚未具有如德国式的原始的、真正的立法理由汇编,而这些事后的学理解释不具有正式性,法条生效后编写的立法理由都具有非正式性,只能作为法律制定后的学者解读,难以作为法律解释的权威依据。
第三,非权威性。原始立法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的意义在于作为司法和法学研究探究立法本意的权威依据,其必须由立法机关根据原始立法材料整理、总结而来。而且这里学理解释缺乏科学性的地方还在于并未总结出当时立法专家的各个立法意见、讨论过程,以及最终采用的学说观点,这极容易又造成新一波对法条的任意解读,法条制定并未带来定分止争的作用。因此,中国法律解释缺乏原始的立法参照标准,中国目前对民事立法原意的解读仍为尚未克服的难题,这也造成了学界对法律解释的混乱与最高司法机关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具有二次立法的可能。比如201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对知假买假的行为作出的答复就与之前的司法解释略有不同,法律解释标准与依据的缺乏所带来的对法律的任意解释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与权利的安定性。而对该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寻求既有的立法者的“历史主观性决定”的理由。
(二)我国立法资料管理的方向
1. 立法理由的管理
从世界成文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来看,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的民法典立法理由都是写于草案编撰之时,论证并说明草案具体条文拟定的理由。但是从我国《民法典》立法来看,立法机关在公布《民法典》分编草案和整合后的《民法典(草案)》之时并未公布条文制定的立法理由。因此,我国在《民法典》立法时,应在草案拟定之时即撰写相应的条文制定理由,而非在法律生效后才拟定立法理由。基于立法理由是由立法草案的撰写者对草案条文设计的理由说明和论证过程,因此我国《民法典(草案)》的立法理由应由提出第一草案的参与立法的人员撰写。撰写草案条文的立法人员需要对自己设计条文的具体理由以及设计思路进行论证和说明,并在撰写草案过程中形成民法典立法理由。
基于立法理由在于论证草案建议稿中条文设计内容的科学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并论证相应的立法思路和规范具体内容,所以针对草案条文的立法理由对于理解草案建议稿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也是草案建议稿修订时所能够参考的最直接的文献资料。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立法理由的公布主要有与草案同时公布和在法律生效后公布两种。与草案同时公布的有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瑞士在公布民法典各编草案的同时公布了相应的立法理由,德国在草案建议稿公布的同时即公布了《立法动议》,以便他人能够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的设计思路和本意。但是从当前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各国越来越倾向在草案公布的同时公布立法论证理由,这样可以更有利于对草案的理解。比如从德国新近的立法来看,德国政府在提出《遗属抚慰金引入法草案》的同时即制定了详细的立法理由,并同时相应地在《德国联邦参议会公报》或《德国联邦议会公报》上加以公布,以便他人能够真实地理解草案条文设计的原理。30BR Drs. 127/17; BT Drs. 18/11397.
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在《民法典(草案)》公布时并未公布详细的立法理由,事后也并未公布相关立法理由,因此难以获知撰写我国《民法典(草案)》之时是否撰写了立法理由。虽然我国民法典草案各编已经出现了第一草案、第二草案甚至第三草案,但是从2018、2019、2020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内容,或其他立法机关的官方公开文件来看,立法机关也并未公布对民法典草案各编条文的修改记录和理由,因此难以获知详细的立法讨论过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公布的习惯,立法机关在公布相关法律时会同时公布与该法律制定有关的草案说明、修改意见报告等内容。但是这种公布方式具有滞后性,难以让普通民众参与并了解立法过程,难以获知法律制定和修改的具体理由和内容。因此,立法机关需要及时公布与立法理由、立法讨论记录等相关的立法资料,以便公众查阅。
从成文法系国家对立法理由公布的方式来看,一般是立法机关以官方的形式加以发布。比如瑞士立法机关对瑞士民法典立法报告的发布即刊登在《瑞士联邦议会公报》(Bundesblatt)之上。31Bundesblatt 1896 IV, 733-790; Bundesblatt 1904 IV, 1-99; Bundesblatt 1907 VI, 367ff.; Bundesblatt1907 VI, 589ff.当代一般会将立法修订草案与理由发布在立法机关官方的公报上,比如德国第二次债法改革时,立法机关即将草案和立法理由在立法机关的公报即《德国联邦议会公报》中加以公布。德国在制定《关于引入遗属抚慰金法》时,亦将立法草案和立法理由刊印在政府、议会或参议会的公报中。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正式出版刊物。公报主要登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决定、决议、报告、人事任免以及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和检查法律执行情况的报告,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宣传民主法制建设、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刊物。32参见全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hgb/index.shtml,2020年6月15日访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6月15日出版的特刊中同时公布的还有《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公布的资料来看,所公布的报告都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所作的报告。这些立法资料在官方出版物上公布具有权威性,可以作为法律适用和法学研究引用的权威依据。但是从公布的立法资料的类型来看,正式公布的立法资料仍不完全,缺乏具体条文的立法理由和草案条文修改讨论记录方面资料的公布。与我国《民法典》有关的立法理由应该在立法机关的官方出版物上正式公布,以便在法律适用和法学研究中查阅和引用。
2.草案修订记录资料管理
从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的立法经验来看,这些国家的立法机关会将具体的草案讨论及修订过程记录正式地加以公布。比如德国帝国司法部委托阿齐勒斯(Achilles)等三位博士对《民法典(草案)》第二次审议会议的会议讨论内容进行整理,并汇编成两卷本的《民法典草案第二次审议会议记录》(Protokolle der Kommission für die yweite Lesung des Entwurfs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33Achilles/Gebhard/Spahn, Protokolle der Kommission für die zweite Lesung des Entwurfs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Band I, II, Berlin: J.Guttentag Verlagsbuchhandlung, 1897.瑞士的大专家委员会在1901到1903年间在卢塞恩、纳沙泰尔、苏黎世、日内瓦召开民法典草案讨论会议,这些对民法典会议的讨论过程被全程记录下来,并整理后加以公布。34Hurni, Christoph/Reber, Markus/Hofer, Sibylle (Hrsg.), Materiealien zum Zivilgesetzbuch, Stämpfli Verlag AG Berm, S. 2.这些会议记录中,会议记录的编写者会将立法草案讨论和修订过程记录在联邦议会会议记录或联邦参议院的会议记录之中,这两份记录文件都有严格的记录和公布程序。德国联邦议会对于议会讨论记录会按照会议的场次、时间、讨论内容等要素进行编排。对立法草案的讨论会真实地记录议员的姓名、议员所发表的相关言论的具体内容等。在议会记录整理完毕后,德国联邦议会按照具体的时间段会将该时期的议会讨论记录正式地公布。这些立法草案讨论记录的公布使得所有人都可以查阅并了解议员对于草案具体内容所发表的修改意见和修改理由,让他人能够获知法律条文的修订过程和修订理由,这对于法律条文内容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合国外的立法经验,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我国的立法修订资料管理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改进:
首先,涉及立法机关对草案修订过程的记录。我国的立法机关需要对立法机关所组织的对草案的论证过程中各个专家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条文审议中的相关意见、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对于草案条文的审议意见进行详细地记录。但是从我国公布的关于修改的立法资料来看,仅公布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之类的立法资料,此类资料都是立法机关的总结内容,虽然这一种立法文献对于立法修订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立法者的选择,但是这种对于草案修订结果的总结内容缺乏对草案条文修订理由的详细论述,在对法律的解释中这并不能够完全取代立法机关真实记录的法律草案讨论的详细内容和立法机关最终对于修订草案的详细论证内容。从域外立法经验来看,德国对于民法典草案的讨论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比如《德国民法典》立法资料中重要的七卷本的《〈德国民法典草案〉第二次审议会议记录》(“Protokolle der Kommission für die zweite Lesung des Entwurfs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今天德国的立法机关仍然对自己的立法过程进行详细地记载,比如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对于法律修正案的讨论内容也会真实详细地记录下来,并公开发布于《德国联邦议会会议报告》(Deutsche Bundestag Sitzungsbericht)之中,在该记录档案之中详细地记录了议案讨论会议举行的时间,以及每个参与讨论人员论证的过程。我国立法机关尚缺乏类似记录立法讨论过程的官方公开发布的会议报告,为了能够让民众真实、详细地了解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过程,我国应该将立法会议讨论的过程以官方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便法律适用者和研究者能够查知立法的修订过程。
其次,涉及立法机关对所记录的草案修订过程记录的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6月15日特刊中公布的具有草案修改性质的文件有《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35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特刊,第198页。《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36同上注,第205页。。这里首先涉及公布的载体,立法机关应该将草案修订记录公布在官方的载体之上,一方面这体现了这些草案记录内容的正式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便于法官、律师、研究人员等对于该文献的查找和援引。其次还涉及对于草案修订记录公布的时间。立法机关的草案修订记录内容是对正式立法过程的记录,公布的时间应该具有明确性和正式性,需要确定按月、按季度、按年份公布等形式。从德国立法机关公布立法资料的经验来看,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员对于自己议会的讨论记录具有按时间和按会议场次正式公布的方式,但是这一种全面、详细的公布方式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目前只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中公布简略的立法资料。有规律地正式公布立法机关详细的立法讨论记录可以使得公众能够准确及时地获知立法过程,便于关心立法的法律人及时了解立法进程,并对新的草案内容作出相关的分析和批判,这有利于提高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因此,从立法资料的全备性角度来看,我国立法机关需要对立法讨论、修订记录的详细内容加以及时公布。
3.立法资料的综合整理
立法机关正式公布所有立法资料后,为了能够更便于寻找、学习和研究,立法机关和学界有必要对立法资料进行综合整理。但是对立法资料的综合整理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立法资料的整理须建立在官方公布的原始立法文献的基础之上。从程序上来看,首先是立法机关公布权威的、真实的立法资料,这些立法资料包括立法草案、立法理由、草案修订过程及理由。瑞士著名的《伯尔尼民法典评注》前三卷并非是针对民法典的评注,而是汇编了《瑞士民法典》的立法材料,包括了原始的立法报告、法典草案及立法理由、法典起草者胡伯的立法说明、立法机关组织的法典草案讨论记录,以及其他立法机关立法过程中所撰写的关于《瑞士民法典》立法的相关文件。对于立法资料的选择对象,《伯尔尼民法典》评注编纂者只是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委托他人公布的官方内容为选择对象,排除了参与立法的人员以自己的名义撰写的相关内容。37同前注34,S. 1ff.从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写的关于《民法总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条文说明、立法理由来看,在对法律的条文说明和立法理由阐释中并未以任何官方公布的权威的立法资料为基础,难以认定为对立法资料的整理,因此也并不具有立法资料的权威参考价值。
其次,对于立法资料的整理可以参照不同的标准。《伯尔尼民法典评注》对《瑞士民法典》的立法资料以立法理由、立法会议记录、立法会议的报告为标准来编排。38同前注34,S. 1ff.从德国的立法资料整理来看,对于立法资料的整理一般采用以条文顺序为编排的整理方式。这一编排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全面了解该条文从拟定到最终成形的发展过程,这里不仅可以看到立法理由,而且可以看到该条文的发展与变迁过程,这对于真实、全面地把握该条文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编排方法需要对于之前立法资料中的内容进行重新整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在遇到条文合并的时候,对于立法资料的整理需要综合处理立法资料。从我国的《〈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的立法资料汇编来看,主要涉及立法机关的草案说明、立法报告及调研报告。由于我国缺乏立法理由和草案修订记录,因此缺乏这两种最详尽且对理解法律最有参照性的立法资料。39参见《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编:《〈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及以下。因此我国立法资料汇编的资料选择标准:一方面要遴选直接的立法资料,而非对立法只有间接影响的调研报告。另一方面要选择对法典条文解释最具有价值的立法理由和立法修订记录。
最后,立法资料的综合整理要保持立法资料的原始内容。对立法资料的综合整理并非是对立法资料的综述,而是保持对立法资料的原貌的整理。瑞士《伯尔尼民法典评注》中对于立法资料的整理即严格遵循了立法文献的原始性,包括对原始文字的拼写和表述都并未依据当代德语进行修改。同样,对于官方原始文献的边码在编排中都作了保留。40同前注34,S. 5.对立法资料的综述是对立法资料内容的再加工,属于一种内容创新,并不具有立法资料作为参考工具的价值。瑞士的《伯尔尼民法典评注》在《对文献选择的说明》中指出了严格的立法文献选择对象,只限于立法机关自己或委托公布的文献,这些文献形成于立法过程之中,包括议会草案、草案大纲、议会报告、解释说明、专家委员会会议记录等。41同前注34,S. 4.德国的立法资料整理则主要由议会报告、立法理由、立法讨论会议记录构成。我国当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法室编写的关于《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条文说明和立法理由中虽然述及了立法理由和一些修改的依据,但是并非原始的具体的立法资料,而是类似于对立法资料的综述和分析,属于对立法资料的研究成果,而非立法资料本身。因此我国对立法资料的整理应从原始的立法资料出发,杜绝对原始立法资料内容进行加工,从而可能导致对立法者立法原意的篡改。
四、我国立法资料的应用
我国《民法典》立法资料的科学管理在于其相应的法治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一)建构权威的民法教义
从中国的法学发展来看,国内已经对法典评注这一形成法教义的形式有了较大发展。法教义学是以一国的现行法为基础所形成的权威的理论。法教义学在司法中的功能:一方面是由成文法的地位决定的。法教义学的构建首先立足于现行法,因此对现行法的解释即为首要之义,而诸如立法理由、立法会议记录等立法原始资料在释法中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法典评注即以立法理由中的观点来解释条文,这保障了条文释义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是由成文法系国家中法学家的研究方法所决定。欧洲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的法学家在构建法教义学时会与审判实践紧密结合,一方面注重条文的解释;另一方面注重条文在案例中的运行。
从我国当前的《民法典》立法实践来看,《民法典(草案)》公布后并未公布相应的立法理由,这使得他人对《民法典(草案)》的规则制定难以准确把握,只能依据中国《民法典(草案)》的具体规范内容加以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民法典(草案)》并非如立法者原初所预定的是对既有规范的整理,而是具有许多重大改变之处,比如体系上没有债法总论、加入了人格权编等。这些改变都并未附加任何的理由说明,使得人们对草案的立法目的和条文本意难以把握。因此,《民法典》规则制定后的立法理由对于民法典具有重要意义,缺乏立法理由对于我国民法典的立法实践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必然具有严重损害。特别是我国民法现代化过程中受外来法影响较多,德国法、法国法、日本法、英美法等概念、规则在我国的影响较为混乱,立法条文的渊源溯及也难以厘清,因此需要从立法中加以确立和界定,以便在解释条文时追溯规则的传统。因此,从法教义学的建构来看,我国《民法典》立法时的立法理由、草案修改理由等就显得尤为关键。
(二)司法实践中的引证
1. 规避二次造法
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成文法系国家的法官受制于制定法的约束。因此,大陆法系法官的司法功能排斥造法功能。但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最易引起二次造法之处在于法律解释之时,“出释入造”是法官司法中容易涉及的一个宪法问题。“二次造法”从某种意义上不同于法官造法,一般指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偏离了立法的本意。比如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的解释最容易产生二次造法问题。法官对于“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的解释会影响购买者是否可以获得多倍赔偿这一法律效果。司法的地位和功能属于一国的宪法问题。一方面涉及权力分配原则;另一方面涉及依法司法原则。我国《宪法》第131条、《德国基本法》第101条第1款第2句规定了依法司法的原则,即法官司法需要遵守一定的成文法规则,但是在英美国家的法官却无须遵守一定的抽象规则来审理具体的案件,法官可以在案件审理中发表独立的意见(seriatim opinions),无需与其他法官保持意见一致。42Maultzsch, Joachim, Grundstrukturen der englischen Case Law-Methodik, in: Rückert/Seinecke, Methodik des Zivilrechts - von Savigny bis Teubner, Nomos Verlag, 3. Auflage, Rn. 478ff.但是成文法系国家的法官造法受到严格的限制,比如所谓的一般人格权法作为德国法官造法的成功例子在德国的成文法制度中仍属于极端的例外情形,因此不可以某个极端的法官造法来过分夸大法官造法的角色和过分轻视成文法的地位。比如在著名的“升值案”判决中,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严重不公,帝国法院在裁判中改变了《货币法》中“纸币马克等于黄金马克”的规则。这受到了利益法学大师菲利普·黑克的批判,虽然菲利普·黑克主张法官的利益衡量,但是只是依据法律的利益衡量,并不主张违反法律的利益衡量。43Manegold, Jutta, Mehode und Zivilrecht bei Philip Heck (1858-1943), in: Rückert/Seinecke, Methodik des Zivilrechts - von Savigny bis Teubner, Nomos Verlag, 3. Auflage, Rn. 1327.从中国实际问题来看,虽然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了法院依法审判的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在解释法条的时候往往很难正确地理解法条的原意,且也没有详细的原始立法资料可以参照,法官在司法中“二次造法”在所难免,这导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成为了司法机关在司法中的全新立法活动。44参见刘风景:《司法解释权限的界定与行使》,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齐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释法抑或造法》,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比如201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对知假买假的行为作出的限制性答复,此处涉及欺诈对民事行为法律效力的影响。由于对于知假买假行为是否有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食品安全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导致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此法条的解释多种多样,产生了法官“二次造法”的问题。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的答复与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第3条的规定中支持知假买假诉讼的解释有了改变。因此,从立法理由中约束司法中的解释活动,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就显得尤为必要。德国学者齐默曼认为,立法资料在历史解释中具有核心的地位。没有立法资料就限制了对法律的历史解释和客观“目的解释”,因为这两种解释的方法都需要借助立法原始资料来探究立法者的原意。45Zimmerman, Reinhard,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in Deutschland, inÖ RabelsZ 2019, 241,260.
2. 塑造裁判合理性
裁判的合理性有别于规范的合理性。规范合理性为立法者法律制定中所要实现的目标,而裁判合理性则为法官在裁判发现中所要关注的要求。裁判的合理性塑造一般采取两种策略:一种是寻找权威依据作为支撑,比如权威法学家的观点、权威书籍的观点、立法原始资料等,其中最具权威性的当属立法原始资料。另一种策略是适用适当的论证方法,比如利益法学方法、衡量法学方法、评价法学方法、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
首先,涉及裁判合理性的论证依据的合理性。法官在裁判发现过程中涉及对裁判依据的论证,这关涉对所援引法律规范的解释和运用,而此解释和分析过程中对规范的不同理解会导致论证的不同走向。此时对论证依据的选取就尤为关键。选取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立法文献资料中阐述的内容还是选取法律制定后民法学者对规范的解读分析,特别是当法律制定时的立法者的制定理由与后来学者观点并不一致之时,这一论证依据的选择可能引起裁判结论的合理性问题。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成文法系国家裁判论证合理性的建构应符合法官的宪法定位。在判决合理性论证的建构过程中对论证依据的选取应以立法者的立法理由为优先,否则摈弃立法资料中的立法依据而选取契合法官理解的其他论证依据的合理性的宪法基础就可能受到质疑。
其次,涉及裁判合理性的论证结论的合理性。论证结论的合理性一般由论证过程的合理性所导致。但是当权威的论证依据缺失之时,论证结论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比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知假买假”情形中“消费者”的认定和《物权法》中物权变动模式的认定,这些都导致了判决结论的不同,也导致了判决结论合理性的欠缺。因此,为了保证裁判结论的合理性需要具有对规范理解有分歧时立法者意思决定的立法资料支撑,这对于裁判结论合理性的保障具有决定意义。但是对于立法理由有质疑时,法官是否可以摒弃依据立法理由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立法者恣意与法官恣意之间冲突的问题,这涉及宪法问题,即法官是否可以作出未被法律支撑的判决。在成文法系国家以及我国宪法中的法官地位,宪法并未对此作出授权,此时法官的恣意应被限制。因此,个别的法官对法律的质疑并不是法官不按立法者意志司法的理由。当法律有争议或者过时时涉及的是立法者修订法律的问题,而不是法官实质上修订法律的问题,而新修订的法律的修订理由可以成为新的裁判合理性的依据,比如2012年德国债法现代化时新的详细的立法理由。
五、结语
大陆法系中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对立法资料保存、整理、公开与使用的经验表明,立法资料对于大陆法系法教义学的塑造、司法裁判的合理性以及司法中二次造法的避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我国《民法典》制定后需要塑造权威的法教义学,这需要立法资料这一核心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中国立法后单纯的法典文本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释法中二次造法现象难以避免。目前中国尚不存在诸如德、奥、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意义上的立法资料。当代立法的文明与科学需要立法者对立法的严肃性、权威性与科学性进行塑造,这需要立法者对原始立法文献的整理与公开,以便后来法律运行中对立法原意作出正确的把握,而立法资料中最为关键的是立法理由。只有这样法律适用者才有了法律适用的标杆,才可以使得守法者、司法者与法律研究者能够更真实、客观地理解立法者的意图,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守法者、司法者与法律研究者进行二次造法的可能,否则会造成法律理解上的混乱,对法律的权威性造成损害。鉴于此,我国《民法典》颁布后需要对立法原始文献进行整理与公开,否则中国的民法教义内容建构就不会客观地实现,司法理由的论证也难以树立权威,同时也难以解决我国当前立法后对法条随意解释所带来的“二次造法”的问题以及司法中裁判的合理性、权威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