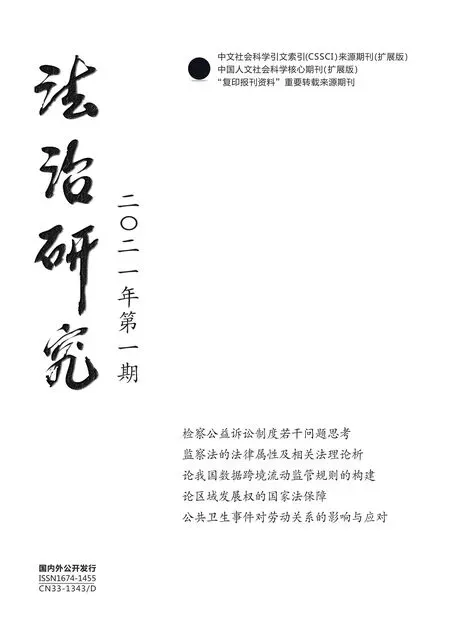国际经贸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及其解释问题
张乃根
一、条约法上的安全例外:观念与条款的由来及发展
“安全”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当代欧美国际关系学理论较多讨论“集体安全”“国际安全”问题。①如英尼斯·克劳德的“均势、集体安全和世界政府”理论,参见倪世雄、金应忠主编:《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又如“国际安全新论”,参见倪世雄主编:《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页。其实,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形成之初,“安全”就是一个基本观念。对于每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而言,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或条件必不可少。因此,国家的“安全”观具有本国不受他国武力侵犯或威胁和独立生存而避免根本上依赖他国的基本内涵。格劳秀斯在最初探讨现代国际法原理时曾提出两项包含“安全”观念的自然法戒律:“第一,应当允许保护(人们自己的)生命并避免可能造成其伤害的威胁;第二,应当允许为自己取得并保有那些对生存有用的东西。”②[荷]格劳秀斯:《捕获法》,张乃根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他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将这两项戒律运用于论证正义战争的合法性:“就战争之目的与宗旨在于保全生命与身体完整,并保存或取得对于生活有用的东西而言,战争完全符合这些自然的基本原则。”③Hugo Grotius,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 translated by Francis W. Kelsey, the Clarendon Press, 1925, p.52.这在传统国际法上被称为每个国家的“自我保全”原则,涵盖自卫和自存两方面的固有权利。④See Amos S. Hershey, The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9, p.144; “自卫”又称“自保”,参见[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2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原则上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同时第51条允许“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⑤《联合国宪章》(1945年6月26日),载《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页。这是相对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例外,⑥See Kenneth Manusama,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Martinuis Nijhoff Publishers, 2011, p.299;又参见黄瑶:《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可以说,这是现代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多边条约第一次规定自卫权的安全例外条款。此前,《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第124条规定对于违约者,受害者应首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法律措施”,经三年无法解决争端,可使用武力。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10月24日),载《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其实质在于允许一个国家使用武力解决与他国的争端,因而不是禁止使用武力的安全例外。这一支配现代国际关系数百年的法则直到联合国成立才得以改变。
在《联合国宪章》问世后不久,1947年10月30日签署并于翌年1月1日起临时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⑧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55. U.N.T.S. 94; Protocol of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of the GATT, 55. U.N.S.T. 308.第21条以“安全例外”为标题,明确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a)要求缔约方提供其认为如披露会违背其基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或(b)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i)与裂变和聚变或衍生这些物质有关的行动;(ii)与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贸易有关的行动,及与此类贸易所运输的直接或间接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或物资有关的行动;(iii)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或(c)阻止任何缔约方为履行《联合国宪章》项下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任何行动。”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47),载《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页。这是多边条约首次明确规定的安全例外条款。这不仅对此后国际经贸关系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作为严格意义的条约法上安全例外条款,在一般国际法上也堪称先例。
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一揽子协定随着1995年1月1日WTO的成立而生效实施,其中,《货物贸易多边协定》包括1947年GATT,上述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不仅原封不动地保留,而且一字不差地被复制到新的《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第14条之二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73条,成为WTO三大实体性贸易协定下安全例外的共同条款。
不同于多边贸易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之由来和发展,自上世纪50年代末,尤其70年代兴起,迄今已达数千项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或协定(BITs),⑩1959年德国与巴基斯坦《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是第一项BIT,截止2020年1月25日,全球共有2899项BITs,其中已生效为2340项。此外,含有投资条款的经贸协定共有389项,319项已生效。参见UNCTAD网站: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2020年9月2日访问。起初的安全例外实质上是“公共秩序”范畴下的投资待遇例外,如1973年德国与马耳他BIT的议定书补充第2条(a)款规定:“基于公共安全与秩序、公共健康或道德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不应视为第2条含义下‘低于优惠的待遇’。”⑪Protocol to treaty between Malta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oncerning the encouragement and reciproc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7 April 1973.此后的BITs将“公共秩序”例外延伸到“基本安全利益”,形成比较明确的安全例外条款,如1983年美国与塞内加尔BIT第10条标题“本条约不得调整的措施”下第1款规定:“本条约不得排除缔约任何一方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其公共秩序与道德,履行其有关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或安全的义务,或保护自己基本安全利益。”⑫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Senegal concerning the reciprocal encour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6 December 1983. 这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BITs的条款范本。其他国家间部分BITs逐渐采纳了这样的做法,并参照了多边贸易协定的安全例外条款。如2008年日本与乌兹别克斯坦BIT第17条第1款规定:“本协定任何条款不得解读为阻止一缔约方采取或实施措施,(d)对其认为有必要保护基本安全利益,(i)在战时或武装冲突,或其他该缔约方或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⑬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for the Liberalization,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15 August 2008.与多边贸易协定不同,BITs安全例外条款尚无统一表述。
尽管在国际关系中,安全对于每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但是,除了安全保障或核安全等领域极少数条约,⑭如《日本和美国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1960年1月19日),载《国际条约集》(1960-1962),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7页;《关于核子能方面建立安全管制的公约》(1957年12月20日),载《国际条约集》(1956-1957),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662页。一般而言,条约本身很少冠以“安全”。贸易、投资等国际经贸条约仅包含安全例外条款。其原因在于安全事关国家主权,通常由各国自行处置,毋庸以条约与他国约定。国际经贸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特指对缔约方承担的国际贸易或投资方面义务而言,可基于国家安全理由,例外地不履行。因此,安全例外的实质是正当行使国家主权的体现。鉴于“条约必须遵守”⑮这既是“举世所承认”的习惯国际法,也是条约法的基本规定。参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年5月23日),载《国际条约集》(1969-1971),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页,序言和第26条。,有关缔约方通过安全例外条款作为履行条约义务之例外,仅限于涉及基本安全利益或发生战争及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可以说,这是条约义务的履行与缔约方“自我保全”相冲突或发生武装冲突致使以和平为宗旨的条约⑯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将整个条约范畴一概归为希腊人所谓“狭义的和平”,条约亦即和平。参见前注④,p.394.及其义务无法履行等极端情况下适用的。相对《联合国宪章》下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集体安全”“国际安全”而言,国际经贸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主要以单个缔约方例外地不履行其条约义务的自身“基本安全利益”或发生武装冲突等危及国家安全的极端情况为适用对象。下文分析的国际贸易、投资条约中安全例外的解释问题都与此类适用有关。
二、 国际贸易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解释问题
如上所述,1947年GATT以及1995年WTO三大实体性贸易协定早就有了安全例外条款,在GATT时期也有过涉及安全例外条款的争端解决,但均未对GATT第21条作过条约解释。⑰如,捷克斯洛伐克诉美国出口控制案,GATT/CP.3/SR.22 (1949),参见GATT Disputes:1948-1995, Volume 1: Overview and one-page case summaries, Geneva: WTO Publications 2018, p.3;又如,尼加拉瓜诉美国禁运案,L/6053,专家组报告未通过(1986年10月13日),参见[美]约翰·H·杰克逊:《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张乃根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WTO成立至今,直到晚近才接连发生两起有关货物贸易和贸易相关知识产权的安全例外争端解决案件,即,“俄罗斯有关过境运输措施案”(俄罗斯过境案)和“沙特阿拉伯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案”(沙特知识产权案)。⑱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 WT/DS512/R, 5 April 2019;该案未提起上诉,已通过专家组报告。Saudi Arabia-Measure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567/R, 16 June 2020, 该案已提起上诉。通过WTO争端解决专家组对涉案安全例外条款的条约解释,使人们对国际贸易中安全例外的内涵以及适用条件有了进一步理解。在当前美国肆意滥用其所谓“安全例外”,频频挑起国际经贸争端的情况下,⑲如,2018年3月美国以安全例外为由对进口至美国的钢铝制品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中国率先向WTO起诉美国实质上是采取违反WTO规则的保障措施。US-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China), DS544/1, 9 April 2018. 随后,欧盟等8个成员相继以同样理由诉告美国。如何运用条约解释的国际法,⑳参见张乃根:《条约解释的国际法》(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正确理解和适用国际贸易条约中安全例外条款,显得格外重要。
(一)“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解释含义之一“一般是指武装冲突或潜在的武装冲突”
俄罗斯过境案是“第一起WTO争端解决专家组被要求解释GATT第21条(或GATS与TRIPS的相同条款)。”21同前注⑱,WT/DS512/R,para.7.20.该案起因于俄罗斯以国家安全例外为由,禁止乌克兰货物经由俄罗斯公路和铁路过境至哈萨克斯坦等国。
专家组首先对俄罗斯主张安全例外的“自裁性”进行分析,认为包括WTO争端解决专家组在内的国际裁判庭都拥有履行其职能所需的“内在管辖权”,包括对其行使“实体管辖权”有关所有事项的裁定权。22同前注⑱,WT/DS512/R,para.7.53.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1条第2款,WTO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适用于包括GATT第21条在内一揽子协定的诸条款,DSU附录2所规定适用特殊或附加规则与程序也不包括GATT第21条,因此,俄罗斯援引该第21条作为其违反GATT第5条过境自由规定的“安全例外”,属于适用DSU一般规则与程序的专家组管辖权范围。
然后,专家组侧重于该第21条(b)款(iii)项的解释,并明确依照DSU第3条第2款,应适用作为“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第31条、第32条。该第21条引言句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接着三款(a)、(b)、(c)均以“或者”分开规定WTO成员履行GATT义务的安全例外。第21条(b)款也有引言句:[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为”。该引言句可以不同方式解读,得出多种解释。特别是“其认为”可解释为:其一,仅对“必需”这一用语而言;其二,也包括对“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而言;其三,对第21条(b)款的三种情况而言。专家组认为对于同一条约用语可有不同解释,但没有明确根据VCLT解释规则,是否允许多种解释的并存。在WTO的规则体系中,只有《反倾销协定》第17条第6款(ii)项明确规定专家组依据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认为本协定的有关规定可以作出一种以上允许的解释”,并可选择其一。根据DSU附录2,这属于特殊规则,仅适用于《反倾销协定》。换言之,第21条(b)款可有多种解释,但并没有协定依据允许并存的情况下选择其一。更何况对于《反倾销协定》第17条6款(ii)项,上诉机构始终否认多种解释的并存。23在“美国洗衣机案”中,一位上诉机构成员对上诉机构有关《反倾销协定》第2条第4款第2项下W-T比较方法不允许归零法的多数意见表示异议,并认为这也是《反倾销协定》第17条第6款(ii)项所允许的解释。US-Washing Machines, DS464/AB/R, 7 September 2016, paras.5.191-5.203.
专家组对这三种可能的解释,逐一展开,但重点在于第三种。第21条(b)款的(i)、(ii)、(iii)项分列的情况实质不同,且不是累加的,而是“替换的”。但是,专家组认为,其中任何行动必须满足其中之一的要求,“以便落入第21条(b)款的范围内”。24同前注⑱,WT/DS512/R,para.7.67.这是该解释的关键,即,尽管三种可替换的情况不同,但都属于第21条(b)款,因而具有一定的共性。这是将(iii)项的“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放在整个(b)款的上下文中,加以解释。
就(iii)项的“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之词义而言,专家组解释:“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这一规定提示战争是“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这一大范畴下一种情况。战争通常指的是武装冲突;紧急情况包括“危险或冲突的情况,系未曾遇见的起因并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国际关系一般指“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主要是主权国家的关系”。
就(iii)项的“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之上下文而言,专家组认为(i)和(ii)项的事项,即“裂变物质”和“武器运输”,与(iii)项的战争均与国防、军事的利益有关。因此,“‘在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必须理解为是从第21条(b)款所规定的其他事项引起的同样利益中引申而出的。”25同前注⑱,WT/DS512/R,para.7.74.亦即,第21条(b)款引言的“基本国家安全利益”具有相同性。“因此,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看来一般是指武装冲突或潜在的武装冲突,或高度紧张或危机,或一个国家内或周边普遍的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况引起有关国家的特定利益,即,国防或军事利益,或维持法律或公共秩序的利益。”26同前注⑱,WT/DS512/R,para.7.76.这类利益存在与否,属于可经专家组“客观认定的客观事实”,而不是主张安全例外的WTO成员自己主观“认为”即可。这与专家组认为安全例外不是主张者“自裁”事项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第21条安全例外的成立与否,既不是主张安全例外的成员自己决定,也不是其主观认定,而是在专家组的管辖范围,并应该经由专家组的客观认定。
就(iii)项的“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之目的及宗旨而言,《建立WTO协定》及GATT之总目的及宗旨在于促进互惠互利安排的安全性、可预见性以及实质减少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同时在特定情况下,成员可偏离其GATT和WTO项下义务,以便在最大限度接受此类义务时保持一定灵活性,但是将这专家组的上述解释更多依赖于该条款的起草史。这包括美国于1946年提交的始初文本包含如今GATT第20条、第21条的例外条款,1947年5月的起草本将一般例外与安全例外分开。美国代表团对“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作了如此解释:“我们特别记得上次战争结束前的情况,在1941年底我们参战前,战争在欧洲已进行了两年,我们即将参战时,为保护自己,要求可采取许多如今宪章已禁止的措施。我们的进出口在严格管控下,原因在于战争在进行着。”27同前注⑱,WT/DS512/R,para.7.92.也就是说,在美国参战前夕,所采取的进出口管制措施属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但与战争直接相关。正是在该起草史的印证下,专家组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包括潜在的武装冲突。这一解释符合第21条(b)款(iii)项的初衷。
但是,按照如今在条约解释的国际法实践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演进”解释规则,即,对缔约的时代较久远且依然有效的条约所具有的一般性用语,“作为一项基本规则,必须假定缔约方有意使这些术语具有演变的含义。”28Dispute Regarding Navigational and Related Rights, ICJ Reports 2009, p.243, para.66.“国际关系”和“紧急情况”都属于一般性用语。在当代,除了战争这一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还有其他不属于武装冲突范畴的紧急情况。尤其应指出,根据当代的一般国际法,调整传统的主权国家间战争法已发展为包括主权国家下内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29参见《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1977年6月8日订于日内瓦。)的武装冲突法。根据VCLT第31条第3款(c)项,作为“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当代武装冲突法,应与解释第21条(b)款(iii)项的上下文一并考虑,从而避免像本案专家组将“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首先解释为“武装冲突”,与当代武装冲突法下的“战争”重叠,使得“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多余,与条约的有效解释相悖。些偏离仅作为某成员单边意愿的表示,则有悖于这些目的及宗旨。专家组在解释第21条(b)款之目的及宗旨时,似乎并未紧扣“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而是指该条款项下的客观认定问题。进言之,如第21条(b)款(iii)项下“国际关系中的其他情况”首先也是“武装冲突或潜在的武装冲突”,与作为武装冲突的“战争”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样几乎同义反复,第21条(b)款(iii)项只需规定“战时”,即可。
综上专家组关于GATT第20条(b)款(iii)项的解释,一方面将该款项放在(b)款的整体中解释,认为“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涵盖(b)款三项的共性,都具有“国防或军事利益,或维持法律或公共秩序的利益”,一方面强调(b)款引言“其认为”针对每一项而言,必须满足每一项的要求方可成立,而(iii)项首先须与武装冲突或潜在武装冲突有关。30该案专家组认定俄罗斯援引安全例外的情况包括2014年3月至2016年底乌克兰与俄边境接壤的东部地区武装冲突构成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同前注⑲,WT/DS512/R,para.7.123.
(二)“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解释含义之二“高度紧张或危机”
沙特知识产权案所解释的TRIPS第73条本身与GATT第21条完全相同,但涉及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因而条约解释的语境不同于俄罗斯过境案。该案起由是近年来沙特及其他海湾地区部分国家与卡塔尔的关系恶化,直至2017年6月沙特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及领事关系,关闭与卡塔尔有关所有陆海空通道,禁止卡塔尔国民进入沙特。卡塔尔诉称沙特同时禁止总部设在卡塔尔的一家全球性体育娱乐公司(beIN)继续在沙特从事该公司拥有专有转播权的体育赛事广播业务,并允许沙特本地一家广播公司(beoutQ)未经许可广播beIN的所有体育赛事,构成TRIPS第61条下“具有商业规模的蓄意盗版”而不采取任何刑事措施。沙特虽未明确以安全例外为该盗版行为抗辩,但辩称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等全面措施是在国际关系中紧急情况下采取必要的安全例外措施。实际上,此类盗版行为是实施这些措施之后发生的。因此,专家组认为一旦认定盗版行为存在,沙特也没有适用相应的刑事程序和刑罚,就应根据沙特为其全面措施抗辩所援引的安全例外,分析此类不适用TRIPS第61条的刑事措施是否属于TRIPS第73条(b)款(iii)项的安全例外。31该案专家组最终裁定沙特对于beoutQ商业规模的盗版行为不采取任何刑事程序和刑罚违反TRIPS第61条,并与沙特断绝与卡塔尔外交等关系而终止或阻止与卡塔尔国民有任何交往的安全例外措施无关。同前注⑲,WT/DS567/R,paras.7.294.
该案专家组以俄罗斯过境案为指导,阐明了评估援引TRIPS第73条(b)款(iii)项的四步骤:1. 是否确实存在该款项下“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2. 是否“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动”;3. 援引安全例外的一方是否形成相关“根本安全利益”并足以能够判断所采取的行动与之相关性;4. 所采取的行动对于保护紧急情况下的根本安全利益是否必要。32同前注⑱,WT/DS567/R,paras.7.242.下文限于评析专家组对第一步骤中有关“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的条约解释。
该案专家组基于俄罗斯过境案对“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的条约解释,即,包含“武装冲突或潜在的武装冲突”,或“高度紧张或危机”,或“一个国家内或周边普遍的不稳定状态”,认为沙特援引安全例外的“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属于“高度紧张或危机”。33同前注⑱,WT/DS567/R,paras.7.257.专家组同意沙特主张WTO某成员断绝与另一成员的所有外交及经济关系可视为“存在国际关系中紧急情况的国家最终表示”,并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VCLT第63条“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的评注为依据,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单边和自由裁量的行动,通常是派出国与接受国关系出现严重危机时采取的最后手段”。34同前注⑱,WT/DS567/R,paras.7.260.该案专家组还认为应将这一“高度紧张或危机”放在沙特断绝与卡塔尔外交及其他关系的背景下考察,即,沙特一再声称卡塔尔“破坏地区稳定与安全”,而卡塔尔强烈拒绝此类指控。专家组表示对双方此类争执不持任何立场,只是认为“这本身反映了与安全利益有关的高度紧张或危机的情况”。35同前注⑱,WT/DS567/R,paras.7.263.
值得留意,沙特知识产权案专家组对“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含义与其说是条约解释,不如说是对俄罗斯过境案有关条约解释用语的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将当事方之间“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作为体现国家间关系“高度紧张或危机”的含义所在。问题在于:“高度紧急或危机”用语本身不是安全例外条款的条约用语,而是先前专家组的条约解释用语。这种类似遵循先例的做法,在条约解释的国际法实践中十分普遍,也是保持同类案件对相同条约款项的解释“判理稳定性”36参见前注⑳,第106页。之习惯做法。尤其是俄罗斯过境案专家组报告未经上诉而通过后,其条约解释的判理指导嗣后专家组作出进一步解释,充分体现了当前在WTO争端解决上诉机构无法运行的情况下,已通过的专家组报告具有很强的类似先例作用。37沙特虽对专家组报告提起上诉,但并不涉及专家组对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这表明该解释已得到当事方的认可。参见沙特上诉通知,Notification of an Appeal, WT/DS567/7, 30 July 2020.
还应进一步留意,沙特知识产权案不存在俄罗斯过境案中的武装冲突情况,因而不必涉及上文提及将“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首先解释为“武装冲突或潜在武装冲突”,会产生与当代武装冲突法包含战争的含义重叠问题。但是,“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下“高度紧张或危机”不限于断绝外交关系等情况,因而如何进一步解释安全例外条款,尤其是“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国际法问题。
(三)全球贸易战的背景下安全例外条款解释问题
上述两起案件的专家组在当前全球贸易战的背景下对国际贸易条约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具有特殊意义。两起案件本身与贸易战没有任何关系。俄罗斯过境案是由于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恶化,尤其是克里米亚公投并入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地区武装冲突,导致美国、欧盟等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与俄罗斯的反制裁,包括俄罗斯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乌克兰货物经由俄罗斯公路和铁路过境至哈萨克斯坦等国而引起的贸易争端。沙特知识产权案则是在中东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因部分国家与卡塔尔断交引起的贸易相关知识产权争端。
然而,2018年3月美国以安全例外为由对进口至美国的钢铝制品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中国率先向WTO起诉美国实质上是采取违反WTO规则的保障措施。38同前注⑲。美国辩称:“国家安全是政治问题,不属于WTO争端解决的事项。每一个WTO成员均有权自己决定对于其重大安全利益的保护必要性,如同这体现于1994年GATT第21条规定。”39US-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China), DS544/2, 17 April 2018.在专家组审理俄罗斯过境案时,美国作为第三方强调安全例外的自裁权是“GATT缔约方和WTO成员反复承认的‘固有权利’。”40同前注⑱,WT/DS512/R,para.7.51.尽管该案专家组通过条约解释,已明确在WTO的国际贸易条约下安全例外问题一旦进入争端解决程序,就不是其成员自行主观判定的事项,而应由专家组基于个案事实的客观评估加以认定,但是,美国作为沙特知识产权案的第三方,再次提出TRIPS“第73条(b)款是一项自裁性条款”。41同前注⑱,WT/DS567/R,para.7.238.沙特知识产权案专家组重申认定安全例外属于适用DSU一般规则与程序的专家组管辖权范围。这对WTO争端解决机构处理此类贸易争端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具有重大意义。
值得进一步探析的是“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究竟涵盖哪些情况?俄罗斯过境案专家组的解释至少涵盖三种情况:“武装冲突或潜在的武装冲突”,或“高度紧张或危机”,或“一个国家内或周边普遍的不稳定状态”。沙特知识产权案专家组又将“高度紧张或危机”进一步解释为至少涵盖国家间“断绝外交与领事关系”。如上文评析时认为,从演进的条约解释来看,“武装冲突或潜在的武装冲突”的涵义与如今武装冲突法涵盖战争的情况重叠,有悖条约有效解释规则。“高度紧张或危机”涵义宽泛,本身不是条约用语,嗣后专家组按照类似遵循先例的做法,将先前专家组解释延伸的用语当作进一步解释的基础。已故著名WTO法学者杰克逊教授曾担忧安全例外条款“这一规定的表述是如此宽泛、自我判断和含糊,以致显然会被滥用。”42同前注⑰,第256页。晚近WTO成员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接二连三地援引安全例外条款,作为其违反WTO法规则的正当性抗辩理由。美国根据国内法,在对外经贸关系中滥用安全例外,对其他WTO成员的进口产品单边加征关税,或封杀他国企业的产品或投资等,更是无所不及。
目前在全球贸易战的背景下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涉及GATT第21条(b)款(iii)项下“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的两个关联问题。其一,在中国等诉美国钢铝制品案中,美国声称的安全例外是否构成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或更具体地说,“高度紧张或危机”?其二,美国以所谓不公平贸易的301调查结果为由对数以千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实施加征关税的单边贸易措施。对于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中国不得不被迫进行必要反击。这样的贸易战是否属于该第21(b)(iii)条下“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以致中国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以维护自己的重大安全利益?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美国辩称:根据其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节采取加征关税措施“对于调整威胁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钢铝制品进口是必要的。国家安全问题是不属于由WTO争端解决来审查或能够处理的政治问题。WTO各成员保留自己决定那些它所认为有必要保护基本安全利益,正如GATT第21条所体现的那样。”43US-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China), DS544/2, 17 April 2018.美国明确援引了该第21条作为其违反WTO规则加征关税的安全例外依据。如果参照俄罗斯过境案的解释,所谓“威胁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钢铝制品进口”显然与战争无关,也不属于“国际关系中紧急情况”的“武装冲突或潜在的武装冲突”,或“高度紧张或危机”,或“一个国家内或周边普遍的不稳定状态”,而是与美国钢铝制品产业因进口过多而受损有关。中国等诸多WTO成员因而诉告美国假借国家安全例外,实质是针对短时期内某类产品进口激增而采取的保障措施。正如杰克逊教授曾比喻:如果滥用安全例外,“甚至有人提出保留制鞋行业作为例外,因为军队必须有鞋穿。”44同前注⑰,第256页。如将因进口过多而影响其产业等经济安全也作为“国际关系中紧急情况”,那么在俄罗斯过境案所列三种情况之外,或者沙特知识产权案所解释的“高度紧张或危机”涵盖“断绝外交与领事关系”之外,至少还要增加“国家经济安全”这一更加宽泛的情况,从而极大地扩展安全例外的范围。从条约解释的角度看,一国的产业存废或发展程度主要不是国际关系的问题。国际关系的通常涵义是在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中的主权国家间关系。在GATT第21条(b)款的上下文中,“紧急情况”一般指的是危险或冲突的情况,未曾遇见的起因并要求采取紧急行动的情况。美国钢铝制品产业的相对停滞或减弱是其本身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与2002年美国对进口钢材采取保障措施时碰到其钢铁产业衰退的情况,如出一辙。当时欧盟为主包括中国等多个WTO成员诉告美国违反WTO保障措施的规则,并胜诉。45参见杨国华:《中国入世第一案: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研究》,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如今美国打着安全例外的旗号,实际上采取保障措施。在GATT包括保障措施的条款等上下文看,美国单方加征进口钢铝制品关税的所谓国家安全例外难以归入第21条(b)款(iii)项的“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美国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可归入“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涵盖国际关系的“高度紧张或危机”。从演进的条约解释看,GATT第21条(b)款(iii)项的“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的通常涵义应该是相对于“战时”,也就是当代武装冲突法所涵盖的两个或数个国家之间,或一国内部的武装冲突等军事行动而言,和平条件下的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如断绝外交与领事关系)、经济(如所谓贸易战之类特别重大的经贸摩擦)等方面突发事件,或邻国突发重大事变等危及本国安全的情况。因此,中国面临美国强加的史无前例、超大规模的双边贸易战,两国经贸关系处于“高度紧张或危机”的紧急状态,为了维护自身经济方面的国家安全,只得对来自美国的进口产品采取实质等同的加征关税措施。这是真正的安全例外措施。或许正是如此,美国迄今未在WTO诉告中国采取此类关税措施违反WTO规则。46相比之下,对于中国等反制美国加征钢铝制品关税而采取WTO《保障措施协定》第8条第2款项下的措施,美国在WTO提起争端解决。参见China-Additional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T/DS558, 16 July 2018. 同类案件还有美国诉告欧盟等,WT/DS557, 559, 560, 561, 566, 585. 这些案件目前均处于专家组审理阶段。
简言之,相比泛泛而论的“国家经济安全”,“贸易战”涉及国际经贸关系,构成“高度紧张或危机”的情况。因此,进一步解释GATT第21条(b)款(iii)项的“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至少可增加诸如中美“贸易战”此类情况。诚然,美国并未就此启动涉及条约解释的争端解决,这只是本文的假设性解释。但是,中国等诉告美国钢铝制品案的专家组将无法回避解释产业相关“国家经济安全”是否构成“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47该案原定在2020年底前完成专家组审理。参见US-Steel and Aluminium Products (China), DS544/10, 10 September 2019.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 国际投资协定中安全例外的解释问题
(一)国际投资协定中安全例外条款的“自裁性”
由于阿根廷国内经济危机导致政府颁布《紧急状态法》等相关措施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在2000年之后有数十起有关投资争端仲裁案件,48自2001年Enron Creditors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3起,截止2019年12月,有57起诉告阿根廷政府的投资争端仲裁案,参见联合国贸发会议官网: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country/8/argentina,2020年9月8日访问。其中不乏涉及BITs安全例外条款的案件。如,安然公司诉阿根廷案所涉阿根廷与美国BIT第11条的解释。该第11条规定:“本条约不得排除缔约任何一方适用必要措施以维持公共秩序,履行有关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或安全的义务,或保护自己基本安全利益。”49转引自上注48,ARB/01/3,para.323.该案仲裁庭表示在审理中对于该第11条的讨论显得特别复杂,除了当事双方提出了各自许多主张,该仲裁庭还听取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法律意见。
关于安全例外是否为“自裁性”条款,阿根廷认为美国对此一贯持肯定立场,基于BITs的互惠性,阿根廷也应从相同的理解中受惠,也就是说,可以自行判断采取应对国内经济危机以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的必要措施。该案的外国投资者认为如将安全例外解释为“自裁性”条款,“将创设条约下义务的宽泛例外,并削弱此类条约之目的及宗旨。”50同前注48,ARB/01/3,para.330.该案仲裁庭倾向于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认为:“首先必须关注该条约之目的及宗旨,作为一般的立场,是适用于经济困难情况时也要求保护国际保障的受益者权利。在这一范围,任何导致摆脱既定义务的解释均难以与该目的及宗旨相吻合。因而必需采取限制解释。在承认允许将经济紧急状况纳入该第11条上下文的解释同时,将该条款解释为自裁性条款肯定与该条约之目的及宗旨相悖。实际上,该条约会被失去其任何实体意义。”51同前注48,ARB/01/3,para.332.从条约解释角度看,该案仲裁庭基于条约之目的及宗旨解释涉案BITs第11条,并不完全符合VCLT第31条解释通则所要求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应在其上下文中兼顾条约之目的及宗旨,加以善意解释。该案仲裁庭除了通过上述限制解释而强调涉案BIT的安全例外条款不应由投资东道国“自裁”,没有对该第11条作更多的解释。
正是因为该案仲裁庭一味偏向外国投资者,所以阿根廷不服该案裁决,尤其是对第11条的解释,请求撤销该案裁决。阿根廷诉称:“即便该第11条不是自裁的,该案仲裁庭也未适用涉案BIT第11条,因为它未作实体性审议,而是简单地以有关习惯国际法对必要性分析代替了该第11条,从而有悖于条约的有效解释规则。”52Enron Creditors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3 (Annulment Proceeding), 26 January 2010, para.353(e).审理该请求撤销的临时委员会认为该案仲裁庭对涉案BIT第11条有关“必要措施”的解释不充分,构成可撤销裁决的“未充分阐明理由”这一错误。53根据《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ICSID)第52条(1)款(e)项,“裁决未陈述其依据的理由”,可予以撤销。参见Antonio R. Parra, the History of ICSI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60.该委员会针对仲裁庭要求阿根廷的安全例外抗辩须满足“必要措施”是“国家保障其陷入严重和迫在眉睫的灾难之根本利益的唯一方法”,且在论证阿根廷采取的措施并非“唯一方法”时,未充分阐明理由。比如,该仲裁庭没有充分阐释“唯一方法”的含义。“该表述有多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潜在的字面解释为在诸如本案的情况下,阿根廷所依赖的必要性原则是它确实不可能采取其他措施应对经济危机。”54同前注52,para.369.诚然,一国政府面临经济危机可能有多种应对方法,然而,这并不意味这就是正确的解释。政府可能考虑有必要采取不违反或最少违反其国际义务的措施,而这可能正是“唯一方法”。再如,可替代的方法是否有效,等等。该案仲裁庭过于依赖支持外国投资者的专家有关阿根廷采取的并非“唯一方法”意见,而径直作出相关认定。该委员会通过多方面分析,指出该案仲裁庭没有充分陈述理由,决定撤销该裁决。55同前注52,para.395.
(二)国际投资协定中安全例外条款的“基本安全利益”
CMS煤气输送公司诉阿根廷案也涉及阿根廷与美国BIT第11条的解释。在该案中,阿根廷政府首先否认该公司的投资损失与其经济管制措施有关,其次作为可替代的实体性抗辩理由,援引了应对当时经济危机的《紧急状态法》,“作为豁免国际法与条约项下责任的依据”。56CMS Gas Transmission Co.,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May 12, 2005, para.99.阿根廷政府认为该危机所涉经济利益构成“严重和迫在眉睫的灾难所威胁的国家基本利益”,“《紧急状态法》出台的唯一目的在于控制阿根廷面临的经济社会崩溃的混乱局势。基于该危机的必要性应排除政府采取措施的非法性,尤其是不负赔偿责任。”57同上注56,paras.305-306.
首先,该案仲裁庭认为:涉案BIT“显然旨在保护经济困难或政府采取具有负面作用的措施之情形下的投资。然而,问题在于这些经济困难可能严重到什么地步。严重危机不一定等于完全崩溃的情况。”58同前注56,para.353.这并不是解释“基本安全利益”本身,而是解释在什么情况下必须采取例外措施保护基本安全利益。换言之,基本安全利益取决于经济困难的程度,如果到了“完全崩溃”的地步,一个国家难以维持生存,那就涉及基本安全利益了。“在缺少此类根本性严重条件的情况下,很清楚,条约[保护投资]将优先于任何[例外措施]必要性的抗辩。”59同前注56,para.354.根据该仲裁庭的评估,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尚未到“完全的经济及社会崩溃”,因此,还缺乏援引涉案BIT安全例外条款的理由。其次,该仲裁庭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国际责任》条款第25条第1款(a)项为依据,认为一国仅在应对国家基本利益处于严重迫切危险的措施为“唯一”时,方可豁免由此违反其国际义务的责任。在本案“并没有显示相应义务存在的国家基本利益或国际社会作为整体的利益受到损害。”60同前注56,para.358.再次,该案仲裁庭认为涉案BIT第11条虽未提及任何种类的经济危机或困难,但也不能排除该条款包含主要的经济危机。这实际上间接地解释了该条款“基本安全利益”包括经济危机所触及的国家基本安全。“如果基本安全利益的概念限于直接的政治和国家安全关注,尤其具有国际特点。并排除其他利益,比如主要的经济紧急状况,这会导致对该第11条的失衡理解。”61同前注56,para.360.在承认基本安全利益涵盖“主要的经济紧急情况”的基础上,该案仲裁庭认为关键在于如何认定经济危机的程度以及构成可采取例外措施的基本安全利益,并最终否定阿根廷的抗辩。总之,涉案安全例外条款下基本安全利益虽包括经济危机,但该危机须达到国内经济崩溃的地位方可采取例外措施,且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方法。
值得留意,阿根廷对该案裁决不服,请求予以撤销,理由包括该裁决没有充分陈述涉案安全例外措施未满足“唯一”性要求。审理该撤销请求的临时委员会承认:“该仲裁庭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第11条的决定之进一步理由。……在本委员会看来,虽然该裁决的[说理]动机可以更清楚一些,但是,仔细的读者可以理解该仲裁庭隐含的理由”。62CMS Gas Transmission Co., v.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8(Annulment Proceeding),September 25, 2007, paras. 123,127.与前案撤销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复审不同,该撤销委员会显然对此敷衍了事,偏袒外国投资者。
(三)比较国际贸易协定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判理
比较国际贸易、投资协定的安全例外条款及其解释,可见,虽然有关条款均有“其认为”或“不得排除”等具有“自裁性”含义的用语,且上文所分析的案例都反映美国(虽都不是涉案当事方)主张适用安全例外条款的“自裁性”,但是,WTO国际贸易协定和至少本文分析所涉美国与阿根廷BIT的安全例外条款经解释均不具有“自裁性”。值得比较的是其不同的解释判理。
比如,俄罗斯过境案专家组将GATT第21条(b)款引言句的“其认为”与涉案(iii)项的“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作为整体解释,认为采取安全例外措施的成员主观上“其认为”的前提是发生了需要争端解决专家组经过客观评估,加以认定的此类紧急情况。由此推理,该案专家组首先解释什么是此类紧急情况,并将解释澄清的此类情况中的第一类“武装冲突或潜在的武装冲突”适用于涉案事实,认定在该案中确实存在此类紧急情况;然后,再回到解释“其认为”保护的“基本国家安全利益”含义及其采取措施的必要性,并认为援引安全例外的成员有权对此判断,但应秉承善意,避免将安全例外“作为规避其义务的手段”。63同前注⑱,WT/DS512/R,para.7.133.沙特知识产权案将此类措施的“必要性”解释为需满足援引安全例外的一方是否形成相关“根本安全利益”并足以能够判断所采取的行动与之相关性。
再如,安然公司诉阿根廷案在承认允许将经济紧急状况纳入涉案BIT第11条上下文的解释同时,强调将该条款解释为自裁性条款肯定与该条约之目的及宗旨相悖。在该案仲裁庭看来,BITs目的就是保护外国投资者,如听任东道国自行判断可否采取安全例外措施,就难以实现该目的。CMS煤气输送公司诉阿根廷案从另一角度驳回了阿根廷主张的安全例外条款“自裁性”,认为东道国可自行判断和采取相关措施,但是,“如果此类措施的合法性在国际法庭受到质疑,那么就不是涉案国家,而是有管辖权的国际法庭决定必要性抗辩可否排除非法性。”64同前注56,para.373.这种看法已超出了条约解释范畴,认为一旦进入国际争端解决程序,就不存在安全例外条款的“自裁性”。至少这两起国际投资仲裁庭站在外国投资者一边,都没有对安全例外条款“自裁性”进行符合条约解释惯例的充分解释。
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国际经贸协定的安全例外条款“自裁性”,国际经贸争端的否定性实践表明相关的争端解决专家组或仲裁庭均拥有管辖权,已是不争的现实。比较而言,国际贸易协定的安全例外条款比较完备,包括“其认为”采取必要措施的“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通过解释延伸为“武装冲突或潜在的武装冲突”“高度紧张或危机”和“一个国家内或周边普遍的不稳定状态”,以及援引安全例外的一方须形成相关“根本安全利益”并足以能够判断所采取的行动与之相关性。也正是这样的缘故,如今一些BITs的安全例外条款,如上文提及日本与乌兹别克斯坦BIT,更接近于国际贸易协定安全例外条款的共同模式。
总括全文,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条约法上的安全例外观念出自于一般国际法上的“自我保全”原则;《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条款是条约法上第一次明确规定相对于禁止使用武力原则而言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国际经贸条约方面,GATT第21条是最初的安全例外条款,并发展为WTO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贸易相关知识产权三大实体性条约共同的安全例外条款;国际投资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从隶属公共秩序例外逐步延伸并发展为单独的条款,与国际贸易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趋同,但尚无统一表述。国际经贸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在有关争端解决的适用中经过条约解释,大致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援引一方主张自行判断可否采取安全例外措施的“自裁性”已被否定;安全例外的抗辩一方可自行决定采取相关措施,但一旦进入国际争端解决程序,其必要性以及“基本安全利益”的认定则不具有“自裁性”;国际贸易条约安全例外条款中有关“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涵盖的范围有所扩大,国际投资条约安全例外条款中的“基本安全利益”的界定倾向于相对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而言,限于因经济危机导致国家经济社会崩溃此类极端情况引起的东道国安全利益。对于我国目前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相关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与解释,以及今后可能参与国际投资仲裁涉及的安全例外问题而言,65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2012年9月9日签署,2014年10月1日生效)第33条第5款规定了安全例外。期待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