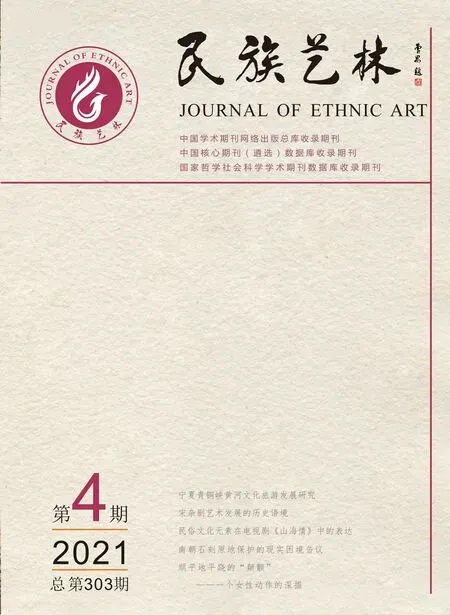宋杂剧艺术发展的历史语境
张 彬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一、宋代商品经济的活跃
唐、宋两个朝代的都城建制各具特色,并且差异显著,如唐代的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城建制规整有序,宫城、皇城、街坊与两市等的功能分区明确,里坊如棋盘式,整齐美观。并且里坊间的道路通畅,交通便利,犹如“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它与宋人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熙熙攘攘的城市景观差异显著,这一差异成为唐宋城市转型的典型景观之一。宋代都城建制是现代都城建制的滥觞,临街设店,生活烟火气息浓郁。伴随着唐宋的城市转型,唐代后期严格的坊市制开始发生变化,官方在管理上逐渐松弛。发展至北宋中期,坊市制便彻底崩溃,此事件大概发生在宋仁宗中期以后。从此,坊市之名,多失标榜,宋人也不再像唐人那样称呼它,并且夜晚的城市中再也听不到官吏巡街敲鼓的声音,金吾卫这一职位从此废除。宋代城市在此基础上,市民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市行的数量不断增加,充斥大街小巷,而且夜市开放,通宵达旦均可看到宋代形形色色不同人群的身影。就连东京的主街(御街),也变得人群熙熙攘攘,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发展壮大。有宋一代,市民构成了城市中日常生活的主体,城市空间的变化以及政府政策对城市中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艺术领域,宋代诸多的通俗文艺的种类逐渐增加。
宋以前,坊市的开闭时间均有政府特定的规定,其中夜市更是被政府所严禁。入宋后,宋人的生活空间进一步扩大,夜市日益兴旺,宋人可以通宵达旦地吃喝玩乐,不受限制。宋建国初,乾德三年(965 年),宋太祖下令开封府夜市不得禁止,可以开放到三鼓。此后,夜市的规模和开放时间不断增加。在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也有大量关于东京夜市景观的记载,如潘楼东街巷“直南抵太庙街、高阳正店,夜市尤盛”,马行街北诸医铺“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甚至有的地方“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1]。宋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三中,专门记录了杭州的“夜市”景观,多次提及商贩在中瓦前买卖交易的场景,从侧面我们可知宋代瓦舍勾栏中充满商业味道的娱乐表演一定是热闹非凡。由此可见,商品经济活跃,夜市发展,促使宋人的生活空间更加多元。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类似的描写,大意是说太平的日子持续的时间很久,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儿童学习礼乐,而且年纪大的老者不知道打仗的兵器是什么样。一年四季的节日中充满了欢声笑语,在城市的柳陌花衢和茶坊酒肆中,经常是歌舞升平,热闹非凡。在东京的市场上,人们可以买到各地的珍宝,他们的衣食住行奢侈华丽。由此可见,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十分活跃。
商品经济的活跃,为宋代娱乐行业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杂剧表演等伎艺由宫廷走向了民间,消费对象由统治者转向庞大的市民阶层,其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古代剧场在宋代的正式确立。剧场中瓦舍勾栏的兴起,使宋杂剧艺术与市民观众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同时,瓦舍勾栏中的演出具有商业性质,它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成正比。宋杂剧艺人的收入来源是宋代的有闲、有钱阶层,他们通常是瓦舍勾栏中的常客,瓦舍是宋元时期在城镇里建筑的商业性剧场,它里面设置的演出场所称作勾栏,瓦舍是宋代城市文化娱乐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何为瓦舍呢?这一问题恐怕宋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条记载:“瓦舍者,谓之‘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2]笔者认为,瓦子里设置的演出场所称勾栏,瓦舍也经常与勾栏并称瓦舍勾栏,它是宋代市民娱乐的中心,是专门供艺人表演的固定场所,杂剧艺人占据其中的一大部分。宋代的瓦舍与唐代所受限制的戏场相比,在管理制度、营业时间、观众规模等方面都更加开放,它是“一种在市集上供市民常年冶游的大型游艺场地,其营业时间等是不受限制的”[3]。宋杂剧演出的场面十分壮观,经常是无论风雨寒暑,在大小瓦舍勾栏中观看的人群众多,这种宏大的场面每天都在上演。由此也可以看出,宋杂剧在宋代多样的娱乐行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两宋时期的文献中关于对戏剧艺人的演出的固定场所瓦子有多处记载,如在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有桑家瓦子、中瓦、里瓦、朱家桥瓦子、新门瓦子、保康门瓦子、州北瓦子、州西瓦子等瓦舍,“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4],其中的丁先现是北宋后期宫廷中的表演艺人,老年时离开内宫在瓦舍中卖艺谋生。东京市民每天都在此逍遥快活,而且不知不觉就从早上到了晚上。东京相国寺被宋人称为瓦市,其中也有优戏演出。如宋王安石《相国寺启同天节道场行香院观戏者》诗曰:“侏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贱。心知本自同,所以无欣怨。”[5]南宋时期,杭州瓦舍的规模数量进一步扩大,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6]。宋西湖老人在《西湖老人繁盛录》中记载城外就有20 座瓦子。除此之外尚有独勾栏瓦市,位置稍远,一般在夜晚演出。在深冬冷月,杭州市民没有社火表演观看的时候,就会去瓦市中消遣快活。除此之外,当时在南宋的其他城市中,如镇江府、建康府、湖州、绍兴府等地均有瓦子的记载。如明正德年间修《松江府志》记载:“平康坊,中亭桥西,有瓦市在焉。”[7]清同治年间修《湖州府志》记载:“波斯巷(南瓦)、北瓦子巷。”[8]在《乌青镇志》中记载:“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9]供艺人表演的瓦子,在文献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勾栏是瓦舍中专门化的演出场所,其中设立戏台和神楼,它与之前唐代的看棚不同,专门指瓦舍中设置的演出棚,也就是“俳优棚曰钩栏”。这种勾栏演出棚就是宋代的商业剧场。它四周闭合,上部封顶,建造形制是全封闭的,排除季节、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营造了适宜于观众的观演环境。廖奔先生说:“在勾栏内部的观演空间里,一面建有表演用的专门场地——高出地面的戏台,其他面则环绕从里到外逐层加高的观众座席……勾栏实行商业化的演出方式正式向观众进行售票。”[10]瓦舍勾栏在娱人的同时,也带有浓浓的商业味道,除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外,宋代也有一大批杂剧艺人在城市中四处流动,临时演出,宋人称其为“路岐人”或者“打野呵”(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由此可见宋杂剧表演艺人的队伍是十分庞大的。
商品经济极度活跃,致使宋代习乐风气炙热,大批男女进入娱乐行业,在瓦舍勾栏中进行商业演出。瓦舍勾栏中不仅有像杨惜、丁都赛、薛子大、薛子小等后来者不足数的表演技艺高超的民间杂剧艺人,同时也会有像老年时离开宫廷的丁先现等宫廷杂剧艺人。他们不仅表演技艺高超,同时文化水平也很高,舞文弄墨样样精通。例如文献中记载的表演技艺高超的杂剧女艺人丁都赛,其形象在国家博物馆和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馆藏砖雕中均可看到。她风姿绰约,双手交于胸前作示敬状。当她还活跃在汴京的瓦舍勾栏舞台上演出时,她的形象已经被做成砖雕,镶嵌在二百里地之外的偃师地区。由于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宋代墓葬中经常出现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丁都赛形象在宋人墓葬中的“提前”出现,说明她不仅表演技艺高超,声名远播,同时也可以看出宋人对杂剧艺术的狂热追求,堪称现代“追星族”之滥觞。
由此可见,宵禁制废弛,坊市制瓦解,导致宋代商品经济极度活跃,出现了一大批有闲、有钱阶级,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市民文化蓬勃兴起,“中国传统社会的市民文化,是到了宋代才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是从宋朝的瓦舍勾栏与市井间生长出来的”[11]。瓦舍勾栏作为宋代商品经济活跃的外在表现之一,伴随着其数量的增多及空间上分布的广泛,从侧面也反映出宋杂剧艺术已经成为宋人日常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人最喜爱的文化娱乐方式之一。
二、宋人对杂剧的喜爱
夜禁废弛,坊制破坏,这种现象加速了宋代城市的繁荣发展与通俗文艺的大量出现,市民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的“市民”已经不是指单一的工商业者,而是囊括更加广泛的社会阶层,如城市工商业者、歌妓、表演艺人、小商贩等在籍与不在籍的各个社会阶层。
上自皇帝,下及平民,人们都醉心于对世俗欢乐的享受中,对杂剧艺术这种通俗文艺更是十分喜爱。笔者将从皇帝、官僚士大夫、一般文人群体、市民群体等进一步分析宋代各个阶层对杂剧的喜爱。
宋人对杂剧的喜爱主要是因为杂剧自身的艺术特色,彰显出无穷的魅力。宋杂剧演出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即是副末色与副净色的谐谑之语,即“诨”,滑稽调笑的表演形式,给宋人带来了无穷的快乐,这种语言上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宋人。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宋辽金三朝之滑稽剧……宋人亦谓之杂剧,或谓之杂戏……宋人杂剧,故纯以诙谐为主。”[12]在宋人的许多文献记载中,均有对杂剧艺术特色“诨”的记载,如宋杨万里《诚斋诗话》记载:“东坡尝宴客,俳优者作伎万方,终不笑。一优突出,用棒痛打作伎者曰:‘内翰不笑,汝犹称良优乎?’对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盖优人用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云:‘非不治也,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见子由五世孙奉新县尉懋说。”[13]杂居艺人把苏东坡的作品当作演出过程中的素材,使严肃的苏东坡哈哈大笑。可见,在演出过程中,杂剧艺人的素材来源广泛,并且他们非常聪明,会十分巧妙地制造演出中的笑料,这种贴近生活的表演,增强了杂剧艺术表演时的张力。
宋杂剧的表演形式以滑稽调笑为主,从北宋的两段式发展到南宋的三段式表演体制,正杂剧都是演出中的核心部分。其正杂剧演出的目的在于达到滑稽逗乐的艺术效果,引人发笑,增强宋杂剧表演艺术的张力。中国戏剧作为中国艺术中俗文化的代表之一,自从它正式诞生以后,素材的选择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片段,这些片段充满世俗气息,其中的插科打诨是杂剧表演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后世戏剧艺术表演中的滑稽调笑表演部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宋史·石守信传》中,记载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太祖与石守信的一段对话大意是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不如享受人生,多积累钱财、田地、家宅留给子孙。置大量的歌儿舞女,每天在笙歌燕舞中逍遥快活,颐养天年。在君臣的这段对话中,太祖的主要目的是让石守信等人放弃手中的权力,但从侧面也可以看出皇帝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及世俗娱乐文化的提倡。实际上,这也是统治者的一种怀柔政策的具体体现。除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劝慰属下多置歌儿舞女颐养天年外,宋真宗还曾恩赐宰相“细人”[14]。此外,宋代多位皇帝均具有艺术上的才能,如太祖“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音”“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元脱脱等《宋史·帝王本纪》)等。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八记载了仁宗经常在宫中宴饮,温成皇后张氏擅长戏剧表演。仁宗每次观看完表演后,心情大悦,所以她深受宋仁宗的宠爱。宋代的宗室们也表现出了对戏剧的喜爱,赵允迪经常组织男女奴仆在宫中进行戏剧表演。宋代继承了唐、五代宫廷教坊制度,也设置了教坊,《宋史·乐志》十七记载前代有宴乐、清乐、散乐,隶属太常寺。此后,归教坊管理,有立、坐二部伎。宋初,依照旧制,设置教坊,凡四部。宋杂剧艺人归教坊管理,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使、副岁阅杂剧”)主要承担的任务是为皇家和朝廷的各种宴会演奏和表演,为皇室提供耳目之欲。其中杂剧表演在宫廷中的地位很高,因为宫廷乐部中都有杂剧艺人。如宋陈《乐书》卷一百八十六“乐图论·俗部·杂乐·剧戏”条记载:“圣朝戏乐:鼓吹部杂剧员四十二,云韶部杂剧员二十四,钧容直杂剧员四十,亦一时之制也。”[15]宋代教坊内部乐官的职制比唐代复杂,《宋会要·职官二二·教坊》记载得十分详细,国朝凡举办大宴、曲宴,设置都色长、色长、杂剧、板、歌、琵琶、箜篌、笙、筝、筚篥、笛、方响、羯鼓、杖鼓、大鼓、五弦人数不等。另外设置排乐多人,掌撰文字1 人。此外,在宋代散乐中,传学教坊13 部,唯有杂剧是宋代教坊中唯一具有正色地位的部门。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致使有钱又有闲的官僚士大夫也将享受人生视为当然,杂剧艺术自然也是他们最喜爱的娱乐方式之一。宋郊、宋祁兄弟之间的一次对话最能说明问题[16]。其中“歌舞俳优相继”着实令官僚士大夫“忘疲”。此外,他们经常为宫廷杂剧和歌舞演出写作“勾队词”“放队词”,如宋祁《教坊致语》,王禹玉《集英殿秋宴教坊乐语》,苏颂《坤成节集英殿宴教坊词》,苏轼《集英殿秋宴教坊词》《兴龙节集英殿宴教坊词》《紫宸殿正旦教坊词》等。在临安的瓦舍勾栏中也时常能见到士大夫的身影,如中瓦在临安的御街上,它是士大夫们的必游之地。如王安石作为宋代知名的官僚士大夫之一,时常去相国寺观看杂剧演出,看完后做诗《相国寺启向天节道场行香观戏者》。
由于宋代科举制度兴盛,录取人数逐年升高。再加上统治者在建国初期大力提倡读书,此种举措致使宋代受过教育的一般文人群体大量增加,他们对戏剧艺术也是情有独钟。仁宗朝,建州人江沔曾经游历相国寺,与很多书生背靠店柱,观赏倡优表演。士人也经常穿便服,白天到瓦市观赏倡优表演。此外,有些文人还是戏剧剧本的创作者,如南宋温州九山书会的才人们所编的《张协状元》剧本,被称为戏剧艺术的“活化石”,它是目前留存下来的唯一一个完整的南戏剧本也是目前所见现存最早的中国戏曲剧本的始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市民阶层是宋代的新型阶层,构成了宋代社会最庞大的一个群体,是大众娱乐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宋杂剧艺术成为市民群体最喜爱的市井文化中的艺术之一,因为杂剧艺术生于民间,成长于民间,杂剧的题材来源于宋人的日常生活,它是与宋人日常生活关联极为紧密的一种艺术。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使杂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两宋的瓦舍勾栏中,市民群体队伍异常庞大,络绎不绝。北宋东京瓦舍勾栏每天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酒肆瓦市,经常是车水马龙,昼夜笙歌曼舞。从魏晋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的《目连救母》杂剧更是受到了市民阶层的喜欢。北宋时出现的《目连救母》杂剧已经是剧情比较长的连台本戏,可以连续演出七天,观看演出的观众每日成倍增长。南宋临安瓦舍中十三座勾栏更甚,每日的演出数量庞大,文化娱乐景观十分繁荣。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首先,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致使宋人的世俗娱乐生活更加丰富。两宋时期除了东京、临安两地以外,瓦舍勾栏还在其他城市大量出现,这种现象是宋以前的朝代所不曾出现过的,其为宋杂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演出固定场所。其次,宋人自上而下从统治者到市民群体都表现出对杂剧艺术的喜爱,杂剧与宋人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成为宋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并且使它不断发展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虽然影响杂剧在宋代快速发展的原因颇多,但笔者认为宋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宋人对杂剧的喜爱是其快速发展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