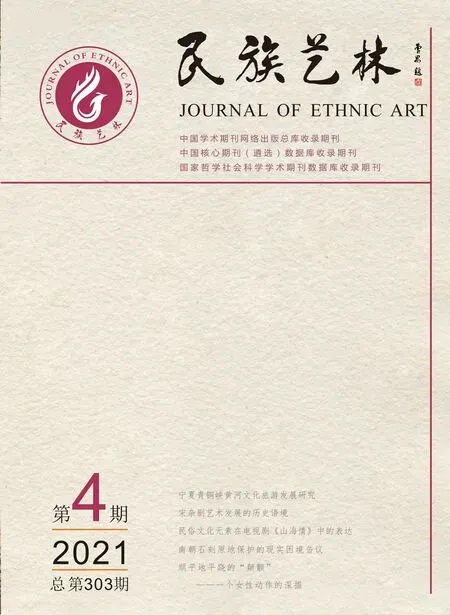越剧艺术表演形式的发展研究
友燕玲
(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000)
一、问题的提出:要发展男女合演
越剧走过百年,在历史的选择和沉淀下相继出现过男子越剧、女子越剧和男女合演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是越剧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表现。除却“男扮女”的特殊形式在时代因素下逐渐成为末流,男女合演及女子越剧在越剧的成熟发展阶段都成为不可缺失的两种艺术形式。诚如越剧老艺术家袁雪芬所说:“男女合演与女演男两种艺术形式都是越剧本身的需要,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男女合演的出现,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越剧的题材,是发展而不是损害了越剧的风格,是增强而不是削弱了越剧的表现能力。”[1]在这一层面语境下反观当前的越剧发展,两种样式的发展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差距,无论是演出团体的实力还是演员队伍的组成,男女合演都略显弱势,而女子越剧追求写意、诗化几乎到达了极致。因此,就越剧艺术本身发展而言,要突破它在这一个百年中的发展,个人认为必须要关注越剧男女合演的形式,并为其发展进行谋划。
从另一层面上说,新时代对文艺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2]。长期以来,观众对于越剧的青睐,多缘自于女子越剧从审美上可以满足人们对细腻、清新、柔美的欣赏需求。“‘女子越剧’的形成是越剧‘清新柔美’审美取向的最终成果”[3],这是当前越剧艺术表现上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势,女子越剧是越剧未来发展主要的艺术形式之一,不可否定、不可打压。在此同时,新时代下艺术表现多元化、人民审美需求多元化的今天,女子越剧的艺术表现力就会显得单薄。在这样的认知下寻求发展,目光必然投向越剧的男女合演。首先,这种发展具有可行性,因为前人已经有了很多探索和实践,只是目前尚存在一些需要破解的难题。其次,男女合演在表现历史事件、重大题材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从而使男女合演能在细腻抒情的基础上增加刚毅的,甚至是恢宏的审美感受。如果说女子越剧是用委婉的方式来表现人情美和人性美,寻求一种更平和的表达方式的话,那么男女合演则让越剧多几分硬朗和豪迈,用振奋、热烈的艺术感受来鼓舞人心、洗涤心灵。新时代下,传统戏曲艺术在不断地探寻如何突破程式束缚,尝试用丰富的手段更多地表现现代生活、歌颂祖国和人民。男女合演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无疑是越剧艺术时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
二、越剧男女合演的历史演变
男女合演目前并非越剧主要表现形式,但在过去的几个历史阶段中有过突出的成绩,展现出了其独有的艺术价值,分别是改良文戏时期、戏改时期、“文革”前后以及改革开放的新越剧时期。以下将从历史的角度详细阐述越剧男女合演的发展阶段,以期寻找可借鉴之发展经验。
(一)雏形:绍兴文戏时期的男女混演
越剧男女合演的雏形最早出现在“绍兴文戏”时期,那时叫“男女混演”[4]。这是女班出现之后、男班还没有完全解散之前,两种形式同时存在的一种交融现象,通过男、女艺人互相搭班的形式表现出来。1925 年就有男班名旦琴素娥,在男班维持不济的情况下加入此时在嘉兴演出的女班。在男女同台的串演过程中,创造了“四工调”,解决了“女唱男调”音域脱节的问题。也有女艺人搭男班演出的情况,1928 年小生屠杏花参加男班,与老生童正初、小丑谢紫云、小旦月月红主演《二堂放子》《玉蜻蜓》等戏。这时的混演,还不是现在男演男、女演女意义上的“男女合演”,要么是男性演员在女班扮演女性角色,要么是女性演员在男班扮演男性角色,但可以说是男女合演的源头或雏形,它打破了“全男班”“全女班”的模式,为越剧男演员和女演员同台演出提供了一种范式,而且在这种混演中不断磨合并解决音乐问题的范本也为后来男女合演在唱腔上的改进提供了经验。当时的男女混演还有另外一种存在方式,男艺人培养自己的女儿学戏,最具代表性的是白玉梅父女。白玉梅原名朱岩铨,早期男班的“四大名旦”之一,他的女儿朱巧凤(艺名小白玉梅)在随班生活期间跟父亲学艺,她12 岁开始就在上海挂牌演出,且经常参与男班演出。小白玉梅与男班老生董正初合作演出《武家坡》,将越剧男腔“正调腔”帮腔的结束句“一吟哦”以及整个乐句“Rue do la sol la do! ”的终止音do 改为低音sol,拓宽了唱调的音域,“一音之差,男腔变成了女腔”[5]。女腔的出现和与男演员同台的演出,标志着男女合演正式登上越剧舞台。尽管这一时期的男女混演没能成为演出的常态,但在全男班和全女班更替中的融合,催生了女腔女调,这在越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说明“男女同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观众认可。
(二)尝试:改良文戏时期的“的笃戏”
再次看到大量男女合演的越剧剧目是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的笃戏”。1942 年,以四明山和三北地区(余姚、慈溪、镇海)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新四军浙东抗日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四明山根据地所在的几个县是越剧最流行、流动越剧戏班较多的地区。为了配合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1943 年文教处决定成立浙东行政公署社会教育行动队,主要任务是对越剧和民间艺术进行改造,编演几个较大型、较完整的剧目,来鼓舞根据地军民的斗志。起初,社教队由部队中爱好家乡戏的嵊州、新昌籍战士和从四明山鲁迅艺术学院抽调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还招聘了一些嵊州男班艺人。后来,社教队发现两支队伍难以满足根据地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他们决定把民间艺人和民间戏班争取过来加以改造,形成强大的宣传力量。1944年11 月社教队吸收了高升舞台整个戏班。1943年到1945 年间,社教队的创作演出建立在“编戏首先想到演给谁看,观众想的是什么,看完戏解决了他们什么问题”[6]的基础上,编写了二十多部反映当地人民斗争生活的现代戏。比如《义薄云天》《生死恨》《英烈缘》《大义灭亲》《桥头烽火》《儿女英雄》等。在演出形式上,实行男女合演,以适应演出现代戏及女演员不多的现实条件。在音乐上,适当吸收了绍剧、武林调、民歌小调和男班早期比较质朴的音调,来表现革命题材的激昂和豪壮气势。两年多的改革演出,不仅起到了鼓舞抗日军民斗志、启发民众觉悟的作用,同时也对越剧实行“男女合演”摸索了一定的经验。可惜的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1945 年社教队被改成鲁迅文工团,并跟随部队北撤,虽然也在山东演出过《北撤余音》《红灯记》等男女合演剧目,但因“水土不服”、没有观众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最后历时三年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男女合演被迫终止。
(三)推行:戏改时期的两地发展
自1951 年全国戏曲界在以“改人、改剧、改戏”为内容的改革背景下,越剧如何来表现现实题材、现实生活,再次沿袭抗日战争时期的“笃戏”的创作方法,实行男女合演。1949 年,袁雪芬在11月13 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越剧当前的问题》一文,文中说:“对于男女合演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今后我们要把现实生活的思想以及伟大的革命过程,都要在舞台上传达出来。我们要演工农兵,如果还是由女孩子扮演男角的话,由于生理上的限制,实在是有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培养男演员来配合。”[7]于是,在袁雪芬的推动下,上海开始积极推进越剧男演员的培养。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演员训练班、上海越剧院学馆、上海越剧团演员训练班相继开办男演员培训班,培养了三批男女合演的演员,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进入男女合演实验剧团,成为上海越剧男女合演的主力。同时,为了能持续推动男女合演的发展,也创作相应的剧目作为演出载体,袁雪芬参与实践,主演了《秋瑾》《火椰村》《祥林嫂》等剧目。
上海男女合演的发展,也推动了浙江等地男女合演的发展。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全省相继有12 个男女合演的越剧团成立。其中最主要的是浙江越剧二团、嘉兴越剧二团和宁波市越剧实验剧团,尤以浙江越剧二团的探索和创造最引人注目。浙江越剧二团的前身是1952 年成立的浙江越剧实验剧团二队,它以文工团员为基础,吸收少数越剧演员和昆曲“传”字辈教师,演出现代戏。男演员田成效、方海如等,女演员姚水娟、薛莺等曾在该团做过演员。在剧目创作上,浙江越剧二团不仅有现代戏《罗汉钱》《未婚妻》《雨前曲》《风雪摆渡》,还创作了清装戏《五姑娘》、传统戏《庵堂认母》。并在戏曲程式上做了尝试,创造了纱巾舞、雨伞舞、草帽舞、手杖舞等,开拓了表现现代生活的手段。在有演员和剧目的充分保证下,浙江越剧二团三进上海演出,渐被观众认可和接受。
(四)停滞:具备现代戏编演优势而得“一花独放”之地位
20 世纪60 年代末到70 年代末,编演现代戏成为全国风潮。这于此时影响力远不如女子越剧的男女合演来说,看似得到良好发展机遇。1964年4 月中旬,“上海所有越剧团体,几乎全都演现代剧”[8],一时间创作排演了近二十部现代题材的剧目。此后,上海、浙江、南京、福建等地原本以女子越剧为主的剧团,也纷纷选调、培养男演员,创作排演现代戏,成为男女合演团。这之后,所有越剧团只演“样板戏”,各大剧团都尝试过用普通话进行念白,并把唱腔设计得更高亢激越,然而语言和音乐上的变革使越剧本身的特点模糊化,剧种辨识度大大降低。为了“把越剧改得还像越剧”,只能从剧本下手,改变最初简单移植、拿来就用的方法,有针对性地修改剧本的唱词符合越剧的格式和韵脚,以此恢复剧种在方言上的特点。同时,在培养演员上,上海越剧团奉命开办演员训练班,培养了四十多名男女演员。“男演员成了应时而走‘红’的‘抢手货’,被同仁谑称为‘男宝贝’”[9]。
当然在1966 至1976 年间,也并不是所有的剧团都能够进行男女合演,很多剧团被整编合并,改制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简称“文宣队”。比如当时宁波地区革命委员会以宁波专区越剧团做班底,抽调宁波市实验越剧团、宁波市甬剧团、宁海平调剧团等五个戏曲团体的一些主要演员和武戏演员,组成了120 人的宁波地区毛泽东文艺宣传队。女小生相继离开舞台,男女合演全面推开,演出了《火椰村》《金沙江畔》《奇袭白虎团》《沙家浜》《海岛女民兵》等剧目。男女合演经历了很长一段在唱腔、音乐上的探索过程。越剧《沙家浜》的音乐经过五次修改才得到观众认可,直到越剧《江姐》的推出,男女合演现代戏才终于在音乐唱腔创作上找到了合适的路子。当时在浙江承担越剧改造任务的只有“浙江越剧改革组”;允许男女合演移植演出“样板戏”的越剧团只有上海越剧团和南京市越剧团。
这一时期的“男女合演”看似繁荣,却是一种在艺术上的停滞不前。首先是创作跟不上,应时现代戏要求上马快,导致剧团只能简单地移植其他剧种的剧目,无法顾及艺术质量;其次是只有少数剧团可以进行男女合演,使艺术上的交流和竞争缺位,这对男女合演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当然,在女子越剧被批为“靡靡之音”的背景下,男女合演的形式保住了越剧剧种的生命,这也足以印证袁雪芬对两种艺术形式互相补充的定论。
(五)再起航:新时期的男女合演
1976 年后,古装戏解禁。自1949-1976 年期间培养的“男女合演”演员们成为舞台的重要力量,在人员和剧目的现有条件下,越剧坚持男女合演,使之在三年间从复苏渐繁荣。其间,上海、浙江的两个重要剧团:上海越剧团和浙江越剧团,不仅演出现代戏,还创作排演历史剧。上海排演的现代戏《祥林嫂》《报童之歌》《忠魂曲》《三月春潮》,浙江排演的现代戏《刑场上的婚礼》《强者之歌》、古装戏《小刀会》《胭脂》等,成功上演,受到观众欢迎,尤其是《报童之歌》《三月春潮》和《胭脂》三部戏于1979年,即建国三十周年参加全国戏曲调演,载誉而归,这是越剧男女合演历史上的一个高峰。
1978 年越剧电影《红楼梦》的上映标志着女子越剧重新登上舞台,此后,男女合演和女子越剧两种形式成为越剧发展的两条腿。80 年代初期,越剧人才新老交替,为了薪火不断,越剧界大力培养戏曲新人,赵志刚、许杰、张伟忠、华渭强等一批男演员成长起来。虽然此时鼓励两种形式共同发展,但浙江“小百花”会演再次开启了女子越剧的全新时代,男女合演一定程度上受到挤压。如宁波1980 年地区越剧团创排《齐王斩后》,创排初期的演员表是男女合演,到了后来录制录像时,“齐王”的演员分上、下半场,男小生和女小生轮流上场,这套录像带不得不说是新时期两种形式地位悄然变化的痕迹记忆。
尽管如此,男女合演依旧在不断探索发展和传播的模式。首先,男女合演也用两条腿走路:演出现代戏和古装剧并存,涌现出《明月何时圆》《巧凤》《金凤与银燕》《红色浪漫》《茶花女》《我的娘姨我的娘》《枫叶如花》《沙漠王子》《家》《被隔离的春天》《第一次亲密接触》等一批现代戏和《乾嘉巨案》《柳玉娘》《一鸟九命》《三篙恨》《孔乙己》《赵氏孤儿》《九斤姑娘》《游子吟》《铜雀台》《早春二月》《玉卿嫂》等古装、清装戏,尤其是《第一次亲密接触》改编自同名小说,青春气息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其次,男女合演采用两种传播和发展方式:舞台演出和电视传播。除了坚持舞台演出,还借助电视这一大众传媒来传播越剧。“1979 年,浙江电视台首开风气,将越剧现代戏《桃子风波》改编成戏曲电视剧”[10]。随后,浙江越剧团影视部于1991 年9 月成立,拍摄了《汉武之恋》《大义夫人》《一鸟九命》《仇家姑娘》《天之骄女》《血溅清风石》《陈三两》《秋瑾》《宫墙柳》《范蠡救子》《乾嘉巨案》等多部戏曲电视剧,全部荣获全国戏曲电视剧评选一、二等奖,其中8 部荣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电视媒介的传播,是智慧的双赢。
三、越剧男女合演艺术形式当下生态分析
越剧男女合演艺术形式在越剧艺术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传承中有发展,但相对于“女子越剧”而言,传承艰难、发展缓慢。其中,艺术生态的不断变化一直起着重要作用。20 世纪初,人们开始用生态学的方法分析社会问题,从根源上反思阻碍社会发展的原因。同理,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越剧的男女合演,研究男女合演当下推进中的困难,寻找更合理的发展方式,不失为一时之途径。以下将从剧本生态、传播和传承生态以及价值生态三方面来做具体阐述。
(一)剧本生态
剧本,乃一剧之本,它是从戏曲扮演角色的本质角度出发的一种内在生态,包括题材、内容、情节、念白、音乐唱腔等因素。首先,唱腔是剧种的灵魂,唱腔的发展决定着剧种的发展。对男女合演来说,制约其发展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突破唱腔上“男调”与“女调”之间的和谐转化,使之更动听。长期以来上海和杭州两地的男女合演剧团不断地进行探索实践,首先是“创造了不少悦耳动听的男女‘二重唱’‘三重唱’,这些唱腔都得到了专家的肯定和越剧观众的喜爱”[11]。其次是在演出实践中总结出的三种解决办法是:“同调异腔”“同腔异调”和“同调同腔”[12]。但这三种方法目前还只能满足唱词结构上“男一段”接“女一段”的模式,而无法很好地解决“男唱一句”接“女唱一句”的紧凑对唱模式中的音乐转调,这往往无法满足戏剧情绪需要情况下的推进和丰满。其难以突破的最主要原因是无论“调”怎么转,依旧是在“女腔”为基本腔调上的转化,而不是在男腔基本调和女腔基本调之间的转化。其次是题材和内容,男女合演在表现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上具有先天的优势,而这两个题材的创作一直以来是当前戏曲创作的难点。但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剧目所能带来的振奋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远是女子越剧难以企及的,时代召唤越剧男女合演的再度辉煌。
(二)传播和传承生态
传播和传承是戏曲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空间,属于外在生态。传播生态体现的是戏曲在横向维度里的发展,折射一种空间特性。电视的传播把男女合演的生态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传播学认为,大众传媒在迅速而有效地满足社会的共同需求方面有着难以匹敌的力量,尤其是电视传媒[13]。电视能更多地展现现实生活、体现现代思想、展示时代精神,以此来满足电视受众的共同需求,并在其产生到发展的一个世纪中成为世界第一传播媒介。当大量优秀的越剧作品用男女合演的形式,通过电视走进千家万户,越剧的传播就突破了剧场限制。那些无法走进剧场的观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越剧;同时为这一时期被“女子越剧”挤压的“男女合演”开辟了另一方舞台,并使之拥有了独特而无以取代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越剧用电视剧的形式传播打破了地域的界限。越剧作为江南地域文化的代表,在借力现代传媒的过程中,跨出了江南的地域,让西北和东北的观众也能欣赏到江南艺术,感受江南文化。电视以一种更为随和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拓宽了越剧审美接受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了越剧的影响力。不过好景不长,进入21 世纪后,互联网的出现使电视传媒也渐渐式微,越剧电视片、电视剧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
传承生态体现的则是戏曲在纵向维度里的发展,反映一种时间特性。戏曲的传承分成物质性传承和非物质性传承,其中传承人不仅是艺术和技术的继承载体,更是艺术和技术活态展现的发展载体。长期以来,男女合演的传承在政治外力的帮助下起起落落,但传承人的培养一直没有间断,比如浙江越剧团现在男演员已经培养到第七代,并且近两年为了培养年轻演员还专门复排了历史剧《天之骄女》,创排了新编戏《游子吟》。尽管艰难,尚有一脉传承。
(三)价值生态
价值生态由内价值和外价值共同构成。内价值是从业者的需求和受众群体需求之间的关系共同构建的。具体来说是演员在舞台创造过程中实现的职业价值以及受众群体在观看过程中获得的审美享受,二者构建了剧种的存在价值。外价值是不同层次的观众对剧种的不同需求组成,比如普通观众、戏迷观众、学者、官员等对同一场演出所要获取的价值存在多样性特点。不管是内价值还是外价值,都集中体现在剧种以及演出的“被接受”中,传播的价值在于对受众的抵达,因此这种生态可谓是戏曲生产的终极生态。当代的戏曲研究者赵山林在《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一书中提出:“一部中国戏曲史,应当由两条线构成:一是作家对作品的创作史,二是作品的传播史以及观众、读者(包括评论者、研究者)对作品的接受。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戏曲史都是不完全的。”[14]这种接受包括对剧目主题的接受,对音乐唱腔的接受,对演员的接受,对舞台呈现的接受等。越剧男女合演的“痛点”在于对男演员的接受和对唱腔音乐的接受问题。举例来说,越剧男演员的观众接受度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20世纪30 年代后的越剧观众群,他们被“女子越剧”的魅力所征服,一旦看到男性演员出现在台上就毫不客气地喊倒彩,“对男演员的上台和开口唱念,甚至非常反感”[15]。这当中除了存在固有欣赏习惯的问题,还有男女合演初期剧目在男声唱腔上的问题。但到后来出现了《两兄弟》等比较好的剧目时,那些虽不熟悉的男演员的不俗表现,还是让观众渐渐接受了这些舞台上的男演员。就当前而言,戏曲演员流失和“戏校招生”困难是普遍问题,越剧来说,一方面男演员依旧数量不多,另一方面女小生的接受度更广,因此“男女合演”的价值生态依旧不容乐观。
四、推进越剧男女合演艺术形式发展的对策
根据“男女合演”历史演进体现出的艺术发展要求和当前时代背景下“男女合演”发展的迫切性,以及当前“男女合演”的戏剧生态,提出以下四条推进发展的意见。
第一,打造适合的剧目作为推进“男女合演”的载体。优秀的剧目不仅可以吸引观众的目光,更能够将演员推入大众视野,比如文中提到的《两兄弟》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难点在于历史题材和现代题材如何才能赢得观众,历史题材的厚重以及在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矛盾,往往成为受众接受历史题材剧目上的“拦路虎”;而现实题材则要在摆脱现实束缚,达成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统一,才能获得观众喜欢。基于此,提出不管是历史题材的剧目还是现实题材的剧目,都须谨记:戏剧一定是写人的,一切要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艺术史上留下的一定是某个经典的艺术形象而不是某个戏曲故事;艺术必须是有情感的,而情感又是相通的,情感上的沟通才是剧场里最有效的沟通;注重细节,才是成败的关键,戏曲以歌舞演故事,一定是要放大细节才能出情感、出人物。同时,越剧男女合演的剧目要选取与“剧种个性和气质”相匹配内容,这才是双赢之道。
第二,用技术突破音乐层面上的难题。研究学者在《百年越剧音乐新论》中提出:“联系男女合演试验的成败得失就可以看出,其收效甚微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出现一个既能与渊源于“孟调”的女腔基本调相适应的,但又适合男腔的高质量的男腔基本调。”[16]目前在唱腔上,男女演员都在运用“女子越剧”时期创立的女腔调式,比如“四工调”“弦下调”“尺调腔”“新六字调”“反四工调”等。这对男女合演以及男演员的发展都造成了一定束缚。尽管有张国华、史济华、赵志刚等男演员曾对男腔发展进行过探索和尝试,但始终没能形成具有固定特色的男腔或者男腔的流派。当前越剧剧团乐队普遍大量引入西洋乐队的现实条件下,对男腔还可以做更深入探索。二胡的伴奏音乐限制了唱腔的发挥,而提琴、扬琴、长笛等西洋乐器可以拓宽伴奏的音域,使唱腔更自由。形成具有阳刚之美的越剧男腔流派,必然是越剧男演员内在价值的提升途径,也是对越剧男女合演艺术发展的突破。
第三,开拓具有时代特点的传播途径。鉴于电视传媒曾在男女合演传播的历史上担任过重要角色,当下也不妨多做一些越剧电视剧制作发行的尝试。同时,互联网打破了一个时代,也带来了新的时代,微博、微信、抖音等各种传播形式给“男女合演”的传播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首先是选择多元化,这杜绝了因为一种媒介的式微而使传播受到影响的情况;其次是传播更有力了,4G 网络时代传媒的最大优势就是快,它缩短了电视剧制作的周期,更具时效性;同时,这些技术掌握在年轻人手中,他们用更时尚的方式进行再传播,必然能加强、加深传播的程度。对“男女合演”来说,要尽快走进全媒时代,用更多更有效的形式传播男女合演的艺术,展示魅力,增加流量。
第四,制造越剧男演员的“明星效应”。“明星效应”目前在话剧界打造得特别红火,名人是票房和产业的保障,《暗恋桃花源》《四世同堂》等一批明星话剧在市场上的红火程度可见一斑,越剧的明星版《梁祝》的运营模式也无非是参考了话剧的成功模式。当下,与“明星效应”相对应的是“粉丝”和“粉丝经济”,“粉丝”制造了“明星效应”。《粉丝力量大》一书中提出,“粉丝经济以情绪资本形式投入,以偶像与品牌的品牌价值为产出”[17],这种情绪来自对偶像的崇拜,输出的是偶像的“明星”品牌。茅威涛“粉丝”的崇拜情绪来自演员在舞台上的艺术魅力,王君安“粉丝”的崇拜情绪来自演员舞台下的个人魅力,这两种属于“明星形象”中的专业形象和个人形象。此外,还有表演形象和影视形象。借鉴影视圈经验,越剧男演员的“明星效应”也是可以打造的。通过网络时代中的各种媒介,借用具体的上演剧目,制造鲜明鲜活、有正能量、有召唤力的形象进行“自我推销”,或借助团队力量,用具体的意向打造越剧男演员群像,以此来打造越剧男演员的“明星效应”,进而推动“男女合演”粉丝经济的发展。用“女子越剧”的例子来说,当年就成功推出了越剧“五朵金花”的群像,成为“小百花”的代言,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