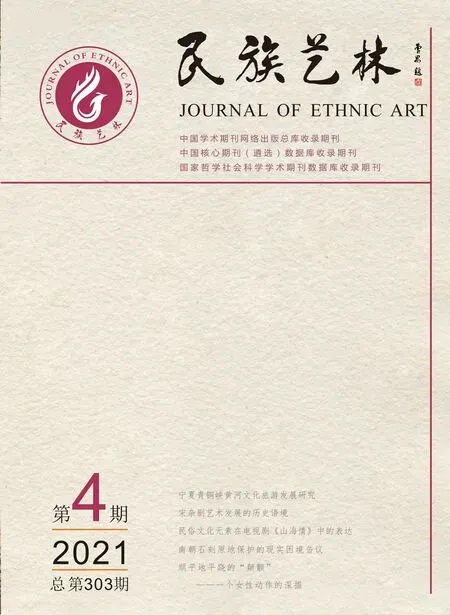《山海情》:山海相望,真情相守
王菲菲,李 亮
(西吉县文化馆,宁夏 固原 756200;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04)
2021 年初,电视剧《山海情》的播出无疑是文艺界的一个“现象”,甚至火出了圈,成为一个“事件”。仅23 集的《山海情》很快就已播完,收视率和口碑实现了双赢,观众普遍觉得不过瘾,都表示没有看够,经典的呼声也随之而起。这在第27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得到印证。电视剧《山海情》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以及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摄影四个奖项,与《觉醒年代》《三十而已》《装台》同在获奖之列。
《山海情》“讲述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引导下,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西海固的人民群众移民搬迁,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探索脱贫发展办法,将风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1]从第一集开始追剧,笔者就在想这部剧应该如何描述和评价,建立什么样的标准,得到的结论又是否合理。最初的印象是现实主义、乡土景观、时代精神和人民情怀,这些理论术语似乎可以概括该剧的艺术特色。在某一时刻,我们的内心却又产生了一丝动摇。这些术语并非不合适,恰恰是还算贴切,在剧中确实有很多细节可以印证。但仅是如此吗?总觉得以此思路写一篇剧评,却把最珍贵的部分弄丢了。评论者贫乏的语言不能穷尽这部电视剧的深意,这自然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对这部非常接地气的电视剧,笔者却也产生了一些经验之上的感觉,是不是可以说《山海情》在平淡中蕴藏深刻,在生活中见出哲理?因此,不能单纯停留在这部电视剧上,视野应该更为开阔,当然,有些评论文章已经这样做了。初步想法是建立多层次的对照,一是试看这些对立统一的视角,如现实与理想、生活与艺术、东部与西部、都市与乡土、时代与个体、男性与女性等,导演孔笙还提及“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寻根与断根”。二是明确这些互补并济、相依并存的概念并不为某一学科所独占,都有其相应的理论渊源和文化背景,如果非要用某一个词语来总括,似乎可以选择“文化现代性”。三是《山海情》自然可以纳入文化研究之中,尤其从影视人类学的角度审视,《山海情》就具有了超越其自身艺术价值的多重意蕴。
一、历史意识的彰显
艺术作品的思想力度,主要源于深广的历史意识。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有着振奋人心的“强”历史感,这很容易感受到。而《山海情》这部现实题材的电视剧,被称为“从黄土地长出来的故事”,讲述的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时间太过逼近,历史感就显得有点“弱”。其实不然,从每一集片尾的一段话可以看出,这部剧是“时代大潮写给每个人波澜壮阔的史诗”,其题旨是“变迁”,时间跨度也有20 多年。大部分的评论文章在叙述《山海情》的故事情节时都提到从涌泉村到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跨越式转变,称之为“现代社会变迁的时代画卷”(王金芝《〈山海情〉:呈现现代生活变迁中的力与美》),王晓芳则从“历史、群像与主旋律创作”的角度进行解读。历史意识的彰显,已经呼之欲出。
《山海情》是一部“年代剧”,在时光之河的流动中,有着清晰完整的时间线索。剧情结构简明,依据时间脉络进行线性叙事,观众容易投入情感,随着时间的推进,尤其是宁夏地区的观众更容易对照剧情,回忆起过去的苦难生活,切实感受剧中人物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变迁。在这个图像与声音、时间与空间相互交织的互文性艺术世界中,首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个开放的绵延的文化历史空间。
固原是历史文化名城,丝路重镇。西海固地区包含7 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市,有“苦瘠甲天下”之说,1972 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又将其确定为最不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吊庄”原是黄土高原上一种农业生产模式,具有流动性,农户开垦出来的荒地比较分散且距家远,在农耕与收获时节,不得不在田间地头挖窑洞、搭窝棚临时住下,从而方便进行农业生产。“吊庄移民”借用了这一概念,远距离移居到新建的村镇,形成新型社区。宁夏发起“吊庄移民工程”就是要把西海固地区那些不适宜生存的村庄搬迁到较为适合生存、具有发展前景的地方。闽宁镇就是这样一个移民村镇。20 世纪90 年代,在中央东西扶贫协作战略部署中,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后经考察选定在贺兰山东麓创建宁夏西海固移民村。习近平同志当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并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建议建立一个移民开发区,以福建、宁夏两省区简称(闽、宁)来命名,于是,最初的闽宁村就这样诞生了,重点帮助西海固地区的贫困农民走出大山,脱贫致富。这一巨大的文化历史空间,为《山海情》营造了开阔而深厚的历史感。[2]
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一真实的“短”历史?还是要放到“四史”的大历史视野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史,闽宁镇的变迁就有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闽宁镇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在同一历史进程之中,这一历史性飞跃本来就是“大江大河”中的一朵浪花。《山海情》仅有23 集,时间起点是1991 年,终于2016 年,展现了从涌泉村、金滩村、闽宁村到闽宁镇25 年间的历史变迁,其截取的时间点也非常具有代表性。“1991 年,吊庄。1996 年,移民。1998年,双孢菇的故事。2001 年,梦的翅膀。2004 年,迁村。2016 年,美丽家园。”经过20 多年坚持不懈地建设,曾经的黄沙漫天,如今是绿意盎然,创造出了一个现代化的闽宁镇。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道:“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深情回望3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宁夏回族自治区在脱贫攻坚上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到“精准扶贫”的实施,我国30 年来的扶贫历程,通过《山海情》中的历史变迁完美呈现出来。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一历史过程凸显的就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一次伟大的飞跃。今昔对比的脱贫攻坚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3]因而,“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这些成绩的取得,依靠的是“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
从文化空间的角度看,西海固山区与银川平原,宁夏与福建,西部与东部,直到党和国家层面的领导和支持,局部和整体辩证统一,闽宁镇的变迁是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也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的“闽宁模式”的历史标本。正是由于历史意识的彰显,《山海情》才成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思想力度也极具穿透性。
二、实录笔法的刻画
艺术作品感人至深,唯有真实二字。如今的电视剧市场几乎被都市情感、军事谍战、古装玄幻等题材所霸占,感觉很久没有出现如此耐看的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了。“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土味儿”的《山海情》之所以有如此不俗的表现,主要原因就在于真实。这种真实源于故事素材的生活真实,也源于创作技法的艺术真实。当然,历史意识的彰显也离不开实录精神。《山海情》用实录笔法记录历史、描绘时代,更像一部非虚构的纪录片,被王琳琳称为“一部中国西海固移民脱贫故事的影像志”。
如果说《山海情》整体上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那么每一集的内容、每一个人的故事,分开来看,则是一首抒情诗。抒情诗与史诗的交汇,构成了剧情发展的动力。伟大的艺术都是抒情的生活本身,而真实的生活才能打动人心。写到这里,我想起刚追剧的时候与一个朋友闲聊,她也是西海固移民中的一员,在20 世纪90 年代,十来岁的时候,她在老家还有吃不饱饭的经历。她对《山海情》的评语是“贴近生活”。可见,从一开始,这部电视剧就触动了人心,树立了口碑。
在展现西海固的贫穷落后上,《山海情》没有刻意渲染,却也不掩饰某些农民身上缺乏远见等小农意识,而且还有一定保留;在表现闽宁镇的富裕发展上,《山海情》也没有刻意夸大,更不回避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社会问题,而只是客观地呈现。这很让人动容,其中有善意,其中也有良知,时不时让观众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一首花儿,一张笑脸,一次争吵,一个拥抱,都显示出细节的真实。这种实录精神既有现实品格,又有理想光辉,不隐恶,也不溢美,尤其难得。
在国家广电总局主办的电视剧《山海情》创作座谈会上,一位从西海固走出来的观众饱含深情地说道:“《山海情》大结局后有很多人夜不能寐,大家争相在朋友圈发布跟剧情相关的动态。一部电视剧能引起如此轰动,足以证明它的成功。”《山海情》制片人侯鸿亮介绍:“自2019 年年底创作启动以来,团队就确立了坚持扎根大地,到人民中间寻找力量的宗旨。”导演孔笙表示,“实”是《山海情》最重要的特点,从创作原型到拍摄制作,从演员使用方言、用心投入表演,到具体故事中不刻意回避扶贫工作中的重重矛盾,都展现出了“真实、现实、踏实”。[4]
《山海情》的拍摄环境异常艰苦,没有水电,连一棵树都没有,几乎找不到纳凉的地方。如此艰苦的拍摄环境,成就了《山海情》艺术表现的真与实。一个个故事接连从这片黄土地上冒出来,一幅幅真切的画面,瞬间将观众带回了20 世纪90 年代。电视剧中的地窝子、土坯房、黄沙漫天飞舞等场景高度还原了当时的生存状况,真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演员和闽宁镇当地的群众生活在一起,群众里有不少是故事中的原型人物。演员们穿着有年代感的服装、装扮得灰头土脸,尤其是李水花的扮演者热依扎,没有一点偶像包袱,一改往日时尚靓丽的女神姿态,在剧中从朴素的少女成长为坚忍的母亲。拍摄时没有使用任何滤镜效果,演员们一开口就是浓郁的方言,表演自然,举手投足间,塑造出极其传神的“土味”角色。
“真实”“土味”“贴近生活”也成为观众评价最常见的评语,观众们喜爱那种“从土里拔出来”的真实感,感受到了土地的深情、青春的力量、生命力的迸发。这些都源于创作团队到宁夏的闽宁镇、西海固地区以及福建深度调研和采访,深入了解了很多精彩的人物和真实的事件。
《山海情》对细节的把控也让观众为之叹服。剧组为了拍出移民村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避开了城镇生活区,“在戈壁荒滩上搭建了‘1.0’版闽宁村和‘2.0’版闽宁村两个现场”。道具团队在现场种下剧中戏份很重的“双孢菇”,几乎找不到穿帮镜头。[5]
“方言”的使用不仅是《山海情》的重要特色,也再现了语言的真实。《山海情》有西北和福建方言原声版和普通话配音版,原声版《山海情》看起来更有代入感,更有味,“西北话一出,马上就有味儿了”。语言上的选择让《山海情》更接地气,更有时代特色和地域风貌,更快地走进了观众的内心,引起他们的共情。导演孔笙自豪地说,“大家有机会有时间一定看一看方言版,它是原汁原味的,是接了我们的心、接了我们地气的一个版本!”[6]当然,普通话配音版本的存在,也有益于电视剧走进千家万户。
三、家国情怀的厚植
艺术作品缺乏情怀,就会空洞无物,行之不远。情怀只是一种朴素的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或是对家国,或是对事业。《山海情》厚植家国情怀,铸造史诗品质,既散落着的一首首抒情诗,又唱响了一首首赞美诗。
一位东北的朋友也追完了《山海情》,她的基本评价是“西北情怀,文艺范儿,自我奋斗励志”。西北情怀与自我奋斗(励志),这还能想到。文艺范儿,却使人惊奇而又惊喜,放到《山海情》上,确实有点出人意料。所谓的“文艺范儿”,大概就是活泼的青春气息,拼搏的奋斗精神和崇高的家国情怀,是真切现实中孕育出来的浪漫理想。因此,《山海情》既是一部“创业史”,又是一曲“青春之歌”。
赵彤在《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一文中认为:“电视剧《山海情》运神思之笔,从一个小伙子的成长写出了大时代的奋进,用一个小村镇的故事讲出了大中国的情怀,以小体量的篇幅浓缩了大道之行的气象。”爱国情怀的厚植主要是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来完成的,集中表现在每一个人物追逐梦想的过程之中。
马得福是《山海情》中的“男一号”,由黄轩饰演,青春与创业在其身上交汇到一起。这位刚从农校毕业的年轻人似乎并没有受到重视,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却十分的艰巨,就是追回“逃跑”到家乡涌泉村的吊庄户。“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蚊子都能把人给吃了”“饿得直吐酸水”……这些情况虽说略有夸张,也有戏谑的成分,但这些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村民们拒绝移民搬迁的理由很现实,态度也都很坚决,马得福刚走上工作岗位就碰了一个“大钉子”。这些人与他都是涌泉村的村民,也有他的长辈,工作实在是不好开展。黄轩感慨说道:“我真的要向这些兢兢业业的基层扶贫干部致敬。”从绞尽脑汁、苦口婆心劝返吊庄户,到带领村民走向移民搬迁地,从三番五次蹲守供电所、拉下脸面近乎哀求给移民村通电,到冲进会场争取到灌溉移民村干涸麦田的黄河水,从鼓励村里姑娘“走出去”到福建务工,到带领村民们学习“引进来”的蘑菇种植……马得福也曾迷茫,最终坚定地选择走上了一条的艰难而伟大的道路。困难一个接一个而来,马得福永远选择迎难而上,在为村民们解决遇到的各种生活生产问题,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得管,宁肯亏待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也不愿意让其他村民吃亏,宁肯不顾自己在仕途上的发展也选择站在老百姓一边,有苦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地之子”的义务、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干部的责任,在马得福身上得到了统一,带领人们摆脱贫困,走向小康。这样坚定不移、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扑在脱贫致富工作上的人物形象,正是基层扶贫干部的缩影,他们展现出来崇高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值得崇敬。[7]
王一川在《地缘美学密码的魅力——电视剧〈山海情〉观后》一文中,对电视剧《山海情》中“性格鲜明的脱贫攻坚主体群像及其灵魂人物”有过精彩的分析。王一川认为,《山海情》“塑造了一组浮雕般鲜活动人的脱贫攻坚主体群像”,并且尤为关注两个有知识的人物:一个是来自福建的凌教授,另一个是西戈壁小学的白校长。他们的事迹不用多说,相信看过电视剧的人,都会为这两个人为村民、为孩子的真情实意和实际行动所感动。“这两个人物,呈现出一闽一宁、闽宁合璧的组合格局,分别体现科技扶贫和教育扶贫理念,宛若贯串全剧的一对双核,属于其中最用心用力而又感人肺腑的灵魂式人物。这两个灵魂式人物的设立及其精神支柱作用的传达,深化了全剧的脱贫攻坚题旨及其文化意义。”[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毫无疑问,马得福是《山海情》着力塑造的“地之子”形象,对土地、对家园、对乡亲、对事业,满怀热情,脚踏实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而李水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生命的壮美,具备女性之坚忍的宝贵品格。可以说,闽宁镇的变迁与马得福等“人的成长”是该剧中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马得福、李水花、马得宝、白麦苗,以及所有投入这项扶贫伟业的每一个人,都展现出崇高的家国情怀。宁夏人或福建人,男人或女人,知识分子或农民,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而恰到好处的真情实感更有助于形成雄浑的风格,崇高的情怀。
伊格尔顿认为:“公开地表明政治态度在小说中是不必要的(当然不是不可以的),因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本身就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各种重要力量……作者不必要在作品中塞进自己的政治观点,因为,如果他客观地揭示出了当时正在起作用和潜在的各种力量,那么,他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党性的了。”(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这一论述可以为主旋律艺术的创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山海情》的结构是完整的,从“吊庄”出走到“返乡”归来,首尾呼应,昔日的涌泉村旧貌换了新颜,黄土地披上了绿色的新装,而且还有代际的交替与传承,不得不令人感叹“换了人间”——“如今的涌泉村也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然而,23 集的电视剧集数终究是有点短,剧中有些情节似乎没有完全展开,观众普遍认为看得不过瘾,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某些情节上具有跳跃性,不妨看作一种留白,没有展开的情节可以依靠想象去填充,其实也不必苛求。另外,《山海情》的多重意蕴还可以从生态美学、空间诗学、乡土景观等角度来解读。
赞曰:五千里路,山海相望;二十余载,真情相守。志同道合,山海不远;人比山高,情比海深。我们相信,闽宁镇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到那时,“再唱花儿等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