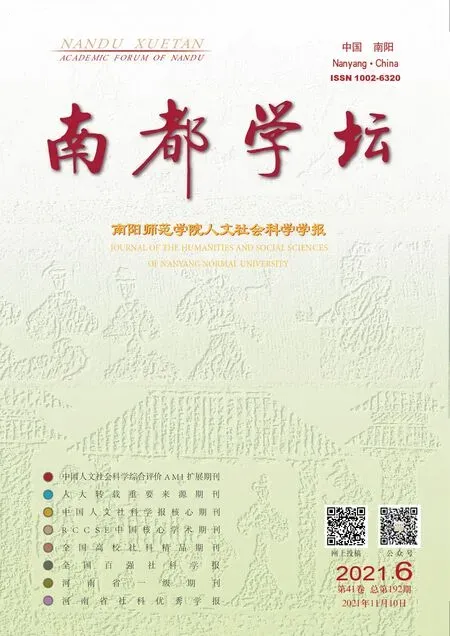汉代宗教和谐与形成机制的图像学研究
刘 克
(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宗教题材汉画分布极其广泛,胶东半岛以西,巴蜀甘疆以东,陕晋京辽以南,浙赣黔滇以北大片国土上的考古发掘,都曾出现过她那靓丽妩媚的身影。其数量目前已达16000余幅,成为汉代宗教发达繁荣的生动写照。作为当时宗教生活的反映,这些汉画蕴含着原始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及其信徒,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等基于宗教交往所产生的复杂关系。通过对这些关系的归纳研究,在宗教所面临的内外部诸多宗教因素与非宗教因素中提炼汉代多元宗教和谐关系的生成机制,抽绎多元宗教和谐共存的运行机制,对于从动态视角把握汉代宗教的宏观格局,推进宗教学理论研究向纵深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汉代多元宗教和谐关系在汉画中的表现
和谐,是和睦协调的意思。宗教和谐就是宗教间承认彼此存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相处融洽友好。宗教题材汉画在墓室里如何布局,谁跟谁刻画在一起,除信仰自身的因素外,还具有政治、社会、文化、风习等多元维度,包含着宗教与宗教、中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等诸多复杂关系(1)宗教关系具有与社会、权力、文化、时代、地缘、族群、宗教自身等宗教内外部诸多复杂因素互动的多元维度。对于汉代宗教与社会、权力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有专文谫探,详见《暨南学报》2014年第1期拙作《管制与因应——出土文物所见汉代宗教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对这一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是我们深入把握和精确提炼汉代宗教多元和谐关系及其机制的重要前提。
(一)本土宗教之间的和谐关系
冲突、融合、和谐是宗教关系最常见的三种形态,每种形态都有其相应的外部特征。和谐作为宗教关系中一种最理想的形态,其鲜明的特征,在汉画中有着生动的表现。
首先,两种或两种以上宗教同处一墓。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建于东汉早期,方向274度,雕刻画像153幅。其中与道教有关的6幅,计有西王母、东王公画像各1幅,位于墓门门楣正面;羽人画像3幅,分别位于北主室北壁东柱正面、北主室门北柱东侧面和中主室北壁门楣正面;仙人乘龟画像1幅,位于中主室南壁中假门后壁。这些画像大多带有云气,仙意甚为浓郁。与儒教有关的画像5幅,计有驱鬼图3幅,分别位于前室西壁门楣、北壁门楣、南壁门楣;穷奇、强梁画像各1幅,分别位于中主室南壁正面和东柱西侧面。与原始宗教有关的画像5幅,计有黄帝画像1幅,位于前室盖顶石下面;伏羲女娲画像2幅,分别位于南主室门北柱的北侧面和北主室门北柱的南侧面;风神和雷兽画像各1幅,分别位于北主室北壁正面和中主室南壁的东柱正面[1]。西王母东王公是仙境的象征,该墓西王母头饰发髻,人首蛇身。东王公戴冠着长襦。羽人为人背生羽翼者,通常既指仙人穿羽衣,也指神话中的仙人。屈原《远游》有“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句,其注曰:“《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2]仙人乘龟画像中的仙人,手执仙草,骑于神龟背上。如果说羽人是仙境成员的话,那么仙人乘龟表现的则是成仙途径。道教题材汉画反映的是墓主子孙希望墓主升入仙境的愿望。驱鬼图展现的主要是汉代大傩禳祭仪式,只是汉画在表现时,限于条件,只能以仪式的核心情节示人。《周礼·夏官》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驱,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3]穷奇、强梁为大傩祭仪中的驱鬼神兽。虎之生翼者叫穷奇,虎首人身操蛇衔蛇者为强梁。《山海经·海内北经》云:“穷奇状如虎,有翼。”[4]364《神异经·西北荒经》亦云穷奇“西北有兽焉,状似虎,有翼能飞”[5]。强梁也是食鬼天神,《山海经·大荒北经》云:“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强良(按:梁)。”[4]332在墓室刻绘驱鬼主题的画像,表现了墓主子孙息魔灭鬼、涤污荡秽,祝愿亲人在地下不受厉鬼侵扰的意涵。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黄帝戴三叉冠着袖袍盘坐于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之间。刻绘伏羲女娲黄帝神像是原始宗教中祖先崇拜的孑遗,表达了民众敬天法祖的思想感情。风神名叫飞廉,雀头有角,鹿身有翼,尾似长蛇。画中风神飞廉一边驾雾腾飞,一边口吐云气。飞廉也叫龙雀,张衡《东京赋》云:“龙雀蟠蜿,天马半汉。”注云:“龙雀,飞廉也。”[6]424画中雷兽龙爪龙颈,长尾,口大张,腹鼓朝上,右前爪着地。《山海经校注》引郭璞注云:“雷兽,即雷神也,人面龙身鼓其腹者。”[4]371此雷神画像与文献所载基本相符。汉墓中的这些风神雷神画像反映了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表达了汉代民众乞求祖先护佑家族的意匠。从上述宗教汉画在墓室里的布局来看,各种宗教都能平等友好地对待对方,尊重对方的特殊性。无论是儒教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和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八德,还是道教的道法自然尊道贵德及原始宗教的报本追源,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彼此之间都是伙伴,而不是敌人。
诸宗教汉画同处一墓的典型墓葬,还有山东邹城卧虎山西北侧的汉画石椁墓,发掘报告称为M2者[7]。该墓建于西汉晚期或东汉早期,画像分布于石椁内外四周,共20组。其中宗教题材画像主要为戴胜杖的西王母和戴雄鸡冠者2幅。西王母戴胜手扶鸠案而坐,位于石椁南板的内壁右格,周围祥云星象环布,其下为九尾狐、三足乌及捣仙药的玉兔。风采鲜明,光仪淑穆。戴雄鸡冠者位于石椁北板外壁中格,应为儒教代表人物子路。理由有二:一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记载子路这位孔子高足的装束时,不仅有“冠雄鸡,佩豭豚”之表述[8]2191,而且还有“君子死而冠不免”的强调[8]2193;二是参考出土汉画,如山东武氏祠前石室东壁刻孔子贤明弟子画像左起第九人戴雄鸡冠者头侧识以“子路”二字[9]36,在嘉祥齐山出土的画像石上著雄鸡冠者头侧亦刻有“子路”二字[10]。西王母在汉代道教中的神格极高,子路在卧虎山石椁上与其对应,表明在冥界神祇的安排上,儒教代表人物子路是以与西王母相匹配的男性神这一平等身份出现的,汉画构图不存在抑此扬彼的倾向。
道教和儒教的和谐亲近在汉墓里成为风气,信仰的多样性被看作正常现象而受到尊重,不仅深刻诠释了儒门和而不同和道门有容乃大的思想精髓,而且也为实现多教并讲共信,形成百家异说末离本同、殊途同归观念备下了沃壤。中和之道和柔和之道既是二教各自的底色和标识,更是二者和谐的桥梁与纽带。
其次,宗教关系的和谐还体现在各宗教友好地存在于同一块汉画像石上。此类汉画目前出土较多,汇聚了一大批很有代表性的画作。如陕西米脂县官庄四号汉墓,画像石上所刻纪年显示建于安帝永初元年,左门柱画像分内外两栏。外栏七格,自上而下分别为:执瑞草的人身蛇尾神;玉兔捣药;戴进贤冠、着袍服、作讲述之人,其后捧牍(简或笏)之人面向讲述者跪于地上;动物等。内栏四格,自上而下分别为:两仙人在神树上博弈;二戴冠着袍之人,袖手面向外栏第三格讲述者站立;鸡;博山炉[11]。图中玉兔右手执臼锤,左手护臼沿,给人以奋力捣制仙药之感,树上仙人各执棋子,对弈正酣,呈现出一副悠闲自在之态。从第三格讲述者所戴进贤冠判断其为儒者。因为,据《后汉书·舆服志下》,可知依汉制,进贤冠乃儒者所戴之缁布冠。“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12]3666该人在宗教氛围极浓的场合摇臂讲述、对面二人袖手倾听的构图,给人以讲述儒学教义过程中与倾听者互动之感。在山东嘉祥南武山出土的汉画像石上,也出现了戴雄鸡冠的子路与西王母组合的构图模式。西王母坐于榻上,左一头生双角的长尾羽人向其递碗,羽人后为一人首鸟身仙人。西王母右为一奉献三珠果的羽人,羽人身后依次为马头人身仙人、戴雄鸡冠的子路和一狗头人身仙人,他们均举板向着西王母跪坐[13]。著名儒者子路进入以西王母为首的神仙行列中,通过“儒道友好相处”和“身形距离西王母远近”的构图形式,似乎构成了儒道双方超越教种背景而实现两教“互动”“会讲”的表达意义,符合宗教间和谐关系生成过程的内在逻辑。
再次,孔子见老子。严格地讲,孔子和老子相见汉画理应属于上述不同宗教同在一块汉画像石的范畴,但因其重要特殊,近年讨论热烈,故把它单列为一类。我们通过对收集的36幅孔子见老子汉画进行数据统计和画像分析,能够得出如下认知:此类画像在今山东、江苏、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的汉墓中最为流行,从画像内容上看,此类画像主要由繁简两种形式组成。所谓繁,就是孔子老子及其弟子都出现在画面中,甚至连孔子拜会老子时行贽礼所用的雁也一应俱全。如山东嘉祥齐山出土的孔子和老子相见汉画像石,孔子带领子路、子张和颜回等20名弟子,带着雁去拜会老子,老子带领项橐及7名弟子以礼相迎。孔子、老子头后分别刻“孔子也”“老子也”榜题[14]46。汉画内容与史乘所记“孔子适周问礼”[8]1909于老子的文献相符。所谓简,就是画面所表现的人物主要为孔子、老子二人,把二人相见作为表现的主要情节,其他一些细节都尽量舍弃不表。如四川新津东汉崖墓石函刻孔子问礼图,画面由三人组成,每个人的头上方分别刻有“孔子”“老子”“□子”榜题[15]。只刻问礼情景中的主角。对于孔子见老子汉画含义的理解,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种观点都有历史实事或思想逻辑的支持。巫鸿从画像人物形态判断出孔子、老子相见汉画的意旨是二人互致敬意[16]。赤银中认为二人相会象征儒道学说融合发展[17]。陈东认为孔子见老子汉画表现的是“孔子协助老子助葬于巷党的情景”[18]。姜生从汉代道教升仙仪式角度分析,认为其所表达的是,“在地下世界,死者将和孔子及其弟子们一样,往拜老君得道受书”以成仙[19]。以上观点表面上看各执一词、言人人殊,相互之间很难说服,但若回到汉代宗教文化进程,从宗教与宗教因素之间的联系中去考察其间关系,就会发现上述各说不仅合理,而且科学。虽有交叉,但无重叠。在汉代的宗教生态上,虽然西汉曾有过不能公平对待各信仰的历史,但是在西汉后期,随着儒术经学没落和谶纬神学兴起,老子孔子都得到了神化。老子被称作“太上老君”,成为道的化身,孔子被尊为“太极上真公”,也成了仙界的一位真人,儒道两家完美地走到了一起。只是孔子的地位在这次组合中较之老子,下降了不少,成了老子的学生。东汉《白虎通·群雍》中“孔子师老聃”一语,就来自儒生所造《论语谶》。这是儒道两教在“独尊儒术”后期亲密和睦接触的背景,也是两教在通和之路上渐行渐近、出现孔师老说的来历。后来,谶纬神学嬗变为原始道教,汉纬的好些内容也与道教融为一体。道教对于安康长寿的重视,使它很快占据了汉代社会的精神世界。因为历经残酷战争和疠疫肆虐折磨的汉王朝,自上而下都十分看重身体。为了实现身体的不朽,在这种特殊的文化形态里,人们千方百计去寻找成仙的路径。刻绘表达升仙要旨的孔子见老子汉画,自然会使人兴致盎然。姜生等学者把孔子见老子汉画从汉代墓葬与宗教背景相联系的视角进行阐释,识见可谓卓越。道教的升仙信仰帮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获得了精神支柱,极大地丰富、充实了只注重品德修养的儒教的不足。儒道两教由于和而不同,所以天生就不存在强对抗基因。
在孔子见老子汉画里,儒道两教和谐错杂、共存共美。它们以和谐为教,有效地避免了神学垄断。这些汉画的出土,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就了解汉代宗教之间的关系而言,仍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宗教在汉画中所呈示的这种亲近,是宗教间和睦友爱的表现。从宗教汉画入手分析儒道两教的和谐内涵,有利于认清汉代多元宗教之间和谐关系生成的动力和原因。
(二)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之间的和谐关系
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和内蒙古和林格尔汉代壁画墓均建于东汉后期,都曾出土过佛教题材汉画,有佛像,也有表现佛教教义的力士、白象、舍利等画像。沂南佛像出现于墓室八角柱上,共两尊。八角柱由四个斜面和四个正面组成,四个正面分别朝向东南西北方向,佛像刻在南北两个面上。面南的佛像处在顶端,立像,捧鱼,头上有项光,其下刻人面双首鸟身的神像,再下乃一带双翼,左手蜷于胸前,右手形态近似于佛教手印的坐像,该像下为一羽人,最下为一龙形神兽。面北的佛像也位于顶端,亦有项光,双手捧一鸟,其下为一力士,再下乃一翼牛,最下为一鸟首翼龙。柱的东面自上而下刻东王公、羽人捣药、青龙、大龟、鸟驮螺等,柱的西面由上而下则刻西王母、白虎、麒麟等。柱的四个斜面主要刻神禽、异兽、羽人等画像[9]151。从画面构图来看,佛、道对称的意旨明显。和林格尔墓的佛教题材汉画主要出现在前室。骑象图位于南壁,有“仙人骑白券(按:象)”榜题,西边偏上画凤鸟,榜题“朱爵”,北壁有画像两幅,墨书榜题“玄武”,“雨师驾三虬”。东壁上方画东王公,其下画装在盘中的四枚球形物和蛇形动物,并分别榜题“猞猁”“青龙”。西壁则画西王母和白虎[20]。从壁画布局来看,佛教画像跟道教画像显然也是对应而画的。这种现象说明佛教初来乍到,采取融入中土的策略是依附而非对抗。“仙人骑白象”画像,依据东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可知其表达的是佛教降身经义。榜题“仙人”一语在佛经里是对尚未修成正果的各类佛徒的称呼。如桓、灵时期安息沙门安世高所译《佛说婆罗门避死经》就有“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有四婆罗门仙人,精进修善法五通,便作是念”(2)参见《大正藏第三卷》,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第854页。。又如献帝时来自西域的昙果共康孟详等沙门所译《中本起经》卷上亦有“于是如来便诣波罗奈国古仙人处鹿园树下”(3)参见《大正藏第四卷》,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第148页。。这种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有利于促进中外宗教友好交往。猞猁乃舍利之借字,统常指佛祖的遗骨。在佛教信仰里,供养舍利就如同供养佛身。在壁画中将盛装舍利的宝盘绘于“仙人骑白象”的对应位置,表现的正是这种供养意匠。这些佛教义理出现在壁画中,说明佛教降身故事及舍利之说最迟在东汉后期已经进入了民众的信仰之中。另外,在中室南西北三壁还绘有历史故事80余幅,从榜题来看,有舜、老子、孔子、颜渊、子张、子贡、子路、子游、子夏等圣贤。从这些宗教题材汉画在墓中的布局来看,汉代堪称宗教的熔炉,在这个熔炉里,佛教的到来,不是破坏尊天敬祖这一中华民族尊奉了几千年的基础性信仰,而是跟本土宗教熔铸一体,适应中国的信仰文化,积极与本土宗教信仰和睦相处、和谐共存。
宗教题材汉画是汉代宗教活动的反映。从上述佛教画像与传统信仰画像亲密接触的形态上,能够对汉画所承载的本土宗教与外来佛教的和谐关系给出如下判断:敬天法祖是华夏民族的传统信仰,儒道两教分别在“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思想指引下,以和为贵,追求福寿德仁的核心价值,形成了包容差异、推崇多样的宽广胸襟,尊重外来的宗教并支持其本土化。佛教进入中土后,经过与儒道两教相结合,调和了外来宗教跟本土宗教的关系,很快在中国化道路上实现华丽转身,被民众接纳,拥有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儒道在文化上的开放气量使佛教进入后很快与本土宗教的人文性、宗教性实现了融通,建立了三教鼎立的主体架构。汉代盛行的谶纬神学虽然给儒家的仁礼之学注入了一些宗教因子,但没有从根本上推动儒学走向宗教化,其本质上的人学比重仍然很大。虽接受神灵,却更崇拜圣贤。佛教跟儒道相互亲近、和谐会通后,道释的神灵慰藉、彼岸世界弥补了儒教的不足,而儒教的人文理性则引导它们贴近生活,沿着人神一体、以和为教这一正确的发展路向去宣德教化。三教相得益彰,在相依相扶中永葆宗教活力,一起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信仰需求。
(三)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的和谐关系
汉画墓的存在形态也生动地呈现了信教者与不信教者和谐相处的情况。如1996年陕西省考古所等在神木大保当发掘了24座汉墓,其中13座出土有画像石。其规模之大,是目前不多见的。通过对这13座汉画墓出土的50余幅画像进行比对分析发现,虽然有好些墓室刻绘了很多宗教画像,但也有很多墓室却没刻宗教画像。如M1,其画像集中在门楣、门柱、门扉处。门楣石刻狩猎图、车骑出行图,左门柱自上而下刻人物、舞蹈、輂车等图,右门柱所刻画像与左门柱颇为一致。门扉刻绘常见的朱雀、铺首等内容[21]24-33。自始至终未出现一幅以宗教为表现内容的画像。M2的画像形制与M1基本相同,画像也是集中在墓门处,墓门也是由门楣、门柱、门扉组合而成。除了具有相邻的M1所有的车骑出行、朱雀铺首等画像外,在右门柱偏上的地方赫然刻绘了一个飞翔的羽人[21]39。因道门言飞升成仙,故世人常以羽人作道士的代称。这种情形还表现在M23和M24出土的画像中。M23为东汉中期墓葬[22],画像刻绘在门楣、门柱和门扉上。门楣外栏刻狩猎图,两端刻日月,月轮内刻玉兔捣药,玉兔身上缀白色斑点,日轮内刻金乌,内栏为车骑组合画像。因传说月内有玉兔,故以玉兔作月的代称。又传说日中有三足乌,故以金乌作日的别名。因此,在这样的构图环境中,此玉兔捣药代指月亮,显然不是西王母仙境中的玉兔捣药。左右门柱皆刻人物、乐舞等,右门柱画像与左门柱基本相同。左右门扉均刻朱雀、铺首、独角兽等[21]130-141,未见宗教题材的画像。M24与M23相邻,形制相同,画像也是出现在墓门区域的门楣、立柱、门扉上。门楣两端分别刻日月,日轮内刻金乌,月轮内刻蟾蜍。中间刻驯象图,大象面右伫立,象奴头戴尖顶帽,面象站立,左手执钩作驯象状。左门柱刻西王母,头戴冕冠坐于神树顶端,神树树干间刻仙兔、蟾蜍、神禽。右门柱虽残,但仍能辨出其画像布局与左门柱相同[21]142-149,只是从汉代刻绘内容有对称、呼应的规律这点判断,其上的人物应为东王公。西王母、东王公到东汉的时候,已经是仙界大神,从《老子中经》所列的55个位格的道教神仙名单中,可知东王公为第三神仙,西王母为第四神仙[23]。关于驯象图的属性,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佛教画像,以驯象喻御心;一种认为它与佛教无关,只代表一种祥瑞。鉴于神木在东汉属于上郡,该汉画墓的建造年代和位置,距离和林格尔汉壁画墓均不远,也鉴于驯象图与西王母东王公同在一处的构图方法跟和林格尔壁画有相似之处,因此笔者倾向于该驯象图与佛教相关(4)关于上郡汉代佛教的情况,详见《东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拙作《东汉奉佛样态——以民间汉画葬俗中的圣迹为中心》。。这种宗教题材汉画墓与非宗教题材汉画墓错综杂陈的现象,在米脂县官庄、绥德县黄家塔等地的汉画像石墓群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古人在建筑坟墓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和谐关系的表征。
一般而言,汉画大多都是由石刻艺人在墓地现场制作而成,刻绘的也多是墓主心仪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刻绘宗教题材汉画的墓主是信教的,至少有宗教情结,而不刻绘宗教题材汉画的墓主是不信教或是在信仰上不够虔诚的,不一定拥有修行情怀。信与不信的两类人死后能够葬在同一块墓地,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不存在相互歧视和排斥。同时也说明在汉代民间,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享有信仰自由,身份意识不明显,其和谐相处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较小,选择墓地时并没有因为信仰宗教与否而受到干扰,宽容度较高,相互尊重包容是信众与非信众之间的主基调,和谐相处是共识。作为世代为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信仰上的差异只是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反映,处于次要地位,远不及亲缘、地缘、人缘重要。另外,他们在汉画中刻绘的,都主要集中在祈求吉祥和教人为善方面,不存在伤害彼此感情的内容,因此不会引起不满情绪。这是汉代民间形成信教与不信教民众和谐相处这一传统的深层次原因。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认知,能够对汉代的宗教关系和谐形态给出如下意见:汉画见证了汉代国内不同宗教、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的和谐关系。虽然排他性是宗教的固有属性,也是产生社会矛盾的主因,但在汉代民间却出现了多元宗教的和谐相处现象。各个宗教的教义固然不同,不信教者也各有各的精神追求,但他们都推扬宽容、仁爱、正义、诚信和互助这些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这既是他们立身社会的基础,也是构建宗教和谐关系的关键。汉画所彰显的不是一神教传统,而是农牧文明养育的多元文化和谐习惯。汉画所呈现的宗教关系启示我们,既然儒释道三教能够在中土和谐相处,既然同一个体能够同时接受四种宗教,那么五教乃至更多的宗教也必然能够和谐相处,同一个体也可以同时信仰更多种宗教。西方学界多元宗教关系研究所持守的排他主义和兼容主义两种立场,因心胸失于狭隘,所以难以构建出真正和谐的宗教共同体“新秩序”。在今天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对作为时代宗教文化长河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和谐关系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提炼,从其深厚的历史脉络之处撷取与当今中国乃至国际宗教生态健康发展的新流,对于涵养宗教和谐生态、强化处理宗教和谐问题的理论自信和方法自信来说,都大有裨益。
二、汉代多元宗教和谐格局的形成机制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能摆脱时空的规定性,汉代的宗教活动自然也不会例外。多元宗教的诞生和宗教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始终都离不开汉代特定的时代和环境。这种紧密关系不仅体现在各种宗教的发展演化上,也体现在本土宗教与外来佛教的交织互动上。汉代多元宗教格局的生成和和谐局面的出现,是在汉代卓殊的时空中孕化而成的。
(一)汉代产生多元宗教和谐格局的时间因素
通过对10000余幅宗教汉画进行归纳分析,能够得出汉代宗教多元和谐格局形成经历三个阶段的认识。
第一阶段,起于西汉昭宣二朝,止于东汉章帝时期。这一阶段是宗教汉画的肇兴期,典型墓葬有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唐河新莽郁平大尹画像石墓、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等。这一阶段宗教题材汉画反映的主要是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内容。卜千秋墓建于昭宣之间,墓顶脊从前向后依次绘女娲、仙翁(方士)、朱雀、白虎、双龙、伏羲等。伏羲女娲为人类始祖,在汉画中多有发现。卜千秋墓出土的伏羲戴王冠,下身蛇躯,女娲人首蛇身,形貌端庄。仙翁(方士)披羽衣,持节,呈腾云驾雾状。朱雀鹰头凤尾,做飞翔状。白虎张口翘尾,做奔跑状。双龙交缠一起,做飞驰状[24]。唐河郁平大尹墓是一座有纪年的早期墓葬,建于西汉晚期,主室中柱刻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柒日癸巳葬”铭文。该墓墓门门楣刻二龙穿璧,墓门门扉分别刻白虎、朱雀,南车库门楣刻羽人、二龙交尾、人物等[25]。唐河针织厂墓建于东汉早期,墓门门扉上分别刻白虎朱雀瑞兽祥禽,主室门外对称的南北柱上分别刻绘女娲、伏羲,南主室北壁门楣自左至右分别刻绘白虎、羽人、苍龙、羽人,北主室顶部刻四神和长虹,白虎苍龙皆生双翼[26]。卜千秋墓画像的画面构图与《焦氏易林·临之》所描述的“驾龙骑虎,周遍天下,为人所使,西见王母,不忧不殆”[27]升仙旨意冥契相合。方士是原始宗教中的重要角色,其作用跟后世宗教的神职人员相当,既是沟通人神的中介,也是祭祀活动和占卜活动的主角。他们在汉代十分活跃,不仅进入宫廷,接近帝王,影响高层的思想和生活,而且还沉潜于民间社会,言神谈仙,呼风唤雨,干预社会政治和引领文化思潮,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史记·封禅书》载:“仙人好楼居,(武帝)于是令长安则作蜚蠊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8]1400龙、凤、虎具有吉祥的寓意,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向往。郁平大尹墓的画像组合反映的也是辟邪升仙思想。针织厂墓中的四神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合称,分别居于墓顶石的左右上下,龙虎均有羽翼,朱雀展翅欲飞,玄武以蛇缠龟。四神象征四方神明,有辟除不祥之意。长虹在画像中被刻成半圆拱形,极似单孔桥梁,其两端被设计成龙首,一看便知与行雨有关。汉画墓里供奉这些画像,折射的是汉代社会存在的原始宗教之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羽人画像是当时盛行的神仙崇拜在画像石上的反映。神仙思潮的形成,既与西汉初年黄老之术借助政权力量居于统治地位、道家神仙思想得以滋长有关,也与西汉中期董仲舒对儒学进行神学化、宗教化改造而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有关。武帝极其向往成仙,他说:“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28]1228宣帝成帝对神仙也痴迷到了神魂颠倒的程度。王莽深陷鬼神世界而无力自拔。《汉书·郊祀志》云:“莽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28]1270祭祀神仙之多,规模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进入东汉,光武和章帝接踵而行,对鬼神的祭祀也十分频繁。章帝元和二年曾下诏云:“今山川鬼神应典礼者,尚未咸秩。其议增修群祀,以祈丰年。”[12]149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各自独立演化和多神崇拜。二者之间的平等互融和演化,在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的同时,也为以后容纳其他宗教、与不同信仰和睦相处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起于东汉和帝朝,止于安帝朝。该阶段最大的特点是西域佛教进入中土与原始宗教、儒教等和谐互动共处。重庆丰都槽房沟出土摇钱树佛像,其底座侧面刻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纪年。“延光”为东汉安帝年号,佛像带项光,“火焰状发饰,高肉髻,无口髭”,“圆领,袒右肩,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袈裟”[29]。是目前发现最早且有确切纪年的佛像。跟槽房沟属于同一个时期的佛像,还有四川安县出土的摇钱树佛像。安县摇钱树佛像,其年代当“为东汉中期”[30]。树座上有羽人1人,树干上有佛像5尊。光头,大肉髻,穿圆领衣,右袒,结跏跌坐,施无畏印。树枝共28支,其中1支上有佛像,坐在礼天神物的玉璧之上,其造型与树干佛像近似,周边饰玉璧和莲花。另外27支树枝对有佛像的树枝作拱围状,其上饰龙、凤、神兽、仙草、莲花、玉璧等图案[31]。摇钱树佛像的这种布局,不仅表明佛教在东汉中期就已成为民众心目中的重要宗教信仰,而且也表明汉代多元一体宗教格局的形成,是建立在中外宗教以亲近、和睦这一主旋律为总趋势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阶段,起自东汉顺帝朝,止于东汉末年。该时段的特点是原始宗教、儒教、佛教、道教互动,标志是道教的原始形态初步形成,出现了反映道教教义和实践的炼丹画像。由于道教脱胎于方仙道,追求依附鬼神和形神销化,世人服食仙丹的热情极为高涨。在此背景下,不光在东汉后期道教演化出了丹鼎派,而且炼制丹药的鼎器也受到人们的膜拜。成书于此时的《周易参同契》作为“万古丹经之王”,在备言炼丹、冶金、服食之次第的同时,还辟《鼎器歌》专章对炼丹鼎器之法度、立鼎筑炉之规模进行详尽解析[32]。鼎器乃炼丹之重要用具,因能生产仙丹,所以被汉代民间视为神鼎而刻绘在墓室里。巴蜀大地就出土有大量这样的汉画。如四川绵阳出土的模印汉画砖上,中央画巨鼎,鼎左右各有“神鼎”铭文,“铭文之外左右各画一人,一坐鼎旁,一持笏而跪”[33]。在四川泸州七号石棺上刻有一鼎,鼎身上部满刻云气,鼎右站立一手持节杖之人[34]。提示该鼎是炼制金液还丹之神鼎。之所以用鼎来炼丹,是因为鼎在商周时期就是通天祭祀的贵重礼器。以鼎炼丹,可增加仙丹的效力。节作为一种身份标志,在东汉原本是朝廷使者执行王命时使用的凭信,但在此时的道士(方士)那里也成为其司事时一个不可缺少的特征。《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注引《典略》载,东汉熹平年间,太平道的师在为人医病时就持九节杖[12]2436。这些人源于古代巫祝,或交通人神以互传阴阳两界旨意,或炼丹以助人升仙不死,是汉代道教发展的重要力量。
丹鼎及其持节道士汉画的发现,其意义是很大的,它意味着东汉晚期的道教,跟之前的方仙道既有关联更有差别。洛阳卜千秋壁画墓中的升仙图,男女的升仙方式是分别靠三头鸟和舟形蛇,持节方士(道士)仅起引领的辅助作用[25],而在东汉后期的升仙图中,升仙主要依赖道士(方士)所炼丹药的帮助。另外,道教产生后宣扬人若要长生不死,需直接服食道士在鼎器中炼制的金丹。而在西汉,从史乘记载来看,却是靠使用由丹砂炼化出来的黄金制成的饮食器具,然后再“通过祭祀、封禅召唤仙人以成仙”[35]。《史记·封禅书》载,方士(道士)李少君上言武帝曰:“祠灶则致物,致物则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具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8]1385这些变化的背后,隐含的是道教的兴起和道士(方士)在民众升仙过程中作用的提高。
通过汉代多元宗教格局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我们发现汉代多元的宗教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呈现出阶段性,但它总是改中有因、相续出新,一直与源头前后相续、血脉相连。各种信仰在不同阶段交往互动的程度可能有深有浅,佛教进入中土后在不同地区中国化、本土化进程也可能有快有慢,但经过中土宗教洗礼,在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大格局内,佛教在与兄弟宗教建立起共时性的并存和历时性的演化中积极进行接触和会通,成功地走进了主流文化。各宗教之间和谐相处,不仅保证了各宗教都有其比较广阔的信仰市场,而且还拉近了不同信仰群体间的距离。各教所养成的包容差异胸怀,使他们乐于接受外来宗教并支持其中国化、本土化,最终达成多教和谐相处。汉代多元宗教的和谐文化,其发展过程就好像那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不仅水量丰沛而且水质甜美。虽然不断有新流加入,但这些新流总是与源流不离不弃,相伴着一齐向东方文明的海洋流去。
(二)汉代产生多元宗教和谐格局的空间因素
汉代宗教题材汉画的空间分布,按照考古发现,目前主要分为四个区域。第一区域以南阳为中心,包括今河南中西部和湖北北部地区。第二区域以鲁南苏北为中心,包括今山东全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河北东南部和河南东部地区。第三区域以陕北晋西为中心,包括今陕北的米脂绥德神木、晋西的离石等地区。第四区域以巴蜀为中心,包括今四川全部、云南北部和陕西南部地区。
上述区域,汉代均分布于交通便利的驰道两侧。穿越南阳的武关道南可到江汉平原,西可到关中平原,鲁关道北可到洛阳。齐鲁通过卢龙道、傍海道可达于燕赵,通过梁宋之间的商路可到达洛阳,海陆丝绸之路可以抵达西域。榆林在汉代属于上郡,“从西汉初年开始,该地区一直都是奉佛教为国教的大月氏族游牧的地方”[36]。四川在汉代“栈道千里,无所不通”[8]3261-3262,借助子午道、褒斜道、岷山道等,西北可与关中相通而连北方丝绸之路,通过西夷道,可与滇缅相连而接南方丝绸之路,东南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接。沿着四通八达的道路,不同信仰的族群从四面八方迁徙而来,使得这些风行汉画葬俗的区域在逐渐演变成为汉代多宗教汇聚之域的同时,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血缘关系、思想文化等因素也在长期的交融、循环、调节、涵化中,一步一步地形成了原始宗教、儒教、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等特色相对鲜明、影响范围大小不等、具有相对固定区位单元的各类宗教。由于汉代宗教系统是在华夏仁和精神的引导下,通过和平理智的方式形成的,其兴衰起伏和收缩扩张跟外部势力没有关联,也基本没被政治集团操控,传播过程中又不断与各地风土人情层层套叠、错综交叉,所以这些宗教在特定的地域影响特定人群的时候,能够主动自觉地与兄弟宗教共享所在圈层里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和宗教信仰资源。表现在汉画内容的表达上,一个人可以信奉佛教,也可以信奉道教,还可以信奉儒教,更可以信奉原始宗教。在同一座墓室里,既可以祭祀祖先天神地祇,也可以供奉道教神灵,还可以膜拜佛教、原始宗教的神祇。由于尊重人们的教别选择权,不同宗教之间平等相处,交往互动频繁,在交往中有意识地淡化各自谱系,相向而行,基本上做到了和谐相处,没有在争夺信众资源上发生大的冲突。
(三)汉代产生多元宗教和谐格局的人文因素
宗教汉画作为汉代信仰信息的储存库,它不仅真实地保存了汉代宗教文化的演变情况,而且还形象地记录了汉代多元宗教和谐格局生成的相关情境。
如山东省冯卯乡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头戴三连胜的西王母位于第二层正中,捣药玉兔和神怪分列左右。而第三层刻绘的则是孔子双手执雁虔诚地拜伏在太上老君面前的画像[9]135。该墓建于东汉晚期,此时的西王母已是道教大神,太上老君也已是万仙之祖,成为协助西王母治理仙境鬼神的重要仙官。画像表达了孔子从太上老君处受书以升西王母仙境成仙的宗教内涵。儒门这种五体投地、毕恭毕敬的态度,在汉墓壁画中也有出现。如山东后屯出土的汉代壁画上,上层为童子跪呈西王母请赐孔子神仙书的情景,中层为孔子拜太上老君以得道受书的情景[37]。体现出尊师重道,感念仙恩之情。除孔圣拥趸道门的方外之外,孔子那成阵的桃李中也不乏循规积功以乐踏道门仙路者。如前文所表的子路,不光在邹城卧虎山汉代石椁上与西王母在一起,在微山县两城乡出土的汉画像石上,还与光仪淑穆的西王母并肩共坐[38]。这些汉画主题并不复杂玄虚,显然是儒门虔恭自豪心意的延伸。它反映的基本逻辑是,与西王母同在一处就意味着已经进入昆仑之阙的神仙录籍,被度化成了一个涵道挟术的圣真。在汉画中,儒门圣人对于仙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倾情追索和对于方外的真心向往,表明儒圣孔子及其弟子是了解、认同、接纳道门方外之学并以超脱方内尘世功名、追求西方仙境逍遥为乐趣的。他们在专言方内之同时,也是信任、钦仰方外的。虽然专任方内只以伦理为重要,但对于属于人之不可求和不应求范围之外的方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参与热情,谁又能够说得清漆园之精言和方外之宏旨不在其中。其实,通过《列子·仲尼篇》所载圣人出自西方,孔子自认为不是圣人等言论对仙境既知且信意味的流露,《论语》所载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等话语以及对孤竹国叔齐、伯夷和吴国泰伯等“颐光山林”隐士风范的称道,都可见出孔圣对于方外世界的肯定和推重态度。当然,唯以方外为本分的道门,也没有与方内绝缘。因为从东汉唯一有姓名的道士肥致的坟墓发掘来看,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墓室中的随葬品,基本上跟同期方内之人的墓葬没什么区别[39]。假若不是有碑文存在,实在不敢把肥致之墓定为真人之墓。由此可见,东汉时期道士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也没有抛却俗人的生活,这是与后来两者墓葬判然有别所不同的。再者,西王母画像出现最早的墓葬是建于西汉昭宣年间的洛阳卜千秋墓[25]。自此以后,作为汉代墓室里供奉的最重要宗教题材,西王母画像从西汉中晚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末期。这就是说,佛教在中土丧葬情境中出现的时间要比西王母晚二百来年。从佛教画像与西王母画像分布空间基本重合及佛教画像在汉墓里的载体和特征上跟西王母极为相似等方面来看,印度佛教初来乍到不仅在丧葬意义上跟西王母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而且也很可能就是抱着学习模仿的态度因循西王母画像的既有仪轨而让自己的画像进入汉代丧葬情境中的。鉴于汉代丧葬背景和人们对于其内涵理解与期待的特殊性,佛教这种向本土信仰示好的行为虽然乖违于佛教原有的宗教意义和宗教作用,将佛教画像刻绘于墓室的做法也可能跟佛教艺术在印度的追求大相径庭,但这种亲近当时主流信仰并与之在信仰形态上实现交织互构、层累重叠的方式却促成了汉代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和谐共处模式的生成。
以上诸因素,不仅成功地引导了不同人群的信仰需求,使中土汇聚了多种宗教,而且其多元和谐的宗教关系一开始就与中华多元文化一体相连。多神崇拜与排他性、偏执性极强的一神教相比所特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奠定了汉代多元宗教和谐的基础。在漫长的岁月里,汉代通过经历从单一的原始宗教到多元宗教并存互融演化的复杂过程,不仅让宗教进入了一个多元和谐共存的时代,而且还给宗教及其信众创造了一个互相尊重、友好相处的传统。汉代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经验智慧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值得学界深入挖掘。
三、汉代多元宗教和谐关系的运作机制
汉代特别是东汉中后期,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人们为了超脱苦难,从上到下纷纷沉迷于宗教。宗教需求的扩大,不仅导致多种宗教都受到尊崇,而且信仰元素采借、族群关系融洽、宗教在禳解灾殃的过程中与当地民众交往互动等机制的有机结合,也有力地推动了宗教和谐关系的运行和发展。
(一)信仰元素的相互采借
1986年6月四川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什邡县(今什邡市)白果村的一座东汉画像砖墓里发现了模印的佛塔画像砖。“这块画像砖的画面中间有一佛塔,两边为菩提树,再往两边又各有一佛塔,佛塔与菩提树相间而刻。”[40]佛塔,梵文写作stupa,汉译窣堵坡、浮图等,乃供养僧侣舍利的覆钵形坟丘。该佛塔画像的主体,由塔身和塔刹两部分构成。塔身为重楼式,即西汉武帝到东汉初这段时间汉地迎接神仙时所流行的多层木结构高楼。塔刹为覆钵式,就是把古印度的覆钵窣堵坡缩小成模型状安放在高楼的顶上。高楼体现的是汉式“仙人好楼居”的宗教风尚,覆钵反映的是印度僧侣墓葬的建筑特色。佛塔在传入中土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发展出的这种新的建筑形制,按照梁思成的解释,就是“在原来中国的一种宗教用的高楼之上,根据当时从概念上对于印度窣堵波的理解,加上一个刹,最早的中国式的佛塔就这样诞生了”[41]。佛教虽然来自印度,在不削弱宗教意味的前提下通过在自身建筑形制中加入中国宗教元素的做法,迎合了中土的审美趣味和信仰诉求,为佛教中国化的新局面提供了一个可喜的开端。
在摇钱树上,佛教画像出现的位置也常常与西王母画像相同。如成都钱币学会所藏东汉摇钱树,“树枝主体为璧,其上有西王母,坐在龙虎座上。西王母下面的璧两侧为玉兔和蟾蜍图案”[31]。从介绍可知,西王母画像出现在摇钱树的最上层位置。跟西王母所处位置基本相同的佛像,在固县出土的摇钱树枝上也有出现。在这株摇钱树上,佛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结跏趺坐,头顶上有肉髻”[42]。其画像也位于树枝的最上层中间,跟西王母一样,选的也是坐姿。后者吸纳、采借前者的痕迹明显。给佛像加上羽翼的构图,目前也有出土。如沂南汉画像石墓八角柱上的佛像,执手印,着袍,肩生羽翼[9]151,显现出融合道教画像的特征。除此之外,让佛跟西王母一样坐在龙虎座之上的造型,在汉代画像石中也多有出现。上述现象说明,作为佛教在地化过程中的一种“另类格义”,这些旨在强调虔诚皈心道教神祇之意的画像,是佛教融入中土社会、受到广大民众认可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开始知道西方的大神原来就是佛陀。”[43]这种主动改变自己以与传入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传教方式获得了人们的好感,优化了宗教之间的关系,加快了佛教在中土转生为熟的进程。
在长期的共处中,西王母画像也深受佛教画像的影响,出现了头光、肉髻、白毫相等佛教画像的固有特征。如四川泸州出土的汉代石棺上,西王母头部有圆形光环,跟此时佛像的头光相似[44]。这些构图上的变化,可能与佛像的影响有关。肉髻见于四川新都出土的汉纪年画像砖,该砖造于东汉和帝永元元年,位于墓壁左侧上层,画面中西王母居中“端坐于龙虎座上,双袖笼手置于胸前。头上饰髻,左衽”[45]。西王母头部的“饰髻”,李凇断为“肉髻”[46]。李先生将画像放入上古宗教信仰系统考察所得出的结论,比“饰髻”描述得更为具体和准确,文化内涵也更为丰富。白毫相系如来三十二相之一,指世尊眉间右旋的白色毫毛。因其处在眉心间,如日正中,佛教尊称为白毫相,汉画中常以在眉间所画的圆圈作代表。绵阳何家山2号汉画墓[47]和西昌高草汉画墓[48]出土的西王母画像上,其眉心都有这么一个代表白毫的圆圈。西王母画像所呈现出来的这些新变化,跟印度佛教画像都有很大的关联性。西王母画像构图对佛教画像特征的采借,体现了佛教画像对西王母画像的深刻影响。由此观之,佛道之间的关系,并非全如通常所言释附会于道,而实为互资为用,相得益彰。
在共处中,儒道之间也发生了吸纳和融合。例如山东微山两城乡曾出土一座东汉顺帝永和四年的纪年石祠,其西壁所刻西王母端坐于伏羲和女娲交尾形成的阴阳座上,左肩旁刻“西王母”三字,冠顶立一鸟[14]32。表现了西王母对于儒者服饰之美的欣羡。该画像经姜生等学者研究,认为其头饰或许是西王母在子路冠雄鸡影响下的“变相出现”[49]。该判断对于深入考察汉代宗教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儒道之间的交融,交织着极其复杂社会性和人文性因素,构成了有汉一代独特的宗教文化,模塑了社会文化心理的走向。
对于共处的多元宗教,中华文明不是简单地像西方那样采用排斥压制的方式来治理它们,而是秉持殊教相资、共利群庶的理念,将其纳入互相吸纳融合、兼收并蓄、随时应物、优势互补的轨道,使其慢慢走进中华文明的一元格局之中,并从国家民族的需要出发,全家国,播声名,化他为我,弃劣存优,经世致用。由于汉代的宗教基本上都敬重生命、崇尚和平,所以尽管它们各自的义理系统和表现形式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其内在精神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能够使它们在相处中碰撞出相容的火花,从而有效削减、化解教团之间矛盾的破坏力。即使局部出现了冲突,也能通过调适予以平息。这是汉代宗教间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冲突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上相互吸纳融合的过程,也就是宗教间和谐相处实现的过程。作为一种敏锐体现汉代宗教信仰的难得载体,这些反映当时宗教间相互吸纳融合关系汉画,对于我们进一步考察汉代宗教和谐生态的真实状况,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二)族群关系融洽,没有抵触
汉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中土带来了狮子、胡人等绘画艺术。作为文化交流的硕果,这些汉画蕴含着极具丰富的文化信息。凭借这些信息,不仅可以看到西域文化融入汉代宗教信仰的真实情况,而且更可以反推中外族群关系上的融通这一机制对于宗教和谐关系运行的作用。
汉画中的狮子画像皆与墓葬有关,它从不同侧面反映着汉代宗教关系与族群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供讨论的材料主要有如下几例,见表1所示。

表1 反映汉代宗教关系与族群关系之间紧密联系的狮子画像情况
狮子并非中国所产,本是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外邦进贡所得。据《三辅黄图》记载,西汉专门在都城长安建章宫旁造奇华殿以收藏豢养四海所晋包括狮子在内的奇珍异宝。“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狮子、宫马,充塞其中。”[55]179
同时,中国像翼狮这样翼神兽形象的产生系受西方广义文化的影响,也是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56]。这些外来因素被人们与传统固有的辟邪升仙观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到汉代的丧葬文化中,发展出独具中土特色的神兽文化。表中所列翼狮具有神异属性自不待言,就是无翼之狮,我们也认为它不是现实中的狮子,跟翼狮一样具有宗教属性。这是因为,例图1、2、3的狮子在拓片上虽然没有双翼,但其周围分别有凤鸟、羽人、云气等,说明这些汉画表现的不是此岸的世俗世界,而是彼岸的神异内容。特别是例图5,襄乡某君在自己墓地建浮图(按:佛塔)而且还在墓道处设置狮子、天鹿。天鹿又作天禄,具有辟邪功能。狮子与其为伍,说明狮子承担的也是这种职能。墓主将它们置放在此处,目的是让它们护卫尸首免遭妖邪侵害。这种情况说明,当来自异域的狮文化被汉代人创造性地融合到墓葬情境中的时候,表达的已经完全是中国本土的信仰观念了。
胡人,在汉代一般指从匈奴和西域来到中土的人。在容貌和装束上,他们有着迥异于中土的两大特征。一是深目高鼻。苍山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墓为配合解说墓中画像而刻写的长篇题记,其中有“前有功曹后主簿亭长骑佐胡使弩”句,而车骑过桥画像的左上一个回头“使弩”的“胡”正好就是深目高鼻的相貌[57]。东汉繁钦《三胡赋》刻画胡人形象时,使用了“黄目深睛”“洞頞卬鼻”句子[6]977,突出的也是胡人的这一特征。二是戴尖顶帽。山东微山两城乡出土“胡将军”榜题画像石上,胡将军骑在马上,胡兵向汉军冲杀。胡将军和胡兵均戴尖顶帽,深目高鼻。汉军头裹巾帻[58]。在长清孝堂山石祠西壁“胡王”汉画像石上,表现的是胡汉两军交战场面。首领身后刻“胡王”二字,胡王及其胡兵均深目高鼻、戴尖顶帽[59]。除了汉画像石中战争场合,胡人还出现在汉代人的信仰世界里,其跟不同神仙所构成的众多配置关系,极大地丰富了汉代的宗教内容。首先,胡人与羽人组合。羽人画像尽管只是汉代羽化升仙思潮中出现的一种常见现象,表达了世人对于仙境的向往,但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也依然难以排拒胡人的身影。如济宁喻屯城南东汉晚期墓出土的画像石,画面共分为四层。第一层靠左刻凤鸟,凤鸟前面有三人排成一队在跪拜,第一人为羽人,第二、三人戴尖顶帽,深目高鼻,头顶有两只仙鸟相向而飞[14]7。各个人物的特征突出,是考察胡人与羽人组合的绝佳范本。胡人与羽人围绕一定主题共同出现在同一空间并构成明确组合关系的还可举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为范例。该墓八角柱的一个侧面上,自上而下分别刻绘胡人、羽人,怪兽、苍龙、仙人和胡人等六幅画像。最上端的胡人头戴尖顶帽,其下的羽人背和腿部长有羽翼[9]151。这幅胡人羽人同时出现的画像特征明显,仙意极其浓郁。其次,胡人与瑞兽组合。麒麟、鹿等瑞兽是汉画表现的重要内容,胡人经常跟它们进行搭配。如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前室北壁立柱西面,画面分四层,下层刻一高鼻深目、戴尖顶帽的胡人骑在麒麟身上。麒麟头如鹿,生一角,角上生肉赘。另外三层则分别刻仙鸟街珠、翼虎和二羽人持物相对。在该立柱的东面,画面也分四层,胡人戏鹿图位于第三层。一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的胡人骑于鹿背,另二人一前一后立于鹿的身边。第一层为手持钩形器的羽人,第二层羽人表演倒立和舞蹈,第四层为神兽[60]。麒麟为仁兽,常出现于仙境之中。鹿是一种能助人长寿的神兽,乘之可以成仙。这些与胡人在一起的构图,充满了仙境的神奇色彩,其所表达的祥瑞观念应是确凿无疑的。再次,胡人与佛像组合。在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出现了一些胡人与佛像组合的汉画。如安县出土的摇钱树树枝佛像安坐于一块璧上,佛“头发梳成一个大髻,额中施加白毫相,大眼,口之上有髭,上翘,穿圆领衣,镶莲瓣纹边,左手握衣角,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佛旁侧跪一人,戴尖顶帽,大眼,高鼻,张口”[61]51。该类画像表现了胡人与佛之间侍与被侍的关系。上文述及的城固摇钱树佛像,其两侧人物也颇具胡人特征。“佛两旁各跪一人(其一残),戴尖顶帽,大眼,高鼻,张口。”[61]68画像显示的,分明就是胡人的特征。这些与佛像构成组合关系的胡人画像,反映了当时汉代民众心目中的“胡神”这一来华胡人在宣扬佛教过程中同本土黄帝老子一道受到供养并逐渐演变为民间祭祀对象的史实。
西方宗教元素能否进入中土信仰畛域,与族群关系融洽与否息息相关。如果没有族群关系上的和谐这一前提,就很难有外来文化元素被带进宗教信仰行为的发生,更没有宗教间的和谐相处。正是在中外族群相互交织、融通的基础上,各族群成员和各宗教信徒之间感情友好,没有抵触,实现了和谐相处,才会有西域文化元素被汉代宗教画像吸纳的可能,也才会在中土演化形成众教和谐共聚的局面。
(三)宗教在禳解灾殃过程中与当地民众交往互动
汉代宗教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宗教,其理想虽在天国,但着眼点却在尘世。无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儒教原始宗教,它们都关注世人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除儒教“修齐治平”外,上文述及的高道肥致,据其碑文记载,在天上出现主兵乱的赤气,朝阁上下束手无策的危急关头,肥致以己所擅的望气方技,“应时发算”,消除了这一凶气。“时有赤气,著钟连天,及公卿百僚以下,无能消者。诏闻梁枣树上有道人,遣使者以礼娉君。君忠以卫上,翔然来臻,应时发算,除去灾变。拜掖庭待诏,赐钱千万,君让不受诏。”[39]皇帝对肥致的犒赏不仅仅是一种嘉奖和激励,更是对高道肥致在皇朝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时,积极用道教神圣逻辑禳解难题这一做法的信任、钦仰与肯定。考古发掘中还常见解除文、道符等。比较典型的如陕西南李王村5号汉墓出土的解除瓶,其上朱书48字解除文,文右为道符[62]。用意在帮丧家解除殃灾。陕西窑店汉墓出土的解除瓶上,解除文书写于下部,凡24字,最后一句为“死生异路,毋复相忤”,其意跟《太平经》“死生异路,安得为比”相类似。道符画在该文左上[63],体现了道教对于民众死亡的关注。这些解除文、道符的出现,表明道教在积极参与民众表葬活动的同时,还以道符和解除文等神学方式替丧家劾鬼神、免咎殃、解困厄、降吉祥,给沉浸在失亲悲痛中的人们送去一种富于特色的心理宽慰新方式。由于解决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难题,所以道教的这种为生者除殃替死者解适、安冢镇墓的丧葬仪轨深受民众好评。佛教也积极介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关心民众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疾苦。只是与道教以成仙否定死亡的做法不同,佛教采用特有的涅槃说和轮回论以承认死亡,从实现对人精神安顿的角度构筑汪洋恣肆、壮丽恢宏的彼岸世界,在生活层面为汉代人提供了终极关怀。“弥补了儒道两家在死后世界构筑方面的缺憾,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生活。”[36]佛教在承负民众死后世界方面充当了积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常生活是宗教的摇篮,宗教信仰的神圣逻辑与日常生活的世俗需求交往互动,可以及时化解宗教间出现的矛盾。这是因为,在对日常生活实际问题的关注与解决中,民众不仅逐渐了解了各种宗教的基本观念,而且也慢慢习惯了在宗教所构成的氛围中交往和生活。由于宗教都把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当作立足点,获得了民众的尊重,故而各宗教之间的矛盾或何宗教优越、何宗教凡劣等不利于宗教和谐的话题,在生活这个熔炉里自然就会被搁置不谈。另外,不同宗教所特有的习俗即便给生活造成一些“不习惯”“不方便”,但在家庭血缘、亲情等纽带的共同作用下,一般都会逐渐在那不可或缺的“柴米油盐”中得到化解。通过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动,汉代多元宗教已经在对己对人的互助互益中,增进了友谊,形成了积德行善、包容并蓄、和睦相处的宗教文化联合体。它们不仅满足了社会各界的宗教需求,而且也促成了汉代宗教丰富多样的时代特色。
综上所述,汉代多元和谐的宗教关系,文化背景、社会根源都极其深刻,其生成过程、经验模式也极具经典性。通过对汉代画像中宗教之间共存互动情势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对于揭示汉代多元宗教形成的复杂因素,提炼汉代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动态机制,深化对汉代宗教关系的认知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