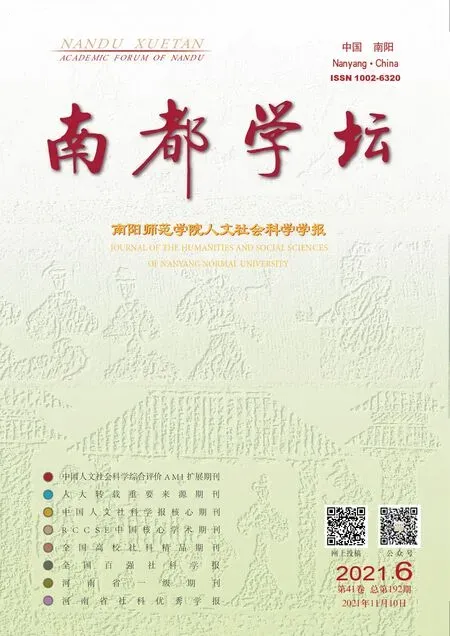汉唐间音乐审美的变迁
——以敦煌乐舞壁画为中心
郭 艺 璇
(浙江音乐学院 图书馆,浙江 杭州 310000)
汉朝与唐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两个繁盛时期,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丝绸之路,自此开启了东西方人类文明交融的新时代。敦煌石窟,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始凿于前秦宣昭帝建元二年(366),拥有自南北朝至元代数以千计的洞窟。窟内壁画的题材包含了佛教宣讲、社会生活和相当多的世俗场景,呈现了大量的音乐信息,是研究由汉至唐间中华音乐衍变不可或缺的艺术宝库。
作为中国古代音乐一段时期内的典型图像代表,敦煌乐舞壁画和两汉时期出土的乐舞画像石(砖)所呈现出的音乐信息,在音乐体裁、表演形式、演奏规模和乐器组合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传承和对比关系。同时,敦煌乐舞壁画作为历时性的音乐图像作品群集,它以更加直观、清晰和相对比较全面准确的方式反映了中国音乐在从两汉到隋唐这一时期内的发展事实,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
因此,敦煌乐舞壁画反映了中国音乐由两汉至隋唐期间的哪些发展趋势?这些变化的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审美偏好?而由此所反映出的中国音乐审美风格的变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将以敦煌乐舞壁画中的图像为主,参考两汉时期的乐舞画像石(砖)及乐器实物,对比分析中国音乐审美在由汉至唐四五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到底发生了哪些方面的改变。
一、以敦煌乐舞壁画内容为例的汉唐音乐发展趋势分析
敦煌乐舞壁画包含有关音乐主体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乐器种类和乐队编排两个部分。其中,乐器种类部分又可以细分为打击乐器、弹拨乐器和吹奏乐器三个类别。
(一)打击乐器
敦煌壁画上的打击乐器种类丰富、造型多样,约有34种2000余件。中国古代根据制作乐器的材质,曾将乐器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敦煌壁画中常见的打击乐器,主要属于金、木和革等。
先秦时期,编钟和编磬这两样大型打击乐器在宫廷雅乐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到了两汉,音乐的使用场所由祭坛、宫廷逐渐转向了日常宴饮生活,而音乐的主要功能也由祭祀祖先、礼赞王道转变为宴饮助兴和日常娱乐。俗乐兴盛、雅乐衰微,直接导致在先秦雅乐中曾占据主导地位的编钟和编磬规模缩小,并逐渐融入汉代丝竹乐队之中。在出土的诸多汉代画像石(砖)中,已鲜有类似先秦时期晋侯苏编钟[1]、曾侯乙编钟编磬[2]这样成编组的编钟和编磬出土,更多的是以特钟、特磬或者编钟编磬的规制较小,出现在丝竹乐队的边缘作为伴奏乐器使用。典型例证如山东临沂出土的北寨汉墓乐舞百戏画像石[3],它的编钟2件、编磬4件出现在画像石画面的左上方,作为下方画面中心位置的两排竽、埙、排箫、瑟等丝竹乐队和盘鼓舞舞者的辅助。
在敦煌壁画中,打击乐器逐渐变小的趋势就更加明显,石制的编磬消失不见,被铁制的方响取代。唐《乐书》记载“方响之制,盖出于梁之铜磬,形长九寸,上圆下方,其数十六,重行编之而不设业,倚于架上以代钟磬……后世或以铁为之,教坊燕乐用焉,非古制也”[4]670。方响,是一种以木为框架、上置长方形铁制音片的打击乐器。隋代的第420窟南壁观音菩萨说法图[5]217的正上方,就有演奏上下两排共5枚音片方响的飞天乐伎。随着时代的发展,石窟中方响的形制不断衍进完善,又陆续出现了两排16枚音片、24枚音片的方响。方响的声音清脆短促和石磬有非常高的相似性,到了晚唐时期,已经被广泛用于代替编磬在乐队中的作用,并沿用至今。
先秦两汉时期乐队中,青铜铸造的编钟亦被更加轻便的一系列铜制小型打击乐器所替代,包括铜钹、铜铙、铜铃、金钢铃、铜锣、串铃等。比较典型的例证是在石窟盛唐第148窟南龛[5]271,如意轮观音经变西角上由六臂飞天所持的小钟,它的外型虽然依旧保持了钟的形制,却不是用钟槌演奏,而是在小钟内部系有小舌,由飞天拿在手上,通过摇动发声。
敦煌乐舞壁画中新出现的打击乐器还有木制的拍板,陈旸《乐书·俗部》记载:“拍板,长阔如手掌,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韦编之。胡部以为乐节,盖所以代抃也,唐人或用之为乐句。”[4]660可见拍板在乐队中起到的主要作用是敲击节奏、提点句读等。它首次出现在隋代的第303窟法华经变[6]中,随后又在唐代各个时期的乐舞壁画中大量出现,可以说是石窟乐舞壁画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打击乐器之一。
打击乐器数量及种类增加最显著的应该就是敦煌壁画中出现的各种形制不同、演奏方法也各异的鼓了。两汉时期,鼓在乐队中的运用已经十分成熟。有体型硕大、在乐队和百戏中起主导作用的建鼓(山东北寨汉墓乐舞百戏画像石[7]),有放置于地面、以槌敲击的鞞鼓(四川成都宴乐画像石[8]),还有形体较小、两侧有耳、以手举之摇动的鼗鼓(河南南阳跽坐式摇鼗画像石[9])等。但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受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的影响,大量鼓类的打击乐器传入敦煌。例如手拍的腰鼓、粗腰鼓、担鼓、齐鼓、毛员鼓、答腊鼓、鸡娄鼓和以槌敲击的羯鼓、都昙鼓、节鼓、手托鼓、手鼓、大鼓、书鼓等。这些种类、造型各异的鼓为敦煌音乐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音响效果,极大扩充了音乐的表现力。
(二)弹拨乐器
从汉朝到唐朝,也是中国弹拨乐器快速发展的时期。汉代常见的弹拨乐器有琴、瑟、筝、筑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敦煌乐舞壁画上常见的弹拨乐器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出现了大量西域传入的弹拨乐器,如琵琶、竖箜篌等;另一方面是中原本土的乐器在壁画上也有大的发展。
从西域传入中原最典型的弹拨乐器应属琵琶,敦煌乐舞壁画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琵琶,它们按弦数可以分为四弦琵琶、五弦琵琶和六弦琵琶,按乐器形制可以分为直颈琵琶、曲颈琵琶、凤首琵琶等。和琵琶形制相似的西域弹拨乐器还有大小忽雷,它们都只有两根琴弦,左右各有一轴。
西域传入弹拨乐器的另一个大类就是竖箜篌,它在敦煌乐舞中十分流行,出现的次数仅次于琵琶。早期的竖箜篌形制较小,弦数也比较少,常见的有7弦、9弦、11弦等,往往由演奏者抱在怀里弹奏。隋唐之后,箜篌的体积变大,弦数也随之增多,最多的甚至能多达22弦。体积的扩张也为箜篌的装饰提供了空间,唐代的箜篌上通常绘制了精美的图案,使得整件乐器更加光彩夺目。
同一时期,中原乐器也开始在敦煌壁画上逐渐发展壮大。首屈一指的是各式阮咸,敦煌壁画早期(如北魏第254窟北壁[5]178)出现的阮咸通常直颈、音箱小、琴杆长,到了晚唐时期,壁画上的阮咸音箱变大、琴杆缩短,变化十分明显。除了传统形制的阮咸,敦煌壁画上还出现过曲颈阮咸、凤首阮咸、五弦阮咸、六弦阮咸等,形制繁复的五弦葫芦琴亦可以看做是具有装饰性色彩阮咸的变种。
中原弹拨乐器在由汉至唐的发展中,也存在形制逐渐缩小的趋势,比较明显的是瑟的逐渐消失和筝的广泛使用。瑟是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常见的弹拨乐器,箱体宽大,23-45弦,弦下有柱。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统计,已出土的实用乐器瑟长度一般在87-200 cm的区间内,其中又以165-200 cm的大型瑟为主[10]72。敦煌壁画早期出现过瑟的图像,如北周的第290窟东壁[5]203就有两件瑟并排出现。到了隋唐时期,壁画中乐伎所持瑟的数量逐渐减少,替换成了弦数更少、音箱更薄、声音更加清脆高亢的筝。
(三)吹奏乐器
汉代常见的吹奏乐器有土制的埙,竹制的笛、篪、排箫,匏制的笙、竽等,这些乐器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逐渐被淘汰,有些则不断得到改进,成为直到今日依旧广受欢迎的民族乐器,在敦煌乐舞壁画中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例如,同属低音吹奏乐器的埙和篪,埙的历史悠久、形制优美、音色独特又非常便于携带,在敦煌壁画中多有出现;而篪底端封闭,属于音量有限的低音吹奏乐器。不管是乐器音色还是乐队功能上都与自西域传入的羌笛,以及唐代由羌笛衍变出的另外两种乐器萧与尺八相冲突。因此,魏晋南北朝以后,除了在宫廷祭典雅乐中依然有少量运用之外,并没有出现在敦煌乐舞壁画中。
从现存的考古成果来看,笛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项传统乐器。不过从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西域笛乐器开始,我国笛乐器的种类得到了极大丰富和扩展。在敦煌乐舞壁画上,最为流行的笛乐器有音色明丽的横笛、高亢的短笛、低沉的羌笛和音色特殊的筚篥,此外还有形制较为独特的勾笛和义嘴笛等。排箫也属于我国非常古老的传统竹制乐器,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有广泛的应用。敦煌壁画上的排箫样式多变、应用广泛,有梯形排箫、三角形排箫、长方形排箫、雁形排箫等多种造型。
匏制乐器主要是笙、竽两种乐器,它们都是从先秦时期就被广泛应用的中原吹奏乐器,均由斗子、簧管、吹管三部分组成,两者的区别在于笙的管苗比竽更为粗短,但竽器型较笙更大。笙在唐代还发展出了区别于旧式直型吹管的弯型吹管笙,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伴奏乐器,相比之下敦煌壁画中出现竽的数量要远少于笙。
除此之外,敦煌壁画上还出现了西域传入被用于军乐的角和宗教乐器法螺。角原来是由牛角所制,后来发展为铜制的吹奏乐器,在敦煌壁画中多有出现,例如著名的晚唐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5]284上,就有队列中的军士吹角的画面。法螺即海螺,佛教中还称之为“梵贝”,是佛教护法的乐器,宗教意味浓厚,经常在早期的敦煌乐舞壁画中出现,例如北凉的第272窟[5]174就有天宫伎乐在吹奏法螺。
(四)乐队编排
两汉至隋唐时期乐队编排亦有两个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乐队的排列方式化零为整,追求更加优美和谐的音响效果;其次是乐器排布的规律化,强调乐队整体的和谐性。
在敦煌乐舞壁画中,乐队的排列分布经过了一个由零散随意到规整有致的变化过程。在早期的敦煌壁画中,无论乐伎数量的多少,常见的排列方式大多是线性散布的,典型例证如北魏第435窟[5]184的前部穹顶两侧,天宫乐伎们由小框隔开,横向排列,依次分别演奏琵琶、横笛、法螺、埙等乐器。这种长带式排列的乐队往往出现在佛像或者大型壁画的边缘,与其他带状花鸟图纹类似,装饰作用大于实用价值,音响效果上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演奏乐伎的长带式分布不利于乐器声音的集中,音响效果会比较凌乱,难以融合。因此,在敦煌乐舞的发展过程中,乐伎长带式线性排列的方式逐渐减少,更多的是向组合集群式的趋势发展。比如在一个乐队中,出现多名乐伎演奏同一种乐器来强调其音响效果(北周第290窟东壁飞天伎乐[5]203),又比如将同一种类的乐器安排在一起组成一个小乐组的形式(唐第148窟东壁北侧药师经变乐队[5]266)。这些变化不论在组合排列形式上有什么不同,都在客观上推进了乐队音响效果的优化。
同时,敦煌乐队的衍进并不是由乐队领导者或是敦煌画工随意安排的,它包含了当时乐人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总结出的审美规律。例如为了在乐队中使各种乐器的音色能够更加和谐,乐工们往往会坚持“对称”的原则。石窟佛像的左侧有乐伎,那么它的右侧也一定会出现同样人数的乐伎;又或者舞者左侧有乐工8人,那么通常右侧的乐工也是8人,这种对称原则发展到晚唐时期,甚至连两侧乐队乐工所奏乐器也要一一对称。
二、汉唐音乐审美发展趋势背后的差异分析
纵观从汉代画像石(砖)到敦煌乐舞壁画音乐内容的发展,中国古代音乐审美在节奏、音色、音响效果等多个方面,呈现出了以下几种较明显的变化倾向。
(一)音乐节奏逐渐丰富多变
打击乐器小型化、多样化的发展,一方面极大丰富了乐器的音响效果;另一方面也利于多种乐器的优化组合,敦煌壁画中流行的鼗鼓、鸡娄鼓组合就是其中的典型。
鼗鼓形制类近现代中国民间流行的拨浪鼓,体积小、手持,鼓侧系有小圆球,通过转动持柄让圆球高速击打鼓面发声,鼓声急促热烈。鸡娄鼓大小比较适中,两头较中间略细,演奏者可以将其夹在肘处,通过另一只手拍击发声,相比鼗鼓更加低沉舒缓。
鼗鼓属于典型发源于中原华夏的汉族乐器,先秦典籍《吕氏春秋》中就记载了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鼗、椎、锺”[11]。可见,在当时鼗鼓就被看作上古时期制作流传下来的雅乐乐器。
两汉时期,鼗鼓经常和排箫一起出现。例如在山东沂南出土的乐舞百戏画像石[12]247上,五人的乐队由两个建鼓乐伎、一个吹奏(乐器疑似为埙)乐伎以及两个播鼗吹箫乐伎组成。播鼗吹箫乐伎右手高举鼗鼓演奏,左手拿排箫吹奏,这是两汉时期常见的一种乐器组合形式,在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区广泛流传。而这种组合在敦煌石窟乐舞壁画中发生了改变,北朝至隋代之前壁画上出现的鼗鼓以单独演奏或与其他鼓类打击乐器合奏为主,排箫不再成为鼗鼓的组合乐器,而是作为一种主奏的旋律乐器单独大量地出现在乐队中。
隋代鼗鼓与鸡娄鼓的组合开始出现,并迅速在唐代普及流传开来。鼗鼓和鸡娄鼓的组合让一名演奏者同时演奏两种打击乐器成了可能,同时这两种打击乐器高低急缓互相配合,既能够营造活泼热烈的音乐氛围,也能够点顿分明,引领乐队的表演节奏。在北周第290窟东壁人字坡佛传故事画[5]203的正下方的飞天乐队中,就有两名飞天乐伎左手高持鼗鼓,右手俯拍放置于腹部前方的鸡娄鼓,两种鼓声呼应配合,为飞天乐队的演奏效果提供了丰富灵动的色彩。同时,乐队中还有另两名手持小钹的飞天乐伎,站在演奏鼗鼓鸡娄鼓乐伎的右侧,和他们共同组成了这个飞天乐队的打击乐部分。
这种乐器组合上大鼓(鸡娄鼓)配小鼓(鼗鼓)、革制打击乐器(鼓)配金属打击乐器(钹)的多层次灵活搭配思路,在敦煌乐舞壁画的发展中呈现出不断丰富扩充的态势。而更小、更多样的乐器形制,更丰富的乐器选材,也为隋唐时期的音乐提供了更灵活多变的韵律节拍,使得音乐在烘托乐曲气氛、渲染情绪方面的效果更加显著。
(二)音色偏好更明亮高亢
观察汉唐时期流行乐器的形制和材质上的衍进,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乐器音色的喜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先秦两汉时期,琴和瑟是当时室内音乐的主奏旋律乐器,在著名曾侯乙墓[12]240的墓葬中室,7架瑟和编钟、编磬、建鼓等大型乐器一起构筑了战国王室贵族钟磬音乐的盛大场面。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三号墓[10]72中,也出土了瑟、琴、竽、笛等陪葬乐器。瑟的箱体庞大,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实用瑟长度在120 cm左右、宽度40 cm左右,声音悠远低沉。琴的板材厚实、共鸣箱小,琴面没有品柱,演奏时需要人以手指按弦发音,音色同样比较厚重悠长。但在敦煌乐舞壁画中,琴和瑟出现的频率较两汉时期走低,壁画乐队的核心旋律乐器更多选择的是更便携的弹拨乐器如琵琶和同样为横卧类弹拨乐器的筝。琵琶体积小、琴弦短,不论是使用拨子演奏还是手拂,声音都高亢清脆,音乐风格活泼热烈。筝的箱体较瑟更纤薄,弦数较瑟少,演奏技法灵敏,音色比起瑟更加尖细明亮,又由于制作板材薄、共鸣箱空间充足,音色亦比琴铿锵。
同样的例证还出现在吹奏类乐器的迭代选择上,两汉时期乐队的吹奏乐器以陶埙、排箫、竽、笙为主,而在敦煌乐舞壁画中,最常见的吹奏乐器变成了复合材质的乐器筚篥和各种形制的笛。虽然不同形制种类的笛子之间音色会略有差异,但与土制、匏制乐器相比,竹制乐器与筚篥共鸣空间细长、材质脆薄,无疑具有更加清越明亮的音色。
音色是音乐审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至隋唐音乐逐渐明亮高亢的音色偏好发展,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在当时民族大迁徙融合背景下,社会的开放包容性不断被扩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隋唐时期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三)音响效果更加多样、搭配更灵活
自两汉至隋唐,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乐器的品类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乐队的组成人数,也由十人左右的常见规模扩充到了三四十人的大型乐队,其中不论是从西域传入的异域乐器,还是由本土古乐迭代改进的新乐器,都极大丰富了隋唐时期音乐的音响效果。同时,敦煌乐舞壁画上的乐器搭配的变化也更加灵活和有逻辑性。
一类是同类乐器的多层次组合,如在第45窟观无量寿佛经变[5]259中,无量寿佛端坐在画面中心的莲花宝座上,面前的平台两侧分列1支由7名乐伎组成的小乐队。两支乐队均由不同种类的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和弹拨乐器组成。打击乐器有羯鼓、钹、细腰鼓、鸡娄鼓、鼗鼓,吹奏乐器有长笛、横笛、排箫、筚篥、笙等,弹拨乐器有箜篌和曲颈琵琶。同类不同种的乐器集群分布、互相衬托的组合,不仅为音乐带来了更加丰富多样的音响效果,同时也能促进各种乐器表演上的互补,扩展了乐队的表现力。
另一类是乐器的模块化分区,即按演奏乐器的种类分区排列乐伎,如石窟中唐时期第112窟北壁西侧报恩经变[5]277中的乐舞场面中,就把弹拨乐器、鼓乐、吹奏乐器分列,左侧4人小乐队前排为弹拨乐器区(筝和琵琶),后排为拍板和笙,右侧4人乐队前排为鼓乐区(细腰鼓、鸡娄鼓和鼗鼓),后排为拍板和横笛。两支乐队旋律乐器与节奏乐器对应分布,吹奏乐器与拍板的位置对称,是一个非常规整的小组合,适用于空间有限、人数有限的中小型乐队。又如石窟第148窟东壁北侧的药师经变[5]267,绘制了上下两层、中心对称的四组共34人的大型乐队。上层以两名舞伎为中心,左右两侧各有一支10人三排的乐队,第一排为演奏琵琶、箜篌、筝、凤首箜篌的弹拨乐器组,第二排是吹奏横笛、筚篥、笙的吹奏乐器组,第三排分别是拍板+手鼓和拍板+铜钹的打击乐器组合。下层两支各7人的乐队,也都是5个打击乐器(都昙鼓、毛员鼓、细腰鼓、鸡娄鼓、羯鼓等)和2个吹奏乐器(横笛、排箫、筚篥)的组合。这种分区组合的思路,使得同类乐器的声音更加集中,乐器的特质和表现力得到强调,有利于乐队整体在音色和音量上的融合平衡。
(四)乐队乐器组合的音量趋向平衡
先秦两汉时期的室内乐队,不同种乐器之间的音量差异往往十分巨大。典型的比如在画像石(砖)乐队中常见的琴钟组合,琴为木制,板材厚实、共鸣箱小,音量十分有限,但中等规模的编钟直径通常有15-30 cm,特钟的直径甚至在40 cm以上,青铜钟声音悠长铿锵,这种音量上的大小差异会极大影响音乐的表达。因此,敦煌乐舞壁画中出现的乐队,开始逐渐倾向于选择音量差异不大的乐器进行组合。弹拨乐器古琴被音量更大的筝、琵琶等替代,青铜钟在打击乐中的位置则换成了携带更简便、音量更小的铁制方响和铜制的锣、钹、铙等中小型乐器。同时,前文提到敦煌乐舞壁画中的乐队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出现的乐器分组意识和搭配互补的组合偏好,使得不同种类乐器模块的音量控制成为可能,极大改进了乐队演奏过程中由不同乐器造成的音量不均衡的问题。
三、结语
无论是墓葬出土的两汉时期画像石(砖),还是敦煌石窟内的乐舞壁画,都只是当时工匠和画家们基于所处时代乐队的现实情况、出资人的要求、个人的主观创作意向、绘画制作的客观环境和工艺技术限制等客观条件所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它们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古代历史上音乐发展的细节,但却没有能力反映所处年代音乐发展的全貌。即使如此,这些音乐图像所呈现的内容还是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客观性,为我们了解这段时期内中国音乐审美的大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前文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汉至隋唐时期的几百年,是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最后又重回统一的过程,是民族融合、多种文化高频交流的重要时期,是西乐东渐、乐器大发展、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彼此交融的关键时间段。在此期间,汉唐音乐的审美偏好由舒缓沉稳走向轻盈流丽,不仅在音色探索上愈发多样包容,同时在音乐组合上也更注重对整体音响效果的优化,变得更加有逻辑性和呼应感。这些审美偏好的变化一方面源于中国历史上流行乐器自身的融合和衍化;另一方面也受到音乐及乐器演奏场景、使用情况变化的影响。同时,外域音乐的传入和流行,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