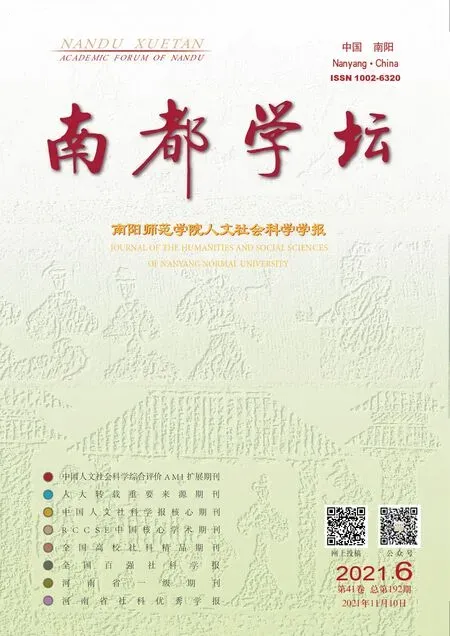论两汉琴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季 伟, 李 培
(1.南阳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2.南阳电视台,河南 南阳 473061)
两汉琴乐发达,琴家辈出,琴论增多,在民俗色彩浓厚的汉画乐舞画像上刻画有大量古琴图像。在汉代,琴的表现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姿态,既有大气磅礴的集体演奏,也有精巧细致的琴歌琴舞,更有情怀独居的独奏。笔者以汉代古琴为载体,曾对丰富的汉代古琴文献进行了分析比较[1],对汉代民间不同质别的弹琴类画像文物进行了甄别[2],对汉画中琴的丰富表现形式进行了归类[3],在此基础上,也对两汉古琴文化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进行了总结[4]。那么,两汉琴乐文化除了上述所研究的特征之外,还有什么特征?这些特征又折射了汉代哪些信息?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
一、两汉琴乐的开放性
两汉琴乐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折射了其多元开放的发展态势,这些态势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走进民间
先秦以来,礼崩乐坏,宫廷琴师四散至民间。古琴并未停滞在当初的雅乐身份状态上,而是放下了身段,积极参与对接到列国的民间音乐发展融合当中,这期间也产生了一些诸如师襄、师延、师旷等民间琴家。汉代亦然,不但民间琴家众多,而且在民俗色彩浓厚的汉画像中,刻画了众多的鼓琴图,说明两汉琴乐与民间结缘的诸多状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与民间歌谣结缘。先秦时,古琴进入民间,与民歌结缘。孔子将其引入《诗经》之中,成就了弦诗三百。汉代社会延续了此种状况,琴在全国各地开始与民间歌谣结缘。汉代社会一统,民歌在以往成就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琴也开始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河南南阳军帐营出土的汉画像石上,一组歌女七人,四坐三立而唱歌,旁边有以琴乐为主的丝竹乐伴奏。这就是具有代表性的、被文献称之“被之管弦”的“一唱三叹执节者歌”的相和歌。同时能够充分反映这种现象的,还有民间出土的独奏歌唱俑。尤其四川等地出土的弹琴俑,表现的就是利用古琴结合民歌所形成的的汉代琴歌。这些弹琴俑与歌唱俑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早期为无丝竹伴奏的民间歌谣“徒歌”,后来随着时代发展,逐步加入了琴瑟等丝弦乐伴奏,成为风靡一时的融民歌、舞蹈、器乐为主的相和歌。此类画像文物在全国发现得较为普遍。
其二,与民间舞蹈结缘。先秦古琴进入民间,与舞蹈结缘,故《诗经》也有着舞诗三百之说。汉代歌舞繁荣,琴与其他乐器组合成乐队,在歌唱和舞蹈中大放异彩。司马相如在描述西汉娱乐时说,“千人倡(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5]66。张衡《南都赋》则描述了东汉乡绅们娱乐时歌唱的婀娜多姿,“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5]460。其中,琴就是一个重要组成因子。
汉代俗舞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由专业伎乐人员表演的、艺术性专业性较强的、较为工整的舞蹈,如长袖舞、七盘舞、建鼓舞等;一类是由民众参与娱乐的、社会性较强,而非注重技巧性的舞蹈,如以舞相属等。在这两大类当中,一则尚工;一则尚俗,风格炯异特色突出。如长袖舞优美华丽大气,时而舒缓时而激扬。又如建鼓舞,节奏以刚健激越著称。琴能凭借自身的优势,以丰富的表现形式烘托参与其中,成为这些舞蹈不可或缺的和乐伴奏之器。在全国各地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砖石中,真实地再现了这些场面。
在四川成都新都区出土的画像砖中,刻画了琴参与以舞相属的画面:左为两舞者,男者头上着帻,上穿紧身衣,下身穿长裤,正回首提脚举巾作舞。女者头挽高髻,身穿右衽广袖长裙,细腰束带,回首顾盼男者,臀部后翘,举巾起舞,体态轻盈,优雅含蓄。图右两人跽坐,一人双手鼓琴瑟,同时张口歌唱;一人右手击一小鼓,左手抚耳歌唱。画面中四人服饰相同,舞式小而生活化,姿态举止属常人,席前有饮酒器物,应为自家厅堂举行的宴饮娱乐[6]168。这犹如文献所云:“玉樽延贵客,入门黄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琴瑟为清商。”[7]这一切说明,琴在汉代宴宾舞蹈中的作用。
其三,融入百戏。汉代是百戏的繁荣时期。在汉代文献中有“白虎鼓瑟,苍龙吹篪”[5]419,“侏儒巨人,戏谑为耦”[5]384等记述,说明古琴走入民间的同时,也与百戏结缘,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也真实地再现了这些场面。
在画像中,琴伴奏百戏的方式主要以乐队为主。如在南阳草店出土的西汉画像石中,刻画了一琴伴奏,三人歌唱,三人百戏乐舞的画面。此为墓室右门楣石,石上共刻九人。左边第一人立姿,执金吾,第二人坐于案前,当为主人观乐,第三人跽坐膝上置琴双手鼓奏,中间三人跽坐歌唱。右一人为俳优作滑稽表演,一人樽上单手倒立,另一人扬长袖,屈身作舞[8]164。
在四川成都羊子山2号墓出土的画像砖上,乐队的组合较为简单,属于一琴三排箫,百戏呈现出俳优、巾舞、剑舞、弄丸为一体的综合特征[6]167。图左上方为伴奏乐队,女伎吹排箫,男伎鼓琴,下方两乐伎捧萧吹奏。图右上方两伎上身赤裸,一伎弄丸,一伎左肘击瓶,右手握剑向上,剑尖正挑弄一丸。图右下方俳优赤身突腹,屈膝张臂,一手执桴,边舞边唱,诙谐滑稽;对面一女伎,头挽双髻,细腰束带,手执长巾,侧身向后,左足向后向上提,正用足尖蹈其覆盘,同时双手持长巾起舞。图中有酒具汤勺之类的炊具饮具等,应在厅堂之内。
在河南南阳七孔桥出土的画像石,则出现了琴、鼓与百戏的配合。画面左起两细腰女子相向倒立于樽上,中部上层一男一女跳双人舞,下有一乐人跽坐,琴置膝上双手鼓奏,右旁两细腰女子各击鼓伴奏。其中琴为旋律乐器,鼓为节奏性乐器,皆可烘托气氛,此伴奏形式是琴和鼓的配合。画面简洁,内容集中,也是在厅堂中[8]180。
历史记载也与汉画图像内容相吻合。《盐铁论·散不足》载:“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办)歌舞俳优,连笑伎戏。”[9]353-354连民间办丧事也要表演歌舞技戏,可见这些艺术形式在当时已广为流传,成为重要的待客之礼。这种民间的习俗,也被官方拿来采用。同书又载:“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而况县官乎?”[9]437这说明,在汉代,琴已经融入百戏之中。
(二)挺进朝堂
两汉时期,金石雅乐衰微,在俗乐兴盛和独尊儒术的背景下,琴依托自身优势,成为集礼器、乐器、法器为一身的集合体,不但在朝堂上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神秘与高贵,也成为两汉君臣们推崇的对象。
其一,琴是汉廷乐器。在娱乐方面,琴乐经过春秋战国的革新转型,以其特有的底蕴和表现成为众乐之首,跃为新乐代表。如上文所述,琴参与了汉代所有的乐舞表演,无论是抒情自娱的独奏,还是帮腔和乐的伴奏,琴都能充分地参与其中。
汉初高帝乐楚声,俗乐挺进朝堂,琴乐伴随其中。高帝所唱《大风歌》,被乐师改编成琴歌,进入雅乐序列,使得琴乐在汉廷影响深远。淮南王刘安不但习尚琴曲,还亲自创作了《八公操》。武帝时期,民间琴乐进一步繁盛,出现了不少的琴家高手。武帝每遇大事要事,都要乘兴而起,即兴作歌。为了能听到心仪的琴声,特在宫中设立琴待诏,招民间弹琴好手到宫中献艺。在重建乐府时,特设了“琴员工”一职,造琴修琴。同时,诏司马相如、李延年等入驻乐府,创作琴歌辞赋。
汉代琴乐挺进朝堂,琴成为宫中崇尚的乐器。汉元帝每遇到大事,便乘兴作琴歌诵徘辞。宣帝励精图治,看到国家逐步强大,也禁不住雅兴大起,创作了不少琴歌徘辞。东汉光武帝更是喜尚琴乐,常让桓谭为他弹奏民间新声。汉桓帝不但特别善弹古琴,还会吹笙;汉灵帝常在后宫弹琴吹箫,搞琴箫合奏。汉帝们如此喜好琴乐,除了琴所具备的深厚底蕴外,与琴师开放的思想及不断革新其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二,琴是汉廷礼器。进入汉代,携上古神韵与实用为一体的古琴,成为汉廷礼器的最佳承载者。而在这些礼乐言论中,琴所承载的这些信息是较为丰富的。而儒家依托琴所产生的论述、论著也是不胜枚举,如《琴赋》《琴道》《琴论》《琴清英》等。
在汉代画像中,有不少弹琴画面,均是两旁人物矜持站立静听,中间一跽坐者双手抚琴,神情严肃庄重,而周围环境是深宅大院。很明显,这些弹琴画面,不仅仅是弹琴娱乐,同时也融入了深厚礼乐之法,众人听琴可以受礼乐之道的教育。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将军冢出土的东汉大型乐舞画像石,其场面宏大,钟鼓管弦各类乐器一应俱全,并有严格明确的分组[10]。在这样的乐队当中,琴与其它乐器成组严谨排列。很明显,这是一场大型的、仪式性的礼乐演出。
《史记》对琴的此种功用,给出这样的论述:“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11]314《史记》对琴的界定,也与金石钟磬一样,属于礼乐之器。而儒家经典《乐记》,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其云:“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1]230东汉依然延续了这些思想,《白虎通义》对于琴的定义是:“琴者,禁也。”[12]101所谓的“禁也”,就是禁止淫邪,教人向善。明显,这些官方文献对琴的定义就是礼法礼教之器。
其三,琴是汉廷法器。大乐与天地合德,大礼与天地同节。上古时期,琴具有通天应地沟通人神的神奇作用。两汉巫风弥漫,使得琴的这项功能得以突显。琴和乐成为巫祭的最佳载体。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虽然礼乐治天下成为主旨,但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将儒家理论与黄老思想汇聚于一炉。借助于儒道思想和原始信仰,借助于古琴的法器载体及特有的法天神韵,琴成为汉代人心目中理想的通天之器。
史载汉武帝祀仙好巫。为求得长生,汉武帝在长安四周布设高楼,带领乐府中的童男童女彻夜笙歌,目的是招引神仙下凡。汉武帝还经常将遇到的一些神奇事象,即兴为歌乘兴为赋,让李延年等谱仙乐。如元鼎四年的《宝鼎之歌》《天马之歌》。元封五年,七旬的汉武帝亲射蛟龙于水中,作《盛唐枞阳之歌》。太初四年春,汉武帝获得向往已久的汗血马,即兴写下了《西极天马之歌》等。这些歌辞基本上都成了汉乐府中的仙乐、仙舞和琴歌。汉武帝还令李延年和司马相如,将张骞从西域带回的乐舞《摩诃都乐》改编为国家的祭典大乐,这就是著名的《郊庙十九章》。
在《乐府诗集》记载的汉代乐种乐器组合中,琴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平调曲在描述乐器的演奏程序时说:“未歌之前,有八部弦、四器,俱作在高、下、游弄之后。凡三调,歌弦一部,竟辄作送。歌弦今用器。”[13]356又如,清调曲:“未歌之前,有五部弦,又在弄后……”[13]393瑟调曲、楚调曲也无一例外地有类似记载,这说明琴在乐队中,具有重要的引领功用,也同时说明琴是众器之首,也是汉廷中的迎仙祭神的重要法器。
(三)融入信仰
两汉礼乐治国,“士无故不撤琴瑟”。琴所具备的修身、齐家、治国等功能,成为士人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也成为汉代人的信仰之一。
先秦时期,孔子倡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琴所代表的乐教文化,成为汉代士子们的主要信仰,故汉代士人好琴、尚琴、崇琴。《史记·乐书》云:“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14]《史记》开宗明义,指出礼乐与君子的关系,那就是礼致外、乐致内,礼体现刚性原则,乐体现柔性之美。故而后一句“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更明确指出乐音者就是君子们的信条,不可须臾离开,需时时牢记。
大儒刘向的《琴说》将弹琴的利好总结为七点:“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15]13在以上七点利好中,“明道德”成为首选。刘向还在《雅琴赋》云:“观听之所至,乃知其美也。潜坐蓬庐之中,岩石之下。游子心以广观,且德乐之愔愔。末世锁才兮知孔寡。穷音之至人于神。弹少宫之际天,援中徵以及泉。葳蕤心而息愬兮,伏雅操之循则。”[5]153刘向在赋中,将琴声之美描述为“德乐”,将弹琴的动作称之为雅操。这种音乐不但可以娱人,也可娱神。
东汉亦然,大乐师及琴家桓谭,将其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提出了“琴道”的观点。《新论·琴道》:“八音之中,惟丝最密,而琴为之首。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八音广博,琴德最优。”[16]63-64桓谭提出“八音之中,惟丝最密”,将琴乐提高到了超越金石之乐的高度。而“八音广博,琴德最优”的提法,说明琴的地位已经远远高出金石礼器,并成为最佳替代物。而“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及“君子守以自禁也”等,这是古代圣贤的信条,也是汉代士人君子所遵奉的人生信条,不能违背。
士阶层的推崇,使得琴在民间的影响更大。在汉代出土的画像石中,有不少弹琴画面,常常是主人正襟危坐,双手俯仰屈伸弹奏琴乐,旁边有少量婢女或仆人矜持站立。整个画面,就是一幅明显的深受古琴陶冶的乐教图。四川地区出土的弹琴俑以及各地民间出土的大量弹琴画像砖石,也许能更好地说明这一切。琴于民间虽然以实用为主,但也包含着礼乐信仰。
汉代民间信仰杂多,涉及山川湖海、日月星辰、门灶井户、先祖圣贤及鬼神精怪等。《风俗通义》说:“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时盛矣。至平帝时,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17]350地域不同,信仰也不同,如中原和西北地区崇拜西王母。在其他地区,有的信仰自然神祇,如山神、河伯、海神等,还有一些崇拜神树,如桑树、栗树、桃树等。信仰虽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需要适时祭祀。而祭祀,需要乐器法器作为媒介。如此,琴也逐步承载这些信息,成为民间诸神信仰的象征。
如西王母崇拜在汉代风靡,就因为西王母是一个主管生死、婚姻、生殖等的神灵。在汉画艺术中就有不少琴乐伺服西王母的画像,目的就是祈求长命百岁、家庭和睦、子嗣兴旺等。而类似神树崇拜,也属此类。树在汉代是生命的象征,是家族兴旺发达的标志,在汉代画像中均有大量树的刻画。在大树下或周围,往往有跽坐弹琴者,说明神树的崇拜和祭祀也需要古琴和乐舞。而类似其他的画像,也有弹琴的画面,如郊野中,或者山川平原之中,或者乡村社里等。这些画像,都足以说明琴在汉代所充当的重要功用。
二、两汉琴乐的包容性
两汉古琴的开放,促使琴的发展更为多元化,尤其在文献记载和汉画图像中,其形式多样,题材众多,呈现出包容万象的特征。
(一)雅俗性
两汉思想博大开放。秦亡的教训,时刻警醒着汉室的君臣们,为此统治者实行霸王道而杂之的统治思想,在琴乐领域也体现了这些特征。
其一,琴是雅乐。雅乐是上古先秦时期代表王朝宫廷的音乐,是统治阶级意识的体现。雅乐主要用金石之器和丝竹之器等来演奏。汉代雅乐既包括上古乐舞以及周秦时的音乐,也包括汉代改创的音乐以及在民间搜集上来的音乐等。在这几部分雅乐中,琴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古琴进入雅乐序列。礼崩乐坏后,轻巧实用的丝竹乐兴起,琴瑟等成为时代的宠儿。汉代继承了这一切,一方面,琴以其特有的神韵走入上层社会,帝王后妃们喜欢琴乐,成为身份高贵的象征。汉武帝重建乐府时,大力采集民间俗乐,这些被改良过的民间歌辞及新编的乐歌乐舞进入宫廷,逐步成为汉廷的宫中之乐。琴在宫廷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另一方面,汉代流行的丝竹乐队中,琴的作用巨大,被汉儒们推举为“众器之首”。
在《乐府诗集》记载的汉乐府相和歌辞中,就有大量的琴歌弦歌等。《风俗通义》将琴定位为“乐之统也”[17]293。大儒刘向将弹琴视为“明德”之举,桓谭又将其上升到“道”的高度。由此,这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使得琴的地位飙升,成为雅器。琴同时还是汉代丝竹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琴也是俗乐。琴的包容性,还体现在琴在某种程度上是俗乐。古琴参与了大量的民间乐舞活动,无形中成为俗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俗乐主要体现以下特征。一是节奏欢快;二是抒情恣意;三是激越狂放。在这几个方面,琴均有大量的参与。在汉画中,体现专业技能性较强的舞蹈中,可直观地看到琴参与的各种俗乐活动。如体现激越奔放的建鼓舞,琴的表现就以快速激越为其特征;如抒情华丽大气的长巾舞,琴的伴奏就以抒情缓慢为其特征;如快捷迅猛的短巾舞,琴的弹奏以其激越、快速为主要表现特征;融迅捷、华丽为一体的盘鼓舞等,其旁边更有古琴的烘托渲染。
汉代社会宴宾乐舞风气异常浓厚,琴乐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琴在这些场合,皆以娱乐为主要目的,其节奏快速、动作激越、抒情华丽,突出的是大开大合的情感宣泄。在先秦及两汉士人的心目中,弹琴的场合应该是清虚、雅致、幽静的,而非笙歌艳舞、狂放不羁的宴乐场所。但在汉代文献和汉画像中,琴可谓是:“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寮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裔裔。”[18]这种用琴瑟弹奏异域激越民间音乐之法,已远超雅乐的标准。琴在汉代已经成为俗乐的代表了。
其三,雅俗一体。所谓雅俗一体,也就是琴包含了以上两种音乐形式。一则庄重典雅温润敦厚;一则激越华丽优美抒情。两种风格迥然不同的音乐集中在一件乐器上。
汉代音乐的组成包括两部分。其一,自进入汉代以来,在叔孙通的主持下依照先秦雅乐的模式,从先秦以来继承的雅乐,如六代乐舞等不断地得到修改增删。如将《韶舞》改编为《文始舞》等,以及新创作《昭容乐》《礼容乐》等。其二,是重新制礼作乐和重建乐府后,在李延年和司马相如的主持下增修创改而成雅乐。其中,一部分是朝廷创作的相和歌辞,如汉高祖的《大风歌》、汉武帝的《宝鼎歌》《天马歌》等。这一部分乐歌经过改编成为琴歌或者相和歌辞,最终进入太乐的序列。另一部分是根据外来的音乐进行改编创修的,如张骞从西域带来的《摩诃都乐》等。在汉代风靡的丝竹乐队中,惟琴地位最高,被汉儒们推崇为“乐之统也”,在八音之中,琴德最优。
但是,先秦礼崩后,古琴还有一支融入了民间,以弹奏民间音乐为主体。那么,琴在民间的这一支,就一直沿着民俗化的方向在走,以弹奏民间民俗音乐为其主要特征。民间古琴由于其作品较为世俗化,也深受宫中欢迎,后来汉武帝重建乐府后,民间古琴以琴待诏方式进入宫廷。上文所说的西南巴渝地区司马相如、东南夷的东海诸郡的赵定、龙德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因此,在汉代宫中实际上存在三种古琴音乐。一是弹奏艰涩难懂的先秦古雅乐的古琴;二是司马相如及其后代创作的新作;三是汉廷喜欢的民间音乐和自己创作的相和歌辞等。这三种古琴音乐,融古雅、近雅、新雅为一体。所谓的近雅、新雅,其实就是优化后的俗乐而已。汉代君臣,对古雅乐均不感兴趣,其所欣赏琴乐均是优化后的俗乐。由此,在汉代民间,琴乐同样融雅俗为一体,既有修身养性的士人琴乐,也有弹奏俗曲、伴奏俗乐的相和之乐。琴在汉代社会是融雅俗为一体的。
(二)礼俗性
汉画中的古琴,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礼俗性。所谓礼俗性,就是一定程度上具有民间仪礼之乐和礼俗之乐的功能和特征。
其一,琴是民间礼乐。两汉礼复乐兴,金石衰落,丝竹兴起。董仲舒认为,乐与礼一样是移风易俗的方法,“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19]2499。在文献中,《礼记·曲礼》中,将君子无故不撤琴瑟,作为衡量生活之礼的重要标准。《风俗通义》载,“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虽在穷阎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17]293,认为琴是君子最亲密的朋友,即使在穷乡僻壤或深山幽谷,犹不能失琴的情怀。这种观点与《史记》等同出一辙,只是《史记》认为琴音调和就会天下大治。而后汉《白虎通义》的“琴者,禁也”也是此观点的延伸。
在汉画像中,琴的这种礼乐功能,并没有因俗乐的兴盛而消失,反而不断在加强。在汉画中,刻画有聂政刺韩王、荆轲刺秦的惩暴扬善故事,在刻画的许多深宅大院中,很多画面是众人矜持站立,围绕着一弹琴老者在听琴。很明显,其中的礼教信息不言而喻。在汉代民间琴家的作品搜集当中,仍然有诸如《微子操》《舜畅》《文王操》等歌颂圣贤的作品。这说明,汉代古琴礼乐教化的思想,仍然在民间盛行。
总之,在汉代社会,这种思想是纲举目张,上下一体,朝野与共,其所主张的学说和贤雅精神,仍然在左右着民间汉代礼乐的发展。
其二,琴是汉代民间的玩器。汉代俗乐发达,丝竹繁盛,以琴为首的丝竹乐,成为时代的佳音,充斥于各色娱乐宴饮当中。
在汉代,民间琴乐依然有着繁盛的特质。这些特质大部分是以娱乐玩赏为其主要特征。《淮南子·修务训》描述一位西汉民间盲人弹琴的情景:“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篾蒙,不失一弦。”[20]说明西汉前期琴艺已十分高超,已具备攫援摽拂四种鼓琴手法。而这些手法,均是古琴与民间俗乐相互融合的结果。如果缺乏民间音乐的滋润,不可能迫使古琴做出改变,也不可能让过去的礼乐之器,成为演奏俗乐的高手。
哀帝罢乐府后,大量宫廷乐人回流民间,对民间琴乐的提高普及起到很大的反哺作用。风靡一时的相和歌,按张永的《伎录》的说法,就是琴、瑟、筝、笙、筑之曲与歌唱的混合体。而在《乐府诗集》所记载的琴歌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民间俗乐的基础上改编的。两汉琴乐的繁荣,使得弹琴、听琴、赏琴成为时尚。赵国、中山国等地会弹琴的姑娘们,在两汉炙手可热,“弹弦跕屣,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19]1655。因为民间琴乐的繁荣,使得弹琴成为汉代社会热门的职业。
在这个大环境下,琴一度成为全国的娱乐之器。在偏远的赵国、中山国故地,经常是“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类似的还有《盐铁论》中对民间古琴繁盛的描述,如在荆扬这个偏僻的地方,虽然住的简陋,但是对于歌讴和鼓琴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偏远地区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发达地区就更不言而喻。这也说明,琴乐和弹琴和乐歌唱,已经成为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古琴在这里,也只是一件普通的乐器玩器而已,其民间形象朴实生动。
其三,礼俗一体。所谓的礼俗一体,就是琴在民间也具备礼乐与俗乐为一体的属性。如桓谭《琴道》中,一边主张琴乐要创新,要多从民间汲取营养;一边仍要保持一部分雅乐礼乐的属性。琴及琴乐具备以上礼乐与俗乐为一体的功能。他在大量弹奏民间新声的同时,又在整理《微子操》《尧畅》《文王操》。在民间,琴时而是礼乐之器,时而是娱乐之器。“礼是成文,经过国家制定,期于能使上下共同奉行的。而俗则是一般的惯习,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大致说来,礼,是范围人心,引导大众为善的;而俗则是有善的,也有不善的。”“(礼)被公认为合情合理,有范围人心和维持、安定国家社会的效用,而且易于施行,于是由政府采用,或者更加以斟酌损益,著之文书藏之官府。”[21]礼是向善的,俗不一定都是善的。
在汉代雅乐过于古涩也缺乏实质的变革,但如上述所说,雅乐具有修身之作用,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会对俗乐中的不良部分,起到抑制和校正的作用。这也许就是两汉琴文化既矛盾又统一的地方。俗乐不一定都是向善的,但俗乐具有娱人的作用。汉代琴家如桓谭、龙德、赵定等人,一边弹民间俗乐;一边推崇古琴的修身养性的作用。而在汉代的士人当中,也几乎呈现出类似的情况。故而,琴就是礼俗一体的重要体现形式。
(三)华夷性
所谓华夷性,一方面,琴乐是华夏正声的代表,代表着古老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琴也包容了夷狄的文化,融华夷为一体。
其一,琴是华夏正声。所谓华夏正声,就是以夏商周时期所形成的中原王朝早期京畿音乐。这些音乐以体现统治者治国的功德、颂歌等礼乐文化为核心,是中原文化的原始组成部分,是元文化。西周时期,琴乐进入雅乐序列,成为宫廷礼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还设立“琴师”一职教育贵族子弟。而这部分音乐,也是后世所谓的华夏正声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里,琴突出的是其文化内涵和象征作用,其文化象征意义大于实用价值,也是华夏正声中最为纯粹的一部分。
两汉社会虽然民俗意味浓厚,但统治阶层复古意识却十分强烈。上文所述,琴是雅器、琴是雅乐,是代表士人阶层及统治阶层的象征之物。而在崇尚儒家治国的汉代,古琴所蕴含的这种礼乐精神,恰恰是汉代社会所推崇的。琴虽然走进民间融入大众,但其作为华夏正声的象征成分依然非常浓厚。尤其在礼乐文化强大的中原地区,琴的这种修身养性的特性更为突出。此特性就是从上古先秦华夏正声的核心思想演变延伸而来。因此,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华夏正声的代表。
其二,琴是四海归一之代表。两汉时期,琴居八音之首,不但承袭了金石礼乐的精华,也是汉文化强大的象征。随着国家的统一,中原礼乐文化开始在四夷地区传播普及。如何能有效地传播国家的意志。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作为华夏正声的核心组成部分,琴乐在其中充当重要的载体。琴取材方便,易于制作,同时轻巧易带,表现力丰富,很容易成为传播礼乐之道的重要载体。两汉崇儒之风盛行,借助于古琴,其小能伴唱伴舞,相和而歌;其大又可传播礼乐之道,移风易俗,可谓是一举数得。
西南夷的巴蜀之地,汉初仍处于蒙昧状态。汉景帝时文翁治蜀,选川蜀贤良子弟到京师太学接受礼教之道。此举措也同时开辟了琴乐的入蜀之路,蜀地琴风由此大盛,不但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的弹琴妙手,也在民间带动了一大批人好琴、尚琴、学琴。在四川新都、大邑、广汉、乐山等汉墓中,出土有大批抚琴俑或琴乐图;在遍及蜀地的摩崖造像上,刻画有不少鼓琴图,这均是蜀地琴乐繁荣发展的最好例证。而在远离成都紧邻西羌的雅安,也竟然在汉阙上刻画有师旷鼓琴图。在这些弹琴画像中,有一部分以高鼻深目宽颜的少数民族人的面孔出现,说明汉代蜀地琴乐达到了相当发达程度,且已在少数民族区域广泛流行。
战国时,善弹琴的邹忌,受齐威王重用,被封在邳地做官。在邹忌的影响下,原本偏僻的这里,琴乐开始兴盛。汉武帝时已出现像师中这样的民间高手。刘向在其《别录》中说:“至今邳俗犹多好琴。”[15]12可见,此风已经积淀很厚了。又如,渤海赵定,善弹古琴,手法高妙,当他弹琴时,听之者“多为之涕泣”[22]。龙德是梁国人,也非常善弹琴,他和赵定都是宣帝时被封的可以进宫献艺的“琴待诏”。师中、龙德、赵定不但琴弹得好,且都有著述问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雅琴赵氏》七篇,《雅琴师氏》八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19]1711
在江苏、山东等地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砖)中,弹琴的画面可谓比比皆是,反映了这些地方民间琴乐的繁荣局面。而类似的陕西、内蒙古出土的弹琴图等均说明在这些区域,琴乐已经渗透其中。《盐铁论》云:“荆、扬……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赵、中山……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9]41-42连荆、扬等偏远的地方,弹琴也已经相当普遍了。可见,琴乐已经体现了四海归一的局面。
其三,华夷一体。华夷一体,就是少数民族音乐和中原音乐同台演出相互融合。在开放包容博大的汉王朝中,四夷之乐也融入中原,成为汉代君民享受的对象。
《西京杂记》载,汉高祖“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23]。《于阗乐》是西域古乐,说明西域之乐于汉初已经传人宫中。而东南越地著名的船歌《櫂歌》在西汉时期传至京师,为皇室贵族所喜爱,汉武帝在昆明池舟楫娱乐时,就喜唱这支歌。汉武帝时,西南少数民族的乐舞也传入中原。《子虚赋》就曾记述了《文成颠歌》,“颠”同“滇”,即今云南等地。东汉时,“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22]3272。类似的还有东北高丽国的《箜篌引》等。这一系列的影响,使得这些异域艺术,在汉代朝野上下,刮起了一阵学习热潮。
司马相如《上林赋》云:“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5]66西汉天子大宴四海宾朋,四夷“狄鞮之倡”与中原“郑卫之音”及“韶濩武象”古乐等济济一堂,融洽无比。班固《东都赋》云“天子受四海之图籍,应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乃盛礼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金石,布丝竹……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5]330。班固的《东都赋》中描绘的四夷之乐与中原古乐相得益彰,已成为东汉在重大礼仪场合有机的组成部分。
张衡《西京赋》对此记载得更详细:“大驾幸乎平乐……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鷰濯,胸突铦锋……总会仙倡,戏豹舞罢(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5]419在以上这些音乐演奏中,作为众器之首、乐之统领的琴不但弹得好,还得带上华丽的代表少数民族的图腾面具(白虎、苍龙等)。可见,琴乐已经与少数民族的音乐融为一体了。而汉画中,大量的弹琴图像以及四川出土的高鼻深目、宽颜环眼的胡人弹琴乐舞俑的图像反映了民族融合之风。
三、结语
总之,琴在两汉的发展,呈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与两汉特有的气质及琴本身所具有的属性紧密关联。一方面,汉王朝发迹于草根,实行的是霸王道而杂之的统治思想,其思想开拓进取,行为追求事功,凡是能为我所用的皆可容纳。另一方面,琴自上古先秦就被视为具有沟通天地的神秘功用,西周时成为雅乐的化身,两汉之际为统治阶层所喜爱,加之儒家思想的确立,又成为士人心目中的修身之器。两汉乐舞的转型,琴以其丰富的功能参与其中,成为俗乐兴盛的参与者,成为民间的乐器。这一切因素,使得琴乐琴文化与两汉特有的环境融为一体,琴同时博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由此产生了质的变化,呈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