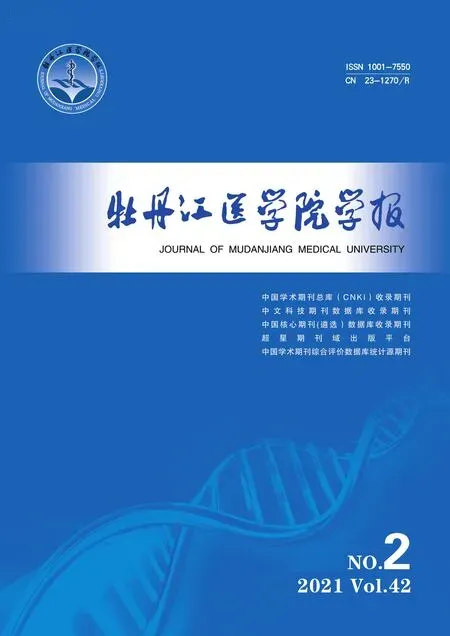组织定居B细胞的免疫学特征研究进展
刘 洋,闫冬梅
(1.佳木斯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病原学部,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上海 200040)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科学家们相继发现了许多组织内的“非循环淋巴细胞群”[1]。它们不参与血液循环,无需抗原提成、细胞激活就可发生快速的免疫应答。最近的研究表明,肺部组织定居记忆B细胞在流感病毒二次入侵后,提供了比淋巴器官中的循环效应细胞更快速、更有效的保护[2]。“组织定居”一词意味着这种非淋巴组织中的淋巴细胞群与在血流、淋巴器官和外周组织中循环的相应淋巴细胞极少交换[3]。组织定居淋巴细胞[4]主要包括:TRM (tissue-resident memory T cells)、iNKT (invariant natural killer T cells)、MAIT (mucosal associated invariant T cells)、γδ T cells、IELs (intestinal intraepithelial lymphocytes),ILCs (innate lymphoid cells)和BRM (tissue-resident memory B cells),其中组织定居B细胞(BRM)于2019年才被明确鉴定[2]。
1 组织定居B细胞的发现过程
经典免疫学认为:抗原初次入侵后,从骨髓迁移到外周淋巴组织的原始B细胞被活化,它在滤泡树突状细胞(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s,FDC)和T细胞帮助下形成生发中心。活化的原始B细胞经历了增殖、免疫球蛋白可变区体细胞超突变、免疫球蛋白同型转换后,离开生发中心,分化为产生免疫球蛋白的浆细胞或记忆性B细胞。浆细胞储存在骨髓中,记忆B细胞贮存在外周血或次级淋巴组织中。循环系统中记忆B细胞发挥了有效的免疫调节作用,它产生的抗体比骨髓中浆细胞产生的抗体更快地到达病毒入侵部位[5]。传统观点肯定了循环系统中的淋巴细胞对免疫应答的重大作用,一直以来这也是免疫学研究的关注点[6]。然而阻断循环系统的淋巴细胞向局部组织迁移后,Park等人发现结核菌感染肺部时,起保护作用的细胞主要是肺部定居的淋巴细胞[7]。
组织定居淋巴细胞的鉴定有赖于循环系统消融法、联体共生小鼠模型以及一系列细胞追踪与成像技术的发展。其中联体共生实验[8]是确定组织定居淋巴细胞的金标准,该实验通过外科手术将两只小鼠的皮肤缝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微血管,建立了一套共用的交换系统。研究者再诱导联体小鼠其中的一只产生淋巴细胞,发现有些淋巴细胞并不随血液循环迁移到对侧小鼠,同时其他各种细胞进入共用的循环系统后均匀分布在两只小鼠体内[9]。这种组织中的抗原特异性记忆B细胞亚群最早被描述为组织样记忆B细胞(Tissue-like memory B cells),也称为非典型记忆B细胞。2005年Ehrhardt等根据是否表达跨膜免疫调节因子FcRH4,将人类扁桃体中的组织样记忆B细胞分为两个亚群:FcRH4+记忆B细胞和FcRH4-记忆B细胞。FcRH4分子的表达仅限于扁桃体中记忆B细胞的一个亚群,在外周血、骨髓和肌肉中很少被检测到。于是Ehrhardt等对含FcRH4细胞的组织分布进行探索,发现FcRH4+记忆B细胞和FcRH4-记忆B细胞表型特征、组织分布和功能特性均不相同[10]。
2008年Moir等首次[11]在HIV病毒血症患者的外周血中发现了组织样记忆B细胞,这种细胞和以前研究的扁桃体组织记忆B细胞[10,12]相似,均表达FCRL4。此外,正常供体中有一半组织样记忆B细胞表达FCRL5分子。LI等[13]根据是否表达FCRL5分子,区分了异质性组织样记忆B细胞亚群,这些亚群在表面分子、体细胞突变率、基因表达谱和对刺激的反应方面都有显著差异。随后其他研究表明,组织样记忆B细胞可以产生保护性抗体,从而发挥抗疟疾作用[14]。
2019年BRM终于被确切证明。流感攻击C57B/L小鼠后,Allie等利用荧光标记的血凝素(Hemagglutinin,HA)识别小鼠肺部流感特异性B细胞,并且发现这些细胞具有定居记忆细胞的标记物[2]。Allie等借助连体共生小鼠模型证明了肺脏中的BRM不参与血液循环,并用流感病毒二次感染C57B/L小鼠后,发现第一次病原体入侵产生的肺部BRM迅速原位分化,产生特异性抗体有效抵御局部感染,而产生于病毒入侵部位的特异性抗体又与疫苗保护效果直接相关[15]。
2 肺脏和淋巴器官中组织定居B细胞的表型比较
Allie等发现小鼠肺组织产生的BRM与淋巴结/脾脏产生的BRM在CD62L、PD-L2等细胞表面分子的表达上存在差异。小鼠淋巴结和脾脏中约10%的BRM表达血管地址素L-选择素(CD62L),而肺脏中的BRM几乎不表达CD62L[2]。此外,淋巴结和脾脏中部分BRM表达趋化因子受体CXCR3,而在肺脏中BRM高度表达CXCR3,表达率接近100%[16]。这些现象通常是同种型转换记忆B细胞所共有的,可见肺脏和淋巴器官具有十分相似的同型分布,但是依然可以确定肺中的BRM与淋巴组织中的BRM在表型分布上存在不同。
3 外周组织和循环系统中记忆B细胞的表型比较
现有研究表明,BRM和循环记忆B细胞在表达趋化因子和归巢受体方面情况不同。组织定居细胞不表达淋巴结归巢受体CCR7和CD62L,但却表达外周组织的归巢受体CXCR3[17]。其中CD62L表达于造血细胞的分化阶段,包括大多数B细胞和未致敏T细胞等,CD62L对于未致敏淋巴细胞经HEV归巢到外周淋巴结和派氏集合淋巴结起着重要作用[18]。趋化因子受体CCR7是一种G蛋白偶联受体[19],它通过其配体CCL19和CCL21在外周组织和淋巴结中的分子梯度变化,引导淋巴细胞和树突细胞(Dendritic cell,DC)离开组织。BRM表达趋化因子受体CXCR3,CXCR3是趋化因子CXCL9、CXCL10和CXCL11的共配体[20]。IFN-γ诱导产生的CXCL-9/10/11和CXCR3结合后,可使CXCR3+特异性T淋巴细胞向外周组织迁移,这种反应对淋巴细胞驻留组织有重要意义。此外,CD73分子是小鼠淋巴器官中记忆B细胞的重要标记物,它促进了原始B细胞向浆细胞分化并产生抗体,然而肺脏中的BRM多数不表达CD73[16]。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表面分子来标记所有外周组织中的BRM。
4 组织定居T细胞与组织定居B细胞的表型比较
CD69糖蛋白和αEβ7整合素CD103是BRM的关键标志物。 CD69表达于含有TRM的绝大多数外周组织,例如皮肤、呼吸道、肠道、女性生殖道、肺、脑、唾液腺、感觉神经节等,甚至存在于次级淋巴器官。CD69降解了1-磷酸鞘氨酸受体1( Sphingosine-1-phosphate receptor 1,S1PR1),下调S1PR1的表达,S1PR1在血液、淋巴结、外周组织中由高至低,呈现梯度分布,这种梯度可以引导T细胞离开外周组织。CD69与S1PR1结合后阻止了S1PR1活性信号的传导[21],从而使淋巴细胞驻留在外周组织中。BRM高度表达CD69,但是并不表达TRM的标记分子CD103。此外,TRM区别于中央型记忆T细胞(TCM)和效应型记忆T细胞(TEM)的标记分子CCR7和CD62L[22],BRM和TRM都不表达。
5 展望
相比于其它组织定居淋巴细胞的研究进展,BRM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没有明确的标志物对其进行标记。探索多种细胞表面标记分子有利于了解BRM的产生和发育方式,有利于了解其分化为局部抗体分泌细胞的特征。BRM产生于病毒入侵部位的特异性抗体发挥了疫苗保护效果,疫苗可在病原体感染部位产生足够数量的病原体特异性B细胞[23],从而有效地限制病毒传播,这样便可以通过疫苗接种产生BRM,建立起防止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线,但通过疫苗诱导产生的BRM是否可提高对某些病原体的保护效力,以及BRM是否存在于人类体内还需进一步的评估[24]。总之,我们期待深入研究BRM的免疫学特征和功能机制,发挥其抵御感染、免疫调节或组织修复的重大作用,并为疫苗设计及免疫策略优化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