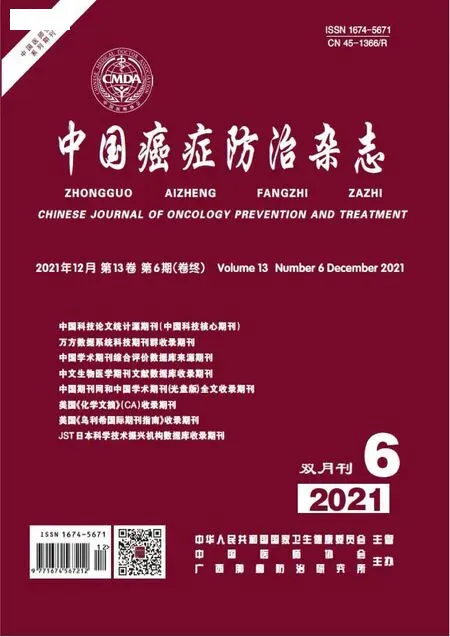从微观到宏观漫谈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的影响因素
杜成 金山琇 谢晓冬
作者单位:110016 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肿瘤科
2018年以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疗法获得诺贝尔奖,自此ICIs治疗在几乎所有癌症治疗中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ICIs的应用显著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然而在非筛选人群中,单药治疗有效率仅为20%左右[1]。因此,如何筛选出免疫治疗获益人群尤为重要。大量研究证实,PD-L1高表达、高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高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high,MSI-H)等都是免疫治疗的预测标志物,但也有相当多的患者未能从ICIs治疗中获益。究其原因,肿瘤自身基因突变、肿瘤微环境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都会对ICIs疗效产生重要影响[2-3]。本文将从上述三个方面总结目前可能对ICIs疗效有预测价值或产生客观影响的因素,以期为临床工作中更精准地筛选ICIs治疗潜在获益人群提供参考。
1 肿瘤基因表达谱
1.1 PD-L1、MSI/MMR 和TMB
大量研究证实,PD-L1、MSI/MMR和TMB是目前ICIs治疗比较好的预测标志物。从分析目前几项高筛选人群单药治疗的研究中能够更客观地评估其预测价值。如2016年RECK等开展的KEYNOTE-024研究对比了帕博利珠单抗与含铂化疗在PD-L1高表达(TPS≥50%)的驱动基因阴性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中的疗效,结果显示两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分别为44.8%和27.8%,允许化疗的情况下两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分别为10.3个月和6.0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分别为30.0个月和14.2个月[3]。在KEYNOTE-177研究中,既往未接受治疗的MSI-H/dMMR结直肠癌患者随机接受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或化疗,结果免疫治疗组的ORR(43.8%vs33.1%)和中位PFS(16.5个月vs8.2个月)均优于化疗组[4]。与之相似,在Ⅱ期CheckMate 142研究中,在经过至少一线治疗的MSI-H/dMMR结直肠癌中,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的ORR达51%[5]。
目前关于TMB对ICIs疗效的预测价值大多为回顾性分析,2020年发表在Lancet Oncology上的KEYNOTE-158研究前瞻性探索了帕博利珠单抗在高TMB(≥10 mut/Mb)既往经治的泛癌种队列中的汇总数据,结果显示,帕博利珠单抗在105例高TMB患者中ORR达29%,而在688例低TMB患者中ORR仅为6%[6]。即使是在高选择的人群中ICIs单药有效率也仅为30%~50%,还有许多研究显示PD-L1(特别是阳性界值降低至1%的患者)和TMB与ICIs疗效并无相关性[1-2,7]。这些数据表明,PD-L1、MSI/MMR 和TMB对ICIs治疗有重要影响。
1.2 DNA损伤修复系统
近年研究发现,DNA损伤修复系统(DNA damage repair,DDR)相关基因突变也会影响ICIs治疗疗效,比较经典的基因包括ATM、BARD1、PALB2、RAD51、ATR、POLD1/POLE等。最近,中山大学徐瑞华教授团队[8]发现,相比野生型人群,存在POLE或POLD1突变的患者使用ICIs治疗后其OS显著延长(34个月vs18个月,P=0.004),但是在POLE/POLD1突变的肿瘤患者中,MSI-H患者与MSS或MSI-L患者的OS差异并不明显,说明无论是PD-L1、TMB、MSI还是DDR相关基因突变,均对ICIs的疗效预测有较高价值。
1.3 驱动基因
肿瘤驱动基因是抗肿瘤靶向药物的主要靶点,近年研究显示驱动基因突变会对ICIs治疗产生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是负相关因子,有些驱动基因突变还预示免疫治疗超进展。在NSCLC中,驱动基因突变谱是靶向治疗和/或ICIs治疗疗效的关键预测因子。其中EGFR突变和ALK融合这两种突变提示肺癌患者ICIs疗效欠佳;在NSCLC患者中,ROS1融合阳性患者也对ICIs反应不佳,但由于该突变较罕见,因此缺乏更系统的评估[9]。既往有研究报道MET突变的肿瘤可能与高PD-L1表达相关,尤其是在具有肉瘤样特征的癌种中[10],而ERBB2突变和RET融合阳性患者对ICIs治疗的反应率与未经基因选择的人群相似,但是也有例外。此外,对于许多癌基因依赖性肿瘤来说,针对性的靶向治疗有效率远远超过免疫治疗,尤其是在一线治疗中[11]。因此,若条件允许应在决定系统治疗方案时检测潜在的驱动基因突变,并以靶向治疗为主导。
在驱动基因突变阳性NSCLC中,KRAS突变与ICIs治疗的高应答率相关[9,12],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当存在其他基因共突变时,KRAS突变对ICIs治疗反应的应答效果不一样[13]。如STK11(编码LKB1)和KEAP1作为改变肺癌免疫环境或代谢状态的常见突变,当两者共突变时可能是不良的预后因素,能特异性地预测KRAS突变肿瘤对ICIs治疗疗效欠佳。也有研究在肺癌的基因工程小鼠模型(GEMM)研究中发现,STK11/LKB1缺失会导致中性粒细胞浸润,同时伴随T细胞耗竭增加,而LKB1突变可能直接导致GEMM中的TMB增加,且这种突变率增加的原因可能是KRAS/LKB1突变细胞中Rad51招募失败而导致双链断裂所激发的同源重组修复功能产生缺陷[14]。同时,免疫细胞中参与抗原呈递的成员分子存在mRNA表达缺陷,因此通过MHC-1途径进行的抗原呈递明显减弱[15],这也可能是TMB较高但免疫反应减弱的原因。一项关于PD-1抑制剂单药治疗的队列回顾性分析中,与KRAS突变/STK11野生型肿瘤相比,KRAS和STK11共突变的肿瘤显示了较短的PFS和OS[16]。
HER2基因突变/扩增似乎对ICIs治疗无负向影响,相反在联合抗HER2靶向治疗、化疗与ICIs治疗研究中证实两者具有一定协同增效作用[17]。临床前研究证实,抗HER2与ICIs协同增效的机制可能与阻断HER2能上调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PD-L1表达有关。最近报道的KEYNOTE-811研究[18]显示,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化疗可以将HER2阳性的晚期胃癌ORR从51.9%提升至74.4%。基于该研究结果,2021年5月美国FDA加速批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化疗用于HER2阳性晚期胃癌的一线治疗,帕博利珠单抗也成为目前全球首个用于一线治疗该类胃癌患者的PD-L1抑制剂。以上研究结果提示,某些驱动基因活化或许并非ICIs治疗的禁区,在同步阻断这些信号通路后再联合ICIs治疗可能是非常有前景的治疗策略。除上述基因外,MDM2、MDM4、EGFR、FGFR等基因扩增,以及PTEN、P53等抑癌基因突变也显示出了与ICIs治疗疗效的相关性[1-2],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2 肿瘤微环境
肿瘤微环境既是肿瘤细胞赖以生存的“温床”,也是免疫疗法抗击肿瘤的主要“战场”。肿瘤微环境主要由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细胞外基质、炎症因子、代谢产物、特殊理化特征(如低氧气、低pH)和肿瘤细胞自身组成。肿瘤微环境的“大家庭”构成非常复杂,而且几乎每一大类成员又分为“促癌”和“抑癌”两种表型,在特定条件下肿瘤细胞可以诱导微环境向免疫抑制状态方向转化[19]。
2.1 免疫细胞
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是影响ICIs疗效的关键因素。发挥抑癌功能的免疫细胞主要包括CD8+细胞毒T细胞、CD4+效应T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M1型极化巨噬细胞、N1型极化中性粒细胞等[19]。发挥促癌功能的免疫细胞包括调节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s)和骨髓来源的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其中,以Foxp3+Tregs为代表的调节T细胞可以抑制效应T细胞活性,MDSCs则可以分泌VEGF、IL-10、TGF-β等因子,诱导新生血管、抑制T细胞功能。研究显示B细胞具有促癌和抑癌双向功能,其在肿瘤微环境中发挥的作用目前尚存争议[20]。总之,上述细胞的分化方向主要由肿瘤细胞及微环境中的各种细胞因子和代谢产物决定,当然即使微环境中存在正向抑癌的免疫细胞,也有可能因为肿瘤细胞高表达PD-L1等免疫检查点配体而诱导T细胞耗竭状态,进而实现免疫逃逸。此外,除了PD-1/PD-L1和CTLA-4这两类免疫检查点外,TIM-3、LAG-3、TIGIT和CD96等也发挥类似功能,有可能成为新的ICIs治疗靶标[20]。
2.2 代谢产物的微环境
近年研究发现,肿瘤代谢对免疫微环境有重要影响。人体微环境中的葡萄糖、谷氨酰胺和精氨酸耗竭,乳酸和犬尿氨酸大量堆积,脂质代谢水平升高,缺氧和低pH值等均会诱导抗肿瘤免疫抑制状态。这种抑制状态可表现为效应T细胞凋亡或耗竭、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向MDSCs分化、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向M2极化、DC细胞抗原提呈能力降低、Tregs细胞增多等[21]。基于这些机制,很多学者提出靶向肿瘤代谢进而实现微环境重构。但是,由于微环境成分复杂,特别是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共存,难以选择性阻断一方,因此许多调控代谢策略也变成一把双刃剑。如采用糖酵解酶抑制剂或葡萄糖竞争性类似物2-DG抑制糖酵解途径能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但同时也会抑制免疫细胞的抗肿瘤活性[22]。同样,抑制乳酸脱氢酶活性虽然能降低乳酸水平从而抑制肿瘤生长,但也会导致T细胞和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减少。也有学者提出替代策略,即抑制乳酸转运体MCT1/4,这既不影响免疫细胞活性,又可以显著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此外,由于免疫细胞对氨基酸和脂质代谢的依赖性与肿瘤细胞存在差异,因此靶向氨基酸和脂质代谢似乎更有望在实现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同时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总之,靶向细胞代谢、调控免疫微环境进而实现抗肿瘤治疗是有前景的策略,但要真正实现临床转化依然任重道远[23]。
2.3 肿瘤转移部位的微环境
肿瘤微环境对ICIs治疗影响的最典型外在体现是脑转移瘤和肝转移瘤ICIs疗效普遍不佳。其中脑转移瘤的ICIs治疗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血脑屏障的存在导致大分子药物难以达到靶病灶;第二是脑组织中免疫细胞较其他组织少。因此,与其他部位转移不同,脑转移瘤的ICIs治疗效果欠佳,因此绝大多数ICIs临床研究将脑转移瘤作为排除标准。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小样本研究和个案报道ICIs联合传统治疗在脑转移瘤治疗中取得一定疗效。KEYNOTE-189、KEYNOTE-021和KEYNOTE-407研究的汇总分析显示,PD-1单抗联合化疗较单纯化疗能显著延长NSCLC脑转移患者的OS和PFS[24]。因此,ICIs联合放化疗或靶向治疗有可能为脑转移瘤患者带来新希望,尽管目前仍缺乏更高级别的证据,但是仍可以把ICIs作为脑转移患者的治疗选择。
肝转移瘤的微环境也非常复杂,一方面,肝脏中具有占机体80%~90%的巨噬细胞(也称枯否细胞),这类细胞会导致NK细胞抑制,诱导Tregs活化;另一方面,肝脏中还存在大量骨髓细胞分化而来的MDSCs。因此,肝转移瘤患者接受ICIs治疗时疗效往往较其他部位转移患者差。但在KEYNOTE-189研究中,无论NSCLC患者是否存在肝转移,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均较单纯化疗能带来更好的生存获益[25]。说明免疫治疗在联合常规治疗后有可能改变免疫微环境状态,从而更好地发挥功效,这在IMpower150研究中也得到验证[26]。
综上可见,肿瘤微环境对ICIs治疗效果有重要影响,而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代谢产物、炎症因子等有可能作为预测因子和干预靶标,有助于实现更精准的免疫治疗。但是由于肿瘤微环境成分非常复杂,而且随着肿瘤发展和治疗演进会不断发生变化,因此难以选定某一特定标志物或靶点进行干预。但是近年来,得益于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高通量多重荧光标记以及生物信息学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肿瘤微环境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因此未来有望实现上述目标[27-28]。此外值得肯定的是,常规放疗、介入治疗、化疗、抗血管靶向治疗等治疗原理就是对免疫微环境的调控,因此与ICIs联合应用具有潜在协同增效作用。最近有研究在动物模型中发现低剂量放疗虽然不影响肿瘤生长,但能促进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浸润,诱导肿瘤细胞DNA损伤,进而增强免疫治疗效果[29]。目前,该团队已经开启Ⅰ期临床研究,拟对表现为“冷”肿瘤的患者进行低剂量放疗、低剂量环磷酰胺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结果值得期待。
3 患者自身因素
除了上述的肿瘤细胞自身基因突变和肿瘤微环境因素外,患者整体的临床特征也会对ICIs疗效产生影响[30],因此在筛选获益人群时应给予关注。
3.1 年龄
年龄是影响免疫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KUGEL等[31]在黑色素瘤小鼠模型中发现年轻小鼠在对抗PD-1治疗的耐药性更强,这与临床患者的研究数据一致。该研究还发现老年小鼠对抗PD-1治疗的应答更明显,而通过CD25减少年轻小鼠的Tregs数量则出现明显的应答,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与调节性T细胞中的Foxb3蛋白阳性率有关;此外研究者还通过统计538例黑色素瘤患者的免疫治疗情况,也得出了与上述小鼠实验相似的结果,而且每隔10岁耐药概率降低13%[31]。但在NSCLC等研究中却发现肿瘤免疫治疗的获益幅度与年龄无关[32-33]。此外,以60岁分组的KEYNOTE-040和KEYNOTE-042研究[34-35]也显示年龄不会影响相应的肿瘤免疫治疗效果。因此,目前虽然老年患者在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疗中取得令人鼓舞的数据[31],但临床医师仍需要考虑老年患者群体中免疫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合理应用免疫治疗,此外年龄对其他肿瘤免疫检查点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探索。
3.2 性别
性别对ICIs疗效的影响目前尚无定论,既往报道存在一定争议。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女性相比,男性的ICIs治疗有效率更高,而这种性别上的差异是由基因、激素、环境以及共生微生物共同影响所致[36]。但是,另一项Meta分析发现免疫治疗疗效与性别关系并不大[37]。叶幼琼等[38]发现不同癌症类型的免疫特征存在性别差异,如黑色素瘤中男性偏向具有高水平的免疫反应相关特征,而NSCLC中女性偏向具有高水平的免疫反应相关特征。总之,ICIs治疗中显示的性别特异性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3.3 体力状态评分
目前有研究认为ECOG-PS评分可能对ICIs疗效产生影响,但也有研究指出,ECOG-PS评分作为肿瘤的预后因素,其在预测ICIs疗效中的价值有待证实。在一项针对意大利非鳞状NSCLC患者的扩大访问计划(EAP)多因素分析中发现,ECOG-PS评分(1vs0和2vs0)是 OS的独立预后因素[39-40]。CheckMate 153研究分析了ECOG-PS=2的癌症患者与总人群(ECOG-PS=0,1,2的患者),其ECDG-PS=2的患者中位OS比总人群的中位OS少了4.1个月[41],可以看出ECOG-PS评分好的患者OS往往更长。但是,KEYNOTE-052研究[42]在利用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尿路上皮癌中发现,体力较差(ECOG-PS=2)的患者采用ICIs治疗仍然显示了明显的抗肿瘤活性,且单用帕博利珠单抗的中位OS优于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方案(11.3个月vs9.3个月)。由此可以看出,在ICIs治疗中,ECOG评分不适用于指导用药,但对预后具有指导意义。
3.4 吸烟史
吸烟是最主要的致癌因素,在所有癌症引发的死亡中吸烟者占总数的30%以上,其中肺癌死亡患者中吸烟者高达80%[43]。但是有研究发现接受免疫治疗和化疗的高TMB吸烟患者,PFS也较长[44]。一项关于接受抗PD-L1单药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也发现,抗PD-L1单药治疗的应答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吸烟者(36%)、既往吸烟者(26%)、从不吸烟者(4%)。还有研究报道,在PD-L1高表达(≥50%)的患者中,与从不吸烟的患者相比,目前和曾经吸烟患者的缓解率更高[45]。由此可见,吸烟的肺癌患者抗PD-1治疗效果更好,而这可能与吸烟引起的高突变负荷有关,且吸烟可使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对PD-1/PD-L1阻断物敏感,从而增强免疫治疗反应[46]。但值得注意的是,吸烟的肺癌患者抗PD-1治疗效果虽然更好,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吸烟可以增强疗效,更多的是提示可能这一群体更具针对性,此外吸烟会增加罹患肺癌风险,而且对于大多数癌症患者而言,吸烟者更容易复发,治疗后也更容易出现并发症,因此仍需减少吸烟或者戒烟。而吸烟状态能否用于预测化疗联合ICIs治疗的疗效也仍需进一步研究。
3.5 外周血细胞及生化指标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升高可反映其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功能较低,从而使患者预后不良。CAPONE等[47]关于NLR在晚期黑色素瘤的研究显示,绝对中性粒细胞计数(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ANC)、NLR和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升高均与OS显著相关,但在多因素分析中仅NLR与OS保持显著相关,提示NLR可用于晚期黑色素瘤患者对免疫治疗的预后预测。在不受其他预后因素影响的转移性NSCLC患者中,纳武利尤单抗治疗前NLR升高与较差的OS(HR=3.64,P<0.001)和较低的缓解率(HR=0.17,P=0.013)相关[48]。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PLR)对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与NLR相似。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晚期NSCLC患者用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后4周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LMR)增加超过10%与更好的治疗效果相关[49],但这一结论仍需进一步开展前瞻性研究验证。MEZQUITA等[50]基于305例接受ICIs治疗,特别是PD-1/PD-L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生成了肺免疫预后指数(lung immune prognostic index,LIPI));LIPI的综合得分是基于[绝对中性粒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绝对中性粒细胞计数)]和LDH水平计算,且根据dNLR>3,LDH水平高于正常值上限,将LIPI分成3个危险组,即良好、中等和差。该研究还发现,LIPI与305例接受ICIs单药治疗的队列患者预后有关,但与162例接受细胞毒性化疗的队列患者的预后无关。此外,除了常见的NLR、PLR、LMR等比值外,C-反应蛋白、IL-6、LDH、凝血指标(D-二聚体)等也与ICIs疗效相关,但具体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和验证[51-53]。
3.6 肠道菌群与膳食
近年来,多项研究提出肠道菌群微环境可影响癌症患者的ICIs治疗疗效。SIVAN等[54]发现通过喂养双歧杆菌促进不含有利微生物菌群小鼠体内的树突状细胞成熟,增加CD8+T细胞活性,可使小鼠重新获得抗PD-L1功效。VÉTIZOU等[55]研究发现,在SPF和无菌条件下,阻断CTLA-4的免疫治疗只能控制SPF条件下培养的小鼠肿瘤大小,但在肠道无菌的小鼠肿瘤中无法发挥免疫作用。还有研究发现,除了提高免疫细胞活性外,肠道菌群产生的代谢物肌苷也能有效激活抗肿瘤T细胞而杀伤肿瘤[56]。GOPALAKRISHNAN等[57]在经过抗PD-1治疗的黑色素瘤患者中发现富含高丰度费氏菌的患者具有更高丰度的免疫细胞和抗原呈递加工标志物,PFS也更长。最近一项关于免疫细胞动力学和肠道微生物的研究表明,24例接受中性粒细胞移植后接受自体粪便菌群移植的癌症患者较未接受菌群移植患者外周血中每种白细胞类型的计数更高[58]。BARUCH等[59]开展的Ⅰ期临床试验中,10例抗PD-1难治性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先清除肠道微生物,然后接受抗PD-1治疗,且至少获得1年完全缓解的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粪便菌群移植,结果发现3例患者肿瘤缩小,其中1例患者治疗前对ICIs治疗无应答但治疗后获得完全缓解,其余2例分别在119 d和204 d后出现免疫应答,但最终也出现疾病进展;且3例应答患者在免疫治疗浸润和免疫相关基因表达方面都出现有利变化。
肠道菌群对ICIs治疗疗效的另一个影响是缓解治疗不良反应。通常ICIs治疗可能会诱发腹泻、心肌炎、免疫相关肺炎、结肠炎等自身免疫反应。有研究报道,常见的益生菌双歧杆菌能增加肠道调节T细胞IL-10Ra和IL-10表达,或者优化共生菌群组成,从而增强免疫抑制作用[60],缓解阻断CTLA-4导致的肠道不良反应。目前经临床实证研究、国际文献发表并获得专利认证的有益菌株有[61-62]: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A2)、加氏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 gasseri A5)、约氏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 johnsonii A9)、长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longum BR022)、副干酪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 paracasei BRAP01)、唾液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 salivarius A6)、洛德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 reuteri BR101)。综上认为,患者肠道菌群种类和数量也应该成为ICIs治疗重要的考量因素,这有利于制定个性化干预措施、提高疗效并降低ICIs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3.7 体重与身体成分
体重及身体成分对肿瘤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影响,但与ICIs治疗的相关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大多以黑色素瘤和NSCLC为主。CORTELLINI等[63]在接受ICIs治疗的晚期癌症患者中发现超重或肥胖患者(BMI≥25 kg/m2)的中位PFS和OS均较体重正常患者(BMI<25 kg/m2)显著延长。另一项有关晚期黑色素瘤患者BMI与预后的研究发现,与正常BMI相比,肥胖(BMI≥30 kg/m2)与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生存率提高相关,接受ICIs治疗的肥胖男性患者中位PFS和OS也显著改善[64]。另一项观察晚期NSCLC患者阿替利珠单抗治疗疗效与BMI关系的回顾性研究发现,高BMI患者的疗效更好,死亡风险也显著降低;其中超重组和肥胖组患者的OS较体重正常组延长,PD-L1表达阳性的高BMI患者也有更好的获益[65]。但在肾癌研究中却发现肥胖使基于ICIs疗法的疗效降低[66]。考虑以上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可能与肿瘤类型不同有关。此外,当判定BMI能否作为ICIs治疗疗效及预后预测指标时,还需分析患者的肌肉状况或动态监测BMI变化等。有研究分析了ICIs治疗前后患者的身体成分变化,结果显示骨骼肌指数、总脂肪组织指数、肌肉质量及密度均较治疗前增加[67]。此外,肌肉质量也会影响ICIs的抗肿瘤疗效,其中肌肉减少症与NSCLC的ICIs治疗疗效较差有关,伴肌肉减少症的患者中位PFS和OS明显缩短[68-69]。一项荟萃分析也显示,在ICIs治疗前患有肌肉减少症的患者预后较非肌肉减少症患者差,且肌肉减少症是ICIs疗效不良的影响因素[70]。另一项研究在肌肉减少症的基础上联合炎症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同时具有肌肉减少症及高炎症指数的患者中位PFS、OS显著缩短[71]。因此认为,在进行ICIs治疗时应关注患者的营养状态并适时调整,这有利于改善预后。
3.8 合并使用激素或抗生素
关于激素对ICIs的影响目前存在不同观点。如有研究表明,在接受PD-1/PD-L1单抗治疗的NSCLC患者中,治疗开始时使用≥10 mg剂量强的松的患者疗效较<10 mg剂量患者降低,中位PFS及OS显著缩短[72]。一项小样本研究同样证实在接受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的NSCLC患者中,每天使用>10 mg剂量泼尼松使患者临床获益减少[73]。而关于激素剂量,ARBOUR等[72]研究显示,对于使用PD-1/PD-L1单抗治疗的患者,基线时激素用药剂量越高,疗效下降也可能更明显。但是RICCIUTI等[74]研究认为,接受激素治疗患者的预后较差并不一定是由激素对ICIs疗效的抑制作用造成,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肿瘤患者自身合并其他预后不良因素。该研究进一步根据激素使用原因,将患者分为癌症相关症状治疗组和非癌症相关激素使用组,结果显示:在ICIs治疗开始时接受≥10 mg泼尼松治疗的NSCLC患者比接受0~10 mg泼尼松治疗的患者预后更差,这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但进一步对激素组患者进行亚组分析,发现癌症相关症状治疗组较无激素治疗组的中位PFS及OS显著缩短,但非癌症相关激素使用组对比无激素治疗组中位PFS及OS则无显著差异,多因素分析结果也显示非癌症相关激素使用患者应用激素并未显著降低ICIs疗效。说明接受基线激素治疗的患者自身合并其他更多预后不良因素会导致较差的预后,若激素使用适应证为非癌症相关,则不影响ICIs的疗效获益。此外,当在联合化疗前的预处理时使用激素,激素对各类PD-1/PD-L1单抗疗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如在NSCLC患者中,各类PD-1/PD-L1单抗治疗联合化疗的疗效均未受明显影响[75]。KEYNOTE-407研究[76]也证实紫杉醇应用激素预处理与不应用激素预处理的ORR无明显差异。总之,在ICIs治疗期间若需要应用激素,应避免过大剂量,需根据患者病情谨慎评估,但对于非癌症相关疾病不应停用激素治疗。
目前大多研究认为PD-1/PD-L1单抗治疗期间应用抗生素会给疗效带来负面影响。PINATO等[77]研究显示,ICIs治疗前30 d内应用抗生素会对患者的反应率和生存率造成不利影响。TINSLEY等[78]研究显示接受抗生素治疗的ICIs治疗患者的中位PFS和OS降低,其他研究[79]结果也体现出一致性。但是,也有研究[80]表明,使用窄谱抗生素不影响ICIs治疗疗效,而广谱抗生素则会降低ICIs治疗反应率。一项荟萃分析[81]显示,在PD-1/PD-L1单抗治疗期间使用抗生素的患者较未使用抗生素患者的疾病进展风险、死亡风险增加,且OS缩短;亚组分析显示,当抗生素与PD-1/PD-L1单抗的治疗间隔在90 d以上,抗生素对疗效没有显著影响,而间隔90 d之内的患者ICIs治疗疗效则下降。总体而言,多数研究显示抗生素对ICIs治疗反应及生存有负面影响,因此在接受ICIs治疗的癌症患者中应谨慎使用抗生素。
4 小结与展望
从宏观到微观,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对ICIs治疗疗效产生影响,此外还有许多影响因素未被发现,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探索。总之,ICIs治疗疗效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需要关注微观基因、分子层面的表达差异,也要注重患者宏观状态,且未来如何结合诸多因素建立便于应用的预测模型,仍需广大同仁不懈努力探索。